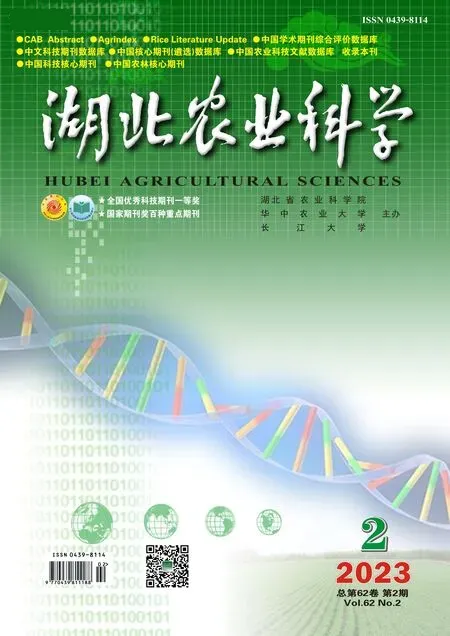村莊共同體的重塑與環境保護實踐
——基于川西藏族村寨神座村的社會學觀察
段 雨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1100)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1],要實現鄉村振興中的“生態宜居”,必須毫不動搖地將環境保護放在突出位置。然而市場經濟的入侵加速了村莊共同體的終結,產生一大批只愿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只追求個人利益而不注重集體利益“無底線的個人”[2]“無公德的個人”[3],這給地方生態文明建設造成巨大阻礙。重構村莊共同體作為環境保護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為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平衡提供了契機,改變了農村經濟落后與環境污染之間的惡性循環。針對如何重塑村莊共同體,有學者提到通過重構村落道德體系的方式建構村民普遍認同的價值形態,從而形成村民精神共同體[4];以國家權力力量作為中介,建設以村委會為中心的農村日常生活秩序,同時不斷彌合城鄉二元體制下城市與農村的巨大鴻溝[5],增進村組成員對共同體的認同感。已有研究認識到了村莊共同體的極端重要性,卻忽視了村莊共同體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在對神座村的調研過程中,發現村莊共同體的形成對地方環境保護實踐有顯著正向作用。鑒于此,本研究以神座村為例,重點關注村莊共同體重構邏輯及其對地方環境保護實踐產生影響的內在機制,探析共同體塑造與環境保護聯結的背后機理,試圖找出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平衡的普適性途徑。
1 危機:市場經濟的侵入與鄉村共同體的裂變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中指出,一旦完全依賴于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它便會從政治、宗教及社會關系中脫離出來,進而將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完全商品化,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毀滅[6]。市場經濟改革后,人們的思維方式從生存理性過渡到經濟理性,利益成為普遍的價值追求,神座村也不例外。村民們無止境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給改革時代下的村莊共同體帶來了猛烈沖擊,對其能否繼續維持形成了巨大威脅。村民行為的高度市場化導致村莊共同體產生裂變,逐利過程中村民們甚至產生了破壞公共資源的“攀比”心態,出現了“公地悲劇”,集體價值觀的消解給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以神座村為例,探究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如何沖擊鄉村共同體進而破壞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
1.1 集體經濟時期神座村的自然環境
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神座村的自然環境相當好,“以流經村子的河流為界限,一邊是廣袤無垠的高山草場,一邊是茂密蔥郁的原始森林……草原中蘊藏著諸多珍貴藥材,森林中活動著諸多野生動物”。集體主義時期的神座村村民能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主要得益于以下幾方面因素。
首先,相較于改革開放時期,神座村總人口在集體化時期比較少。村民們小農意識形態濃厚,保持著知足常樂、安逸自足的生活態度,只求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在開發自然資源時基本不會出現過度索取的現象。當人口增長維持在一定限度時,人類發展與資源開發保護便達到了某種均衡,這種均衡推進了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相處,維持著村莊的存續,村莊也因此成為適宜人類生存發展的天然場域。其次,公共精神與集體意識對村民的思想及行為有重要的約束作用,受傳統地方性知識及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當地民眾構建起精神層面上的意識形態共同體。因而,村民對環境保護知識具有良好的認知,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中也很注重保護環境。再次,市場經濟改革以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國家對私人財產管控非常嚴格,村民們缺少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農業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磨洋工”及勞動力投入“過密化”的現象。在這一背景下,村民公共生活急劇膨脹,而私人生活空間受到了極大壓縮,以勞動工分作為標尺衡量村民勞動及分配生活資料、勞動生產成果全部歸公,村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因而大大降低。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個人欲望的萎縮抑制了人們發掘公共資源的動力,間接起到了維護生態環境的作用。最后,以畜牧業為主的農業產業結構相較于發展大工業對環境的破壞程度更低。卡爾·波蘭尼認為進入市場化的經濟體系后,勞動力及自然資源皆成為純粹的商品,作為“異化”的勞動力與資源服務于大工業的生產,從而造成人與自然的毀滅,神座村原始的產業結構反而緩和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1.2 市場經濟改革與環境危機的產生
根據調查來看,神座村的自然環境在市場經濟改革后受到了嚴重破壞,市場經濟主要通過刺激人口增長及撕裂鄉村共同體兩條路徑對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產生深刻影響。
第一,改革開放以后,神座村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集體化時期,村子里本來人口比較少,大概只有30 來戶……改革開放以后,就有50 多戶人口了,人口增長了快接近50%”。為滿足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村民們不得不喂養更多數量的牦牛、種植更廣面積的青稞,通過對自然資源進一步發掘的方式,村民得以獲取所需求的生存資料,維持了生命的存續。然而,過度開發自然的行為及當地粗放型的農業生產模式使原本就極其脆弱的生態系統更加惡劣,導致山體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頻發,反而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市場經濟的入侵帶來當地人口的激增,為保證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人們把目光投向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卻忽視了開發不當導致的嚴重自然災害,進而阻礙了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不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現實,孤立地看待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問題,致使當地村民落入了“越貧窮越開發,越開發越貧窮”的惡性循環之中。
第二,市場經濟改革不僅推動國家向更多元化、更開放的發展模式轉變,同時帶來了多元文化價值觀念,由此形成的思潮與村莊原有傳統觀念相互交織碰撞,對其提出了巨大挑戰,新思潮不斷改變著村民的認知、重塑村民思維模式。在充滿各種各樣新矛盾的轉型時期,村莊共同體最終無法抵御市場經濟的沖擊,產生了裂變。首先,市場經濟體制改變了村民們“明哲適度”的意識,塑造出一大批“理性個人”,他們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不斷擺脫道德框架的約束,而村民們的趨利行為本身就給當地生態環境增添了諸多負面影響。“那時候50 多戶人家,幾乎家家都養牦牛啊……這對草原環境破壞相當嚴重,所以那個時期諸如山體滑坡、泥石流之類的自然災害特別嚴重”。其次,市場經濟的發展深刻改變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它將個體從集體中“剝離”出來,從而推動了個體的崛起,使獨立的個體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這意味著傳統文化及道德規制的約束力被大大削弱,個體逐利的主動性得到進一步釋放,對他人及群體的義務與責任感知變得更加微弱,在破壞環境的逐利行為中便更加無所顧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個體是“畸形的個體”。一方面,他們極力追求自由,反對國家以任何形式對私人領域進行干預,但同時卻不得不依賴國家制度來應對與日俱增的市場風險。在與集體脫嵌的過程中,他們僅僅是馬克思筆下的“一口袋馬鈴薯”,是毫無聯系的個別單位的排列。另一方面,他們只尋求獨立自由的個體權利,卻忽視了肩負的責任與義務,不均衡的個體性發展推動了公共生活的衰落[7],進而改變了地方資源開發利用的具體形式。最后,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與城市化的推進緊密結合在一起,伴隨城鎮化腳步的加快,大量村莊開始消逝。村與村之間的邊界不復存在,實體意義上村莊的消亡預示著鄉村共同體的終結。
總而言之,市場經濟改革以前的神座村因為合理的人口數量、傳統文化與道德規制對村莊日常生活秩序的維護、國家對私人生活的大力干預以及發展適度規模的綠色農業,生態環境得到了良好保護,真正實現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個體化發展成一種強勁的社會潮流,以及經濟理性群體的出現,村莊共同體原有的集體意識受到巨大沖擊。伴隨人們對舊意識形態的逐漸舍棄,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新穎社會思潮開始支配著人們,鄉村精神共同體的“大廈”崩塌。與此同時,城市化的“巨輪”仍在持續推進,不斷吞噬著廣大鄉村地區,對鄉村共同體提出了巨大挑戰,村莊共同體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
2 重塑:村莊共同體的再造與地方環境保護實踐
從空間場域角度出發,快速城市化不斷吞噬著村莊的邊界,鄉村實體未來能否繼續存在成為未知數。從精神層面看,市場經濟的急速深入形塑著村民的思維方式,鄉村精神共同體也出現了裂痕。上述兩個視角揭示的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在于:在社會劇烈變動的新時代,鄉村共同體繼續維持并發揮作用的可能性何在,如何幫助村民擺脫個體化困境,重新建構鄉村精神共同體成為村莊共同體再造所要面臨的核心議題。在神座村,政府極力構建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新型村莊共同體,村民們則通過對地方性傳統文化知識的運用及舉辦一系列鄉村集會主動參與鄉村共同體的重建,環保實踐再次呈現積極取向,村莊共同體的建構與地方環境保護重新實現了結合。
2.1 政府主導背景下村莊共同體的再造
鄉村共同體是個體化時代下村民抵御與日俱增的市場風險的重要保障,是村民心理穩定感及安全感的重要來源,它為村民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準則,維持著村莊秩序的正常運行。因此,重建鄉村共同體事關村莊的生存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神座村,政府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及重塑鄉村文化兩種方式積極參與村莊共同體的再造過程。
第一,大力推動綠色旅游業的發展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市場經濟是造成衰落村莊共同體的重要原因,它追求絕對理性,推動村莊人口遷往經濟發達的城市地區,因而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成為建構鄉村共同體的重要舉措。神座村走上發展旅游的道路與地方能人大張密切相關,大張從副縣長的位置上退休后就回到了神座村,他在擔任公職期間獲得了村民們的廣泛認可,一方面,大張積極動員村民改建民房、鋪筑通往外界的道路,盡最大努力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和條件,以提升發展旅游業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積累起來的人脈資源,為神座村拉來大量政府及社會投資,這些資金在神座村旅游業發展初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在能人效應的帶動下,政府決定在神座村大力發展旅游業,開始投入大量資金。對村書記的訪談了解到,僅在2017年政府便投入4 000 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提升村莊路面情況,并相繼鋪設電纜、光纜及飲水管道,解決了村民用電用網用水的難題,政府從此主導了神座村綠色旅游產業的發展。此外,政府在神座村積極推進牧民定居計劃,修建大量牧民定居點以滿足牧民們的住房需求,保證了發展旅游業所需要的最低人口要求。同時,建造了一批垃圾處理點、落實了“洗澡房”入戶的項目,極大完善了公共服務設施,提升了村民生活質量,增進了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在政府的扶持及地方能人的推動下,神座村的旅游業實現了良好發展,高度依賴自然環境發展旅游業的神座村,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還需要注重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而旅游業本身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時,也增強了村民保護自然生態資源的能力和信心,神座村因而得以維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者的均衡,綠色旅游業的命運與環境保護的實踐緊密相聯,實現了良性循環。更關鍵地是,政府在神座村旅游業的發展過程中,始終強調村民的主體地位,把村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通過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的實踐一步步重塑著村民的思維模式,在村民間構筑起新的精神共同體。市場經濟條件下,混亂無序的逐利行為給當地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對自然資源的惡意開發加劇了村民的貧困程度,而政府主導發展的旅游業,按照“保護環境-發展旅游-進一步保護環境”的實踐邏輯,成功幫助當地村民脫貧致富。因而,村民的思維方式再一次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公共精神與合作精神得到接納,新的集體意識在廣泛的村民群體中得以重構。
第二,建設和宣傳地方性傳統文化知識,進一步推動鄉村精神共同體的形成。一方面,改變對農村的工具性態度,控制市場經濟入侵村莊的程度,將建設生態宜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鄉村社會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使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再造鄉村文化及道德體系,使之重新發揮約束村民行為的效用。活佛在鄉村文化及道德體系重建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與活佛積極合作的方式,向村民們宣傳環境保護相關知識。訪談過程中,一位村民透漏,“我們都聽活佛的,活佛說的話我們都信,除了要求我們撿垃圾,活佛還會向我們宣傳一些其他思想,如牛不要偷、酒不要喝、煙不要抽、要積極配合國家干部的工作等”。利用佛教文化在當地巨大的影響力,當地政府不僅在實踐層面上避免了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村民之間的惡性競爭,促進村民保護環境的行為自覺,從精神層面來看,這同時推動了環境保護這一意識形態在村民心中達成集體認同。
2.2 傳統性地方文化知識與精神實體的建構
地方性知識往往是某個區域內獨享的知識文化系統,有著豐富的意涵,某些地方性知識詳細講述了村莊的起源與發展,以此加強村民對村莊實體的認同。據村民介紹,神座村是由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山神帶來的。她為了躲避戰火,帶領著她的部落臣民從遙遠的天邊草原上趕著牛羊、馱著帳篷來到了神座,發現這里山清水秀、氣候溫和,于是帶領大家在這里住了下來。從此,神座部落就在女首領的帶領下不斷發展壯大。通過對村莊起源的追溯,村民們不斷強化“神座人”的身份認知,對一定范圍內的村莊實體的認同感也持續提升。與此同時,村民們還會通過對某些苦難記憶的集體回憶,進一步提升自身的身份感知。以神座村為例,神座村在許多年前出現了男女比例失調的危機,為了寨子的永續發展,當時的寨首請來了活佛打卦,求取拯救寨子的良策。后來,在女神山的對面立下了男山神,且村民們天天祭拜,沒過兩三年村莊就陸續有男童出生。神座村男女比例逐漸平等,再次興旺發達。對村莊在某個時期重大危機的集體回憶,可以強化村民的危機意識,通過“共情”的方式來增進彼此之間的團結,進而提升村民對共同體與集體意識的認同感。
地方性知識還蘊藏著豐富的生態文化知識[8],在神座村,類似于神山圣水的地方性知識廣泛存在于村民腦海中,它們不僅深刻影響著村民們的日常實踐活動,還逐漸發展成為普遍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村民的環境保護實踐。神座人民信奉萬物有靈論,認為萬事萬物都有靈性,與人一樣是生命體,擁有特殊的意志和能力。賦予自然事物這樣一層特殊含義之后,村民對自然事物便產生崇拜,這個過程往往包含著一系列禁忌,而這些禁忌與神鬼觀念緊密相聯。它們對村民行為具有比較強的約束力,強迫村民在實踐活動中自覺保護生態環境。正如村中一位老人所解釋的那樣,“樹木是神仙的化身,村民砍樹的行為是禁止的,河水也是神仙的化身,村民一切污染河水的行為也是禁止的……然而,迷信神鬼并不是真正的目的,通過這種方式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才是神鬼觀念的目的,迷信本身只是一種手段”。傳統地方性知識的運用對村民價值觀念的再塑造,有利于在村民群體內部形成普遍認同的集體共識,推動鄉村精神共同體的形成。
此外,藏傳佛教文化在當地村民中有深遠影響,廣泛地域上的村民對佛教文化的高度認同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共同體,在此基礎上,佛教文化中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對村民環保實踐有顯著正向作用。以神座村傳統喪葬習俗為例,受佛教文化影響,當地村民認為人在去世之后回歸自然是一種最好的狀態,所以追求去世之后回歸自然,正所謂“從自然中出生,在自然中死去”。因此,神座村村民去世之后多采用天葬形式處理遺體,或采取水葬、樹葬或火葬等形式。與廣泛流行的土葬相比,神座村的喪葬習俗對環境的破壞更小,事實上,在佛教文化的影響下,當地許多習俗與自然環境幾乎沒有矛盾。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精神共同體,形塑了大批村民的日常實踐活動,使人類活動與環境保護融為一體。此外,藏傳佛教中的活佛、喇嘛也會主動向村民們宣傳環保相關知識,積極號召村民保護生態環境,在神座村,每月22 日是村民們集體外出的“撿垃圾日”。
最后,集體活動與婚姻圈的選擇也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村民間的集體認同。盡管村民在神座村已經定居了很多年,卻仍然受到游牧文明的影響,他們在牧區舉辦很多活動,諸如唱歌、跳舞、賽馬、跑步等,甚至有的村民會將婚禮舉行地點定在草原上。通過頻繁舉辦與參加村莊集體活動,村民安全感與歸屬感不斷上升,對村集體的認同度也不斷攀升。此外,在婚姻圈的選擇方面,當地村民傾向于將結婚對象選定為藏族,很少與漢族通婚。封閉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外來文化價值觀念對本土思想的沖擊,有利于鄉村精神共同體的維續。
總之,傳統性的地方文化知識采取多元形式,一方面推動了村民對鄉村實體的集體認同,另一方面又加快了鄉村精神共同體的建設。而且,傳統性地方文化知識本身就蘊含了諸多生態環保知識,在推動共同體重塑進而保護生態環境的進程中,其自身已經與環境保護聯結在了一起,并對當地村民環保實踐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作用。
3 小結
以川西藏族村寨神座村為例,本研究從兩個方面考察了地方環境保護的實踐。首先,通過分析市場經濟改革前神座村生態環境良好的現狀,說明市場經濟沖擊給鄉村造成影響的全面性與深入性。調研發現,市場經濟進入鄉村之后,帶來了人口急劇增長及鄉村共同體的破裂,而合理的人口數量及普遍認同的集體意識是當地維持生態穩定的重要手段,對它們的破壞便意味著原有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不再存在。結果是地方生態環境嚴重惡化,而地方經濟發展也受到巨大阻礙,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失去平衡。其次,本研究闡明國家與村民為保護自然生態環境進行的重構村莊共同體的嘗試。基于當地獨特的自然資源優勢與文化優勢,國家通過大力發展旅游業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村民收入,建構起“環境保護-經濟發展-進一步保護環境”的新型集體意識。同時,借助牧民定居計劃的實施,處理好旅游業發展人口不足的難題。此外,國家與村民對地方性傳統知識的運用,進一步推動了精神共同體的形成。正是在這些努力之下,新的鄉村共同體才得以出現,地方環境保護也有了新契機。
需要指出的是,國內相關領域對共同體的重塑與環境保護實踐關系的研究并不充分。但在當下農村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對二者進行社會學考察實屬必要。本研究主要對村落終結、重塑與環境保護實踐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內陸地區如何建構集體意識、國家力量介入的尺度大小等因素對重構村莊共同體的影響也亟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