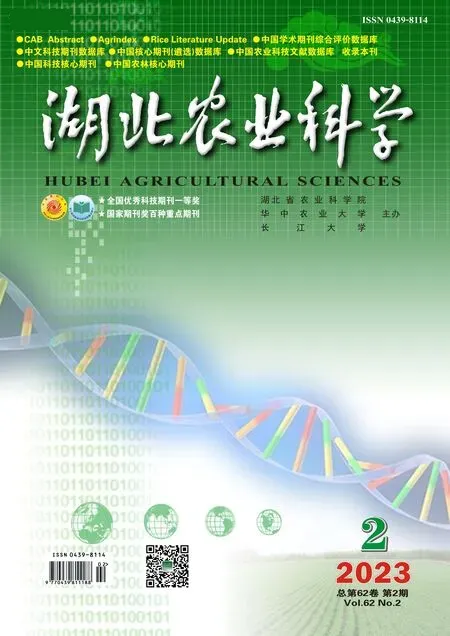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農民工復工行為選擇分析
石苗苗 ,夏春萍 ,王翠翠 ,童慶蒙
(1.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武漢 430070;2.長江科學院農業水利研究所,武漢 430014;3.華中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9)
2019 年底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簡稱新冠感染疫情)嚴重影響了中國宏觀經濟和部門產業[1],出現大面積的勞動力停工、企業停產以及供應鏈中斷現象[2],經濟形勢異常嚴峻。統計數據顯示,2020 年第一季度中國GDP 負增長6.8%,上半年GDP 增速下降1.6%,城鎮失業率高于5%,農民工復工困難,整個社會就業面臨沉重壓力。而農民工復工不僅有利于鞏固中國脫貧攻堅成果,還是評估“六穩”“六保”政策的重要標準,對疫情常態化下穩就業、保居民就業,保障農民工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影響深遠。為了減緩經濟損失,促進就業,各地逐步出臺政策促進復工復產。探討新冠感染疫情下影響農民工復工的因素,對增強農民工抗風險能力、提高農民工就業質量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學者圍繞農民工就業展開了廣泛研究,歸納起來主要從3 個方面探討了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因素。一是人力資本。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的提升能夠激勵農村勞動力遷移并促進融入性遷移的出現[3],特別是在遇到外部環境沖擊時,差距會更加明顯[4,5]。二是家庭特征。家庭勞動人口占比越大、家庭農業耕地面積越小,家庭成員越傾向于外出務工[6,7]。三是外部經濟環境及政策體制。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惡化會導致市場對勞動力需求的下降,致使大批農民工失業[8]。政策體制主要涉及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因素[9,10]。體制和政策的不完善會造成一定的就業歧視[11],導致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間的社會差距[12]。然而,面對社會公共衛生危機,經濟發展停滯,此時哪些群體復工情況更好,哪些因素制約農民工復工類型的選擇,有關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研究從公共衛生危機背景出發,基于多維視角的人類行為理論,以農民工作為研究對象,利用2020 年5 月對湖北、湖南、河南、廣西等22 個省(自治區)農民工的調研數據探究新冠感染疫情下農民工復工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1 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1.1 變量選取
在人類社會行為分析中,一般關注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13]。因此,本研究選取4 類變量來對農民工復工行為的影響因素展開分析,各變量具體測度見表1。變量的選擇依據如下。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1)心理因素。組成心理因素的認知發展對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本研究選定就業風險認知指標衡量農民工復工的心理因素。
2)個人因素。農民工的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流動有重要影響,且具有個體異質性[14]。已婚、家庭人口數量越多的農民工家庭負擔越大,越傾向于復工就業。一般而言,工作經驗越豐富、月收入越高的農民工受到外部危機沖擊的影響越小[8]。因此,選取農民工的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人口數量、外出年限、2019 年月收入8 個指標。
3)環境因素。行為受到個體所在“社區”,即群體、區域的影響,個體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可促進行為產生。各行業受疫情影響不同,復工復產時間存在差異。農民工輸入地和輸出地疫情嚴重程度影響農民工復工機會。因此,本研究選擇行業、工作地疫情嚴重情況和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3 個指標。
4)制度因素。勞動合同與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城鎮就業具有保障作用,能夠促進農民工就業[15,16]。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和是否繳納失業保險衡量農民工的制度保障情況。
此外,本研究的考察對象為農民工復工行為,具體包括農民工是否復工和農民工復工類型。復工即農民工恢復工作,實現非農就業,包括回到原崗位以及找到新工作兩種情況。以戶籍所在地為依據,農民工就業地點可分為本地就業與外出就業。農民工復工單位可分為回到原單位與未回到原單位。綜上,本研究將農民工復工具體分為回到原單位原崗位、回到原單位不同崗位、繼續本地務工(除原單位)、繼續外出務工(除原單位)和就業地點轉移。
1.2 數據
1.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樣本數據來自2020 年5月對農民工的隨機調查。在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18 級本科生中隨機抽選來自不同省份的農村戶口學生,對學生進行調研培訓后,通過學生發放問卷給周圍農民工。最終共收回707 份問卷,篩選掉缺失數據以及無效數據后,共獲得有效問卷632 份。
1.2.2 樣本基本概況
1)農民工基本情況。從調查數據來看,男性農民工占66.30%,女性占33.70%,并且86.55%的受訪農民工身體優秀或良好。被調查者大多為受過一定教育的中年群體,平均年齡在41 歲左右,學歷以初中為主。樣本農戶基本特征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高度一致,說明樣本數據具有典型代表性。
2)農民工復工行為現狀。被調查樣本中絕大多數農民工已經復工,占86.71%,未復工農民工占13.29%。復工群體中,回到原崗位的農民工占75.36%,回到原單位里不同崗位的農民工占5.29%,有19.35%的樣本農民工沒有回到原單位。具體情況如表2 所示。

表2 樣本數據統計
1.3 模型選擇
1.3.1 二元Probit 模型 由于農民工是否復工是一個二分變量,本研究采用二元Probit 模型對農民工是否復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二元Probit 模型具體構建方式如式(1)所示。
1.3.2 多元Logit 模型 農民工復工類型分為回到原單位原崗位、原單位不同崗位、繼續外出務工(除原單位)、繼續本地務工(除原單位)以及就業地點轉移 5 類,分別用j=1,2,3,4,5 表示。由于農民工復工類型是無序分類變量,因此選用多元Logit 模型來分析農民工復工類型的影響因素。其具體表達式如式(2)所示。
1.3.3 ISM 模型 ISM 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即解釋結構模型,常用來分析復雜社會經濟系統結構問題,對要素進行結構化分層,確定因素間的關聯性和層次性。本研究在Probit 模型之后,進一步通過ISM 分析顯著性影響因素之間的層次結構。在根據式(3)確定鄰接矩陣Rij的基礎上,通過式(4)得到可達矩陣M。
式中,i、j=0,1,2,3,…,k。
式中,2≤λ≤k;I為單位矩陣,矩陣的冪運算采用布爾運算法則。
最高層影響因素(L)由式(5)確定:
式中,i= 0,1,2,3,…,k;P(Si)表示可達集,Q(Si)為先行集。
通過式(5)依次從高到低逐步確定各層所包含的因素,具體過程為得到最高層L1后,刪去L1所對應的行與列,得到M1,以此類推,得到所有層次含有的因素。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由于農民工復工行為決策上具有較強的自選擇性,會受到一些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樣本可能存在選擇性偏誤,因此本研究引入了Heckman 兩階段模型檢驗模型中的自選擇偏差。回歸結果顯示,逆米爾斯比率(IMR)不顯著,說明模型不存在選擇性偏誤。
2.1 農民工是否復工的回歸分析
表3 為對全部有效樣本的參數估計結果。第(1)列為Heckman 第一階段回歸結果,第(2)、第(3)列為用二元Probit 模型擬合的實證結果,其中第(3)列報告了平均邊際效用。

表3 農民工是否復工的回歸結果
1)心理因素。農民工的就業風險認知顯著影響農民工是否復工,具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下,就業風險認知水平每降低1%,農民工復工的概率將提高2.4%。這說明就業風險認知水平越高的農民工越傾向采用保守策略,產生抵制應對行為。就業風險認知水平高的農民工對就業復工的“無助感”和焦慮更強,短期內更傾向回避、簡化型應對策略[17],即等疫情情況變好再復工。
2)個人因素。農民工健康狀況、外出年限和2019 年月收入對農民工復工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表明資本稟賦能夠減弱個體的生計脆弱性[18],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積累提高了農民工的競爭力和抵御風險能力。
3)環境因素。行業對農民工是否復工影響顯著。具體來看,相比于其他行業,建筑業和制造業農民工復工概率分別增加了7.5%和16.2%,建筑業和生活保障類制造業復工均早于其他行業,特別是建筑業在3 月初就實現了復工初反彈[19]。輸入地和輸出地疫情嚴重性均顯著影響農民工復工,對于勞動力輸入地,疫情不嚴重地區企業率先復工復產,因此在該區域工作的農民工復工概率更高。然而,對于勞動力輸出地,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越近的農民工復工情況越好。本次疫情重災區華中地區為中國最主要的農民工輸出區域,疫情期間湖北省及周圍各省市出臺多項政策扶持農民工復工,可見積極的政策能夠有效緩解疫情期間農民工復工的壓力。
4)制度因素。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復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相較于沒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有失業保險保障的農民工復工概率高出6.7%。農民工作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常年暴露在各種社會風險下[20]。失業保險能有效減少農民工工作的后顧之憂,降低就業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促進農民工復工就業。
2.2 農民工復工影響因素的層次結構分析
用S1、S2、S3、S4、S5、S6、S7、S8分別表示就業風險認知、健康狀況、外出年限、2019 年月收入、行業、工作地疫情嚴重情況、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和失業保險情況。在詳細調查以及咨詢相關專家的基礎上,給出上述8 個影響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表4)。其中,“1”表示行因素對列因素有影響,“0”表示行因素與列因素間不存在相互影響關系。

表4 影響因素邏輯關系
根據式(5)依次得到L1={S1},L2={S4,S6,S7},L3={S2,S3,S5,S8}。基于此,將影響農民工是否復工的 8個因素分為3 個層次,新冠感染疫情背景下,健康狀況、外出年限、行業、失業保險為影響農民工復工的深層因素,2019 年月收入、工作地疫情嚴重情況和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為中間層次因素,就業風險認知為直接驅動因素。
2.3 農民工復工類型的回歸分析
為探究已復工農民工的復工類型,在剔除未復工農民工的樣本后,使用多元Logit 模型,以回到“原單位原崗位”為對照組,進一步對新冠感染疫情下農民工復工類型的影響因素展開分析,結果見表5。

表5 農民工復工類型的回歸結果
1)心理因素。就業風險認知對農民工繼續外出務工具有負向影響,與就業風險認知水平高的農民工相比,就業風險認知水平低的農民工選擇繼續外出就業的概率是回到原崗位的76.4%,表明就業風險認知水平高的農民工反而不會回到原崗位。這可能是因為就業風險認知水平高的農民工對疫情認知消極,心理預期差,其對短期內復工復崗的不確定性更加敏感。因此,為了降低疫情對自身的影響,減少經濟損失,他們更傾向于盡快找工作復工。
2)個人因素。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均在10%的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民工到外地就業,表明已婚年輕男性就業競爭力和社會融入性更強[21],更愿意外出工作。農民工健康狀況顯著正向影響其外地就業,表明健康狀況越好的農民工回到原單位的可能性越高。家庭人口數量和2019 年月收入對農民工本地就業影響顯著且為負,表明家庭人口數量少、月收入水平低的農民工更傾向在本地就業。外出年限對農民工回到原單位不同崗位、繼續本地務工(除原單位)以及就業地點轉移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外出年限長的農民工回到原崗位的可能性越高,這與現有研究的結論一致[22],外出務工年限長的農民工就業地點慣性更強。
3)環境因素。行業對繼續外出務工和繼續本地務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具體來看,建筑業農民工回到原單位的概率較低,這與該行業工作特點有關。建筑業工作以項目為單位,農民工流動性大,且農民工大部分是通過熟人推薦或包工頭帶隊,因此他們回到原城市復工的概率較高。制造業的農民工更傾向于繼續在外地務工,這體現了農民工流動方向和產業集聚方向的高度一致性,由于中國制造業主要集中于南方沿海城市,因此大量農民工外出到該區域工作。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對農民工回到原單位不同崗位、繼續外出務工(除原單位)和繼續本地務工(除原單位)均產生顯著影響且為負,表明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越近的農民工回到原崗位的概率越低。其可能的原因是該區域農民工受防疫管控更嚴格,居家隔離期更長。因此,相較于其他群體,他們回到原崗位的可能性更低。
4)制度因素。勞動合同對農民工繼續外出就業(除原單位)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回到原單位不同崗位有顯著正向影響,對農民工繼續外出就業(除原單位)和繼續本地就業(除原單位)具有負向影響。相較于沒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回到原單位不同崗位、繼續在外地務工(除原單位)和繼續在本地務工(除原單位)的概率分別是回到原單位原崗位的2.715、0.212、0.278倍。這表明勞動合同、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回到原單位起到了保障作用,農民工失業風險主要表現在不穩定性和脆弱性[23],社會保障制度能有效降低失業率,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農民工穩定就業。
3 小結及政策啟示
本研究通過分析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總體上,農民工復工情況較好。截至2020 年5 月,86.71%的農民工已復工,復工類型以回到原單位為主,占總復工人數的80.65%。第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農民工是否復工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心理因素是直接驅動因素且對農民工是否復工具有負向影響。個體、環境與制度因素是間接影響因素,健康狀況、外出年限、2019 年月收入、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和失業保險對農民工復工有正向影響,而工作地疫情嚴重情況具有負向影響。第三,不同層面因素對農民工復工類型的影響不盡相同,總體而言,復工類型受環境約束影響較大,但是制度保障(如勞動合同、失業保險等)對復工的穩定性有較大幫助。此外,就業風險認知水平越低、家鄉到疫情重災區距離越遠、社會保障越完善的農民工回到原單位的概率越高。
基于以上結論,為推動農民工就業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增加信息獲取渠道,提高農民工風險認知能力。推進個人、政府與企業三方面的對接,充分利用多種渠道為農民工提供具有權威性和指導性的就業信息,加強引導,提高農民工風險認知能力。第二,建立健全多層次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提高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但是大量農民工無法被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覆蓋。因此,要擴大保險覆蓋范圍,提高低收入農民工安全感和抗風險能力。第三,統籌區域發展,優化產業布局。協調東中西平衡,統籌南北發展,推動區域間各產業協同發展。增加農民工就業機會,分化農民工失業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