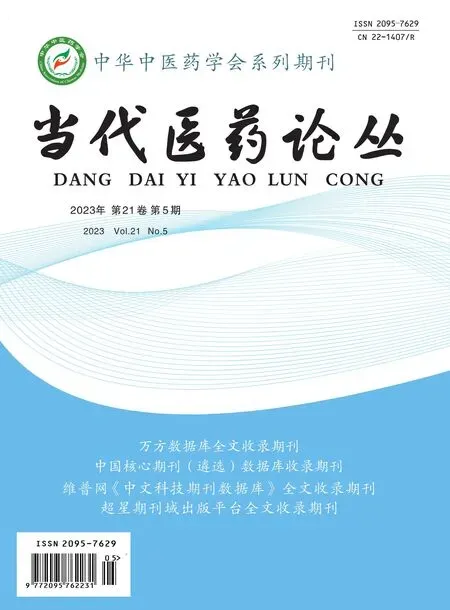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神經心理發育的研究進展
汪文慧,樊利春
(海南省婦女兒童醫學中心科研科,海南 海口 570206)
早產是臨床上公認的影響兒童及青少年發育的危險因素。多年來,相關研究的重點一直是極早產( 妊娠<32 周)嬰兒的發育情況。然而,最近有數據顯示,與39 ~41 周出生的同齡人相比,妊娠32 ~36 周出生的中晚期早產兒及37 ~38 周出生的早期足月兒也面臨著更大的發育問題風險。中晚期早產兒出現認知延遲、語言延遲、運動遲緩、腦癱、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孤獨癥及焦慮癥、社會情感及行為問題等神經發育障礙的風險顯著增加,早期足月兒的認知和運動領域功能、社會功能方面也存在缺陷。由于這部分嬰兒占全部出生嬰兒的絕大部分,且該人群中不良結局的小幅增加可能會成為相當大的公共健康負擔,因此有必要對這部分新生兒進行長期的隨訪研究,找出一種更加精確的、可以預測長期結果的衡量標準,對他們的長期神經發育障礙進行系統的分析,從而制定合理的干預計劃,促進其健康全面發展。本文主要是對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神經心理發育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中晚期早產兒的神經發育障礙
1.1 認知障礙
認知功能是指人腦認識和反映客觀事物的心理功能,包括感覺、知覺、言語、執行、記憶、歸納推理、理解判斷和決策等,可影響社會交往、學習等各方面。認知功能障礙即是指上述功能的損害。研究表明,與足月出生的嬰兒相比,中晚期早產(Moderate-to-Late preterm ,MLPT) 嬰兒在2 歲時出現神經發育障礙的風險較高(是足月出生嬰兒的兩倍)。大多數相關損傷發生在認知領域,認知障礙是最常見的不良后果;尤其是男孩MLPT 更有可能出現中度/重度認知障礙[1-2]。MLPT 嬰兒在校正胎齡2 歲時進行貝利量表評分可見,其認知延遲的發生率較高。研究表明,認知延遲與興奮性異常、嗜睡、喚醒異常有關[3-4]。此外,MLPT 兒童在學齡早期有發展成邊緣智力的風險,其執行商和記憶商均低于臨界值。他們在學校期間的總入學準備率、閱讀、數學和語言表達能力的得分明顯低于足月兒,接受特殊教育的需求明顯增加。這表明,這部分孩子在較大年齡時可能面臨更大的學習障礙風險[5-6]。
1.2 語言障礙
中晚期早產兒會表現出發育遲緩,在語言領域最為明顯。MLPT 兒童的語言障礙發生率是足月出生同齡人的3 倍,其接受性和表達性語言都會受到影響[7]。語言障礙兒童多伴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焦慮癥、行為障礙和情緒障礙等,這會增加其出現學齡期學習問題的幾率[8-9]。MLPT 兒童在5 個月、20 個月、4 歲、6 歲、8 歲時的語言評分均低于足月兒,差異主要表現在接受詞匯和表達詞匯方面;且這種語言表現的差異從20 個月開始至8 歲逐漸更加明顯。與同齡足月兒相比,MLPT 兒童在學齡期語言能力持續落后。對2 歲左右的MLPT 兒童進行語言評估可預測其學齡期的語言能力,有助于針對其語言能力進行及時的早期干預[10-11]。
1.3 運動障礙
晚期和中期早產兒發生神經運動障礙的風險高于足月新生兒,其粗大運動及精細運動能力均明顯落后于足月兒[4,11]。腦癱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主要表現為運動障礙。對MLPT 兒童進行運動評估主要是為了將腦癱患兒識別出來,并盡早進行干預。研究證實,腦癱發生的危險因素主要與早產有關[12]。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中發現,201 名MLPT 嬰兒和同等數量的足月分娩兒的對照中,MLPT 組發現2 例腦癱患兒,1例偏癱患兒,1 例四肢癱患兒;而足月兒組中未發現有腦癱或偏癱的患兒;該研究中MLPT 組的運動障礙發生率明顯高于足月兒[11]。與足月兒相比,中晚期早產兒被診斷為腦癱的可能性較高(是足月兒的三倍多)。在臨床實踐中腦癱通常在患兒1 ~2 歲時被發現,根據病史及患兒運動姿勢,如拉坐、站立、行走、腱反射肌張力等,采用標準化運動評估,結合影像學表現,并在重復檢查后才能做出明確診斷。臨床上應動態監測MLPT 兒童的發育過程,進行早期篩查,并行針對性指導訓練,以減少MLPT 運動障礙的發生;同時盡早將腦癱患兒識別出來,進行早期干預,盡可能改善其不良預后。
1.4 社會情緒和行為問題
早產相關行為障礙的特征是注意力不集中、焦慮和社會交往問題,這通常表現為兒童期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情緒障礙和自閉癥譜系障礙發生風險的增加。MLPT 兒童比足月出生的兒童更容易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相關內化問題( 情感和社會技能問題) 比外化問題更普遍,而且還存在性別差異,男生外化問題較明顯,女生內化問題較明顯。也有研究發現,男嬰的行為問題和延遲社交能力的發生率高于女嬰,但差異不顯著。近幾年對MLPT 兒童社會情感和行為問題的研究得出相互矛盾的結果。部分研究發現MLPT兒童與足月兒童相比,總體的社會情緒能力較差,2歲時出現社交能力延遲的風險顯著增加,但在行為領域無明顯差異。然而,也有研究發現MLPT 學齡前兒童在行為領域出現問題的風險顯著增加。盡管存在相互矛盾的結果,但是MLPT 兒童出現社會功能問題的數量整體上是較足月兒童明顯增多的。2 歲之前出現的行為問題( 攻擊性、挑釁性、過度活動、焦慮和退縮)和不良社會能力( 共情、親社會行為和順從等社會運動能力的延遲發展) 可以預測兒童后期的精神病理學表現。在與他人交往和形成社會關系方面的困難可能會影響兒童在學校的融入和表現,并長期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行為、社會和情緒問題的早期發現和長期隨訪管理可以改善MLPT 兒童的長期預后。在學齡前早期鼓勵育兒干預,加上學校的額外支持,可能有助于提高MLPT 兒童的社會能力。
2 早期足月兒的神經發育障礙
2.1 認知障礙
嬰兒的孕周和一般認知能力之間往往存在密切聯系。與孕37 ~38 周出生的嬰兒相比,孕39 ~41周出生嬰兒的認知得分有所增加,且每延長1 周都有相應的增加(37 ~41 周之間差異約3 個智商點)。與完全足月分娩的兒童相比,早期足月出生的兒童在1歲、4 歲和6 歲時的智商得分較低,到了學齡期,一般學習成績得分明顯低于完全足月出生的兒童。與孕39 ~41 周出生的兒童相比,孕37 周出生的兒童其全面智商得分明顯較低;但在孕38 周出生兒童與孕37 周出生兒童的對比中沒有觀察到這種差異。此外,在大量健康嬰兒樣本中,出生于妊娠37 周和39 周的嬰兒在智力發育指數上有顯著差異,但出生于妊娠38 周和39 周的嬰兒之間幾乎沒有差異,說明在早期足月妊娠的短短兩周內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神經發育結果。但是目前國內外對早期足月兒認知能力的研究較少,早期足月妊娠對認知障礙風險的影響程度尚不清楚[7]。
2.2 語言障礙
早期足月兒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與完全足月兒童相比,早期足月兒童發生認知語言能力障礙的風險較高,其發育性語言障礙或語言發育遲緩的發生風險明顯增加。語言能力與學齡期乃至成人后的學習能力密切相關。語言能力落后的早期足月兒童其在低年級及中等教育階段,學習成績低的風險增加,學習困難兒童的語言和閱讀成績較完全足月兒童差,數學成績差和拼寫困難也較多見。因此早期足月兒對特殊教育的需求增加,即使在成人后也會導致工作成績不佳。與完全足月兒相比,早期足月兒的語言能力較差,這種差異在20 個月至8 歲之間是一致的。兒科醫生和父母們應該意識到,即使是早期足月分娩的兒童,與完全足月兒童相比,也有語言延遲的風險。到20 個月大時,相對于同齡人表現不佳的兒童很可能在成人后繼續表現不佳。在2 歲左右對語言的評估是對以后語言能力進行預測的高效方法。事實上,早期干預已被證明能明顯改善語言發育結果。通過對幼兒的定期檢查,有機會發現語言能力落后的兒童,以便及時對其進行早期干預。
2.3 運動障礙
早期足月兒大運動及精細運動能力較完全足月兒落后,發生腦癱的風險增加[4]。只是目前國內外對早期足月兒童運動能力方面的研究較少,缺乏系統的理論和評估方法總結早期足月兒運動能力的特征;同時也體現出當前對早期足月兒的關注程度較低,仍將其視為低風險兒童。
2.4 社會情感和行為問題
關注早期足月出生兒童情緒或行為問題的研究較少,而且與MLPT 兒童一樣,目前對早期足月兒童社會情緒或行為問題的研究同樣存在相互矛盾的結果。部分研究在早期足月出生的兒童中并沒有發現社會情緒或行為問題風險的增加,有些研究則發現早期足月兒童的適應能力及個人- 社會能力較落后;同時孕37周和38 周出生的兒童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孕37 周內出生兒童出現行為問題的風險增加,但孕38 周內出生的兒童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問題;而按性別來分析,早期足月兒童中女童出現情感問題的風險增加,男童則較容易出現行為問題[4]。社會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存在將會影響早期足月兒童的長期發展,例如其出現學生時代學業問題和成年后生活及事業問題的風險會顯著增加。因此,臨床上需要更多地對早期足月兒童的社會情緒和行為問題進行研究,以期能早期識別并進行早期干預,促進早期足月兒童的早期發展。研究發現,早期足月兒童社會情緒和行為問題的特征與認知障礙的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兩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同樣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3 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童神經發育問題的大腦基礎
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童發育問題的潛在大腦基礎尚不清楚。近幾年的研究發現,較大的腦組織、白質和小腦體積與較好的認知、語言和運動得分相關,腦容量可能是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神經發育缺陷的重要評價指標。妊娠后期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34 周時,胎兒大腦的重量是足月兒腦重量的60%;在35 ~41 周之間,腦容量增加了5 倍;持續活躍的大腦成熟發生在妊娠的最后幾周,包括神經發生、突觸發生和樹突分枝;若早期分娩打斷了這一過程,使嬰兒脫離了子宮的自然保護環境,均可導致神經發育問題的出現。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腦生長發育的改變可能是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童神經發育缺陷的基礎。
4 結語和展望
中晚期早產兒和早期足月兒易出現長期神經發育障礙,包括認知功能下降、運動及語言障礙、社會情緒或行為問題風險的增加,這種風險有可能持續到學齡期甚至是成年。對中晚期早產兒和早期足月兒進行定期評估和長期隨訪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即使他們在早期生活中沒有出現神經發育障礙的跡象,但是一些細微的改變往往會隨著其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更加明顯。筆者希望能通過越來越多的研究,找出一種更加精確的、可以預測長期結果的衡量標準,能對他們的長期神經發育障礙進行系統的分析,找出其中預后相對較差的領域,從而制定合理的干預計劃,對風險最大的發育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監測和干預,以促進中晚期早產兒及早期足月兒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