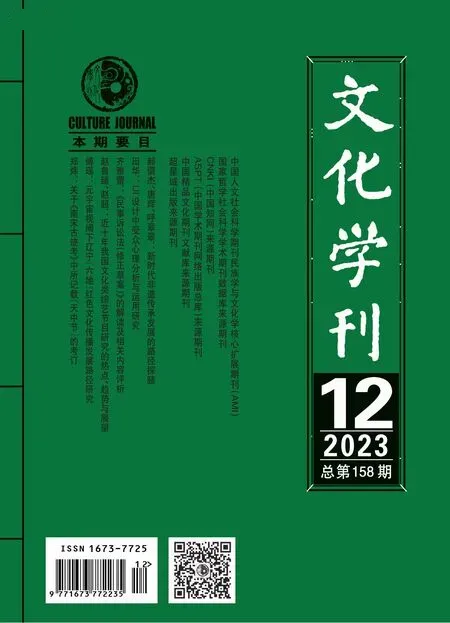德江儺堂戲源流考略
趙海陬
由于史料文獻的匱乏,學者們在著述中涉及德江儺源時或語焉不詳,或一筆帶過,給后續學人的研究造成許多困擾。自商周迄,以文獻考據為治學要務的官學傳統可謂一以貫之。王國維先生于1925年提出文獻與考古材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史學界長期依憑文獻考據的不足。在此基礎上,后續學人又相續提出“三重證據法”和“四重證據法”(1)二重證據法,即通過“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的互釋,打破了沿襲已久的傳統治學方式。“三重證據”,即傳世古書文獻、考古發掘實物和民俗學材料。四重證據,指傳世文獻、出土文字材料,民俗學、民族學相關材料,古發掘實物及圖像。參見王國維.古史新證[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3;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導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葉舒憲.四重證據:知識的整合與立體釋古[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6):24-28。。多重證據法在充分利用多種證據材料的基礎上,使傳統文獻難以解決的問題獲得重新考察的機緣。長久以來,儺學研究多聚焦于宏大層面的探討,對于地方儺源的深入探究則顯得相對薄弱。本文借助多重證據法,以前輩學者的研究為基石,通過歷史文獻、神話傳說、遺存實物、口傳史等材料的互釋互疏,對德江儺源進行多維立體的闡釋。
一、專家觀點
1986年11月,由貴州民族學院民研所與德江縣民委聯合舉辦的“儺堂戲學術研究會”在貴陽召開,曲六乙先生與會并作發言——《建立儺戲學引言》。曲氏在《引言》中指出,與宋元時期的南戲、雜劇及至地方戲曲的興起相呼應,在偏僻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還活躍著儺戲潛流,由于史料的匱乏,很難判斷西南地區儺戲產生的最早時間,就相關文獻顯示,至少在明初西南地區就已有儺戲的出現[1]13。
德江學者李華林先生認為,德江儺堂戲源自商周儺祭,唐宋受世俗生活及戲曲文化的影響,逐步衍變為“酬神還愿的儺堂戲”。然而,由于無明確史料,儺戲何時傳入德江縣境“已難以考證”。依《貴州通志》中“除夕逐出,俗于是夕具牲禮”及《思南府志·風俗篇》中“信巫屏醫、專事鬼神”的記載;結合20世紀90年代的德江縣民委的調查:德江儺堂戲之茅山教、師娘教共同頂敬——“玄壇會上趙侯圣主儺公大法老師”,以及二教門后來各自走向獨立;再參以虞舜時巫凡居(師娘教)南下經湖南、湖北輾轉至德江傳教的傳說[2]2。于是李氏得出結論:德江儺堂戲起源于中原儺祭,湘鄂川等地的儺戲傳入是其直接來源,至明嘉靖年間,思南府(含德江)已有儺戲的明確文獻記載。
貴州民族大學侯紹莊教授撰有《德江儺堂戲源流試探》一文,是迄今對德江儺源探討最為詳盡的文章。文章以土家先民的一支——古羌戎——在歷史中的遷徙為線索,推演中原儺祭隨古羌戎南遷而帶入武陵山區的歷史:周武王時,古羌戎作為周之與國進入中原地區,后輾轉南下經湖北枝江、湖南常德進入武陵山區。古羌戎在進入中原后必然會接觸或吸收中原儺祭的習俗,并在遷徙的過程中帶入湘西、黔東北一帶的廣大區域。侯氏進一步推導,德江儺堂戲是“隨西北戎人輾轉遷徙過程中帶入的古代中原傳統儺祭的發展演變”,是中原儺祭與濮、僚土著俗信相融后,又經一代代職業巫者的雜糅,最終“在明代基本形成今天儺堂戲的格局”[3]。
據貴州學者高倫先生考,漢唐以來,大量外來移民遷移至武陵山區,以及歷史上的駐軍和行政官員及家屬的留居,使得外來風俗禮儀、祭祀娛樂得以在當地流傳。黔東北地區與渝東地緣相鄰,習俗相近。宋代高僧冉道隆《大覺禪師語錄》“頌古”詩對涪州儺戲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戲出一棚川雜劇,神頭鬼面幾多般。夜深燈火闌珊甚,應是無人笑倚欄。”[4]秦漢以來,德江就是烏江流域的重要樞紐,沿烏江上游的德江可直通涪陵,涪州“神頭鬼面”戲難免不會影響到黔東北地區;加之《宋史·蠻夷列傳》中“漢牂牁地(含黔東北部分地區)……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鼓、沙鑼以祀神”(貴州“儺祀”最早的文字記載)、《大元一統志·思州軍民府》中“蠻有佯儣、仡佬、木搖、苗、儨……疫疾則信巫屏醫,專事鬼神,客至則擊鼓以迎”(2)據高倫先生考,元代思州軍民府地轄今德江、沿河、務川、鎮遠、石阡、思南、天柱、三穗、銅仁等縣、市。兩條文獻,高氏由是認為:貴州儺或儺堂神戲是由漢民遷徙帶入,至少在元代,黔東北少數民族地區已有“儺(的)活動或者(簡單的)儺堂神戲”的存在。
在《貴州戲劇史》(2004年版)一書中,作者將貴州戲劇置于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探討了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對貴州文化的影響。書中指出,由于歷代移民的遷入,特別是宋元時期晉贛湘川等地移民的涌入,他們在帶來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儺祭和歌舞。又,“黔東北的一些縣古屬巴郡”“黔涪”地區巴人習風相近,南宋涪陵地區的儺戲“已具雛形”“儺戲在此文化生態區內”難免會相互影響。宋元時期的貴州民間巫儺活動中不僅有儺歌儺舞,而且“貴州儺歌儺舞(還)摻雜故事(情節),大致在宋代也有了儺戲的雛形”[5]。
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在文著中涉及德江儺源。譬如,羅受伯先生認為,自秦統一后,部分流散于南方民間的楚文化在與鄉間民俗相融后遺存至今,“特別是德江一帶土家族的儺堂戲,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1]110。在《德江儺堂戲》一書中,庹修明教授指出:儺的傳入應與巴楚文化有關,“據史料考證,德江儺堂戲始于明洪武年間,至嘉慶年間已初具規模”[6]。惜庹氏在書中并未指出這一文獻來源。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黔東北及德江一帶的儺戲是由外來移民的遷徙而帶入,它與中原儺祭有著歷史的淵源;德江儺俗信仰除受中原巫儺文化的影響外,還受到巴蜀、荊楚巫文化的影響,川渝湘鄂是德江儺堂戲傳入的主要區域;黔東北及德江一帶的儺(戲)向前追溯可至商周時期的儺祭,德江儺戲的出現至遲不應晚于明嘉靖年間。
二、神話推演
據德江縣民委調查資料,虞舜時期,巫凡居(女)隨行“三苗”南下,她先后于湘鄂兩地傳法,最后輾轉至德江平原、煎茶、長豐等地傳教[2]3。在《德江儺堂戲》(謝勇版)一書中記述了一則傳說:三苗首領讙兜南下開疆時,其專程前往“豐沮玉門山”請巫咸南下輔政,巫咸不愿隨行,于是派門下弟子巫先隨讙兜南下。巫先在武陵山區傳法時收下弟子劉先,劉先學藝精湛,后被巫咸封為茅山傳人,從此茅山教在武陵山區傳播開來[7]9-10。
唐宋時期是儺(禮)“戲化”“俗化”的重要階段,與此關涉的儺源傳說似有歷史憑據。初唐劉武周叛逆,李世民請尉遲恭保唐討逆,尉遲將軍講,如要其保唐須天下“粉裝”,李世民覺得奇怪,于是將此事奏告玉帝,……故事一路延展,引出大雪紛飛(粉裝)和烈日當頭,滾滾洪水將昆侖山中沉香木沖入大海,東海龍王以此打造出龍床一張,不想公主卻因之一病不起,于是龍王許下愿信,“大儺十二祭,小儺十二堂,許下長標丈二長,短標一尺二,……又許下了神戲二十四個”[8]24。另一則傳說來自穩坪鎮掌壇師張華軍,“傳說唐明皇時,三公主染上瘟疫,久病不愈,聽說土家人跳茅山戲很靈,于是請他們帶上儺公儺母到皇宮表演。此后,三公主的病漸漸好轉,于是唐明皇賜他們竹席一張,從此在儺堂表演時就有了一張竹席。”
明清時期,由于戲曲、小說和說唱文學影響,在儺戲中也呈現出多樣的角色及簡單的情節,表現在地方傳說上有西天取經的故事。傳說開山土老師(土巫)去西天取經,在佛祖處求得一部半經,在回來的路上,客老師(漢巫)要去一部,苗老師(苗巫)又要去半部,于是,土老師不得不再次西行,佛祖聽其述說后言:“客老師一本經;苗老師半本經;土老師亂搬經,百說百靈。”法事禱念經文時用的木魚也有傳說,據楓香溪掌壇師王國華說:“唐僧過污泥河時,船被魚精拱翻,經書翻到河里,唐僧師徒撈起一半,還有一半被魚精吃了,后來玉帝把魚精做成真身,先生用丁木來敲它一下,經書就吐出來一本。”
思南縣流傳的神話源自北宋。相傳宋仁宗時,水閣楊幺于洞庭湖聚眾作亂,宋廷派牛皋率大軍征討,因有仙人相助,牛皋一舉將亂眾剿滅,又將楊幺削首拋入湖中,楊幺之妻蘇月英聞訊自刎,人頭落入湖中,兩顆人頭隨波漂向遠鄉。一日,一漁夫在“轉”(捕魚工具)中發現兩顆人頭,隨即將人頭拋入湖中,次日漁夫在“轉”中再得人頭,一連數日皆是如此,漁夫只好將楊、蘇之頭放于岸上。后來,兩顆人頭被放牛娃搬入洞中,他們邊唱邊跳進行祭奉,鄉民前來許愿也多靈驗。天長日久人頭腐爛,于是人們用木雕偶像作為替代,儺堂戲從此在思南傳播開來[9]。
黔東北土家族地區的儺源傳說有很多,這些傳說上可追至“三苗”時期的巫術活動、唐宋時期的歷史演繹,這些神話傳說表明黔東北及德江一帶的儺戲與中原儺祭、唐宋儺儀有著某種歷史的淵源;巫凡居、巫先南下傳法、土老師“西天取經”等傳說亦從側面印證德江儺為外來文化傳入的事實。
三、實物證據
儺俗一向被視作巫風鄙習而為士人所不屑,因此,在歷代文獻典籍中少見記載,加之古代儺事離現代生活已然遙遠,儺實物早已于湮滅歷史之中,實物資料的匱乏給后世儺學研究造成諸多困擾。因此,新近發現的儺實物就成為研究考證重要憑據。
德江縣可循證的最早的儺實物為明宣德年間的儺法器。長堡鄉巫師周興堯處遺存有5件儺法器:4個儺法鈴和1個儺香爐,均為青銅器皿,在儺香爐底部刻有陽文“宣德元年制”(宣德元年,即1426年),此物足以佐證明代中期德江一帶有著儺的活動。另,煎茶鎮龍溪雪峰山吳氏一壇“神母子”(《歷代祖師歌》),其中歷代師承160多人;長豐區泉口陳氏一壇傳承依“興旺開揚勝,通靈高真清,道立安應廣,順明正乾坤”進行排序,陳氏儺壇承續人名已換兩輪,算來應有40余輩,若一代人以20年為計,恐已有800余年的歷史,如向前推演可追至宋末元初;又,潮砥鄉龍橋留有《歷代傳師譜》,上面記錄師承80余人,這些材料足以證明德江一帶的儺活動有著漫長的歷史。
蕭飛羽笑了,他扼腕道:“想起來了,原來你就是那傲慢得要命的丫頭。”他起身出臥室取來一件寶藍色罩袍塞進羅帳。
此外,古建筑及墓碑中的文字、圖案亦可作為一種實物佐證。楓香溪鎮袁場尚存一儺藝人墓,墓碑上刻寫——洪武五年(1372),又刻“八仙慶壽”“三元和會”等圖案,其中人物皆為儺堂戲角色扮相;穩坪鎮平頂壩遺存有一清道光時期民居,其主人為儺戲藝人,所建民居窗花上有“耕、讀、漁、樵”等雕刻裝飾,內中亦為儺堂戲人物裝束;煎茶鎮龍溪朝陽大墳堡墓葬,其中一儺戲藝人墓碑上刻有歷代師傳名號24輩傳人。
從遺存古代城圜遺址看,德江縣境內遺存有隋扶陽古城、唐費州城圜及南宋庸州治所3處遺址,隋、唐、宋三代在此斷斷續續進行管轄持續數百年時間。官府儺自漢末而始,至唐已有嚴格規制,《大唐開元禮制》在“大儺之禮”行文之下分七處用雙行附注,以對“諸州縣儺”進行規制,這些規定在內地和邊疆都有實施,然而在地方史志中卻多不予列出(3)唐“州縣儺制”作為慣例,方志文獻多不予記載,但還遺留有少數史例,如廣西柳州柳公祠碑文(唐永和十五年)、江西修水縣長茅北堡方相氏面具(唐末)、敦煌《兒郎偉·驅儺詞》(唐中期)等官府儺文獻及實物遺存。。宋紹興六年(1136)朝廷派兵3000余人駐守沿邊溪洞諸州,這些兵士“平居則事耕種,緩急以備戰守”(《貴州通志》卷6),在石海波先生看來,這一時期,貴州駐軍的情況“雖未見載于史……根據當時軍隊里有戴面具的習慣和有軍儺的情況看,宋代駐守在貴州的屯軍無疑也有戴面具的習慣和軍中儺戲”[1]81。原德江縣文化局局長謝勇先生從民族遷徙及邊地治理角度,認為早在隋唐時期就有大量移民的遷入,加之王庭對黔東北及德江一帶管控的加深,黔東北長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德江或已有儺或儺戲的存在,只是無相關文字留傳下來而已。
在《貴州德江儺堂戲簡介》宣傳冊中,德江縣民宗局提供了兩個傳承譜系表,一是穩坪鎮茅山教張月福儺壇傳承譜系表,一是煎茶鎮師娘教曾廣東儺壇傳承譜系表。張月福儺壇傳承譜系中第一代傳人冉法林的從藝時間為11世紀初,即宋真宗在位期間。曾廣東儺壇師承譜系中第一代傳人甘法興的從藝時間為15世紀初,為明成祖在位時期[10]。另外,在開壇儀式中,把壇老師自述:“我祖原是湖南湖北人,來在貴州顯威靈。”在科書唱本中,柳三自稱:“家住湖廣武昌縣,棋盤格子我家門。”[2]382青苗土地唱:“家坐江西南康州十字縣,永先橋下姓蕭人。”甘生自報家門:“家坐江西康州十字縣,永興橋下姓蠻人,父親有名蠻百萬,母是堆金積玉人。”這些材料亦可視作德江儺堂戲經由外地傳入的旁證。
如依唐宋城圜遺址、吳氏“神母子”,又參以唐代儺儀規制,黔東北及德江一帶在唐初或已有儺(祭)的傳入,只是未見史料列出。從張月福儺壇傳承譜系看,儺戲傳入的時間上限或可追至北宋中期;結合明代儺香爐、明清時期儺堂戲刻繪人像及地方志書等材料,可證至遲在明嘉慶年間,德江已有儺的演出,且初具規模;就曾廣東師壇圖中“湖北啟教”“湖南啟教”,以及科儀唱本中“問根生”戲詞進行分析,德江儺堂戲經川渝湘鄂等地傳入應為事實。
四、歷史考據
自西周始,儺已有確信的文獻佐證。宋高承《事物紀原》“驅儺”條:儺“雖原始于黃帝,而大抵周之舊制也”。曲六乙先生說:儺“發端于上古的夏商,形成于周而規范于‘禮’”[11]。儺源于商周祭禮已為學界普遍認同。
商周之際,土家族先民巴人隨武王伐商。西周建立后,周武王封其親族姬姓于巴地,名曰巴子國,即今渝東、鄂西一帶。周顯王時,巴國故地漢中、巫、黔中為楚國轄地。西漢初年,吳芮將軍因南豐境內“軍峰聳峙”“煞氣”太重,于是在此行“周公之制(以)傳儺”(4)傅子大輝《儺神辨記》:“輝嘗考宋時邑志舊本載漢代吳芮將軍封軍山王者。昔嘗從陳平討賊,駐扎軍山,對豐人語:‘此地不數十年必有刀兵,蓋由軍峰聳峙煞氣所鍾。’”收錄于《金砂余氏重修族譜》。;漢武帝時,川蜀大姓大量遷入梵凈山區;蜀漢時期,諸葛亮率大軍南征,一些川蜀大姓隨軍遷入西南各地,漸成地方豪族。至南北朝,隨著中原及周邊各民族的遷入,這些外來移民在長期的共同生產和生活的過程中,與當地土著共同形成西南邊地的“蠻苗部曲”。
唐宋時期,隨著國家權力觸角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不斷深入,中央王廷對湘鄂渝黔邊地區逐步加強軍事控制。《方輿紀要》載:北周宣政元年(578)置費州;隋設庸州府,轄周邊鄰縣,唐貞觀四年(630)改置思州,轄務州、涪州、扶陽三縣。(5)北周置費州,治所在德江縣潮砥鎮官宅村;隋設庸州府,治所在德江縣泉口鄉;扶陽古城位于德江縣合興鎮朝陽村扶陽河畔,據《舊唐書》載,古城興建于隋仁壽四年(604),廢于宋。扶陽古城遺址內含城池、衙署、練兵場、兵營、馬場、戲臺、園林等,共占地6萬余平方米。《土家族簡史》引唐杜佑《通典》卷183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朝廷設黔中道,“嘗以黔州挖扼險要,往往置鎮重兵,以兼總羈縻州郡”[12]。兩宋時期,朝廷對武陵山區采取“樹其酋長,使自鎮撫”,于是諸多土酋紛紛上表歸附。德江縣煎茶鎮今遺存有3座宋墓,墓內分別刻有“太極圖”“加官進祿”“寶玉滿堂”“東海南山”等字符,可見宋時中原文化對黔東北少數民族地區的深刻影響。北宋時期,朝廷對各州縣官府儺亦有嚴格規制,《政和五禮新儀》“軍禮·大儺儀·州縣儺儀”條:“方相氏,州四人,縣二人,俱執戈楯;唱帥,州四人,縣二人;侲子,選年十三以上、十五以下充……”且民間儺多與官府儺同時進行。從德江儺堂戲角色看,尖角將軍、梁山土地、幺兒媳婦、勾薄判官、鐘馗等可與宋代宮廷儺儀中的將軍、土地、小妹、判官、鐘馗一一對應。雖然在德江儺堂戲中并無門神、灶神等角色,但在“開壇禮請”時仍被一一提及。譬如,穩坪鎮安永柏儺班誦詞:“奉請何神,奉請何主……門丞戶尉、井竈龍神、東廚司命灶王府君……”可見,德江儺堂戲與宋代宮廷儺有著明顯的承續遺痕。
到了元代,朝廷開始在湘鄂渝黔等地設立土司制度,梵凈山區全面納入王廷的掌控范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思州田氏(田景賢)內附并被授與“思州安撫司”之職,正式獲取梵凈山區的世襲統治權。至元年間,朝廷派駐軍隊于梵凈山區修筑道路。《梵凈山區土家族歷史文化研究》引《元史》:至元十七年“……思、播道路不通,發兵千人與洞蠻開道”[13]。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廷在播州、思州等地駐軍并設立驛赤(驛站),進一步加強對梵凈山土家族地區的控制。蒙元統治者并不崇儺,而是信奉“敬天畏鬼”的薩滿教。然而,在廣大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仍活躍著儺的潛流。元吳萊《時儺》詩:“侲僮幸成列,巫覡陳禁方。……惜哉六典廢,述此時儺章。”[14]即為當時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儺活動的生動描述。
明洪武十四年(1381),潁川侯傅友德率三十萬大軍南征,明軍沿云貴交通要地廣設軍事衛所,又于駐地屯田開墾。漢人的涌入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時還帶來家鄉的儺歌舞和說唱藝術,這些外來藝術與土族民俗、祭祀相融合,漸成新的儺事樣態,這在貴州各地方志中都有反映。明清始,貴州儺俗記載逐漸增多。明《貴州通志》載:除夕逐除,鄉民于家中陳火燭、列紙馬、……如上古驅儺狀。《思南府志·風俗篇》載:土民信巫屏醫,專事鬼神,客至則擊鼓相迎。清《思南府續志》載:鄉民各禱其事,如其所愿,則報之以牲,奉之以酒,采戲相酬。民國《德江方志》載:冬日間或有家戶舡儺,“迎春則扮臺閣演古戲文”[7]V,沿街巡演以暢春氣。
從相關文獻看,土家族先民自商周時就與中原地區保持著政治文化上的聯系。隋唐以前,黔東北地區的儺事活動難以考證。及至宋時,黔東北地區已有“儺祀”的明確記載。從《思州軍民府》中的簡略片語看,元代思州府境內或尚未出現完全戲曲化的“儺堂神戲”。明清時期,隨著大量移民的涌入,黔東北及德江一帶的儺戲變得熾熱起來。
五、結語
自夏商迄,土家族先民就與中原地區保持著政治文化上的聯系,然而,由于史料的匱乏,唐宋以前的中原儺祭在武陵山區傳播與否后人無從知曉。唐宋以降,中央王權觸角在西南邊地的深入,為后人提供了可資研究的材料。隋唐城圜遺址、儺源神話、儺壇傳承譜系、《宋史·蠻夷列傳》等材料表明,至少在宋代,黔東北地區已有“儺祀”的存在。依元代學者吳萊《時儺》詩對西南地區儺戲的描繪,以及南宋涪州“神頭鬼面”戲對黔東北地區可能產生的影響,再結合《大元一統志·思州軍民府》中的描述,有理由認為,元初黔東北地區已出現簡單“儺堂神戲”,這些“‘儺堂戲劇’當是一些單個神戲為主的戲劇,而不是戲曲化的‘儺堂戲’。”[8]19如將明代儺香爐、清代窗花儺堂戲人物,及《貴州通志》《思南府續志·風俗篇》等材料彼此關聯,可知明清時期的德江縣境內已出現以“戲”酬神的儺戲。依民國《德江方志》所載:儺戲“冬時”“亦間舉,……迎春則扮臺閣演古戲文”,讀者可以想見民國時期德江儺戲表演的盛景。
黔東北與湘鄂川渝地緣毗鄰、習尚相近,德江儺堂戲由周邊土家族地區傳入應是無疑。雖然黔東北儺戲與巴蜀、荊楚巫文化有著歷史的淵源,但并非原生的土著文化,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由外來移民將中原儺祭輾轉帶入,再經一代代巫師不斷雜糅后的發展與衍化。
——鄉村儺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