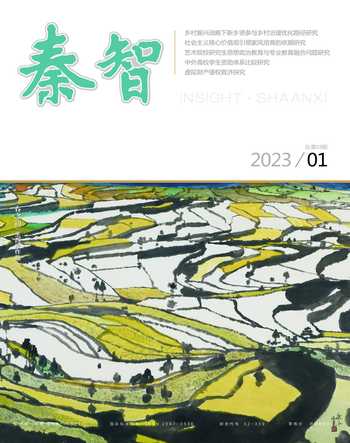正當解雇事由體系化構建問題研究
[摘要]解雇問題是勞動法中的核心問題。我國采用列舉式的正當解雇事由模式難以概括所有解雇事由,缺乏反歧視條款,僵化不易變通,而且對不同規模企業一視同仁,條文定義籠統,沒有統一標準,不利于司法適用,不利于勞資關系平衡。應該明確正當解雇事由的基本原則,對不同企業設立雙重規范,參考本土經驗,對條文的司法適用加以明確,構建體系化的正當解雇事由模式。
[關鍵詞]勞動法;解雇事由;體系化
一、問題的提出
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就是勞動關系,而解雇問題一直是勞動法中的核心問題。《勞動合同法》第四章對此進行了專門規定,第39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了企業在某幾種情境中可以運用法律解雇員工。
然而,《勞動合同法》正面羅列“正當事由”的做法,雖然在形式上符合國際經驗,但實踐中只用正反列舉往往難以囊括社會事實[1],而且對不當解雇并沒有法律上的明文規定[2],對于歧視性、報復性解雇等沒有相關的保護條款。
同時,目前我國《勞動合同法》的傾斜保護過度強調穩定性,忽視流動性,對不同規模的各類企業一視同仁[3],這種保護已經超過了社會現實的承受能力,造成的后果可能會使實務上的適用和立法目的背道而馳。以及法律條文上的抽象規定,給了勞動關系主體以及司法機關很大的操作空間,沒有統一的標準,導致司法不一致,不利于保護勞資雙方權益。
二、正當解雇事由的列舉缺失
(一)列舉模式導致內容模糊
我國解雇權中關于解雇事由的規定存在相當大的抽象空間,導致了企業在依法解雇或勞動者維護自己權益時存在各種誤讀[4]。地方性文件也沒有確定具體的實施標準,只對公司規章的程序性內容作了規定,比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所公布的文件規定對于公司的規章制度內容應當進行合理性審查,但如何審查和審查標準都并無提及。
(二)不當解雇事由立法缺位
我國現行的勞動相關法律以及法規,沒有法條對不當解雇進行規定。盡管《勞動法》中有法條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的權利,即在求職時不因種族、族裔和個人宗教信仰的差異而受到歧視,然而在解雇方面特別是因為歧視而被解雇的法律救濟沒有相關規定。雇主往往以表面合理的解雇理由掩蓋對工人的實質性歧視,導致勞動者因受到歧視被不公正解雇而提出的申訴往往得不到支持。
(三)列舉模式適用封閉落后
《勞動合同法》中有關“正當事由”的列舉模式具有封閉性,在第39、40條列舉的正當事由中,并沒有法律中常用的“最后條款”[5]。換句話說,雇主只能從法律規定的單一清單中挑選事由,出現任何例外情況即使符合情理,也可能觸犯法律。“正當事由”的封閉定義代表了法律知識的局限性與實踐的多樣性之間的矛盾。
三、正當解雇事由的規制僵化
新時代背景下,市場經濟中最具有活力和最大體量的群體就是小微企業,他們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升值轉型的巨大力量,但同時抵抗風險和市場變化的能力遠遠小于大型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屬于弱競爭對手。《勞動合同法》尋求設定一種“穩定的雇傭關系”不符合小微企業的發展需要將解雇的“正當事由”限制得較為嚴格,因此小微企業行使解雇權的成本極為高昂,無法靈活應對市場變化。
(一)小微企業不宜適用過錯性解雇規定
規章制度對公司的經營和發展至關重要,可以有效協調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勞動合同法》第39條規定,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屬于過錯性解雇事由之一。對勞動者少、勞動關系靈活的小微企業來說,這一規定可能會給法律的適用帶來困難,因為他們沒有相應的技術能力制定合理的規章,以至于不能明確什么是“嚴重”的情況[6]。在以上背景下,小微企業如果要避免非法解雇,只能僵化遵守法律,后果就是失去用工自主權。事實證明,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這一事由,對小微企業的經營是有害的,應該通過制定法律來改進。
(二)小微企業難以適用無過錯性解雇規定
在無過錯解雇的條件下,小微企業更難解雇不稱職的員工。小微企業需要靈活管理,然而《勞動合同法》第40條所規定的崗位流動和員工培訓卻增加了其經營的壓力,一方面,小微企業普遍由于經營規模小、用工少而缺乏轉移崗位的能力;另一方面,小微企業有較大的資金管理負擔,沒有能力再雇傭一個管理人員來規范化管理企業。在這種極為嚴格的解雇條件下,根本無法真正意義上擁有用工自主權。
(三)小微企業無法適用經濟性裁員規定
經濟性裁員在適用上具有特殊性,即它只能適用于中大型企業。經濟性裁員中包含一種優先留用條款,這一條款規定用人單位如果想解雇員工,應當優先留用與用人單位簽訂長期固定勞動合同的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的員工和有沉重現實壓力的員工,主要原因是這些勞動者被解雇后重新找到工作的能力較低。因此,企業必須在法律范圍內承擔社會責任即保障這些勞動者的生存權,這顯然是不合理地將國家的義務轉移給用人單位。尤其是小微企業經濟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都較弱,如果要求他們依據經濟性裁員的規定來解雇員工,無疑會使其擔負起過重的社會責任。這些條文不僅給小微企業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影響其發展,甚至可能導致其陷入經濟泥沼。
四、正當解雇事由的適用困難
思想是行為的先導,行動是在思想的前提下進行的,最終結果也會被思想所影響。在司法判決方面,法官自由裁量權也被這一概念影響,在法律條文抽象模糊的情況下,法官不可避免地會考慮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通過法律解釋將其應用于具體情況[7]。然而,由于缺乏相對統一的標準或準則,不同的法官不可避免地有不同的判斷方法,例如關于確定“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含義,一些法官認為,雇主有權確定哪些行為是規章制度中的“嚴重違反”行為,需要審查的部分只有規章里規定的部分;然而另一些法官卻認為,如果雇主的自主權被過分保護,規則和條例的內容就不會得到合理審查,員工很容易陷入被侵犯權利的風險。由于這些裁判思想的不同,導致的最終裁判結果當然也不一樣。
五、正當解雇事由的體系化構建
“體系”思想意味著在多樣性中展開統一性,由此多樣性被理解為某種意義的脈絡關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勞動法》暫時擁有了這一體系化模式的細節分支,但相關法律條文仍然相對分散,使得法條之間的配合變得困難。因此,有必要系統地構建而不是分割“正當事由”這一概念,在考慮到我國國情的前提下,《勞動法》應既具有靈活性又能有效保護勞動者權益。
(一)以基本原則為展開中心
1.明確最后手段原則
“最后手段原則”是比例原則的一項部分原則,這是德國三項最重要的就業保護原則之一,意味著雇主必須利用其他可能的、溫和的方式都無效后才能解雇勞動者[8]。“最后手段原則并不是要雇主采取絕對和最低手段,是在預期的范圍內,平衡雙方的利益,在不過分侵犯雇主財產權的情況下維持雇傭合同。”因為“最后手段原則”可以外化為司法控制手段來進行解雇事由的審查,所以它可以對個別案件作出全面判斷,以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
2.增加歧視性、報復性解雇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嚴禁公司在三個時期(懷孕、孕期和哺乳期)解雇員工,但這種非法解雇仍然頻繁出現。因此,分析這一行為并將其納入現行法律框架也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3.加入合法正當解雇做兜底條款
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般來說,法律是在一段時間之后制定的,這很難有效和全面地保護所有社會上可能出現的解雇情況。要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補充相關立法,增加相關的兜底性要求,即增加“客觀、合理、合法且符合要求的其他情況”,以更好地彌補在立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遺漏。
(二)賦予正當解雇事由雙重規范意義
1.減輕小微企業制定規章制度的義務
首先,小微企業普遍缺乏具有專業水平的管理人才,在大多數情況下制定的企業規章內容不全面、形式不標準;其次,當前絕大多數小微企業的企業規章只是《勞動合同法》相關法條的簡單摘錄,對企業沒有任何實行方面的意義。因此,最佳選擇就是讓小微企業不必強行制定規章制度,以促進其進一步發展。
2.放寬小微企業適用不能勝任工作的規定
首先,小微企業在人員和物資方面無法進行有效地管理,如果企業中有不稱職的工人,可以通過協商終止雇傭合同;其次,如果雇主和雇員無法達成協商結果,他們可以依法進行必要的培訓或工作調動,前提是公司有適當的條件;最后,如果企業沒有適合的培訓和安置條件,可以向仲裁機構申請終止與員工的雇傭關系,并給予足夠的經濟補償。
3.豁免小微企業適用優先留用規則
我國《勞動合同法》確立的優先留用制度,是《勞動法》社會性的體現。然而小微企業風險應對能力較弱,生存時間短,員工流動性高,無法確定解雇工人時應當依法留用的人員[9],這很容易在法律適用方面造成問題。從這個層面考慮,有必要免除小微企業對優先留用制度的適用,以促進其良性發展。
(三)淬煉于本土經驗的共性聚焦原則
根據一般法律理論,必須在國家體制基礎上確定解雇的體系化標準,特別是一般解雇保護制度產生的共同需要,對“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進行厘定。
首先,應該考慮到勞動者的主觀狀態。員工的過錯程度反映了信賴利益的損害程度,員工的過錯程度越嚴重,信賴利益的損害程度就越高,雇主越不可能期望繼續保持勞動關系;只有當員工主觀過錯嚴重,用人單位才能解雇。
其次,應該考慮社會公共利益。在疫情背景下,考慮這些因素尤為重要,雖然一些員工行為不會對雇主造成嚴重傷害,但由于公共利益的變化也會帶有社會影響。此時,當雇主提出解雇時,法院應考慮社會影響因素,但這一標準原則上不是評估雇員“嚴重性”的標準,也只能用作輔助參考。
六、結語
通過以上幾種方式,以“最后手段”基本原則為展開中心,考慮到小微企業的特殊性,賦予其正當解雇事由雙重規范意義;并根據國情對法律條文進行明確化規范,建立有效的正當解雇事由體系,在維護勞資關系平衡的前提下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地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國慶.解雇權限制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2010.
[2]胡謙.不當解雇的法律問題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2021.
[3]倪雄飛.《小微企業豁免適用規章制度的思考》[J].中國勞動,2015(21):23.
[4]閆冬.論正當解雇事由的體系范式[J].法學,2020(04):177-191.
[5]郭溪芳.解雇保護法律制度研究[D].遼寧大學,2021.
[6]倪雄飛.《我國解雇保護制度對小微企業的適用及其制度完善》[J].山東社會科學,2015(10):174.
[7]朱卉.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用人單位解雇權限制法律問題研究[D].東南大學,2021.
[8]董保華.《十大熱點事件透視勞動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2007.
[9]曹有康.《論我國解雇保護制度的完善》[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19(03):24.
作者簡介:趙凡菲(1997.11-),女,漢族,遼寧葫蘆島人,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勞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