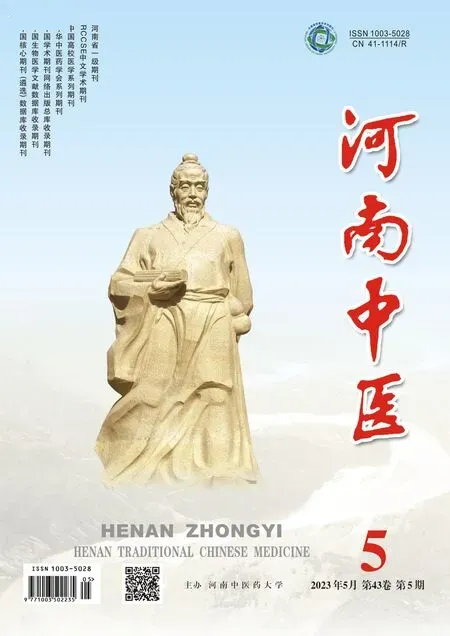基于網絡藥理學和分子對接探討大黃-黃芪藥對防治糖尿病腎病的作用機制*
王曉斐,吳深濤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381; 2.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糖尿病腎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常見的微血管并發癥之一[1],在我國成年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已達11.2%[2],其中約20%~40%合并有DKD[3]。DKD發病機制復雜,臨床癥狀及并發癥繁多,病程遷延日久,預后不良,已成為慢性腎臟病和終末期腎病的主要病因,嚴重危害人類健康[4-5]。現代醫學針對DKD常需明確病因和病理診斷,早期予降糖、降壓等治療延緩其進展,后期采取透析或腎移植,但都存有一定局限性[6]。中醫藥防治DKD方法眾多,對改善臨床癥狀、減少并發癥發生、延緩疾病進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醫學中并沒有“糖尿病腎病”的明確記錄,常依據其臨床癥狀、演變及預后的規律歸為“腎消”“尿濁”“水腫”等范疇,現代醫家將其中醫病名確定為“消渴病腎病”,認為其核心病機為本虛標實,虛者臟腑氣血陰陽皆虛,實者氣、血、痰、濕、濁、毒等邪氣內停機體。據統計,治療DKD的中藥專利復方中大黃與黃芪配伍頻次最高[7],大黃、黃芪作為治療DKD的代表藥對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實踐中,大黃瀉下解毒、逐瘀通經,黃芪補氣托毒、升陽利水,二者相須為用,療效顯著,且副作用小、安全性高。但中藥有效成分多樣,作用于人體和防治DKD的機制復雜,仍需進一步探究。網絡藥理學為研究藥物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提供方法,可預測中藥防治疾病的潛在靶點和機制[8]。故本研究借助網絡藥理學預測大黃-黃芪藥對預防或治療DKD的成分和靶點,并進行生物信息學分析,為后續分子機制研究及臨床應用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大黃-黃芪有效成分及靶點篩選在中藥系統藥理學數據庫與分析平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platform,TCMSP,https://old.tcmsp-e.com/tcmsp.php)中檢索“大黃”“黃芪”,獲知所含主要化合物成分,依據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OB)≥30%和類藥性指數(drug-likeness,DL)≥0.18進行篩選,得到其有效成分及其靶點蛋白[9]。通過Uniprot數據庫(https://www.uniprot.org/)對靶點蛋白進行標準化處理[10],最后用Excel梳理去重,構建大黃-黃芪的“藥物-成分-靶點”數據庫。
1.2 DKD疾病基因靶點篩選綜合GeneCards(https://www.genecards.org/)、Drugbank(https://go.drugbank.com/)、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數據庫(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OMIM,https://omim.org/)[10],檢索關鍵詞為“Diabetic kidney disease”,以物種“Homo sapiens”為篩選條件,篩選實驗研究驗證的與DKD相關的疾病基因,匯總并去重后得到疾病靶點數據庫。
1.3 交集靶點篩選及“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網絡構建利用Venny2.1.0軟件將篩選得到的有效成分相關靶點和疾病靶點取交集,并繪制韋恩圖。通過Cytoscape3.9.1軟件,構建“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可視化網絡圖,并對其進行網絡拓撲分析篩選關鍵成分。
1.4 蛋白質互作網絡(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PPI)構建與核心靶點篩選PPI可將靶點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可視化,直觀表達各靶點在DKD防治中的相互作用。將交集靶點輸入String數據庫(https://www.string-db.org/),限定物種為“Homo Sapiens”,交互可信度設置為0.7,獲取PPI網絡關系。利用Cytoscape 3.9.1軟件網絡拓撲分析插件CytoNCA篩選得到核心靶點。
1.5 基因本體(gene ontology,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與基因組百科全書(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信號通路富集分析運用R語言軟件對交集靶點進行GO富集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R3.6.3軟件安裝并引用Biocmanager、clusterProfiler、ggplot2、Pathview等程序包,首先將基因Symbol轉化為基因ID,選擇物種為人(Homospanies),設定閾值為P≤0.05且Q≤0.05[11],進行GO-生物學過程(biological process,BP)、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細胞組分(cellular component,CC)分析和KEGG信號通路富集分析,并繪制氣泡圖。
1.6 分子對接利用Atuodock軟件對關鍵成分和核心靶點進行分子對接。從TCMSP數據庫中獲得主要成分的結構文件,從PubChem(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數據庫下載核心靶點的三維結構,使用PyMol和Atuodocks軟件進行去水、去配體、加氫等預處理后對有效成分和核心靶點蛋白進行對接,以最低結合能作為分子對接的結果,使用PyMOL將對接結果可視化。
2 結果
2.1 大黃-黃芪藥對有效成分及作用靶點基于TCMSP檢索得到大黃-黃芪藥對有效成分27個,其中大黃10個、黃芪17個,見表1。27個有效成分對應225個作用靶點,其中黃芪218個、大黃71個。應用Uniport數據庫將靶點標準化處理,去重后得到有效成分作用靶點212個。

表1 大黃-黃芪藥對有效成分
2.2 DKD疾病基因靶點篩選基于GeneCards、Drugbank、OMIM數據庫,以“Diabetic kidney disease”為檢索關鍵詞,獲知DKD疾病基因靶點,去重后共計3 513個。
2.3 交集靶點及“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網絡取212個藥物靶點和3513個疾病靶點的交集,并利用 Venny2.1.0工具繪制韋恩圖,見圖1,得到有效成分靶點與疾病關聯靶點的交集靶點156個。利用Cytocsape軟件構建“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相互關聯網絡,網絡包含186個節點,561條邊,見圖2,圖中菱形代表DKD疾病,圓形代表有效成分,八邊形為中藥(綠色為大黃,橙色為黃芪),其余為交集靶點。網絡圖說明大黃-黃芪作用于DKD是多成分、多靶點起效的復雜過程。黃芪中的槲皮素、山柰酚、7-O-甲基異木糖醇、芒柄花素、異鼠李素及大黃中的蘆薈大黃素、β-谷甾醇是藥物活性成分中度值排名前7位的成分,可能在大黃-黃芪藥對防治DKD中起到關鍵作用。

圖1 大黃-黃芪有效成分靶點與DKD交集靶點韋恩圖

圖2 “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網絡圖
2.4 PPI網絡與核心靶點運用String數據庫獲取交集靶點的PPI網絡關系,通過Cytoscape軟件初步構建PPI可視化網絡圖。該PPI網絡圖包含有147個節點和1 090條邊。靶點節點按Degree值排列,Degree值越大,顏色越深,節點越大。根據連接度中心性(Degree)、中介度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BC)、緊密度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CC)值排序篩選大黃-黃芪治療DKD的核心靶點,得到腫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蛋白激酶B1(protein kinase B1,AKT1)、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 3,CASP3)、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1,MAPK1)、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IL-1β等,見圖3。

表2 核心蛋白拓撲參數

圖3 PPI網絡
2.5 GO和KEGG富集分析GO分析共富集到 2 752 條生物過程條目,包含生物過程2 512條,涉及對氧化應激、營養水平、脂多糖、細菌源分子、抗生素、金屬離子、類固醇激素的反應,細胞對藥物、氧化應激的反應,還有活性氧代謝過程等;分子功能168條,主要有蛋白質絲氨酸/蘇氨酸激酶、受體配體、DNA結合轉錄激活劑、內肽酶活性細胞因子、絲氨酸水解酶等活性,細胞因子受體、泛素樣蛋白連接酶、泛素蛋白連接酶、磷酸酶等結合以及RNA聚合酶II特異性等;細胞組分72條,主要有膜筏、膜區、囊泡腔、轉錄因子復合物、神經元細胞體等。分別選取條目前10位進行氣泡圖的繪制,如圖4。KEGG共富集到186條信號通路,按基因富集數排序并繪制前20條通路的氣泡圖,見圖5。交集基因主要富集于5類通路:①人類疾病通路:糖尿病并發癥的AGE-RAGE、液體剪切應力和動脈粥樣硬化、胰腺癌、內分泌抵抗等通路;②代謝通路:脂質和動脈粥樣硬化等通路;③細胞進程通路:細胞衰老、細胞凋亡等通路;④有機體系統通路:IL-17等通路;⑤環境信息處理通路:TNF、MAPK、磷脂酰肌醇 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s,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缺氧誘導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HIF-1)等信號通路。

圖4 GO富集分析

圖5 KEGG富集分析
2.6 分子對接將PPI分析得到的部分核心靶點與部分有效成分進行分子對接,獲知其結合能,結合能越低,表示結合能力越好,見表3。槲皮素與CASP3、IL-6,山柰酚與AKT1、IL-1β、IL-6,7-O-甲基異木糖醇與AKT1、CASP3、IL-1β、IL-6,β-谷甾醇與AKT1、IL-1β、CASP3、IL-6、TNF,蘆薈大黃素與AKT1、IL-1β、CASP3、IL-6、TNF的結合能均<5 kcal·mol-1,具有較好的結合能力。選擇分子對接最佳構象將其可視化,見圖6。

圖6 分子對接模式圖

表3 分子對接最低結合能 (kcal·mol-1)
3 討論
消渴日久及腎,正氣虛損,醫家對消渴病腎病認識多集中于本虛標實,虛則無法正常代謝運化致毒邪蓄積,且無力抗邪出體外,邪實進一步阻滯氣機、戕害人體,如此惡性循環、病無轉機。大黃、黃芪為治療消渴病腎病常用中藥,既可單獨起效,又具有異源同流、協同增效的作用,是消渴病腎病扶正祛邪、攻補兼施之治療原則的縮影,兩藥合用,升降相因,大黃瀉濁解毒,黃芪升清納精,可概括為固利相兼、祛粗取精,瀉而祛除糟粕使其無蓄積于體內而戧伐正氣,補而納攝精微使其留存體內而固護正氣。動物實驗研究證明,大黃、黃芪均具有調節糖脂代謝、抗炎及氧化應激、抗腎臟纖維化等作用,并且兩藥合用,事半功倍[12]。臨床研究證實,含大黃-黃芪藥對中藥復方可明顯改善DKD患者相關指標,延緩疾病向終末期腎病進展,提高患者生存質量[13]。
本研究首先構建了大黃-黃芪藥對治療DKD的調控網絡,其27個活性成分與156個DKD疾病靶點密切相關,可見該藥對發揮作用具有多成分、多靶點的特點。從“中藥-有效成分-交集靶點-DKD”網絡圖可知,黃芪中的槲皮素、山柰酚及大黃中的蘆薈大黃素、β-谷甾醇等藥物成分度值排名靠前,提示以上成分可能在大黃-黃芪藥對治療DKD中起關鍵作用。槲皮素可通過抑制氧化應激和TGF-β1/Smad信號通路,增加足細胞特異性標志物腎素和足細胞特異性標志物的表達,并降低足細胞損傷標志物desmin的表達,改善足細胞損傷[14]。山柰酚可降低腎臟TNF-α和IL-6的表達,通過介導Nrf-2/HO-1軸提高抗氧化能力[15]。蘆薈大黃素通過調控IRF4改善糖尿病腎病[16]。β-谷甾醇可改善血糖,調節脂代謝,進一步保護腎臟[17]。
有研究顯示,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在DKD的發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高血糖使得晚期糖基化終產物的逐步累積,進而腎細胞氧化損傷,細胞凋亡增加,炎癥隨之發生,腎小球和腎小管的生理功能受損,加速DKD進程[18]。GO分析中也可見生物學過程富集于對氧化應激的反應上。KEGG 富集結果顯示,大黃-黃芪藥對有效成分可能通過糖尿病并發癥的AGE-RAGE信號通路、MAPK、PI3K-AKT、HIF-1等信號通路發揮作用。AGE受體(RAGE)與其配體的結合可激活不同的細胞內信號通路,如PI3K/AKT、MAPK/ERK和NF-κB,促使大量炎癥因子(如 IL-6、VEGFA、TNF-α等)表達和釋放,引起腎組織中的氧化應激和慢性炎癥,最終導致腎功能喪失[19]。HIF-1α升高可增加結締組織生長因子CCN2的表達,進一步誘發炎癥及腎臟纖維化[20]。
PPI網絡分析顯示,TP53、AKT1、TNF、EGFR、IL-6、CASP3、RELA、MAPK1、VEGFA、IL-1β等靶點可能是大黃-黃芪藥對治療DKD的關鍵靶點。TNF、IL-6、VEGFA、EGFR、RELA等涉及炎癥反應[21],TP53、AKT1、MAPK1、CASP3等涉及細胞凋亡和細胞增殖[22-23]。IL-6被認為是慢性炎癥產生的關鍵基因,DKD患者高糖和晚期糖基化產物誘導腎小管上皮細胞表達,并分泌IL-6,使其在機體內水平明顯升高[24]。通過降低IL-1β、TNF、IL-6等炎性因子的表達,可抑制高糖介導的氧化應激反應,從而改善腎臟功能[25]。
大黃-黃芪藥對是長期DKD防治臨床實踐中的精華,用藥精少、療效顯著,前期已有大量的研究證實其可以有效延緩DKD患者腎功能惡化,本研究運用網絡藥理學探尋大黃-黃芪藥對治療DKD可能的作用機理發現,槲皮素、山柰酚、蘆薈大黃素等多成分可作用于 IL-6、IL-1β、VEGFA等多靶點,參與糖尿病并發癥的AGE-RAGE、PI3K-AKT、HIF-1等多信號通路,通過抗氧化應激、抗炎、改善足細胞損傷、抗纖維化等作用途徑治療DKD。本次網絡藥理學研究為大黃-黃芪藥對防治DKD的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其具體有效成分、作用靶點與詳細機制尚需進一步的實驗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