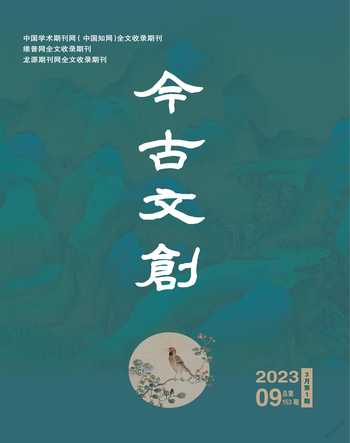簡論宋代愛國詞的發展軌跡
朱壯昳
【摘要】愛國主題歷來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主題之一。兩宋特殊的外部環境極大催發了詞人們的愛國心,愛國詞掀起了一陣陣的創作高潮。宋代愛國詞以北宋范仲淹《漁家傲》為起點,經歷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三個主要階段,直至宋亡仍綿延不絕。
【關鍵詞】宋代;愛國詞;風格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9-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13
一、宋代愛國詞的源流與誕生背景
宋代的愛國詞的發展大致以靖康之禍,宋室南渡為界,在這之前的北宋愛國詞數量極少,且從內容和情感上來看,也不及后來的南宋愛國詞,比起愛國詞,稱呼其為邊塞詞更為合適。
北宋滅亡后,趙構建立起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江南,不思光復故土外族威脅愈發嚴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人心中的愛國主義傳統被喚醒,涌現了一大群創作愛國詞的詞人,愛國詞在詞壇上開始崛起,并成為南宋詞壇不可忽視的重要題材。
我國古典文學的愛國主義傳統最早可以上溯到商周時期的《詩經》《楚辭》及史傳和諸子散文等先秦文學,《秦風無衣》是《詩經》中比較著名的愛國主義詩篇,楚辭的代表性作家屈原更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可見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人的優良創作傳統,每逢國家處于危難之際,愛國主義的傳統就促使文人大量創作反映愛國情懷的作品,為救國奔走呼號。
雖然詞誕生于花前月下,最初是為鶯歌燕舞,滿足人們的日常娛樂需要而產生,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文人加入詞的創作,詞人經歷的豐富多樣也促使詞的題材的日益豐富,愛國主題開始出現在詞的創作中正是詞的題材不斷擴充的表現之一。
因此,宋代愛國詞的出現既是文人不斷拓寬詞境的表現,同時也是愛國主義傳統始終流淌于我國古典文學長河的一個重要證據。
相較于唐代,宋朝自建立至滅亡始終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不曾有過開元盛世般的宏偉氣象,積貧積弱一直是宋王朝國力的代名詞,外加北宋與周邊的西夏、遼有連綿不斷的戰爭,局勢可謂空前嚴峻。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宋代的文人始終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對于邊疆戰事也多有關注,但礙于“詩莊詞媚”的傳統影響,詞中涉及時事、政治等嚴肅主題的較少,因此北宋的愛國詞從數量和內容上來看都不夠成熟。
然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禍對于宋朝是一個巨大轉折點,對于宋詞同樣是巨大轉折,國破家亡的悲慘讓許多文人將目光投向國家大事,國家的苦難激發了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并將這種熱情灌注于詩詞的創作中,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奔走呼號,要求朝廷出兵北伐,恢復中原。“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從這時起,愛國詞人和詞作大量出現并逐漸成為南宋詞壇不可忽視的一股創作力量。從這個角度來說,宋代愛國詞的發展始終是與國家命運綁定的,是應時代變遷和國力變化而生的一種作品題材。
二、北宋的邊塞愛國詞
據《全宋詞》和《全宋詞補輯》所收的作品來看,北宋詞人筆下的愛國詞數量極少,僅有十余首,僅占兩萬多首宋詞總數的千分之一 二。
而更嚴格地講,這些愛國詞更像是邊塞詞,其反映的多是邊塞生活和風光,借以表達自己報效祖國,建功立業的志向,愛國主題始終與邊塞主題相關聯,詞的愛國情感表達并不像后來的南宋愛國詞那么直接,富有爆發力。北宋最典型的以邊塞和愛國為題材的詞是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但風格與唐代的邊塞詩迥異,其中除了詩與詞在創作時情感表達的方式不同外,還與時代背景有所關聯。唐朝國力強盛,時代精神是充滿活力,蓬勃向上的,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邊塞詩派在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的鼓舞下筆調是積極進取的,詩歌中彌漫的是將士馳騁沙場,橫掃賊寇的樂觀精神,側面反映的是唐王朝國力的強盛和人民樂觀積極的精神。
而范仲淹的《漁家傲》寫于宋夏戰爭時期,宋軍苦戰日久卻勝少敗多,邊防吃緊,范仲淹對于戰事也不敢抱有樂觀的態度,《漁家傲》雖然意境也可謂壯闊,表現了戍邊將士的高度責任感和為國捐軀的精神,但落日、孤城、濁酒、白發、淚等一系列含有蕭瑟之意的意象以及“家萬里”“燕然未勒”這些帶有哀傷之意的用詞奠定了整首詞悲涼孤寂,清苦的感情基調,歐陽修評價其為“窮塞主之詞”,足見其筆調之蒼涼沉郁,而這與北宋王朝積貧積弱,外族威脅嚴重的時代背景有關。
除了范仲淹的《漁家傲》,后來蘇軾的《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里“西北望,射天狼”和賀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都是直接表現了邊塞戰事正緊,詞人渴望報效朝廷,蕩平賊寇的愛國志向。蘇軾和賀鑄雖不像范仲淹那樣親歷過邊塞戰事,目睹過邊塞風光,但他們的愛國詞也常常與邊塞戰事相聯系,借此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可以說,北宋的愛國詞始終是與邊塞這一主題相聯系的。而在時局上,北宋的“和約外交”雖然屈辱,與周邊的國家的摩擦不斷,但總體呈現穩定的狀態,統治集團和文人的生活并沒有因此大受影響,遠在和平地區的居民也感受不到戰爭的威脅,國家內部的安定使蘇軾和賀鑄等文人雖然有報國之志,但也只是停留在“馮唐不遇”的牢騷,并沒有進一步的生發,情感上沒有后來北宋滅亡后的愛國詞來的強烈濃郁。
三、南北宋之際的愛國情感
北宋末年宋金聯手滅遼,在消滅遼國的同時也將北宋的腐敗和宋軍的孱弱暴露在金人面前。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軍南下攻陷北宋首府東京,俘虜徽、欽二帝,將東京城洗劫一空后北歸,北宋滅亡,趙構南渡,即位為高宗,建立南宋小朝廷,自此偏安一隅。靖康之禍使文人們終于親身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國事劇變,國家和個人的命運如浮萍飄忽不定,在心中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此時具有強烈愛國情感和漢民族情懷的詞人,在國難當頭和民族危亡之際紛紛以高昂的姿態高歌抗金和北伐之曲,愛國詞派從此成為南宋詞壇的一大主旋律。
四、南宋愛國詞的流變
南宋初期的愛國詞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張抗金的將帥之臣,如李綱、趙鼎、胡銓、岳飛等,他們或居廟堂之高,或作戰在戰爭最前線,對于抗金大業和國家興亡有最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愛國詞在氣勢上也是最磅礴豪邁的。李綱的愛國詞借古諷今,激勵君王親征,反對投降逃竄之舉,《水龍吟太宗臨渭上》和《水龍吟光武戰昆陽》都是借前代帝王親征之事來勸說高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從而推動抗金事業,其抗金詞多表達抵御外辱、復仇雪恥的決心,氣勢豪邁。趙鼎詞則多思念故國山河,感情沉郁,多憤慨之情。
岳飛的詞作數量雖不及以上兩位,但得益于其長期在前線與金人作戰的經歷,目睹過金人對故國的殘虐暴行,他的愛國詞感情更為深沉激昂,除了有堅決收復中原故土、復仇雪恥的愛國熱情外,更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豪情壯志和決心,“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夸張的手法表達了對兇橫敵人的憤恨之情,同時也表現了作者發誓光復中原故土的堅定信念和大無畏精神,其“壯志”二句把收復山河的宏愿和艱苦的征戰融合在一起,以一種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來,使這首詞在抒發愛國熱情之余又催人奮發圖強。
相較于將帥之臣愛國詞的熱烈豪邁,那些不曾有機會觸及軍國大事的文人的愛國詞則從另一個角度抒發了故國之思和愛國之情。他們大多生長在北宋,因靖康之禍而被迫南渡,前后境遇的巨大落差使得他們在感嘆人生無常的同時又飽含故國之思,并將其轉化為抗金北伐,光復故土的愛國情懷。一些婉約派詞人雖不曾大聲疾呼抗金救亡之音,但他們的詞風也一轉之前的溫婉綿柔,他們的詞因傷于國事,也在潛移默化中沾染了時代的風云色彩,例如葉夢得、朱敦儒、李清照等,向子諲將他的《酒邊詞》以南渡為界分為《江北舊詞》和《江南新詞》,變清新風流為山河之哀的悲涼,足見宋室南渡對文人創作情感的影響之深。
比起婉約派詞人,張元干和張孝祥可以說是南宋早期最有影響力的愛國詞人,張元干的詞長于抒發愛國抗金的激憤之情,代表作兩首《賀新郎》,其中“曳杖危樓去”寄李綱,大力支持其抗金事業,表達自己渴望報效國家的鴻鵠之志和報國無門的感嘆。“夢繞神州路”寄胡銓,為因堅持抗金戰略而遭秦檜排擠迫害的胡銓打抱不平,字里行間表露了對金人入侵的憤怒和對投降派的憤慨。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強烈抒發了恢復華夏故土的迫切愿望和壯志難酬的哀號,痛斥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茍且偷生,不思進取的懦弱行為,陳霆《渚山堂詞話》載“張安國在沿江帥幕。一日預宴,賦《六州歌頭》云歌罷,魏公流涕而起,掩袂而入。”可見其感人之深。二張的愛國詞雖然礙于經歷所限,不似岳飛般慷慨淋漓,但同樣境界廣闊,感情深沉而濃郁,風格豪邁,成為后來以辛棄疾為代表的愛國詞人之先導。
推動南宋愛國詞到達巔峰的是辛棄疾的愛國詞。辛棄疾出生北地,歷盡艱險回歸南宋,多次要求帶兵北伐,收復中原,但礙于主和派阻撓,壯志始終難酬,最終抱憾病逝。辛棄疾的愛國詞慷慨激昂,熱情奔放,風格多樣,以豪放為主的同時又不拘一格,沉郁、清新、明快、奮揚兼而有之,拓寬了愛國詞的風格限制。他雖是一介文人,但武藝超群,也曾親身經歷過戰爭,因此他的愛國詞中除了有文人之思外也有一股武人之勇,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就形象地描繪了士兵在戰場作戰的豪邁氣和自己的沙場生涯,這是未經歷過前線戰爭的文人不曾具有的感觸。辛棄疾繼承了蘇軾的豪邁詞風和南宋初期愛國詞人的傳統,并進一步擴大詞境,將軍旅之事,沙場之情融入詞作,在他的筆下無事無意不可入詞,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同時也將愛國詞的表現力推向了新的高度,開辛派詞人之先河。
以辛棄疾為中心聚集了一批受辛棄疾影響的文人,其成員主要有稍長于辛棄疾的韓元吉、陸游,同輩的陳亮、后起的劉過、劉克莊、戴復古、岳珂等,他們繼承辛棄疾愛國詞作的特色意象壯美,風格豪邁,情感上慷慨悲涼,在辛棄疾影響下用詞來抒發愛國情感,表達收復故土的豪情壯志,其中不乏名作,如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陳亮登多景樓,觀察山川地勢,借此激勵孝宗憑借京口之利,長江之險,征募將士,北上收復中原,實現國家統一,詞作中洋溢著作家的愛國之情和積極奮進精神,與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如劉克莊《沁園春答九華葉賢良》上片回憶壯年時征戰沙場的豪情壯志,下片敘述今日無門請纓,報國無門的憤慨,筆力矯健,情調悲涼,頗有稼軒之風。這些聚集在辛棄疾周圍的詞人大多也抱有收復故國的壯志,但因時局所迫而報國無門,心中有所郁結,因此他們的愛國詞基調也大多呈現出悲涼蕭瑟,惆悵憤慨之情,他們的愛國思想雖然與辛棄疾相同,也以抗敵愛國、感懷時事為主要創作內容,但題材不如辛詞廣,風格也不如辛詞豐富,且直率稍過,不如辛詞蘊藉可誦。
南宋中期,隨著“隆興和議”的逐漸穩定,以及同時期的金朝在金世宗的治下出現“大定之治”,兩國戰事減少,宋廷也找不到邊釁可作為破壞和約和北伐的借口,加之朝中主和派主政,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文人的抗戰熱情逐漸被消磨殆盡,鶯歌燕舞、奢侈享樂的風氣再一次占據上風,以姜夔、吳文英為代表的風雅詞派興起,雖然姜夔也有如《揚州慢淮左名都》這樣反映戰爭殘酷,控訴金朝統治者發動侵略戰爭為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譴責南宋統治者偏安政策的作品,但終究不是其詞作的主題,情感上也比愛國詞人的詞作要淡的多,更多的是表達戰爭所帶來的黍離之悲。
然而在風雅詞主導南宋詞壇時,愛國詞并未就此落寞,劉克莊、陳經國、吳淵、黃機等愛國詞人仍繼承了辛派詞的愛國傳統,以豪邁雄壯,風格沉郁的稼軒體,抒發其憂國傷時的情感和渴望早日完成恢復大業的愿望,雖然這些詞人大多地位低下,但他們以“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精神堅持創作愛國詞,從而使這個時期的愛國詞仍能在南宋詞壇占據一席之地。
南宋末期宋軍在與蒙軍聯合滅金后,蒙古軍隊旋即將矛頭對準了南宋朝廷,在蒙古的鐵蹄下,南宋國土快速淪陷,國家已然是風中殘燭,太平的泡影終究斷滅,在國家處于危急存亡之秋時,文人的愛國心再次被喚醒,愛國詞的創作再次迎來高潮。
不同于南北宋之交的愛國詞,宋末愛國詞的國土淪亡之悲更加濃重,而收復故土的壯氣則淡了很多,或許是在絕對的軍事實力差距下文人們看不到恢復中原的希望,因而專注于抒發故土之思。雖然不乏文天祥這樣的烈士詞人,但更多的文人選擇了隱居不仕,例如劉辰翁、汪元量、蔣捷等,他們選擇成為南宋遺民,繼續以凄婉哀傷的筆調訴說自己的故國山河之慟,因而比起南北宋之交的愛國詞在情感上更為掩抑凄涼。
宋代的愛國詞以范仲淹《漁家傲》為起點,至宋亡而不絕。其內涵與情感經過百年戰爭的洗禮而愈發豐富,無論是婉約派還是豪放派詞人,都以自己的風格描寫山河之慟和愛國之情,宋代愛國詞人以其凜然不可侵的正氣,對故國鄉土的深沉愛戀,譜寫出一首又一首撥人心弦的愛國詞,并對后代,尤其是清朝末年的愛國主義詩詞產生了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唐圭璋編.全宋詞[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3]陳霆.渚山堂詞話[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陶爾夫,諸葛憶兵.北宋詞史[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
[5]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