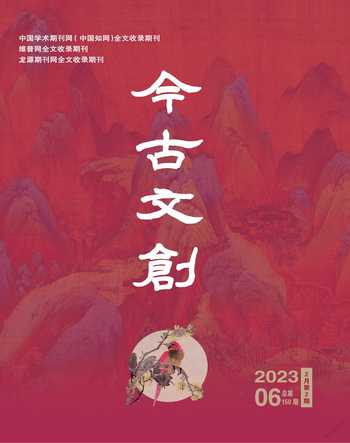審美形塑下的酷兒形象
【摘要】 薩拉·沃特斯是英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家,縱觀她的文學創作過程可以發現同性戀主題始終貫穿其中,以此為基調,沃特斯創作了一系列女性酷兒形象,這些形象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展現出獨特的美學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因此在審美形塑的視野下,以沃特斯筆下的酷兒主題小說《荊棘之城》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分析作家筆下的酷兒形象,進一步挖掘酷兒形象的美學特征,理解作者要表達的女性主義,也可以進一步推進對薩拉·沃特斯的研究。
【關鍵詞】薩拉·沃特斯;酷兒理論;女性形象
【中圖分類號】I561?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6-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6.003
“酷兒”一詞是對“queer”的音譯,它的本意是怪異,指具有怪異傾向的一類人群,“從廣泛意義上來說,‘酷兒是各種性少數人群的代稱,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者和跨性別者。”①薩拉·沃特斯是當代英國文壇備受矚目的一位女作家,作為一名女同性戀者,她結合自己的體驗創作了一系列以維多利亞時代為背景的女同性戀小說,從1998年開始,沃特斯陸續出版了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小說《輕舔絲絨》 (1998)、《靈契》(1999)和《荊棘之城》(2002),這三部小說均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倫敦為背景,因此被稱為“維多利亞三部曲”。這些作品關注到女同性戀這一邊緣群體,通過女性酷兒在男性社會中的一系列經歷傳達出被壓抑的女性體驗,呈現了女同群體長期存在的身份認同困境。因此薩拉的作品強調了一種酷兒體驗,在跨越性取向的書寫過程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酷兒形象,這些女性酷兒形象一方面受到男性審美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薩拉對女性的審美期望,具有獨特的美學意義。而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在女性身份構建的嘗試上,最后一部《荊棘之城》都比另兩部更加成熟。
《荊棘之城》圍繞瑞佛斯的三場騙局展開。在荊棘山莊教貴族小姐莫德畫畫的瑞佛斯聽說莫德有一筆不菲的嫁妝,因此他找到了盜竊團伙里的蘇聯合騙婚,企圖婚后將莫德關進瘋人院以霸占財產,這是騙局一;但莫德長期被舅舅驅使閱讀色情書籍,對男女之情厭惡至極,因此瑞佛斯意識到莫德根本不會被騙,于是改而和莫德聯手,企圖讓蘇代替莫德進入瘋人院換取莫德的自由,這是騙局二;但誰也沒有想到莫德和蘇在相處過程中產生了感情,兩人袒露內心互相合作,雙雙逃離禁錮,最終成功地擺脫瑞佛斯并重回莊園開始新的生活,這是騙局三。圍繞這一主線,薩拉塑造了莫德和蘇這樣兩位女性酷兒形象。
一、男性審美造就的“淑女”外觀
《荊棘之城》中對女性酷兒形象的塑造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對男性審美要求下的女性外觀的描寫,主要從女性由服裝裝飾而成的外觀這一角度展開。小說中出現了大量對維多利亞時期女性服裝的描寫,“服飾,表面上是人體的附加物,但實則遠不如此。它本身既內隱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又完全以外顯形式表現出來” ②,在《荊棘之城》中,作者極大地還原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風貌,將男性對女性的審美要求賦予在服飾層面上,因此在這里服飾超越了單純的美化外觀的作用,體現出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在《荊棘之城》中,女主角莫德的服飾具有更深層的文化意味,傳達出男性社會對女性身體以及精神的壓抑。
小說將背景設置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那時女性無法實現經濟獨立,完全依附男性生存,當時著名的性學家威廉·阿克頓就提出高尚、完美的女性必須天真、純潔、順從,是家中的天使這樣的觀點。在這樣的審美要求之下,女性被要求按照男性的審美期望成為“淑女”,身體塑形正是手段之一。維多利亞時期,繁復、華麗成了女性服飾的特色之一,女性服飾中大量運用蕾絲、蝴蝶結、荷葉邊等元素,并使用魚骨束腰緊勒腰部,在剪裁上也追求盡可能地突出女性身體的曲線美,這樣的服飾風格旨在創造完美的女性形象,但是它們在裝飾女性的同時也限制她們的行動、損害女性的健康,當女性必須依賴女仆才能穿上她那華美的衣裙時,就很難獨立完成任何事了。這種服飾特點將女性禁錮成為柔弱纖細、必須依賴男性的個體,將女性培養成為符合男性審美要求的“淑女”,其實質是男性對女性審美期望的體現。薩拉·沃特斯真實再現了那一時期的社會風貌,更是將女性的服飾作為塑造女性形象、體現女性困境的重要工具來處理,因此在《荊棘之城》中服裝成為男性社會禁錮女性的重要意象。小說中多次出現了對莫德這位貴族小姐的著裝描寫,不僅多次出現束腰、束裙等衣物,更是把手套作為囚禁莫德的男性權力的縮影進行描寫。
在《荊棘之城》中,年幼的莫德被舅舅的管家從寄養的瘋人院接到布萊爾莊園之后,立刻被要求按照舅舅李里先生的要求穿上符合男性審美的衣裙,當第一次穿上束腰時她感到痛苦萬分,“窄小的裙子勒著我,令我呼吸困難,靴子磨著腳踝,羊毛手套扎手”③,這是“淑女”的服裝帶給她的第一感受,華美的外表帶給內心極大的不適感。自此幼小的莫德必須每日穿著符合貴族小姐著裝要求的衣服,而且只要她因不適而扔掉手套,李里先生就會用珠串抽打她的手心來施加殘酷的懲罰,以要求她以后不再忘記。在舅舅長期的控制之下,莫德逐漸被馴化成了一名合格的“淑女”,不僅有窄窄的細腰、柔弱的外形,更成為完全符合男性審美要求的家中的“天使”,她嚴格按照舅舅的指示生活,從不離開莊園半步。小說就借蘇的視角向人們展示了莫德被男性審美所塑造的“淑女”外形:“她的束腹很長,上面有鐵質的骨架,而她的腰則細到病態;她的硬襯裙是以手表發條制成,襯裙和內衣則以白棉布制成……脫掉這些衣物的她,就像奶油一樣的柔軟光滑,也像一只脫去外殼的龍蝦。”這是莫德的外形。如果說纖細的窄腰是時代的審美要求,那么柔軟細嫩的手指就是舅舅的審美喜好,為了達到舅舅的審美要求,莫德從未取下過手套,她有幾十副不同材質的手套,一旦染上臟污便立刻更換,因此在時代和男性審美的共同塑造下,造就了莫德這樣一位具有柔弱外形的“淑女”。
沃特斯通過對莫德由服裝裝飾而成的外觀的描寫,塑造了一位維多利亞時期受到男性社會審美觀念影響的柔弱“淑女”形象,她外表纖細柔弱,完全依附于舅舅生存,如蘇所說,在衣裙堅硬的外殼下生活的莫德,像奶油也像失去了殼的龍蝦,柔弱而又敏感,這就是前期的莫德形象——一位被男性審美塑造的“淑女”。
沃特斯將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生存現狀通過女性服飾展現出來,因此服飾就不單單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的單一作用,而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女性被男性的審美要求塑造,以此體現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壓迫,進一步加強對男權社會的批判。
二、女性覺醒而來的“反叛”性格
《荊棘之城》中女性酷兒形象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她們性別意識覺醒之后而迸發出的反抗精神和反叛的性格。如上文所述,在沃特斯筆下,在男性社會中生活的女性酷兒們面臨著非常艱難的生存環境,莫德從幼年開始就面臨著來自舅舅的控制,她從小就被當作“圖書管理員”培養,整日接觸色情文學,被強迫閱讀并表演色情文學的內容,在遇到蘇之前,她一直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沒有生命的活力。而蘇是來自賊窩的女孩,在薩克斯比太太的保護下,蘇并沒有過多的遭受壓迫,她善良、坦率,直到卷入瑞佛斯的騙局。在第二個騙局之中瑞佛斯假扮蘇的丈夫將蘇關進精神病院之中,這意味著當時男性利用男性權力就能輕而易舉地控制女性的身體和精神世界。沃特斯在作品中讓女性受到來自男性和社會的操控和規訓,成為體現男性權威的工具。
從此可以發現,《荊棘之城》的女性酷兒面臨著來自男性和社會現實的壓迫,她們在性別意識覺醒之前嚴格按照社會的要求生活,可是兩個人的接觸卻觸發了彼此的生命的熱情,“所有的事情都變了”,因此她們對壓迫她們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激烈的反抗,成了積極的反抗者。相較于“三部曲”中的另外兩部,《荊棘之城》中的莫德與蘇的反抗更為激烈,她們都經過了“被塑造——解構塑造——重建自我” ④的過程,最終實現了對自我身份的建構,因此,莫德和蘇的戀情不僅是對自我的重新發現,同時也是對壓抑、扭曲的社會進行的反抗,在一次次的反抗過程中,她們展現出了強烈的反叛精神,給女性酷兒形象增添了一抹亮色。
她們的“反叛”性格集中體現在她們的反抗過程中。莫德的反抗首先體現在對荊棘山莊的逃離,在瑞佛斯的陰謀中,她與瑞佛斯一起逃出荊棘山莊并把蘇當作替代品送進瘋人院,就是為了換取自由,盡管這一陰謀因陷害蘇而存在道德的瑕疵,但為了擺脫生存的困境她義無反顧地做了,她希望逃出山莊之后在倫敦找到自由,過沒有書本也沒有束縛的生活。對荊棘山莊的逃離,喻示著她對于禁閉性的權力空間的逾越,在逃離之前莫德銷毀了一直殘害她的色情讀物,這是全文最具爆發性的一幕,莫德用刀具劃破她每日閱讀的色情書籍,當她劃破紙張時仿佛聽到書頁傳來嘆息之聲,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對長期受控制的自我的釋放,也是對所有被男性禁錮的女性的救贖,莫德的這一行為象征著她們這一類邊緣女性對男性中心話語權的解構,迸發出激烈的反叛精神。但是僅僅逃離禁錮她的山莊是沒有用的,逃離山莊之后莫德馬上陷入了更大的陰謀,陷入了另一重的控制之中,薩比克斯太太將她囚禁在小房子里,這就意味著莫德的反抗并沒有完全成功,因此她開始勇敢地嘗試“工作賺錢”,通過獲取經濟獨立來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在小說結尾,莫德與蘇回到山莊成了山莊的主人,走上了一條非同尋常的謀生之路——創作色情小說,至此莫德從當初依附于舅舅的色情朗讀工具轉變成了依靠寫作色情文學為生的創作者,成為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從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束縛中解脫出來。由此可以發現,莫德這位“淑女”不僅勇于向父權制社會和男性文化發起挑戰,更積極地追求女性自身的獨立性。
蘇的反叛從一開始就具有合理性,和莫德這位貴族小姐不同,蘇自小生活在賊窩,加上薩科比斯太太的保護,獨特的生活環境使蘇具有坦率、天真的性格,如果說莫德代表被壓抑的生命力,那么蘇則代表著女性原生的生命激情,因此當她被瑞佛斯關進瘋人院之后就開始嘗試逃離這里,她大吵大鬧試圖向醫生論證自己并不是莫德,但卻被認為她具有精神問題,她嘗試用各種方法逃離這里,最終在荊棘山莊一位仆人的幫助下成功逃離了這里,和莫德匯合。因此莫德和蘇這兩位女性酷兒在女性意識覺醒之后迸發出強烈的女性生命力,表現出堅定、勇敢的一面,這種“反叛”現實的精神為她們增添了光輝的一筆,實際體現了作者對于女性酷兒的審美期望——同壓迫女性的男權社會進行積極的反抗。
三、不斷升華的道德意識
沃特斯從“淑女”外觀和“反叛”性格兩方面塑造了兩位女性酷兒形象,在此過程中她們不斷升華的道德意識一直復合其中。沃特斯在人物的設置上賦予了人物不同的道德內涵,和以往的女性形象不同,她們都不是道德上的完美者,但又不是徹頭徹尾的妖婦,傳統文學中“天使—妖婦”單一模式的女性形象已經不能概括沃特斯筆下的女性酷兒形象,在道德層面上她們都具有瑕疵,因此她們不再是男性期望的家中的“天使”,但她們也絕不是道德徹底敗壞的“妖婦”,在對自我認知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她們的道德品質不斷升華。通過道德規范和不同人物在不同時期的道德選擇之間的沖突,沃特斯將莫德和蘇道德完善過程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也讓這兩位女性酷兒的形象更加飽滿,充滿人性的光輝。
莫德和蘇在最初都具有道德上的瑕疵,她們因各自的目的卷入了瑞佛斯的騙局之中。蘇原本無意加入這場騙婚,但是在金錢和完成薩科比斯太太任務的雙重誘惑之下,她無奈答應,隨著情節的發展,蘇意識到莫德是個“好女孩”,但是為了完成養母薩科比斯太太的任務,也為了真正完成一件事給薩科比斯太太看看,盡管在此過程中她常常受到內心的譴責,她依舊按照計劃對莫德進行欺騙。莫德同樣如此,她與瑞佛斯合謀將蘇關進瘋人院頂替自己,一開始也是出于為自己換取自由的目的,盡管需要犧牲另一個無辜的女孩。她們二人各自懷有不同的目的,做出了不同的道德選擇。但是她們又并非徹底的無情者,蘇并沒有完全被金錢蒙蔽雙眼,她從最初就認為瑞佛斯的計劃是一個殘酷又卑鄙的詭計,只是出于向薩比克斯太太證明自己能力的想法參與到這次騙局當中。莫德在實施自己的計劃后也并沒有為自己逃離山莊而感到如釋重負,當她配合瑞佛斯將蘇送進瘋人院時,她感到“心都碎了”,隨之陷入了內心的煎熬,因此她決定離開倫敦,甚至不惜回到荊棘山莊,也要找到蘇,而蘇在明白一切真相后,也放下曾經的仇恨逐漸諒解了莫德,并重新踏上尋找莫德的道路。在作品中,莫德和蘇在這樣一場驚天大陰謀的洗禮中歷經種種磨難,逐漸從天真變得成熟,二人原先受遮蔽的道德意識逐漸掙脫束縛,不斷升華。
沃特斯通過不同視角的敘述將莫德與蘇的道德瑕疵呈現給讀者,讓她們在內心的矛盾與沖突中經歷道德的歷練,最終實現人性的復歸,小說結尾,蘇用寬容代替了背叛和仇恨,莫德也回到禁錮她的荊棘山莊從事創作,用文字表達對蘇的情感、抒寫自己的心聲,完成了對自身的道德救贖。正是她們道德意識不斷升華的過程,使沃特斯筆下的兩位女性形象變得真正立體、生動起來,富有更迷人的魅力。
總的來說,《荊棘之城》中薩拉·沃特斯塑造了維多利亞時期兩位受到父權文化禁錮和壓抑的女性形象,她們在男性社會中沒有個體獨立性,在物質和精神上都受到禁錮和壓迫,但是她們沒有甘于成長為符合男性審美的“天使”,而是勇于反抗,敢于向社會禁忌挑戰,努力擺脫社會的壓迫并積極構建自身的主體性,在性格中展現出堅強、勇敢、自立的一面,成為具有主體獨立意識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沃特斯筆下的女性形象超越了傳統文學中女性非天使即妖婦的單一形象特點,她們都存在道德的瑕疵,但在此過程中,她們在內心沖突中不斷完善、升華自身的道德意識,使這一形象展現出獨特的光彩。
注釋:
①鄒楊蘭:《酷兒理論視角下身體符號在當代藝術中的應用研究》,四川美術學院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
②郭珊珊:《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中上層婦女時尚文化研究》,云南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
③薩拉·沃特斯著,林玉葳譯:《荊棘之城》,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④張澎樹:《論〈荊棘之城〉對“閣樓上的瘋女人”模式的解構和重寫》,《新鄉學院學報》2020年第10期。
參考文獻:
[1]鄒楊蘭.酷兒理論視角下身體符號在當代藝術中的應用研究[D].四川美術學院,2021.
[2]郭珊珊.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中上層婦女時尚文化研究[D].云南大學,2016.
[3]薩拉·沃特斯.荊棘之城[M].林玉葳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
[4]張澎樹.論《荊棘之城》對“閣樓上的瘋女人”模式的解構與重寫[J].新鄉學院學報,2020,37(10).
作者簡介:
張強慧,女,漢族,山東臨沂人,山西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