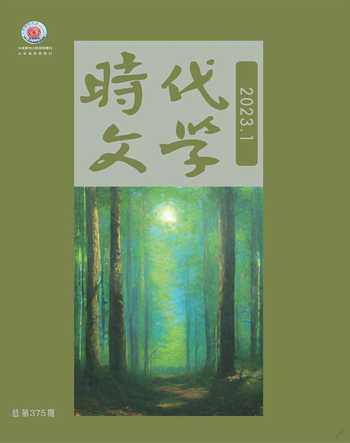印象記:高山流水
侯健飛
1
人之一生,如朝陽東升而西落,不過半日之功,生命之寶貴,無與倫比。因而不論達官富賈,亦不論販夫走卒,于人世間留下足跡,層層疊加,千年萬載,終會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之標記與范本。這標記范本之流傳,在遠古或結繩記事,或龜甲刻文。到了文明時代,藝術誕生——圖文影視,音樂之聲……藝術把光明和美好之人生故事,匯集成滾滾洪流,滋潤大地,影響世界;而作家作品,當然不獨作家作品,不論名頭大小,不論作品高下,乃歷史洪流中一股藝術清泉,晝夜奔流。
李一鳴先生,文藝批評家、散文作家,自喻中國作家“服務生”。
2
辛卯年五月(2012年6月),首都北京。春夏之交,鵝黃柳綠,天地祥和。中國作家協會向社會公開招錄魯迅文學院副院長。霎時,如鼓擊春雷,文壇矚目,蓋因魯迅文學院名聲太大,高山仰止。
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簡稱“魯院”,與昔日“魯藝”血脈相連,又難分伯仲,乃當今公認之文學圣殿、作家搖籃。副院長,職位特殊,不可小覷。出人意料,先生之名出現于報考名單之中,其職為山東濱州醫學院副院長。
筆試、面試、考察,結果令人驚愕,名不見經傳者,卻一鳴驚人。
有問,試題難否?或言不難,然考生若對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生態和作家作品缺乏把握與洞察,蓋試題之難,足可令人戛然止步。
彼時,先生業已擔任近12年副廳級領導職務,連續數年被省委組織部考核優秀……
當年十一月,先生接到中央組織部調令,不日從山東啟程,赴京履職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副院長。
先生就職演說,題目大意:被選擇之神圣與光榮。一千五百言,四個關鍵詞統領全文:學習、團結、盡責、為人。
后有同道著文稱:此乃一次非同尋常之招錄。中國作協黨組以寬廣之視野、博大之胸懷,于眾多精英中選擇了先生……
3
先生就職魯院,如雄鹿失群,地遠人生,一切從頭開始,其言其行,無不引人注目。此乃人之常情,自古皆然,不以為怪。然圣人云:行腳至此,必有來路,必有因緣。先生自山東入京,若問何也,不過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此器奇也不奇,文學理想及人生追求而已。
先生甲辰年十月(1965年11月),生于山東博興縣。博興地處魯北平原,黃河下游南岸,西南臨淄博,東望入海口,北倚濱州城。
先生15歲首次公開發表作品。其文學啟蒙,與大多受惠鄉下艱苦生活之饋贈者并無二致。幼年貧苦,塑其性敏感而早熟。彼時其父工作于遼寧煤礦,父子離多聚少。年假探親,其父總不忘帶回小量畫書。此舉在閉塞鄉村,并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屬另類。如此稀少之文藝讀物,成為先生精神食糧,亦成為先生瞭望外部世界之窗口。一顆向往文藝之種子,從此在心田埋下。小學三年級,首篇作文即獲老師贊賞。當眾宣讀,對懵懂少年來說,意義非凡!此事最大之意義,乃促成先生對師者責任之認知。
啟蒙如迷途旅人找到大路,雖則路途曲折漫長,但目標就在前方。關于啟蒙,不在早晚,因人而異,早可幼年,晚到而立。先生青年行旅最可贊譽者,乃不忘來路,走不多時,必定停下回望,思索一番,停一停,等一等,等到精神之靈與肉體完全融合。每提及此,先生總要無限感慨。及至近年,臺上臺下,先生常常引身為喻:啟蒙者,父母之勞、師尊之勞也。特殊境地,關鍵時刻,父母或師尊一言半語,足以影響晚輩之興趣愛好、職業選擇,甚至影響一生命運,所以,為人父人母,為人師者,不可不察矣。
讀初中,先生語文成績卓爾不群,曾在學校作文比賽中獲頭獎,其作常被抄寫于教室外黑板之上。高中就讀,始迷古體詩詞,曾寫詩作:揮筆墨幻黃浦江/擱管跡潛未名湖/李賀神馳化名詩/太白情逸夢花雨。詩言志,此詩乃青澀學子對北大、復旦之向往,詩借對李姓詩人之贊,道出自己于文學之癡迷與未來之志向。
后讀大學,先生放情游弋于書之海洋,激昂放歌于文學高岡。甲子年七月(1985年9月),山東省大學生文學創作評選,所作散文《串楊葉》獲頭獎散文榜首。以此勢頭,畢業作入高校執教中文之想,并非癡人說夢。然造化弄人,陰差陽錯,先生大學畢業,卻在醫學院落腳。先生卻坦言,一切自有道理。
眾所周知,政府各級、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最繁忙之部門,辦公室是也。先生任辦公室之職,忙亂辛勞之余,夜深人靜之后,文學星火被重新點燃。數不清之日月,先生用心靈去苦苦感受,默默追尋,陸續發表了《野地漫步聽黃昏》《禮拜》《婚期》《磕頭》《岳父的眼神》《產房門前》《我的理發館》等散文。部分佳作被《中國散文年選》《散文》《散文選刊》等選載。
歲至丁亥年八月(2007年9月),先生以教授身份,考取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有人不解:青年才俊,順風順水,安居樂業,博士并非雪中送炭,乃錦上添花而已,何必費心勞神!噫!社會百態,人生旅途,總有人醉,亦有人醒。先生有言:工作、家庭、上老下幼人人共有;盡責、盡孝、盡慈既是中華美德傳統,亦是做人標準,此理言多無益,然人有不同者,一求物質豐沛,生活安適;一求精神飽滿,學而勤思。精神何來?生活饋贈之外,讀學精研,一以貫之。有精神追求之人,閑暇讀書如饑似渴;夜深奮筆,不愿一刻緩停。西哲斯賓格勒言道:人,不唯生命本身,除擁有長度、寬度之外,更為重要者,乃擁有第三維度——深度,深度即人文維度。不言而喻,生命有長有短,生活面有寬有窄,然,靠人文維度生活之人,精神之滿足乃最大之滿足,理想之追求乃最好之追求。以文學世相而言,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看似相異,實則緊密交織,殊途同歸。中國乃至世界著名作家,之所以比常人站得高,看得遠,想得透,寫得精,極大程度得益于學養深,而語文、文理學研乃學養之基礎,更乃涵養人文情懷之渠道。學習又如登泰山極頂,只有眼界寬、思維深刻者,作品才可能富有穿透力。作家,也唯有清晰地建構其文學史框架,才更容易找到自身文學之定位、發展之方向。先生博士論文《中國現代游記散文整體性研究》出版,最終獲得冰心散文獎散文理論獎。導師王澤龍先生序評此著:從文化心理論與審美藝術論之視角,該論著初步建構了一個中國現代游記散文之研究系統。
戊子年四月(2009年5月),先生獲“首屆山東省十佳青年散文家”稱號,此時先生任濱州醫學院副院長已8年矣。
壬寅年七月(2022年8月),先生出版新作《在路上》。“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四輯,構成先生半生自傳,亦呈現半個世紀中國社會之變遷。一本書即可撥云見日,先生于當代文學,尤其散文創作,雖不致讀者德宏才羨,屢屢懷慕,卻也躬身力行,卓有貢獻。
4
常有學子問師:人生何為長久?師曰:人生無長久。乍聽悲觀,實則真理。人活百年者曰壽,百年之后終歸泥土,生命不存,何說長久!學子又問:人生至情如何?師曰:情重重情,可,然不可靠。夫妻反目、兄弟失和、父子成仇者比比皆是。
先生則言:人生有長久者——藝術也;人生至情——感恩、赤誠、愛,可信可靠。
至親以孝,孝以順先。先生祖居齊魯,家風純良,儒文化耳濡目染,孝行父母自始至終。然先生并不諱言,孝在祖德,上行才會下效。當年攜新婚妻子回鄉敬祖,正值春節,舉家歡騰。按鄉禮俗規,新婚夫婦要挨家給長輩下跪磕頭。先生少小離家,一路讀書入仕,接受文明教育,如今妻子在側,不免躊躇,但依規矩、尊鄉俗,年輕夫婦磕遍同宗同族,還到了鄰家百舍……
含辛茹苦,母子情深——那年秋天,先生十一二歲,其父工作在外,母親生病臥床,兄妹三人鳥兒般看著臉色蒼白、不能動彈的母親,先生心中升起一種莫名之感。更于多年之后,先生出差千里之外,終未能見上母親最后一面……關于母恩難報,先生言必哽咽。兄妹三人,童年困苦,母親頂天立地。先生20歲,足穿母親手做布鞋,初次落腳北京長安街。是夜,先生作詩《詩人》:媽媽也是詩人/她一針一線寫成的詩/被我發表在長安街上……
如今父母先后離世,先生常悵然若失。幸好兄妹在,先生為弟者,思而事兄;為兄者,關愛小妹。孝悌恭親,先生半生走不出故國文化目光。
從古至今,文人多閉談自家愛情婚姻。先生則異,朋友間,文章里,常以激昂明亮之聲調,贊美嬌妻愛子,誓愿把余生獻給所愛之人:“是的,這嬌小的女人將要成為我的妻子,她將和我手挽手走完一生。痛苦,歡樂,失敗,成功,將交替著在我們身邊盛開凋落,沒有什么可以再使我心灰意冷!當生命的黃昏來臨的時候,我們將攙扶著來到我們年輕時相戀的地方,彼此默默地回憶著過去,讓天邊的晚霞把我們的白發涂染,我們以深情的目光把愛情的時光一寸寸點燃!然后,我們會緊緊擁抱著快樂地死去,我們對自己的一生將了無遺憾!”
文短情長,多少人生況味!每讀至此,難抑百感交集。
先生事公,拼命三郎。幾十年如一日,盡職盡責,披荊斬棘;然對親人、愛人、友人則百轉柔情。如此忠義兩全者,世殊少見也。
前日,先生友人王兆勝君評先生新作《在路上》乃“逆旅中之心曲”。兆勝君言,先生散文,除將自己心曲彈奏給路人聽,還于逆旅中靜下心來,聽別人之心曲。尤其那些悲苦者、柔弱者之傾訴。此言不虛。先生常乘地鐵上下班,某日于地鐵入口處見一年輕母親坐地哺乳嬰兒,衣著不整,面帶愁容。先生立刻上前,噓寒問暖。先生言:“我看那母親,想到我母親;看那孩子,就像看到幼時的我。”先生體格健碩,面膛微黑,然其心思縝密、俠骨柔腸無人不曉。先哲有言:“吾亦攜家累,媼人誰可憐。”而先生絕非多愁善感,秉性使然。
通讀《在路上》,除謳歌歷史名人文天祥、蘇東坡、王懿榮之外,現實如岳父宋公,兒子李響,恩師王鳴亮,鄉鄰老寶、九奶奶,朋友清華,魯院學子朱珠、溫青、魚禾、張幸福等諸人,既無高官,也無顯貴。此等凡人小事,輕言細說,一一道來,但掩卷沉思,終各有其明亮溫暖在。
更有讀者言,先生最具思想之光、大愛之巔者,應推《蟋蟀》《禮拜》兩篇。前者一蟲乃見宇宙之大;后者尊重之下寓大愛大善于胸也。
5
人常言,高山流水,知音難覓,其實不然。王兆勝君評先生之作乃“逆旅中的心曲”,真知音也!一語道破先生為人、為官、為文之品行。兆勝君言此文在生命意義上,其實人之生命意義,就在不斷探索前行中,所有生靈都要經過逆旅,無論順遂還是坎坷。只是有人更喜歡寫人生歡歌,有人則陷入悲情,少有人能穿越成敗得失進入一個覺悟的空靈境界,而先生,恰成這少有之人。
10年履職中國作家協會,先生事必躬親、認人益處、予人可近、不食言信、赤誠待人。10年已過,先生之身影如天邊彩霞,吸引著眾多文人學子之目光——以其忠誠于信仰的品性踐行承諾,成為作家同仁們優秀之“服務生”。
6
李一鳴先生,吾師是也。雖為同齡,然師嚴道尊,不敢造次。吾生鄉野,南征北戰,不過一行伍人也。吾平日無他好,素喜讀史,才疏學淺,幸早悟人生三事,師親并重。
吾嘗言,讀史就是讀人。及年長,漸漸愛上散文,蓋因散文起筆收鋒皆有“恕”字在。恕乃將心比心,“用我心換你心”才是將心比心。人與人相交,唯心心相印才得長久,然這心心相印,必得有志同道合作之根——這志同道合,亦有如兩心之間一條汩汩而流之血管,不然哪得兩人之同心共振,哪得兩人之情感相融!行伍人平生重友,雖不敢奢望伯牙子期之緣,幸有可托生死之友。吾之知己有兩種,一種是日久生情,一種是一見如故,其實這兩種之根本并無不同,如果不是一樣之理想,一樣之德行,相近之學識,這“如故”何來?朋友如是,師生同此不悖。
壬辰年二月(2013年3月),吾以學子身與先生初識魯院,一見如故。自此先生竭人之忠,亦師亦友;我與先生情同手足,而先生予我尤多矣!
值次機會,恭祝師父師母安!
壬寅年(2022)于北京三鏡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