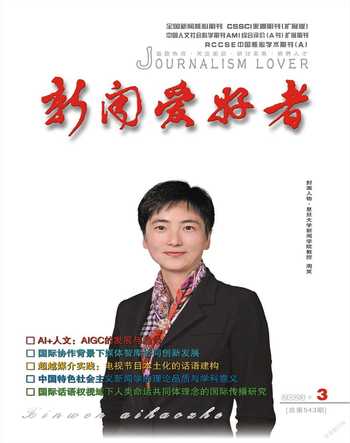自媒體平臺圖像傳播中的異化及倫理風險
符冰 強月新
【摘要】自媒體的興起使得圖像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然而用戶在使用自媒體圖像進行傳播的過程中卻出現了圖像審美的異化、社交表達與社交關系的異化,商業圖像傳播中的異化也越來越明顯。異化現象滲透在日常生活中,其深層影響不容忽視,它帶來的后果包括技術倫理的危機和自媒體信息傳播的信任危機等。通過建立技術倫理的規則與規范、對商業圖像傳播進行約束與管理、對個人圖像的審美進行社會化教育等措施,能夠逐步消解自媒體時代圖像傳播中的異化現象。
【關鍵詞】自媒體;異化;圖像審美;技術倫理
一、自媒體、圖像與異化
對自媒體的定義,可以追溯到謝音·波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在2003年撰寫的報告中提出的“We Media”一詞。二人將自媒體定義為:一個普通市民經過數字科技,與全球知識體系相聯結,提供并分享一種通過數字技術而獲得的知識,以及發表對于新聞等內容的個人觀點。[1]彼時以博客為代表的個人媒體開始在信息內容生產和傳播中漸漸呈現出不同于傳統的官方、權威媒體的模式及優勢,從而引起學者的關注。發展到今天,人與媒介已經密不可分:具身認知理論將人的認知和行為視作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開始強調人的身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信息發生機制以及表征作用。彭蘭在論及數字時代新聞業的變化時指出:在新聞價值的評價與賦予機制中,人—機互動日益深化。[2]這些驗證了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3]可以說,今天的媒介形態中,“自媒體”及其內容以其存在的無時空邊界性、碎片化、滲透性,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眾所周知,圖像從誕生開始,就是為觀看而存在。觀看的主體、觀看的介質、觀看的語境等都會影響觀看的結果。而當自媒體與圖像產生聯結之后,這種觀看變得無處不在,觀看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加深,觀看的介質和方式多元化,觀看變得日常化,圖像與觀者之間的關系隨之變化。
具體而言,從圖像的生產和傳播的維度看,在傳統媒體時代,圖像的生產和傳播在媒體和民間兩條線之間的界線較為分明。然而在自媒體時代,網絡技術和智能手機的發展給圖像的生產和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借助于自媒體,圖像的生產與傳播日益生活化、常態化,權威性被日益消解,圖像的生產無處不在,傳播也呈現出即時性的特點。
異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他指出了勞動的“異化”和“人的異化”:“(生產者)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在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中,勞動的這種現實化表現為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4]“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5]馬克思的“異化”著眼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剖析,旨在提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以往生產方式的不同,以及思考如何消除這種“異化”背后的剝削和不平等。此后的法蘭克福學派將異化理論“從生產和勞動領域引向科技、消費、文化、交往等領域”。[6]本文借用“異化”理論,意圖對自媒體圖像傳播中傳播主體、目的與圖像傳播的結果相分離的狀態進行分析。
二、自媒體時代圖像功能的異化表現
(一)個人在自媒體平臺圖像化傳播中的異化表現
首先是圖像審美的異化現象。當圖像被自媒體用戶用于個人化的表達時,人們逐漸陷入對于虛假圖像的集體化沉浸式滿足,從而呈現出大眾對于圖像審美的異化。這里的“異化”含義包括:一是原本更有利于忠實記錄現實的數字攝影技術,在技術的加持下竭盡全力致力于改變“現實”本來的樣貌;二是原本服務于個人表達的媒介最終實現的是“千人一面”的表達——當絕大多數的自拍都是濾鏡加持之后的“白、瘦、美”之后,審美趨同、表達單一,個體的特征和識別性已經被大幅減弱;三是傳播素養較低的個人用戶在獵奇心理和流量快感的刺激下,會不惜侵犯他人隱私甚至產生圖像暴力——2020年7月發生在浙江杭州的“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以及2021年11月發生的“外孫女與外公合影被造謠為‘老夫少妻”等事件即是如此。圖像審美的異化,帶來的是圖像倫理的異化,大眾不再在意圖像是否真實,逐漸適應了“非真實”并被非真實的圖像所裹挾,持續生產和傳播同一類型的圖像。
其次是自媒體平臺的圖像化社交表現出的社交介質的異化:如今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圖像在社交信息的傳達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表情包、截圖、自拍、景觀、食物等內容傳達著不同的情緒信息,代替著人們的文字表達。人們用數字技術處理后的自拍圖像、加了濾鏡的食物、景觀圖像,甚或盜取并加工而來的圖像等,可以塑造一種滿足自我期待或昭示自我“理想”社交形象的、自媒體化的“數字生活”;同時,在大眾將“非真實”的圖像當作“現實”而予以接納并成為習慣和依賴的狀態下,在社交場中就逐漸產生了對那些不經加工的、真實圖像的忽視、排斥或者非議。最終,在自媒體平臺,圖像作為社交的介質,作為塑造個人形象的重要媒介形式而存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圖像的作偽泛濫,并加劇了個人在自媒體表達中的異化傾向。
最后,標簽化的社交評價導致社交評價的異化:正因上述社交介質的自媒體化現象,人們會根據他人所展示的或不展示的圖像,對他人進行標簽化的評價,同時也被他人評價。自媒體賬號所呈現的圖像構成了特定的圖景,是被篩選和設計過的圖景,由于社交雙方的身體均不在場,所以導致人們會通過這一特定的圖景去給予社交評價,從而逐漸形成片面的、標簽化的社交評價。隨著自媒體對社交意愿的滿足,線下的交流越來越貧乏,線上的圖像構成的圖景成為彼此社交評價的依據,從而形成了社交評價的異化。
(二)自媒體平臺商業圖像傳播中的異化表現
自媒體平臺的商業傳播,幾乎是與自媒體平臺的成長同時開始的。在傳統媒體時代,圖像就一直在廣告信息的傳播中占據核心地位。然而傳統媒體的發行量和收視率都是廣告商自身無法控制的因素,媒體給予廣告圖像的版面空間和時間資源更是有限和昂貴的,相較之下,自媒體平臺卻給廣告傳播提供了一個自身可控、資源無限、代價相對低廉的時間和空間。因此商業廣告在自媒體平臺順勢而起,商業廣告的圖像傳播也逐漸在這一新的媒體平臺顯露出異化跡象。
其一,追逐流量和被流量追逐的圖像傳播。在自媒體時代,流量意味著注意力,注意力帶來經濟利益,而圖像是吸引注意力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圖像在商業表達中的功能逐漸成為獲取流量的手段,流量導向又反推了圖像的商業流量追逐,使得商業傳播中的圖像不再以服務信息傳播為核心,而是被流量捆綁的產物,圖像本身與圖像生產的目的相脫節。
其二,圖像與其所表征的實體分離的商業傳播。當自媒體平臺被用于商業形象的傳播,在商業形象的構建過程中,圖像與實體逐漸產生了分離:自媒體的“自”字背后的監管盲區,“媒體”屬性的傳播優勢,使得商品和品牌的傳播中,圖像與對應的實體之間常常不再是真實的對應關系。
其三,商業性質的個人圖像傳播的異化。商業性質的個人社交,指的是為了完成商業形象構建和商業性的溝通而產生的個人社交行為,如明星微博的內容發布與互動,其微博圖像傳播表面上與普通用戶的個人表達無差異,實質上往往是商業資本經過策劃、市場定位、扮演的方式產生的商業表達。
三、自媒體時代圖像功能的異化成因分析
(一)技術層面:技術便捷帶來的“低門檻”和技術應用價值的導向偏差
技術的便捷化帶來的圖像生產和發布的“低門檻”,是自媒體平臺圖像傳播異化的重要推手之一。正是智能手機終端在攝影功能上的不斷更新迭代以及手機應用軟件市場的發展,讓圖像生產徹底進入“低門檻”、遍在化的時代。而圖像的傳播則由于3G、4G、5G技術的快速發展,變得更加便利和快捷。當圖像成為隨時隨地可得的生產,大眾便基于各自的目的開始對其進行個人“改造”,強目的性的介入由此催生了圖像傳播的異化,異化反過來又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圖像傳播的異化加重。
技術應用的價值導向偏差導致了風險缺口。按照韋伯的工具(合)理性的觀點,圖像傳播的行動由追求功利性的動機所驅使,并追求傳播效果的最大化,背后是對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的漠視。在筆者看來,自媒體的圖像傳播以“潤物無聲”的方式、以滿足社交需求的“借口”改變了大眾對審美和自我的認知,使圖像審美朝著單一的方向而不是多元的方向前行。
(二)社會層面:公共教育、主流媒體、社會沉默的多因素促成
公共美育的缺失。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城市化進程,相對于很多領域的發展和進步,我國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目前仍存在不足,各省、市、縣美術館、圖書館的數量屈指可數,公共美育課程體系尚未成型和普及,一些相關部門缺乏美育意識。
傳統主流媒體在圖像傳播上對自媒體的妥協與跟風,使異化的圖像審美進一步成為主流。當自媒體通過單一風格和形式的圖像生產與傳播影響了大眾的圖像審美后,傳統媒體的圖像生產也開始妥協與跟風。2021年10月16日,中國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有人注意到,新華社在呈現航天員王亞平的個人照片時,對其進行了膚色更白、更亮的處理,更符合在自媒體當中個人形象傳播的大眾化趨勢。這種顯而易見的改變與趨同,可能意味著傳統媒體對自媒體圖像審美觀的認同或者妥協,也使得異化的圖像審美從自媒體擴大到了主流媒體,朝著社會共識的方向不斷前行。
圖像傳播中的沉默螺旋現象。隨著網絡傳播越來越呈現低齡化趨勢,圈層化的傳播、高活躍度、高網絡依賴度的年輕群體逐漸成為網絡用戶的主體,他們在網絡中的話語權不容忽視,而異化恰恰更多發生在低齡化的群體當中。在此壓力下,沉默的群體便產生了,他們雖不認同這種異化的圖像審美,卻不會用任何形式對抗和提出異議,從而使得審美的單一化更加明顯。
四、異化的倫理風險及其治理
(一)倫理風險:媒體信任危機與技術倫理危機
圖像功能的異化會帶來自媒體信息傳播的信任危機。在大眾的認知中,對自媒體傳播中的圖像進行美化或者技術處理似乎是個人行為,或社會默認的、普遍的行為,然而正是這種美化和技術處理會對媒體判斷中的信任程度形成沖擊,人們在意識中會逐漸達成共識:自媒體傳播的圖像信息是可加工可扭曲的,可以是“不誠實”的。
自媒體圖像傳播功能的異化同樣會加重技術的倫理危機。近年來對“反轉新聞”“后真相”“算法剝削”“信息繭房”等話題的關注和討論說明,公眾對于迅速發展并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社會認知的信息技術開始持審慎的、反思的態度。加上自媒體平臺當中由于圖像技術的濫用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道德等產生的一系列影響,在此背景下,自媒體圖像傳播的異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信任危機,會導致技術的社會評價被持續貶低,公眾對技術的道德操守漸失信心,從而引發技術的倫理危機。
(二)風險治理:技術倫理、法治約束與社會引導
面對技術的“原罪”,圖像技術倫理的建立與維護需要學界、技術界和管理方共同努力。對技術的評價到底該不該以道德的標準來衡量,技術的發展和進步該不該有邊界,技術的發明者和使用者之外是不是應設立管理者,這些都是技術發展過程中應當思考的倫理問題。市場主導的自媒體圖像傳播實踐顯露出來的信任危機和道德失范正召喚著圖像技術倫理的建立和維護。自媒體圖像技術的倫理雖屬于技術倫理的微觀層面,但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對于圖像的數字化處理和媒體傳播的邊界進行合理的界定,是構建圖像技術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技術倫理規則的建立和維護需要技術倫理的研究不斷深入、社會治理的步伐和理念不斷進步等多方面綜合因素的共同促進和努力,目前來看還任重道遠。
商業自媒體圖像傳播行為的規制。對商業自媒體的規范管理需要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傳統的媒體管理者需要繼續履行好職責,強化對包括自媒體在內的媒體行為的監管;二是商業行為的管理機構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職責,探索新的媒體環境下商業行為的管理規范和制度。
個人自媒體圖像傳播行為與觀念的引導和約束。在個人自媒體圖像傳播中體現出來的圖像審美的異化,應通過公共文化教育的普及予以引導。實施教育普及的主體包括國民教育系統、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媒體,教育的客體應關注低齡層包括幼兒、小學、中學,教育的內容包括獨立思考和辨別能力、正確的審美價值觀和圖像解讀方法,教育普及應該是持續的、各部分有機結合的整體。而針對個人自媒體圖像傳播中的違規行為,則需要通過互聯網立法的完善、互聯網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加強社會法治教育實現有效約束和治理,同時應當將立法約束與道德約束形成合力,利用互聯網技術強化社會監督功能,合理推進用戶監督和治理,最終實現對違規行為的有效治理。
參考文獻:
[1]鄧新民.自媒體:新媒體發展的最新階段及其特點[J].探索,2006(5):135.
[2]彭蘭.數字新聞業中的人—機關系[J].新聞界,2022(1):5.
[3]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157.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6]國吉.法蘭克福學派異化理論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21:24.
(符冰為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訪問學者;強月新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校:張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