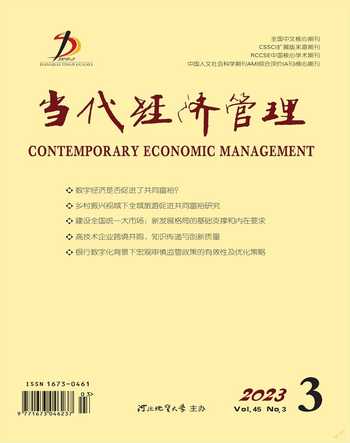銀行數字化背景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有效性及優化策略
唐紳峰 蔣海 吳文洋
[摘要]基于手工收集和文本挖掘方法建立的2011—2020年中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指數的季度面板數據,考察了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銀行數字化背景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優化策略。研究結果表明:首先,商業銀行推進數字化轉型能顯著提高其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其次,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具有較強的逆周期性,而流動性水平則呈現較強的順周期性特征,但兩者均受到銀行數字化水平的影響。最后,我國商業銀行逆周期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是有效的,但數字化轉型會弱化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和流動性水平的監管效果。研究將為我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順利推進及深化、建立健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資本監管;流動性監管;周期性;優化策略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3)03-0086-11
一、引言
數字經濟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指出要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加快培育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推動企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發展。而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源動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要“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2022年1月,人民銀行印發《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再次強調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高質量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并明確金融數字化轉型的總體思路、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實施保障。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商業銀行紛紛擁抱數字科技與新興技術并啟動數字化變革,使得數字化轉型成為銀行之間新一輪的軍備競賽。
此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各國監管當局帶來了深刻啟示,即保障金融機構個體穩健的微觀審慎監管并不能確保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健,要想維護金融系統的健康穩定,需要彌補微觀審慎監管所存在的不足,防范金融體系的順周期變化和風險傳染所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危機之后,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當局開始重視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性,加大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力度。2010年巴塞爾委員會出臺的《巴塞爾協議Ⅲ》不僅大幅提高商業銀行的監管要求,也進一步擴大了監管范圍[1]。其中,主要通過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的方式從時間維度上解決原先僅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監管框架的不足及其所存在的順周期性問題,并通過對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的識別和附加資本要求,從截面維度上降低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發生重大風險的可能性。由于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一種創新,那么商業銀行在大力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勢必會對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造成影響。202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強調,要確保金融創新在審慎監管前提下發展,持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同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宏觀審慎政策指引(試行)》,表示要持續健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夯實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在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水平以及如何保障銀行資本補充渠道等相關問題已受到我國金融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而隨著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推進,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宏觀審慎的資本監管工具和流動性監管工具能否發揮有效的監管效果,實現降低銀行風險,從而維護銀行業的健康穩定?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研究,對我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有效推進、維護銀行業穩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也可為我國金融監管政策框架的完善提供經驗支撐。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信貸類、資本類和流動類三個方面的監管工具[2]。其中信貸類監管工具所針對的是金融機構的借款者,?其主要目的是限制貸款數量。資本類和流動類監管工具所針對的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其主要目的是緩解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以及增加金融機構抵抗流動性沖擊的能力。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商業銀行,因此將重點聚焦于研究數字化轉型對資本類和流動類監管工具有效性的影響。
(一)數字化轉型對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
在數字時代,金融科技企業紛紛進入金融領域,尤其是支付及貸款領域,使得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的盈利空間被不斷壓縮。然而,商業銀行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實現自身業務的重新搭建與構造,升級原有的業務系統,提升經營效率,并憑借數字技術進行金融產品等方面的創新,有效維護了自身的競爭優勢。具體來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新的電子平臺服務渠道實現在沒有分支機構的情況下提供金融服務,能夠大量增加銀行所能接觸到的客戶,降低其交易成本并提高其運營效率,從而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3-4]。同時,銀行盈利能力越強,其產生的利潤也越多,因此能夠提供更多的利潤留存與資本金,有效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而數字化轉型對銀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與之相像,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實現業務收入的快速周轉,大幅提高資金周轉速度與流動性水平,進而降低流動性風險。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化轉型會對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產生正向的影響。
(二)數字化轉型對資本與流動性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
關于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周期性,大量研究表明,我國資本監管工具存在逆周期性[5-6],即在經濟上行期,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反而會增加。而商業銀行數字化程度可能會弱化資本緩沖的逆周期性。具體表現為,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全面提升了商業銀行的風險管控能力。一方面,憑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運用,銀行和貸款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得到較好的緩解,同時在數字化技術的共識機制作用下,信息的披露會更加貼近于真實情況,從而能夠有效減少信息操縱、惡意欺詐等道德風險的發生,使得銀行能夠有效控制自身風險[7]。另一方面,大數據等新興數字技術的應用,大幅提升了銀行的貸前審查能力,促進銀行風險評估的智能化,有助于打造覆蓋風險識別、計量、決策、實施全流程的風險管理體系,從而全面提升銀行的風險管控能力。而銀行風險管控能力的大幅提升,將激勵銀行在經濟形勢較好時加大貸款投放力度,從而降低了資本充足狀況。同時,在流動性監管工具方面,銀行的流動性水平會受到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的影響[8],進而呈現出順周期性的特征。一般情況下,經濟上行期,資本的預期收益較高,銀行傾向于高風險高收益的長期投資,爭取最大的利潤。但這種激進的投資行為可能會受到銀行數字轉型的影響,由于數字時代的商業銀行業務經營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逐漸邁向多元化與智能化,大幅提升了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9],使得其承擔高風險的意愿降低。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具有逆周期性,但流動性水平可能呈現順周期性特征,同時它們的周期性會受到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三)數字化轉型對資本與流動性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
研究表明,我國資本監管與流動性監管制度的引入,能夠避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片面擴張,從而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有效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定[10]。一方面,資本監管要求的提高將迫使商業銀行以自身資本承擔損失,強化對銀行信貸的資本約束效應,有助于商業銀行強化風險防控意識。另一方面,從商業銀行債務期限選擇方面來看,流動性監管要求將影響銀行管理層對債務期限與資產結構的選擇[11]。當短期債務在可用穩定資金中的權重足夠低時,商業銀行將會降低短期融資的比例,否則銀行需要通過降低風險資產占比的方式達到監管要求,從而降低銀行破產概率,提高其穩定性。因此,管理層對流動性監管要求提高,一是可以選擇增加資本份額或延長債務期限,二是可以降低風險資產的持有或縮短此類資產的持有期限。而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會對其可用穩定資金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監管工具的監管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資本監管與流動性監管能夠降低銀行風險承擔,但其監管效果也會受到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第一,為了考察銀行數字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其資本充足水平與流動性水平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同時避免研究變量之間及研究變量與殘差項之間的內生性、隨機擾動項的異方差以及實證模型遺漏變量等問題所引起的結果偏差,本文借鑒張強等(2013)[12]的做法分別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Carit=α0+α1Carit-1+α2DTIit+Xit+εit(1)
Liqit=β0+β1Liqit-1+β2DTIit+Xitβ+εit(2)
其中,Carit代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以資本充足率來表征資本充足水平;Liqit代表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水平,以流動性比例來表征流動性水平。DTI代表銀行數字化轉型水平,以上市銀行的年度報告中相應關鍵詞詞頻的對數值來衡量。Xit代表控制變量組;εit為隨機誤差項。
第二,為了進一步驗證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是由其分子資本渠道抑或是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所導致的,本文分別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檢驗數字化轉型對銀行資本水平與風險加權資產的影響:
sheit=α0+α1sheit-1+α2DTIit+Xit+εit(3)
RWAit=β0+β1RWAit-1+β2DTIit+Xitβ+εit(4)
其中,sheit是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子部分,以資本比率來衡量;RWAit是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母部分,以風險加權資產占比來衡量。資本比例越高,則說明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子越大,其資本充足水平越高,若數字化轉型對資本比例有顯著影響,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分子渠道發揮作用。同理,風險加權資產越高,說明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母越大,其資本充足水平越低,若數字化轉型對風險加權資產有顯著影響,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分母渠道發揮作用。
第三,關于數字化轉型對資本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本文借鑒ADRIAN?&?SHIN(2008)[13]的研究,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考察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商業銀行資本緩沖的周期性:
BUFit=α0+α1BUFit-1+α2Cyclet+Xit+εit(5)
BUFit=β0+β1BUFit-1+β2Cyclet+β3DTIit
+β4Cyclet×DTIit+Xitβ+εit(6)
其中,BUFit代表資本緩沖水平,Cycleit代表經濟周期,Xit代表影響資本緩沖水平的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若α2>0,說明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是具有逆周期性的,即銀行要求的資本緩沖水平會在經濟上行期增加,而在經濟下行期減少;若α2<0,說明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是具有順周期性的,即銀行要求的資本緩沖水平會在經濟上行期減少,而在經濟下行期增加。同樣,若β2>0,同時β4<0,則說明數字化轉型弱化了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逆周期性;若β2<0,同時β4>0,則說明數字化轉型弱化了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順周期性,反之則反。
第四,針對數字化轉型對流動性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同樣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考察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的周期性:
Liqit=α0+α1Liqit-1+α2Cyclet+Xit+εit(7)
Liqit=β0+β1Liqit-1+β2Cyclet+β3DTIit
+β4Cyclet×DTIit+Xitβ+εit(8)
其中,Liqit代表流動性水平,Cycleit代表經濟周期,Xit代表控制變量組;εit為隨機誤差項。若α2>0,表明商業銀行會在經濟上行期持有更多的流動性資產,因此同樣可以認為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是具有逆周期性的;若α2<0,則說明商業銀行流動性
水平是具有順周期性的,即商業銀行會在經濟上行期減少流動性資產的持有。同樣,若β2>0,同時β4<0,說明數字化轉型弱化了銀行流動性水平的逆周期性;若β2<0,同時β4>0,則說明數字化轉型弱化了銀行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反之則反。
第五,為了進一步考察數字化轉型會對資本監管工具的監管效果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文在JOKIPII?&?MILNE(2011)[14]研究基礎上,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Riskit=α0+α1Riskit-1+α2BUFit+Xit+εit(9)
Riskit=β0+β1Riskit-1+β2BUFit+β3DTIit
+β4BUFit×DTIit+Xitβ+εit(10)
其中,Riskit代表銀行風險承擔水平,分別以Zscore和不良貸款率來表征銀行風險承擔。BUFit代表資本緩沖水平,DTI代表銀行數字化轉型水平,Xit代表控制變量組;εit為隨機誤差項。
第六,針對數字化轉型對流動性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同樣建立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Riskit=α0+α1Riskit-1+α2Liqit+Xit+εit(11)
Riskit=β0+β1Riskit-1+β2Liqit+β3DTIit+β4Liqit×DTIit+Xitβ+εit(12)
其中,Riskit代表銀行風險承擔水平,Liqit代表流動性水平,其余變量的定義與上文一致,不再贅述。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
資本充足水平。資本充足水平是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重要指標之一[15],其主要代理變量包括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資本比重。由于核心資本充足率與核心資本比重的數據缺失較為嚴重,因此本文采用資本充足率(資本比率/風險加權資產占比)作為銀行資本監管的代理變量。一般而言,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越高,其風險承受能力越強。
資本比率和風險加權資產占比。資本比率是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子部分,表征分子資本渠道,采用股東權益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其中,資本比率越大,銀行資本充足水平越高。而風險加權資產占比是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分母部分,表征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采用銀行風險加權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顯然,風險加權資產占比越大,銀行資本充足水平越低。
流動性水平。流動性水平是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的重要指標之一[16],而衡量銀行流動性水平的指標主要有存貸比、流動性比例、流動性覆蓋率、流動性匹配率、凈穩定資金比例和優質流動性資本充足率等。由于存在監管套利等問題,銀行存貸比監管指標已在2015年被取消,同時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例等監管指標卻只適用于資產規模大于2?000億元的商業銀行,而優質流動性資本充足率所針對的是資產規模小于2?000億元的商業銀行。從適用范圍來看,流動性比例適用于所有商業銀行,也符合本文樣本選擇的要求,因此本文選取流動性比例作為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的代理變量。
銀行數字化轉型水平。相關研究表明,銀行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相關特征信息更容易體現在具有總結和指導性質的年度報表中[17]。因此,通過統計銀行年報中涉及“數字化轉型”的詞頻來刻畫其轉型程度,具有可行性和科學性。具體而言,本文借助Python?爬蟲功能對中國40家上市銀行年度報表進行爬取,并采用Jieba分詞模塊對銀行“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關鍵詞進行分詞與統計。使用Jieba的優勢在于其能夠精準地對中文文本進行識別與分詞,同時支持用戶自定義詞典,可以有效提高分詞的準確性。在詞庫方面,本文借鑒吳非(2021)[17]的研究,將銀行數字化轉型細分為“底層技術”與“實踐應用”兩類,不僅包括了數字化轉型的四種典型底層技術,即“ABCD”技術;同時也包含了這類技術在具體實踐中的運用表現。此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關鍵詞詞庫進行有效補充(具體見圖1),并在此基礎上,根據詞庫對上市銀行年度報表進行匹配與詞頻匯總,同時剔除關鍵詞前存在否定表達的詞頻后進行對數化得到銀行業數字化轉型指數。
圖1構建銀行數字化轉型指數的關鍵詞詞庫
資本緩沖水平。由資本緩沖的定義可知,銀行資本緩沖水平是指商業銀行實際資本充足率與監管當局最低資本監管要求的差額。在2012年之前,巴塞爾委員會對所有商業銀行執行統一的資本要求,即銀行資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的指標要求。同時為了防范系統重要性銀行發生重大風險時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在2012年之后采用了分類資本監管制度,即根據是否為系統重要性銀行執行差異化的資本監管要求,具體如表1所示。
經濟周期。關于經濟周期,本文主要采用兩種方法進行衡量。一是借鑒AYUSO等(2008)[18]以及蔣海等(2018)[19]的做法,以實際GDP增長率來衡量。二是使用通過HP濾波方法剔除GDP增長率中趨勢項后的剩余部分進行度量,該方法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周期波動[5]。
2控制變量
在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指標水平及其周期性影響部分,本文參考蔣海等(2018)[19]的研究,從微觀銀行特征和宏觀經濟環境兩個方面進行控制變量選擇。資產規模,采用對數化的總資產來衡量;貸款規模,以貸款占總資產之比進行度量;信用風險,采用銀行不良貸款率表示;盈利能力,以凈資產收益率進行度量;宏觀層面的變量,主要選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作為主要代理變量。
在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部分,由于被解釋變量是銀行風險承擔,因此本文在顧海峰和張亞楠(2018)[20]和蔣海等(2021)[16]的研究基礎上,從微觀銀行特征和宏觀經濟環境兩個方面進行控制變量選擇。資產規模,采用對數化的總資產來衡量;盈利能力,一般使用銀行總資產利用率和營業凈利率來衡量,分別以總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占營業收入之比進行度量;存貸款比例,采用銀行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之比表示;生息資產收益,以凈息差進行度量;非生息資產收益,以非利息收入占比進行度量;宏觀層面的變量,主要選擇銀行業景氣指數以及M2與GDP比值作為主要代理變量。
(三)樣本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0年中國A股上市的全部商業銀行季度數據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部分缺失值則通過手工查找銀行財務報表進行補充。最終獲得40家上市銀行的“銀行-季度”非平衡面板數據,數據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設定的動態面板模型包含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使用OLS和面板固定效應估計方法容易造成有偏估計,而系統GMM估計方法能夠較好克服模型的內生性、異方差等問題,因此本文運用系統GMM方法進行實證檢驗。同時,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可靠性,進一步對回歸結果進行以下兩個方面檢驗:一是考慮到系統GMM方法需要滿足殘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自相關的前提要求,因此對模型的殘差項進行二階序列自相關檢驗;二是采用漢森檢驗(Hansen?test)考察回歸結果中是否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薩甘檢驗(Sargan?test)需要在同方差的前提下才有效[21],因此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造成估計偏誤,本文將報告Hansen檢驗的結果。
(一)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指標水平的影響
1數字化轉型對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
表3給出了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結果,由表3可以看到,所有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具有動態連續性,使用動態面板模型估計具有合理性。同時,基于GMM估計的序列相關性檢驗AR(2)的P值分別為0154、0247和0204,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模型二階序列自相關檢驗的原假設,運用系統GMM模型進行估計是合理的。此外,Hansen檢驗的p值均大于01,也說明本文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
從表3的第(1)~(3)列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對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數字化轉型會提高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商業銀行通過運用數字化技術能夠提高貸款質量,促進銀行業務多元化經營,加速銀行中間業務發展,從而提高銀行資本補充的及時性,進而增加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從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分子渠道的影響來看,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為0425,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加了其資本水平。這一點也驗證了前面的分析,數字化技術的運用不僅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提高貸款質量,同時可以促進銀行資產和貸款業務向多元化發展,實現根據客戶多樣性需求開發創新金融產品,從而有效提高銀行非利息收入及其盈利能力,使得銀行資本補充更加快捷[22-23],致使銀行數字化轉型可能會通過分子資本渠道增加其資本充足水平。從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分母渠道的影響來看,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為0356,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將提高其風險加權資產占比,即數字化轉型會通過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降低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大幅提升銀行的貸前審查能力,提高貸款質量,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此時,銀行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目標,會采取較為激進的經營策略,增加對高風險和高收益項目的投資,從而提高了銀行風險資產。
數字化轉型雖然會通過分子資本渠道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但數字化轉型也會通過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降低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然
而,可以發現,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小于分子資本渠道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說明數字化轉型對風險加
權資產的影響程度并沒有其對銀行資本水平的影響程度那么大,由此導致了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銀行資本充足水平。此外,從宏微觀控制變量對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來看,經濟增長率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之間顯著負相關,說明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在經濟上行期會下降,具有顯著的順周期性。銀行貸款的增加和不良貸款率的提升能夠顯著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可能的原因是:貸款的增加提高了銀行的盈利水平,從而增加銀行資本水平,而隨著銀行資本水平的提高,其放貸能力得到加強[24],進一步促進銀行資本水平的提升。而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則意味著銀行需要計提更多的資本用來覆蓋其信用風險。在經濟形勢較好時,由于企業經營良好,貸款違約率較低,此時商業銀行傾向于降低資本充足率,發放更多的貸款,獲取更大的利潤;而當經濟形勢惡化時,企業貸款違約率上升,商業銀行出于控制風險的目的,會減少貸款的發放,積累更多的資本用來抵御風險。
2數字化轉型對銀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
表3同時報告了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結果。從回歸結果來看,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化轉型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水平。可能的原因是:數字化技術的運用不僅能夠提高銀行貸款質量,減少不良貸款,提高資金回收率,同時數字化轉型促進了商業銀行以中間業務為主的非傳統業務活動的多元化發展,使得銀行能夠實現業務收入的快速周轉,從而提高銀行資金周轉速度與流動性水平,進而降低流動性風險[25]。從控制變量的影響情況來看,經濟增長水平與銀行流動性水平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銀行流動性水平與經濟形勢呈現出反方向變動的特征,即經濟形勢越好,銀行流動性水平越低。同時規模越大的銀行,其流動性水平越低,主要的原因是大型商業銀行自有資本較為充足,具有國家信用背書,債權人對其流動性風險抵抗能力有足夠的信心,使得大型商業銀行短期償債壓力較小。此外,不良貸款率對流動性水平影響顯著大于零,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尚未達到監管機關規定的監管紅線時,商業銀行可以運用貸款重組等方式降低和化解貸款風險,從而有效降低不良貸款對銀行流動性資產的損耗。
(二)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
1數字化轉型對資本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
表4報告了數字化轉型背景下銀行資本緩沖周期性的檢驗結果。由表4可以看到,在兩種不同衡量經濟周期變量的方法下,經濟周期對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影響均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在經濟上行期,銀行資本緩沖水平會增加,而在經濟下行期,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則會減少,即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緩沖具有較強的逆周期性特征。這一結果也側面說明了我國對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能夠較好地緩解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減少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同時,經濟周期變量與數字化轉型交叉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72和-0071,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逆周期性會受到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影響,即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逆周期性。原因在于: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將大幅提升商業銀行的貸前審查與貸后風險管理能力,有效降低了銀行的信貸風險,導致在經濟形勢較好時,商業銀行為了追逐更高利潤,將發放更多的貸款,減少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從而弱化了資本緩沖水平的逆周期性。
2數字化轉型對流動性監管工具周期性的影響
表5給出了數字化轉型背景下銀行流動性水平周期性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到,在兩種不同衡量經濟周期變量的方法下,經濟周期對銀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銀行流動性水平在經濟上行期會減少,而在經濟下行期增加,即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具有順周期性特征。這一結果也側面說明了流動性監管并不能緩解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即在經濟形勢較好時,商業銀行預期資本回報率較高,此時商業銀行傾向于投資那些長期限高收益的項目,使得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正反饋機制推動經濟進一步繁榮,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經濟周期變量與數字化轉型交叉項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銀行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會受到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影響,即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銀行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可能的原因是: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將促進商業銀行業務向移動化、數據化、智能化方向發展,有效拓展其業務發展的深度、廣度與多元化程度,從而大幅提升銀行的盈利能力。而隨著銀行盈利能力的不斷加強,不僅能夠實現銀行業務收入的快速周轉,提高其資本充足水平,同時能夠減弱銀行投資長期限高收益項目的意愿。
(三)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
1數字化轉型對資本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
表6報告了數字化轉型背景下資本緩沖水平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結果。可以看到,在沒有加入數字化轉型變量及其與資本緩沖水平交叉項時,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對銀行破產概率和不良貸款率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2和-0018,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提高能夠降低其風險承擔水平。這一結果也側面反映了我國商業銀行逆周期資本監管的有效性,即逆周期資本監管機制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當加入數字化轉型變量及其與資本緩沖水平交叉項時,可以發現,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驗證了本文理論分析中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降低銀行風險承擔的結論。而數字化轉型與資本緩沖水平交叉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9和0008,且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監管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影響,即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弱化了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監管效果。這是因為商業銀行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能夠有效改善其與貸款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憑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銀行能夠實現風險評估的智能化,并打造出覆蓋風險識別、計量、決策、實施全流程的風險管理體系,全面提升風險管控能力。而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信心加持下,銀行可能會加大貸款的發放以及高收益高風險項目的投資,使得銀行資本監管效果出現減弱的現象。
2數字化轉型對流動性監管工具監管效果的影響
表7則給出了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流動性水平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結果。可以看到,在沒有加入數字化轉型變量及其與流動性水平交叉項時,銀行流動性水平對銀行破產概率和不良貸款率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0和-0004,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流動性水平的提高能夠降低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這一結果也說明了我國宏觀審慎的流動性監管是有效的,即提高商
業銀行流動性監管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而當加入數字化轉型變量及其與流動性水平交叉項時,可以發現,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再次驗證了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降低銀行風險承擔水平。而數字化轉型與流動性水平交叉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2和0002,且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同樣說明銀行流動性水平的監管效果會受到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影響,即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銀行流動性水平的監管效果。這一結論同樣可以從以下角度進行解釋: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能夠幫助商業銀行實現實時的移動貸后監控和更加精準的信貸風險控制,由此激勵商業銀行進行激進的經營行為,使得銀行風險承擔水平上升,流動性監管效果出現減弱的現象。
此外,出于穩健性的考慮,本文進一步以銀行科技人員占比作為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替代變量,對上述所有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①,實證結果同樣支持本文的研究結論。
五、進一步討論:數字化背景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優化策略
上述研究表明,當前金融領域尤其是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對監管主體、監管制度、監管方式都帶來全新的挑戰,因此將數字化轉型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治理機制已迫在眉睫。
(一)在加強資本監管的同時,建立逆周期的流動性監管機制
針對資本監管,本文發現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具有逆周期性,提高資本監管要求能夠降低銀行風險承擔;雖然流動性監管同樣具有抑制銀行風險承擔的監管效果,但銀行的流動性水平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因此,在加強銀行資本監管的同時,要實施逆周期的流動性監管機制,以此緩解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由于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會導致商業銀行在經濟上行期減少流動性水平,增加其隨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因此,可借鑒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在經濟上行期,實施計提銀行流動性緩沖水平的監管政策,適當積累流動性資本;而當經濟下行時,資產減值等各種風險逐漸暴露,此時需要商業銀行釋放在經濟上行期所積累的流動性,以此緩解經濟下行所帶來的流動性沖擊,維護銀行業穩定性。
(二)實施差異化的宏觀審慎監管策略,提升金融監管實效
實施差異化的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策略是我國宏觀審慎監管優化的基礎策略,能夠加速提升金融監管實效。首先,要加強對資本緩沖水平較低的商業銀行的監管。這類銀行資本充足水平較低,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差,容易在經濟形勢不好時出現流動性風險,發生擠兌行為,因此要對此類銀行給予更多的關注,倘若其違反最低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要加大懲罰力度,必要時可通過增資擴股等方式改善其資本質量,優化其資本結構。同時,對資本充足水平過高的商業銀行,也要進行適當管控,防止其出現惜貸行為,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可引導其持有較優的資本緩沖水平。其次,要根據商業銀行風險評級的高低,進行差異化的資本監管政策。在最低資本充足要求方面,可在根據是否是系統重要性商業銀行進行差異化監管的基礎上,適當提高風險評級較高的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充分發揮資本監管抑制其風險承擔的效果;同時適當降低風險評級較低的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要求,讓其擁有充足資金推動數字技術的應用,實現數字化轉型。最后,在流動性方面,可依據商業銀行的股權性質、規模大小、業務類型等要素的不同,實施差異化的杠桿率監管政策,以此改善監管政策的針對性和適用性,以期獲得更加符合金融市場實際運行情況的監管效果。
(三)構建納入數字化轉型因素的前瞻性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機制框架
金融數字化發展會對現有的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機制產生新的不確定性沖擊,因此在持續完善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機制過程中,要納入數字化轉型因素,提升宏觀審慎壓力測試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一方面,要搭建金融數字化大數據平臺,建立銀行體系宏觀審慎管理數據庫和數字技術服務體系,確保壓力測試機構能夠實時獲取充足的數據信息和技術資源,同時在壓力測試的模型方法、壓力情景設計等方面納入數字化轉型因素的影響,以此提升壓力測試機構的評估能力以及測試效率與精準度。另一方面,監管部門要加大資本和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工具的投入力度,盡可能及時了解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資本充足狀況和流動性風險的真實情況,實現對不同經濟周期下銀行風險的前瞻性、針對性地識別,從而達到對資本和流動性風險的動態監管,逐漸打造出適用于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壓力測試體系。此外,本文研究還發現,數字化轉型對大型商業銀行盈利水平具有更大的促進效果。因此,為了避免此類銀行通過數字化轉型追逐高收益卻忽視掉潛在風險的情況發生,監管部門要定期對大型商業銀行尤其是系統重要性銀行開展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評估這些銀行的資本充足狀況和流動性風險、及其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度,并根據壓力測試結果視情對其提出額外的監管要求或采取相應監管措施,進而加強宏觀審慎壓力測試結果應用、完善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機制框架。
(四)建立數字化轉型與監管政策的協調機制,完善數字化背景下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宏觀審慎監管政策雖然能夠有效抑制銀行的風險承擔,但隨著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推進,這種抑制效果會被弱化。因此,要建立數字化轉型與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協調機制,進而完善我國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具體而言,要實施數字化轉型與監管政策動態協調機制。在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初始階段,銀行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較低,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影響很小,此時可維持或者適當減弱銀行的監管要求,讓其擁有充足資金提升數據開發和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助力銀行數字化轉型的加速。而在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中后期階段,銀行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盈利能力較強,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影響已較明顯,此時要適當提高銀行的監管要求,控制銀行風險。此外,考慮到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的監管效果是存在差異的,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對非協調背景下數字化轉型與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沖突機制進行分析,合理布局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資本監管與流動性監管,充分考慮不同監管政策組合的監管效果,以期提升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全局性與系統性。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旨在探討“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有效性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該如何優化”。因此,通過選取2011—2020年我國40家上市商業銀行的季度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響,并得到以下結論:第一,數字化轉型與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之間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商業銀行推進數字化轉型能顯著提高其資本充足水平和流動性水平。第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和流動性水平分別具有較強的逆周期性和較強的順周期性特征,但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銀行資本緩沖水平的逆周期性以及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第三,我國商業銀行逆周期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是有效的,即逆周期資本監管機制和流動性監管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但數字化轉型會弱化銀行資本緩沖水平和流動性水平的監管效果。
本文的研究結論揭示了數字化轉型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因此,在加快推進銀行業數字化進程時,也要兼顧數字化轉型可能帶來的挑戰甚至不利影響。建立健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有助于構建運行順暢的宏觀審慎治理機制,推動形成統籌協調的金融風險防范化解體系,促進我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具體而言:在國家監管層面,一是可借鑒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在加強銀行資本監管的同時,建立逆周期的流動性監管機制,緩解流動性水平的順周期性。二是要實施差異化的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策略,改善監管政策的針對性和適用性,以此提升金融監管實效。三是建立納入數字化轉型因素的前瞻性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機制,強化風險監測、評估和預警,從而保障我國銀行業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四是實施數字化轉型與監管政策動態協調機制,完善金融數字化監管政策框架,提升監管政策的全局性與系統性。在銀行層面,商業銀行要合理調整自身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借助數字化轉型紅利提高資本緩沖水平,從而達到資本監管要求。本文發現數字化轉型會通過資本充足水平分子資本渠道與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來影響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但其對銀行資本的作用更大。因此,商業銀行可借助數字技術力量創新資本工具,加快資金周轉速度,增強資本補充能力,通過資本充足水平分子資本渠道提高資本緩沖水平。在風險加權資產管理方面,可運用數字技術改造后的風險管控體系,加強風險資產監督,通過貸款質量,以間接的方式通過分母風險加權資產渠道提高資本緩沖水平。
[注釋]
①?篇幅所限,穩健性檢驗結果未予以列示,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參考文獻]
[1]AYSAN?A?F,?FENDO?LU?S,?KILINC?M.?Macroprudential?policies?as?buffer?against?volatile?crossborder?capital?flows[J].?The?Singapore?economic?review,2015,60(1):418-452.
[2]方意.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研究[J].世界經濟,2016,39(8):25-49.
[3]FORCADELL?F?J,?ARACIL?E,?BEDA?F.?The?impact?of?corporate?sustainability?and?digitalization?on?international?banks?performance[J].?Global?policy,2020,11:18-27.
[4]KITSIOS?F,?GIATSIDIS?I,?KAMARIOTOU?M.?Digital?transformation?and?strategy?in?the?banking?sector:?evaluating?the?acceptance?rate?of?eservices[J].?Journal?of?open?innovation:?technology,?market,?and?complexity,2021,7(3):1-14.
[5]黨宇峰,梁琪,陳文哲.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周期性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2(11):74-85.
[6]蔣海,羅貴君,朱滔.中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的逆周期性研究:1998-2011[J].金融研究,2012(9):34-47.
[7]金洪飛,李弘基,劉音露.金融科技、銀行風險與市場擠出效應[J].財經研究,2020,46(5):52-65.
[8]李志輝,王文剛,王近.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形成機制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1-11.
[9]李志輝,李夢雨.我國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的關系——基于50家商業銀行2005—2012年的面板數據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4(1):74-86.
[10]周小川.保持金融穩定防范道德風險[J].金融研究,2004(4):1-7.
[11]WEI?X,?GONG?Y,?WU?H?M.?The?impacts?of?net?stable?funding?ratio?requirement?on?banks?choices?of?debt?maturity[J].?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17,82:229-243.
[12]張強,喬煜峰,張寶.中國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存在嗎?[J].金融研究,2013(8):84-97.
[13]ADRIAN?T,?SHIN?H?S.?Financial?intermediaries,?financial?stability,?and?monetary?policy[J].?FRB?of?New?York?staff?report,2008,346(9):1-37.
[14]JOKIPII?T,?MILNE?A.?Bank?capital?buffer?and?risk?adjustment?decisions[J].?Journal?of?financial?stability,2011,7(3):165-178.
[15]蘇帆,于寄語,熊劼.更高資本充足率要求能夠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嗎?——基于雙重差分法的再檢驗[J].國際金融研究,2019(9):76-86.
[16]蔣海,張小林,唐紳峰,等.貨幣政策、流動性與銀行風險承擔——基于銀行微觀流動性視角的理論與實證[J].經濟研究,2021(8):56-73.
[17]吳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
[18]AYUSO?J,?PREZ?D,?SAURINA?J.?Are?capital?buffers?procyclical??evidence?from?Spanish?panel?data[J].?Journal?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2004,13(2):249-264.
[19]蔣海,張小林,陳創練.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商業銀行的資本緩沖行為[J].中國工業經濟,2018(11):61-78.
[20]顧海峰,張亞楠.金融創新、信貸環境與銀行風險承擔——來自2006—2016年中國銀行業的證據[J].國際金融研究,2018(9):66-75.
[21]李雙建,田國強.銀行競爭與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渠道:理論與實證[J].管理世界,2020,36(4):149-168.
[22]李宏瑾.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的挑戰及應對[J].國際金融研究,2015(2):65-76.
[23]謝婼青,李世奇,張美星.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對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38(8):145-163.
[24]吳瑋.資本約束對商業銀行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基于175家商業銀行數據的經驗研究[J].金融研究,2011(4):65-81.
[25]宋清華,宋一程,劉金玉.多元化能降低銀行風險嗎?——來自中國上市銀行的經驗證據[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6,37(5):9-15.
The?Effectiveness?and?Optimization?Strategy?of?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
Policy?under?the?Background?of?Bank?Digitalization
Tang??Shenfeng1,??Jiang??Hai2,??Wu??Wenyang3
(1.?School?of?Economics?and?Statistics,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2.?School?of?Economics,Jinan?University,
Guangzhou?510632,?China;?3.?School?of?Finance,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and?Business,?Changsha?41020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2011?to?2020?quarterly?panel?data?of?China?Commercial?Bank?Digital?Transformation?Index?established?by?manual?collection?and?text?mining,?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the?effectiveness?of?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tools.?Furthermore,?this?paper?proposes?the?optimization?strategy?of?Chinas?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policy?under?the?background?of?digital?transformation.?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first,?the?promotion?of?digital?transformation?of?commercial?banks?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ir?capital?adequacy?and?liquidity?levels;?secondly,?the?capital?buffer?level?of?commercial?banks?is?strongly?countercyclical,?while?the?liquidity?level?is?strongly?procyclical,?but?both?are?affected?by?the?digitalization?level?of?banks;?finally,?countercyclical?capital?and?liquidity?supervision?of?Chinese?commercial?banks?is?effective,?but?digital?transformation?will?weaken?the?regulatory?effect?of?banks?capital?buffer?levels?and?liquidity?levels.?The?research?in?this?paper?will?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the?smooth?advancement?of?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commercial?banks?and?the?further?improvement?of?the?macro?prudential?regulatory?framework?under?the?background?of?digit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capital?regulation;?liquidity?regulation;?cyclical;?optimization?strategy
(責任編輯:蔡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