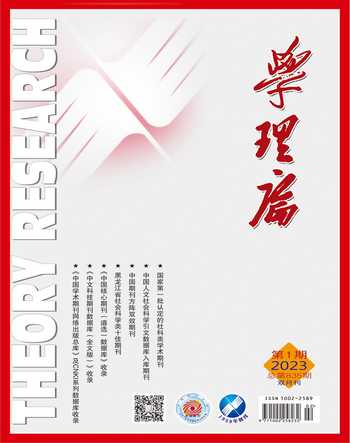清初東北內務府皇莊的經營及管理
徐祝申

摘 要:清代內務府皇莊是皇室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初在東北地區及長城內外設立大批的皇莊。皇莊作為清朝皇室的私產,建立時間早,經營時間長,經營管理完善,是皇室經濟賴以生存的重要因素。皇莊的生產關系和經營方式對壯丁的剝削嚴重,由于壯丁的反抗、租佃關系的發展,皇莊逐漸走向衰落。
關鍵詞:內務府;皇莊;經營管理
中圖分類號:K241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23)01-0085-04
皇莊主要功能是定期向政府、皇室送交貢品及繳納賦稅等。清初在東北地區及長城內外設立大批皇莊。清代統治者對皇莊管理十分重視,由內務府管理,并由莊頭監督壯丁勞動生產,形成了極具特色的皇莊經濟。內務府皇莊不僅為清廷提供大量的稅收,也是清廷皇室開銷的重要保障。
一、內務府皇莊的設立及土地來源
(一)皇莊的設立
內務府皇莊淵源于入關前的拖克索(滿語農莊之意)。最早皇莊設立于天命年間。“太祖高帝駐兵奉天建極時,有土著莊戶報效糧石,上嘉以報糧多的莊戶派當頭自,封為糧莊頭,編入旗籍”[1]130。皇太極時期開始設置內務府,為更好管理皇家私產,將盛京皇莊交內務府管轄。清入主中原后,盛京內務府皇莊進一步發展壯大。順治初年,盛京僅有10處糧莊,康熙初年,糧莊達27處,果園120處,鹽莊3處。順治、康熙初年的莊與入關前莊田(拖克索)略有不同。每莊一般撥丁10人,牛6頭,田120坰,納糧額120石。順治、康熙初年清政府為充實龍興之地,迅速改變“沃野千里,有土無人”的局面,大規模編置莊田。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內務府在盛京的糧莊達84處[1]131。錦州內務府糧莊順治年間設立。據乾隆初年錦州糧莊莊頭沈某回憶說:“竊奴才等祖父從龍,于順治二年,蒙恩撥為大凌河等處莊頭,彼時地廣人稀,祖父率領壯丁效力開墾”[1]131。
(二)土地來源
1.漢人帶地投充的土地。《盛京時報》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一日載:“太祖高帝駐兵奉天建極時,有土著莊戶報效糧石,上嘉以報糧多的莊戶派當頭目,封為糧莊頭,其土人帶地報糧之始也”。所謂土著之人是指遼沈地區的漢人,大多在洪武初年或明末清初從直隸、山東、山西等省移住遼東地區。據當時投充戶講:“竊莊壯等系明末遼東攜家口墾田實邊,成熟未久,即值清太祖占據遼東,令滿兵屯田,圈占熟地,在其區域,所屬恐被奪去墾地,慌迫無奈,聚以三五名或六七名為一起,湊集軍糧百余石,赴清太祖帳前報效軍糧,請發執照”[2]第4327號。清朝初年許多來到遼東地區謀生的漢人,迫于清廷的和生活的壓力,沒有辦法最后成為帶地投充為糧莊壯丁。《清朝文獻通考》卷五載:錦州官莊云:“帶地納糧莊頭一名,報地六十四石”。清初東北地區皇莊經常出現莊頭和佃戶爭議的事情,莊頭則稱“莊則為帶地投充,照應自領”,而佃戶則謂“承種有年宜領執據”[3]。
2.圈撥官荒。明末清初,因長期戰爭的破壞,整個遼沈地區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清廷利用無主荒地,圈撥官荒,招民承領。《奉天通志》載:“清初招發莊頭,領地墾種,多者千余繩,少者數百繩,名為官圈,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盛京徐廷奇蒙放廣寧縣北團臺子圈地1 200繩。康熙中葉,打牲烏拉設立5所糧莊,每莊額定14人,每丁圈撥荒地15,都屬于官撥圈荒”[4]卷1196。
3.民地編莊。清初由于明清戰爭的破壞,人口銳減。清朝定鼎北京后,積極鼓勵關內人民到東北墾地。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規定:“是歲以山海關外荒地甚多,民人愿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關道造冊報部,分地居住”[5]645。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以遼陽為府,轄海城、遼陽二縣,設官管理漢民,并頒布著名的遼東招民開墾令:“是年定例,遼東招民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上,文授縣丞主簿,武授百總。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每名口給月糧一斗。每地一坰給種六升。每百名給牛二十支”[6]456。于是山東、直隸、山西等地漢族民人紛紛移往東北就食求生,開墾田數十萬畝。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以后,清廷在盛京附近大規模地將移民墾熟之田編為莊。設內務府莊頭84缺,將開墾的土地均變為內務府糧官地,按年交陵寢祭祀牛羊豆石,并內廷倉谷糧及宮殿等處貢款各項差徭[2]。
4.緣罪籍沒官宦的土地。清初八旗貴族王公在東北有很多的田莊,這些田莊或由帝賞賜,或自行圈占。但一旦犯罪,其土地便沒收為官,多充內務府莊。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多爾袞、阿濟格等因罪被籍沒家產,他們在盛京的22所田莊,全部充公[1]134。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鰲拜與蘇克薩哈黨爭激烈,蘇克薩哈失敗,籍沒家產,同時被查抄家產的還有其侄海蘭、吐爾特依,將他們在東北各地的土地、田產、人丁、財物、牛馬等全部充公,成為內務府皇莊的一部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查抄鰲拜、班布爾善、馬爾塞、阿思哈等在盛京的家下人畜、地畝,編了3處莊[1]131。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又將孔有德的家下人畜,籍沒編了6處糧莊。上述“有罪之家所籍入之奴仆,均撥給各莊,以充壯丁,如有逃走該管官即行呈報”[4]卷1196。
二、內務府皇莊分布與經營
清初內務府在東北地區的皇莊遍及東三省,主要由盛京內務府皇莊、打牲烏拉糧莊衙門、錦州皇糧莊衙門三部分組成。盛京內務府皇莊主要有鐵嶺、蓋州、開原、遼陽、金州等地;錦州皇糧莊衙門則分布在廣寧、錦州、寧遠、中前衛等地;打牲烏拉糧莊分布在五官莊、三道、喀薩哩諸地。清初各種皇莊具體分布和面積比較大,據乾隆四十八年版《盛京通志》卷三十八,制成下表。
內務府主要莊分布及面積[7]
據上表得知如下問題:第一,糧莊主要分布在興京、奉天、鐵嶺、錦州、寧遠、義州等地,莊總額約150萬余畝。康熙以來,由于分賜給王公貴族,從而使糧莊面積逐漸減少。第二,果園約241處,分布盛京、遼陽、開原、鐵嶺、海城、廣寧、義州等地,總面積29,740畝。第三,鹽莊3處,鑲黃旗鹽灘256座,正黃旗鹽灘258座,正白旗鹽灘70座,計584座,每座征鹽150斗,設莊頭3名,計丁167名,經理鹽產[8]99-127。
各莊散布各地與各地旗民地交錯在一起,盛京內務府糧莊“散處各城,與各項旗民地段鱗次毗連”。一般來說皇莊的土地并不集中,都是星羅棋布分布在多個地區。“每莊代理官田不下數千畝,坐落非一處,如南城之莊經理北城之地,北城之莊經理南城之租,兩間相隔數百里”[2]4197。皇莊土地的分散性,決定了莊土地分散經營的特點,也決定了在皇莊勞作的莊丁和佃戶的生產活動以家庭為中心。
皇莊分散經營的另一個原因,是壯丁領種莊地具有世襲性。隨著壯丁家庭的繁衍生息,人口不斷增加,家族也開始壯大,土地不斷分種,導致每個莊丁的土地也會越來越少。如盛京內務府莊頭董永修的糧莊,當年“領名冊地一千二百七十八畝,當年按六丁分種,董姓五丁,李姓一丁,以十二畝為一日,每丁分得十八日,并無別戶分種。后因族大支繁,地已按支分種”[1]136。上述論述可以說明,皇莊是以個體家庭為基本單位,分散經營,年終向莊頭處匯交地租。
三、清廷對皇莊的管理
(一)清廷管理皇莊的體制
清初管理皇莊事務的最高機關是總管內務府。總管內務府下設廣儲司、都虞司、掌禮司、會計司、營造司、慶豐司、慎刑司等機構,其中會計司負責莊田地畝之事。會計司初名“內官監”。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改為宣政院,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改為會計司。其官有郎中2人,員外郎6人,主事1人,委署主事1人,筆帖式25人,書吏3人,分掌會計司各項事務。會計司所管莊園共有781莊[4]卷1170。除對畿輔等莊直接管理外,還負責東北皇莊的一些事務。
管理東北莊具體事務。分別由盛京內務府、錦州內務府莊糧衙門、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管理。盛京內務府負責管理盛京莊一切事務。設總管大臣1人(盛京將軍兼任),協同管理大臣1人(由盛京五部侍郎中奏派兼攝),佐領3人,堂主事1人,委署主事1人[9]139。錦州莊糧衙門設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附設于錦州副都統衙門,因其只管錦州官莊,不涉及族的其他事務,與盛京內務府比規模小。內設委署主事1人,筆帖式3人,催長3人,拜唐阿6人,掌錦州官莊征租諸事務[9]140。打牲烏拉莊五所。由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兼理。設三品總管1人,四品銜翼長2人,五品銜委署翼長4人,各級屬官若干名。掌采取東珠、松子、蜂蜜、貢魚等及同地糧莊、官牛的飼養事務。其中直接分掌糧莊事務者驍騎校、章京、倉官及官莊領催,以驍騎校總轄之。章京以下分路(官莊分成四路),任其管理催收[10]568。
上述為內務府莊的管理機構,其具體職責如下:第一,編審莊丁。莊人丁的編審稱為比查壯丁,簡稱“比丁”。由內務府催長、領催定期編審,上報總管內務府。清廷規定內務府莊的壯丁,必須編入旗籍,定期檢查。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奏準:“凡撥置他處壯丁,仍歸原莊冊內編審。每三年由府委會計司官一人,前往屯莊編審丁冊,新丁年十六以上者增入,舊丁年七十以上者開除,逃亡者注冊,送會計司備案”[11]125。第二,催征莊糧。內務府與莊糧衙門最重要的職責是協助莊頭催征莊糧、莊銀,包括果子、人參、松子等。每年夏秋兩季催征。催征過程中,對按規定完征的莊田有權獎勵,對未完征的莊田有權懲罰。盛京內務府對各莊的賬目、銀兩、農副產品,年年清查,定期將每年收支、庫存上報總管內務府。第三,選拔莊頭。莊頭的選拔關系著整個皇莊的生產壯大情況。莊頭由于自然的生老病死出現出缺的情況,一般由莊頭的親族子弟或者推薦的親丁來補缺。同時需要經過層層上報,把詳細的情況由盛京內務府佐領上報給總管內務府,由總管內務府進行審核和批準。
(二)皇莊的內部結構
皇莊是由土地和人丁組成,構成皇莊基本社會形態。土地是按照相應情況進行劃分和繳納相應貢物。在皇莊的組織結構中,莊頭屬于管理人員,壯丁則進行生產生活工作。壯丁又有親疏遠近之分。莊頭戶下壯丁、寄養人丁。佃戶又有原佃戶和現佃戶之別。因出現時間不同,社會地位不同。
1.莊頭。莊頭為一莊之首,負責管理丁、佃戶,又定期征收莊租,納糧當差。清初莊頭僅是壯丁代表。每年將壯丁所交地租匯總,向上交納,而自身也承擔地租和差徭。隨著莊由農奴制向封建租佃制過渡,莊頭日益有利可圖,地位日漸提高。莊頭來源主要通過諭派、世襲、選充、補款等途徑。
諭派是由帝或內務府官員直接指派。文獻記載:“太祖高帝駐兵奉天建極時,有土著莊戶報效糧石,上嘉以報糧多的莊戶,派當頭目,封為糧莊頭,編入旗籍”。后來凡是投充均“以大戶地多定名莊頭”。不僅如此,對圈撥荒地所設的莊也于“殷實壯丁內選充莊頭”[1]138。
世襲是莊頭的主要來源。在清代很大一部分莊頭均由其子弟內選充。如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二月檔案記載:“伊圖管領下莊頭沈碩僧,年已六十三,且患病在身,業已辭退,遺缺已補放其子沈朋。喀伊吉利管領下莊頭何闊證,年已六十歲,因年邁不堪,將其辭退,遺缺已補放其子何天保”。即所謂“凡遇莊頭年邁辭退以及病故出缺,向準其呈請與長子,長孫、長曾孫襲替”[4]卷1219。
選充是產生莊頭的第三種方式。從有資格的莊頭子弟或異姓壯丁中選補。通常是原莊頭“欠糧或緣事革退及新設之莊”的情況下,方“于本莊及別屬壯丁內選補”[2]139。
莊頭產生第四種方式是包款接充。莊頭的主要任務是征納莊租。清初規定,莊頭務必按期催交地租,如所管之莊交納拖欠六成以上,即將莊頭革退,“其子弟親丁及異姓壯丁內,有情愿代完者,皆準其頂補”[8]99-127。
莊頭在內務府的監督下,實行管理莊園的職責。其職責不僅僅是負責租差的收納,而且負責官莊的日常行政事務。具體職責如下:(1)承領莊園。經營官莊的土地,賦予行政上的管理權。所謂“內務府莊頭官地,均系莊頭領名,糧由莊頭匯交”[1]142。官莊土地原則上不允許個人私有,莊頭只有管理的權力沒有所有權。(2)監督壯丁。莊頭對莊園和壯丁具有監督的權限。如莊頭在戶口調查,在比丁之際,調查所轄壯丁的戶口,做成簿冊,呈報內務府。還掌壯丁的任免權。莊頭據事實呈請罷免壯丁,同時對后任者有推薦權。(3)征納租差。內務府設莊頭最主要理由就是征納租差。所以租的征納是管理莊園的主要任務。“莊頭按租帳征租,而棉花莊頭及鹽莊頭按照發下的征租督促狀督征租差,若有抗違,解送官署處罰”[9]170。
2.壯丁。壯丁分為親丁、異姓壯丁、莊頭戶下壯丁、寄養人丁四種。由于親疏遠近不不同,與莊頭同族的一般稱為親丁,其他的為異姓壯丁。無論親丁、異姓壯丁身份是一樣的,都和莊頭一樣,入旗籍,載正冊,確定為旗人身份。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經理所分領的莊地,屆時向莊頭交納莊租。莊頭、親丁、異姓壯丁都是糧莊土地的占有者,他們世代使用土地,不斷分予子孫,從而使糧莊內部逐漸形成若干具有血緣關系的大家族。如莊頭董朝富領名冊地1 278畝,“后因族大支繁,地已按支分種”[1]146。莊頭戶下壯丁和寄養人丁是官莊內部載入另冊,不入旗籍的壯丁。他們多是發遣罪犯、契買奴仆、俘獲人口等,是壯丁中地位最低下者。
莊頭戶下壯丁、寄養人丁的來源如下:第一,帶地投充。盛京內務府莊大多是天命以后,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前后,明清戰爭時漢民帶地來投編設的,對此前文已述。第二,犯罪。據《大清律》記載:“犯有謀反大逆罪或謀叛罪者,除正犯及其父子、兄弟等處以死刑外,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及婦女妻妾皆沒為官奴,撥給官莊使役”[4]卷1219。官莊也有許多流遣罪犯,供莊頭使役,刑滿可以回原籍。第三,買賣。盛京各官莊有莊頭契買的壯丁,他們同旗下壯丁同樣,從事官莊的耕種。然而這些契頭壯丁是莊頭的奴仆,為戶下人,不能單獨構成一戶,附在家長戶籍冊上,比丁時不能列入正冊,稱為另冊。親丁、異姓壯丁主要來源是招墾流民。順康時期官莊大量的壯丁為招墾的漢族流民。據文獻記載:官莊漢人“則籍隸直隸、山東者為多,言順治三年移民實邊遷徙以至此者”[12]13。又載:其官莊“漢人土著者甚少,順治十年招民,由山東、直隸陸續遷來者”[13]25。這些開墾土地的漢民后來均編為內務府壯丁。
3.佃戶。佃戶是指租種糧莊土地的民人,分刨山戶和現租戶。刨山戶系建莊時期的民人或因刨種內務府莊荒地而被納入莊的民戶;現租戶系莊陸續代招的民戶,租耕莊地,交納地租。刨山戶即“原墾佃戶”,從順治年間就存在,但為數不多。刨山戶一般是刨墾在先,后劃歸內務府莊,定期納租,對莊地有永久的使用權,即“不欠租即不撤佃”[3]。刨山戶具有世襲的永佃權,并非一種純粹的租佃關系。現佃戶以契約或口頭的形式與莊頭或壯丁訂立租佃合同,這種現租戶,康熙年間就已產生,乾隆以后迅速發展。現租戶對莊地使用具有臨時性,所以對莊的隸屬關系不大,受室限制亦小,所以身份較自由。但常遭受莊主增租奪佃之苦。
四、內務府皇莊對壯丁的剝削
(一)地租剝削
順治、康熙年間,糧莊地租非常苛重。清廷規定:“凡莊賦皆準其地以為額”,即“以領地之多寡,定交糧之差等,當時,盛京莊每莊耕地720畝,額征120石,合倉石432石。畝折6倉斗”[4]卷94。同期奉天民地田斌,“每畝征銀3分。按清初糧價,每倉石折銀2錢計,6倉斗合銀1錢2分。盛京莊的正額租糧3倍于民地田賦。比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以后租額高出3倍、4倍”[14]623。這樣高的正額租糧迫使壯丁難以交納。皇莊剝削之重,令人吃驚。不僅如此,租糧常運到離莊二三百里不等之倉,這樣“往返拉運、守候,待收盤費等項,通共合計較比額米數糜費數倍”,使壯丁“徒費盤纏,而誤農事,人夫、車馬均屬勞瘁”[1]146。正額地租外,附加租名目繁多。如豬、鴨、鵝每年要定期貢納。豬、鴨出自盛京,鵝由盛京、錦州共出,一二等莊每年各納豬3口,三等3口[8]99-127。此外,皇帝巡幸費用也由各莊開銷。上述附加租物繁量多,是壯丁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不僅如此,莊的雜泛差派繁重。內務府常令壯丁修治馬圈,采集料草,喂養馬群。壯丁常被調往深山,采蜜伐木,捕捉水獺。
上述所列,無論正額地租、附加租,還是各種雜泛差役,其差役之重不言而喻。清廷將地租谷糧,各項差徭核計為十成,規定:“其拖欠五成以上至十成者,始革退莊頭,其拖欠一成至五成者,例不革退莊頭,僅按所欠成數分別鞭責,枷號治罪,仍勒限催追完交”[8]99-127。
(二)人身剝削
皇莊土地由清廷所有,耕墾者與經營者主要是漢人,內設莊頭、壯丁等。清朝初年,莊沿襲了入關前的農奴制生產關系。清初莊,每莊以十丁為限,一人為莊頭,領地720至780畝。壯丁繁衍則留于本莊,缺則補足。各莊給牛6至8頭,量給房屋,器皿、田種、口糧及衣服,免第一年錢糧[1]147。壯丁基本沒有什么生產資料,家中所有,都是官府的。
1.壯丁身份世襲制。為了維持官莊生產與人丁再生產,規定壯丁世代充當,即所謂“系上世代奴才”。并對壯丁的婚姻也加以限制,“壯丁女子則惟準與莊頭壯丁結親”[1]148。凡有違禁將女子寡婦私嫁于旗民人等,“則將女子父母及娶者一并治罪,并將已嫁之女子、寡婦抽回為內奴”[1]149。由于官莊對壯丁婚姻嚴格限制,致使許多壯丁難于成家。因此,清室只好用錢置買女子配給壯丁加以補救。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總管內務府責成管理盛京莊事務佐領安塔木“酌情動用盛京賣糧稅司銀兩買給女人”[1]149配與壯丁。
2.壯丁遷徙束縛。一般的壯丁出行和舉家遷徙是受限制的。導致他們行動極為不便,只能依附于土地進行生產勞作,不能隨意脫離土地和莊園。對壯丁逃跑者處罰極嚴。清初法令規定:“凡奉天府居住旗下人逃走者,盛京刑部審理,分別次數,照例治罪”。所以壯丁踏入官莊,猶“久沉淵底,無升天之望”[1]150。
3.壯丁可以隨意買賣。清廷規定:“其人丁、地畝典賣悉由本主自便”[1]150。而且壯丁也作為室私產,可由帝任意支配,分賜給子孫莊田時,連同該莊壯丁一起分賜。分賜而外,皇莊也根據各莊丁額情況在各莊之間調整。
4.壯丁及其子女發展限制。壯丁幾乎沒有成為官紳的可能性,其子女也不能躋身上層社會。因此許多壯丁雖讀書很多,才華橫溢,辦事能力較強,卻很難進入仕途發展。
5.壯丁還受地租與各種差役的盤剝。當時每莊給地120畝,“一夫種二十,收谷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為等”[15]45。這就導致許多壯丁除了繳納稅收和地租之外,很難養活一家老小,處境十分艱難。此外,正額地租還應由壯丁運到指定地點交納,使壯丁受往返之勞。除此而外,附加租繁多。吉林官莊每莊要交“草三百束,豬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16]3。錦州官莊,每年每莊必交茜草、線麻、小根菜、柳蒿菜、黃花菜等。不僅如此,還要承擔各種差役,壯丁常常被征派采蜜伐木,捕捉水產,包括清帝東巡所需人力、物力也由官莊壯丁負擔。
綜上所述,皇莊的壯丁領種莊地,繳納高額地租,負擔繁重徭役,世代束縛在官莊的土地上,雖不是奴隸,卻是典型農奴。這種超經濟的強制在清前期的皇莊得到充分的反映。
參考文獻:
[1]衣興國,刁書仁.近三百年東北土地開發史[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130.
[2]馬汝珩,成崇德.清代邊疆開發[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256.
[3]曹明.1860-1911年東北地區招民墾荒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5.
[4]孔經緯.東北經濟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26.
[5]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107[M].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出版,1983:645.
[6][清]阿桂,等纂修.盛京通志:卷23[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7:456.
[7]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268.
[8]周遠廉,楊學琛.關于清代皇莊的幾個問題[J].歷史研究,1965(3):99-127.
[9][日]滿洲舊慣調查報告.內務府官莊[M].株式會社,1935:140.
[10]長順修.吉林通志:卷38[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568.
[11]烏廷玉,衣保中.清代滿洲土地制度研究[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25.
[12][清]管鳳和.新民府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13.
[13]海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海城縣志[M].海城:海城縣辦公室,1987:25.
[14]清朝文獻通考:卷5:田賦五[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623. [15][清]顧永年,楊賓.柳邊紀略[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45.
[16][清]吳臣,等.寧古塔紀略[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