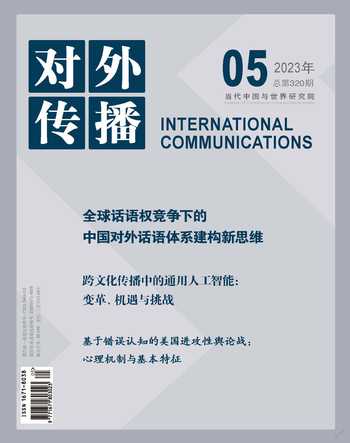身份政治與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的新階段
楊雪冬 莫明墉
【內(nèi)容提要】隨著西方社會中身份政治的加劇,全球話語體系場的競爭進入新的階段,國內(nèi)話語與全球話語兩個場域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身份政治不僅造成了國內(nèi)話語場的碎片化、對立化、非理性,而且嚴重干擾著全球話語體系已經(jīng)明確的議題共識,誘發(fā)話語冷戰(zhàn)。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的本質(zhì)是各國發(fā)展道路的競爭,反映了非西方國家發(fā)展道路選擇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中國作為全球話語體系的重要塑造者,應該始終堅持和倡導在全球話語體系構(gòu)建中的對話和互鑒,在全球范圍積極倡導和推動以發(fā)展治理安全為主題的實踐優(yōu)先,同時要始終堅持提升國家治理績效,改進各個群體福祉,勇于并善于承擔全球范圍對話交流和塑造共識的責任。
【關(guān)鍵詞】身份政治 全球話語體系 發(fā)展道路 全球文明
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是全球力量格局變動在觀念、理論和輿論場域的反應,既深受全球力量格局調(diào)整轉(zhuǎn)化的影響,也會引導,乃至塑造全球力量格局的走向和形態(tài)。無論是在冷戰(zhàn)期間,還是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我們都可以看到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產(chǎn)生的社會政治后果,尤其是陷入話語體系競爭泥淖的超級大國在國內(nèi)和國際場景中的窘態(tài)。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全球力量格局加劇調(diào)整,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交疊出現(xiàn),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力量,通過各種形式的“去全球化”政策、“逆全球化”舉動,力圖阻塞、延緩全球力量格局的調(diào)整變動,也攪動著一度平靜的全球話語體系場,明確地將一些深刻影響全球力量格局的國家定位為戰(zhàn)略對手,乃至敵人,從而使全球話語體系競爭加劇,在日益濃烈的冷戰(zhàn)氣氛中不時嗅到“熱戰(zhàn)”的硝煙。在這種偏執(zhí)的思維影響下,美國在國內(nèi)外四處渲染“中國威脅”,宣揚零和博弈話語,強迫各國選邊站,并在政治、經(jīng)濟、科技等多領(lǐng)域主動挑釁中國,企圖拉中國下水,參與新冷戰(zhàn)。
身份政治在西方國內(nèi)政治的全面登場,為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注入了新動力,將其推進到了新階段。國內(nèi)話語與全球話語兩個場域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身份政治不僅造成了國內(nèi)話語場的碎片化、對立化,而且干擾著全球話語體系已經(jīng)明確的議題共識,比如氣候變化、生態(tài)保護。一些國家有意輸出國內(nèi)身份政治議題,使之國際化,乃至全球化,從而在轉(zhuǎn)移國內(nèi)話語矛盾的同時,也干擾到了其他國家的話語場議程,進而造成了全球話語體系的無序競爭。
一、 身份政治正在成為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的顯性驅(qū)動力
身份政治是以諸如族群、信仰、性別、性取向等長期被制度化民族國家認同所遮蔽或壓制的身份標簽,來構(gòu)建團體認同,進而實現(xiàn)權(quán)利訴求的集體行動方式。身份決定立場,立場是不妥協(xié)的。身份政治有兩個鮮明特點:
一是以維護多元性反對多元化。盡管各類身份政治運動往往以例如少數(shù)族裔、性少數(shù)群體等“社會弱勢群體”的平權(quán)運動名義進行,但正是因為其對身份標簽的強調(diào),會使得其顯露出明確邊界,傾向排他性,進而會強化清晰的敵我劃分。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因身份政治而被調(diào)動的集體行動者們所追求的是尊嚴,其需要的是一種來自他者的承認。①因此,作為承認的提供方,這個他者必然應當是不可被原諒且不可被吸納的,否則身份持有者不僅會產(chǎn)生對自我認知的迷失感,還可能因這個承認可能被拖欠而產(chǎn)生不安全感。這也就是當部分白人男性在借用性別流動理論等平權(quán)運動者們的慣用話語體系,以例如“我不自我認同為白男”“逆向種族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眾生平等(All lives matter)”等話語來試圖規(guī)避來自四面八方的性別與種族霸權(quán)指責時,不僅不會被平權(quán)運動者們接受,甚至會被其進一步批判為一種可恥的、逃避責任的作弊行為的原因。
二是以釋放激情對抗政治理性。如福山所說,身份政治的興起源于對尊嚴的渴求,而這是一種來自人類內(nèi)心深處的激情。②正是這種激情,賦予了身份政治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而也恰恰是身份政治所含的天然激情,使得其與民主政治體制中對理性公民的期待產(chǎn)生了根本對立。當一群身份高度同質(zhì)化的群體聚在一起集體表達訴求時,往往會聚生出一些過于以自我為中心的理想化訴求,而忽略了群體外的他者的實際境遇。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其官網(wǎng)上所提到的“禁止特朗普參選”“禁止特朗普使用社交媒體”“消減警察預算”等諸多充滿激情且沒有政治可行性的訴求。③因此,在現(xiàn)實政治中,不難看到一場場因身份政治而起的社會運動,往往會因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而控制不住其政治激情,最終發(fā)展出對政治體制的沖擊以及對社會穩(wěn)定的破壞。
身份政治在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凸顯,也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下的全球話語體系構(gòu)建,為西方惡化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提供了條件。
第一,身份政治塑造著國家間制度、文化的鄙視鏈。身份政治的思維邏輯中存在自我與他者的二分法,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制度、文化被割裂性地視為比較主體,從而人為地制造出高級與低級的文明鄙視鏈。例如,在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書中,④由于身份劃分,原本如光譜般連續(xù)共生的人類文明就被一塊塊地割裂,而以這種身份政治視角看待世界文明,必然就會因過于著眼于文明的邊界而強調(diào)文明的沖突與碰撞。與此同時,正是在這種文明高低鄙視鏈的邏輯假設(shè)下,文明被默認為總是有擴張與征服的野心,從而總會與其他文明發(fā)生碰撞。然而,這種人為的高低劃分本質(zhì)上是對世界多樣性的錯誤構(gòu)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yōu)劣之分。”⑤
第二,身份政治的蔓延加劇了西方國家制度運行的僵局和停滯,加速了國內(nèi)矛盾的全球外溢。一方面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革命催生了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民眾在得到物質(zhì)層面的滿足以及技術(shù)層面的充分賦能后,開始追求更高層面的表達欲望;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時代,政治家對民眾話語的簡單迎合似乎很容易被淹沒。為了順利贏得民眾手里的選票,美國政治家們開始使用高度激化的身份政治話語,通過激烈的情感表演來試圖觸發(fā)民眾內(nèi)心深處的共鳴,正如在2016年總統(tǒng)大選中一路狂飆的特朗普。美國國內(nèi)的政治家們似乎并不關(guān)心身份政治帶來的社會撕裂,他們甚至將其作為一種實現(xiàn)快速上位的政治手段。與此同時,對身份政治使用嫻熟的美國政治家們,還試圖在國際層面復刻其國內(nèi)的沖突矛盾,以打斷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和平發(fā)展進程。為了自身霸權(quán)的考量,美國本末倒置,罔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shè),無視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疾病控制、饑餓與貧困消除等諸多需要國際合作才能應對的世界性難題,轉(zhuǎn)而將重心放在如何激化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渲染“中國威脅”與世界民主體系的危機。
第三,身份政治對立場優(yōu)先的強調(diào),使得全球話語場域中的話語競爭失去了理性的有力制約。如果任由當下的話語建構(gòu)過程被以國家為身份的“國家身份政治”影響,那么最終構(gòu)建的話語體系便會呈現(xiàn)出身份政治特有的高度排外性與反建制性。美國政治界當前的各種反華政策,就是一種通過外部建構(gòu)敵人,來分散國內(nèi)矛盾的政治手段。在部分美國政客看來,全球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大流行、甚至連美國自己國內(nèi)的通貨膨脹,都是責任在中方。對美國,甚至聯(lián)合國而言,這種“甩鍋”的手段可能在短期內(nèi)對國內(nèi)政治團結(jié)與共識凝聚是有效的,但長期來看,不正視且任由自身的內(nèi)部問題惡化,并在國際層面持續(xù)惡化外部環(huán)境,會使得美國遲早有一天同時面臨內(nèi)憂與外患。
第四,一些國家利用身份政治議題,將本國議程移植到他國,通過支持鼓勵個別少數(shù)群體,夸大和制造基于認同的矛盾,引發(fā)了國家間新的沖突和對抗熱點。多年來,一些美國政客頻繁炒作所謂的“新疆問題”,通過將美國自己的種族矛盾邏輯投射到中國境內(nèi),試圖在中國復刻已經(jīng)在美國內(nèi)部四處泛濫的身份政治沖突,從而達到擾亂新疆,并遏制中國平穩(wěn)發(fā)展的目的。但顯然,這種以己度人的荒謬方式只會反過來彰顯出美國政界中深深的種族主義,以及其對中華民族融合歷史的粗鄙無知。但不得不看到的是,由于美國對世界體系的主導,身份政治這一美式政治已經(jīng)悄無聲息地潛入到了向世界敞開大門多年的中國。近年來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區(qū)的身份政治苗頭的萌發(fā),已經(jīng)給中國社會的平穩(wěn)發(fā)展留下了現(xiàn)實隱患。
第五,身份政治與價值觀政治的合流,塑造了新冷戰(zhàn)形態(tài)。卡斯·穆德(Cas Mudde)曾將民粹主義稱作一種“薄”的意識形態(tài),因為其僅僅提供了一個人民與精英對立的框架,而正因如此,民粹主義可以與其他各種“薄”或“厚”的主義,例如民族主義等結(jié)合起來,從而實現(xiàn)具體政治議程的推進。⑥而正如上文所言,身份政治同樣具備民粹主義的各種特征,因此其亦可以被稱為一種“薄”的意識形態(tài),從而實現(xiàn)與具體價值觀政治的結(jié)合。在當下,人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美國為了在當代國際社會復刻出一種冷戰(zhàn)形態(tài)并盡可能地強迫世界各國選邊站,將身份政治的邏輯捆綁到了諸多傳統(tǒng)的價值議題上,例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的獨立、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對立等等。
二、 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本質(zhì)是發(fā)展道路的競爭
話語作為語言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和語言一樣,是“一定共同體的產(chǎn)物”,⑦并隨著社會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因此也具有實踐性、互動性,是反映現(xiàn)實的意識。盡管話語可以被構(gòu)建出來,具有主觀性、相對獨立性、自成體系性等特征,但歸根到底,凡是用語言表現(xiàn)出來的各種精神生產(chǎn),包括表現(xiàn)為某個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都不過是人們物質(zhì)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⑧
政治實踐是塑造政治話語的根本力量,全球話語體系的競爭,從根本上說是在全球場景中,各國發(fā)展道路的全面展示和充分比較。在全球信息社會中,隨著交往的擴展和深化,各國的發(fā)展道路都被置于無影燈下,優(yōu)點和缺點均毫無保留地展現(xiàn)了出來,接受著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個人和組織的審視和檢驗。這為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的理性化提供了客觀條件。
進而言之,身份政治激發(fā)出來的激情和非理性終究會淡化、消解,人們終究會回到日常生活,面對生活現(xiàn)實,話語體系的構(gòu)建也要從發(fā)展實踐、日常生活的基礎(chǔ)之中獲得不竭的動力和活力,從而不斷去除話語體系本身的虛偽性,展現(xiàn)話語內(nèi)在的對話本質(zhì)。正如巴赫金所說:“語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間的對話交際之中。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lǐng)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等),無不滲透著對話關(guān)系。”⑨
西方話語體系雖然在當下取得了“普世性”地位,但其所依賴的現(xiàn)代化道路實踐是無法被復制的。西方式民主的誕生源于資產(chǎn)階級崛起對國家執(zhí)政者的分權(quán)制衡,其起初仍是一種由少數(shù)精英執(zhí)掌的特權(quán)政體,經(jīng)過漫長的民權(quán)運動的抗爭,精英不得已而不斷向下釋放權(quán)力,才最終發(fā)展成為當今成熟的西方民主體制。但這段歷史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普遍將資本主義作為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而這種片面地把自身的特殊實踐經(jīng)驗作為世界各國均應當遵循的普遍發(fā)展路徑的行為,忽視了西方式現(xiàn)代化實踐中的諸多問題以及其在當代的不可復制性,例如殖民主義、對環(huán)境的破壞、對勞工的剝削、高度的貧富差距等等。二戰(zhàn)后歐亞大陸百廢待興,實力強勁的美國得以趁虛而入建立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如沃勒斯坦所論證的那樣,處在世界經(jīng)濟網(wǎng)絡中心位置的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利用先行現(xiàn)代化而積累下的實力優(yōu)勢,強迫發(fā)展中國家接受不平等的分工以及分配關(guān)系,使其被困在半邊緣以及邊緣位置并接受來自中心國家的剝削。⑩
盡管冷戰(zhàn)結(jié)束后,新興國家力量開始崛起,全球力量格局出現(xiàn)變化,美國國內(nèi)矛盾持續(xù)爆發(fā),綜合實力也相對下降,但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將自己定位為全球話語體系主導者、塑造者的想象,反而利用話語體系來制造新的對抗,并繼續(xù)營造觀念上的假象,以維護自己在發(fā)展道路選擇上的“最終裁判者”地位。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jīng)過70余年的艱苦摸索,中國人民在黨的領(lǐng)導下,通過自力更生、團結(jié)奮斗、和平發(fā)展,不僅創(chuàng)造了世所罕見的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xiàn)代化、兩極分化的現(xiàn)代化、物質(zhì)主義膨脹的現(xiàn)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xiàn)代化老路,拓展了發(fā)展中國家走向現(xiàn)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的實踐道路充分證明,“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jié)論的破產(chǎn),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chǎn)。”11
改革開放是人類社會的一場偉大實踐,中國的發(fā)展是對全球發(fā)展的偉大貢獻,在不到70年的時間內(nèi),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12這場在不到半個世紀內(nèi)發(fā)生的偉大變革充分說明,任何一套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體系,雖然可以短時間束縛人民的頭腦和行為,但無法從根本上束縛住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必然會隨著實踐的發(fā)展、人民認識的提升,被徹底拋棄,并被新的更加包容開放團結(jié)的話語體系所代替。
改革開放實踐證明了,在全球話語場中,只要放棄意識形態(tài)偏見,尊重各國發(fā)展實踐探索,是可以將各國話語體系的競爭轉(zhuǎn)化為良性對話交流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與外部世界在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等多個維度上是隔離的、對抗的,而改革開放的出現(xiàn)則扭轉(zhuǎn)了這一格局,帶來了中國與世界關(guān)系的歷史性變革,世界見證了一個自信、開放與包容的中國,也收獲到了共同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成果。這種共同發(fā)展實踐顯然不同于西方話語體系的經(jīng)典說教。
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的治理績效,顯示了中國制度在全球化時代的優(yōu)勢,也印證了“定于一尊”式的制度偏見的荒謬。西方學界長期立場先行,將中國的制度視為“非常態(tài)”存在,因而對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抗擊各類風險和沖擊的制度韌性,為全體人民持續(xù)提供福祉的制度績效和能力持懷疑乃至悲觀態(tài)度。但改革開放的實踐成就對這些傲慢與偏見給予了有力回應。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在全球話語體系競爭中,任何國家固守意識形態(tài)偏見和制度“優(yōu)越感”,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三、 避免陷入身份政治制造的話語競爭困境
全球話語體系的無序競爭,不僅會影響到各國以合適的、符合本國國情的方式處理好國內(nèi)矛盾,也會干擾不斷多樣化復雜化的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因此,努力避免陷入身份政治制造的話語體系競爭困境,對于各國,尤其是全力走向民族偉大復興、努力為人類和平發(fā)展事業(yè)做出更大貢獻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
第一,要始終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gòu)建放在首位,避免身份政治對于國家整體性認同的割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正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guān)系,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xiàn)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xiàn)好各民族具體利益,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shè)。”13避免身份割裂與促進共同體意識的基礎(chǔ)前提就是社會的高度融合,而在當前這個時代背景下,實現(xiàn)不同民族與不同省市民眾的進一步融合,就是要順應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的規(guī)律,調(diào)整和完善相關(guān)政策法規(guī),清除社會融合的體制機制以及觀念心理的阻礙。
第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以法律保障民眾的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guī)體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quán)益。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于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quán)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14要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gòu)建,首先要避免出現(xiàn)基于身份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不平等待遇。要認真分析其他多民族國家在解決國內(nèi)多民族認同關(guān)系方面的經(jīng)驗和做法,避免用形式平等的制度安排人為拉大社會心理落差,加劇認同分裂,乃至對立的誤區(qū)。只有擺脫身份政治的慣性思維,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有效化解民眾心中的尊嚴落差感,從而防止身份政治對共同體意識構(gòu)建的破壞。
第三,始終以提升和改進國家治理績效為核心,夯實全球話語體系構(gòu)建的基礎(chǔ)。身份政治凸顯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發(fā)展的不平等不均衡。只有不斷地提高國家治理績效,滿足各個群體的物質(zhì)和精神需求,才能避免身份政治的非理性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現(xiàn)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現(xiàn)代化道路最終能否走得通、行得穩(wěn),關(guān)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現(xiàn)代化不僅要看紙面上的指標數(shù)據(jù),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15只有讓各個群體在祖國大地上親身感受到并享受到國家發(fā)展與共同富裕帶來的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滿足,才能讓其理性地把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擺在諸多身份中的優(yōu)先位次。
第四,始終堅持全球話語體系構(gòu)建中的對話和互鑒,以對話交流對沖和約束全球話語體系競爭的可能性失序。盡管“文明的沖突”這個預言依然在全球上空游蕩,并借助身份政治還魂顯靈,但是在全球風險和不確定性不斷衍生中,我們看到的主流是全球文明的曙光,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不斷加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diào)的:“各種文明本沒有沖突,只是要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16中國的話語體系具有先天的全球性,要始終堅守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繼續(xù)將文明間和平共生、交流融合的理念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并推向世界舞臺的中央。
第五,在全球范圍積極倡導發(fā)展治理安全為主題的實踐優(yōu)先,以塑造全球話語體系的良性競爭狀態(tài)。在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動蕩和不確定性將成為常態(tài),這就更需要放棄在話語上制造敵對和對抗,回到能夠真正應對不確定性的發(fā)展、治理、安全實踐中。中國先后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目的就是為了將全球話語體系競爭引入良性渠道,推動全球發(fā)展和維護世界安全,同時避免少數(shù)國家以抽象的身份政治邏輯,捆綁各類意識形態(tài)去攻擊他國,展開零和博弈式的惡性競爭。后者這種行為,不僅損人不利己,還會給國際社會造成惡劣后果,引發(fā)更大的危機。
第六,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要勇于并善于承擔以對話為核心的全球話語體系的建構(gòu)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nèi)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tài)對抗。” 17因此,面對全球話語競爭,中國應采取的策略,不僅是勇于善于斗爭,而且要積極建構(gòu),不僅要直面挑釁,敢于回應,而且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的不懈團結(jié)和塑造共識。聯(lián)合能夠聯(lián)合的一切國際力量,促進更廣范圍、更深入的對話,擴大全球共識圈和全球話語共同體,實現(xiàn)更多的全球?qū)嵺`行動,是全球話語體系競爭應該堅守的“正道”。
楊雪冬系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莫明墉系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rofile Books, 2018. .
②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rofile Books, 2018.
③“BLM Demands.” Black Lives Matter. Accessed April 6, 2023. https:// blacklivesmatter.com/blm-demands/.
④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⑤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 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國政府網(wǎng),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 content_5395471.htm ,2019年5月15日。
⑥Mudde, Cas.“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 no. 4(2004): 541-563.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頁。
⑨《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頁。
⑩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lǐng)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網(wǎng),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583383,2014年2月17日。
12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wǎng), http://www. gov.cn/xinwen/2018-05/04/content_5288061.htm?cid=303,2018年5月4日。
13習近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zhì)量發(fā)展》,人民網(wǎng),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829/c1024-32211248.html,2021年8月29日。
14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jié)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wǎng), http://www. 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113.htm,2019年9月27日。
15習近平:《攜手同行現(xiàn)代化之路 ——在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網(wǎng),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645371,2023年3月15日。
16同⑤。
17同15。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