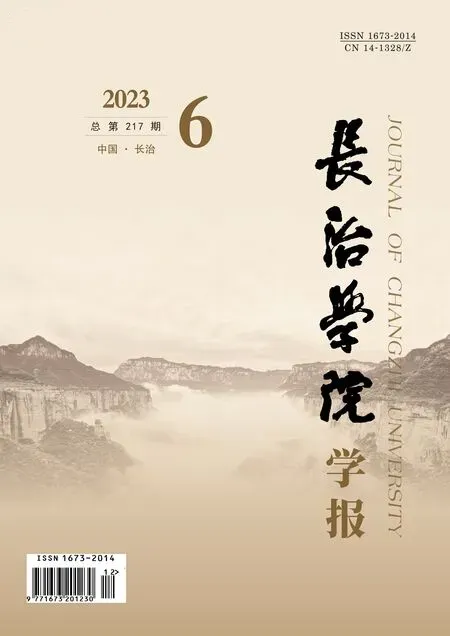山之有神:傳統時期村民對山的精神構建
——以山西澤州地區關于山的信仰為中心
楊 波
(山西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山區的村民常常需要和山打交道,他們在南山種樹,北山燒香,東山放羊,西山求雨,他們知道翻過東山是另一個村,而那個村的人卻用西山來稱呼同一座山,山是山區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地理學角度給山下個定義是容易的,無非是用相對高差或者坡度等地理指標來界定。然而這樣的定義是蒼白無力的,要想真正理解山對村民的意義需要回到豐富的歷史事實之中。澤州多山,顧祖禹說:“州境山谷高深,道路險窄。”[1]村落碑文中這樣描述山:“如吾鄉之北,有山名曰白華山,層疊而來,其風脈蓋有本矣。下□四境之內,桑株林木,阜林平川,一為取用之資,一為風脈之本,甚不可有以剝削也。”①道光十年《(無題名禁碑)》,現存高平秦家莊玉皇廟戲臺西側,壁碑,高79cm,寬37cm。一方面,山為“取用之資”,既為人類提供了各種物質資源(植物、動物與礦物),又在交通上帶來阻隔。另一方面,山為“風脈之本”,影響著村民的思想和文化,村民又反過來在精神文化上構建山的形象。村民在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完成著對山這種自然物的“人化”過程。本文主要是從民間信仰的角度關注村民對山的精神構建。
一、山的人格化:山與山神信仰
山與信仰的關系在最淺層面上表現為山的人格化和神靈化。澤州山神信仰有其不同于其它類型信仰的特征。
和其它山區一樣,澤州地區也廣泛存在著將山“神靈化”和“人格化”的祭祀場所——山神廟。澤州的人們是這樣理解山神的:
從來山之有神,所以庇山中之老幼男女而無物患也;神之在山,所以驅山中之虎豹財狼不為人害也。故山各有神。村之近山者,往往廟宇恢宏。神靈赫濯,四時之享祀不忒,一時之靈應昭彰,鄉村無不崇祀焉。②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山神廟碑記》,現存高平東山村山神廟,笏首方趺,高160cm,寬58cm,厚22cm。
首先,無論是“山之有神”的“無物患”,還是“神之在山”的“不為害”,兩種說法對山神的理解都是中性的表達,“患”和“害”都是擔憂的詞匯,似乎山神并不是賜福的神,而是以“御災捍患”為主的神。這表現出人們對于山的一種陌生感和畏懼感。其次,碑文也強調了山神奉祀的普遍性:“鄉村無不崇祀焉”,這話并不夸張,澤州地區幾乎每個村都有山,凡有山皆有山神廟。最后,山神廟雖然很多,但是山神在整個澤州的神靈譜系中是很小的神,地位很低。原因就在于山神所管轄的范圍是很小的。“杜贊奇曾經饒有興趣的引述滿鐵調查中關于土地神和關帝的區別。“村村都有土地廟”和“村村都有關帝廟”是完全不同的現象。關帝是管轄所有村莊的大神,而每一個土地都是只管轄自己這一小片土地。[2]在這一點上,山神和土地是類似的。總的來說,山神是以“御災捍患”為主的神,在山區普遍存在,但規模和輻射范圍都很小。
從歷史的演進過程來看,山神廟也有其特色。即便是在澤州這種廟宇林立、碑刻眾多的地區,獨立的山神廟的修繕碑極少出現,出現山神廟記載的碑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地畝四至碑。宋金時期碑刻中就出現了不少山神廟的例子。這些例子幾乎都是出現在大型廟宇的廟產四至碑中,山神廟在其中是作為地理標志出現的。例如定林寺金代碑:“本寺地土數目:一處,山神廟嶺西地一十五段,計九十八畝。”①金大定二年《大金澤州高平縣定林寺重修善法羅漢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記》,現存高平米山鎮定林寺,笏首方趺,高116cm,寬65cm,厚22cm。山以山神廟而得名,可見山神廟創建很早。類似這樣的碑在明清時期屢有出現,性質幾乎完全一樣。例如乾隆四十八年高平企甲院二仙廟村社地畝四至碑、乾隆四十九年高平李莊村觀音堂《李莊村合社公議五處神廟四至碑記》等等。山神廟在這里具有某種山嶺產權宣示標志的含義。另一方面,修繕山神廟的記載常常出現在其它更大的廟中,在全村范圍的較大修廟工程中偶爾提及山神廟。例如同治九年高平石門玉皇廟的《重修補修廟宇碑記》、道光七年東溝常家溝炎帝廟《炎帝廟古佛堂觀音堂山神廟補修碑記》。類似例子太多,不再一一列舉。這表明山神廟出現很早,但一直處于停滯的狀態,基本是不變化的。總的來說,山神廟產生很早,但卻始終停留在一種比較原始的階段,數量多、規模小、地位低、輻射范圍小。
澤州村落大多散布在群山之間的山谷、河谷和盆地之中。山雖然不是和村落對立的,但又是和村落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如果說村落對于村民來說是完全熟悉的、敞開的,那么,山在一定程度上是陌生的、被遮蔽的,山還存在一些模糊的、未知的東西。這種遮蔽既帶來了恐懼與依賴,又帶來了好奇與探究。簡言之,人類聚落與其周圍的山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信仰與山的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從山神信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張力的存在。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人們對山可以有一種趨利(利用山的資源)避害(規避山的風險)的行為。從精神文化的角度說,人們對山是既依賴又害怕,這種復雜而又矛盾的集體心理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非常重視對居住地的選擇,選擇的主要依據就是聚落周圍的山水環境,其中山是最主要的,這就是風水信仰。
二、山的結構化:山與風水信仰
如果說山神反映的是老百姓一種模糊的、非系統化的、比較原始的集體心理的話,那么風水信仰②眾所周知,風水所代表的術數這種知識形態漢代一度地位很高,位列七略之一。但是,至少在宋以后,雖然術數作為一種“一般思想”仍然很重要,但其主要性質是民間的,邵康節幾乎成為那個時代之后的絕響,此后鮮有進入主流的高級知識分子再醉心于術數的研究。就是傳統社會底層文人所完成的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從這個角度說,風水信仰比山神信仰更加精致和復雜。澤州的風水信仰主要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首先,風水信仰中的山有龍脈、來龍、來脈和風脈的說法,意思基本一致。具體來說,還有祖山、主山、青龍、白虎、案山和朝山等一系列的說法,這些風水中用來描述山的用語都是給山賦予了一種文化意義。在中國傳統復雜的風水理論和實踐中,山作為一種文化要素參與到了村落的構成中。風水信仰對村民影響很大:
中村寧靜觀,即炎帝廟,為一村主廟。鹿野園,即觀音坡,為一村主山。統屬闔村十小社及西溝一小社。凡廟、主山之事,十一社共相輔助,而觀音坡山中之木,惟主廟、主山之工得以砍伐使用,十一小社不得妄動。①民國八年《中村炎帝大社整理觀音坡地界及主權碑記》,現存高平中村觀音寺。
以中村為核心的、由十一個小社組成的村社集群既是圍繞著炎帝廟這個主廟展開的,又是圍繞著觀音坡這個主山展開的。主廟和主山共同構成了村莊的精神核心。風水理論賦予村落周圍的山一種文化結構,在村民的信仰體系中占有了原比原始膚淺的山神要重要的地位。
其次,上述例子也體現出作為地理要素的龍脈與作為人工建筑的廟宇結合了起來,它們相互支撐,其作用得到了強化。這進一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正向的功能強化:“村北大廟,乃合村龍脈托落之地,群神會聚之所。凡在村中者,家不拘貧富,人無論窮通,其興衰禍福、吉兇災祥、嗣續繁衍、壽命延長,均賴神靈之保佑焉。”②道光十年《重修大廟并合村堂閣殿宇表頌碑記》,現存高平市神農鎮中廟村炎帝廟二進山門內西側,笏首方蚨,高218cm,寬75cm,厚25cm。“龍脈托落之地”成為了最佳的建廟之所,山強化了廟,廟又反過來強化了山。另一種更為常見的情況就是用廟宇來補龍脈的缺,彌補龍脈的不足:
請堪輿先生言說廟門不宜正開,理宜改為偏門,東南、東北俱有缺陷,東邊居民亦□散渙,理宜修補,始為一村之盛,……卜吉日以鳩工,祖廟寅門改為亥門,正東修文昌閣一所,東北修關帝廟一座,東南修文筆一支,庶幾散渙者而完聚,缺陷者而豐滿矣,豈非村中只盛舉乎。③道光十七年《創修關帝廟文昌閣文筆改修正門碑記》,現存高平馮莊村小馮莊自然村觀音閣。
馮莊村小馮莊自然村的這次修廟工程規模不小,可以說整個村莊的廟宇格局都是按照堪輿先生的指點來建設的,風水其實起到了村落規劃的意義。總之,廟(及其它風水建筑)與山的結合是“天”和“人”的結合,人力可以順天而興,也可以逆天而補,“天人合一”進一步強化了山在村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
最后,為了保護龍脈,官方和民間都會制定禁止興窯挖礦的禁令或規約,這類碑刻數量極多:
高平縣正堂白,為永禁鑿窯保存龍脈事。照得大糧山為米山鎮來龍正脈,蓋鎮生齒所系,千家墳墓攸關。亙古以來,從無行□取煤之事。因被奸民張國龍、張德威鑿山開窯,有傷龍脈。本縣親履其地,立行填塞,仍勒石永遠禁止。④康熙十一年《高平縣正堂永禁鑿窯碑》,現存高平米山鎮定林寺。
這種禁令和上面的建廟、建塔成為互補,一是以人工建筑來修補龍脈之缺憾,另一個是禁止破壞龍脈的行為,體現了同樣的文化心理。
在風水信仰中,山決定了氣的流行匯聚的結構,由此衍生出復雜的理論體系,這種理解遠比山神要復雜,也更精致,但風水仍然是人的居住環境,人和山仍然是對立的,山仍然是為人的生活服務的工具,風水信仰中仍然充滿著對象化的色彩。
三、山神的異變:山神與村落主神
在濫封祀典的宋代,一大批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山神成批量的出現在《宋會要》之中。在宋代社會經濟和民間信仰高度發展的背景之下,山神也開始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異變,和村落主神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
有些神靈在澤州村落信仰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常常是村落主廟或大廟的主祀神靈,這些神靈就可以稱作村落主神。三嵕是澤州地區常見的一種村落主神。高平河西村宋天圣十年碑中的三嵕神靈有明顯的山神特點:
春秋冬夏,揮律候( )以明定四時;暑往寒來,吹灰管而潛分八節。而又三才共立,七氣同分,顯威風而以鎮云雷,化雨露而蘇草木;牧圉得犧牲之滋盛,丁壯有黍稷豐登。在境土(圡)之黎民,賴神祇之重德。⑤天圣十年(1032)《三嵕廟門樓下石砌基階銘》,現存高平河西鎮河西村三嵕廟。
這一段話主要是說天時、氣候以及由它們所決定的好的收成,其中“牧圉”是指牧業,而“黍稷”是說農業。更多碑文直接將三嵕視作山神。北宋宣和四年《紫云山新建靈貺廟記》:“潞之長子縣紫云山靈貺廟者,實出于屯留三嵕,蓋山神也,或謂后羿,或曰三王,語尤不經,莫可考據。有司以靈應事跡上之,朝廷賜名廟額。”[3]金崇慶元年《創修靈貺廟記》也有“夫建祠立像,為神化去,與民祈福。有在世立功于民靈顯致應其所祀者□□可所掩。今端氏明莊紫金山巔有靈貺廟者,實出屯留三嵕。蓋山神也,或□□羿,或曰三王,語尤不經,無可考據。”①崇慶元年《創修靈貺廟記》,現存山西高平寺莊鎮明家溝村公家山自然村。《宋會要》明確表明三嵕的山神性質:“三嵕山神祠,在屯留縣。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賜廟額‘靈貺’。”[4]《宋會要》這部分記載也是在“山川祠”的類別之中。總之,官方和民間兩方面的史料都表明三嵕是山神是當時的共識。
雖然像“三嵕”一樣以山的名字流傳下來成為村落主神的例子非常罕見,但其實其它村落主神大多也和山的信仰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澤州地區影響巨大的湯王信仰和析城山山神有密切關系。《宋會要》載“析神山神祠,在澤州陽城縣,神宗熙寧十年封誠應侯。”②《宋會要輯稿》第20 冊《禮》20《山川祠》之91,中華書局,1957 年,第810 頁。析城山神祠是奉祀山神的,與湯王并不是一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神靈。政和六年《敕封嘉潤公記》說得很清楚:“政和六年四月一日,敕中書省、尚書省:三月二十九日奉圣旨,析城山商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為額,析城山山神誠應侯,可特封嘉潤公。”[5]山神和湯王是同時得到賜封的。何以湯王會和析城山神緊密聯系在一起呢?《太平寰宇記》載“析城山,在縣西南七十五里……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于此。”[6]析城山上有湯王池這樣的遺跡,流傳著商湯在此禱雨的傳說。這種傳說可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至少在五代到宋初已經很流行,才會被收入地理志中。無獨有偶,羊頭山與炎帝也是類似的情況。《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五引用的《上黨記》“神農廟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一白,呼為神農井。”③《上黨記》是山西現存最早地方志,學者考證其創作年代為魏晉時期。上述引文與年代考證均可參看劉緯毅:《〈上黨記〉輯軼》,《山西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2 期。《魏書》中也有類似記載:“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谷關,即神農得嘉谷處。”[7]羊頭山上也很早就有炎帝的傳說和遺跡。澤州地區宋代開始興起的一批神靈占據了歷史較為悠久村落的主神位置,④明清時期興起的村落或出現了嚴重歷史斷裂的村落多以明清時期流行的全國性神靈為主神,如關帝、真武(祖師)之類,與宋元時期差異較大。它們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類似二仙這樣的純粹依賴民間傳說興起的神靈,尤具有唐代仙話故事的余韻,宋金以后才開始倫理化轉變;另一類就是依托古帝王圣賢傳說興起的神靈。后者往往總是和某座山有著密切的關系。大體上,在北朝至唐代,澤州地區一部分山就已經開始流傳著一些帝王圣賢的傳說,并有相應的遺址遺跡,這些傳說和遺跡使得它們具有了與其它山不同的地位。在宋代社會經濟發展、國家支持或放縱、祈雨的現實需求等因素的推動下,帝王圣賢的形象逐步掩蓋了原來山神的形象,在區域內傳播,這些山開始逐步成為區域性的信仰中心,那些帝王圣賢則成為區域性的神靈,山神的形象則有點變得曖昧不清了。⑤三嵕的特殊性恐怕主要是因為后羿或奕形象的曖昧不清,導致三嵕得以以山的名字流傳。關于后羿與羿的爭論參看趙紅:《二十世紀以來羿神話研究綜述》,《太原大學學報》,2009 年第3 期。關于三嵕神的復雜性參看王潞偉、姚春敏:《精英的尷尬與草根的狂熱:多元視野下的上黨三嵕信仰研究》,《民間文化論壇》,2016 年第5 期。
無論村落主神是以帝王圣賢形象出現還是以山神的名稱出現,這都改變不了村落主神與那座或遠或近的山之間緊密的聯系,我們常常會將他們的名字與其起源的山連起來稱呼,如析城山湯王、羊頭山炎帝,而起源之山上的廟也被習慣性稱作“祖廟”,成為這一信仰共同的圣地,在村民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廟在山上:山的非對象化意義
山神信仰、風水信仰與村落主神信仰中所反映的村民與山的關系還是很粗淺的,因為它們都是一種對象化的關系。所有對象化的關系都已經是非常疏遠的關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而真正切近的、奠基性的、原始性的關系是那種主客彼此交融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關系,這種關系無法從對山的信仰的直接敘述中領會,而只能從村民與“山上的廟”打交道的活動中去窺探。這時,核心的概念不再是抽象的山神,而是實在的作為物(建筑)的“山廟”,從“山之有神”發展到“山上有廟”,從“神之在山”發展到“廟在山上”。當精神外化為廟宇建筑的時候,廟宇建筑這個物又完成了更深層次的精神構建,從而將村民對山的精神構建推向頂峰。
山神長期處于村落信仰體系的邊緣意味著其本身內容的簡單和貧乏,風水信仰的復雜理論并不能掩蓋其疊床架屋式的蒼白乏味和功利實用的江湖色彩,與山神有密切關聯的村落主神信仰也只是將祖廟所在的“遠山”放在遙遠的背景板上。相對而言,佛道教這類建制性宗教對山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所謂“深山藏古廟”、“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佛道教喜歡將廟觀建在名山勝境之中,道教甚至為此造作出洞天福地的一整套完整的說法。①參看[唐]杜光庭編撰;《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這樣一種現象絕非偶然,而是無意之間反映出了信仰與山之間的一種本質性的關聯。佛道教的職業宗教徒們實際上是一些中介者,他們身處塵世之中,但又宣稱以出世為志向。惟其在山上才顯得出世,惟其在名山才顯得神圣,何以又不能在深山秘境,而非要在名山勝境,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完全脫離塵世,而又樹立出世的形象。建在山上的廟觀象征著溝通圣俗之間的通道,既能夠超凡脫俗,又不是遙不可及。
相對于佛道教構建洞天福地這種有意識的地理意識而言,像澤州這樣的山區村落的村民更像是無意識地為山構建了一種精神意義,沒有系統的理論,沒有職業宗教徒作為中介者,更沒有成佛修仙的對象化目的,一切都融入到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村民與山的關系最鮮活地體現在人們“入山朝拜、登山拜佛、爬山進香”這樣的日常的非對象化的活動中:“奉香火,執豆觴,登山入廟”②康熙三十五年《創建玉皇廟記》,現存高平常樂玉皇廟。,“登山入寺,瞻禮法相”③康熙二十二年《定林寺七佛殿創修東閣記》,現存高平米山鎮定林寺。,“天空一碧浮云懸,以逾忙種苗未按。天旱不雨人心慌,奉請諸神登山顛,虔誠祈禱求雨澤,南海大士發慈念”④民國二十四年《(無題名墻壁題詩)》,現存高平石末村神山廟南墻。。海德格爾在其哲學中使用了一個源于法語的詞匯Lichtung,作為對其哲學核心概念“此在”的描述。這個詞匯本來的意思是“林中空地”。“林中空地”是在一個陌生的、被遮蔽的地方(森林)開辟出來的一片敞開的空間(空地),以使得我們能夠去通達它。⑤參看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63-64 頁。“林中空地”的意象和“山中廟宇”的意象是非常契合的。村落是人們生活的地方,是完全敞開的空間,沒有神秘性和未知性,也就缺乏了神圣性。與村落相比,山是人們偶爾進入又不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的空間,這種遮蔽就帶來了一定的神秘和未知。在山上建廟就在人與山之間開辟了一條通道,正如林中的空地一樣。韋伯將宗教分為此世(this-world)的和彼世(otherworld)的兩種理想型⑥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oston: Beacon press.1964.,中國人習慣說入世和出世。山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出世與入世之間的過渡。完全的出世而成仙成佛就和世俗世界沒什么關系了,完全的入世就無法與世俗產生一種張力,山正好提供了一種出世與入世之間的過渡。山廟這種形式意味著村民仍然將信仰作為應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工具。
在與村廟相對比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山廟的意義。金元時期,澤州很多原來位于山上的廟搬遷到了村里,村里也建了很多新的廟,這個歷史進程可以稱作“下山進村”。焦河炎帝廟嘉靖碑詳細記載了廟宇從山上遷入村內的過程:“村西北高崗有古建神農廟,按其識,蓋創于金明昌元年也。……嘉靖乙酉歲,廟之故址高峻崎嶇,人皆苦□升降。詢謀僉同,遂卜于村北古道之次。”⑦嘉靖四年(1525)《遷修炎帝神農廟碑記》,現存山西高平焦河村炎帝廟。焦河炎帝廟原位于村外“西北高崗”的山上,嘉靖重修過程中遷入村內。主要理由是“廟之故址高峻崎嶇,人皆苦□升降。”何以以前幾百年不苦“升降”,而這一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廟建在了村里呢?恐怕還是廟的功能發生了較大變化,越來越多承擔起了祭祀之外的村落世俗社會管理的功能。廟所需要具備的那種神秘、未知和神圣的特點不再是最重要的了。當村廟逐步成為主流,山廟就逐步退回到背景之中,而這恰恰是在村民對周圍山林環境改造力度加大之后完成的這種歷史性的轉變。
五、結論
山神信仰、風水信仰、與山有密切關系的村落主神信仰、非對象化的山廟,它們代表了傳統時期村民對山所進行的精神構建的四個層級,也是逐步深入的四個層級。山神是一種原始的萬物有靈論的信仰,風水是一種類科學的前現代地理觀念,村落主神成為了某種地方性知識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作為物質化形態的山廟則成為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四個層級中,山越來越被深入地納入到了村民的精神世界之中。
山越來越深入地進入村民精神世界的過程,也是越來越深入到日常生活的過程。山神作為一種工具只有在其被使用的時候才是重要的,風水這種地理結構只有在與村落相對立的意義上才有價值,村落主神大多拋棄山神形象也表明山終究會被推到背景上去。所有這些抽象的觀念總是會在歷史長河中浮浮沉沉,或輕或重,作為物質形態存在的山廟卻通過爬山拜廟這樣的日常化的身體行為而被納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廟可以被拆毀,神可以被遺忘,而山卻總是在村民記憶之中揮之不去,成為鄉愁的一部分。
任何的自然地理要素都只有通過人類的精神構建才能夠成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自從年鑒學派興起之后,自然地理的敘述幾乎成為歷史學研究的“標準動作”,但也越來越流于形式,一定區域范圍之內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些地理要素與特定區域社會的精神文化是如何關聯起來的。本文即是這方面的一個簡單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