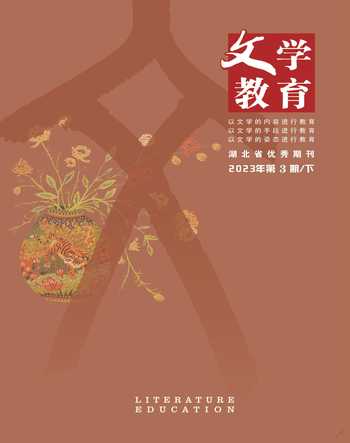利奧波德《大雁歸來》的審美教育價值
池培琦
內容摘要:《大雁歸來》是一篇極具美感且帶有生態倫理意味的文章,本文將從三個方面闡述其審美要質及教育價值:一是語言審美教育價值,文章語言詩意浪漫,表達自然活潑,帶給觀者美的享受;二是情感審美教育價值,作者對自然生靈真摯深切的凝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帶給觀者情感審美的體驗;三是生態審美教育價值,超越環境保護主義,建構人-自然共生的生態倫理觀,指向生態責任意識的審美取向。
關鍵詞:《大雁歸來》 審美教育 價值
語言文字是人類重要的審美對象,語文教育是學生審美知識與能力發展的重要途徑。《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提出“審美鑒賞與創造”,學生在語文學習中依據散文、詩歌等豐富的表現形式,從語言、情感、意蘊等多個角度欣賞文學作品,從而獲得審美體驗,認識作品的美學價值,發現作者獨特的藝術創造[i]。語文教科書中選錄的課文均是文質兼美的文本,挖掘其審美要質,發揮其審美教育價值是學生提升審美素養的關鍵。《大雁歸來》一文自美國生態倫理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自然隨筆和哲學代表作《沙鄉年鑒》。此文雖被選入部編版語文教科書八年級下冊說明文單元,但其充滿詩意的文字敘述,字里行間透露出的抒情意味以及創作者對人與萬物生靈共生關系的深切思索,使得本文蘊含了豐富的語言、形象、情感、價值觀等審美要質。
一.透過語言的審美
文學語言不同于日常生活語言,包含著豐厚的語義信息與審美信息。語言的審美信息即語言進入特定語境后產生的審美線索,體現這篇文章獨特的審美意義,帶給閱讀者語音、形式、內容等美的感知與享受。這些審美信息借由文字或隱或現地散落于文本之內,成為等待讀者挖掘的審美要質。讀者留心于語言表達藝術之時,只有獲得解碼創作者審美信息的鑰匙,才能開啟富有意味的語言審美體驗之旅。
(一)精當的語詞選擇
《大雁歸來》一文在語詞的選用和表達上飽含美感。文章以三月的大雁回歸故地開篇,“當一群大雁沖破了3月暖流的霧靄時,春天就來到了。”句中“沖破”一詞暗含力量積蓄后的噴發,僅僅2個字,就蘊含了豐富的審美信息。沖破前,雁群在暖流外徘徊,積蓄力量的同時尋找與等待穿越時機;沖破時,大雁抓準時機,奮不顧身,一只接一只地沖進暖流,在高速運動且激烈的氣流中與自然展開角力;沖破后,雁群身心俱疲但絲毫不敢松懈,因為它們要盡快到達目的地。正式“沖破”一詞刺激大腦,觸發了讀者的聯想機制,使讀者透過文字表層信息想象文字背后營造的無限空間,體會雁群的力量之美,堅決執著之美,悲壯之美。讀者由此獲得多元的、多層次的審美體驗。作者在提到三月大雁的飛行狀態時,一連用了四個飛行動作——穿行、盤旋、扇動、滑翔,并前置不同的形容詞:曲折、試探性、慢慢、靜靜。將這幾個動詞短語拎出文本,從時間和速度維度構建坐標軸,不難發現這是一張雁群起起伏伏,向下緩慢飛行的折線圖。雁群飛行速度的“慢”在某種角度投射出雁群心理上的“慢”,這種“慢”表現的正是雁群的謹慎小心。而雁群為何如此小心謹慎、左顧右盼,原因不言而喻,這是作者并未直接說明的,但需要我們從文字中讀出。這種精心選擇、斟酌再三選定的語詞往往也是文本解讀的關鍵處。
詞語本身的審美信息有限,可借由詞義增殖將擴大特定言語義場中的詞語的審美信息,進而賦予更多的審美要質。“一觸到水,我們剛到的客人就會叫起來,似乎它們濺起的水花能抖掉那脆弱的香蒲身上的冬天。”動詞“抖掉”具有可視性,將其與名詞“冬天”搭配產生了語言陌生感,擴充了短語審美信息。在這樣的文字描述下,讀者會主動滲入日常經驗,自覺想象雁群戲水、梳理毛發等畫面,以及敏銳地感知到春天即將到來的訊息,神游在廣闊的心理時間-空間之內,達成審美想象的培養。當然,像這樣具有審美價值的詞語文中還有多處,值得我們細讀細究。
(二)精妙的語言表達
《大雁歸來》表面上看是一篇為讀者介紹雁群生活習性的科普文,但在表達技巧上不入俗套,采用了全文人格化的處理方式。“一只定期遷徙的大雁,下定了在黑夜飛行200英里的賭注,它一旦起程再要撤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賭注”是人權衡結果成敗之后做出的冒險性決定,在這句話中,作者賦予大雁人的復雜思想,它們敢于選擇冒險,也勇于承擔風險,這種品質令人敬佩。為了展示大雁的生活情態,作者有意選擇了大雁進食和大雁鳴叫兩個場景。“大雁到了目的地,時而在寬闊的水面上閑蕩,時而跑到剛剛收割的玉米地里撿食玉米粒。”“閑逛”“撿食”等動詞可見大雁此時悠游自在的狀態,由此形成獨特的審美風格,帶給讀者自然、活潑、親近的審美體驗,展現出自然狀態下的大雁形象:自在愜意、無拘無束。“還有觀戰者們激烈的辯論所發出的呼叫聲。隨后,一個深沉的聲音算是最后發言,喧鬧聲也漸漸低沉下去,只能聽到一些模糊的稀疏的談論。”激烈的“辯論”開啟,由稀疏的“談論”結束,從高聲鳴叫到低聲悄語,全面呈現集會中的大雁形象。青年大雁爭相表現自己,如同性子急躁、愿意表現自我的人類青年;年長的大雁出聲總結討論,宛如人類長者閱事多矣,用自己的睿智把控全場。大雁的“鳴叫”不是無意義的吵鬧,是大雁內部的交流與討論,它們在處理族群事務。跳出了人高于動物的固定思維,讓我們看到大雁與人相似,具有豐富的情態、集體意識、長幼之序。作者之所以用人格化的方式描寫大雁,更關鍵的意圖在于為了展現大雁多樣的審美形象,也展示出作者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二.深入情感的審美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 觀文者披文以入情”,語言不僅能表達思想,描摹事物,還可以實現情感的流露,而情感“正是審美活動中最活躍、積極的因素”。審美情感不是單一的,而是由不同層次情感組成的統一體。韻律節奏、文體變式、畫面想象等帶給人知覺層面的審美快感;豐沛情感的表露、深刻思索的呈現給人帶來高級的審美情感體驗,這是精神層面的審美體驗。
(一)文字肌理中的愛鳥情
《大雁歸來》作為一篇抒情詩意的文章,字句之間流淌著創作者對大雁的深厚且復雜的情感。我們只有透過文字表層深入文章內里尋覓作者情感的蛛絲馬跡,才能獲取珍貴的審美體驗。作為一名普通的愛鳥者,在3月的雁群免受冬天捕獵者帶來的膽顫驚心,經歷長途遷徙,順利回到故地,悠然自在地穿行在水洼、池塘間時,“我”的心情也隨之輕松歡快,真切直率地表達出“我們的大雁又回來了”的喜悅之情。當大雁風雨兼程飛行200英里,無所畏懼地沖破霧靄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4月的大雁在沼澤地盡情鳴叫、舒展身體,互相梳理羽翼,這種細致入微的群居生活描寫展現的是作者對大雁無限的喜愛之情。一般的愛鳥者對大雁的喜愛多在飛行、外形等可見的方面,這種情感也就流于“愛物之情”,停留在知覺層面的審美快感。作者在文章中流露出的真正的愛鳥態度是以平等的視角走近、了解大雁之后的尊重。作者是一名生態學家,在長期的雁群遷徙觀察中發現,偶爾多出的孤雁不是“傷心的單身漢”而是喪失親人的幸存者,說明大雁群體與人相似,群體內部有家庭結構。作者進一步發出“單調枯燥的數字竟能如此進一步激發愛鳥者的感傷”的感嘆,是在對失去親人的大雁表達哀痛,其背后是體現的是作者將萬物生靈平等以待的情感。每年三月大雁結伴而行長途跋涉來到故地,從未失約,這是雁群的使命,是一代又一代大雁在傳承下來的生存之道,如此一絲不茍地遵循自然規律,這是人類也極難做到的堅守。在作者眼中大雁每一年突破自然力量的無情阻礙,戰勝自我后回歸故地是一種詩意與浪漫,因而贊其為“野性的詩歌”。從喜愛到敬畏,再到尊重與贊賞,這種超越物種的情感之美對于思索人類與萬物生靈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兩廂對比下的思辨情
在講到人類行為對大雁行為的影響時,利奧波德并未直接敘述,而是用比較的形式呈現大雁與人類之間耐人尋味的關系,借以表露自己的情感。“11月南飛的鳥群,目空一切地從我們的頭上高高飛過。即使發現了它們所喜歡的沙灘和沼澤,也幾乎是一聲不響。”“目空一切”“一聲不響”表明大雁知道地面隱藏著捕捉大雁的人類獵手,因而精神高度集中。這或許是幾代大雁在與人類“打交道”中代代接續的經驗與智慧吧。“它們順著彎曲的河流拐來拐去……向每個沙灘低語著,如同向久別的朋友低語一樣。”“拐來拐去”“低語”表明大雁從高空向地面靠近,相對的放松、自在。比較大雁在兩個月份中的不同行為狀態,不免讓人奇怪。原因不難知道,人類以法規設定的標準為界,只在11月獵殺南飛的雁群,自以為這是對大雁最大的“恩賜”。實際上,大雁在非獵殺期的3月回歸時,仍小心翼翼、心有疑慮,它們會在沼澤上空做試探性的盤旋,才最終落定。兩處對比之下,作者不免對人類行為產生質疑:法規究竟保護了大雁還是在傷害大雁?作者對大雁的喜愛之情是純粹的,但作為人類的他又對同類傷害雁群謀取自身利益的行徑表露出指責與不認可。這樣的思考也出現在文章倒數第3段。“各國之間的聯合是不可預期的”,但大雁的“聯合觀念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寫作手法從描寫轉為議論,意在將大雁與生俱來的聯合行為與人類基于利益暫時聯合的行為進行比較,反思人類自身聯合的虛假,敬佩雁群聯合觀念的純粹。
三.生態審美的取向
生態學家利奧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購買了一處農場——沙鄉,并在此開展了為期13年的生態平衡恢復實驗。正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實驗中,利奧波德對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的思考超越了一般的環境保護,建構出更上位的“土地共同體”的生態倫理觀,且以隨筆的形式在散文集《沙鄉年鑒》中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生態審美的取向超越一般的環境保護主義,以系統整體論為哲學基礎,著眼于生態系統之中的關系之美,關注人與自然在生態關聯中的共生性、家園意識以及詩意的棲居。《大雁歸來》就是以文學的手法闡釋了一種新的審美建構:基于土地倫理的生態審美。
(一)遵循“土地共同體”的生態之美
有別于人類中心主義通過為人類在生態系統中賦予新身份,使人類高于自然。利奧波德認為,個人是一個由各個相互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共同體成員,這個共同體包括土壤、植物、動物和人,概括起來就是“土地共同體”。在土地共同體中,人類必須改變征服者的心態,脫下權威者的身份,將自己定位為共同體中的一員,與其他成員平等對話。這種“平等對話”在《大雁歸來》這篇文章中體現為反復出現十次的一個詞語——我們。“我們”指的是哪些人呢?“向我們農場宣告新的季節來臨的大雁知道很多事情。”“我們”指的是農場主與附近農民。在現代文明尚未到達的年代,大雁對農民來說是最好的幫手,農民通過大雁何時到來知曉季節變化,開展農事活動。“在我們的農場,可以根據兩個數字來衡量春天的富足:所種的松樹和停留的大雁。”此處“我們”是農場主,大雁越多表明農場生態良好,預示著一年的豐收,大雁是一年收成的預測者。“我們喜歡傾聽大雁在沼澤中集會時的鳴叫。”此處“我們”是鳥類觀察者,也是愛鳥者——側耳傾聽不同鳥鳴,想象它們之間的交談,野趣與浪漫在無數個4月的日子里蔓延。“……我們的大雁集會也就逐漸少下來。在5月來到之時,我們的沼澤便再次成為彌漫著青草氣息的地方……”此2處的“我們”是自然,大雁冬去春歸年復一年是自然法則。“我們”帶有親昵之感,將大雁包括在人類、動植物、水、土壤等自然生態之中,也將大雁與人類放置在同等地位。這正是利奧波德宣揚的“土地共同體”倫理觀。
(二)身處其中的生態“參與”美學
“那些被普通人所忽視的事物,通過作者深邃的眼睛和富有鑒賞力的耳朵而變得絢麗多彩、栩栩如生。”對自然的喜愛與敬畏以及生態學家的身份使利奧波德能夠帶著對自然生態的了解與熟悉,運用獨特的審美感知方式去感知自然狀態下的大雁之美。這種感知獲得的審美體驗與人們從城市美術館、博物館的展品中獲得的靜態審美截然不同,更不是純粹的風景欣賞,而是一種參與美學。利奧波德細膩、靈動地描寫了大雁落地動作、集會鳴叫,放棄簡練客觀地敘述,用溫柔的眼光跟隨“它們白色的尾部朝著遠方的山丘,終于慢慢扇動黑色的翅膀,靜靜地向池塘滑翔下來……”以享受的姿態側耳傾聽雁群鳴叫的變化,起先是靜悄悄,然后混亂激烈,緊接著低沉呢喃,最后模糊稀疏歸于沉靜,捕捉到鳴叫變化這一微妙的審美特質,進而獲得視覺、聽覺、觸覺等多維度聯動的動態美感體驗,完全超出了一般生態科普文的范疇。在感知自然的第一層審美之外,利奧波德更贊同基于大雁習性、特點以及生態系統中獨特性而獲得的第二層次審美體驗。人類主觀猜測落單大雁是“單身漢”,將這種發生在雁群內的現象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借此標榜人類對大雁的了解關注。作者則通過長期的、嚴謹的科學觀察、推測與分析發現落單大雁為回歸旅途中失去親人的大雁,由此得出大雁是群居動物,且具有家庭聚合體這一有科學依據的結論。再如,伊利諾伊的玉米粒正是靠大雁的遷徙才能傳播到北極,成為絕地的生命星火。在利奧波德眼里,大雁不是普通的飛禽,而是與人同等的自然生命體。他們是野性、自由、自然的生命形態,自有其生命的華彩。生態美學反對“只遠觀”的淺層審美,強調“參與”其中的深層審美,這是美的內核與本質。
利奧波德通過闡釋人與土地共生的生態美學關系,“以激發人們對土地共同體的由衷熱愛和崇高尊敬,進而產生一種道德責任感。”這種道德責任感首要摒棄用經濟利益去衡量自然物價值,去除基于人類立場做出“有害”抑或“有利”的分類,從人文關懷立場出發,將任何生物包括人類都看作整個生態圈中的關鍵一環,最終獲得人與自然平等對話的生態審美觀。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S].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
[2]曾繁仁.試論生態審美教育[J].中
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04):11-18.
[3]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M]. 侯文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4]溫儒敏主編.語文:八年級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39~42.
[5]劉棟.土地倫理的詩性——《大雁歸來》中的生態意蘊闡析[J].語文建設,2018(36):45-49.
[6]陳卉.“我們”是誰?——對《大雁歸來》文本獨特性的思考[J].語文建設,2007(04):39-40.
[7]羅昕如.文學語言審美功能的語義學闡釋[J].中國文學研究,1995,(04):18-24.
[8]童慶炳.語文教學與審美教育[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3,(05):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