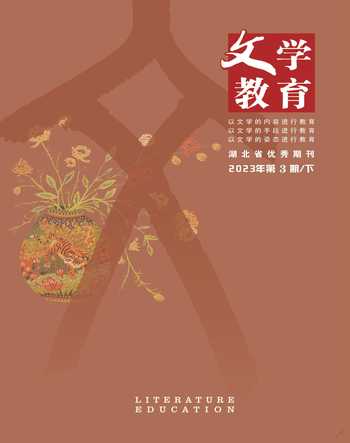繪本親子閱讀方法談
內容摘要:繪本在兒童早期閱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能夠促進兒童語言、美術、音樂、社會性等多方面能力的提高。親子閱讀要根據兒童的年齡階段、認知發展,結合閱讀材料,運用多種閱讀方法,讓孩子在聽、看、畫、講、玩等過程中感受、體驗、想象、創造,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繪本 親子閱讀 方法
繪本(picture book),也稱圖畫書,是一種以圖為主、文字為輔,通過連貫的頁面來表現內容的讀物。繪本是當代兒童文學中最常見的一種圖書門類,也是最能體現幼兒文學藝術特性的文體樣式之一,它在早期閱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被認為是“人生第一本書”。
所謂繪本親子閱讀,是指家長和幼兒共同欣賞繪本,通過講述其中的故事,解答疑難并引導孩子思考,使孩子的閱讀能力盡快提高、人格得到健全發展的一種閱讀教育方式。[1]繪本不僅給人以美的享受,符合學前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而且能夠促進學前兒童語言、美術、音樂、社會性等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對幼兒的發展具有特殊的價值。
2015年10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廣大家長要全面學習家庭教育知識,系統掌握家庭教育科學理念和方法,增強家庭教育本領,用正確思想、正確方法、正確行動教育引導孩子。”親子閱讀是兒童走向獨立閱讀的基礎,成人在親子閱讀中正確的引導、方法的使用,對兒童的獨立閱讀能力的培養會產生積極影響。
繪本親子閱讀有別于其他的閱讀形式,它涉及父母(成人)、兒童和繪本,親子閱讀的效果有賴于三者的協調、配合。兒童是主體,繪本是橋梁,成人是引導者、協助者。繪本親子閱讀也有別于其他閱讀媒介,而是要根據兒童的年齡階段、認知發展,運用多種閱讀方法,讓孩子在聽、看、畫、講、玩等過程中感受、體驗、想象、創造,發展兒童的語文素養、審美能力和道德情操等,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一.共讀法
繪本是由兩種語言共同敘事的,一種是圖畫語言,一種是文本語言(無字書除外)。日本繪畫研究者松居直曾用一個公式形象表示插圖讀物與繪本間不同的圖文關系:圖+文=插圖讀物,圖×文=繪本。[2]敘事的觀點(“誰看”)和敘事的聲音(“誰說”)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繪本中我們能應該把文字作為輸送敘事聲音的主要手段,圖片則作為輸送觀點的主要手段。[3]
繪本在某種程度上,更應該是讓孩子傾聽的書,是大人讀給孩子聽的書,這是一個基本原則。美國學者愛倫·漢德勒·斯皮茨在《在繪本之內》一書中說:“出聲地朗讀繪本,不論是對于大人還是幼小的聆聽者們來說,都是一種非常有益的行為……在親密相偎一起閱讀繪本的同時大人和孩子一起邁入想象的空間。”
成人將圖書中的文字大聲地朗讀給兒童聽,是聽說讀相結合的閱讀活動。大聲朗讀是化無聲文字為有聲語言,口讀耳聽,口耳并用,增加了向大腦傳輸的渠道,這不僅使閱讀真正達到活學活用的程度,而且使兒童印象深刻,便于記憶與理解。[4]作為由父母讀給孩子聽的繪本,家長需要注意語音、語速、語調的變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地調整節奏和語氣,可以重復、可以注解,甚至可以增加繪本中沒有的內容。兒童在聆聽有聲語言的過程中,仔細品讀圖畫內容,將文字和圖畫有機結合起來,產生豐富和立體的閱讀印象,并生發出屬于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在這個過程中,兒童可還可以觀察成人的表情,感知成人的情緒情感。
每個幼兒都是在其已有的心理發展水平或知識經驗的基礎上走進圖畫書世界的,都是在與圖畫書對話、互動中逐步發現、欣賞和品味圖畫書的——幼兒走進圖畫書世界的過程就是幼兒與圖畫書對話,互動建構的過程。[5]所以,家長也要及時關注兒童的反饋,捕捉兒童的表情和情緒變化,停下來等待、回應。如果兒童遇到一些困難或障礙,在孩子求助之前,盡量不要去干擾和影響孩子。要注意避免說教,少提問、少說明、少講解,更不能把閱讀繪本看作是認字、識字的手段,把看書、思考的空間留給孩子,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品味故事。
兒童在共讀中,除了聽到抑揚的聲調、曲折的故事內容,還能捕捉到圖中的妙趣。《爺爺一定有辦法》采用了上下平行式的構圖方式,除了與文字內容相對應的圖畫,還有小老鼠一家的生活場景。《打瞌睡的房子》從第二頁開始每頁都出現的小跳蚤,成了兒童關注圖畫的引線。《我爸爸》“我爸爸什么也不怕,連壞蛋大灰狼都不怕”,畫中的爸爸一手叉著腰,一手指著大灰狼。在圖畫一角,出現了小紅帽和三只小豬。噢,這只大灰狼,就是《小紅帽》和《三只小豬》的大灰狼啊。《古納什小兔》中,一家人奔跑著去找古納什小兔的路上,遇到的那個人T恤上一只“鴿子”,看著眼熟的鴿子原來正是《別讓鴿子開巴士》的那一只。
二.對話法
閱讀本身就是對話的過程。繪本的“雙主體”屬性使閱讀具備雙重視角,親子閱讀中的成人與兒童的互動,拓寬了對話渠道。文本的意義及價值離不開主體間通過文本解讀得以顯現的精神對話。兒童視角和成人視角下人與文本的對話的分享、碰撞、交融,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
對話是雙向的,是一種平等的討論和分享。阿甲說,關于閱讀中的提問,我們不一定要向孩子提問題,而是要重視孩子的問題,聽他提問題,鼓勵孩子的積極反應。[6]父母要牢記,兒童始終處于親子閱讀的中心位置,應允許兒童隨時提問,肯定兒童提問和思考的習慣。提問問題既可以是關于文本內容的封閉性問題,也可以是引發思考的開放性問題,成人隨時可以停下來,等待、回復或者和兒童一起探尋。當然,成人也可以提問,了解兒童的體驗、感受,對隱藏細節的發現等。提問不是目的,只是對話的起點。提問無需特定的問答模式,也不必要求精準的答案和統一的標準,成人不要低估兒童的閱讀和評論能力。
讀《古納什小兔》,兒童會對“自古洗衣店”感到困惑,這時需要家長幫助兒童彌補知識性經驗的缺失。讀《正在消失的圖瓦盧》,兒童發問:圖瓦盧真的會消失嗎?有什么辦法可以讓這個國家不要消失呢?這個問題涉及全球變暖和環保,這樣的問題甚至可以變成一個小型研討會或者引發一場主題閱讀。親子閱讀也可以變成成人的“自覺”引導,讀了《石頭湯》,成人可以引導兒童思考,如果自己是書中的小男孩,會跑回家把鍋拿出來煮石頭湯嗎?這是關于文本內容的開放性問題。也可以引導兒童尋找圖片中的中國文化元素:垂柳、石獅、和尚的名字、中式建筑、傳統服飾等,體會繪本的繪畫風格。
三.演繹法
讀完一本繪本并不意味著閱讀的結束。一本優秀繪本的呈現不只需要作者精心的創作和精湛的創作功力,也需要讀者投入感受力、想象力以及因自身生活經驗而產生的咀嚼與回味,只有這樣,才能從圖像中領悟“真”的信息,發展“善”的意念,培養“美”的感受,在真善美的修煉中,得到精神的陶冶。[7]
繪本的開放性意味著兒童可以演繹繪本,父母要鼓勵兒童把閱讀內容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所謂各種形式,不僅僅是兒童的戲劇表演,還可以是故事的續編、仿編和創編;可以是在閱讀當中即興的表現,也可以是閱讀結束后經過準備的表現;可以是語言的表現,也可以是動作的表現。總之,教育者對于兒童的各種形式的表現要提供資源支持和精神鼓勵,因為兒童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現閱讀內容的時候,就是閱讀和游戲達到最佳結合的時候。[8]
(一)講一講
繪本閱讀對孩子最明顯的影響就體現在語言能力的提高上,喜歡閱讀的孩子在語言表達的積極性、流暢性以及詞匯的豐富程度上較之閱讀經歷較少的孩子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兒童語言學習的一般流程,由語言輸入、內化、語言輸出、反饋四環節構成的連鎖過程。[9]
繪本語言能夠讓孩子在語言感知和語言模仿中獲得語言的技能。對于故事情節性強的繪本如《瑪麗和小老鼠的秘密》《讓路給小鴨子》《第一次上街買東西》等可以請孩子講故事,講給家人聽、講給老師聽、講給伙伴聽,甚至講給玩具聽。在語言輸出的過程中,進一步內化繪本內容,增加兒童的感受力和創造力。
(二)畫一畫
我們看到的每一本繪本,從開本、封面、環襯、扉頁、正文、封底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畫面精美、富有內涵,能給孩子美的熏陶。繪本可以幫助兒童感受不同的繪畫風格、流派、技巧以及美術材料的使用,繪本也可以成為兒童繪畫的范本。
讀了李歐·李奧尼的《小黃和小藍》,一黃一藍兩個近乎圓形的抽象色塊的分合成就了一個故事。兒童可以模仿用紙團沾色畫一畫,感受調色、繪畫工具的多元。《外公的旅程》屬于水彩畫,《別讓鴿子太晚睡》是蠟筆勾勒輪廓,《小蝌蚪找媽媽》屬于國畫,《紙馬》則是剪紙,《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則采用拼貼藝術。接觸這些繪本,兒童可以感受各種風格的繪畫作品,也可以嘗試使用多種繪畫工具和繪畫技法,丙烯、水彩、水粉、水墨、油畫、炭筆等;抽象畫、油畫、水彩畫等,感受繪本中的冷暖色,線條、結構,引導兒童使用多種表現形式來作畫。
(三)做一做
把因繪本引發的奇思妙想變成現實,能讓兒童體會到動手的樂趣,得到成就感和滿足感,還能回味內容。讀完《好餓的毛毛蟲》,兒童可以做一條屬于自己的五顏六色的毛毛蟲。《奇奇妙妙博物館》告訴孩子們,博物館有很多種:手工藝品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藝術博物館、植物博物館等,最后作者還邀請孩子們,一起暢想并創作更多奇妙的博物館,兒童就可以在家設計屬于自己的博物館:旅游紀念品博物館、橡皮博物館、繪本博物館……
(四)編一編
繪本的主題里涉及很多對經典故事、民間故事的“戲仿”。比如喬恩·謝斯卡《三只小豬的真實故事》顛覆了原有的《三只小豬的故事》,以“大灰狼”視角敘事,把大灰狼演繹成孝順的、溫文爾雅的形象。《青蛙王子變形記》則融合了多個經典童話重構了青蛙王子的故事。這種改編可以啟發兒童去續編、改編或者仿編故事,比如續編《晴天有時下豬》,改編《地上一百層的房子》,和媽媽一起仿編《猜猜我有多愛你》。
(五)演一演
很多優秀繪本被紛紛搬上舞臺,比如宮西達也的繪本《我是霸王龍》《你看起來好好吃》《永遠永遠愛你》等。繪本舞臺劇結合舞臺設計、語言、美術、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能夠立體再現兒童對繪本的理解和再創造,而兼具趣味性、藝術性與教育性的繪本則為孩子的戲劇活動提供了最好的藍本。家長一方面可以帶兒童觀看繪本劇,也應鼓勵兒童演一演,比如《鱷魚怕怕 牙醫怕怕》僅有兩個角色,是比較適合家長和兒童嘗試表演的。
四.主題閱讀法
閱讀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閱讀的四個層次,包括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和主題閱讀。[10]主題閱讀是最高層次的閱讀,對兒童而言,主題閱讀首先是讓他們明確了一個事實:對一個特定的問題而言,所牽涉的絕對不是一本書而已。
主題閱讀是以兒童廣泛閱讀為基礎的,是建立在兒童認知發展的聯想基礎上的,可以是相似聯想、對比聯想、接近聯想、關系聯想等。《爺爺變成了幽靈》《爺爺有沒有穿西裝?》都是關于親人逝去的生命主題繪本;《逃家小兔》《猜猜我有多愛你》《我討厭媽媽》《我媽媽》是親情主題繪本;《安娜的新大衣》《阿利的紅斗篷》的故事都是關于衣服的來源的;《年》《灶王爺》《年糕》《團圓》《北京的春節》都是圍繞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的繪本。
主題閱讀是繪本閱讀的高級階段,一方面有賴于兒童豐富的閱讀積累,另一方面有賴于家長的閱讀引導。比如讀了謝爾·希爾弗斯坦的《失落的一角》后再去讀讀續集《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進一步接觸這位童詩大師的《愛心樹》《閣樓上的光》《人行道的盡頭》等其他作品。
五.鑒賞閱讀法
兒童在廣泛長期閱讀過程將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選擇,形成獨特的審美取向,如果孩子在低齡段讀過大衛·香農的大衛系列繪本和《小仙女艾莉絲》,中高齡段就會在接觸《當海盜》、《海盜從不換尿布》、《糟糕,身上長條紋了》感受到大衛·香濃獨特的繪畫和敘事風格,從而上升到繪本賞析的高度。[11]超現實主義畫家安東尼·布朗也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膽小鬼威利》《隧道》《我和你》受到想象力豐富的兒童的喜愛。溫情脈脈則是宮西達也的個人標簽。除了作家風格的鑒賞閱讀外,也可以尋求一些類別化作家或區域性、時代性的繪本特色。比如,拼貼畫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后興起的藝術流派。識別風格和作品喜愛已經上升到作品鑒賞的高度,是閱讀個性化的體現。
松居直把繪本比作“幸福的種子”。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個體,應有屬于每個兒童獨有的親子閱讀書單,每個家庭也應有獨屬于每個家庭的閱讀方式,不固守且不局限于繪本的圖文,甚至不謀求與作者的同一,以自己的方式解讀、體驗和闡釋作品,繪本因此在開放性閱讀中由讀者(兒童或成人)最后完成。[12]親子共讀,是父母與兒童共赴的一場獨特的旅程。親子閱讀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構筑一種新的家庭生態。
參考文獻
[1]王西敏.繪本在親子閱讀中的使用[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3.
[2]松居直.我的繪本論[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3]瑪麗亞·尼古拉杰娃.繪本的力量[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4]周兢.早期閱讀發展與教育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5]肖涓.論圖畫書閱讀與兒童發展[J].湖南第一師范學報,2004(9).
[6]梅子涵等.中國兒童閱讀6人談[M].成都:新蕾出版社,2009.
[7]林美琴.繪本有什么了不起[M].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
[8]吳念陽.讓孩子愛上閱讀:互動式分享閱讀指導手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9]李宇明.兒童語言的發展[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0][美]莫提默·J.艾德勒.如何閱讀一本書[M].商務印書館,2004.
[11]徐鵬鵬.學前兒童繪本親子閱讀指導策略[J].教育觀察,2021(12).
[12]陳暉.論繪本的性質與特征[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