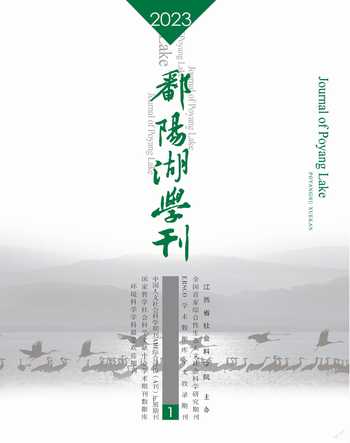人類世、生態文明與有機過程思維
王治河
[摘 要]盡管人們對“人類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承認人類活動已對環境造成毀滅性影響。“人類世”不僅僅是一個地質時代命名的問題,更是對工業文明中占統治地位的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全新的質疑。由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概念被許多人認為是應對人類世危局的最佳方案,但這一概念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深陷發展主義的窠臼,依然是在“發展”上做文章,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誰的發展”“發展令誰真正受益”的問題。因此,人類需要改弦更張,時代需要生態文明。作為一種全方位的偉大變革,生態文明需要一種新的有機過程思維。作為生態文明的理論支撐,有機過程思維不僅在中國擁有深厚的思想基礎,而且在當代西方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關鍵詞]人類世;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有機過程思維;共命意識;建設性后現代主義
長逾三載的新冠大流行不僅令人類文明的發展進入一個轉折點,也給了人類一個絕佳的反思機會。如果說在前疫情時代人們對“人類世”概念還未給予足夠重視,還在期盼疫情早點結束,以便早日回歸常態,回到“往日既定的美好生活”中去,那么后疫情時代則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審視“人類世”概念。愈來愈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修修補補不能解決問題,人類社會需要一場根本性的變革。拉丁美洲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口號:“我們不應回到常態,因為常態是問題開始的地方。”①人類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類應該如何應對人類世的到來?為什么可持續發展不是最佳應對方案,只有生態文明才是?生態文明需要一種怎樣的思維?本文試圖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視域中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不妥之處敬請方家賜教。
一、追問“人類世”的根源
“人類世”(anthropoence)一詞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Jozef Crutzen)于2002年首次提出的,他認為人類活動的影響足以產生一個新的地質時代。雖然這一術語提出后在學術界曾引起激烈爭論,但據2019年《自然》(Nature)雜志報道,權威科研小組“人類世工作組”投票決定,認可人類世為地球新的地質年代,“以標識人類活動對地球造成的巨大變化”。②
反對這一概念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兩個:一是認為“人類世”概念表征著“人類的傲慢”;①二是認為“人類世”概念沒有考慮到“少數國家和文化”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有關研究資料表明, 在21世紀初,全球最貧窮的45%人口產生了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最富有的7%人口則產生了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英國《柳葉刀-星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雜志剛剛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表明:“高收入國家是全球生態崩潰的主要責任者,它們欠世界上其他國家一筆生態債。”②因此,一些“人類世”的反對者將資本主義看作“生態危機的首要決定因素”,③有的西方學者甚至提出用“資本世”代替“人類世”。④毫無疑問,對于今日遍及全球的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制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一理論卻“無法解釋包括前蘇聯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生態危機”。⑤正如有的中國學者所追問的那樣:“為什么社會主義的中國生態危機竟比起國外許多國家更為嚴重、更為復雜?”⑥在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看來,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西式現代性也即現代世界觀或現代機械思維的犧牲品。
此外,將危機的根源完全歸于制度,也容易導致人們推卸個體責任的結局。對于“外賣塑料袋不到三天可覆蓋一個西湖”“外賣盒一天可以堆出770個珠穆朗瑪峰”這種觸目驚心現象的發生,⑦個體消費者顯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無論是“人類世”概念的贊成者或反對者,都承認人類活動已對環境造成毀滅性影響。雖然自有人類以來,人類活動就對環境產生著影響,但“人類世”的產生無論如何與工業革命和工業文明對環境史無前例的破壞是分不開的。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類活動強度不斷升級,諸如修建道路港口、開發礦山、蓄水建壩、采用地下水等劇烈活動,已經改變了地球原有的地質結構。此外, 在過去的300年間,地球上的人口數量已經增加了10倍,達到70多億,預計到21世紀末將達到100億。地球30%—50%的陸地資源已經被人類占用。與此同時,人類飼養家畜的數量達到14億,它們產生的甲烷也對熱帶雨林產生破壞作用,從而導致二氧化碳的增加和物種滅絕的加速。人類對土地的耕種和開發利用也加速了對土壤的侵蝕,這比自然速率要快15倍。⑧“我們每年向空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火山的100多倍,目前我們正在目睹25億年來對地球氮循環的最大破壞。”⑨大量物種滅絕、農田沙漠化、土壤毒化、珊瑚大量消失、海洋酸化、全球氣候變暖等現象的發生,就是這種破壞的結果。地球生命正面臨第六次大滅絕。可以說,正是工業文明以來人類“過度生產、過度攫取、過度消費,最終導致地球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破壞,生態危機產生了”。①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之巨大,已經到了不容忽略的程度,“人類世”概念的提出正是地質學界對這一事實的應對。
在筆者看來,“人類世”不僅僅是一個地質時代命名的問題,更是對工業文明中占統治地位的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全新的質疑,也是對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控訴。“人類世”概念的提出,不僅給了人類一個巨大的警示,也給了人類一個撥亂反正的機會。按照著名過程哲學家凱瑟琳·凱勒(Kathleen Keller)的說法,今天的我們“已經無需被告知我們正面臨災難。現在到了問我們還可做些什么的時候了”。②那么,到底該如何應對人類世的到來呢?由聯合國開出的“可持續發展”藥方被許多人認為是應對人類世的最佳方案,但在筆者看來,“可持續發展”雖然不乏積極意義,但它也是一個有待商榷的概念。
二、反思“可持續發展”概念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人類當前需要,又不對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這一概念是挪威首相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于1987年在她任主席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首先提出來的。
應該承認,“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自有其價值,特別是與“有今天沒明天”、竭澤而漁式的過度發展相比,它的提出無疑是個巨大的歷史進步。然而,“可持續發展”概念也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第一個缺陷是依然沒有擺脫“發展”的宏大敘事,依然囿于發展主義的窠臼。據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考察,“現代意義上的‘發展一詞,是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理論興起時才出現的,但現在卻已成為現代話語的集中表達”,“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發展為中心的時代。雖然表述不盡一致,但‘發展已經成為每個人、每個地區、每個國家都關注的中心問題”。③人們篤信發展就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是一個單向度的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然而,問題在于發展是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如果一個系統一直不停歇地持續發展,“其最終結果就是毀滅”。④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作者、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舒馬赫(E. F. Schumacher)就已經指出,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中,物質消費的無限增長是不可能的。因此,《神圣的經濟學》(Sacred Economics)一書作者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追問道:可持續發展“真的是我們的最高期許嗎”?⑤在他看來,人世間許多美好的事物諸如懷孕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發展不該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一如僅僅活著不是生活的終極目標一樣”。⑥
站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來看,所謂“發展主義”在根底上也是一種經濟主義,或者說是為經濟主義服務的。所謂“經濟主義”(economism),是一種將經濟增長作為社會首要考量的意識形態。按照世界著名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的分析,“經濟主義是我們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宗教”。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主義取代民族主義成為主導整個世界歷史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一種毀滅性的價值觀”。②經濟主義篤信,經濟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社會應該以經濟的擴張和增長為中心進行組織,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就是為經濟增長而存在的”。③無論是民族利益還是國家利益,都應服從經濟利益,“都應從屬于經濟目標,都應唯經濟利益馬首是瞻”。④因此,經濟原則被認為可以應用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人們可用經濟衡量一切、估價一切。在經濟主義者眼里,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只要經濟發展了,其他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對于生活中那些廣泛存在的非經濟部分,“經濟主義不是不屑一顧,就是視而不見”。⑤在經濟主義的詞典中,“可持續發展”僅僅等同于“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⑥
歷史的發展表明, “經濟主義不僅沒有兌現其提出的遏制環境惡化的承諾,反而成為環境惡化的重要推手”。⑦因此,可持續發展“是個成問題的概念”。⑧可持續發展在很多時候被資本主義綁架和利用,它僅僅意味著確保大公司的可持續盈利,而從未考慮對土地的長期影響以及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例如在中非,以建設生態保護區、提供工作機會的名義建造生態小屋、游戲公園,導致成千上萬生活在雨林的原住民背井離鄉,許多人被迫成為“偷獵者”。正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名義下,“人的問題被忽略了”。⑨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第二個缺陷是它的自相矛盾性,即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與可持續發展理念是相悖的。按照經濟人類學家、《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作者、英國皇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賈森·希克爾(Jason Hickle)的分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得分最高的國家恰恰是“世界上環境最不可持續的國家之一”。⑩以瑞典為例:瑞典在該指數上獲得84.7分,位居榜首,但生態學家一直指出,瑞典的“物質足跡”,即該國每年消耗的自然資源數量,為每人32噸,與美國一樣為世界之最;而全球平均水平約為每人12噸,可持續水平約為每人7噸。換句話說,瑞典的消費量是這個邊界的近5倍。如果地球上的每個國家都像瑞典那樣消費,全球每年的資源消耗將超過2300億噸。再以高居可持續發展指數第三位的芬蘭為例:芬蘭的碳足跡,即每人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是13公噸,與沙特阿拉伯類似,是世界上人均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也是氣候崩潰的主要責任者。相比之下,中國的碳足跡約為每人7噸,印度則不到2噸。如果全世界都像芬蘭一樣消耗化石燃料,這個地球無疑是不適合居住的。11也就是說,“可持續發展”概念“失之于沒有追問那些已經過度發展的國家是否還需要增長”。①
此外,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中絕大多數的生態指標都是領土指標,沒有考慮其對國際貿易產生的影響。以其中的空氣污染指標為例:富裕國家看起來很干凈,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它們已經將大部分污染產業轉移到全球南方國家,從而將問題轉移到國外。實際上,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顯示了富裕國家的優勢,卻對它們造成的損害視而不見。②
有批評者據此認為,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者其實并非真心推動可持續發展,而是“以‘綠色的面孔實現一切照舊”。③他們優先考慮的是跨國公司的紅利,環境的福祉在他們那里屬于第二位考慮的因素。以可持續的名義獲得的好處“通常是通過洗綠毀滅性的實踐和意圖而獲得的”。④
可以說,正是由于“可持續發展”概念存在上述內在缺陷,導致從2015年世界各國政府簽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承諾使全球經濟與生活世界恢復平衡以來,全球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愈演愈烈,以致2018年10月8日聯合國向全人類發出警告:“只剩12—22年,地球將陷入危機。”⑤
人們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不滿在語言中也可見端倪。西方學者考察,近年來“可持續發展”一詞已不再占據話語中心,人們嘗試用新的概念取代它,“25年來,詞匯從以可持續性和可持續發展為中心,轉變為平衡、和諧、彈性、再生、未來思維、轉變、健康、內心世界、靈性......”⑥其中,“再生”是取代“可持續”呼聲很高的一個詞。“再生”不僅僅是指可持續的、旨在為后代提供基于當前資源的機會,而且還側重于自然和社區的再生,以便給后代一個比今天更好的機會。⑦
中國學者蕭淑貞也認為,“‘可持續(sustainable)的字面意義是可以延續某種模式或狀態。但是,我們已經做出了太多破壞生態、破壞文化和社群的行為,所以僅僅持續現狀已經不夠了,必須學習如何使社會和自然得到‘再生(regeneration)。比如在很多地區,因為化學農業的污染,土壤已經變得貧瘠、不利于生態農作。我們不是要持續(sustain)現狀,而是要再生(regenerate)土壤,讓適合生態農業的環境重新回來。社會層面也是一樣。比如為了構建社群,我們要做的不僅是維系目前存在的關系,更需要去修復那些已有的疏離、沖突、誤解、分裂……讓人與人的關系得到‘再生”。①
在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看來,“可持續發展”概念另一大根本性的弊端是它僅就環境談環境,沒有觸及工業文明的實質問題。事實上,現在的危機不僅僅是環境的危機,而且是文明的危機,用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話說:“這不是氣候變化,而是一切都在變化。”②(Its not climate change— Its everything change)生態危機其實是人類文明的危機,確切地說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危機,因為這是一種“個體摧毀共同體的文明,是城市摧毀農村的文明,是理性摧毀感性的文明,是競爭摧毀和諧的文明,是抽象摧毀具體的文明,是消費摧毀生活的文明,是金錢摧毀精神的文明,是知識摧毀智慧的文明,是虛無摧毀價值的文明,是人類摧毀自然的文明”。概而言之,工業文明“是一種內含自毀基因的文明,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文明”。③因此,設想在不觸動文明的情況下解決環境問題,不啻緣木求魚。正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的提出者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當前面臨的危機,“不是所謂的‘環境問題,而是工業社會本身的一場影響深遠的制度危機。……以前看似‘功能性和‘理性的東西現在成為對生命構成威脅的東西”。他強調,“正如前幾代人生活在驛站馬車時代一樣,我們現在和將來都生活在災難蔓延的危險時代”。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物種自殺即將到來。”④新冠疫情只是個“奢侈的彩排”,還有“更巨大災難在前面等著人類”。⑤希克爾則明確斷言: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滅絕的時代”。⑥
因此,要避免人類的滅頂之災,顯然不能寄望于可持續發展。人類要想繼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需要一種革命性的新理念,生態文明出場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三、時代需要生態文明
盡管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被寫入黨章和憲法,但不少人依然站在工業文明的立場看問題,把生態文明看作對工業文明的修修補補,認為生態文明僅僅是工業文明的“升級版”,尚未認識到生態文明是一種文明范式的變革。在小約翰·柯布博士看來,這種認識的不足正在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的巨大障礙。對此,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許多談論轉向生態文明的人仍然堅守著現代性的特質,正是這一點阻止他們在生態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事實上,生態文明呼喚深刻的變化和巨大的犧牲。”⑦它要求人類文明“發生決定性的轉變”,呼喚“一種新的變革性范式的出現”。⑧用習近平的話說,“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①它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是一場“全方位的偉大變革”。②它不僅需要哲學、政治、經濟、農業、教育、社會治理等一系列的變革,而且需要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轉變,需要從人類中心主義走向有機整體主義,從個人主義經濟學走向共同體經濟學,從工業化農業轉向生態農業,從以職業培訓為旨歸的專才教育走向立德樹人的通人教育。
首先需要的是哲學觀念的變革,因為哲學是文明的核心,哲學支撐著文明。正如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言:哲學“是精神建筑的建筑師”。③哲學觀是人們思想和生活的基礎。“正是我們所關注的那種想法,以及被我們放入不易覺察的背景中的那種想法,支配著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恐懼以及我們對行為的控制。我們是怎么想的,我們就是怎么活的。這就是為什么哲學思想的匯聚不僅僅是一種專門化的研究。它塑造著我們文明的類型。”④
事實上,正是主宰工業文明數百年的人類中心主義哲學,為今日的生態危機種下了禍根。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自然的毀滅者”。⑤因此,要建設生態文明,首先需要對這種人類中心主義進行理論清算,進而實現從人類中心主義向有機整體主義的轉變。
所謂“人類中心主義”,又稱“人類優越論”或“人類例外主義”,是指將人類視為宇宙的核心或最重要的存在。在人類中心主義者看來,人是可以與自然分離的,是優于自然和地球上其他生靈的。自然萬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礦物等)被看作供人類使用的資源,它們本身沒有內在的價值,僅僅具有工具價值,僅僅是達到人類目的的手段。這一點在現代哲學的巨擘康德那里表現得最為明顯。他曾明確寫道:“就動物而言,我們沒有直接的責任。動物沒有自我意識。它們在那里只是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人是目的。”⑥人類中心主義不僅在認識論上是錯誤的,因為它扭曲了世界的真實圖景;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因為它直接構成了“生態危機的根源”。⑦
與工業文明視萬物為器相反,生態文明是一種敬畏自然的文明,一種以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為旨歸的文明。
與現代工業文明標舉人的中心地位不同,后現代生態文明強調所有生命在本質上都是有價值的,強調地球不是資源庫,它應該有自己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受到尊重的權利,再生其生物能力的權利,并繼續其生命循環和過程的權利”。⑧這就要求我們要善待自然,對自然要厚道。所謂“對自然的厚道”,就是用一種有機的眼光看世界,不是將自然看作與人類對立,而是看作與人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類與大自然中的其他生靈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要像對待自己的至愛之人一樣呵護自然、關愛自然、敬畏自然,因為不是我們去保護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護我們。如果我們毀滅了自然,“我們也就毀滅了我們自己”。①
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自大之后,強調人對自然的敬畏和依賴,強調師法自然,并不意味著人的主動性的消失,更不意味著人的無所作為。在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那里,強調人對自然的依賴和敬畏,恰恰令人獲得根性、獲得歸屬感,并因此獲得保護自然的動力和底氣。在為2021年再版的《是否太晚?》(Is It Too Late?)所撰寫的序言中,柯布明確指出,“今天我認為,我們可以說,‘生態文明已經在路上了。這意味著,以一種關愛的方式將我們與其他人聯系起來,將人類與自然世界聯系起來”,既強調萬物一體,萬物互聯互通,又強調“我們與萬物有一種獨特的關系,我們有巨大的能力決定它們的命運”。②我們有責任保護所有生命的整全性,乃至為生物多樣性的豐富作出貢獻。也就是說,人類可能不僅有史以來首次具備了足以維持地球生命運行的能力,而且有史以來首次“具備了創造一種真正的生態文明的能力”。③
與敬畏自然相聯系,生態文明也是一種重農的文明。這里的“重農”,包括珍惜鄉村、重視農業、尊重農民。
與現代工業文明鄙視鄉村、視之為“失敗之地”、“絕望之地”、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后現代生態文明將鄉村視作中華子孫繁衍生息的根基,視作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孕育和傳承的深厚載體,視作生命神圣的象征。按照著名生態文明研究專家、中共中央黨校張孝德教授的說法,鄉村是離天最近、與地最親的地方,鄉村承載著中華文明的記憶和活歷史,它是“中華文明興衰的底線”“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戰場”“文化和智慧的寶庫”,是生態文明建設“成本最低、優勢最大”“效果最好、資源最豐富”的地方。④“北京、上海、紐約、東京這類現代巨無霸城市盡管貌似強大,然而離開鄉村的糧食供給,一天都難以存活,都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恐慌。”⑤此次全球疫情的爆發,再次彰顯了農業的重要性。沒有農田的城市,自己無法生產糧食和蔬菜,面對洶涌的疫情,顯得格外脆弱。而鄉村有地、地里有菜、地窖有糧,所以才有“大疫止于野”的古訓。中國抗疫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鄉村功不可沒。鄉村不僅是新冠肺炎感染率最低的地方,而且在源源不斷為封城中的人們提供新鮮蔬菜和糧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鄉村的的確確“是中國安全的保險閥、化解危機的蓄水池”。⑥展望未來,隨著生態危機在全球范圍的加劇,鄉村的重要作用會越來越凸顯出來。因此,一種重農的生態文明就是必需的。要振興鄉村、繁榮鄉村,離不開對農人的尊重。生態文明正是一種尊重農人的文明,農人被看作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價值的存在。正如中國著名環保作家徐剛的詩意表達:“農人是一種高貴的生活方式。”⑦
沒有人是孤島!個體充分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的最好方式是繁榮有機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文明是一種追求有機共同體繁榮的文明。
從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視角來看,工業文明最大的弊端之一是對有機共同體的摧毀。城市的“冷漠癥”、農村的“空心化”現象就是這種弊端的突出表征。正如查爾斯·艾森斯坦所言:“我們的房子大了,但家卻變小了;……我們可以到月球走個來回,卻很難過條馬路去問候新鄰居。”①
作為對工業文明的超越,“生態文明是這樣的一種文明:其中每一個共同體都認為自己與其他共同體一樣共處于共同體之中”。②它意在重建個體與社群的關系,因此格外重視有機共同體的繁榮。所謂“有機共同體”,就是由跟自己關系密切的人構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包括親人之間的關系和鄰里之間的關系。受現代西式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文明視這些關系和聯系為一種束縛,是“落后”的標志,因此必欲摧之而后快。生態文明則強調內在關系和有機聯系,它格外珍惜共同體,力促共同體的繁榮和發展。在小約翰·柯布看來,關系是構成我們的核心要素,個體與群體血肉相連。個人的發展有賴于社會共同體的繁榮,“他人的健康恰恰有助于我們的健康”。③那些通過損害共同體的福祉而獲得財富的人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幸福,因為我們個體的幸福與他人的幸福是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一個健康的共同體一定是既高度提升個體的幸福感,又極大增進群體和生態體系福祉的共同體。在柯布看來,面對生態災難,這些基于互愛基礎上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共同體“更有可能生存下來”。④
正是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對鄉村的珍惜、對有機共同體的呵護,使得生態文明拒絕惡性發展,倡導厚道發展,拒絕個人主義經濟學,推重共同體經濟學。共同體經濟學認為,包括地球所有居民的健康在內的整個星球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的”,經濟應該為整個系統的福祉服務。這就是柯布所說的“大經濟”,即一種旨在為人類和自然的共同福祉服務的經濟,是生態文明迫切需要的經濟。
四、有機過程思維可以為生態文明提供理論支撐
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⑤建設生態文明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同樣離不開理論思維。由于作為工業文明哲學基礎的固化的、靜態的機械思維業已暴露了諸多弊端,已經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⑥因此,生態文明亟需一種新的思維,我們稱之為“有機過程思維”。
有機過程思維是一種基于有機過程哲學的整全性思維。它視生成、變化和創新為存在的本質屬性,視有機關系為事物構成性的存在。它強調,我們不僅與他人是深度聯系在一起的,而且與宇宙萬物都是深度聯系在一起的。有機過程思維將宇宙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無縫的相互聯系的事件之網,其中沒有一個事件能夠與其他事件完全分離。萬物互聯,萬物互涵”。⑦在這個有機整體的宇宙中,機械二元論沒有生存的空間,“有感知與無感知、有生氣與無生氣、有生命與無生命之間并無一種最終界限”。⑧有機過程思維視域下的宇宙觀是一種生態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將世界看作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它無意將生命體與其所處環境分離開來。①
在有機過程思維中,“關系”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關系(relations)比實體(substances)更為首要”。②也就是說,關系是事物構成性的要素,“正是關系特別是內在關系構成了事物本身”。③由于萬物皆由其關系構成,如果這些關系在同步或歷時上都沒有邊界的話,“那么一事物都或多或少地與任何其他特定事物相關聯”。④
因此,強調萬物互聯互依互通是有機過程思維的精髓。按照未來學家斯邁兒(Rick Smyre)和理查德森(Neil Richardson)的說法,“或許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歷史性轉變就是從獨立不依到相互倚賴的轉變”。⑤在弗里喬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看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是有解決辦法的,其中一些甚至很簡單,但需要我們的看法、我們的思維以及我們的價值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一旦我們開始恢復對地球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星球的看法,看到一切都在一個錯綜復雜的生態系統網絡中連接起來,而不是從還原論的地球角度看待它,我們將邁出治愈我們家園和我們自己的第一步”。⑥
可以說,按照有機過程思維,萬物互聯互依互通是宇宙的實相。不實現萬物互聯互依互通這一認知和思維方式上的轉變,生態文明是不可能建成的。
有機過程思維在中國擁有深厚的思想基礎,因為“作為《易經》的民族,中華民族可以說是過程思維的民族”,⑦中國人的宇宙觀和自然觀按照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說法是“有機主義的”。⑧根據著名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的考察,“中華文化傳統內具有悠久歷史而形成的互系性思維方式”。⑨他認為,“互系性思維方式可讓人們對這個千變萬化的世界有深刻的認識與參與意識”。⑩這意味著中國文化“支持一種萬物互聯互通的世界觀”。11作為一筆“寶藏”,中國萬物互聯互通的哲學“為我們以一種更有利于服務健康星球上的福祉的方式重構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提供了機會”。12其實,今天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可以看作是這一優秀傳統的延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包含了人類在21世紀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安全等各方面相互依賴、共贏共生的關系。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一步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的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各國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①按照《何謂生態文明?》一書作者的說法:“生態文明不僅僅有關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它還需要人類彼此之間要和平相處,從而促進所有生命的繁榮興旺。”②如果說現代工業文明是一種尚爭文明的話,那么“后現代的生態文明應該是一種尚和的文明”。③因此,有機過程思維不僅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生態文明的需要。
事實上,有機過程思維在當代西方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發生在當代西方的“過程轉向”或“關系轉向”就是證明。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試圖根據構成事物本質要素的過程和關系來理解復雜的現實”。⑤許多交叉學科研究(諸如科學與技術、環境人文學與后人文學等)也開始依據有機關系思維“重構對自然-文化的學術理解”。⑥有機過程思維被認為是有助于“克服學術界和科學界時下的碎片化現象”。⑦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和思想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戈爾德(Tim Ingold)就曾強調,生物學家在考察有機體的發展時也開始接受有機過程思維,揚棄遺傳學的觀念傳統,“采取過程性的、發展性的、關系性的視角”,還原生物個體本來面目,將人與非人有機體的生成與維持視作“整個關系矩陣的展開”。⑧在間性論的倡導者、著名媒介哲學家弗盧瑟(Vilem Flusser)看來,存在即互在。無論是在賽博空間還是面對面,“我”和“你”都互為結果、一同產生。“無論我們把目光投向何方,我們都會看到相互依存、共同發揮功用、相互適應和共同演化”。⑨
由于相互依賴是生命的本質,相互成就是生命的升華,因此有機過程思維呼喚一種“共命意識”。所謂“共命意識”,就是意識到我們和他者是共享命運的,是同呼吸、共命運的,是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這既包括與他人共命,也包括與自然甚至病毒共命。“共命意識”令我們時刻意識到,我“生活在與其他生物例如細菌或病毒的共生關系中”。⑩這意味著我們的生命得以存在,完全有賴于其他生命形式包括微生物和病毒的存在,我們與病毒也是共享命運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持續不退的今天,這一點格外具有現實意義。這要求我們“學會尊重微生物世界,學會敬畏病毒,學會善待病毒,與病毒共存”。①這也要求我們“放下‘不惜一切代價消滅微生物病毒的愚蠢執念。因為,縱觀人類災疫史和病毒史,任何一次瘟疫的結束都不是以真正消滅了那種病毒為勝利的標志的,而是人類以生命為代價去學會適應這種病毒,并最終學會與之和解為標志”,“妄想消滅病毒的執信最終會徹底解構人與微生物世界之間的極為脆弱的共生存在的平衡框架,結果只能是人的個體生命的消逝和人類的毀滅”。②
所謂尊重病毒,就是自覺地意識到病毒的存在也是我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物學的最新研究表明,病毒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親密伙伴”。③從這樣一種視角出發,我們也不應該把新冠看作敵人,而應看作“信使”。它的使命是勸說人類把極速發展的腳步放慢,旨在提醒我們注意“大自然的存在對于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是如何至關重要”,④我們和地球之間是如何休戚與共,是如何同呼吸共命運的。正如西班牙薇薇安女士借助新冠病毒之口所明確表達的那樣:“我讓你們發燒……因為地球在燃燒;/我讓你們呼吸困難……因為污染充滿天空;/我讓你們軟弱……因為地球一天天在衰弱”;“我的來臨不是要懲罰你們,而是來喚醒你們”;“停止污染地球,停止相互爭斗。/不要再關心物質上的東西,開始愛你們的鄰居吧 。/開始關心地球和所有的生命……”⑤
有機過程思維對我們每個個體的啟迪就是: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無需等待“蜘蛛俠”“鋼鐵俠”“超人”之類的大英雄來拯救世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改變的力量。
相信隨著新冠大流行所彰顯的“全球的互聯性和人類的脆弱性”,⑥特別是隨著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體認,有機過程思維一定會大有用武之地,也必定會有一個璀璨的未來。
責任編輯:胡穎峰
特邀編輯:胡春雷
責任校對:王俊暐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