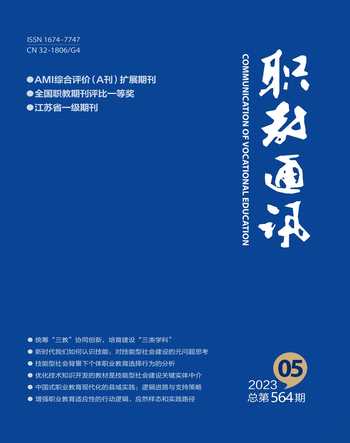優化技術知識開發的教材是技能型社會建設關鍵實體中介


摘 要:技能型社會建設可被理解為旨在通過強調技術知識傳播,有效培養技能人才并豐富技能組織的社會改良行動,其落地不應局限在傳統技能社會建設的體力訓練,而應更加關注技術知識在技能人才上的傳播、在社會組織的固化、在技能文化的隔代傳遞等方面的加強。缺乏承載技術知識的實體中介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關鍵難題,而作為全民使用的教材可作為全局性的實體中介,能夠消解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空心化問題。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生根,亟待優化技術知識進教材,彌補教材不足,關鍵包括三重策略:科學開發技術知識,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具體素材;優化教材呈現邏輯,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知識脈絡;開展教材知識治理,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培養保障。
關鍵詞:技能型社會;技術知識;職業教育;教材;實體中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四五”規劃2022年度教育學重大課題“技能型社會測度模型、驅動因素及路徑優化研究”(項目編號:VJA22000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四五”規劃2022年度教育學重大項目“新發展階段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研究”(項目編號:VFA220003)
作者簡介:賓恩林,男,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課程、教學與教材、職業教育產教融合。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747(2023)05-0025-09
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技能型社會建設目標,“到2035年,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會基本建成”。隨后,學者們描繪了系列制度建設、機構運作與標準設計等技能型社會建設藍圖,國家亦推出了系列制度或相關政策。但要確保技能型社會落地生根,使其在現實中成為人人自主追求的社會理想,必須尋找到能發揮關鍵中介作用的實體,才能把社會藍圖轉化為社會現實。
一、技能型社會建設內涵與實踐難題
(一)何謂技能型社會建設
剖析技能型社會建設內涵的關鍵在于深度分析社會與技能的概念實質。社會(society)原有兩重含義:其一是通常人們所理解的由人組成的文化、經濟與政治等組織,一般指各種組織的總稱;其二是社會學中相對較為原本的理解,即與家庭等私人領域對應的公共領域,這些公共領域由一定社會事實所揭示,強調人自行結合而組織化的過程與結果[1]。建設是一種行動,技能型社會建設就是強調技能傳播與傳承的社會實踐行動。社會實踐變革的根本,在于通過教育來改變社會中的人與組織,想要形成何種社會或組織,就需要培養或孕育何種人才,技能型社會建設亦是如此。技能人才培育與組織建構是技能型社會形成的關鍵。如,有學者主張,全民普及技能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基本前提[2];有學者提出,學習職教先賢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形成某種社會組織思想或實體組織,進而推動大職業主義、職業陶冶教育、職業補習教育的普及,有助于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3]。
技能型社會建設中的技能概念到底是什么含義?技能型社會建設的背景是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經濟相對較為發達的當代社會,技能的含義與傳統職業教育所強調的肌肉訓練等動作技能或普通教育所強調的純思維認識技能有所不同。雖然技能養成的艱苦與重復訓練的要求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但是技能型社會所強調的技能概念更加廣泛,涵蓋了融通知識與技能、融匯理論與經驗的一線崗位專家型人才的培養和推廣。這些人才及其組成的技能組織或技能網絡,應推動整個社會文化轉向技能型文化,扭轉傳統社會偏見所表達的對學術社會或文憑社會的大眾化追求。此外,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重點不在于重回幾十年甚至百年前的對苦力訓練的強調,而是在新經濟、新技術背景要求下,注重技術知識在技能人才上的傳播、在社會組織的固化、在技能文化的隔代傳遞等方面的增強。
綜上,技能型社會建設是一項旨在通過強調技術知識傳播,有效培養技能人才并豐富技能組織的社會改良行動。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適應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通過大力開發、傳播和創新技術知識,改變社會的技能型組織結構,提高技能人才素質,建設具有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的技能型人才隊伍,推動社會文化多元化發展,尤其強調符合新技術知識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培養,并將技術知識的固化和傳承視為關鍵。只有充分容納技術知識的技能訓練,才能滿足當前智能化時代社會形態和產業發展對技能人才的需求,才能為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奠定技能創新和技能傳播的基礎,成為真正面向未來的技能型社會建設行動。
(二)缺乏實體中介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關鍵難題
實體中介是任何社會藍圖成為現實的重要中間環節。根據不同社會藍圖的性質,其成為社會現實的難題也不相同。例如:知識型社會建設的難題是如何構建知識團體、知識網絡、知識載體等社會中介;數字化或智能化社會建設的難題是如何構建儲存數據與傳播智慧的平臺,如何培養適應數字化或智能化社會需要的建設者。技能型社會建設亦是如此。如何打造滿足技能型社會發展需要的實體中介,進而傳播技能文化、積累技術技能、創新技能文化等,整體性提升社會的技能積累能力與發展能力,成為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關鍵難題。
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關鍵在于其所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培養與技能組織網絡構想能夠成為社會現實,而承載技術知識的實體中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其作用不僅在于信息傳遞、溝通交流,還在于技能發現與驗證、中介與傳承等。一是實體中介發揮著發現技能、驗證技能的作用,這一作用是技能型社會建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實體中介是技能人才培養與使用之間不可缺少的橋梁和紐帶,有了橋梁才能把社會藍圖落實為現實中個體的具體追求;三是實體中介發揮著保障社會技能文化傳承質量的作用,空間局限性導致個人經驗、技能的傳播與傳承是有限的,而實體中介的儲存、傳播與傳承相對是無限的。目前,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處于關鍵時期,迫切需要轉變傳統觀念,打破思想禁錮,突破思維定式,克服思想保守傾向,積極探索,從國家全局的高度尋找實現技能型社會藍圖的關鍵實體中介。
二、作為全局性實體中介的教材與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空心化問題
(一)承載技術知識的教材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全局性實體中介
教材對社會改良的影響是全局性的。教材是傳遞知識、訓練技能、引導技能文化傳承的全局性、全民性實體中介,是所有院校與整個社會培養技能型人才所必須準備的基礎性工具。雖然從具體的教材運用上看,似乎存在較大的個體隨意性,甚至在西方“自下而上”的教材機制和行政管理體制下,教材作為“一課之本”的地位也在逐步動搖,但在我國“自上而下”的教材機制中,歷來重視教材的標準化內涵,迄今這仍然屬于天經地義[4]。因此,教材勢必成為實現社會藍圖的重要支撐。國家教材委員會的成立,以及職業教育類國家教材研究基地的專門設立,就是試圖從全國整體層面扭轉意識形態式微的局面,進而改良社會現實。
職業教育教材主要是承載技術知識的載體,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重要實體中介。與概念、命題及實驗數據等組成的科學知識不同,技術知識是對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技術規則、操作方法與實踐判斷等工作過程中關鍵要素的描述。職業教育直接面向產業所需要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流程等技術知識,因為掌握各類技術知識是勝任工作任務的基本前提。技能型社會建設需要更新培訓體系,關鍵在于深化校企合作,加強對技術知識的挖掘整理。技能型社會建設還需要職業技能培訓體現終身性、發展性與制度性,其重要的中介手段就是筑實職業院校對技術知識的系統開發[5]。隨著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不斷深入,教材在承載技術知識、建設技能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有學者指出,職業教育專業教材是知識傳播和技能培養的重要載體,事關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和職業崗位工作勝任能力[6]。教材是課程改革與課堂落實的關鍵中介,“高質量教材的缺乏已成為當前制約課程改革深化的關鍵性因素”[7]。承載技術知識的教材也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實踐支撐,因為它是將理論知識與職業技能有機結合的載體。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必要條件是技術知識在社會內部與代際之間能夠順暢傳播,關鍵是要把新流程、新工藝、新材料與新方法等技術知識納入到社會學習體系、國家技能人才儲備體系與創新體系之中。在經濟社會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已經具有相當水平的今天,技能型社會建設已經不同于傳統上偏重體力的技能型社會構建,其新要求是要針對不同領域的技術知識進行全面而深入的開發與整理,充分運用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技術知識,而教材開發是技術知識開發的重要抓手。“只有教材才能夠為技術知識具體內容開發提供動力源泉和方法支撐”[8],因為教材可為技術知識開發提供資料支撐、路徑與方法,是工作場所訣竅系統化的抓手。教材通過將技術知識符號化,進而融合到系統的課程與教學之中,可以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更好地適應技能型社會發展的新要求。
(二)承載技術知識的教材之迷失與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空心化
技能型社會建設空心化問題是指盡管社會有相應的制度或倡議,但缺乏有效的社會實體中介或這些實體中介的影響范圍不足,導致技術知識的流通和傳承受到阻礙或不暢通。例如,技術知識可能缺乏承載素材、缺乏整理脈絡,或即使有這些素材和整理,但缺乏知識治理作為保障。教材是關鍵的實體中介,在技能型社會建設中具有全局性的影響,然而,當前存在教材內容迷失的問題,這進一步加劇了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空心化。
一是教材內容遠離技術實際而呈現出淺表化,導致技能型社會建設所需的技術知識缺素材。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教材內容與實際工作任務脫節,導致技術知識缺乏所需的基本素材。機械、工具、材料等素材是技術知識呈現的基礎,教材作為表達這些素材相互聯系的綜合性材料,影響著技術知識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與傳承質量。然而,由于技術知識的概念定義存在分歧和難以妥協,教材內容往往偏離實際工作任務,停留在概念解釋和行動指導的表層,缺乏揭示概念內在關聯和行動內在機制的深度分析。此外,教材內容也存在偏重理論知識而缺乏職業技能訓練的問題,導致教材內容偏向知識,而不是技能。這會導致教材內容的技能空心化,即存在有知識無技能的情況。并且,由于缺乏實際應用和綜合性訓練,教材與實際應用脫節,缺乏實際案例的引導,實用性與適應性不足,無法滿足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教材內容缺乏對技術知識特質與層次的深度認識,導致教材內容缺乏技術知識開發,內容過于陳舊,缺乏創新性,與現實社會脫節,難以滿足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需要。
二是教材呈現缺乏組織依據而呈現出零散化,導致技能型社會建設所需的技術知識缺組織脈絡。職業教育教材具有知識性、技能性和實踐性的多重邏輯特性,這要求其所呈現的知識、技能必須與企業生產緊密結合,否則教材呈現就會因缺乏依據而變得零散,從而導致技能型社會建設所需的技術知識缺乏組織脈絡,難以促進技能人才的培養。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多種邏輯交錯的零散化。職業教育教材的邏輯系統相對于普通教育教材來說更加復雜,而多種邏輯打破了傳統知識類型的條理,導致教材的邏輯變得零碎。普通教育教材主要呈現科學知識,以系統性和精確性為主要特征,從而形成了針對知識對象的知識分類和呈現樣式。相比之下,關于職業教育教材的知識對象細分研究不足,對技術知識對象特性的研究也不足,技術知識分類缺乏標準,導致職業教育教材缺乏科學的知識規整邏輯,內容呈現出較大的經驗性成分。此外,職業教育教材主要強調活動成分,而忽視了知識內容,雖然技術知識的實踐部分得到了肯定,但技術知識理論缺乏整體性和體系性,從而直接導致技能人才培養的零碎化。這可能是國家整體層面技能型人才培養質量參差不齊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是實踐邏輯內部的零散化。雖然職業教育教材強調實踐邏輯的重要性,但由于企業參與技能人才建設不夠充分[9],教材的實踐邏輯難以得到有效展開或缺乏脈絡。要充分展開教材推動技術知識學習的實踐邏輯,需要教材開發者與教師了解實際生產過程,具備分析、判斷和優化實際生產過程的能力,以及具備與企業需求相匹配的知識和技能,進而具備有效綜合應用的意識和能力,這些都有賴于校企“雙元”開發教材以及對教材知識理論的深入研究。
最后,是教材運用與評估階段的治理鴻溝,導致技能型社會建設所需的技術知識傳播缺保障。隨著國家層面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的完善、國家職業教育教材基地對教材開發的引領以及活頁式教材開發的普及,我國也出版發行了一定數量的、能夠推動技能型人才培養的優質教材。然而,由于職業院校存在分散化管理的慣性和教師學習新教材的惰性,導致出現了兩種治理鴻溝。一是設計與運用治理鴻溝。由于缺乏分類治理技術或管理經驗,國家、院校、地方層面難以實現教材技術知識的全國性整理以及職業領域化整理。二是運用與評估治理鴻溝。雖然有些教材開發了相對完整和優質的技術知識,但因缺乏行動與評估的治理保障,教材未必能夠得到合理使用,也難以通過新教材進行課程教學或學習績效的評估。
三、優化技術知識進教材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的三重策略
(一)科學開發技術知識: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具體素材
科學開發技術知識的前提是建立一般化技術知識概念共識或認知。
其一,對技術知識的定義與真假意義形成共識是必要的。學術探討的差異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技術知識觀點,甚至許多學者認為技術知識并沒有真假之別。然而,服務于教材實踐和社會構建的技術知識必須具有相當的確定性。技術知識指的是認識工作世界的現象、理解工作世界的思維以及試錯后執行工作任務的訣竅,這些思維或操作的結果需要在現實中有明確的判斷,并產生行動意義。因此,技術知識勢必有真假之分,否則在現實工作中無法完成任務,甚至會發生工作事故。真正的技術知識能夠幫助行動者理解工作世界,獲得嫻熟的職業技能,作出準確的職業判斷。在基于工作任務的技術知識開發過程中,運用經驗試錯且能重復驗證并保持自洽的工作信息,更可能成為真技術知識;同時,運用科學方法所獲得的技術知識也很可能為真,因為在科學方法下得到的技術知識一般能夠滿足自洽、他洽與續洽等知識標準要求。在技術知識體系中,全面的真假判斷是開發技術知識的基本前提。
其二,對技術知識特質的認知。基于上述對技術知識的定義,技術知識是工作世界的反映,而工作世界總是具有前因后果關系的,否則就無法呈現秩序,因此,開發技術知識必須遵循三個特性。首先是邏輯性。所有技術知識的前因后果判斷鏈必須符合工作邏輯,并遵循基本的思維邏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因為形式邏輯的先驗性與工作邏輯的實踐性是保障技術知識真理性或真實性的前提。其次是系統性。基于感官知識的歸納,可以得到上一層抽象技術知識,而根據下一層抽象知識的歸納,則可得到更上一層的技術知識。因此,技術知識不是僅局限于情境或“眼見”的具象對象,而是由感官知識和抽象知識雜糅而成的有結構的狀態。對整個技術知識體系從上往下進行整理可以獲得系統性,因為工作世界具有秩序,因此技術知識也具有系統性。最后是原則性。盡管工作情境因技能類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情境性,但只要確立了某種工作情境內部的原則,就是一種通式,萬變不離其宗,就能“以不變應萬變”或“以當前練習應未來技能判斷”,從而成為真正能夠輔助未來工作判斷和技能創新的技術知識。
其三,明確技術知識的涉及范圍包括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聚焦各層次的重點。微觀層次是指技術知識中的每個技能點、知識點或素養點,都需要理解其前因后果和思維邏輯,以便得到組織教材素材的線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目的在于“知其所以然”。此外,在脫離個體情境對技術知識進行抽象提煉時,需要同時開發能夠表達或指示該知識的感官知識以及程序性描述文本,進行流程機制圖示或推理講解,從而真正系統化開發與工作任務相關的技術知識。中觀層次是指技術知識的整體架構。技術知識開發需要了解技術知識的全貌,其目的在于“知其所從”。雖然傳統上技術知識是反學科理論的系統化的,但卻具有其獨特的系統性。因此,技術知識開發需要將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的知識系統整理出來,以便讓學生了解一個技術問題的來龍去脈,并能舉一反三、周詳考慮,應對未知的技術難題。宏觀層次是指有關技術知識共有的實踐規則或原則,以便形成前后有因果、左右有聯系的技術學科,成為專業性的學習材料或科目,其目的在于“知其所宗”。雖然技術知識在跨領域時具有情境變化性,但在同一工作領域中具有“萬變不離其宗”的實踐原則。
形成技術知識共識之后,技術知識開發的關鍵就在于明確與規范整理技術知識的方法與過程,包括簡單化、系統化與原則化三個核心環節。簡單化環節是指將一門包括工作內容描述與理論知識體系的技術學科的要點摘錄出來,成為每章教材所表述的專業名詞、技能行動描述、問題解決方案等。簡單化的目的在于掌握技術知識的重點。系統化環節是指按照要點的行動邏輯順序把技術知識排列成體系,比如活頁式教材直接以職業能力作為教材組織邏輯,形成了直接作為教材目錄的職業能力條目體系。系統化的目的在于掌握技術知識的本末。原則化環節是指將一門技術知識的內部原則歸納出來,其目的在于掌握知識的通性。如此,借助教材開發傳播或傳承技術知識就有了素材與憑借,有了重點就可以執簡馭繁,有了本末就可以知所進退,有了原則就能確立專業領域內部安身立命的方向,技術知識開發就能夠在技能型社會中因其專業性而獲得社會認可與社會地位。
(二)優化教材呈現方法: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知識脈絡
明確靜態符號與實際行動呈現的區別,整合技能型社會建設中技術知識的理論脈絡與實踐邏輯,關鍵在于技術知識的符號化分類與組織。技術知識與傳統單純的抽象符號知識不同,它的呈現需要符號與實際行動(觀摩、模仿等)的互相配合。首先,要對所開發的技術知識的符號化呈現與實際行動呈現的表達限度進行判斷,盡可能系統地以符號呈現技術知識的全貌,即便是難以呈現的觀摩與模仿行動,也應盡量采用影像或其他數字化手段進行輔助呈現,實在難以符號化的內容則應當在教材相應的教學法指導部分對任課教師的課堂行為加以說明。其次,依據知識分類呈現相應的符號類別。呈現符號的紙質教材或電子化教材,實際上均在回答“是什么(what)”“為什么(why)”及“如何(how)”三個問題。這三類問題中又有偏重高深的認知性思維(高等數學、大學物理等)與偏重復雜性行動實踐(數千頁的飛行員操作手冊等)的區分,進而區分出“直觀是什么(what)”“是什么(what)”“做什么(what)”“為什么是這樣(why)”“為什么這樣做(why)”“如何理解(how)”與“如何做(how)”這幾種知識,具體見表1。其中,“是什么”指的是感官或名詞與動詞的定義,“為什么”指的是論點或行動的性質,“如何”指的是解決問題或執行操作的方法。“直觀是什么”的技術知識必然要求有五官的實際體驗,或者至少要有配套實物圖;“是什么”的知識則應強調認知的結構化與系統性,比如教材中應補充與技能相關的知識圖譜;“做什么”則應當充分挖掘程序或過程,比如教材中應較為詳實地呈現流程圖。
技術知識的符號化組織呈現,從知識開發到知識符號化、組織化并形成教材,需要考慮教材的知識結構、學習者的特質以及知識解決問題的排序。技能型教材通常采用“頭小中間大”的喇叭型形態,中間內容要盡量均衡分布。教材開始應當介紹教材的基本設計理念、內涵與結構,接著詳細說明每一種技能項目、技術知識等。為了避免教學邏輯對教材邏輯的干擾和縮減閱讀壓力,教材結尾一般不用過多總括或延展。針對初學者的特質,教材的基本邏輯應按照知識要解決的問題難度、實踐邏輯逐步推進,無關內容的夾雜會嚴重干擾知識學習或技能訓練質量,從而使技術知識傳播效率降低。一般來說,每個章節都應具有相對獨立性,同時又有統一性。根據技能領域知識性質的不同,整本教材、整個章或整個節可能采用不同的章節命名形式,比如“工作領域—工作任務—職業能力”,但根本上都在回答知識的三個問題,即“是什么”“為什么”和“如何”。在符號化呈現技術知識時,首先應呈現直觀敘述型、抽象敘述型、親身敘述型三類知識,然后在此基礎上根據項目和任務表達與訓練的需要,適當安排說明型和解釋型知識,以滿足行動與概念整合的需要。通過符號化組織技術知識,可以推動技術知識的組織和傳播,促進技能訓練的組織化,從而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有技術知識脈絡可遵循、可參照。
(三)開展教材知識治理:確保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有培養保障
呈現技術知識的教材開發后,不代表教材就能被實際運用,也不能僅把運用作為評價依據。要真正實現技能型社會建設藍圖,還需要推動教材生命周期整體循環的知識治理,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落地生根有保障。技能知識不比科學知識的固定性,其治理不是僅僅通過國家管理部門、圖書館與學科協會等中介安排與相關制度建設就能較好完成。技術知識注重行動性、創新性、開發性,因而其教材治理的關鍵在于行動。在宏觀管理機構設立與規章制度設計之后,教材治理還需要做到技術知識與教材開發全生命周期(發展目標—執行—評估)的規整化、秩序化,才能有序、高效地培養技能人才,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藍圖落地有保障。
首先,整體上要明確與遵循技術知識治理的行動邏輯。一要在國家管理制度層面明確教材技術知識治理整體目標。職業教育教材的編寫、修訂與使用,應在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對接產業發展需求、遵循職業教育規律、反映行業發展趨勢的前提下,注重體現時代特色,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突出綜合育人的重要地位,體現產教融合育人思想。在國家戰略目標引領下,教材及其技術知識開發、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分析,要緊密圍繞服務技能型社會建設,圍繞職業教育和技術知識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二要明確復雜的執行與評估層面的技術知識治理邏輯,從技能型社會建設角度明確教材知識治理重復運轉的閉環系統,推動各類社會組織、不同角色的個人采取合理的知識治理行動。三要評估教材知識治理是否達成目標。整個治理閉環系統包括三項關鍵事件。一是設計期望發生的技術知識傳播與傳承目標,促成技能型社會建設這個總體行動目標。二是執行環節,包括實現目的的意圖、具體動作的順序與動作的執行三個子環節。行動目的是指達成什么樣的結果,一般表述相對比較含糊,因此還需要明確設定實現目的的意圖,把意圖分解為具體動作,進而按照既定動作順序具體執行行動步驟。三是從外部技術知識與對教材世界的感知、解釋及對解釋進行評估等方面來判斷知識治理是否達到了最初設定的目標。具體見圖1。總之,環節一是總體目標設計階段,環節二是執行階段,環節三是評估階段,通過目標—執行—評價循環,最終實現目標與外部技術知識、教材世界構成動態而良性的持續循環。比如,國家教材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教材行政管理部門與資深行業專家、優秀專業教師等組成專家委員會,設計技術知識傳播與傳承的目標,國家教材委員會、職業教育管理機構、院校技術知識開發機構、教材開發機構與專業人員明確“去做什么”與“檢查這樣做的結果”,以知識治理的“執行”與“評估”行為促成知識治理目標的達成,最終間接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其次,重點任務是綜合教材符號表達的技術知識與教學呈現的實際技術知識,開展雙邊統籌的知識治理。教材承載的技術知識必定是有限的,一些關鍵的技術知識只能保留在工作場所或其他實踐環節。因此,在確保技術知識盡可能顯性化并成為教材符號的同時,如果某些技術知識不能被顯性化或教材化,也必須明確在哪些活動或實踐中能獲得何種技術、鍛煉何種技能,然后將這些活動和實踐程序、過程提煉為教材內容的指示對象,使符號與實際活動相互關聯,形成“理實一體化教材”。教師應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把這類技術知識融入到教材中,結合實際案例進行講解,幫助學生掌握工作技能,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有通過教材符號與教材實際的互動治理,學生才能在實踐中獲得更多的技術知識、鍛煉更強的工作技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技能型人才,從而為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技能人才培養保障。
參考文獻:
[1]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93-94.
[2]劉曉,王海英.技能型社會下職業教育公共服務的現實訴求、體系構建與實施路徑[J].現代教育管理,2022(6):90-98.
[3]石偉平,郝天聰.職業教育如何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黃炎培職教思想的當代啟示[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23(1):59-67.
[4]陳桂生.變化中的“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解讀[J].全球教育展望,2006(11):37-42.
[5]劉曉,錢鑒楠.技能型社會下的產業工人職業技能培訓探析[J].中國高等教育,2021(21):45-47.
[6]高建榮,王素霞,高藝恒.類型定位視域下基于協同理念開發職業教育專業教材的路徑探索[J].職業技術教育,2022(20):49-53.
[7]徐國慶.職業教育的教材建設[J].職教論壇,2015(18):1.
[8]徐國慶.開發技術知識:“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課程建設的突破點[J].教育發展研究,2020(9):47-55.
[9]雷世平,謝劍虹,樂樂.技能型社會視域下企業在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及實現路徑[J].職教通訊,2023(1):15-21.
[10]賓恩林.職業教育專業課教材的結構化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21:12.
[責任編輯? ?賀文瑾]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ed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ocial improvement action aimed at effectively cultivating skilled talents and enriching skilled organizations by emphasi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ts implementa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physical training in traditional skill society construction, bu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mong skilled talents,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kill culture. The lack of physical intermediaries that carry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s a key challen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ed society. As a textbook used by the whole people, it can serve as a global entity intermediary and solve the hollow problem of building a skilled societ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ed society, it is urgent to optimize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to textbooks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key strategies include: scientifically develop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ed society with specific materials; optimize the presentation logic of textbooks an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kill society construction with knowledge context; carrying out textbook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illed society with cultivation guarantees.
Key words: skilled society; technical knowledg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physical intermedi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