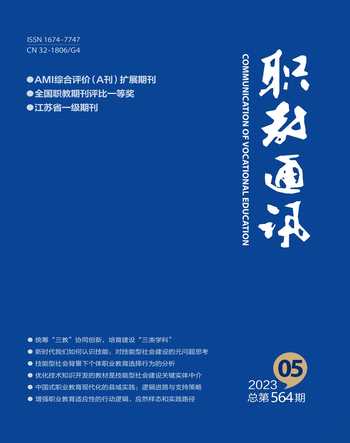產教融合背景下高職院校合作產權重組:政策需求與機制創(chuàng)新
張曉湘 周勁松
摘 要:高職院校深化產教融合需要在合作產權重組上破局。當前高職院校合作產權重組面臨產權歸屬界定難、產權價值確定難、產權讓渡實施難、各方目標統(tǒng)一難等問題,需要定位合作產權政策變革的目標指向、增大高職院校國有資產管理授權、實施合作產權全面保護、引導規(guī)范合作產權交易。高職院校需要理性選擇合作主體、健全產權讓渡流轉制度標準、構建多元產權結構形態(tài)、建立辦學成本分攤及運營收益分配機制、完善內部產權監(jiān)管體系。
關鍵詞:產教融合;高職院校;產權重組;政策需求;機制創(chuàng)新
基金項目:2022年度湖南教育科學“十四五”規(guī)劃課題“公辦高職院校校企合作產權重組與資產管理研究” (項目編號:XJK22CZY014);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學研究工作者協會課題“高職院校校企合作實訓基地項目建設關鍵問題研究”(項目編號:XJKX22B148)
作者簡介:張曉湘,女,湖南工業(yè)職業(yè)技術學院資產管理處高級經濟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經濟、事業(yè)單位資產管理等;周勁松,男,湖南安全技術職業(yè)學院副院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區(qū)域職業(yè)教育政策、院校發(fā)展等。
中圖分類號:G7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747(2023)05-0072-07
職業(yè)教育與產業(yè)有著與生俱來的淵源,一直以來產教融合也被認為是促進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重要舉措和高質量發(fā)展的邏輯主線。在產教融合項目實施中,伴隨產業(yè)主體與教育主體之間產權的流動、組合和運營,高職院校也面臨著“產權壁壘”、產權糾葛等突出問題,影響校企跨界資源配置共享和產教雙方共生發(fā)展。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中對財產的所有權界定,表現為對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具有經濟實體性、可分離性和可流動性等內在特征。校企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對各自產權進行分離讓渡后形成的共享性產權就是“合作產權”,“重組”則是指“合作產權”經分解的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在政府、學校和企業(yè)三個主體之間的權能歸屬結構組合及其運行模式[1]。產教雙方的矛盾組合及其呈現屬性,大多歸因于合作過程中的產權沖突,而且必須通過產權安排才能解決矛盾沖突。因此,有針對性地解決高職院校產教融合實踐中的產權重組問題,形成產權讓渡、轉換及產權收益保護的激勵性環(huán)境,才能破解高職院校“自給自足”辦學困境,促進高職院校與行業(yè)企業(yè)達成生產項目、設備、人員及科技成果資源的共享,形成“利益共同體”發(fā)展模式。產權重組的政策需求和院校自身的機制創(chuàng)新,也就成為推動高職院校持續(xù)深化產教融合的必然邏輯。
一、產教融合背景下高職院校合作產權存在的問題分析
市場經濟發(fā)展要求建立產權歸屬清晰、產權權責明確、產權保護嚴格以及產權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當前,高職院校在實施“校中廠”建設、開展“廠中校”合作、共建實訓室及科研創(chuàng)新平臺等產教融合項目中,跨界配置和利用實物資產、人力資產、無形資產等已成為一種必要而普遍的行為。這些跨界的資產具有鮮明的“交互性”特征,即校企合作資產在主體形式上的校企“雙元混合”、在功能上經營性與非經營性的“雙向互動”以及在資源利用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方交織”。但由于產教雙方投入來源和管理體制的差異,其在跨界資源的“合作產權”界定及管理上會產生分歧或沖突,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糾纏不清,造成合作項目利益交換不平衡。高職院校在合作產權界定、產權重組實施及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一)產權主體不明確,產權歸屬界定難
市場交易的實質是產權交易,明確產權主體歸屬是實現合作產權運營的前提條件,保護產權以及共享合作剩余分配才能發(fā)揮對產權主體的激勵作用。但是,當前高職院校與企業(yè)合作成立產教融合實體的審批手續(xù)繁瑣并受到多部門政策制度的掣肘,這些外部干擾使得產教雙方的產權安排出現“兩廂情愿而第三方不同意”的情況。資產產權的界定是產教融合中首當其沖的瓶頸問題,教育部門固然出臺了鼓勵性文件,但因缺乏具體操作細則,學校的對外產權合作項目在報批時常常難以被主管部門或財政部門通過。產教融合項目必然存在不同所有制屬性和不同主體產權的融合,這就要求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但由于高職院校及其主管部門十分在意國有資產是否會因此而流失,同時又因無現成的政策性規(guī)定可供依據參照,因而難以有效實施產權歸屬劃分及收益分配比例劃分。以常見的產業(yè)學院模式為例,校方依托共建的實訓基地、研發(fā)中心、培訓中心等平臺,在開展人才培養(yǎng)、應用技術開發(fā)、“1+X”證書考證和社會服務過程中,雙方的場地設施、實習及科研設備、專業(yè)人才、無形資產以及其它技術資源的投入無法進行產權的明確界定[2]。
(二)產權結構不合理,產權價值確定難
高職院校產教融合呈現出校方社會效益與企方經濟效益交織并試圖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一體化的特征,與此同時,高職院校產權的所有權“二元結構”以及管理權、使用權牢固附屬于所有權的特性也非常明顯,妨礙了合作產權以及高職院校自由產權的經營賦能和增值。公辦高職院校因為自身原因不是獨立的產權主體,而其作為產權授權管理委托人通常也得不到充分授權,因此其向其他組織讓渡或分享部分權能的行為必須得到上級行政部門的明確單次授權,且學校作為產權代理人在當前政策環(huán)境下的產權權能讓渡及合作剩余分配行為與“利益輸送”之間的界限不夠清晰,在客觀上都會抑制學校的產權授權管理意愿。當前高職院校產教融合項目大部分是“學校提供場地、教學設施設備及教師,企業(yè)投入資金、生產設備、技術人員”的模式,存在校方直接投入資金少而場地估值大、企業(yè)方資金投入大因而回報期望高的矛盾。但如何權威、公平、公正地確定雙方投入在項目運營中的價值,當前尚無明確的政策規(guī)定和計算模型,也缺乏相應的專業(yè)性和權威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難以對其進行科學的價值評估及產權價值的合理分割[3]。由于對教育組織和社會經濟組織的區(qū)分度把握不準,以及評估法律制度依據不足的緣故,評估機構在國有資產增值保值屬性和企業(yè)資產盈利屬性之間的沖突面前無所適從。
(三)產權流轉不順暢,產權讓渡實施難
就公辦高職院校而言,產教融合必須通過合作產權授權、讓權、用權和享權進行重組,形成“國家擁有所有權、校企共享使用權或管理權”的三元產權結構。當前公辦高職院校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歸屬過于單一,伴隨而來的是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自然歸屬于“國家”這個權力主體,因此國家的約束作用明顯超過社會理想水平,合作產權流轉缺乏通暢的渠道和路徑支持。從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校長”固然可以作為國有產權的代理人,但事實上“校長”受到多個上級部門的約束而不能充分使用權力,客觀上就形成了合作產權雙向讓渡實施進退兩難的處境。高職院校在“使用權”讓渡方面,由于缺乏成熟的制度性經驗和專業(yè)性人才,在面臨“占有權”和“收益權”一同捆綁讓渡的復雜情況下,以及涉及內部的不同部門、各類“委員會”等決策或執(zhí)行、監(jiān)管機構等權限交叉的局面下,其合作產權讓渡實施和監(jiān)管的難度就會進一步加大。對于企業(yè)而言,其設備、資產投入的產權讓渡沒有明確的規(guī)范性法規(guī)可循,所以多半只能以“捐贈”方式投入到學校,而“捐贈”行為發(fā)生之后這些資產便在法律層面上與企業(yè)進行了切割,因而企業(yè)的產權得不到明確界定和有效保護。
(四)產權內容不明晰,各 方目標統(tǒng)一難
高職院校基于權力制衡的需要而形成的事實上的組織結構臃腫,使得產教融合項目的實施及管理機制重組較為艱難;而因對合作產權的界定不夠明晰,也導致產教雙方產權行使的目標難以統(tǒng)一,產權使用運行的成本較高。高職院校過分強調直接的人才培養(yǎng)效益和資產安全,企業(yè)更多關注短期內營利目標,教育部門和財政部門則單一聚焦經濟活動的審計及保值增值等經濟性指標考核,各方目標的差異性增大了產權內容協調一致的難度。事實上,產教融合對校方來說,其收益主要體現在專業(yè)建設、人才培養(yǎng)、辦學品牌等非經濟性增值及增益方面;對企業(yè)方來說,除了經濟收益外還有技術研發(fā)、人力資源獲取以及潛在客戶、品牌口碑等“軟性”效益的獲得;而對校方的主管部門來說,更多的是國有資產的使用效率提升及長期增值。但是,這三方的產權真實收益并不能通過財務報表的數據來衡量。由于三方之間互補性目標需求的匹配性不佳,產教融合項目的激勵性大打折扣,其以產權激勵為內核的自組織性價值發(fā)揮不夠,創(chuàng)造經濟效益和“軟性”價值的能力也隨之下降,使得整個社會的投資增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較為困難。
二、推進高職院校產教融合產權重組的政策需求
產教融合是建立在產業(yè)主體與教育主體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命運共同體”模式,兼具市場性、教育性雙重特征,在雙方的協同育人、協作科研、攜手發(fā)展過程中,伴隨著雙方各自產權的分解、讓渡及使用,也就是產權的重組。作為產業(yè)主體,企業(yè)在產教融合項目中對投資權屬及成本補償有著必然的要求;作為教育主體,高職院校在產教融合項目中基于資產安全、治理結構現代化以及合作發(fā)展效能的考慮,對合作產權的重組和利用有著強烈的愿望。在產教融合發(fā)展方向不可逆轉和產業(yè)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的大趨勢下,必須從政策層面推動產教融合辦學中多方投入、多元主體的合作產權權能歸屬結構組合及其運行模式的規(guī)范與落實。推進高職院校產教融合產權重組,需要破除現有制度、政策與法律層面的障礙,尤其需要在推進合作產權分離、讓渡、重組實施及管理等方面進行大膽的政策創(chuàng)新。
(一)定位合作產權政策變革的目標指向
權、責、利的高度統(tǒng)一是現代產權制度的宗旨,而明確的產權主體和收益歸屬則是其可靠運行的基礎,因此,明確產權關系才能激發(fā)各主體的投資及生產經營積極性,并促進社會財富積累及其合理分配。首先,要將利益相關者納入其中作為產權政策設計的積極參與者,以協調政府、學校、企業(yè)、行業(yè)等各方主體利益,使合作產權的政府監(jiān)管、學校管理使用、企業(yè)投資回報等權益達到協調統(tǒng)一。其次,要厘清合作產權的歸屬類型。可以依據合作產權形成及其特征,分類設置單一產權、共享產權等不同歸屬方式,采取依合作貢獻分配或事前協議分配等產權分配方式。對于以科技開發(fā)為重點合作內容的產教融合項目,通常以共享產權模式較為合適,并采取以合作貢獻分配產權的方式;對于以人才培養(yǎng)為重點合作內容的產教融合項目,可以采取單一產權模式并實施協議約定產權分配。最后,要規(guī)范“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各自的管轄空間。發(fā)揮政府政策引領和主導的權威性,明晰產教融合負面清單,保障各方權益和國家利益得到尊重和維護;要發(fā)揮企業(yè)和學校自主管理能動性,賦予企業(yè)人才培養(yǎng)權及用工權、學生“自由勞動者”權、學校合作辦學權和各方投入產出回報權[4]。
(二)增大高職院校國有資產管理授權
基于理性選擇,合作產權的良性運營必須建立在產權保護和產權重組基礎之上,因此,政府要授權高職院校對其國有資產進行更加寬泛的自我管理。要建立基于比例分成的辦學收益分成機制,通過多元投資主體辦學形成“所有權”多元化格局,實現其“所有權”自身權能的重組,并通過內部競爭促進發(fā)展?jié)摿Φ陌l(fā)掘,逐漸構建對接市場的辦學模式。要進一步確立公辦高職院校產權代理人的授權范圍,明確賦予其對社會實施合作辦學的必要權力,提高其與企業(yè)等利益相關者的談判能力。在此基礎上,要落實高職院校充分辦學自主權,允許其依法依規(guī)將部分權能讓渡給其它社會組織,同時接納企業(yè)等社會組織的部分權能進入學校。對于一般性的校企合作實體項目,可以授予學校對外投資方面的完全自主權,由學校按照規(guī)定程序決策后向主管部門報備。同時,還要簡化較大金額、較大影響的合作項目向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的報批程序。要改革高職院校的國有資產績效評價方式,授權學校依規(guī)決策實施國有土地使用權、房屋場地租賃、資金、軟硬件等國有資產的對外使用,建立“軟性辦學貢獻+剛性經濟效益”的保值增值評價體系,對“軟性辦學貢獻”按照一定的對價或測算標準予以認可。
(三)實施合作產權全面保護
破除合作產權重組的制度性障礙,需要政府部門健全合作產權的保護制度,明確合作產權保護的原則、內容及合作剩余分配的規(guī)定或指導性意見,將產權激勵的內核融入校企合作機制,明晰其產權歸屬,推動校企雙方通過授權、讓權、用權、享權重組產權,并以此為基礎,培育出具有自組織性的產教融合發(fā)展機制。因此,需要建立以利益均衡為基本原則的合作產權保護制度,實施對產教雙方或多方利益的全面保護,實現社會凈效益最大化;鼓勵合作雙方實施基于成本效益的利益分配,降低產權交易成本,騰出產教融合無效費用用于產教融合項目內涵建設的提質增效。在產權重組實施性規(guī)范標準的供給上,要明確學校的固定資產、科研技術、資金等要素在產教融合項目中的產權計算標準及產權比例劃分依據,明確企業(yè)的硬件設施、專利技術、資金投入的計算方式及確權比例,以及對校企雙方和其他自然人的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本投入的利益分配等,并出臺明確的核算、評估和分配產權的規(guī)定。在智力型成果為主的無形資產產權確認方面,要建立系統(tǒng)化的產權價值評估制度、產權分配規(guī)范和產權使用規(guī)程,引導產教雙方依法依規(guī)保護各自權益;明確界定企業(yè)行業(yè)投入資本的產權,保護其投資收益權,允許其從產教融合項目結余中提取合理利潤。[5]此外,還應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對于失敗的產教融合項目,其清算后剩余財產的所有權、收益權、轉讓權及其分割,要明確規(guī)定依照相關財政稅收制度及經濟法律法規(guī)辦理。
(四)引導規(guī)范合作產權交易
在宏觀政策供給上,政府應完善公開、公平、公正、規(guī)范的產權交易機制,建立健全交易規(guī)則和運作制度,促進各類產權合法化交易以及資產的自由流動與重組。要保障投資主體產權的轉讓權,保護投資者收益權,促成產權標的物在各社會主體間的轉移流動。在合作產權管理方面,可以允許投資人在不損害學校資產完整性和保值增值目標的前提下,自由開展合作產權轉讓。應出臺產教融合財政補貼以及稅收優(yōu)惠實施細則,建立產教融合補償基金,實施稅費減免,對示范性產教融合項目實施獎補以充抵合作中的經濟效益,鼓勵合作產權創(chuàng)新轉化,優(yōu)化合作產權交易環(huán)境,挖掘產教融合發(fā)展紅利。
三、創(chuàng)新高職院校產權重組機制,促進產教互利雙贏的策略選擇
合作產權重組是凝聚產教共同體的過程,創(chuàng)新構建合作產權分配及管理制度體系,促進高職院校厘清合作產權歸屬、實施權益保護、完善治理體系,可以推動高職院校向資產“賦能”、資源“整合”轉型以及高質量合作發(fā)展。
(一)理性選擇合作主體
談判理論認為,合作主體須依靠談判來篩查合作的可能障礙并判斷產權安排能否消除障礙,同時就合作風險進行事前研判,分析合作剩余實現方式并預判能否達成分享合作剩余的一致協議,這樣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關系。高職院校對于產教融合項目的合作企業(yè)選擇,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和自由談判并選擇最佳合作者的能力。因此,高職院校要對合作企業(yè)的資源稟賦情況進行全面考察并將其作為理性選擇的重要依據,在不能確認對方資源稟賦特征時要慎重選擇將其納入長期合作者,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合作風險。當然,理性選擇合作項目及合作者的最終目的指向無疑是合作剩余的分享,高職院校應該克服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對廣泛的潛在合作者開展基于成本支出與收益回報的權衡比較,以最大限度保證合作能達成趨利避害的目標。只有建立在合作內容對于雙方都是稀缺性資源需求的基礎上,合作才能長久和互惠。因此,在原則上高職院校應該選擇中高端企業(yè)進行合作,一方面可以共享企業(yè)的核心技術及其技術研發(fā)團隊、先進裝備、生產項目等資源,另一方面可以使學校生產的人力資源實現相對更大的市場價值,并促成“合作剩余”的共享和雙方期許的一致[6]。為此,堅持對等匹配進行合作主體的理性選擇,是確保合作產權的分配與保護、產權鏈形成以及產權激勵作用發(fā)揮的前提和基礎。
(二)健全產權讓渡流轉制度標準
產教融合是一種圍繞共同需求開展的合作發(fā)展行為,從產權安排的角度看,必然涉及使用權、管理權或所有權共享并進而實現互惠共贏。合作產權是由合作雙方以權能分解與重組的方式形成新的產權結構及運行的結果。授權、讓權、用權、享權既是高職院校合作產權重組及運行的循序過程,同時也是產權讓渡流轉制度標準的形成要素和組織結構。在政府充分授予校企雙方產權讓渡流轉權利后,雙方各自按照“權責對等”原則將自身部分使用權、管理權讓渡給對方或與之共享,而校企“用權”則是雙方按照“效率優(yōu)先”原則整合資源并實現合作剩余最大化目標的過程。“享權”是在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基礎上,由雙方按照投資比、貢獻度或事前協議對合作剩余進行合理分割的行為。在第三方產權評估基礎上,高職院校要探索基于“三權分置”的校本化合作產權管理體系,形成實物資產、人力資產、無形資產等方面包括校企合作產權重組標準、資產確權規(guī)范、會計核算及資產管理等在內的制度體系,涉及確權標準、讓渡流轉制度、組合配置標準以及核算管理標準、資產評估管理制度等。
(三)構建多元產權結構形態(tài)
產權結構是由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讓渡權等形成的產權權利結構,高職院校合作產權涉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教育資本與產業(yè)資本的組合,必須首先明晰多元主體中各方在投資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方面的確權。在產權重組過程中,政府需要給公辦高職院校和國有企業(yè)授權,允許其將一部分權能讓渡給對方,以建設基于利益的“共同體”。當然,非國有企業(yè)無需政府授權就可以直接決定是否讓渡或接受校方產權。此后,雙方要按照“權、責、利對等”原則實施所有權配置,達成合作剩余分享的基本方案,在雙向互動的產權讓渡重組之后,開始使用權或管理權的共享。一般使用權共享是合作發(fā)展的開端,并在此基礎上開放管理權的共享,但現實中也存在因為使用權、管理權不便分離而同時讓渡或共享這兩種權能的情形。產權重組后的公辦高職院校,就會形成所有權歸國家、學校與企業(yè)分享使用權或管理權的“三元”產權結構。在產教融合項目的管理上,要實施股份制與董事會制,建立收益共享、責任共擔的制度,同時允許實施自由投入、轉讓、流通、退出機制。可以考慮將合作產權的一部分作價入股并進行產權交易,在學校既有資產得到充分保護的前提下,實現產教雙方增量投入的資本化,進而奠定校企利益分享的制度基礎。高職院校還可以在場地、設施和人力資源“使用權”的權利讓渡方面進行擴充,包括將“閑置”資產、“功能冗余”資產以及因與辦學核心功能關系較遠而“沉寂”的資產進行“使用權”權利讓渡,使讓渡的“使用權”權能發(fā)揮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并為學校增加收入的雙重作用,促進國有資產在經營中獲得增值。
(四)建立辦學成本分攤及運營收益分配機制
高職院校要建立以產權秩序重構為先導的成本分擔機制,通過產教雙方抵消部分成本以及按比例分配收益,解決產教融合項目成本、收益、資產安全等爭議。對高職院校而言,產教融合項目的最終目標落實在專業(yè)建設、人才培養(yǎng)和科技開發(fā)上,必然涉及學校相關教學及管理活動,因此對相關成本不宜采取直接法人獨立核算方式,而應將其從辦學主體成本中“抽取”出來,抵消核算后再將相關成本資金計入學校或者企業(yè)法人賬戶[7]。如對于水、電、氣消耗以及人員費用等產教融合項目日常運行費用,可當成共有成本。對于使用企業(yè)設備成本(包括租用費、折舊費、維保費用等)、原材料消耗成本,以及企業(yè)提供的教學培訓人力成本、知識產權的使用成本等,應與企業(yè)使用學校方相關資源的成本進行抵消后進入企業(yè)方或學校方賬務處理。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可對校企合作利益按總收入直接分配或者按總利潤協商分配,以推動合作產權跨界流動并重組。在產教融合項目運營收益的分配實施上,可以考慮將產品生產收益、技術服務收益、人員培訓收益等在支付共有成本之后,其剩余部分按投入比例支付給雙方自有賬戶。一般應以年度為單位,在完成各自成本核算并沖抵之后,實施單向支付以轉移支付非共有成本。
(五)完善高職院校產權監(jiān)管體系
合作產權是高職院校一種特殊產權,產權重組要得到科學利用和安全運行,必須建立有序的監(jiān)管體系。因此,要依照政策法律法規(guī),對照新的權利組合特點實施產權的全面監(jiān)管,據實進行會計核算,科學進行資產管理,強化資產績效考核,確保資產不流失、不損毀;要加強對知識資產的法律認定和依規(guī)評估。在資產歸屬及產權風險防范方面,要對產教融合項目的共有資產、獨有資產及后期資產處置、合作成果的歸屬等進行明確的協議規(guī)定。適應“管辦評”分離的大勢所趨,高職院校可以委托第三方機構監(jiān)督管理產權重組及運行,以增強監(jiān)管的專業(yè)性和公平性。
參考文獻:
[1]王為民.合作產權保護與重組:職業(yè)教育校企合作機制創(chuàng)新[J].教育研究,2020(8):112-120.
[2]張震,劉繼廣,張雪彥.混合所有制職業(yè)院校體制創(chuàng)新、實現路徑與治理結構研究——產權經濟學視角的分析[J]. 中國職業(yè)技術教育,2020(20):57-64.
[3]郭欣.企業(yè)參與職業(yè)教育校企合作的成本構成及補償機制構建[J].中小企業(yè)管理與科技,2020(12):114-115.
[4]公丕國,付靜.高校產權結構重組的具體路徑研究[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17):42-45.
[5]羌毅.職業(yè)院校二級學院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下的產權配置與費用分成機制研究[J].中國職業(yè)技術教育,2020(19):54-59.
[6]王文杰.高職校企合作共建生產性實訓基地的探索[J].長江叢刊,2020(10):73-74
[7]謝軍.高職院校產教深度融合的路徑研究[J].新校園(上旬刊),2017(11):62-64.
[責任編輯? ? 曹? ?穩(wěn)]
Abstract: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s to break the situation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cooperative property rights. At present, cooperative property rights reorganization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difficulty in defining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rights,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property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s and unifying the goals of all parties. It is necessary to locate the goal of the reform of cooperative property rights policy, increase the authorization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oopera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transaction of cooperative property righ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choose the cooperative subject rationally, perfect the system standard of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 construct the multi-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s, set up the mechanism of cost sharing and opera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erfect the internal property rights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perty rights reorganization; policy demand; mechanism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