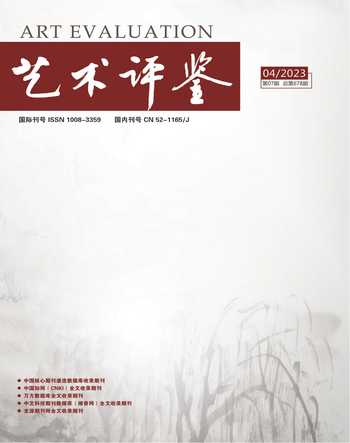影游融合對(duì)電影本體化敘事的雙重解構(gòu)與重塑
張君如
摘要:影游融合的年代正處于科學(xué)技術(shù)迅猛發(fā)展的20—21世紀(jì)之交,此時(shí)期的電影工業(yè)制作達(dá)到了一個(gè)高峰,媒介自身的發(fā)展駛?cè)肓寺侔l(fā)展階段,媒介之間正進(jìn)入全面融合并相互磨合的時(shí)期。而在兩者交融發(fā)展的工業(yè)進(jìn)程下,電影的本體化建構(gòu)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塑。本文針對(duì)電影敘事技術(shù)及主體觀影審美兩個(gè)層面的變革展開簡(jiǎn)要論述,并引入“虛擬美學(xué)觀”“無意識(shí)入片狀態(tài)”等概念,對(duì)于媒介交互下的新型電影敘事模式如何被重塑進(jìn)行了更為深入的理解,由此觀照電影內(nèi)在本體化的表達(dá)方式。
關(guān)鍵詞:影游融合 ?電影本體化 ?跨媒介交互敘事
中圖分類號(hào):J90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8-3359(2023)07-0168-05
縱觀整個(gè)影游融合的發(fā)展進(jìn)程,其實(shí)就是代表大眾文化的電影和代表亞文化的游戲之間相互平衡的過程。1993年,全球電子游戲收入首次超過電影行業(yè)收入。產(chǎn)業(yè)融合不成熟的早期,電影在洞察到游戲如此利好的市場(chǎng)形勢(shì)之下,便依靠模仿改編和大篇幅引用游戲內(nèi)容元素使電影在價(jià)值觀上盡可能地與游戲貼近,借助融合文化價(jià)值層面的差異消除文化偏見。隨著產(chǎn)業(yè)的深入融合,品牌IP效應(yīng)的不斷增強(qiáng),觀影者不再因?yàn)閮r(jià)值層面的相似而被媒介吸引,而是自主地參與到影游融合體系的開發(fā)之中。市場(chǎng)的傾向被開發(fā)商及時(shí)捕捉,他們注意到了觀影者更多的主體需求,于是電影和游戲在造型設(shè)計(jì)、場(chǎng)景設(shè)置、角色命運(yùn)走向和氛圍渲染上開始走向受眾主導(dǎo)的時(shí)代,這就使第一人稱視角電影以及后來出現(xiàn)的互動(dòng)電影應(yīng)運(yùn)而生。總的來說,受眾在觀影中獲得了更好的情感體驗(yàn)、更多的自我認(rèn)可和更深的投入度,而在新的媒介融合場(chǎng)景被不斷構(gòu)建時(shí),電影的本體化屬性必然遭到了解構(gòu)和重塑。傳統(tǒng)經(jīng)典時(shí)期電影再現(xiàn)真實(shí)的能力隨著觀影心理的變遷和虛擬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而退居二線,讓位于文化和資本的密切協(xié)同。
一、影游融合對(duì)于本體化敘事的革命性震蕩
在漫長(zhǎng)的經(jīng)典電影時(shí)期,觀眾一直是被動(dòng)的凝視者,無法干預(yù)敘事,更無法參與敘事。而敘事模式也一直沿用經(jīng)典的用影像說話、用故事吸引受眾的方式。隨著時(shí)代的進(jìn)步,這個(gè)方式不免顯得有些老套,熟悉電影的受眾顯然開始感到傳統(tǒng)劇情片的乏味。從技術(shù)到理論、從電影符號(hào)輸出端到接收端、從開始解讀符號(hào)到最終審美境界的調(diào)動(dòng),影游融合工業(yè)徹底顛覆了電影敘事語言表達(dá),甚至形成了新的電影敘事理論體系。其中,電影的本體化敘事正是受到影響而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的一個(gè)分支。
(一)被豐富的語言敘述手段
1.可選擇的分支敘事走向
影游融合的數(shù)字技術(shù)豐富了影像本位的“語言敘述”功能,這里的豐富是指放大了電影時(shí)空的特性,創(chuàng)作了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和敘事可能。游戲較經(jīng)典電影有著更為復(fù)雜的敘事線索,影游融合電影不再通過強(qiáng)化故事架構(gòu)使觀眾信服,而是采取更加復(fù)雜的敘事線構(gòu)制整個(gè)影片劇情。游戲研究專家愛斯潘·阿爾薩斯提出,線性文本是“劇本化的架構(gòu)”,而游戲中這類非線性的文本是一種“賽博文本”,其深受機(jī)器思維的影響。所謂“賽博文本”,具體就表現(xiàn)為分支敘事模式。比如最典型的互動(dòng)影片之中,每種選擇都對(duì)應(yīng)一個(gè)分支,形成一種樹枝狀或者網(wǎng)狀的情節(jié)走向。這種敘事形態(tài)可以根據(jù)觀眾自己的選擇而讓觀眾相信:真實(shí)即“我親身操控”,真實(shí)影像即“我自主參與生成的影像”。當(dāng)選擇完選項(xiàng),梳理好目前的劇情,就會(huì)出現(xiàn)下一個(gè)選擇,這種直到影片結(jié)束才能夠使觀眾稍稍放松的新型敘事形態(tài)也恰好迎合了電影本體指涉的多義性與曖昧性。放在這里,也指一種隨時(shí)的可被改變性。在影游融合觀念深入電影工業(yè)制作之后,一個(gè)好的故事就不再是一方的獨(dú)角戲了,缺乏受眾參與的劇本只能算是情節(jié)跌宕的一出戲而已,電影媒體的敘事必須借助觀眾的參與才能產(chǎn)生意義。這一點(diǎn)相當(dāng)于接受美學(xué)在電影行業(yè)中的應(yīng)用,電影媒體的敘事必須借助觀眾的參與才能產(chǎn)生意義,電影最后的生命力也是在與觀眾的深入交互中實(shí)現(xiàn)的。
2.多次強(qiáng)化的敘事符號(hào)
從另一個(gè)角度來談電影敘事語言的豐富,影游融合電影還能夠提升觀眾對(duì)于劇情的參與次數(shù)。傳統(tǒng)電影雖然能為觀眾提供豪華的視覺奇觀享受,當(dāng)觀眾走出電影院后,隨著時(shí)間的推進(jìn)和下一部視效大片的出現(xiàn),它的生命力可以說是薄弱的,因?yàn)樗倳?huì)被取代。它缺少了影游融合類電影能夠?yàn)橛^眾帶來的一種重要心理感受,即缺憾感,而這種缺憾感就賦予了電影獨(dú)一無二的特性。因?yàn)橛^眾代入了自身各感官,因此電影已不再是單純的一部電影,而是由自身參與選擇過但是可能沒有達(dá)到最好效果或結(jié)局的一個(gè)互動(dòng)作品。大多數(shù)影游類作品,尤其是互動(dòng)電影的觀眾會(huì)選擇二刷、三刷,其目的就在于體驗(yàn)不同的劇情,就如同每次回到最初從頭再來,觀眾總會(huì)抱有全新的、試圖要和前幾次不一樣的心態(tài),感受不同選擇所帶來的不同觀影體驗(yàn),一方面直接增加了電影票房,另一方面因?yàn)槎啻芜x擇,必然會(huì)重復(fù)接受電影符號(hào)。那么從這個(gè)角度看,電影的敘事作用也會(huì)被強(qiáng)化,并因?yàn)橛跋駭⑹路?hào)的多次出現(xiàn),給觀眾以事實(shí)感,從而又加強(qiáng)了電影語言的本體自我指涉能力。
3.開放式的塊狀敘事走向
此外,影游融合帶來的最大的電影語言變化還是轉(zhuǎn)向游戲化的敘事結(jié)構(gòu)。《羅拉快跑》影片中采用了塊狀的敘事方法,描繪了在三種不同情況下主人公為男友籌集資金的不同結(jié)局。這就與游戲的操作模式大同小異,之后的《恐怖游輪》《明日邊緣》《前目的地》《忌日快樂》等帶有游戲化色彩的影片都滲透著玩家經(jīng)驗(yàn),在輪回多段式的故事溯洄中建構(gòu)著全新的敘事邏輯和結(jié)構(gòu),并不斷深化了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某種社會(huì)運(yùn)作法則的暗示,從而達(dá)到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反思,強(qiáng)化了電影的本體性。影片展現(xiàn)了平行時(shí)空下的多種事件的展開方式和結(jié)局,這樣的電影較之以往傳統(tǒng)電影的封閉式敘事和結(jié)局而言是非常人性化的,它給觀眾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塊狀敘事下的每一塊故事走向都不分先后,沒有對(duì)錯(cuò)之分,觀眾完全可以選擇自己所相信的那一支。由于結(jié)局變得開放,電影的本體化也正是通過此種多義的、人性化的敘事方式而被受眾的心理所認(rèn)同和接納。
4.電腦成像特技下的自由化敘事
影游融合工業(yè)化發(fā)展中最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時(shí)還有特效技術(shù)。2019年李安導(dǎo)演的《雙子殺手》上映,除了沿用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chǎng)戰(zhàn)事》里3D+4K+120幀的幀率配置外,影片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電腦成像數(shù)字真人技術(shù)的應(yīng)用。電腦成像技術(shù)被廣泛運(yùn)用于電影、電視、視頻游戲、互動(dòng)多媒體等領(lǐng)域,能夠創(chuàng)造視覺上的奇觀特性。1994年上映的《阿甘正傳》中阿甘和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等總統(tǒng)會(huì)面的場(chǎng)景可以稱為電影史中最令人難忘的場(chǎng)景。電腦成像技術(shù)讓已經(jīng)離開人世的人物重新活靈活現(xiàn)地出現(xiàn)在銀幕之中,再現(xiàn)了未用歷史鏡頭記錄下的真實(shí)歷史,這是電影發(fā)展史上一個(gè)里程碑的鏡頭畫面,它讓歷史在技術(shù)外衣的作用下得以復(fù)現(xiàn)。
除了人物電腦成像,這一特效還能夠使場(chǎng)面更加炸裂,達(dá)到更為逼真的呈現(xiàn)效果,它成了推動(dòng)劇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黑客帝國(guó)》中的“子彈時(shí)間”名場(chǎng)面,它可以說完全違背了傳統(tǒng)力學(xué)定律,但是對(duì)于夸張的電影表現(xiàn)手法而言,這一技術(shù)是必需也是極為精妙的,它拓寬了電影的時(shí)空表現(xiàn)力,將電影某一維度的時(shí)空特性進(jìn)行了放大,進(jìn)入了一個(gè)高度自由的時(shí)空王國(guó),大大增強(qiáng)了電影的敘事張力。游俠型科幻片、魔幻型科幻片以及災(zāi)難型科幻片中運(yùn)用電腦成像制作技術(shù)的鏡頭甚至比真人扮演的部分更加精彩,因?yàn)槠渲斜宦俜糯蟮奶貙憽⒑[席卷時(shí)蜂擁的人群以及合成影像惟妙惟肖的神情動(dòng)作,都讓完全虛構(gòu)的內(nèi)容充滿了人性化的色彩和極為逼真的畫面表達(dá)。于此,電影本體化的自我指涉就達(dá)到了最高的境界,即讓無法再現(xiàn)的真實(shí)躍然于鏡頭,讓真實(shí)中的細(xì)節(jié)被無限放大和延長(zhǎng),給觀眾帶來了足夠的欣賞及體驗(yàn)空間。
(二)被解構(gòu)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
當(dāng)提到關(guān)于電影藝術(shù)如何貼近現(xiàn)實(shí),如何尋求更為真實(shí)的表達(dá)時(shí),有人總會(huì)自詡站在巴贊的肩膀上高呼:反對(duì)蒙太奇而追求真實(shí)。然而這一命題的邏輯本身就有待考究。西方詞源中的“真實(shí)”與“現(xiàn)實(shí)”是兩種概念的詞,從詞義上來區(qū)別,“真實(shí)”是形容詞,而“現(xiàn)實(shí)”是名詞。這意味著從某種角度上說,“真實(shí)”代表著現(xiàn)實(shí)表達(dá)的某一方面,而電影藝術(shù)作為一門再現(xiàn)藝術(shù),本身就無法用真實(shí)來形容。巴贊指出“電影是現(xiàn)實(shí)的漸近線”,其在原文中用到的正是“現(xiàn)實(shí)”一詞,而非“真實(shí)”。大家都知道現(xiàn)實(shí)是曖昧的、多義的,而真實(shí)是具體的、具象的,電影的魅力也正在于不完全真實(shí)性。簡(jiǎn)單來說,電影媒介一旦借助某個(gè)鏡頭去觀察世界,就無法達(dá)到100%的真實(shí)了,它總會(huì)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就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來說,其特點(diǎn)在于鏡頭保持了一種冷靜旁觀者的態(tài)度,這種旁觀與現(xiàn)實(shí)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而現(xiàn)實(shí)又具有多義性,這里的多義性正是相對(duì)于真實(shí)而言的,因此就更加佐證了電影只能無限靠近于真實(shí),而無法達(dá)到真實(shí)本身。指出這一命題“追求真實(shí)”的邏輯錯(cuò)誤后,再來談“反對(duì)蒙太奇”的問題所在。的確,巴贊的理論通常被視為蒙太奇的反義詞。但是巴贊本人從未提出過要完全摒棄蒙太奇的存在,因?yàn)槊商娴撵`感原型就是來源于現(xiàn)實(shí)本身,他反對(duì)的是一種極端化的蒙太奇,即以一種自負(fù)的剪輯手法剝奪觀眾的自我思考能力,而以一種強(qiáng)行的教學(xué)式拼貼告訴觀眾所要表達(dá)的觀念。蒙太奇一旦落入這種誤區(qū),越想通過電影的手法讓觀眾理解就越會(huì)使觀眾體會(huì)到一種不被信任的挫敗感,觀影的樂趣就會(huì)大打折扣,并讓觀眾對(duì)整個(gè)電影語言的體會(huì)起到負(fù)面作用。對(duì)于電影而言,即使是最接近事實(shí)的紀(jì)錄片,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簡(jiǎn)單的剪輯手法,更是很難界定每一部電影中蒙太奇色彩的強(qiáng)烈程度。那么蒙太奇手法演變到今天,則應(yīng)被允許在不破格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應(yīng)用,因而,最優(yōu)秀的剪輯是不被觀眾洞察卻依然能起到重要意指或敘事作用。
1.更接近真實(shí)本身的虛擬美學(xué)觀
蒙太奇和長(zhǎng)鏡頭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二元對(duì)立的,長(zhǎng)鏡頭派所代表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與蒙太奇派代表的“虛擬美學(xué)”也不是完全互斥的。數(shù)字技術(shù)顯然已經(jīng)撬動(dòng)了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電影美學(xué)觀念——一種基于現(xiàn)實(shí)且最后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美學(xué)觀。這種美學(xué)觀歸根于傳統(tǒng)電影的制作方式,具體表現(xiàn)為:電影真實(shí)與否在于其表達(dá)的內(nèi)容是否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原型。而今天影游融合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大量“仿真技術(shù)”讓人們開始意識(shí)到電影的表達(dá)并不用過度依賴于現(xiàn)實(shí),人們看到的電影畫面不一定需要真真實(shí)實(shí)地存在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反過來說,甚至一些真實(shí)的畫面無法用純紀(jì)實(shí)鏡頭的方式表現(xiàn),一些虛擬的影像卻能夠非常完美地復(fù)原現(xiàn)實(shí)。比如《泰坦尼克號(hào)》中著名的巨輪上擁抱的場(chǎng)景,觀眾很難相信這個(gè)鏡頭是一個(gè)純特效鏡頭,人物拍攝實(shí)際上是在室內(nèi),背景為綠幕,然后拍攝室外的天空,最后通過摳圖將兩者結(jié)合起來就達(dá)到了以假亂真的效果。可以說虛擬現(xiàn)實(shí)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可行范疇,進(jìn)而比真實(shí)更加真實(shí)。影游融合類電影中的虛擬影像也是如此突破了人們?cè)患夹g(shù)限制的視野,把曾經(jīng)只在腦海里出現(xiàn)的畫面,包括看不見摸不著的一些事物都進(jìn)行了技術(shù)的還原。如前文所提及的具有空間導(dǎo)航的長(zhǎng)鏡頭,紀(jì)實(shí)派美學(xué)的鏡頭無法達(dá)到在影像中任意穿梭的效果,但是虛擬美學(xué)經(jīng)過特技的安排與合成卻可以達(dá)到貌似渾然天成的效果,《盜夢(mèng)空間》可以隨意穿梭多個(gè)平行時(shí)空,《頭號(hào)玩家》可以跟隨鏡頭任意的上浮下沉穿越與主人公一探究竟,《黑客帝國(guó)》的“子彈時(shí)間”在特技的幫助下,將某一時(shí)空無限拉長(zhǎng)而使觀眾欣賞到了極具美感的暴力美學(xué)瞬間。
2.影像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呈現(xiàn)的演進(jìn)
當(dāng)畫面進(jìn)行有調(diào)度跟拍時(shí),需要保證拍攝區(qū)域明顯的顏色對(duì)比,這需要保證跟拍的精確度,比如飛碟慢速入場(chǎng)或出鏡的場(chǎng)景和火焰熊熊燃燒的場(chǎng)景,這樣方能保證后期制作時(shí)鏡頭追蹤的物體特征。這樣匠心獨(dú)運(yùn)的“長(zhǎng)鏡頭”功能再現(xiàn)了觀眾曾經(jīng)只能想象的片段領(lǐng)域,影游融合的制作理念滲透在電影的每一步制作中,現(xiàn)實(shí)存在與影像的關(guān)系再也不是傳統(tǒng)電影那種“存在——表現(xiàn)”的關(guān)系,而是“想象——呈現(xiàn)”的關(guān)系。試想,當(dāng)大家將真實(shí)的界定局限于現(xiàn)實(shí)存在的表現(xiàn)基礎(chǔ)之上,那么影像能夠呈現(xiàn)出的真實(shí)的范圍也會(huì)是被局限的;而當(dāng)大家將真實(shí)的界定囊括了虛擬世界的呈現(xiàn)部分,那么影像的未來前景就可以說是無限的。在影像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呈現(xiàn)的變化這一點(diǎn)上,虛擬美學(xué)正侵占著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穩(wěn)固地位,它代表了在影像真實(shí)性理論界定上范圍的擴(kuò)大,從而也瓦解著電影本體性自我指涉的傳統(tǒng)步驟。
3.快消費(fèi)時(shí)代下的虛擬美學(xué)效應(yīng)
陳旭光在研究中指出:“一種強(qiáng)化影視藝術(shù)假定性的美學(xué)特征,正強(qiáng)勁地顛覆原先藝術(shù)所恪守的所謂‘真實(shí)性’原則的假定性美學(xué)原則”。當(dāng)人類社會(huì)進(jìn)入后現(xiàn)代時(shí)期,人們的審美偏好發(fā)生了相應(yīng)的轉(zhuǎn)變,20世紀(jì)50—60年代來自新現(xiàn)實(shí)主義派的美學(xué)觀顯然讓觀眾感到了深深的審美負(fù)擔(dān),在快節(jié)奏的時(shí)代腳步下,人們擺脫了物質(zhì)消費(fèi)的困擾逐漸進(jìn)入了精神消費(fèi)時(shí)期。數(shù)字特技在各類影片中展現(xiàn)出的強(qiáng)烈奇觀性、娛樂性以及具有市場(chǎng)利好的高度商業(yè)性使得數(shù)字特技下的虛擬美學(xué)成了電影必不可少甚至占比重最大的部分。虛擬美學(xué)釋放出的強(qiáng)大美學(xué)效應(yīng)正貼合了人們的精神消費(fèi)需求:濃厚的后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后現(xiàn)代主義強(qiáng)調(diào)無中心意識(shí),主張多元價(jià)值取向,虛擬美學(xué)的奇觀化景觀就滿足了這兩點(diǎn)。傳統(tǒng)電影的大主角光環(huán),由故事內(nèi)核主導(dǎo)影像發(fā)展的原則被推翻,人們需要的只是在影片亦真亦幻的影像變化中獲取現(xiàn)實(shí)欲望的滿足感。虛擬美學(xué)在視覺上的強(qiáng)沖突搭配、簡(jiǎn)單明了的故事內(nèi)核,讓觀眾在不用費(fèi)力解讀的基礎(chǔ)上,同等地接收到了大量的影像信息,只不過這種信息符號(hào)來自更簡(jiǎn)單暴力的視覺沖擊。如此說來,這樣的虛擬美學(xué)是消費(fèi)時(shí)代受眾的最佳選擇。它用痛快淋漓的暴力美學(xué)緩解著人們的疲憊和壓力。
二、受眾主體審美層面的顛覆性想象敘事
(一)無意識(shí)心理下的沉浸式體驗(yàn)
觀眾在欣賞電影時(shí)保持的是怎樣一種精神狀態(tài)對(duì)于電影敘事語言的傳達(dá)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美學(xué)家蘇珊·朗格認(rèn)為,電影與夢(mèng)境有某種關(guān)系,電影觀賞的過程就與夢(mèng)境有著相同的方式。從形式上來說,觀賞電影的情感體驗(yàn)是一種特殊的“無意識(shí)入片狀態(tài)”,即電影滿足了觀眾潛藏于內(nèi)心深處的無意識(shí)欲望,使觀眾漸漸模糊了現(xiàn)實(shí)與夢(mèng)幻的幻覺,雖然能夠明晰自己不過是在觀看影片,但還是會(huì)像睡著了一樣沉湎于影像之中。
1.“居安思危式”的觀影傾向
影游融合類電影屬于娛樂導(dǎo)向型電影,它誕生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是娛樂產(chǎn)業(yè)工業(yè)化運(yùn)作期間的產(chǎn)物。在這類電影中,占比最大的內(nèi)容就是驚險(xiǎn)動(dòng)作類。即使影片對(duì)于游戲原作的植入更加偏重于游戲角色、場(chǎng)景的移植,而非情節(jié)的套用,電影制片人們也會(huì)盡可能地將故事改編,加入大量能夠呈現(xiàn)出視覺沖擊的情節(jié)畫面。從觀眾的審美心理角度來說,這類電影能夠給觀眾帶來超出平常生活的驚險(xiǎn)刺激感,觀影者們非常想要在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借助電影的“入片體驗(yàn)”親歷緊張突發(fā)的危險(xiǎn)事件。弗洛伊德則指出人的深層潛意識(shí)中包含“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兩大部分,在他看來這個(gè)本能世界充滿了邪惡與黑暗的力量,它屬于人性中的“本我”部分,“本我”雖被隱藏但是極度渴望被釋放出來。那么此時(shí),觀看電影時(shí)的“入片狀態(tài)”就提供了一個(gè)能夠釋放本能無意識(shí)需求的良好載體。而影游類電影中呈現(xiàn)出的大量殺傷、破壞、暴烈、死亡、打斗、血腥、虐待的畫面就使觀眾在本身安全的情況下體驗(yàn)到了無意識(shí)欲望被釋放的極度快感。這種接近零成本卻能體驗(yàn)到“死亡本能沖動(dòng)”的方式無疑加深了觀眾觀看此類影片的投入程度,滿足了觀眾的獵奇欲望。
2.“游戲化電影”下的主觀操控沖動(dòng)
影游融合類電影需要進(jìn)行的第一個(gè)層面的變革就是游戲化電影如何使觀眾像玩游戲般投入沉浸式體驗(yàn)。眾所周知審美心理是作用于審美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這一心理包含著多種情感情緒因素:聯(lián)想、想象、理解、共鳴等。為了達(dá)到沉浸式的審美體驗(yàn),影游融合類作品首先豐富了影片中的劇情任務(wù),使得觀眾產(chǎn)生了一種代入式的主觀操控沖動(dòng)。其次,作品中的視聽語言通過第一人稱視點(diǎn)或者VR鏡頭讓觀眾在視覺上“擬真”,引起了自我身份認(rèn)知的沖動(dòng),進(jìn)而愿意跟隨主觀鏡頭代入式體驗(yàn)劇情。最后,在沉浸式體驗(yàn)過程中,觀眾會(huì)想象、聯(lián)想,這也歸功于影游融合中的人、事、物的擬態(tài)化設(shè)計(jì)。即使是影游融合中虛構(gòu)世界的描繪,也是從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原型演變而來的,觀眾在欣賞的過程中會(huì)自然而然地根據(jù)既有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藝術(shù)素養(yǎng)對(duì)畫面中的語言符號(hào)進(jìn)行解讀,最終達(dá)到與影像同呼吸的“共鳴”感。究其沉浸式的精神狀態(tài),最深層次的其實(shí)是來源于人類的無意識(shí)選擇。從社會(huì)心理學(xué)的角度上來看,影游融合類電影作為商業(yè)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能夠像極端的實(shí)驗(yàn)電影般僅表達(dá)個(gè)人的某種欲望和情緒,它將會(huì)是一種群體化的“集體無意識(shí)”的宣泄。在電影的邊邊角角均迎合了人類群體的某種情緒和狀態(tài),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也潛移默化地接受著這樣若隱若現(xiàn)的符號(hào)的暗示,而落入了無意識(shí)心理的“圈套”,產(chǎn)生了對(duì)電影的沉浸式體驗(yàn)感。
(二)游戲化經(jīng)驗(yàn)的想象力消費(fèi)
自從電視、游戲等新媒介誕生,人們對(duì)于電影的要求越來越高,從最初的被動(dòng)理解電影提供的信息符號(hào),到如今不僅要求以平等的身份介入影片敘事,更是對(duì)電影的內(nèi)容有了更多期待和衡量標(biāo)準(zhǔn)。
1.環(huán)境線的有意弱化
構(gòu)成游戲化界面的有兩個(gè)部分,一部分是以觀眾沉浸代入自身體驗(yàn)的主角部分,另一部分則是具有信息負(fù)載功能的環(huán)境背景。然而,其實(shí)在游戲體驗(yàn)或者觀影過程中,這些作為背景的劇情場(chǎng)景除了起到氛圍渲染和提供信息的作用,貌似沒有起到直接的本體化敘事作用。西莉亞·皮爾斯指出:雖然往往被渲染得很華麗,但是很多玩家發(fā)現(xiàn)劇情場(chǎng)景其實(shí)是對(duì)游戲經(jīng)驗(yàn)的干擾。玩家在游戲時(shí)其實(shí)很少會(huì)刻意地注意到周遭環(huán)境的精美設(shè)計(jì),換句話說,除了對(duì)畫質(zhì)有特定的要求外,玩家是偏重享受闖關(guān)體驗(yàn)而無暇顧及游戲進(jìn)程中的場(chǎng)景和故事設(shè)計(jì)的。在影游類電影的觀賞中,觀眾也因沉浸于主角的情節(jié)走向,而不能過度分心于其他精美絕倫的環(huán)境。只能說環(huán)境的精致設(shè)計(jì)和呈現(xiàn)會(huì)帶給玩家和觀眾賞心悅目的舒適觀感,但是聰明的制片商還是會(huì)有意地弱化環(huán)境背景的過度刻畫,而花費(fèi)更多的心思在如何將過關(guān)斬將的情節(jié)進(jìn)行深入刻畫之上。
2.游戲化視聽語言的還原
如何使得影游融合類電影發(fā)揮最大的媒介功能的移植作用,最直接的辦法即還原游戲中的視聽語言。要想能夠在影游融合類電影作品中充分發(fā)揮游戲媒介的想象力,一方面即游戲場(chǎng)景的還原,比如:游戲改編的電影《魔獸世界》中,游戲中出現(xiàn)過的沙漠、雪山、草原等景觀都被極大程度地進(jìn)行還原。至少對(duì)于游戲玩家這部分的受眾群體來說,觀影體驗(yàn)與游戲體驗(yàn)是十分接近的。因?yàn)閳?chǎng)景的類似,能夠使受眾幻想曾經(jīng)在游戲中經(jīng)歷過的角色歷程,增加受眾對(duì)影片的信任度。數(shù)字科技的發(fā)展也讓電影無論從攝制還是放映層面,都具備了更好的畫質(zhì)。必須承認(rèn)的是,更優(yōu)的界面畫質(zhì)不僅能夠吸引普通電影觀眾,更能夠拉近與游戲玩家的距離。另一方面,電影中也對(duì)聲音進(jìn)行了游戲化還原。由于聲音具有使玩家聯(lián)想到相關(guān)游戲畫面的特殊能力,同時(shí)聲音又能夠很好地烘托環(huán)境氛圍,增加情節(jié)敘事的能力,因此游戲化的聲音還原能夠促進(jìn)觀眾的想象延展力,并使得游戲玩家這部分觀影群體增加觀影的情懷感。
影游融合類電影帶來的審美層面的嬗變,突破了傳統(tǒng)電影敘事的側(cè)重點(diǎn),游戲化經(jīng)驗(yàn)的植入正適配于快節(jié)奏時(shí)代人們的精神消費(fèi),通過觀眾審美層面的調(diào)動(dòng)打破了以往的觀影審美定向思維,也打破了電影工業(yè)制作的內(nèi)在桎梏。未來,影游融合所代表的想象力美學(xué)還將有更加廣闊的市場(chǎng)。
三、結(jié)語
影游融合的年代正處于科學(xué)技術(shù)迅猛發(fā)展的20—21世紀(jì)之交,此時(shí)期的電影工業(yè)制作達(dá)到了一個(gè)高峰,媒介自身的發(fā)展駛?cè)肓寺匐A段,媒介之間正進(jìn)入全面融合并相互磨合的時(shí)期。正是這樣的磨合讓不同的媒介雙方煥發(fā)出了新的生機(jī)。媒介也需要不斷地推陳出新以融入這個(gè)大浪淘沙般的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并通過吸納不同的可適用于自身的媒介特性讓自身成為不會(huì)被取代的那一個(gè)。影游融合就是這樣典型的存在,兩者同樣依靠科學(xué)技術(shù)而運(yùn)作,傳播手段也是依靠視聽語言的獲取與理解。兩種娛樂形態(tài)有著很大一部分的相似之處。影游融合的進(jìn)程一經(jīng)開始,就預(yù)示了一些不可扭轉(zhuǎn)的結(jié)果。
從技術(shù)本身的奇觀化表達(dá)到受眾主體的沉浸式審美體驗(yàn),電影再現(xiàn)事物時(shí)間延續(xù)的功能可以說越來越強(qiáng)大。數(shù)字技術(shù)已然為當(dāng)今的世界開辟了新的天地,媒介交互也是得益于此。但不論未來的媒介融合發(fā)展到哪一步,不論想象力可以達(dá)到多么瘋狂的邊界,人們總要在倫理道德的合理范圍之內(nèi),秉持著最純真的人文關(guān)懷,站在藝術(shù)本體的角度上去回歸現(xiàn)實(shí)、觀照現(xiàn)實(shí)。
參考文獻(xiàn):
[1]陳旭光.從《頭號(hào)玩家》看影游深度融合的電影實(shí)踐及其審美趨勢(shì)[J].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2018(07):101.
[2]楊揚(yáng),孫可佳.影游融合與參與敘事:互動(dòng)劇的發(fā)展、特征及趨勢(shì)[J].編輯之友,2020(09):75-82.
[3]王圣華.媒介演化視域下電影的人工智能換臉術(shù)的探究[J].當(dāng)代電影,2022(08):36-44.
[4]趙懷勇,袁媛.數(shù)字時(shí)代前景下運(yùn)動(dòng)鏡頭與電影時(shí)空的重構(gòu)[J].電影評(píng)介,2007(13):47-48.
[5]余冰清.現(xiàn)實(shí)的邊界:再探電影本體論[J].電影評(píng)介,2020(14):25-28.
[6]陳旭光.“后假定性”美學(xué)的崛起——試論當(dāng)代影視藝術(shù)與文化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向[J].當(dāng)代電影,2005(06):109-115.
[7]夏燕.影視藝術(shù)審美心理機(jī)制描述[J].電影文學(xué),2013(04):17-18.
[8]張晗.國(guó)產(chǎn)互動(dòng)電影的敘事文本形態(tài)研究[J].電影文學(xué),2021(05):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