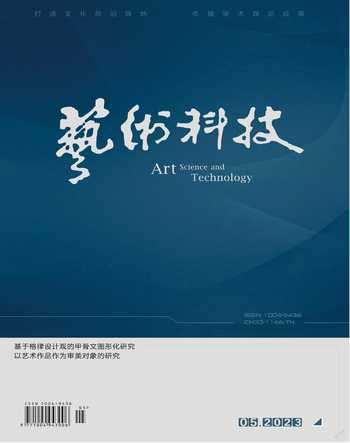侗戲傳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摘要:侗戲是侗族的傳統戲曲劇種,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侗族人民主要在其傳統節日期間演唱侗戲。大利侗戲始于清光緒初年,是大利人民在長期勞動生活中創造出的一種生動的藝術形式。大利侗戲的表演以侗族民間敘事說唱音樂與琵琶歌為主,內容涉及民俗、社交禮儀、愛情故事等諸多方面,曲調優美,旋律起伏有致,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是侗族文藝的一門藝術。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大利侗戲的傳承和保護面臨著傳承人斷層、表演形式受限、表演場所利用不足、普及宣傳力度小的問題。以大利村侗戲為代表的侗戲傳承與發展問題,是與當地鄉村文化振興、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文化強國建設等緊密關聯的重要問題。在實地田野調查基礎上深入發掘和梳理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中存在的系列問題,是推進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在此基礎上,為更好地開展大利侗戲的傳承與發展工作,文章認為,應積極收集、保存大利侗戲及其傳承人的基礎數據,建設侗戲傳承基地,創新表演形式和傳承模式,同時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對侗戲傳承發展工作經費和宣傳方面的協調和支持,在此基礎上探索和建構侗戲傳承與發展的有效途徑,助力大利村鄉村文化產業振興和精神文明建設,為其他地區的侗戲傳承和保護提供一些思路。
關鍵詞:大利村;侗戲;傳承發展;對策
中圖分類號:J8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5-00-03
侗族戲劇作為一種戲曲劇種,根植于侗族聚居區的農耕稻作文化,是侗族現存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1]。大利村位于云貴高原與廣西盆地交界地帶,受貴州省黔東南州榕江縣載麻鎮管轄。大利村域面積9.8平方千米,分為上下兩個寨子,均為侗族,擁有侗族大歌、侗族薩瑪節、侗年、侗戲、侗族婚俗等多項國家級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侗戲文化藝術在傳承發展方面遇到諸多障礙。為此,本文選取貴州榕江縣大利村侗戲藝術為研究個案,就侗戲傳承與發展問題展開研究。
1 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實地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目前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傳承人斷層、表演形式受限、表演場所利用不足、普及宣傳力度小等。
1.1 傳承人斷層
大利侗戲學習者、傳承者數量銳減,出現傳承人代際斷層現象,這是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利村年輕人部分外出求學,部分外出務工。他們在外出求學與務工期間,不斷接收新信息,產生新思想,這使大利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個人發展與追求的聚焦點更多地由本村轉向外界[2]。大利村民眾,尤其是年輕人,成年后便早早離開村寨,這使他們對村寨的侗戲表演藝術知之甚少。同時,他們大多認為學習侗戲并不能維持生計,便失去了學習侗戲的興趣。筆者在調查中發現,這種困境集中表現在大利侗寨內會唱侗戲的基本是老年人,老齡化現象突出;大利侗戲后學者無法跟進,戲班演員的數量在不斷減少等。
1.2 表演形式單一
侗戲是在侗族說唱文學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傳統藝術,具有鮮明的審美特色。它不僅承載了侗族豐富的文化傳統,亦體現了侗族人民獨特的審美意識、審美情趣與審美追求[3]。其表演內容以侗族民間敘事說唱音樂與琵琶歌為主。大利侗戲的形成歷史久遠,藝術風格較為傳統,其表演多受時間和場所的限制。就演出時間而言,大利村民一般只在重大節日時表演侗戲。就演出場所而言,大利侗戲具有特定的演出戲臺,通常只在村寨東側的既定戲臺表演。就演出曲目而言,以侗族傳說故事為題材編寫的《珠郎娘美》《吳勉王》《丁郎龍女》等傳統侗戲曲目,在大利侗戲表演中占有較大比重。從觀眾的角度而言,首先,觀眾需要在固定節日、固定場所觀看侗戲表演,自由度降低;其次,由于大利傳統侗戲的演繹以侗族傳統歷史文化為題材,受眾面較窄,因此外來游客甚至村子里的年輕一輩通常很難領會傳統侗戲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如何豐富大利侗戲演出的時間、地點、曲目等表演形式,解決表演形式的單一化問題,也是筆者著重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1.3 表演場所利用不足
戲臺又稱戲樓,是侗族人演唱侗戲的場所。大利侗寨的戲臺位于寨東,始建于清末,20世紀50年代毀于火災,70年代重建。戲臺是重檐單樓冠木構建筑,項部為三層重檐蹺腳歇山式屋頂,以小青瓦覆蓋;戲臺樓各層正面堂板分別繪有人物、花卉圖案,各層四端蹺腳,前柱雕兩龍;戲臺樓左側緊挨花橋,右側鄰近民宿,前面現為大利侗寨停車場。除了每年春節和各類侗族傳統節日以外,大利村的戲臺幾乎處于閑置狀態。戲臺空間較小,因此人們容易忽視這一重要的文化場所。同時,筆者發現,大利侗寨的戲臺前并未設置介紹標牌;戲臺上落滿灰塵,表明戲臺處于閑置狀態,透視出戲臺利用率低的現實狀況。大利村侗戲演出較少,戲臺利用率低,這就使村內民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受不到侗戲的藝術魅力,學習興趣亦隨之降低。與此同時,游客鮮有機會了解大利侗戲表演藝術。以上種種均對大利侗戲表演藝術的傳承與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
1.4 宣傳力度小
大利侗戲宣傳力度小主要表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
一方面,對本村居民而言,由于大利侗戲的戲師和演員都是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教授侗戲,他們自身很少有接受侗戲藝術專業教育的機會,因此很難將侗戲的技藝知識、藝術風格及其蘊含的藝術價值準確傳達給年輕人,年輕人對侗戲表演藝術的認知淺薄,學習侗戲的態度仍停留在“不能維持生計、沒有發展前景”的層面。
另一方面,對外來游客而言,首先是大利侗寨并未設立向外來人員介紹侗戲及其他侗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專門平臺,其次是大利侗戲推廣宣傳的手段、途徑與方式匱乏。一是大利侗寨與其他侗寨交流較少,侗戲演出幾乎限于本村,很少向外界展示,也難以借鑒與吸收其他侗寨侗戲傳承與發展的經驗;二是即使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大利侗戲表演藝術的信息化傳播率亦較為低下,這集中體現在網絡平臺對大利侗戲表演視頻的承載量較低。大利侗戲的宣傳力度小,成為阻礙大利侗戲傳承和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2 解決大利侗戲傳承與發展問題的建議
針對以上問題,為促進大利侗戲傳承和發展,筆者提出四點建議。
2.1 收集大利侗戲及其傳承人的基礎數據
收集大利侗戲的基礎數據是其傳承和發展的前提。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歷史上,戲師們憑記憶把某一整出戲甚至數出戲記于腦中,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授給演員;有時也利用漢字記音,借用漢文字把傳統的侗戲記錄下來形成劇本。
為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侗戲,筆者認為,首先應收集、整理大利侗戲傳統劇目的劇本,了解戲劇中所講述的民間故事、傳說故事及其蘊含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在此基礎上,將老一輩傳承人的服裝、樂器、道具等拍下來,并予以數字化存檔。每逢節慶日,用攝影的方式記錄下大利人演出的侗戲;邀請戲師和演員專門表演未表演的經典劇目,對這些劇目進行拍攝、記錄、存檔。
其次,收集整理現有的大利侗戲傳承人的相關資料,對侗戲傳承也非常重要。究其原因,一是旨在加大對侗戲傳承人的普查力度,對目前仍在努力傳承大利侗戲的少數民間戲師和演員給予官方認定;二是收集傳承人的基本信息,有助于了解傳承人的經歷,詳細記錄其相關技藝特點;三是通過與傳承人的交流,了解其對各個傳統侗戲曲目的理解,傾聽其對侗戲傳承與發展的意見、建議及其作為侗戲傳承人的訴求。
2.2 建設侗戲傳承基地
為促進大利侗戲的傳承與保護,在大利侗寨內建設侗戲傳承基地是一個有效途徑。筆者認為,侗戲傳承基地作為展示侗戲魅力的專門場所,能夠促進大利村人和村外人認識大利侗戲、學習演唱侗戲技藝。傳承基地既可以聘請大利侗戲傳承人為傳習老師,又可以定期邀請其他縣級、省級甚至國家級侗戲傳承人到大利侗寨授課,這不僅能夠營造良好的侗戲教學氛圍,而且能夠加強傳承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筆者認為,在侗戲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與發展中,挖掘與培養優秀的侗戲傳承人十分關鍵。例如,在貴州侗族聚居區,多數村寨都有群眾自發組織業余侗戲班[4]。建設侗戲傳承基地,能夠在保護傳統侗戲的同時,吸引年輕人,挖掘和培養優秀的侗戲傳承人,組織侗戲班,為侗戲的傳承和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固定的侗戲研習場既能為傳承人的技藝研究提供平臺,又能強化傳承人的行業歸屬感,使傳承人有更多固定的時間用于排練侗戲。
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大利村除了戲師和演員以外,其他上了年紀的人雖然也熱愛侗戲,但對侗戲的了解不深,這不利于這部分人對外來人員宣傳和傳播侗戲藝術。而建設侗戲傳承基地可以引導更多村民參與到大利侗戲的傳承中,培養更多傳播侗戲藝術的人。因此,建設侗戲傳承基地,是大利侗戲傳承和發展的一個有效舉措。
2.3 創新表演形式和傳承模式
保護傳統大利侗戲固然是必要的,但要推動大利侗戲發展,賦予其新的生命力,這需要在表演形式和傳承模式上創新。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
第一,演出形式向旅游產品型轉變。旅游產品型是隨著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文旅變體形式。因其為滿足游客需要進行的表演,所以其演出的內容、時間、場所、觀眾等有較大的不確定性[5]。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大利侗寨的戲臺周圍有四戶家庭旅舍,其在為游客提供食宿服務的同時,還可與村內侗戲戲師和演員合作,為游客提供文化服務,從而增加旅舍及大利侗戲傳承人的收入。這既可以打破傳統侗戲在表演時間上的限制,又能滿足游客了解侗戲、欣賞侗戲的需求。
第二,在侗戲創作中融入現代元素。大利侗寨上演的侗戲以傳統劇目為主,曲目更新不及時,缺乏創新性。鑒于此,可在編創劇本時加入一些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元素,使大利侗戲的劇本創作和曲目表演更貼近大利人民的現實生活,從而彰顯侗戲表演的生機和活力,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向觀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一條重要途徑。
第三,在語言上進行改進。傳統侗戲以侗語道白和演唱,其中的用詞和比喻手法增加了觀眾尤其是非侗族觀眾觀賞和理解表演內容的難度。對此,筆者認為,一是可以借鑒榕江其他侗族地區侗戲傳承的經驗,整理改編現有的大利侗戲,形成兩個版本,一種是侗語版本,一種是漢語版本[6]。可根據游客組成情況,選擇適當版本演唱。二是在傳承方式上,不宜局限于侗戲傳承人在村內傳授侗戲,而應將侗戲帶入校園,讓更多年輕人接觸到這一傳統文化。同時,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大利侗戲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應切實發揮新媒體的優勢,使傳承方式和發展途徑更加靈活。
2.4 政府部門加強協調和支持
大利侗戲的傳承和發展離不開村委會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協調和支持。
首先,是經費上的支持。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既需要政策支持,又需要資金資助。政府部門可加大經費投入力度,為大利侗戲的傳承與發展提供物質保障;政府亦需要給予傳承人相關經濟支撐,以使戲師無須擔心生計,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致力于侗戲的傳承與發展[7]。
其次,加大對侗戲表演設施的保護與整治力度,村委會應組織人員定期維護和清掃戲臺,積極組織村寨活動,以提高戲臺的利用率。
最后,加強大利侗戲的宣傳。大利侗戲的受眾局限于本村之內,其他地區的人對其了解甚少。利用大利侗族“中國第一批傳統村落”“魅力侗寨”的稱號,推動大利侗戲與當地旅游業互動發展,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當地文旅產業的發展中,這亦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協調各方,并給予全方位支持。同時,政府部門應與村委會協調,加大大利侗戲的宣傳力度,在榕江縣城內的各項大型活動中爭取表演機會,鼓勵傳承人參加侗戲、侗族音樂等座談會、交流會,增強大利人對侗戲這一傳統藝術的自信,改變大利村年輕人對侗戲的既有認知,吸引更多人關注大利侗戲,參與侗戲傳承與發展工作。
3 結語
促進侗戲的傳承與發展,既有利于侗族地方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又能推動以侗戲藝術為代表的侗族鄉村文化產業發展,是黨和國家文化強國建設過程中具有區域性的文化工程。在實地調查基礎上,筆者認為,深入探究侗戲傳承與發展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實時采取適當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探索和建構侗戲傳承與發展的有效途徑,是推進這項文化工程建設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羅仙泗.非遺視野下貴州天柱縣農村侗戲傳承與發展的困境研究[J].戲劇之家,2022(15):48-50.
[2] 蔣凌霞.鄉村振興背景下侗戲的保護與文化傳承研究:以三江侗族自治縣為例[J].戲劇之家,2021(11):33-34.
[3] 李嵐.試論侗戲的傳承與保護[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50-53.
[4] 韋強,陸芳梅,王瑩,等.廣西龍勝侗戲的傳承與保護[J].宜春學院學報,2013(2):100-104.
[5] 李延紅.民族音樂學視角下的傳統侗戲音樂[J].藝術探索,2005(6):5-8.
[6] 楊遠松.侗戲在榕江的流傳與發展[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30-34.
[7] 陳誠.侗戲的傳承與保護之我見[J].戲劇之家,2018(14):46.
作者簡介:楊欣然(1999—),女,重慶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民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