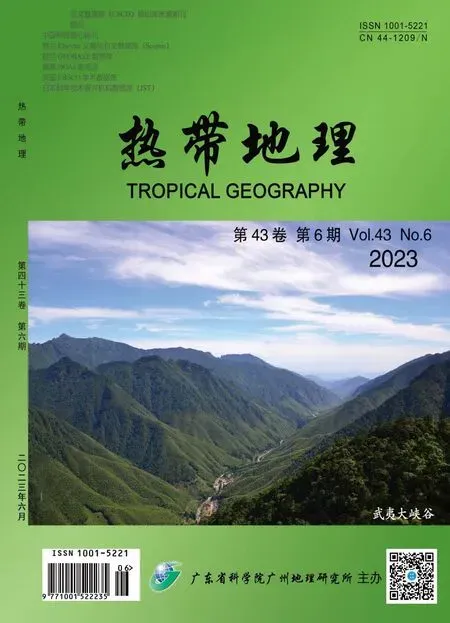日常生活實踐視角下的高校周邊攤販空間生產(chǎn)研究
黃 浩,黃 幸,謝苑儀,宋恒之,羅焜升
(華南理工大學(xué) 建筑學(xué)院,廣州 510641)
社會科學(xué)的“空間轉(zhuǎn)向”引發(fā)社會空間研究的新維度并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熱點。20 世紀(jì)70 年代,列斐伏爾將復(fù)雜的城市空間系統(tǒng)地整合到簡潔而全面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中(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等,2021)。受跨學(xué)科社會空間研究的影響,部分學(xué)者將旅游地(孫九霞 等,2020)、城中村(薛德升 等,2008)等議題與空間生產(chǎn)理論相結(jié)合,非正規(guī)部門空間生產(chǎn)下的主體生存狀態(tài)(薛德升 等,2008)、空間演變(劉毅華 等,2015)等也逐漸被重視。地攤經(jīng)濟(jì)非正規(guī)部門空間生產(chǎn)的相關(guān)研究也都從城市片區(qū)(阮皇靈,2019)、街區(qū)(黃耿志 等,2016)等不同尺度關(guān)注到各相關(guān)利益主體在空間生產(chǎn)中的角色與作用。由于城市不同片區(qū)的流動攤販狀況與成因較為復(fù)雜,地理學(xué)對于流動攤販的的研究視角逐漸轉(zhuǎn)向更為微觀的“日常生活空間”,對攤販的日常生活細(xì)節(jié)有了更多的思考。現(xiàn)有文獻(xiàn)大多研究地攤空間本身成因、特征或管制等(張延吉等,2014;黃耿志 等,2019;張勝玉 等,2020),地攤空間生產(chǎn)對周邊空間的塑造與影響卻被不同程度地忽視。
高校周邊空間與使用主體具有特殊性。高校周邊的攤販空間具有依托高校消費、拓寬高校后勤、服務(wù)高校師生等特點,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高校文化氛圍,是社會空間研究的理想場所。相較于非高校區(qū)域,高校周邊有相對固定的消費群體——大學(xué)生。高校周邊地攤空間交織著不同主體的權(quán)力與話語,通過分析其空間生產(chǎn)的過程,不僅可以探究高校周邊地攤經(jīng)濟(jì)形成與持續(xù)的原因,還可以以點帶面地揭示中國高校周邊攤販空間的內(nèi)在機(jī)制。目前高校周邊相關(guān)研究包括“學(xué)生街”的環(huán)境特征與人群心理(朱昕虹,2007;盧紅艷,2017),周邊商業(yè)空間發(fā)展與經(jīng)營情況(陳煊 等,2006;鄭麗瓊等,2012;陳星宇 等,2014)等,對塑造高校周邊攤販空間所牽涉的攤販、城管、學(xué)生等主體的社會關(guān)系,及社會力量對空間的影響沒有足夠重視,也鮮有學(xué)者運(yùn)用空間生產(chǎn)或日常生活實踐理論對高校周邊非正規(guī)部門這一城市典型社會空間進(jìn)行研究。
因此,選取高校周邊的攤販空間為研究對象,基于空間生產(chǎn)中日常生活實踐的涵義,關(guān)注高校周邊地攤攤主如何通過日常的時空流動與學(xué)生群體等多元主體的社會力量形成反規(guī)訓(xùn)的社會空間,推動相應(yīng)空間實踐的形成,展示日常生活視野下的豐富性;深入探討流動攤販日常生活實踐中對地攤周邊空間秩序的重構(gòu),嘗試根據(jù)“高校-城中村”地攤空間對日常生活豐富片段進(jìn)行實證。以期豐富日常生活實踐理論,為中國高校周邊非正規(guī)空間管理提供參考依據(jù)。
1 研究理論、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理論
日常生活是社會個體或群體常規(guī)的、瑣碎的、具有重復(fù)性的實踐活動(尹鐸 等,2019),其從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中產(chǎn)生,并在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中被強(qiáng)調(diào),使得社會學(xué)出現(xiàn)關(guān)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轉(zhuǎn)向(賴立里 等,2017)。列斐伏爾(Lefebvre, 1911)認(rèn)為空間生產(chǎn)會因日常生活中大眾力量或強(qiáng)或弱的“反作用”而被推動,德塞圖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將這種大眾對抗規(guī)訓(xùn)的能力稱為反規(guī)訓(xùn)戰(zhàn)術(shù),并指出其在日常生活領(lǐng)域下會根據(jù)具體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出現(xiàn)不同的運(yùn)作機(jī)制(張榮,2011;Leary, 2013;孫九霞 等,2014),其更強(qiáng)調(diào)大眾日常生活中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激發(fā)(Elmhirst,1999),也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xì)節(jié)與積極的一面。日常生活豐富片段的還原和微觀視角的空間生產(chǎn)切入,正是本文對地攤經(jīng)濟(jì)空間生產(chǎn)研究的理論視角所在(圖1)。

圖1 理論分析框架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地攤空間相比其他非正規(guī)空間更加零散化,因為塑造這類空間的往往是個體或個體間的行動網(wǎng)絡(luò),而非宏大的規(guī)劃政策(王豐龍,2011)。而日常生活實踐恰恰從個體視角透視空間形成與生產(chǎn)的過程,其觀察視角與地攤空間的微觀形成過程相契合。流動攤販在日常生活視野中,多元的社會關(guān)系推動著空間的生產(chǎn)。城市管理者出于對城市形象的管理,通過一定的規(guī)則與監(jiān)管實現(xiàn)空間的規(guī)訓(xùn),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權(quán)力空間;流動攤販在日常生活中為了爭奪空間的使用權(quán)利,通過社會網(wǎng)絡(luò)的互相支持,采取多樣化的策略進(jìn)行不同程度的反抗,形成了相應(yīng)的社會空間;同時,在多元主體長期的互動與實踐中,形成了具有某種特征的物理空間,實現(xiàn)對原有空間的重塑。而權(quán)力空間、社會空間、物理空間的微觀分析視角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王豐龍等,2011),并延承空間表征、表征空間、空間實踐的理論脈絡(luò)。攤販的日常反規(guī)訓(xùn)戰(zhàn)術(shù)也已成為攤販空間研究的重點,如張楚婧等(2021)針對深圳城中村攤販在就業(yè)與社會生活空間的反規(guī)訓(xùn)戰(zhàn)術(shù)進(jìn)行研究,魏淑媛等(2020)借助生存韌性視角分析攤販的生存策略,都形成了各自分析攤販反規(guī)訓(xùn)策略的研究框架。
國內(nèi)外日常生活實踐相關(guān)研究內(nèi)容相對廣泛,都較為關(guān)注研究對象具體的生活細(xì)節(jié)。如研究涉及非正規(guī)空間(Tran et al., 2020)、地方文化(孫九霞等,2019)等,相關(guān)的人群主體有跨國精英(劉美新 等,2021)、流浪漢(尹鐸 等,2019)等,但以流動攤販為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研究較少。國內(nèi)學(xué)者對包括地攤經(jīng)濟(jì)在內(nèi)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研究較廣,以空間視角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區(qū)域尺度(張延吉 等,2014;黃耿志 等,2019;陳業(yè)宏 等,2020)。而在街區(qū)尺度上,學(xué)者主要探討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空間分布(陳煊 等,2006)、空間演變(黃耿志 等,2016)、聚集機(jī)制(杜培培 等,2017)等。部分學(xué)者如黃耿志等(2011)結(jié)合空間生產(chǎn)視角,對多元主體社會關(guān)系下非正規(guī)部門的生存狀態(tài)進(jìn)行了深入剖析,也結(jié)合了多元主體的語錄等資料進(jìn)行解讀。但上述研究更多聚焦于對非正規(guī)部門自上而下的空間規(guī)訓(xùn),對流動攤販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動性探討,特別是對主體基于反規(guī)訓(xùn)的生活細(xì)節(jié)的關(guān)注還有待豐富與提升。
日常生活實踐既有對生活細(xì)節(jié)的強(qiáng)調(diào),也注重生活細(xì)節(jié)時間性與空間性的特征(賴立里 等,2017)。學(xué)者們更多關(guān)注到研究對象的生活細(xì)節(jié),但對其時間性的特征有所忽視。少數(shù)學(xué)者如Tran等(2020)著重結(jié)合流動攤販的時空分布特征,分析日常生活中流動攤販與城管競爭空間的規(guī)律,認(rèn)為流動攤販的日常生活對城市空間界面是否產(chǎn)生影響并未受到充分重視。本文選取城市典型社會空間之一——高校周邊地攤空間作為空間載體,通過探討物理、權(quán)力、社會空間的形成,聚焦與強(qiáng)調(diào)攤販日常生活的時空特征與反規(guī)訓(xùn)策略,重點解析攤販主體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對高校周邊物理、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與影響,以回答高校周邊的空間秩序如何被重塑的問題,以期有助于進(jìn)一步理解日常生活細(xì)節(jié)中的時空規(guī)律,同時關(guān)注高校周邊空間生產(chǎn)過程中多元的社會力量,助力優(yōu)化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
1.2 研究對象
以廣州大學(xué)城“廣工五飯-南亭村”為例展開高校周邊地攤空間生產(chǎn)研究。廣州大學(xué)城位于廣州市番禺區(qū)北部的小谷圍島,是廣州發(fā)展戰(zhàn)略“南拓軸”上的重要科教節(jié)點。2001年,廣州市政府選定小谷圍島作為大學(xué)城的建設(shè)區(qū)域,南亭村是僅保留的4個城中村之一。大學(xué)城中失去農(nóng)田的村民“靠校吃飯”,自發(fā)形成針對大學(xué)城師生的商業(yè)服務(wù),吸引在校學(xué)生這一龐大的消費群體,彌補(bǔ)大學(xué)城內(nèi)部配套設(shè)施的不足,發(fā)展出房屋租賃、餐飲、零售、娛樂等富有靈活性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活動。擺攤等聚集性行為最終在廣州大學(xué)城形成多條著名的地攤街。
大學(xué)城地攤街以從廣州工業(yè)大學(xué)西區(qū)東門向南延伸到大學(xué)城中環(huán)西路口的“廣工五飯”最具典型特征。大學(xué)城急劇的城市化產(chǎn)生眾多服務(wù)業(yè)缺口,2011年山東煎餅大叔發(fā)現(xiàn)小吃攤的商機(jī)后在國醫(yī)東路擺攤,迎合廣工學(xué)生早、晚餐飲消費的需求,填補(bǔ)廣工校內(nèi)4個食堂的供餐空缺時間,猶如廣工的第五個食堂,因此被學(xué)生們冠以“廣工五飯”的稱號(圖2)。2013年,“廣工五飯”走向繁榮,迅速發(fā)展出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夜宵街,流動攤販近10家。2015 年底,廣州市“十三五”開展城市升級行動,對于地攤的管束趨于嚴(yán)格;2016年初城管開始駐守各個小吃點,驅(qū)趕攤主。由于受到較多的約束,如今“廣工五飯”僅在每晚十一點半出現(xiàn)。夜晚其地攤數(shù)量眾多,具有較為明顯的時間、空間流動特征,且社會關(guān)系復(fù)雜。本文選擇“廣工五飯”作為對象,結(jié)合“廣工五飯”與南亭村地攤空間生產(chǎn)過程的相關(guān)調(diào)研,可較好地總結(jié)高校周邊地攤空間生產(chǎn)的特征,進(jìn)而揭示此類地攤的社會空間特點。

圖2 “廣工五飯”地理位置Fig.2 Location of the Fifth Cantee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3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非參與式觀察法、參與式觀察法、深入訪談法等。于2020-10-16—17 進(jìn)行為期2 d 的預(yù)調(diào)研,又于2021-01-04—09、02-18—22、2022-05-14—29進(jìn)行為期24 d共分3期的實地調(diào)研。實地調(diào)查后,通過微信線上訪談、網(wǎng)絡(luò)問卷等方式與訪談對象保持聯(lián)系,隨時補(bǔ)充實地調(diào)研過程中可能遺漏的材料。此外,收集有關(guān)大學(xué)城的建成歷史、城中村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等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作為二手?jǐn)?shù)據(jù)予以補(bǔ)充。
采用半結(jié)構(gòu)式訪談?wù){(diào)研不同主體生計生活現(xiàn)狀、空間使用情況、社會關(guān)系、對其他主體的看法、對“廣工五飯”的感受等,調(diào)研對象包括地攤攤主、城管保安、南亭村村民、南亭村商鋪鋪主、學(xué)生及教師等,共83 個對象,訪談時間在30~120 min不等;其中重點訪談對象21人(表1),個人訪談時間基本達(dá)1 h 以上。與此同時,為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在訪談過程中運(yùn)用三角互證的思路,并結(jié)合非參與式觀察法對部分?jǐn)傌溸M(jìn)行跟蹤,繪制其日常行動軌跡與路線作為輔證材料。此外,還草圖繪制“廣工五飯”的攤位布置、空間邊界的尺度與情況等,以文字描述地攤經(jīng)營者、消費者、南亭村商鋪老板、城管等主體的空間活動與日常交互,共完成田野筆記約4萬字。

表1 “廣工五飯-南亭村”重點調(diào)查訪談對象基本資料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key survey objects in "the Fifth Canteen of GUT"
針對學(xué)生群體,結(jié)合網(wǎng)絡(luò)問卷調(diào)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124份。在綜合調(diào)研數(shù)據(jù)基礎(chǔ)上,運(yùn)用空間分析、數(shù)據(jù)可視化等方法對“廣工五飯”地攤空間的生產(chǎn)進(jìn)行分析。通過分析不同主體之間的空間、社會關(guān)系等,從物理空間、權(quán)力空間、社會空間3個層面探討其空間形成的過程,隨后重點分析和解構(gòu)攤販“反規(guī)訓(xùn)”的形式、過程及機(jī)制。
2 “廣工五飯-南亭村”地攤的空間形成
2.1 物理空間的形成
南亭村在大學(xué)城的建設(shè)過程中得以保留,高校的入駐恰好為外來人口提供了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契機(jī)。低廉的出租屋與店面鋪租吸納了原來在周邊從事其他工作的外地人,使南亭村逐漸發(fā)展成為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流動地攤的聚集場所。攤主們來到廣州的動因各有不同,但都圍繞著同一個目標(biāo)——為了更好地生活。有的攤主是為了陪伴孩子上學(xué),有的攤主只是將擺地攤視作疫情期間的過渡性就業(yè),有的攤主跟隨同鄉(xiāng)一起出來闖蕩,甚至有攤主通過“抖音”等社交媒體慕名前來,如來自湖南的臭豆腐攤主的敘述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原本我在家鄉(xiāng)市場擺攤,后來從抖音上看到廣州大學(xué)城有幾條很有名的學(xué)生街,廣美的‘墮落街’,廣工的‘五飯’啦,就覺得這邊擺地攤還是能做得不錯的。(TZ01)”
“廣工五飯”的逐漸形成意味著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由城中村向高校周邊道路的定向、定時擴(kuò)散。南亭村毗鄰廣工、廣美的特殊地理區(qū)位,推動了地攤經(jīng)濟(jì)空間的形成;攤主為進(jìn)一步滿足學(xué)生群體消費需求,降低交通與時間的成本,將地攤空間向廣工西區(qū)學(xué)生宿舍一側(cè)的國醫(yī)東路移動。在學(xué)生群體占較高比重的大學(xué)城,國醫(yī)東路到了午夜車流量極少,攤販開始在該處擺攤。“我們是最早一批到五飯擺攤的,說真的,這條路靠近學(xué)生宿舍,又有需求,到了晚上又一輛車都沒有,我們不得利用起來。(TZ09)”
有了這一“先例”,其他攤販也開始積極實踐自己的空間主張。這意味著個體行為逐漸轉(zhuǎn)變?yōu)榧w行動,成為一種有意或無意的利益聯(lián)盟(孫九霞等,2014),這也迫使管理者做出改變——對國醫(yī)東路與南亭村進(jìn)行分時管控。白天大學(xué)城管制較為嚴(yán)格,攤主們在南亭村生活、備貨、預(yù)處理食材,晚上8點陸續(xù)到南亭大道經(jīng)營,而到了晚上11點半城管的分時管控結(jié)束后,依次進(jìn)入國醫(yī)東路擺攤,一直持續(xù)到夜間1點。此后,“廣工五飯”從美食夜宵的聚集點又轉(zhuǎn)變回承擔(dān)交通功能的國醫(yī)東路。“廣工五飯”攤販的物理空間就此形成。
2.2 權(quán)力空間的形成
“廣工五飯-南亭村”的空間生產(chǎn)實質(zhì)上受到了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影響。從宏觀看,“南亭大道—廣工五飯”地攤經(jīng)濟(jì)空間格局的形成源于城市空間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同期的農(nóng)村發(fā)展滯后、進(jìn)城農(nóng)民工的社會再就業(yè)問題等。城鄉(xiāng)二元的戶籍體制導(dǎo)致這些地攤主體難以融入正規(guī)部門,進(jìn)而轉(zhuǎn)入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從事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活動。廣州大學(xué)城“南亭村—南亭大道—國醫(yī)東路”區(qū)域的土地性質(zhì)涵蓋了國有和集體土地,其界限的模糊性為地攤主體提供了制度漏洞條件。“廣工五飯”具有對周邊高校功能的補(bǔ)足、價格的低廉以及深夜?fàn)I業(yè)的特性,而政府自上而下的規(guī)訓(xùn)較弱,底線為不堵塞國醫(yī)東路的交通,使得具有非正規(guī)性的地攤經(jīng)濟(jì)存在持續(xù)的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制度漏洞是結(jié)構(gòu)化因素,攤販、學(xué)生以及城市管理者則是地攤空間中的能動主體。
“廣工五飯”權(quán)力空間的形成與管理者的規(guī)訓(xùn)有著密切聯(lián)系。通過走訪得知,大學(xué)城管理者為塑造正規(guī)化的空間形象和減少“臟亂差”的現(xiàn)象,對大學(xué)城攤販空間采取相應(yīng)的規(guī)訓(xùn)策略與機(jī)制,而“廣工五飯”因其特殊性而受到特殊的監(jiān)管:1)限制時間:小谷圍街道城管中隊外雇保安,每天在國醫(yī)東路南端十字路口處等到十一點半才對流動攤販放行;2)限制地點:城管在相關(guān)道路上劃定范圍,將攤販們限制在某一條路或某一地塊上進(jìn)行集中管理;3)日常不定時突擊檢查。晚十一點半前的時間管制是為防止“廣工五飯”對國醫(yī)東路的交通影響,而晚十一點半后并不意味著地攤主可以“高枕無憂”,城市管理者會進(jìn)行不定時的突擊檢查。管理者自上而下對“廣工五飯”進(jìn)行管制,從而促進(jìn)權(quán)力空間的生成。而地攤攤主則持續(xù)應(yīng)對政府不利管制形成的“對立空間”,也逐漸重構(gòu)城市管理者所計劃的“規(guī)訓(xùn)空間”。
2.3 社會空間的形成
在高校周邊地攤物質(zhì)空間生產(chǎn)過程中,許多外來人口的生計問題得到解決,攤販間的社會關(guān)系得以更新與強(qiáng)化。漂泊無依、貧困待業(yè)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從業(yè)者面臨諸多生活壓力,“廣工五飯-南亭村”為他們提供了謀生的空間。隨著“廣工五飯”地攤經(jīng)濟(jì)逐漸形成規(guī)模,通過商機(jī)探尋、同鄉(xiāng)推薦、新媒體宣傳等方式加入到廣工周邊擺攤的攤販逐漸增多,攤販之間形成了緊密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我07年來擺攤的時候聽說很多外地人在大學(xué)城做生意,我們來的時候沒多少人在擺攤,也就不到十家,每年都在變多。我自己過來的,我們老鄉(xiāng)比較少,聽說湖北的比較多。(TZ02)”
日常生活的社會空間涉及不同利益的空間主體,存在多方主體的利益牽制與協(xié)調(diào)支持,并形成復(fù)雜而緊密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進(jìn)而最終形成高校周邊的社會空間。政府與大學(xué)城管理主體的規(guī)訓(xùn)力量依然存在,而攤主們?yōu)闋帄Z公共空間的使用權(quán)利,通過社會關(guān)系的互助形成自下而上“反規(guī)訓(xùn)”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一套在日常生活實踐上的“反規(guī)訓(xùn)”策略。反規(guī)訓(xùn)策略成為日常社會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由于高校周邊空間的特殊性,學(xué)生群體的消費與聚集行為也成為“廣工五飯”空間得以維系的重要力量。他們將學(xué)生的生活特質(zhì)嵌入到攤販空間中,也推動著攤販對城管進(jìn)行“反規(guī)訓(xùn)”。最終在規(guī)訓(xùn)與反規(guī)訓(xùn)的力量作用下,“廣工五飯”的多元社會主體間達(dá)到一種彼此交錯但互不冒犯的共生狀態(tài),即錯峰擺攤的“不成文約定”。最終,多元主體復(fù)雜社會關(guān)系的牽制與互動促使社會空間的形成。“我們等他們(城管)放寬管制的時間擺攤,也有被便衣民警抓過,不過得掩護(hù)得比較好才能抓得到。便衣民警來的時候大家相互通知,動起來,然后高呼快跑四散開啦。(TZ04)”
此外,攤主之間在“攤位競爭”與“擺攤互助”的二元結(jié)構(gòu)中存在交錯、共存與互動的關(guān)系,比價競爭與同鄉(xiāng)互助的關(guān)系同時存在,形成較為穩(wěn)定的社會空間秩序。“廣工五飯”周邊逐漸形成以學(xué)生服務(wù)為中心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實體,基于日常實踐的社會空間。出于對彼此生存空間的集體保護(hù)意識(劉云剛,2011),社會空間的在生產(chǎn)得以可能——一旦遭到城管驅(qū)趕,攤販之間通過互聯(lián)互助形成規(guī)訓(xùn)與反規(guī)訓(xùn)的機(jī)制。
3 空間生產(chǎn)的機(jī)制
攤主們構(gòu)建的社會關(guān)系對“廣工五飯-南亭村”的空間塑造起著重要作用。在當(dāng)前宏觀制度的背景下,作為社會邊緣群體的攤主依靠自身力量,通過活用高校周邊空間與南亭村空間的特性,實現(xiàn)對空間的占據(jù)。同時,依靠學(xué)生、同鄉(xiāng)等的支持以及其他社會行動者的博弈對空間進(jìn)行鞏固,形成一種相對緩和的空間生產(chǎn)進(jìn)程。
3.1 時空流動下的物理空間生產(chǎn)
作為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南亭村曾涌入大量外來人口。南亭村租金低廉、管制較為寬松,交通便利,外來人口的涌入帶來大量的住房需求。在這些需求的刺激下,南亭村村民向外來人口提供出租屋,狹窄的空間正好迎合了外來流動人口對于低成本的生活和經(jīng)營空間的需求,也為非正規(guī)就業(yè)提供更有利的環(huán)境,空間的粘著性被強(qiáng)化。流動攤販們敏銳地捕捉到高校學(xué)生的消費需求,選擇廣工校區(qū)外圍的國醫(yī)東路作為經(jīng)營基地,依托高校師生的需求不斷擴(kuò)展地攤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實現(xiàn)對空間的占據(jù)和重塑。
特殊的物理空間特征造就了“廣工五飯”模糊的物理空間界面關(guān)系。校園與城市、社區(qū)原本是邊界清晰的兩類空間,大學(xué)更是一個多功能混合的獨立體,而在流動攤販的空間生產(chǎn)影響下,廣工西區(qū)宿舍、“廣工五飯”及南亭村三者形成了一種模糊的界面關(guān)系。廣工校內(nèi)雖然不乏服務(wù)設(shè)施,但其固定的服務(wù)時間與服務(wù)內(nèi)容難以滿足學(xué)生的生活與消費需求。南亭村和“廣工五飯”的商業(yè)內(nèi)容既彌補(bǔ)了廣工大學(xué)商服設(shè)施的缺陷,輻射校園,同時又輻射城市與周邊社區(qū)。作為過渡空間,“廣工五飯-南亭村”模糊了校園與城市之間的界面。
這種模糊的界面關(guān)系展現(xiàn)出高校周邊地攤空間生產(chǎn)的時空流動特征。在實地走訪中發(fā)現(xiàn),南亭村攤販的經(jīng)營活動存在不規(guī)律性,而在“廣工五飯”卻顯現(xiàn)一種在變動中時間與空間特征的規(guī)律性——流動性與相對穩(wěn)定性特征。
流動性體現(xiàn)在日常空間的動態(tài)變化及出攤時間的分配。攤主們白天在南亭村休息,提前備好食材,晚上開始在南亭大道進(jìn)行經(jīng)營,到了將近十一點半陸續(xù)移動至國醫(yī)東路,在城管對空間的動態(tài)管制下實現(xiàn)空間生產(chǎn)(圖3)。攤主的擺攤時間亦會隨著周末或節(jié)假日做出調(diào)整,如在暫時失去大部分的消費群體的寒暑假期間,攤主們會尋找其他臨時性工作作為過渡,如送外賣、在實體店打短工等。

圖3 夜間南亭村攤販空間流動示意Fig.3 Illustr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stall space in Nanting Village at night
相對穩(wěn)定性體現(xiàn)在攤位的分布及微觀尺度特征。攤位分布具有2個明顯特征:1)呈段狀分布在廣工西門以南的國醫(yī)東路,迎合廣工學(xué)生從地鐵口或?qū)W校圖書館回到宿舍區(qū)的路線,同時也是攤主們從南亭到“廣工五飯”的最短路徑;2)各攤點的布局相對穩(wěn)定,在過往10來年間,攤主們自發(fā)形成并維持著“約定俗成”的空間秩序,這種秩序性與攤主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具有一定的關(guān)系。“我這兩年才來,自然就排到路口這邊了,那些來了十幾年的攤主的位置已經(jīng)固定了。位置遠(yuǎn)不遠(yuǎn)無所謂,主要靠的是熟客,我要是挪了位他們就不知道我在哪了。(TZ06)”
地攤攤主在近10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利用界面的模糊性與時空條件,形成一種較為固定的生產(chǎn)和生活機(jī)制,不斷鞏固和強(qiáng)化現(xiàn)有的物理空間生產(chǎn)(劉云剛,2011)。由于彼此聯(lián)系緊密,攤主們形成一定的身份認(rèn)同和信賴關(guān)系,具有對生產(chǎn)空間的集體保護(hù)意識。主體之間通過自覺遵守約定俗成的物質(zhì)空間秩序與模式,保證了物理空間的生產(chǎn)。
3.2 權(quán)力空間生產(chǎn)與“反規(guī)訓(xùn)”戰(zhàn)術(shù)
城市管理主體對攤販空間等非正規(guī)空間進(jìn)行規(guī)訓(xùn),并根據(jù)歷史經(jīng)驗調(diào)整管制方法,不斷推動著權(quán)力空間的生產(chǎn)。為了維持城市秩序和社會的可控性(黃耿志 等,2019),城管、街道辦等通過規(guī)章制度和管制措施形成對大學(xué)城原有空間的管制,構(gòu)建了最初始的權(quán)力空間。在大學(xué)城最初的管理階段,城管出于規(guī)訓(xùn)目的,所采取的措施以驅(qū)逐攤販為主。而在多年來,攤販通過其流動性等優(yōu)勢和多樣的手段來反抗城管的管制,逐漸形成其反規(guī)訓(xùn)的戰(zhàn)術(shù)和策略。在規(guī)訓(xùn)與反規(guī)訓(xùn)的較量與對抗中,城市管理主體逐漸發(fā)現(xiàn),完全驅(qū)逐攤販等強(qiáng)制性干預(yù)并不能完全正規(guī)化攤販經(jīng)營空間,于是轉(zhuǎn)向?qū)傌溝拗朴谝欢ǖ目臻g范圍內(nèi)進(jìn)行管制,如南亭村的村口、“廣工五飯”等空間,本質(zhì)上依然是為了規(guī)訓(xùn)非正規(guī)空間。
面對城管的規(guī)訓(xùn),攤販們自知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平時常通過較緩和的對策來躲避不利管制,如采用撤離、藏匿、返回或轉(zhuǎn)移陣地、靈活流動應(yīng)對、非正式合作等,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通過個體抵抗、集體抵抗來爭奪他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quán)利。近10年的長期博弈形成較穩(wěn)定的“廣工五飯-南亭村”社會空間,較極端的反抗形式出現(xiàn)頻率極低,攤販更多依賴日常迂回的方式,通過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共同構(gòu)筑的信息網(wǎng)彌補(bǔ)自身弱勢,間接地對抗規(guī)訓(xùn)力量(圖4)。

圖4 多主體社會空間生產(chǎn)機(jī)制Fig.4 The mechanism of multi-agent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1)撤離、藏匿、返回或轉(zhuǎn)移陣地 面對城管的壓力,多數(shù)攤主會先仔細(xì)觀望,對檢查的正式程度做出判斷。便衣城管會進(jìn)行不定期的檢查,收繳攤位并罰款。“城管有時候會半夜過來,穿便衣,看著就像學(xué)生一樣。一旦抓到我們擺攤后,他們會把整輛車會被推走,沒收。(TZ08)”如果他們發(fā)現(xiàn)此次檢查是正式的便會及時撤離,轉(zhuǎn)移陣地;如果發(fā)現(xiàn)城管不過是例行公事,維護(hù)交通,他們則把握時機(jī)先行撤離,隱藏在周邊綠化隔離帶或停車場中,等城管離開后再回到原本的地點進(jìn)行經(jīng)營。“如果沒跑掉,攤位被沒收,只能用備用推車?yán)^續(xù)擺攤,不然幾個月都要沒有收入。這些攤住每個人都有備用推車。(TZ04)”初來乍到的“廣工五飯”攤主,遵循這一空間的既有規(guī)則,與其他攤主類似,采用平靜、妥協(xié)、迂回的方式體現(xiàn)他們對空間的爭奪。
2)靈活流動應(yīng)對 攤主往往選擇推車的形式布置攤位,符合他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一方面,推車的尺度較小且具有靈活性,可以通過快速轉(zhuǎn)移以應(yīng)對突發(fā)的管制。這種靈活性保障了足夠的流動性,使設(shè)施和身體構(gòu)成一個空間尺度(圖5),通過這個尺度攤販模糊了販賣與運(yùn)輸、固定與移動之間的界限。另一方面,攤位往往背靠校園圍墻、行道樹以形成圍合空間,從而帶來一定的安全感,攤主們在僅1m2的空間內(nèi)進(jìn)行經(jīng)營與社會交往活動,形成“地攤商業(yè)街道”界面,營造“煙火氣”氛圍。

圖5 U字形和直線形攤位示意Fig.5 U-shaped and linear stalls
3.3 多元關(guān)系下的社會空間生產(chǎn)
非正式社會網(wǎng)絡(luò)是攤販社會空間生產(chǎn)的基礎(chǔ)。非正式社會網(wǎng)絡(luò),即具有某種共同特征的群體由于在一定空間范圍內(nèi)活動而自動相互識別并形成臨時的互助或聯(lián)合關(guān)系。在應(yīng)對管理者的檢查與整治過程中,“廣工五飯-南亭村”的攤主們自發(fā)形成一種互助的、非正式合作的社會網(wǎng)絡(luò)。鄉(xiāng)緣關(guān)系與互助關(guān)系是支持?jǐn)傊鞣钦?guī)經(jīng)濟(jì)的主要力量。來自五湖四海的攤主在擺攤過程中相互結(jié)識,共建信息共享、互利互助的關(guān)系,逐漸形成現(xiàn)有攤位布局(圖6),形成支撐性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4個方面:
1)一些攤主通過家庭合作分工經(jīng)營。由于午夜經(jīng)營的時間較為特殊,有些人無法做到從備貨到收攤?cè)绦詤⑴c,于是與家人配合,一人白天準(zhǔn)備,一人晚上擺攤,輪流交替工作;又或者通過家庭分工分配工作,增強(qiáng)夜間經(jīng)營效率,尤其在疫情期間學(xué)校加強(qiáng)管制、封鎖校門的背景下,這種合作更加頻繁,如鴨血粉絲湯攤主就采用這樣的形式:“做一碗鴨血粉絲湯步驟多,需要更多人手,我們一家五口,除了小孩,全家都出動了。我丈夫負(fù)責(zé)制作,我白天備貨,晚上過來打下手、收款,公公和婆婆就負(fù)責(zé)在校門口接單,然后把我們做好的送到學(xué)生手上。(TZ05)”在該攤點和學(xué)校圍墻僅20 m左右的距離之間,精細(xì)分工與密切配合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2)同鄉(xiāng)關(guān)系使攤主們在異鄉(xiāng)相互依靠。為了不爭奪客源,他們往往會避免選擇售賣類似的食品(見圖6)。此外,相鄰攤位的攤主之間往往是同族同姓的親戚,他們之間發(fā)展出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甚至是跨代互助的社會關(guān)系;此外,這些攤主還會在微信建立同鄉(xiāng)群,在群里聯(lián)絡(luò)或交換信息,尤其當(dāng)城管突擊檢查,群里總是能第一時間發(fā)出緊急通告,提醒各位攤主迅速撤離。
3)即使不是同鄉(xiāng)關(guān)系的攤販也會相互幫助。比如一旦有人發(fā)現(xiàn)城管,他會大喊告知同伴,一傳十,十傳百,其他攤主們立刻撤退散開;又如,突發(fā)急事需要短暫離開的攤主往往會拜托隔壁攤位的攤主幫忙看守推車。
4)學(xué)生消費群體也是非正式合作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中的關(guān)鍵一員。熱情友好的攤主往往和學(xué)生打成一片,他們建立微信群組織點單、抽獎等活動,部分?jǐn)傊鹘ㄈ憾噙_(dá)8個。攤主出攤之前先在群里告知學(xué)生地點,被城管驅(qū)逐后告知學(xué)生轉(zhuǎn)移的陣地,而學(xué)生也會將學(xué)校疫情期間封閉式管理的通知、校門關(guān)閉時段等管理信息告知攤主,以便攤主做出經(jīng)營調(diào)整。
微觀空間中,基于社會網(wǎng)絡(luò)與心理感受而產(chǎn)生的主體日常生活的多元關(guān)系與多樣策略推動著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面對城管的監(jiān)管,多主體的非正規(guī)同盟在日常的博弈過程中不斷強(qiáng)化,從而形成以親戚和老鄉(xiāng)關(guān)系為基礎(chǔ)、以消費關(guān)系為輔助的緊密社群,并形成攤主之間的身份認(rèn)同和信賴關(guān)系(Cloke, 2008)。通過社會網(wǎng)絡(luò)的營建,攤販鞏固了攤主對高校周邊空間的占據(jù),改變了原本大學(xué)城較為單一的學(xué)生社會空間,也進(jìn)一步維護(hù)和強(qiáng)化了其生存和生產(chǎn)空間。
3.4 高校周邊空間秩序的重塑
“廣工五飯”日常社會空間生產(chǎn)的過程涉及多個主體,除了城管的約束管制、攤販之間的互助關(guān)系,還有學(xué)生顧客為“廣工五飯”的經(jīng)營提供支持。
地攤經(jīng)濟(jì)因其較高的性價比和煙火氣與高校學(xué)生有限的消費能力和標(biāo)新立異的消費心理相耦合。“廣工五飯”的影響輻射整個廣工校園,學(xué)生群體因“廣工五飯”的物美價廉、方便快捷,在回宿舍的路上購買夜宵、飽口福,同時與攤主在心理上形成互惠互利的支持關(guān)系。基本每個攤主都有固定的老熟客,學(xué)生之間也會相互推薦攤位,可見流動攤販對學(xué)生群體購買者這一主要顧客群體的市場規(guī)模有較強(qiáng)的依賴性。
物理空間生產(chǎn)反作用于社會空間生產(chǎn),攤販在國醫(yī)東路和南亭村的集聚產(chǎn)生的地攤“煙火氣”,促使學(xué)生們到此消費,形成了具備濃郁學(xué)生文化的日常社會空間。超過40%的調(diào)研對象表示,“廣工五飯”給自己提供了一處具有“煙火氣”的交流與交往的空間。多數(shù)學(xué)生的日常學(xué)習(xí)生活局限在教室、食堂與宿舍之間,僅依靠校內(nèi)的設(shè)施無法滿足學(xué)生們精神上的需求,而學(xué)校周邊商業(yè)空間及流動地攤的發(fā)展則促使學(xué)生邁出相對狹窄的校園生活空間,進(jìn)入一個更加開放的公共空間。在晚上十一點半之后,靠近攤位的人行道上往往會聚集很多學(xué)生,社團(tuán)成員在這一空間團(tuán)建聚會。“到‘五飯’購買夜宵可以緩解平時在實驗室學(xué)習(xí)的壓力,是我們平時夜生活濃墨重彩的一筆。希望城管能寬恕一點,地攤很有煙火氣,是廣工學(xué)子的共同記憶。(XS02)”毗鄰高校的“廣工五飯”因接地氣而受到學(xué)生的喜愛,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學(xué)生化”的空間,將學(xué)生的集體文化屬性嵌入到攤販的空間中,賦予該空間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同時,高校周邊空間活力得到提升,空間的公共性得以重構(gòu),從而吸引其他學(xué)生或周邊居民等更多群體在該空間內(nèi)交流,使其成為多元主體生活交匯及城中村文化展演的舞臺。“有時候雖然我不吃夜宵,也會跟著社團(tuán)的朋友們到‘五飯’來,我們就在路邊坐著團(tuán)建,唱歌、討論什么的,餓了就去旁邊買點小吃,我們管這叫‘壓馬路’。(XS03)”
日常生活會逐漸創(chuàng)造出新的空間秩序(孫九霞等,2014)。在高校周邊空間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中,“廣工五飯”的地攤空間以其活力帶動廣工的校園邊界空間,使得作為過渡空間的“邊界”被使用而重獲活力,此時的廣工邊界和國醫(yī)東路無論在形態(tài)還是功能,或者是意義層面都不能簡單劃分為“校園”或“城市”2個范疇中。此時,基于城管分時管控的前提,城市市民、攤販與學(xué)生等的空間使用需求恰好達(dá)到一種彼此交錯但互不冒犯的共生狀態(tài),原本的場所,被攤販和學(xué)生的空間實踐激活后,被轉(zhuǎn)變成日常生活的空間。
綜上,大學(xué)城的外來流動人口恰好充分地利用了廣工周邊的南亭村及街道的空間特性實現(xiàn)對空間的占據(jù),并通過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鞏固經(jīng)營的地攤空間,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完成對高校周邊空間秩序的重塑。
4 結(jié)論與討論
“廣工五飯-南亭村”地攤經(jīng)濟(jì)空間的形成,作為中國高校邊界與高校旁城中村的典型案例,揭示了其空間生產(chǎn)的復(fù)雜性與其中的規(guī)律性,并通過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結(jié)論:
首先,高校周邊攤販空間具有典型的時空流動規(guī)律性,體現(xiàn)了空間生產(chǎn)中權(quán)力的微觀時空變化。過往非高校區(qū)域地攤空間研究更強(qiáng)調(diào)攤販的流動性與一定的規(guī)律性(Tran et al., 2020),相比之下,高校周邊攤販流動的規(guī)律性更加顯著,同時也呈現(xiàn)相對的穩(wěn)定性。其根源于空間生產(chǎn)中多元主體的規(guī)訓(xùn)與反規(guī)訓(xùn)的協(xié)商,最終表現(xiàn)為日常晝夜城管與攤主的社會關(guān)系變動與擺攤上默許的“不成文約定”。高校周邊攤販空間秩序的規(guī)律變化,既是一種時空約束(王權(quán)坤 等,2020),也是主體間行動的時空秩序,展示了大學(xué)城和城中村結(jié)合區(qū)域中攤販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也從側(cè)面印證了多元主體權(quán)力關(guān)系在微觀時空中的變化。
其次,本文針對過往研究缺陷,著重對攤主日常生活實踐中豐富片段與多樣反規(guī)訓(xùn)策略進(jìn)行還原。在“廣工五飯-南亭村”的高校空間邊界空間生產(chǎn)過程中,城市管理者自上而下的規(guī)訓(xùn)并非如其他研究(孫九霞,2014)中強(qiáng)勢。攤販充分利用“廣工五飯”作為高校邊界的空間特征,通過日常生活實踐中撤離、藏匿、返回或轉(zhuǎn)移陣地、靈活流動應(yīng)對、非正式合作等反規(guī)訓(xùn)策略爭奪公共空間的使用權(quán)力,也重構(gòu)了空間的公共性。與此同時,攤販依靠多元行動者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及個體間復(fù)雜的利益博弈,推動了“廣工五飯-南亭村”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產(chǎn)生了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也改變了高校周邊原本單一的學(xué)生社會空間。
第三,多元主體形成的“關(guān)系共生”實現(xiàn)了對高校周邊空間秩序的重塑,產(chǎn)生了攤販日常生活意義的再思考。“廣工五飯-南亭村”的空間是多元主體社會關(guān)系所織就與重塑的空間,在高校周邊攤販空間的空間生產(chǎn)過程中,權(quán)力空間、物理空間以及社會空間的重構(gòu)與調(diào)適在特定時間內(nèi)反復(fù)上演,攤主與學(xué)生日常生活的積極性在其中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過往許多地攤經(jīng)濟(jì)相關(guān)研究受制于物質(zhì)維度,部分研究關(guān)注到了各主體的相互作用與空間的互構(gòu)關(guān)系(劉毅華,2015),但并未對此展開更深入的探討。本文完整地呈現(xiàn)了攤販空間中多元主體的社會關(guān)系作用過程,發(fā)掘了城管與攤販日常生活中交錯但不冒犯的“共生”狀態(tài)。依賴于攤販之間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非正規(guī)空間的攤主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反規(guī)訓(xùn)”力量,具有“弱反抗性”的特征,學(xué)生群體的支持則促使反抗力量的延續(xù),其與決策者的“弱規(guī)訓(xùn)”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動態(tài)平衡。多元主體的空間生產(chǎn)過程展現(xiàn)了高校周邊攤販空間的日常豐富性與特殊性,也體現(xiàn)了攤販對于活化高校消極邊界空間的意義。
本文試圖回應(yīng)廣州大學(xué)城規(guī)劃的歷史遺留問題和高校邊界空間消極現(xiàn)象。在廣州大學(xué)城規(guī)劃建設(shè)的進(jìn)程中,一方面,高校聚集的廣州大學(xué)城吸引了大量學(xué)生群體進(jìn)入,學(xué)生作為相對單一的群體,其活動的分時性也造成了大學(xué)城的街道定期失去活力。曾經(jīng)許諾不建圍墻的大學(xué)城,也由于各校區(qū)管理需求向現(xiàn)實“低頭”,各校興建的圍墻產(chǎn)生了消極的邊界。另一方面,政府建設(shè)大學(xué)城時征收了農(nóng)田,原先的村民只能另謀生路。低廉的租金和學(xué)生的服務(wù)缺口導(dǎo)致地攤經(jīng)濟(jì)等非正規(guī)部門的聚集(劉毅華,2015)。流動攤販恰恰通過其日常生活的策略與實踐,在時空流動和與多元主體的互動中,生產(chǎn)、重塑與強(qiáng)化了高校周邊的地攤空間。值得一提的是,此過程是長期的,動態(tài)的,空間秩序是不斷被重塑的。現(xiàn)有研究或多或少都意識到流動攤販?zhǔn)情L期且不斷變化的群體(賴立里,2017;黃耿志,2019),而在其長期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中存在時空的規(guī)律性,在規(guī)律性中也存在微觀權(quán)力的動態(tài)變化與多元互動。本文從這一微觀尺度,嘗試對日常生活實踐理論作出一定的辯證性延展。
攤販日常生活實踐對于高校周邊空間的生產(chǎn)與活力重塑的作用并非廣州大學(xué)城才特有,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國高校周邊邊界與非正規(guī)空間狀態(tài)。與現(xiàn)有許多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發(fā)現(xiàn)攤販日常生活中的能動性、積極性是城市管理中可以引導(dǎo)與利用的因素。在此基礎(chǔ)上有助探討文明城市背景下如何通過充分發(fā)揮流動攤販的積極性,引導(dǎo)和疏導(dǎo)各類高校周邊“煙火氣”地攤經(jīng)濟(jì),進(jìn)一步提高城市綜合治理水平。本文對于空間生產(chǎn)理論在微觀層面上的應(yīng)用還只是一個探索,與目前的諸多研究具有互補(bǔ)的關(guān)系。此外,目前缺乏對學(xué)生這一主要消費群體寒暑假時期對攤販空間的影響研究,未來可以擴(kuò)大訪談樣本,以更全面地了解攤販日常生活對空間生產(chǎn)與重塑的影響。同時,高校周邊地攤空間的文化屬性可被進(jìn)一步探討;社會關(guān)系的空間生產(chǎn)在計量層面上的分析與日常生活實踐理論深入的辯證性思考還有待未來進(jìn)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