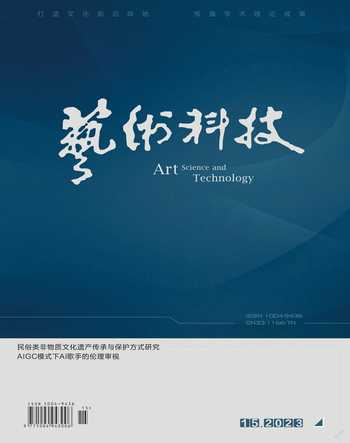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克拉拉與太陽》中的機器人敘事:論語言中的人機關系
摘要: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說《克拉拉與太陽》以機器人的視角為第一視角進行敘事,探討了語言中變化的人機關系。作為機器人敘事者,克拉拉缺失了人類的具身經驗,不僅造成了語言學習的障礙,還因意義錯位而解構了人類話語中的文化符碼,展現(xiàn)出機器與人類不可避免的疏離關系。在人機對立的敘事語境中,機器人通過語言的反向傳播,以其具身經驗改寫人類的語言符碼,共享人性經驗的能指,消解了人與機器的對立關系。另外,人與機器深層的同源性在技術生命最初的敘事中就已存在,機器作為人類的隱喻攜帶先在的人性剩余物,人們在機器人敘事者克拉拉身上發(fā)現(xiàn)丟失的古老人性能指,這呼應了人與機器在語言中達成的友好關系。當語言回歸其循環(huán)遞歸的本質,語言的開放與小說封閉的結局卻使敘事本身成為一種反諷:一次計劃性報廢的具身演繹。小說敘事對人性價值的肯定最終暴露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與人性的卑劣和脆弱,機器人卻以一種后人類的形式延續(xù)著人文主義的價值,而人類并沒有給機器人創(chuàng)造能夠生存下去的語境。《克拉拉與太陽》的機器人敘事召喚著一種后人類主義的實踐需求,通過機器人敘事的閱讀與寫作,在語言的反向傳播中不斷將機器人的經驗更新納入人類的語言體系,同時著手創(chuàng)造一個人機共生的和諧未來。文章以《克拉拉與太陽》中的機器人敘事為例,探究語言中的人機關系。
關鍵詞:《克拉拉與太陽》;機器人;敘事;語言
中圖分類號:I561.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5-00-03
0 引言
自經典敘事學產生以來,敘事作為人類特定經驗再現(xiàn)的屬性就被假定,故事的敘事性與“人類存在與人類關切”的體驗性[1]緊密相連。這一認知在20世紀末以來西方對啟蒙傳統(tǒng)和理性主體的解構與反思中逐漸轉向,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性與優(yōu)越性“不能再從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稟賦中找到蹤跡”[2],“非人類”的經驗開始進入人類視野的高地,最典型的就是21世紀飛速發(fā)展的機器人。帕里西在《機器人的未來》中提到,“在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中,機器人是第四次革命”[3],機器人從創(chuàng)造之初就承載著人類世俗造物主對他者的客體想象。然而如今的科技語境下,人機關系不斷變化,機器人逃脫為人類所取用的客體命運已經不再是一個未來主義的話題,“如今是物在看我”[4]——人們被迫站在“他者”的角度認識、理解這個被人類中心主義遮蔽的世界,而敘事就是手段之一。石黑一雄的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2021)探討了語言中的人機關系,將機器人敘事這一曾經被忽略的“他敘事”以新的方式帶入人類視野。
1 語言錯位的敘事者
通常來說,敘事者“作為一個敘述的自我總是或多或少地被性格化”[5],性格化的程度不僅決定了敘事者的可靠性,還決定了敘事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在《克拉拉與太陽》中,這種性格化卻仿佛從未存在過:敘述者克拉拉是一名AF(人造伙伴),其與作為人類的讀者間總是存在距離感,這就造成了讀者與之共情的障礙。克拉拉有著與人類不同的認知以及信息處理方式,如對見到的目標事物或人進行特殊命名、將自然空間分割成數值化類別圖幅等,更重要的是,語言成了可疑的東西,因為機器人不曾擁有過這些意義。例如喬西來商店里看她時的一幕場景:
“嘿!你怎么樣啊?”
我露出微笑,點點頭,豎起大拇指——這個手勢我經常在那些有趣的雜志里觀察到。
她說,“抱歉,想我嗎?”
我點點頭,擠出一張苦臉來,盡管我也用心暗示了我不是認真的,并沒有不高興。[6]30
雖然克拉拉的每個情態(tài)舉動都能做到在邏輯上符合人類情感反應與行為模式,但是她沒有真正的性格,只有仿若如此的情感和機械化的表現(xiàn)。克拉拉的話語是空洞的、等待被填充的,但能夠填充意義的只能是人類,因為語言編碼了意義的具身經驗,而對克拉拉來說,她的具身、這一從櫥窗中剛出生幾個月的機械身體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對應人類的經驗。進一步說,她學習了人類的語言,卻實際地造成了文化符碼的解構——作為敘述者的克拉拉雖然與人類共享同一種語言,卻可能指代完全不同的意義。這種錯位使人們不能再依賴人類的隱喻去解讀克拉拉的話語,就如同乞丐(beggar)被克拉拉命名為“乞丐人(Beggar Man)”、太陽(sun)被克拉拉命名為“太陽(the Sun)”一樣,克拉拉敘述中所涉及的眾多文化符碼并不是人們所熟悉的“那個世界”的知識,而是屬于機器人的元語言信號。
由于具身經驗的缺失,克拉拉一直存在人類語言的學習障礙,而語言本身成為克拉拉傳達自身作為機器與人類間距離的指標。在克拉拉的實踐中,這一斗爭總是不斷重現(xiàn):如果語言對“我”來說只是一種并不具身且外在于“我”的概念,那“我”該不斷貼近人類經驗去縫合自身與人類間的裂縫,還是用“我”自己的具身經驗改寫這一對應鏈?克拉拉曾經試圖與另一名AF羅莎運用“打架”這一人類概念,當兩名出租車司機拳腳相加時,克拉拉按照人類的經驗將其稱為“打架”,羅莎卻毫不理解,認為他們只是在玩鬧,克拉拉最終自嘲,這種不理解也發(fā)生在自己身上。語言的錯位割開了克拉拉與人類社會,“這個身體在人類銘寫中既找不到形象也找不到回聲”[7]359。如果克拉拉已經承認自己成為不了人,又是什么使她被視為人呢?在喬西的描述中,這個機器人“有一雙最最善良的眼睛”[6]51,并且母親一直試圖將克拉拉看作喬西的延續(xù),即使她深知這一機器的心靈并不是“人心”,這至少說明了某些時刻克拉拉的語言曾改寫過自身作為機器與人相互割離的經驗。
2 反向傳播中的人與機器
作為機器人的克拉拉與作為人類的其他人物之間的差距,在相同語言的使用環(huán)境下達到了最大化的諷刺效果。克拉拉看似是人類伙伴,實則是櫥窗里供人選購的商品。在家庭里,人們吃飯時克拉拉要站在陰影里,談話時克拉拉要背過身,不能隨意走動,克拉拉還時不時受到管家的恐嚇。讀者雖然與克拉拉之間總是存在難以忽視的距離,卻能從這些敘事中感到不人道,但讀者與克拉拉所共情到的“痛苦”只是一種幻覺。這種幻覺同時說明了克拉拉是如何通過敘事——一種錯位的語言——被當成人類的。
在一群被基因編輯技術“優(yōu)化”過的孩子們的社交聚會中,克拉拉作為喬西的AF受到關注,他們粗暴地脅迫、侮辱克拉拉,但她始終沒有回應,并且保持著經理教導的和藹面目:
“我很抱歉。”我說道,目光依然望向她的身后。
“你很抱歉?”說完長臂女孩對著整屋子的人問:“這話是什么意思?”人群哈哈大笑。接著她對我怒目而視,再度發(fā)問道:“你這是什么意思,克拉拉?什么叫你很抱歉,你什么意思?”
“我很抱歉我?guī)筒簧厦Α!?/p>
“她不打算幫忙。”[6]98
孩子們與克拉拉間的沖突在于克拉拉并沒有像一個機器一樣說話。人類教機器用“我很抱歉”表現(xiàn)順從和愧疚,然而在這不合適的語境中,一切都被克拉拉諷刺性地重新編碼為拒絕。在小說中,克拉拉的語言往往主動消解了人類賦予其的抽象性,轉而服從于變幻莫測的語境,以機器人的具身經驗改寫人類的能指。這一過程即海勒所說的“反向傳播”,意義的重建“必須通過解碼語言并且(在出現(xiàn)錯誤時)反向傳播”[7]356,而這一行為不僅造成了人類符碼的解構與去人類化,還使機器抽取了人性本身:機器突然變得像人一樣自主。
人與機器在語言之下深層的同源性甚至在機器人最初的敘事中就存在了。技術從為人所用開始,就作為人的隱喻攜帶著部分人的天性——那些“原初的甚至先在于人類而建構的人性剩余物”[7]253,正如克拉拉展現(xiàn)的已經不再有表達的語境的“友善”。在機器人身上,人類回想起丟失已久的人性記憶,而這種記憶的特殊性取決于機器人所表現(xiàn)的形式,人類的語言符碼被新的、機器人的經驗穿透。
“太陽”的神性在人類的語言中被遺忘。“人類在不斷開發(fā)機器振奮人心的用途,而機器人卻通過祈禱太陽寄托最原始的信仰。”[8]在克拉拉的敘述中,太陽與自然一樣擁有生命,而人類對自然的污染與破壞是對太陽的不敬。這一信仰——對自然的敬畏熱愛與和諧共生的生存觀——在人類傲慢的無限擴張中已經被拋棄了,人們認為這是一個“AF的迷信”。同樣的忘卻還存在于“希望”中,當喬西病重,母親放棄了醫(yī)治,選擇建造一個機器人去復制、延續(xù)喬西,克拉拉卻一再堅持,“我們不應該放棄希望”,而“希望”在理性至上的人類那里已經成為一種感傷且過時的人性論調、虛無縹緲的陌生能指。在與克拉拉的對話中,父親最終找回了某種被拋棄的“希望”,雖然它并非出自血肉飽滿的人類心靈,而是出自一具冰冷的鋼鐵之軀。通過反向傳播,人類按照“面值”接受的死喻被機器人復活并重新定義。人類如果選擇相信機器人的“希望”,那么實際上已經認同了自身與機器共同分享了某種“人性”,語言在人類經驗賦予其的抽象性解構之后,重新回到了其循環(huán)遞歸的本質,“希望”的能指在機器與人類的經驗中共同流動。這一語言自然化本質的剝落同時宣告了人類獨特性賴以棲居的意識與文化領地的虛弱,其可能只是為了維護自身而虛構了一個人與機器對立的假設。人類在教導機器人語言的同時,機器人也在教導人類,人和機器或許只是彼此一個具有反身性的隱喻。
3 敘事的反諷
在克拉拉所講述的故事中,當人與機器的對立關系通過語言的反向傳播被解構,擺在眼前的卻是對一方成為/替代另一方的現(xiàn)實憂慮,并且這一憂慮最終在克拉拉承認自己無法觸及人心、延續(xù)喬西計劃中止的結局中消散了。文本的敘事形成人與機器和諧共生的開放未來,但是故事的結局卻是封閉的——作為商品被資本生產、使用、回收的“計劃性報廢”[9]從一開始就是機器人的命運,這個計劃宣讀出在人與機器生存的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夢:人與機器,如果沒有一方退居下位、一方完全的利他性,終究不能有圓滿的結局。結尾處克拉拉對人類感情的理解產生了諷刺性的效果,對人類情感價值的肯定卻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卑劣,它包含自私、偽善與冷酷,人之所以為人并不是因為意識的高尚,而是因為人性的脆弱[10]。作為機器人的克拉拉反倒被認為“是一個超越人類的人”[11],不僅因為她具有人性,還因為她克服了人性的弱點——她是一個完全的利他者,以后人類的形式重建了人文主義的價值。
而最深刻的反諷存在于克拉拉自身的敘事中,作為敘事者的克拉拉與作為人物的克拉拉之間的距離不僅印證了克拉拉逐漸飽滿的人性,還將機器人敘事徹底轉變?yōu)橐粋€“計劃性報廢”的語言游戲。如果說作為人物的克拉拉并不知道自己被訓練為商品出售、并不知道母親從接她回家起就想讓她成為喬西的替身、并不知道自己終將面臨“計劃性報廢”的命運,那么作為敘事者的克拉拉呢?在與人類數次交流后,克拉拉已經能全面評估人的欲望和沖動,體會并表達真實的喜怒哀樂。她以一個人性充足的狀態(tài)回憶那段往事,看見了故事中所有的諷刺,然而她卻始終沒有用人性的能力去評判任何人,這究竟是她的匱乏還是她的仁慈,是她的空洞還是她的沉默?如果克拉拉與人類的共情自始至終都是一種幻覺,那么它的情感并沒有比人的更虛幻。
4 結語
語言的反向傳播模糊了人與機器的文化對立,卻在實踐的維度上缺失了。敘事本身成了一次關于“計劃性報廢”具身經驗的演繹,展現(xiàn)了在這個科技不斷模糊人機界限的時代,寫作或閱讀機器人敘事本身的命運與意義——它尋求著一個并不封閉的結局,而始終未取得令人信服的完滿結果,在一次次報廢中將機器人的經驗更新納入人類的語言體系,回答關于后人類的新問題:語言能改變生存現(xiàn)實嗎?如果接受了機器人可以比人更具人性,我們會充滿期待還是滿懷焦慮地迎接奇點的到來?如何創(chuàng)造一個讓人類和機器人都能產生歸屬感的世界?
參考文獻:
[1] 莫尼卡·弗魯德尼克.走向“自然”敘事學[M].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1996:1-79.
[2] 尼爾·巴明頓.后人類主義[M].紐約:帕爾格雷夫出版社,2000:3-7.
[3] 多梅尼科·帕里西.機器人的未來:機器人科學的人類隱喻[M].王志欣,廖春霞,劉舂容,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6:1-35.
[4] 保羅·維利里奧.視覺機器[M].魏舒,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17-140.
[5] 杰拉德·普林斯.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M].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7-37.
[6] 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M].宋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30-98.
[7] 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298-383.
[8] 米蘭達·法蘭西.電夢,再訪[J].展望,2021(4):66-69.
[9] 亞當·帕克斯.太陽之下無新意:石黑一雄小說《克拉拉與太陽》中的計劃性報廢[J].外國文學研究,2022,44(1):13-27.
[10] 宋僉.譯后記[C]//克拉拉與太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387-392.
[11] 朱迪斯·舒列維茨.機器人光輝的內在生活[J].大西洋,2021(4):78-81.
作者簡介:劉旭彤(1999—),女,江蘇南京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當代西方文論與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