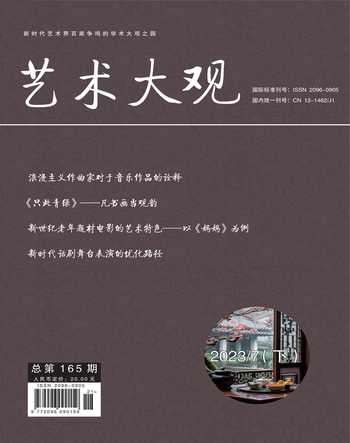文學與舞蹈關系研究
王曉雯
摘 要:文學與舞蹈,兩個歷史悠久的藝術形式,自古以來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我國古代藝術史的研究方面來看,我國自古就將詩、樂、舞看作是一個整體的部分,有著“詩樂舞三位一體”的說法,有著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的關系。而巧合的是,在西方,古希臘文化研究中也有著“詩樂舞同源”的思想。古希臘傳說中的繆斯女神,就監管著文學、詩歌、樂舞等眾多的藝術門類,足以見得詩歌與樂、舞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曾被視作一種混合藝術。隨著歷史的發展,它們逐漸發展成各自獨立的藝術方式,但彼此間互為借鑒、互為靈感,影響著各自的發展。
關鍵詞:文學于舞蹈;舞劇;解讀
中圖分類號:J7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21-00-03
在今天,舞蹈早就從自娛的功能轉變為表演的藝術,文學因為其敘事的特點和龐大的經典作品,成為舞蹈創作者創作靈感的來源。舞蹈編導根據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改編和創作,用舞蹈的表達方式來敘述文學的故事內容甚至是精神內涵,這樣的作品并不少見。國外有許多非常有代表性的經典芭蕾舞劇作品,浪漫主義時期的《仙女》(諾季埃的短篇小說《灶神特里爾比》)、《艾斯米拉達》(雨果《巴黎圣母院》)、《葛佩莉亞》(霍夫曼的童話《沙人》);古典芭蕾時期的《胡桃夾子》(霍夫曼的童話《胡桃夾子與老鼠國王》)、《唐吉訶德》(塞萬提斯同名小說)、《睡美人》(格林兄弟同名童話故事);如莎翁戲劇改編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等大量文學作品改編的芭蕾舞劇作品。國內以文學作品為基礎改編和創作的舞劇作品也不勝枚舉,如編導舒巧的作品《玉卿嫂》(白先勇同名小說)、《青春祭》(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胭脂扣》(李碧華同名小說);趙明作品《紅樓夢》(曹雪芹同名小說);還有近些年非常優秀的舞劇作品《家》(巴金同名小說)、《牡丹亭》(湯顯祖《杜麗娘還魂記》)、《青衣》(畢飛宇同名小說)等。
文學與舞蹈,雖然各自獨立,但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互為借鑒、互為創作靈感。發展到今天,它們之間的關系則更多的以“舞劇(舞蹈)解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呈現出來,它們之間的契合點落在了“戲”上。換句話說,就是以文學作品為基礎改編和創作舞劇作品(舞蹈作品)。在我國大量的創作改編自文學作品的舞劇作品中,筆者認為基本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刪繁就簡”與“刪簡就繁”
保留編導所要表達的精神內涵,對原著內容進行刪改,最大化地挖掘作品的可舞性。
無論是文學還是舞蹈、音樂還是繪畫,所有的藝術形式都源自人類的表達。文學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舞蹈則用肢體動作來表達。從各自的功能性來看,舞蹈無疑是弱于文字的敘事表達的。所以,當用舞劇作品來表現文學作品時,敘事往往成為第一難題,為了能把“故事”敘述清楚,將原著內容用舞蹈的方式表達出來,“刪繁就簡”便成了常態。在充分尊重原著精神內核的基礎上,挖掘原文學作品的可舞性。由于文學與舞劇的表達差異,編導在搭建舞劇作品結構和重組敘述內容時,往往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很大的刪改,從而舞劇作品在原著作品基礎上,衍生出新的情節或事件。
(一)有時是“人物”,有時是“人物關系”
現代舞劇《早春二月》(柔石《二月》)主要想表述青年的胸中志向,以較為抽象的方式表達出來,其題材源于柔石的小說《二月》。小說具有直白語言,描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胸中滿腔熱情改變中國陳舊面貌的知識分子難以得到理想的實現,從中凸顯其被束縛壓抑的惆悵的內心。舞劇《早春二月》的創作以原著人物為切入點,用舞蹈來展現人物情感,以人物情感糾葛為主要敘事重點。舞劇的改編,編導只塑造和保留了三個人物——蕭澗秋、陶蘭、文嫂。雖然原著《二月》的劇情并不復雜,沒有太繁雜的人物關系和糾纏的事件變化,但除男女主角外,對事件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還是有幾人的,如邀請蕭澗秋來小鎮任教的校長陶慕侃(陶嵐哥哥);文嫂的女兒采蓮;同為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因愛慕陶嵐不成而因妒生恨散布謠言的錢正興等。而舞劇中都將一并取消,而是運用了大量的群舞,虛實參半,來推進整個故事的發展。舞劇中看不到一點陶慕侃及錢正興的影子,原著中文嫂有兩個孩子,大女兒采蓮在原著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舞劇中被設計成一個有些夸張的玩偶。編導選擇從人物的角度入手,進行敘述和表達,將配角幾個人物淡化,著重塑造和描寫三個主要角色,并以大量的群舞進行襯托,使舞劇的敘事性更加弱化,著重于個人情感的烘托和表達,在這幾個部分的敘事中,需要觀眾對原著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將舞劇所要表現的事件弄清楚。
(二)有時是“情節”,有時是“細節”
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蘇童《妻妾成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主題思想上舞劇基本可以尊重原著中所表達的故事,同樣以“紅燈籠”作為作品的一個重要形式和伏筆,講述了一個封建社會中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對女人的囚禁與限制,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女人們彼此斗爭的生存原則,原著評論中提到“體現了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嘲諷”。舞劇將頌蓮塑造成了新思想中成長起來的新女性,但她的身上又有著十分對立的矛盾性,就是封建社會對少女的傳統教育使她有著封建思想的烙印,這種矛盾性也明顯地成了舞劇推向悲劇的推手,增加了武生的角色,將整個舞劇圍繞著三姨太與武生之間對愛情對自由的追求而展開,編導利用“愛情的美好”反射著“現實的殘酷”,使觀眾能夠更加理解和同情頌蓮的境遇。舞劇以頌蓮與武生被行刑為結局,封建制度扼殺了追求愛情的生命。但對比電影,更多了份凄美和壯烈。在形式上《大紅燈籠高高掛》也有許多編導創新的地方,如用皮影來表現新婚夜頌蓮奮力抗爭但無濟于事的可憐境況;用噴在白布上的顏料來表現三人被行刑的場面;西方交響樂融合民族樂器和京劇唱腔的中外結合的音樂表現方式,營造了悲涼的環境氛圍……這些手段都很好地利用了“舞”的方式來敘述“文學”的故事。
二、觸處機來
定位原著的中心思想,加入編導的感受和藝術創新。
藝術家借用舞劇中藝術形象身心的矛盾,對話人與社會的矛盾,讓關于人類、社會的悲憫之情在歷史和現實、經典文本和現代演繹中往來穿梭。《雷雨》是中國的經典話劇也是經典文學,對于改編作品來說,最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編導的敘事手法。當然,《雷雨》作為一個經典的存在,他的故事及人物形象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形式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們的記憶中了。[1]但要更好地利用舞蹈的動作語匯,來表達原著中所要體現的人物情感和精神世界,無疑是困難的。像編導自己所說,讓編舞家揚舞之長避舞之短不再解釋其中的故事和人物關系,只利用已經存在的框架自由表達之外,醇厚的人本精神力量才是感動大家的共同原因。所以筆者認為,對于這個作品來說,組成優秀作品的因素之一是成功的敘事,而成為經典則是因為編導在作品中體現了對女性更深一層的關注,使作品有了舞蹈的生命。
在對《雷雨》的改編中,1982年胡霞飛、華超二人編導的《繁漪》、2017年周莉亞編導的《YAO》,以及筆者所研究的王玫編導的《雷和雨》,這幾個版本都同樣選擇了以心理式結構為舞劇的主要敘事結構,以繁漪這個人物為中心來開展敘事。可以說繁漪這個人物是《雷雨》復雜的人物關系中的核心,對于作品中的幾位男性角色來說她是妻子、是情人、是母親,對于其他幾位女性角色來說她是情敵、是主人。而在《雷和雨》的改編中,將魯侍萍從原劇中的令人同情的被侮辱的角色,在舞劇中幻化成了第三只眼,成了冷眼旁觀者。在“她”的注視下,“我”在一步步丟失尊嚴再找回尊嚴。幾位女性角色在繁漪的心理空間中成了繁漪統一戰線的“盟友”,從而引發編導在第一層敘事中所主要想表達的內容,男權世界的受害者——女性。編導通過繁漪的幻想,營造了一個虛構的男權世界,在這個男權至上的世界中,女性是被動和壓抑的。通過男人對女人的注視,形塑了女人的自我理解。編導用這第三只眼揭示了愛情名目下女性自覺認同男性社會標準的愚昧。在繁漪痛不欲生時,在現實中承受無數苦難的充滿母性的魯侍萍依著高高在上的姿態要求繁漪自盡,其理由是女人的美就在于一種告別的姿態,寂寞讓女人美麗……整段由“我”的主觀想象而來,在繁漪的心理世界,男權的思想仍舊戰勝了女性。由此“我”“她”以及四鳳幻化成為男性理想中女性的模樣,搔首弄姿,以博取愛情。這段跳脫的舞段就是對男權的嘲諷和諷刺。編導通過對繁漪心理空間的建構,表達了女性角色之間的共性,使之取代了原著中女性角色彼此之間的矛盾沖突。通過繁漪在戲劇中的掙扎,編導延伸表達了自己個人強烈的女性觀。舞劇最終營造的大同世界,也正是跨越了原著的時代背景和性別地位,鼓勵女性勇敢沖破壓抑和束縛,在作品中給予女性充分的人文關懷。
三、詩情畫意
發揮舞蹈抒情之專長,營造意境放大想象。
舞劇《九歌》(屈原《九歌》)基本上保留了原詩的基調,但在風格上又與原詩保持了“距離”,利用舞美來營造作品原著中所體現出的意境感和情感性。作品以荷花和月亮這兩個元素,營造了一個詩意的古國楚地:湘水之中的荷花,神秘蜿蜒的蹊徑、莊嚴的圓月。事實上屈原原詩中并沒有荷花,但林懷民認為,荷花代表了復活再生,在這樣一部有史詩性的舞劇中,探討人類心靈自我救贖,不能沒有荷花。
舞劇以“迎神”開場,一群白衣素裹、手持荊條的善男信女出現在荷花池畔,在肅穆、清雅的氛圍中紅衣“女巫”出場了,眾人的荊條噼噼啪啪地甩向她,為了通靈,“女巫”瘋狂舞蹈著迎接東君。整場舞劇中,唯獨“女巫”的著裝最為“俗氣”——衣不遮體、舞蹈狂野,她象征的是俗世的欲望。那位戴著金色太陽面具的便是東君,即日神,他的身體也是金色的,象征著陽剛之美。屈原在詩里這樣描繪東君——“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無論東方西方,日神都是萬物生長之神,“女巫”在這里也象征著孕育萬物的大地之母,這是劇中敬天地的舞段,神圣而又充滿了原始的狂野。在楚人的心目中,湘君、湘夫人是一對配偶之神,所以湘夫人是全劇的愛情篇。湘夫人的出場最為莊嚴,有一種圣美,她高高地佇立在四人抬的轎子上,白紗素裹,頭上又披著長白紗。即便她戴著白色面具,你依然能感覺到她思念湘君那種臨風企盼的感覺和久候不見湘君依約而來的哀傷。“女巫”后來摘走了湘夫人的面具,這事實上就是愛情與欲望的一次反襯。云中君的演出是全劇中最考驗舞者的一個舞段,8分鐘的舞蹈中,云中君踩在兩位西裝革履的現代人肩上,始終腳未沾地。神話中云中君即云神,林懷民讓劇中每一位神都戴著面具,但透過云中君的面具你看到的是“兇神惡煞”,也許他并非神,而是操縱人的權貴階級。林懷民想表達的是神從未降臨,因此眾生的苦難只能由眾生自己去救贖。在司命的舞段中林懷民道出了人的生死,在“山鬼”的舞段他和我們談人類的孤獨與恐懼。最為震撼人心的是“國殤”和“禮魂”兩個篇章,從荊軻到岳飛再到鄒容,一個個中華英雄的名字莊嚴地念出來,低沉的旁白逐漸消失在近代蒸汽機火車嘟嘟的聲音中,最終八百盞燈的長龍連向九天銀河,是對英雄的祭奠與贊頌。
意象是中國文學領域具有文學意義的詞匯,是文學領域中詩詞創作的一個較核心的本質。文學作品中的靈感創作源于作者的意象,尤其是古詩詞類的文學作品。意象化更是詩歌較其他文學形式最大的區別。詩詞《九歌》的意象化貫穿全詩詞,經過改編為舞劇形式的《九歌》依靠舞者之間的配合,將云中君、湘夫人的情感通過與文學相呼應的情操進行詮釋,對于現代舞欣賞者無疑是意象化的享受,從舞劇中真切感受到舞蹈與文學遙相呼應的意境。《九歌》中的十一首詩詞將原始圖騰、神靈的俊美意境,敘事的詳盡,全部呈現,這些細致的對神的描寫,通過舞劇難以一一表現,因此借助該題材。同時,因為作品中對神祇細膩而微妙的心理描寫更是詮釋了敘事生動的一筆,屈原用極富文學色彩意境敘事的方式使得《九歌》具有動人的愛情情懷和不休的生命活力與張力。作品以“禮魂”作為最終章,將現場營造成一個壯觀的祭祀儀式,由八百盞燈的長龍連向九天銀河,是對英雄的祭奠與贊頌,讓純凈的靈魂在天國得以安息。《九歌》將神話故事以舞劇的形式搬上舞臺,將原詩詞中的“祭祀”文化呈現得極具震撼,利用意境化重構的舞劇改編方式,使舞劇有了有別于原著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四、結束語
以文學作品為藍本改編和創作的舞蹈作品,其價值和影響在于繼承和發揚原著作品的藝術特色和精神內涵。舞蹈利用自己“舞臺視覺藝術”的優勢來將文學作品“立體化”地呈現在舞臺上,編導在尊重原著作品的基礎上進行了不同層次的創作和改編,使原著作品以舞劇的方式重新呈現出與原著不同的另外一種藝術風格。舞蹈與文學是相融相通的,從古代時期各藝術門類互為一體的共生模式,直至今天各自獨立又百花齊放的態勢。舞蹈的存在既給文學提供合作材料,也不斷地從文學中獲取創作靈感。在這兩者的關系中,已從“共生模式”發展成為舞蹈對文學的“借鑒模式”。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舞蹈利用自己“舞臺視覺藝術”的優勢來將文學作品“立體化”地呈現在舞臺上。第二,無論內容與形式如何改變,一定要保留并表達出原著的精神內涵。這是舞蹈借鑒文學作品的基本,尊重原著的基礎上不斷地去追求形式、創造形式。第三,舞有盡而意無窮。用舞蹈的意象化與意境化將文學作品更好地呈現在舞臺上,只有這樣“取文學之長,發揮舞蹈之長”才是使舞蹈與文學的聯結、合作變得更有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湯旭梅.舞劇《雷和雨》對《雷雨》的解構與創生[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7(03):1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