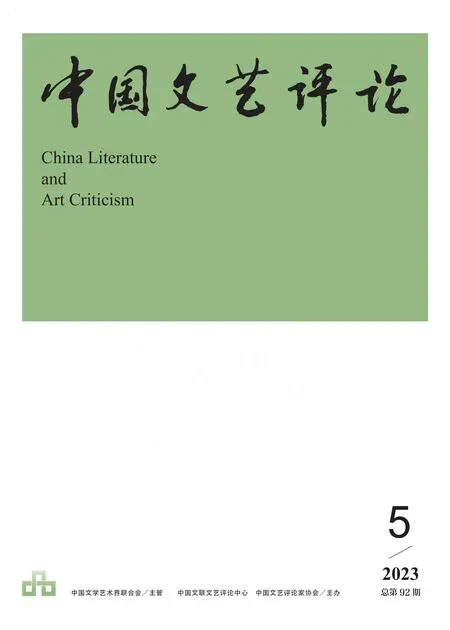惡的悲劇化
——論當前國產影視劇創作的一種趨勢
■ 李 寧
近年來,人物性格刻畫的復雜化、含混化成為國產影視劇的明顯趨向。在此背景下,國產影視劇中涌現出高啟強(《狂飆》)、葉文潔(《三體》)、祁同偉(《人民的名義》)、張東升(《隱秘的角落》)、辛小豐(《烈日灼心》)、王興德夫婦(《開端》)、李承天(《回來的女兒》)、曹建軍(《警察榮譽》)、沈墨(《漫長的季節》)等一大批性格復雜、善惡兼有的反面人物。[1]需要說明的是,將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分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是一種割裂式的做法。畢竟現實中的人性是復雜幽微的,文藝作品里的人物常常也是多元含混的。不過在影視劇中,尤其是類型化作品中,通常會有相對清晰的正反陣營的設置,以契合大眾審美趣味。因此,本文暫且沿用“反面人物”這一概念,來指代與正面人物相伴出現、體現非道德行為的人物。這些人物命運的共通之處在于有著或多或少的悲劇性色彩,并由此屢屢引發觀眾的同情與憐憫。其中像高啟強、張東升等人物甚至在網絡空間中被肆意地戲仿、玩梗,成為全民熱議的藝術形象。這一現象不禁令人深思:塑造令人共情的悲劇式反面人物,為何正成為一種潮流?本文嘗試總結當前國產影視劇中惡的悲劇化書寫的不同路徑,從社會文化與藝術觀念的角度剖解這一創作潮流的深層成因,并進一步探討其中亟待正視與糾偏的問題。
一、化惡為悲的兩種路徑
現實生活中的惡令人深惡痛絕,但文藝作品中的惡卻能引發復雜的審美體驗。作為文藝作品中惡的集中體現,反面人物相對正面人物常常有更為開闊的塑造空間。正面人物如果無法引人共情,可能就很難具備充分的藝術感染力。但對于反面人物而言,令人感到恐懼和厭惡是一種勝利,令人感到同情與憐憫又是另一種成功。
我國影視劇對于反面人物的塑造,常常有定型化、喜劇化等方式。前者是以惡寫惡,從政治或倫理批判的角度將反面人物塑造為與正面人物相對立的功能性配角,南霸天(《紅色娘子軍》)、胡漢三(《閃閃的紅星》)、安嘉和(《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李豐田(《無證之罪》)等都屬此類;后者則是化惡為喜,將反面人物塑造為可供俯視與調侃的諷刺型人物,例如中村下等兵(《舉起手來》)、高博(《人再囧途之泰囧》)、胡廣生(《無名之輩》)等。
當下國產影視劇創作則越來越善于化惡為悲,書寫反面人物有價值的事物及其毀滅的過程,以此呈現某種特殊的悲劇感。在具體的悲劇化書寫中,大致又體現為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展現自我美好本性的喪失。反面人物如果有純善的一面,這種特質又走向淪喪或毀滅,便常常會引發觀眾的憐憫之情。電視劇《狂飆》中,高啟強原本是安分守己、懦弱純良的底層魚販。由于遭受惡勢力的威脅而陷入絕境,他內心黑暗幽深的欲望才被點燃,不斷滑向犯罪的深淵。網劇《漫長的季節》中,由于父母雙亡,女主角沈墨自小被有著戀童癖與控制欲的大伯領養,在精神與身體上常年遭受后者的侵犯,大學時代勤工儉學期間又不幸受到不良商人的凌辱,最終陰暗人格被激發,走上手刃仇人的犯罪道路。
與《狂飆》《漫長的季節》不同,電影《烈日灼心》采取了另一條相反的路徑:先講述辛小豐、楊自道等幾位逃犯在隱姓埋名、亡命天涯的生活中所流露出的善良特質,以及他們混雜著懺悔、僥幸、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心理狀態與生存困境,再展現他們最終伏法的結局。這部影片有意逃離傳統警匪片“二元對立” “非黑即白”的敘事慣例,而是立足于道德的灰色地帶,將善與惡、罪與罰的游移混雜作為敘事的重點。通過先抑后揚的方式,影片中幾位反面人物長期流露出的懺悔心理以及撫養養女的善舉,也能夠有效地激發觀眾的同情之心。
另一條化惡為悲的路徑,是展現外在美好事物的毀滅。一些對于反面人物來說異常重要的美好事物的被摧毀,同樣可以營造人物的悲劇性。例如,在網劇《開端》中,公交車司機王興德及其妻子陶映紅之所以長期謀劃公交車爆炸案,原因在于無法接受女兒意外因車禍而亡、且在去世后遭受網絡暴力的事實。對于王興德夫婦而言,女兒的生命與名譽無疑是他們最為珍視的事物,卻均被無法抵抗的外部力量所粉碎,令觀眾很難不對其遭遇心生憐憫。
需要看到的是,僅僅展現出了自我美好本性的喪失或外在美好事物的毀滅,還不足以使反面人物具有更為充分的悲劇性。悲劇性的產生,在于悲劇人物所遭遇的困厄,更在于悲劇人物深陷困厄時所體現出的抗爭精神。正如朱光潛所說,“悲劇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諒的,就是怯懦和屈從”[1]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各種悲劇快感理論的批判研究》,張隆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152頁。。對于悲劇人物來說,無論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其反抗都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勇于面對命運、打破現實束縛的沖動,常常能夠體現出富有感染力的主體精神與生命價值。高啟強、沈墨、王興德、陶映紅等人物的悲劇性正在于此,只不過他們的抗爭僭越了法律與道德的邊界,體現出的是一種畸形的、非正義的崇高。
此外,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許多作品常常將反面人物的上述兩種價值的毀滅歸咎于家庭環境、社會體制、歷史創傷等外部原因,歸咎于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從而凸顯其命運的悲愴與無奈。電視劇《警察榮譽》中,警察曹建軍在岳父母長期的嫌貧愛富和冷嘲熱諷下養成自卑又自大的性格,由此才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從警界英雄到鋃鐺入獄的囚犯,再到最后自我救贖式的犧牲。電視劇《三體》中,作為地球三體組織的統帥,葉文潔之所以背叛人類,在于她在特殊年代里遭遇和承受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創傷。父親的死亡、家庭的崩塌、個人的磨難以及整個社會懺悔意識的匱乏,讓她切實感受到人性之惡,進而產生精神危機,只能將救贖與改造人類的目光投向浩瀚宇宙。可見,國產影視劇正是通過描寫反面人物的痛苦時刻,刻畫他們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的雙重身份,進而讓反面人物由善入惡的人物弧光更加引人共鳴。
二、進化的觀念與逾越的想象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種反面人物的悲劇化塑造,為何在當前的國產影視劇里成為一種潮流或趨勢?考察這一問題,既要考慮國產影視劇藝術創作自身的演進,也要兼顧社會語境的遷移和受眾趣味的變化。
以往國產影視劇的反面人物塑造,常常流于概念化、平面化,或淪為某種抽象的意識形態或倫理觀念的化身,或缺乏較為豐滿立體的性格。近年來,隨著我國影視工業化程度不斷深入、流媒體產業崛起,以及好萊塢、韓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的創作經驗的不斷滲透,中國內地影視劇的創作觀念也在不斷更新迭代,突出地表現為類型創新意識的強化與現實主義精神的深化。
一方面,類型創新意識的強化尤其體現在懸疑影視劇等類型的興盛上。在當前小屏觀劇的流媒體時代,為迎合注意力分散時代觀眾的趣味,同時規避小屏幕在呈現場面奇觀上的劣勢,創作者們越來越偏愛營造緊湊刺激的故事奇觀,由此導致懸疑等類型的流行。隨著《隱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優質作品引發強烈的市場反響,各大流媒體平臺與影視制作公司紛紛介入懸疑影視劇的生產中,尤以愛奇藝的“迷霧劇場”品牌為代表。由于可將懸疑元素與犯罪、推理、動作、科幻等各種類型進行自由嫁接,懸疑影視劇體現出十分廣闊的生長空間。這一類型天然地善于呈現人性的隱秘幽微,也就為人物性格的復雜化和反面人物的悲劇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另一方面,國產影視劇也在持續探索現實主義書寫的可能。這首先體現在創作者越來越傾向于從現實的邏輯出發去塑造人物,呼應現實生活本身的無邊與流動。現實中的人性原本就是含混幽微的,充滿了模糊地帶。正如高爾基所說,“人是雜色的,沒有純粹黑色的,也沒有純粹白色的”[1][俄]高爾基:《文學書簡》,曹葆華、渠建明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19頁。。與此同時,創作者也越來越傾向于將反面人物進行典型化處理,通過人物去映射或揭示社會現實的某些本質特征。例如電視劇《狂飆》中,如果說正面人物安欣是現代法理社會的代表,那么高啟強可謂傳統人情社會的代表。后者發跡的舊廠街這一熟人社會,又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運作機制隱秘勾連。因此,劇中安欣與高啟強的博弈與其說是簡單的警匪對決,不如說是經歷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之后,尤其是步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狂飆突進的現代化進程中法理精神與人情傳統的沖突。理解了這一層,才能體會到“高啟強”這一悲劇式反面人物的典型意義。
其次,反面人物的悲劇化潮流之所以出現,也與當前受眾群體對此類形象的喜好與認同息息相關。縱觀中西藝術史,文藝作品總是善于通過對惡的描畫,來呈現一種逾越的美學興致。如同德國學者阿爾特在《惡的美學歷程:一種浪漫主義解讀》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惡總是作為擾亂的角色出現,在這種擾亂中一種混亂不堪的結構得到了反映”[2][德]彼得-安德雷·阿爾特:《惡的美學歷程:一種浪漫主義解讀》,寧瑛、王德峰、鐘長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第316頁。。就影視藝術來說,不乏有黑幫片等樣式著力于塑造各式各樣的“反英雄”(anti-hero)或“惡棍主人公”(villain protagonist),以此為觀眾內心深層的越軌心理提供一種想象性的滿足。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當前受眾群體身處網絡社會/妥協社會的獨特語境中。一方面,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時代是解構化、分眾化、狂歡化的時代,網絡時代的受眾擅長以游戲的精神消解崇高、解構權威。“雪姨”“容嬤嬤”等一些熒幕反派角色近年來屢屢遭遇惡搞與調侃便是例證。這些反派人物在“鬼畜”視頻、表情包等各種“網絡迷因”(internet meme)中大肆流轉與傳播。在這一過程中,反面人物原本所攜帶的敘事內容與符號意義被消解,觀眾先前對于這類人物的憎惡之情也隨之淡化,甚至在傳播過程中開始與人物產生共情。這種文化土壤,使得互聯網時代的受眾對反面人物似乎持有更多的寬容與理解。今日受眾對完美的英雄與單薄的反派正日益產生審美厭倦,他們更期望看到現實的人性與人性的現實。
另一重不可忽略的語境在于,當下社會正日益走向“躺平”與“內卷”作為一體兩面、充滿了集體倦怠感的功績社會與妥協社會。韓炳哲認為,這種社會發展狀態的一大特點在于患有痛苦恐懼癥。如他所言,在妥協社會中,“痛苦被看作虛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蓋或優化的東西,無法與功績和諧共存。……痛苦被剝奪了所有表達的機會,它被判緘默。妥協社會不允許人們化痛苦為激情,訴痛苦于語言”[1][德]韓炳哲:《妥協社會:今日之痛》,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3-4頁。。對于妥協社會中的人們而言,悲劇化的反面人物恰恰能夠提供一種痛苦的快感與逾越的想象,以供他們紓解現實生活中的憂郁和苦悶。
在這方面,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的反面人物祁同偉的接受狀況就頗具代表性。劇中,出身寒門的祁同偉在追逐權力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不斷僭越法律邊界,最終走上了飲彈自盡的悲愴結局。這一人物形象身上凝結了攀附權貴的扭曲心靈和貧苦出身的小農意識,可以說是一個于連式的人物。因此,與劇中的其他反面人物相比,祁同偉的命運尤其引發了許多觀眾的同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許多觀眾從這一寒門子弟身上看到了一個底層人物試圖加入權力游戲、打破階層壁壘的野心,也看到了窮盡所有也無法更改的痛苦宿命。
三、如何把握惡的尺度?
然而問題在于,惡的悲劇化也潛藏著惡的正當化的危險。反面人物的悲劇命運使人同情、憐憫和惋惜,進而會令觀眾對其行為與理念產生認同感。如果對惡的尺度把握不好,善與惡、正與邪、美與丑的邊界也就變得含混不清。因此,有論者認為惡的悲劇化書寫是一種“大膽突進”的行為,“不但盡力于邪惡中去發掘反面人物‘否定的美質’及其自我毀滅,而且還因缺乏必要的道德限制往往導致認同紊亂”[2]張均:《論反面人物的敘述機制及其當代承傳》,《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第23頁。。人性原本復雜,但恰恰由于現實的含混,使得文藝作品在書寫復雜性的同時更應該劃出一條善與惡的大致界限,并進一步抑惡揚善。
那么在悲劇式反面人物的塑造中,該如何把握惡的尺度呢?在本文看來,在描寫人物復雜性、展現悲劇性命運的同時,創作者首先應當處理好人物的主導性格與次要性格之間的關系,以惡的主導性格來統領善的次要性格。從整體上來看,反面人物應當以邪惡、反動、暴戾、破壞等負面價值因素為主導,尤其是性格發展的后期,更應該凸顯其惡的主導性格。如果善惡的比重處理失當,就有可能導致反面人物的正面價值過于凸顯。
以電視劇《狂飆》為例,創作者雖然用了大量筆墨展現高啟強心狠手辣、胸有城府、唯利是圖的一面,但同時又用了過多的篇幅來描畫他重情重義的一面,導致后一種性格似乎更占據主導性。該劇一方面極力描畫他與老默、龍哥等人的江湖道義,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他與高啟盛、高啟蘭的兄妹情誼,這就讓高啟強儼然成為一種樸素真誠的傳統倫理觀的化身。例如,該劇不厭其煩地反復展現高啟強吃豬腳面的場面,這并非無意義的日常生活場景。實際上,正是通過反復對“豬腳面”這一飲食符號背后所負載的高家情感故事的追憶,高啟強這一不忘本、重家庭、有擔當的兄長形象也不斷地得以穩固。反觀安欣,由于創作者對他的家庭環境和情感關系的著墨太少,同時將人物塑造得有些執拗、理性甚至不近人情,以至于該人物的共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高啟強所壓制。
其次,在展現反面人物悲劇性命運時,創作者還應該處理好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間的關系,避免將悲劇的根源完全歸咎于外部因素。家庭氛圍、社會環境等固然是個體命運的催化劑,但個人的性格與選擇同樣也是重要推手。將反面人物全然塑造為某種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受害者,那既是一種忽略個體與社會之間復雜互動的取巧的現實主義,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豁免了反面人物應當承擔的責任,從而導致一種倫理的錯位與價值的誤導。
與此同時,在塑造反面人物時,創造者要意識到反面人物常常是作為正面人物的鏡像存在的,二者往往處在辯證互動的緊密關系中。因此,能否塑造一個更加令人信服的正面人物,以此制衡反面人物的共情力量,同樣顯得十分重要。當前許多國產影視劇恰恰在主要正面人物的塑造方面還有待提升。例如網劇《回來的女兒》中,女主角陳佑希作為正面人物就沒有展現出太多令人共情的特質。作為一位身世不詳、敢于挑戰秩序與常俗的孤兒,她一開始只身逃離福利院、千方百計尋找密友的行為展現出有情有義的性格。但隨著故事的發展,這一人物的矛盾之處開始逐漸顯露,不僅時常在沖動與冷靜之間、睿智與失智之間反復搖擺,人物行為還常常前后不一,很難讓觀眾產生情感聯結與價值認同。反倒是劇中的反面人物李承天所流露出的因愛生恨的真實性格,更能引發觀眾的憐憫與同情。
當然,對于觀眾來說,同樣也需要提升對悲劇式反面人物的理解。文藝作品中惡的書寫,說到底所要激發的應當是人們內心的幽暗意識。在“幽暗意識”概念的提出者張灝看來,幽暗意識有廣狹之分,狹義的幽暗意識指代的是我們需要正視與警覺人世間的種種陰暗面,廣義的幽暗意識則是指根據這種正視與警覺去認識與反思人性在知識與道德上的限制。就此而言,幽暗意識并不代表著對陰暗面的價值認可,其目的反而是以惡的剖解來反思善的可能,“是以強烈的道德感為出發點的”[1]張灝:《幽暗意識與時代探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頁。。帶著這樣的幽暗意識去看待當前國產影視劇中的悲劇式反面人物時,我們所惋惜的就不再是其惡的被懲罰,而是其善的被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