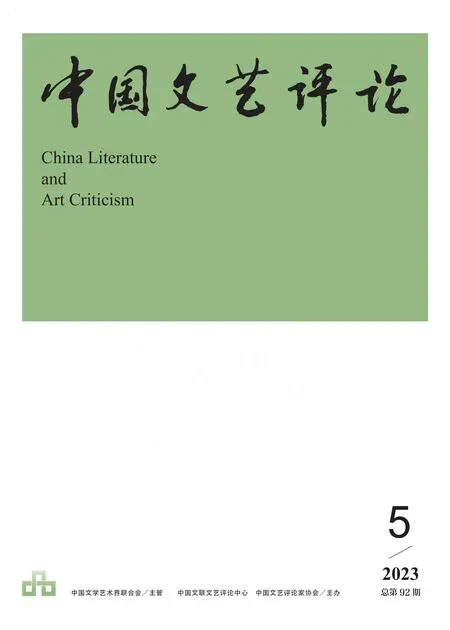中國音樂的傳統美學之維
■ 胡 南
傳統美學思想對中國音樂的孕育、形成有重要影響,是建構中國音樂的根本之一。從20世紀初期興起的“國樂”“民族音樂”到21世紀“中華樂派”“中國樂派”的出場,表明中國音樂并未出現所謂的“歷史的斷裂”,而是保持了文化與審美的延續性,其源頭可以回溯至中國古代“樂”文化的誕生。“中國音樂”之所以具有“中國性”,與其獨特的傳統美學精神有關,如何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統美學內涵是建構“中國音樂”的一個重要前提,離開了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傳統美學精神就沒有所謂的“中國音樂”。進而言之,“中國音樂”并非一個簡單的民族音樂技術構成問題,抑或地域性音樂文化問題,更不是一個簡單的與西方音樂相比較而存在的音樂流派問題,它主要是一個文化審美構成問題,即具有中國音樂美學的獨特性。具體而言,宏觀層面由物、器、象、意等范疇構成的中國音樂本體論,中觀層面由律、調、譜、器、腔、詞、曲、韻等構成的中國音樂風格論,以及微觀層面的作、唱、奏、演等構成的中國音樂技能論,共同構成了中國音樂的美學和哲學基礎。因此,本文擬從美學之元、技術之道與審美之境三個維度闡釋中國音樂的傳統美學精神。
一、聲、音、樂:中國音樂的美學之元
聲、音、樂等中國音樂美學的基本元素是構成中國音樂的前提性條件,它們在不同語境中有著特殊的倫理與審美意義。例如,六代雅樂因重倫理被尊稱為“正”,鄭衛之音因長于情感則被斥為“淫”,故有關“樂”的存在方式是傳統音樂美學研究的一個元命題[1]參見馮長春:《從“大音希聲”到〈4分33秒〉——關于“無聲之樂”及其存在方式的美學思考》,《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第92頁。,如何理解聲、音、樂及其關系,對于中國音樂建構有著重要的美學價值。
首先,聲、音、樂的關系體現了中國哲學對于“音樂”認識的層級化。[2]參見《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74-1081頁。“聲”是“音樂”的基礎,是最初級的和最原始的構成元素,體現“音樂”的自然屬性——美。“音”相較于“聲”,多了人的理性參與,是人將“聲”以某種組織排列的結果,是“成方之文”,基于“音樂”的社會屬性——善與自然屬性——美的相互妥協,貼近今天常識意義上的音樂概念。而“樂”則將人的社會性融合進入“音”發展而來,“音”轉向“樂”,是音樂的“善”抑制“美”,即將人性賦予音樂的結果,故具有人性的“樂”才能反過來節制人欲、啟發人善。聲、音、樂三者的內在關系則體現了中國哲學對音樂心理不同感受層次的認識,即通過對音樂審美層次的感知,將審美主體由低級向高級,分為禽獸、庶人、君子三類,呈現出一種深層審美認知的進階過程,即禽獸與音樂的關系就是作用于本能的“知聲”,眾庶與音樂的關系就是作用于情感的“知音”,君子與音樂的關系就是作用于道德的“知樂”。進而言之,聲、音、樂的關系反映了中國音樂哲學對于音樂藝術生成過程的反思,即人因有感而發后將喜怒哀樂之情顯現于外,并將音樂引起人的情感反應進行分類:一種是在聽覺感知上將哀樂的情感直接歸之于音樂,通過聯覺實現;另一種是由音樂而喚起某種情感但并不指向音樂,而是通過聯想實現。傳統文獻中“音者,聲之余也”“音出于聲”等論述,表明邏輯上“聲”先于“音”,抑或“音”從屬于“聲”。因此,聲、音、樂作為古代音樂美學的重要范疇,呈現為一種由低到高、由簡到繁的特征,有其自身的藝術哲學邏輯,輔以“興觀群怨”的傳統藝術方法論,滲透于文化發展、社會演變與音樂實踐之中。分立于三者之外的則是音樂本身話語的“時空場域”所決定的不同的所指,如在時間上有先后關系的“禮樂”之“樂”、“雅樂”之“樂”和“音、聲”之“樂”,就對應了不同歷史分期中的音樂觀。[3]參見李方元:《“樂”“音”二分觀念與周代“雅鄭”問題》,《音樂研究》2018年第1期,第45頁。
在歷史語境中,“樂”與“禮”并稱“禮樂”,受現代主義音樂思潮的影響,傳統藝術哲學中的“樂”因帶有某種神圣性、社會性和倫理性而被排斥在現代藝術哲學的論域之外。“聲”與“音”字源不同,二者合用可溯及老子的“音聲相和”,之后多為互訓。在現代藝術哲學語境中,“音聲”“聲音”/“音樂”/“音色”/“噪音”等范疇,看似與sound/music/tone/noise等詞匯對譯,但它們在中西文化語系中的所指不同,并非一一對應關系。例如,“音聲”在漢語中可表述為人聲、器樂與器聲,甚至將“心誦”“神誦”等聽不到的音聲也納入其中,是一種典型的聲音缺失而意義在場的表述方式,這種在場必須要與非在場和非感知結合在一起[1]參見[法]雅克·德里達:《聲音與現象》,杜小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1頁。,這顯然與聲波通過聽覺產生印象、具有必然在場的“聲音”不同。故“音”“聲”關系成為了學術界聚訟不已的論題[2]參見田耀農:《“音”、“聲”之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第36-39頁;田耀農:《再辨“音”、“聲”——兼答葉明春、王曄二君》,《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100-105頁;覃覓:《聲、音、樂、響辨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第79-81頁;胡瀟:《〈聲無哀樂論〉“聲”“音聲”“樂”諸概念的理解與認識上的分歧——兼及對三個頗具爭議問題的思考》,《音樂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9頁。,有兩種不同的思路。
第一種為“聲本論”,即主張“聲”為體,“音”為用。這種觀點認為“聲”具有自然的、客觀的物理屬性,“音”則具有人為的、主觀的社會屬性。[3]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音樂 舞蹈》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 舞蹈》,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第1頁。原文:“‘聲’泛指一切聲音,古者又稱之為天籟、地籟、人籟,其中包括各種噪聲;‘音’特指有秩序、有條理、有組織的聲音,相當于由樂音綴合而成的音調、曲調、音響組合等。”“聲”“音”之間,“聲”不僅代表了聲音自然存在下的狀態,更是“緣身性”發出的聲音狀態。[4]參見薛藝兵:《從人聲的緣身性本質探尋音樂美的本源》,《音樂研究》2020年第6期,第30頁。因此,音樂美的核心在于“以其自身而顯現”,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主張音樂是“自然之和”即是這種例證。故而,審“聲”即審美,具有兩個維度:一是時間維度,作為自然客觀的聲音、聲響,其意象的顯現取決于聽覺時長。因外顯的“聲音”作為可感知的符號,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著不同的含義——“在它自身經歷著的不斷變化中,它顯現并展示了時間性的存在”[5][德]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57頁。。一方面,人作為主體無論是聽到還是發出聲音,聲音對于人都會發展成為對象,并形成意味;另一方面,即人與聲音主客體關系所構成的聽覺共同體,往往潛伏著第三者即“聲環境”——由聲音構成的環境是多種聲音事件的組合,具體的某個音很難被從中剝離開。約翰·凱奇的《4分33秒》與道家的“無聲之樂”音樂觀驚人地相似,作品借自然之“聲”說“道”,充分利用了時間與聲響的關系,形成言外之意、話外之音,是在現實聲音之后的意義顯現[6]參見孫月:《“聽”見不在場的聲音——“內在諦聽”概念釋義及音樂作品實例解析》,《中國音樂學》2017年第4期,第125頁。,這種以“無聲”勝“有聲”的呈現方式顛覆了傳統認知意義上的“作品”,提供了新的音樂觀念。二是空間維度,藝術哲學意義上的聲音緣發于“人自體”,即人類身體本身就能自然而然地產生最美妙的聲音,是探尋音樂美之本源的重要研究對象。[1]參見孫月:《“聽”見不在場的聲音——“內在諦聽”概念釋義及音樂作品實例解析》,《中國音樂學》2017年第4期,第125頁。縱觀中國古代樂器的發展,從先秦的“貴人聲”,到唐朝的“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再到宋朝的“弦聲千古聽不改”和元朝的“賽歌喉傾倒賓筵”,從歌者、匏竹之序,凸顯了“人聲”的重要性,且一直為人們所推崇。這種“聲”大于“音”的“大音希聲”觀念,表明古人對聲音之道的遞進認識,發展出“漸近自然”的審美音樂觀,進而產生了以“反其天真”為根本的審美追求。這種以“聲”為體、以“音”為用的“聲音”觀念是中國傳統音樂美學的重要視角,為中國近現代新潮音樂、實驗音樂創作以及聲樂表演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二種為“音本論”,即主張“音”為體,“聲”為用。“聲”是人擊打樂器、歌唱并欣賞的復合概念,而“音”是“言”概念的異化。[2]參見國學大師:《漢字字源》,http://www.guoxuedashi.net/zidian/ziyuan_2383.html。“從甲骨文的字形看,‘聲’字的確是一個很‘熱鬧’的字:一只手拿著小錘敲擊古樂器‘罄’;一個嘴巴在唱著歌;‘耳’被包圍在中間,飽聽著這些聲音。”而“音”:“是樂聲,語音。與‘言’同出一源。”此時的“聲音”是我們聽覺對聲波的一種感知結果[3]參見韓寶強:《關于“音”的性質的討論》,《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3期,第28頁。,即“聲”是客觀存在的作為物理現象的聲音的集合,即審美客體,“音”是主觀存在的作為心理現象的聲音,即審美主體的感受,于內心生、于外有節。[4]參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2頁。這種觀點較之“聲本論”在中西音樂美學上更具有普遍性。以“物感說”為代表的儒家流派,認為“音樂”美是由于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感物而動”的結果,西方接受美學主張從文本(音樂作品)走向讀者(欣賞者)的觀點與此類似。中國音樂有自身獨特的藝術思維和藝術語言,是有組織的聽覺意象模式,傳統的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不僅是審美性的,而且是倫理性的,這種審“音”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我國古代的“五聲”和“八音”對“聲”與“音”有著明確的區分,這種區分不是簡單的類型學分析,而與中國哲學有密切關系。[5]參見[日]林謙三:《東亞樂器考》,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62年,第12頁。古代“八音”及其樂音引領著人們通過“音”去認識物質的狀態。前者今稱為“音律”,后者今稱為“音色”。在音階中,每一個單位稱為“音”[6]參見繆天瑞:《律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年,第1頁。,“音”以可感知的形式表現抽象的認識,并賦予它超越自身物理屬性的意義,表明“音本體”是將“聲音”作為一種對象、以人之“用”而動態發展的。二胡名曲《空山鳥語》、嗩吶名曲《百鳥朝鳳》均表現了作曲家善于發現和提煉自然之聲,并通過各要素的排列組合產生一種顯著的或獨特的音響模式,使外界的合規律性和主觀的合目的性達到統一,以獲得美的形成和審美感受。故而有學者認為“音”作為人為之聲,是樂的表象。[7]參見方建軍:《聲、音、樂及其思想技術涵義》,《音樂探索》2008年第3期,第19頁。根據這種觀點,音樂創作或演奏者以“音”表心,由“音”成象,借由主體的想象,以旋律、節奏等形式建構“樂之象”。“樂之象”與“人之心”相關聯,經過想象而獲取,是對感官之象的超越,表現為心物之間的相互構建和延展,具有時間與空間的超越性,即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知音、辨音、審音、用音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有意識選擇,外顯為從眼中之象、胸中之象到手中之象的審美生成過程,以獲得審美情感的愉悅。
“聲本論”與“音本論”各有其道理,但都忽視了“樂”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古人對“天籟”“地籟”“人籟”的審美追求,使得中國音樂包含了“聲音”美學的“內—外”“虛—實”“物—我”等多重屬性,這種“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境界,傾向于建構一種“聲音文化”。西方音樂往往趨向于表現“實有”,制造“意義”,注重音樂的實際效果和聽覺的復雜性,傾向于“聽覺文化”。兩種不同的致思方式使中國音樂和西方音樂從基底上有了分野,如“譚卞之爭”作為一種音樂批評案例,其分歧在于音樂的核心要義是其社會屬性還是自然屬性的問題,由此引申出音樂究竟是要感動耳朵還是要感動人的深刻命題,其實質是“樂”觀念與“音”“聲”觀念的關系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只有在中國傳統“樂”論、即在宏大的“樂”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才能化解有關“聲”“音”的爭端。換言之,如果以“聲本體”或“音本體”為基礎,那與西方樂派并無區別,惟有將經驗和形而上學并重以考察“樂”本身[1]參見張汝倫:《論“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26頁。,才能使“樂本體”將“聲本體”與“音本體”整合為一體,即美善與道技的融通才構成了中國音樂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樂”作為中國傳統的重要道德觀念決定了“中國音樂”的建構具有獨特的“中國性”。自古以來,“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天地、社會的介入使得音樂的審美功能及其愉悅感被壓制,音樂上禮天地,下牧百姓,內省自身,依附于施用者而不能單獨存在,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呈現為國家制度化存在,由鐘律而雅樂,成為中華文明六藝之樂藝基石。[2]參見項陽:《建立體系觀念,整體認知中國傳統音樂創制理論》,《中國音樂學》2020年第3期,第6頁。又因中國傳統音樂審美具有某種普遍性規范的“集體意識形態”傾向,進而促進了音樂在各階層之間精神的交流,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音樂審美觀開始與百姓日用之“情性自然”的審美觀念有了通融,豐富了“樂”自身。盡管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和精神訴求,但中國音樂家群體在藝術實踐層面往往離不開意識形態、抑或文藝指導方針的影響,不論是六代樂舞,還是解放個性的時代曲,抑或新時代的紅色音樂都成了國家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這種基于國家在場和中國經驗的藝術實踐奠定了中國音樂創作的特色和基礎。另一方面,“樂”作為一種具體的美育方式,其精神內核決定了“中國音樂”具有獨特的“倫理性”。“樂者,通倫理者也”,從“習其曲”“習其數”,到“得其志”“得其為人”,形象生動地詮釋了樂之興、立、成人的完美過程。中國傳統記譜法中的音值定性特征與聲調語言、儒家的社會人倫以及道家象外之象等要素密切相關[1]參見王耀華:《中國傳統音樂記譜法特點初探》,《中國音樂學》2006年第3期,第7頁。,表明“樂”是實施美育最有效的手段。“凡音之起”的論述不僅揭示了音樂與情感之間的復雜聯系,也揭示了音樂對于人性的能動作用,禽獸“知聲而不知音”,眾庶“知音而不知樂”,惟有君子俱知。而孔子對《韶樂》的評價表明音樂的境界不僅在于滿足審美需求,更需要具備維持社會倫理的力量。中國音樂的建構,借助國家在場將傳統的“禮”“樂”合一,將“樂”上升到國家制度。
綜上所言,“聲”“音”“樂”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觀的核心元素,通過“樂”整合“聲”“音”才能構成中國音樂的美學之元。首先,“樂”在層次上高于“聲音”,在本質上樂與聲、音是二分的,與感官聽覺上把握的“聲”與“音”不同,“樂”需要從精神層面才能予以理解和把握。其次,中國音樂得以建構的傳統美學基礎以“樂”為本體,并不意味著中國音樂就不重視“音”與“聲”的地位和作用,只不過在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下,“樂”相對于“聲”“音”更具有支配地位。最后,儒釋道雖然有不同的“樂”觀,樂、音、聲區分在特定語境中是有效的,但大多數情況下樂、音、聲三者是互用的。[2]參見劉承華:《“聲無哀樂”論證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音樂》2021年第6期,第103頁。隨著“當代性”的介入,“聲”“音”“樂”的轉化方式是中國音樂的內驅,激活了三要素的原有內涵,尤其以“樂”作為“聲”與“音”的聯系紐帶,形成了中國音樂的三個支點,其不可見的文化、精神、觀念等諸多形式通過這些支點的交互作用而得以顯現,從而構成了中國音樂的傳統美學根基。
二、筐格在曲,色澤在唱:中國音樂的技術之道
中國音樂的韻致體現為中國音樂元素(語匯、句法、技法、律動)和具有氣派、風格、情趣的美學標度的統一[3]參見喬建中:《創用傳統元素 自成一家新風——趙季平器樂作品中的“語匯”之思》,《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2頁。,最終外顯于音樂形態、演奏技法、藝術風格等技術層面。“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是中國傳統音樂表演理論體系中的核心,是在“人本”“樂用”等維度上形成的技藝觀。具體而言,中國傳統音樂既離不開由“律—調—譜—器”建構的整體音樂觀,也離不開由“字—腔—曲—韻”建構的感性音響模態,前者遵循中國傳統音樂的基本樂理,后者則表現中國特有的樂感。這種技術之美也是建構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美學基礎之一,主要回答中國音樂表現的獨特藝術風格即“中國風格”。一方面,它體現在單個的音、數、律的變化。與西方作曲技術中由“數”定“音”的嚴密邏輯思維不同,中國音樂傾向于因“音”定“數”的關照方式,其聲音的流動性穿梭于“音—音”縫隙之中。如中國傳統民間音樂中的“中立音”/“游移音”/“微分音”現象,這些隱藏于“鋼琴鍵盤縫里的音”恰恰成了中國傳統音樂韻味的關鍵,當代音樂在創作實踐中也十分關注這些依然活躍在民族生命中的、或有極大可能被再次激活的傳統音樂特質。另一方面,它表現在“音—音”的連接之間,其遞變量過程則顯現為一種審美感知形態。[1]參見王耀華:《中國傳統音樂結構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頁。音樂的意象外顯于字、詞、曲、律、調、腔、韻等要素的聯動之中,這些要素以某種確定的、可感知、可識別的形象化模型不經意地刺激我們的感官,或者說我們在鮮活的體驗中獲得了通感的刺激和統一。[2]參見[美]斯蒂芬·戴維斯:《音樂的意義與表現》,宋瑾、柯楊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311頁。因此,此處所言“技術”并非狹義的、作為手段的純工具性意義,而是指具有精神活性的“技藝”或“藝術”。中國音樂中的“樂”是在宇宙論和生存論中建構和發展的,從而使得中國音樂之“技術”既蘊含“形而上”——在理念層對音樂文化整體觀的承載,也包含“形而下”——在經驗層對音樂感性音響模態的把控手段和能力。
首先,“律—調—譜—器”建構了中國音樂文化的整體觀。中國傳統音樂藝術隱含著“律”的科學觀,律學問題發生在科學和藝術之間。[3]參見黃翔鵬:《中國古代律學——一種具有民族文化特點的科學遺產》,《音樂研究》1983年第4期,第111頁。由于律學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盡相同,形成了對“律”的數理性質進行研究的所謂“數理律學”和強調“律”的音樂實踐的“應用律學”[4]參見陳天國:《應用律學的概念和律在音樂實踐中的性狀》,《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第18頁。,其核心論點都在于音樂表演藝術中的“感覺尺度”介于“天(數)”“人(耳)”的參照關系。[5]參見黃翔鵬:《中國古代律學——一種具有民族文化特點的科學遺產》,《音樂研究》1983年第4期,第112頁。以此為基礎的律學具備了屬于中國傳統音樂特色的樂律學實踐標準,其產生背景大到關乎音樂與自然宇宙秩序,即“天道”;小到關乎音樂與社會功用問題,即“人道”。“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先賢嘗試將某種自然規律與人的行為活動相比擬,因而“物”“律”之和諧成為中國古代律學的核心思想。然而,隨著西方音樂文化的介入和中國音樂文化的輸出,全球音樂風格和內涵隨之豐富和深化,五度相生律、純律、十二平均律已成為國際通行的律制。這些樂律法與傳統記譜中的譜字有密切關聯,這種特殊性在當代中國樂派的建構中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中國傳統音樂的“譜”連器、律、調。[6]參見王耀華:《中國傳統音樂記譜法特點初探》,《中國音樂學》2006年第3期,第12頁。傳統記譜法具有“譜簡腔繁”或“骨譜肉腔”的特性,與語言聲調相關。而西方音樂記譜特征是“譜繁音定”,與“數的和諧”相關。為了適應“音”過程的音色、力度的變化,中國傳統音樂在記錄過程中摸索出了獨特的記譜法,諸如文字譜類型的減字譜、俗字譜、工尺譜等,而譜面上的留白也導致傳統樂音時值、速度上的“非確定性”和“即興性”——因為言語之間的音韻和韻味是一種直覺把握,是不可測量的,因而不可精確記譜[1]參見管建華:《東方音樂美學的“味”與音樂風格》《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25頁。,從而賦予了中國傳統音樂意義生成空間和藝術家的想象空間。例如,從演奏家的角度而言,丁承運、龔一和吳文光三位琴家演奏的琴曲《流水》風格不一,通過頻譜方法選擇音高、節奏、力度、音色四個因素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可發現三者的演奏風格各有側重、各美其美。[2]參見蔡際洲、劉曦:《琴曲〈流水〉演奏版本比較》,《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第127-138頁。從作曲家的角度而言,在中國傳唱了三百余年的《鮮花調》(又名《茉莉花》)與歌劇《圖蘭朵》發生了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原有的經典民歌曲調不再被視為“江蘇民歌”或“中國民歌”,而是成為了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世界音樂”。[3]參見楊璐璐:《民歌〈茉莉花〉近現代流傳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14年,第78頁。中國音樂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旋律”得以傳承與傳播,不論是聲樂作品還是器樂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一曲多用”和“萬變不離其宗”的藝術特征,它們在不同歷史階段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被接納而得以流傳。這種特殊的藝術現象是由獨特的藝術語言和表現形式所決定的,更是群眾文化認同和審美心理共同作用的結果,從而成為能夠代表中國樂派、為世人公認、具有中國風格的經典藝術作品。
其次,“字—腔—曲—韻”建構中國音樂的感性音響模態。中國音樂語言的獨特性在于由單個(字音)的音高、音勢借助人性化、色彩化的“聲”以某種規律連綴成“曲”,在由技而藝的過程中生成了“腔”,關于單音或音與音之間連接所蘊含的遞變量變化,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音腔”或“帶腔的音”。[4]參見沈洽:《音腔論》,《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第14頁。簡言之,線型流動的樂音構成與語言密切相關,也正是受各地區發音咬字的殊異,才形成了不同的地方藝術風格,使得中國音樂具有獨特的韻味和美學特征。例如:
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5][明]魏良輔:《南詞引正》,隗芾、吳毓華編:《古典戲曲美學資料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第91頁。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6][明]王世貞:《曲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7頁。
北曲以遒勁為主,南曲以宛轉為主,各有不同。[7][明]魏良輔:《曲律》,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5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5頁。
從上述文獻來看,其“腔”之數樣,“字”(詞)之疏密,“音”之舒緩以及“曲”之形態,構成了洞察地方音樂風格與流派的微分因子。因此,中國音樂的創腔、配樂都有一定的藝術規律。如在戲曲表演藝術中常以“字音”來定“腔”,“依字行腔”和“字正腔圓”成為了中國戲曲、說唱表演中的科學方法和重要美學范疇,而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器樂藝術,如京胡、板胡、大筒胡琴中的“托腔保調”手法都表明,聲樂與器樂的聯系與轉化,與語言音調與音樂音調、語義與非語義、人聲與非人聲幾組要素相關。[1]參見黃漢華:《言之樂與無言之樂——聲樂與器樂之聯系與轉化的美學思考》,《中國音樂》2002年第4期,第4頁。例如,郭文景創作的《戲》通過技法和音色最大限度發掘了三付鐃鈸,戲曲表演中的角色被他從唱腔旋律中提取出來,并從人物聲腔、語態、性格數個層面進行抽象化,從而擺脫舞臺表演中各個人物角色唱腔對于唱腔旋律的束縛,使得這些唱腔的旋律可以被能動地吸收進了三位鈸的演奏者的嗓音模仿之中。[2]參見皇甫慶玲:《郭文景〈戲——為3付鐃鈸和嗓音而作〉樂曲分析》,碩士學位論文,天津音樂學院,2009年,第12頁。
由此可見,中國戲曲藝術的聲腔美感來源于字的變化,而不同審美傾向的音樂是用組織音響構成的聽覺意象:一是實際聽到的聲音,二是想象的聲音,為我們建立了外在體驗和內在體驗的雙重性。中國音樂注重橫向的、線性旋律間的貫通流暢,講究樂音發展的自然過渡,這種聽覺意象決定了中國傳統音樂講究旋律線條美感和曲牌韻律之美,追求內在的意境。例如,被稱為南音之始的“候人兮猗”體現了線性旋律間的貫通流暢,通過“兮猗”等感嘆虛詞,使音樂呈現出流水般的“游動”感,情感借此得到了舒展。雖然短小精練,但顯露出一種精細纖弱的藝術風韻,表明中國傳統音樂不追求聲響在物理層的恢弘,而以旋律發展時所造就的韻律感為旨趣。中國傳統音樂在單音與旋律線性走向兩方面都注重婉轉而有余味的形式。單音內涵強調樂音呈現的遞變量,預示著“音—音”之間的過渡與連續處于某種漸變狀態,其本質是一種聯動反應,且聯動之間存在具有不確定性的模糊領域,這種“模糊音感”是我國民族音樂韻味賴以顯現的基本元素。[3]參見蒲亨建:《論“模糊音感”——中國民族音樂特殊韻味的內在機制研究》,《齊魯藝苑》2021年第4期,第4頁。這種“韻”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特有的“技術”和“樂感”,因而我們稱其為“技術之道”:一方面,音級自身功能指向的多重性導致我們在聽覺心理上的“不確定性”,如具體音高的量化(音韻)/“音”的游移等方面成為了窺視音樂風格的重要因子。如湖南花鼓戲+sol和+re兩音、秦腔苦音的bSi和+fa兩音,以及潮州音樂中的“重三六調”都存有一個共同現象,其中立音均出現在器樂演奏的中指指位上,與演唱者(發音)有直接關系。[4]參見羅復常:《略論“中立音”——中國中指問題》《中國音樂學》1993年第3期,第18-19頁。另一方面,語言節奏的律動導致了“氣”與“韻”的出場,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核心乃至“生命”。“韻”構成了傳統音樂藝術的靈魂,音樂之律動讓人感受到了“情感的節奏”和“想象的自由”。尤其是言語中的情感變化與音樂內部結構中的散、慢、中、快、散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作曲家趙季平創作了以“唐詩宋詞”及“詩經”為文本的系列藝術歌曲,《別董大》《幽蘭操》兩首作品保持著傳統文化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傳統手法與現代創作技法相結合的特征,既體現了藝術性與思想性,也具備了大眾可聽性。又如,王建中創作的鋼琴音樂作品《梅花三弄》融入了傳統的古琴藝術,受毛澤東《卜算子·詠梅》的啟發,將古代樂曲與現代詩詞進行了完美融合,有類似古琴音樂朗誦調的意味。藝術家在融合中華傳統美學的藝術實踐中培養的“樂感”進一步凝練出了審美的“氣韻”,“氣韻”在中華傳統文化語境中具有明顯的寫意性特征。[1]參見彭鋒:《氣韻與節奏》,《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6期,第16頁。例如,作曲家周文中獨創的“填白”“線條與對位”等技巧深受書法的啟發,“一氣呵成”的作品更是深受中國傳統陰陽思維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音樂美學觀念[2]參見潘世姬:《周文中 音樂書法家——從“蒼松”系列作品試論他的對位觀點》,《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24頁。,這種意義單位在音樂藝術中就是寫意,它既可以表現在“樂音”本身,也可表現在“樂音—樂音”之間,亦可超乎“樂音”之外。[3]參見彭鋒:《“之間”與“之外”:寫意音樂的結構分析》,《人文雜志》2021年第5期,第101頁。
總之,中國傳統音樂獨特的技術美學蘊含著樂理和樂感,其藝術風格則外顯于“聲音”。依據審美經驗的不同,我們在聆聽中國音樂的過程中,外顯于表演經驗層的“器(人)→器(人)聲→器(人)聲之意”[4]蕭梅:《響器制度下的“巫樂”研究》,《民族藝術》2013年第2期,第28頁。,進一步引申出了理念層的“直覺的聲音→依托工藝(發聲體)的聲音→關聯個性的聲音和風格的聲音→追究歷史的聲音”[5]韓鍾恩:《在音樂中究竟能夠聽出什么樣的聲音?——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第三研究》,《中國音樂學》2013年第3期,第99頁。。盡管中國音樂是一個龐大的音樂體系,從樂用角度還可區分為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和民間音樂;但總體而言,它們呈現出一種“人本”用樂觀,反映的是人對一切社會審美活動的審視,是一種意識和它的歷史本質的“顯象”,它既離不開審美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也不能脫離審美客體的制約。
三、意象、意境與氣韻:中國音樂的審美之境
中國音樂側重審美關系中的虛實相生、情景交融和物我合一,以獨特的方式呈現中國音樂的意象、意境與氣韻。在中國音樂中,“象”即音樂符號體系的演進,是不自知的,這種審美觀念與中國傳統哲學中將“人”的生命作為一個社會整體的概念密不可分。藝術主體在已有經驗中尋找現有的意義,根據認識的極限和經驗的積累賦予一個新的意義域,進而在藝術作品中轉化為新的“意象”。清代畫家布顏圖對“意”“象”的見解對于理解中國音樂的審美“意象”富有啟發,他說:“意之為用大矣哉!……在畫為神,萬象由是乎出。”[1][清]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204頁。盡管布顏圖論述的是繪畫中的“意”“象”問題,正如他所言“非獨繪事”,同樣可以闡釋中國音樂的意象問題。“意”是在宇宙中不斷生成與變化的,與“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象”因“意”而生,有“意”方能使“象”生動活潑。《高山流水》《瀟湘水云》琴曲中展現的山水意象雖然不可見,但能夠通過“感受”與“想象”而得。[2]參見鄭小龍:《論琴曲山水意象的生命精神》,《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1年第3期,第129-130頁。由此可見,“意象”美學既不限于藝術主體的主觀感受,也不限于萬物的呈現,而是在于主體和萬物的契合,這種契合在其他藝術形式中并不明顯,需要以“觀物”的形式獲取,而在音樂中卻能被直觀地感受。例如,汪立三創作的組曲《東山魁夷畫意》各樂章被命名為《冬花》《森林秋裝》《湖》《濤聲》,雖取意自東山魁夷的風景畫,但不能將其視為簡單的描寫性音畫,而是融入了作曲者自身豐富的情感和思想,尤其在《濤聲》里寫出了中國鋼琴音樂史上獨特的“鐘聲”,這種東方的“鐘聲”傳遞的是中國古代高僧追求理想的堅毅精神。又如,楊立青運用《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古典琵琶曲素材,在交響樂隊恢弘的濃烈聲響的基礎上,將現代音樂元素與傳統調式和聲結合,展現了楚漢戰爭的悲壯歷史,呈現出鮮明的藝術意象。
在中華傳統美學中,“意境”往往超越了“意象”。與追求無形的藝術“意象”不同,“意境”追求的是“溢出”的、極具彌散性的“翕辟成變”的藝術情感過程,即所謂“境生于象外”。藝術主體想象的“象外之象”包含著“意”的生成,從而使得中國傳統的“寫意”美學具有極強的闡釋力和較大的理論生成空間。[3]參見彭鋒:《意象的“雙重性”》,《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3期,第34頁;彭鋒:《“之間”與“之外”:寫意音樂的結構分析》,《人文雜志》2021年第5期,第101-102頁。由“象”表“意”思維方式指導下的音樂藝術,其“意境”的生成包含在對音樂形態、旋律、節奏、音色、音響、和聲與織體的處理之中。因此,中國樂派的藝術創造離不開中國傳統的審美意境的營造。“發竅于音,征色于象,運神于意。……意立而象與音隨之。”[4][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921頁。這種審美意境在保留了歷史文化內涵的基礎上,結合藝術主體和受眾的生命體驗,從而讓中國音樂藝術呈現出與西方音樂藝術完全不同的意境。例如,琴曲《瀟湘水云》之曲意來源于“瀟湘”的文學意象,“瀟湘”之意從文字化為音符、從視覺之意轉為聽覺之意,呈現出“恨別思歸”與“和美自得”兩種意境的統一。[5]參見李笑瑩:《古琴曲〈瀟湘水云〉意境探微》,《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01頁。中國琴曲的記譜法和表現形式具有獨特性,古琴演奏者演奏琴曲時不拘泥于技巧,追求彈奏后音的“余韻”帶來的縹緲“希音”之感,而對“天人合一”的追求決定了古琴音樂的“能指”超出了“所指”的范圍,從而體會到“聲韻兼備”與“弦外之音”的意味,即通過“琴道”領悟琴樂的意境。中國音樂由“意象”上升到“意境”中的“意”,經外化之“象”抵達內心之“境”,從而產生藝術共鳴,其生成過程主要由表演藝術家來完成,其音樂表現技巧是意境創造的重要手段,作曲家完成的音樂作品的“意境”離不開表演藝術家“演技”的營造,因意生技、由藝而道以表現藝術之意境。例如,李博禪創作的雙胡琴協奏曲《楚頌》,以動人優美的旋律、通俗平易的調性語匯、豐富多變的配器設計和清晰流暢的敘事,向人們呈現了“英雄”與“愛情”雙主題的架構,贊頌中華民族英雄英勇執著的品格、忠貞不渝的愛情。[1]參見金萾:《雙胡琴協奏曲〈楚頌〉的“敘事”方法及其意義》,《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第38頁。作曲家的創作意圖在“意”而非求“形”,因而在藝術語言上不再局限于追求“民族性”,而是以更加開闊的心態、更加自由的手法、更加自我的理解方式來抒寫內心所蘊含的文化。當然,中國音樂作品的“意境”也離不開欣賞者的審美體驗。換言之,音樂作品呈現的藝術意象和審美意境如果沒有得到大部分欣賞者的認同,它就是單向的表演。“意象”與“意境”的體驗過程使“以他平他”的審美感受看似不同,但實際上是每個人在不同生命節點對同一主題的循環往復,即每一種審美體驗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中都能找到對應的“地點感”和“時間序列”的聯結點,其邏輯有內在的一致性。在深厚的中華藝術語境中,欣賞者獲得中國樂派音樂獨特的審美經驗是無距離的。這種“無距離”性是自生的,不僅表現為審美空間與日常空間的融合,也表現為感官參與的“親近性”,即人之“六情”與樂之“六意”是同一的。當欣賞者通過一系列感官聯覺對物體或事件進行接觸后,又產生了外部世界的心理感受與情景認知。尤其在欣賞過程中,表演者與欣賞者的互動,使得靜止的場面“活”起來。這種“在場的”“不在場的”都受到統一生命情調統率的性情化在場,是營造者與接受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成為中國音樂審美經驗的主要來源。
中國音樂的“氣韻”主要體現為主體氣化身體的感性外顯,它將“氣”的生命性、精神性、節奏性與“韻”的精神性、形象性、韻律性高度融合統一。如前文所言,中國傳統音樂是在氣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律動和節奏的美感和韻味,是一種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是一種高妙意境和人生境界。在中國音樂語境里,音樂之“韻”需要通過“氣”的承載,以此展現出“聲之波瀾”的起伏和流轉,氣一以貫之,韻由氣生,氣由韻成,氣韻一體。可見,音樂中的“波瀾”是一種隱性的氣之運化節奏和諧的顯現,主要通過音與音、句與句之間造成的一種連續的、線性的“動勢”,這種動勢能夠制造出某種生命運動的“靈動之氣”和“傳神之韻”的美感,講究一氣呵成。如在表演藝術中,句與句之間的換氣,音樂結構里的“起承轉合”與自然的呼吸結合起來演繹音樂情緒的輕重徐疾;對于演奏者的氣韻而言,通過樂句與樂句之間的斷句、氣口來表現音樂的流暢及強弱變化,不論是“靈動之氣”“傳神之韻”,還是“感物而動”“人之心動”,都表明音樂的形成離不開我們自身的呼吸頻率和一種內在的節奏感,從“呼吸”到“聲音”是主體在尋找最適合自身的音樂性。回到問題本身,音樂是由人賦氣而生,氣韻自音樂表達中更多的是一種給節奏以自然情感貫穿而形成的律動感。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節奏”不是常規意義上理解的有規律的、對稱的節奏,其核心實質在于主體“生命的”一種氣化身體觀的自然表達,“節奏”只是代表這種“生命”具有可感知的屬性。因此,在中國傳統音樂中,節奏往往是“即興”的,是一種不受外界干擾、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無意”狀態,主體“乘興而作”的音樂[1]參見彭鋒:《詩可以興:古代宗教、倫理、哲學與藝術的美學闡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3頁。,旨在向往“音已盡而意有余”的審美體驗。因而,中國傳統音樂中的“韻”是有活力的、動態的氣化身體的律動和狀態。音樂中的“韻”是可感知的,但卻是無形的、不可言說的,我們只能從想象中獲得。所以,中國音樂人更擅長于用藝術語言模擬宇宙萬物運行之法,而不善于用邏輯的語言去窮盡它。音樂審美體驗中的“氣韻”將我們的身體當作時空體驗的環節,從身體出發感受不同時空的存在,并以此來丈量存在于物和人之意的審美距離。
綜上所述,意象、意境與氣韻構成了中國音樂的重要審美境界,中國音樂的藝術實踐應作為“創造美的技能”,成為調度“象”與“意”的中介,以“立象”為根本,由其出發,展現所立之處的某種“意”。中國音樂之所以是中國的音樂,是“意”與“象”的統一,而這恰恰是其有別于西方音樂美學的獨特之處。中國音樂的藝術實踐應當傳承“以象呈意”或“以象達意”的傳統表現方式,從而更好地明確自身的藝術身份和發展道路。
四、結語
中國音樂的美學建構離不開傳統音樂中的聲、音、樂美學三元互為體用的辯證關系。相較于西方音樂,中國之“樂”與“禮”之間相輔相成、相融相生,其國家意識更加濃厚,這種獨特的文化圖式和審美范疇構成了中國音樂話語的邏輯起點。中國音樂的美學建構離不開具體的音樂要素構成,諸如由“律—調—譜—器”生成的形而上音樂整體文化觀,以及由“字—腔—曲—韻”等各要素聯動構成的形而下中國音樂技藝風格外顯的支點,二者的貫通構成了“中國音樂”的特性,并期待現代音樂創作將其傳統美學精神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音樂的獨特性取決于不同的審美視角,意象、意境和氣韻是中國人對于身在其中的整個世界的態度和覺解,以及藝術主體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觀照、組合事物的態度,尤其“意立而象與音隨之”“慎以所感”構成了中國音樂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和內核,這種無間距的審美境界構成了中國音樂的核心。當然,傳統美學豐厚的思想是中國音樂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如作為傳統共性的“和”“美善合一”等問題同樣值得關注。本文受限于篇幅,故不予展開。中國音樂及其美學精神的“當代性”是在傳統中孕育和成長的,回應中國音樂與當代審美追求的問題不僅要立足于中國音樂“情本體”“樂感文化”等藝術哲學傳統,更需要透視經典音樂作品,探討其藝術風格和審美規律。“當代性”的提出也不意味著“傳統”的落幕,與之相反,多元文化格局下的藝術介入和沖擊使得“中國音樂”及其傳統美學思想的研究顯得更為重要,它叩問的是在國際語境中,中國音樂陷入體制困境的“傳統美學”之維再出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