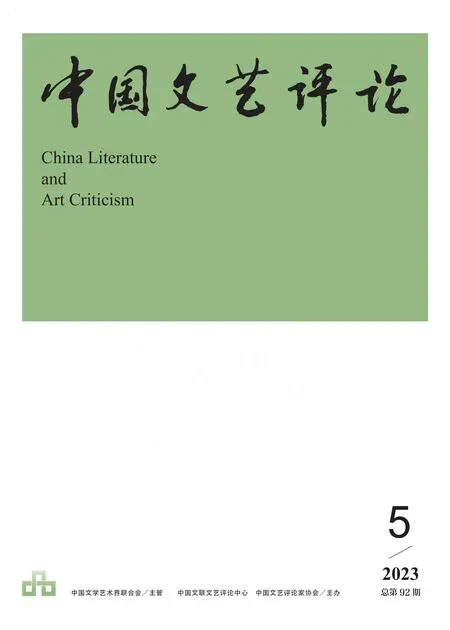中國傳統藝術主題的跨媒介屬性及其哲學基礎
■ 王一楠
古今雖殊,其跡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
——劉晝《劉子》[1]林其錟編:《劉子集校合編(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7頁。
一、“異”與“同”:中國藝術主題研究中的張力
在地理空間的疊印與文化時間的流動中,圍繞名士、文本與名勝,一些經典主題在中國藝術傳統中浮現出來,如“赤壁”“瀟湘”“桃源”“輞川”“蘭亭”等。于當下社會而言,這些傳統資源不僅成為生長復雜歷史想象的土壤,而且被寄托了一種可能的生活向度。顯然,意義的增殖并非我們這個時代的獨創,必有一脈相承的內在意涵賦予經典藝術主題以不竭的當代性,使之獲得不竭的“新”闡釋。而在經典地位的確立過程中,這些藝術主題往往跨越了單一的藝術媒介與藝術門類,依托文學、書畫、曲藝、器物乃至現代的新興載體分衍出多樣的形式。多樣性與穩定性成為這類藝術主題的基本特征:所謂多樣性,既指同主題有著多元的創作者、持續的創作時間和分散的創作地域,又指前者帶來的結果——表現方式的多樣性;所謂穩定性,是指即便對這些主題的表現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不斷開枝散葉,它們依然呈現出相似的、具有公共性的、甚至代際相傳的表現程式。后一特性是這些多樣的表現被歸入同一藝術主題的原因,同時意味著這些“萬變不離其宗”的程式存在相對固定的審美價值,從而在相當長的時間中葆有藝術生命力。
藝術主題的多形式分衍突出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門類與媒介的跨界特性。在“詩書畫印”并舉、“詩樂舞戲”互涉的中國傳統藝術觀念中,不同媒介被認為有著水乳交融的聯系。但是,對主題自身而言,“多樣”與“穩定”本是二律背反的關系,在這樣一組命題的沖突中,各異的媒介形式是否能夠引發共通的審美體驗?它又如何可能?無論對于認識中國藝術主題的深層價值,還是細察總是停留在“統而言之”的中國藝術媒介觀而言,這一追問都是必要的。“異”與“同”的張力理應成為主題研究的關捩之處,但既有討論往往著眼于媒介的外在表征,并進展為不同表征之分析、比較,而未在原理層面對中國藝術媒介的共通性和此一普遍觀念的來源予以辨析。這正是本文的出發點。事實上,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不僅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學科體系與美學話語體系的基礎性工作,而且呼應著當今世界藝術話語場的變革,在這重意義上,無論認為本文的落腳點是“當代問題的歷史淵源”,還是“歷史問題的當代語境”,都將是恰當的。
二、“藝格敷詞”(ekphrasis)的啟發與疏漏
新媒介的涌現、不同物質形態的跨界借用與融合是20世紀西方后現代藝術的重要表現之一,也向藝術理論界提出了一個新的時代議題,即“跨媒介”(intermedia,也稱“媒介間性”)問題。作為源自實踐的呼聲,“跨媒介”一詞最初來自20世紀60年代激浪藝術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創作宣言,他在其中預言媒介的壟斷會隨社會階級差異的彌合而被打破,并倡導藝術創作應為媒介的先天未決性保留空間。他的同道者,如菲利普·科納(Philip Corner)、約翰·凱奇(John Cage)、白南準(Nam June Paik)等人,積極探索將音樂、雕塑、拼貼畫、舞臺藝術、影像藝術與行為藝術混合并置的可能性。因此,媒介之間的混合、互補、置換與轉化也成為一個突出的理論生長點,引發諸多西方學者的興趣。
在跨媒介研究的潮流中,回溯其建構歷史的熱情將“藝格敷詞”(ekphrasis)重新帶回當代視野,并使之成為重要的討論分支。伴隨著西方理論界對媒介表征之認識進路,“藝格敷詞”的意涵實際上經歷了多次的歷史轉換。而對創作實踐的長期觀察與總結,使這一術語逐漸對當代跨媒介藝術產生了廣泛的統攝作用。盡管國內學界對這一西方理論研究的前沿議題已有很多介紹,卻往往忽略評估其本土化的理論潛力,即這塊他山之石是否有著“為我所用”的價值,是否能為厘清中國藝術主題的跨媒介屬性提供可資借鑒的方法與視野?答案是肯定的——盡管它不是不言自明的“萬金油”,而是幫助我們認知中國傳統藝術主題之多樣與穩定特質的“敲門磚”。
“藝格敷詞”的意涵變遷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它最初源自古希臘,本指對城邦公民和智者進行的一種修辭學訓練,其目的是達到把主題描述得活靈活現、仿佛就在聽眾眼前的效果。在這一時期,演講和辯論具有的激發想象的能力對該術語作出了規定,這不但不涉及藝術作品,甚至主題與內容都是第二位的。只要這一敘述刺激了觀眾想象力的運作,使他們仿佛看見了圖景并被激發起記憶中既有的認知和體驗,便可被稱作“藝格敷詞”。[1]參見Ruth Webb,“Ekphrasis Ancient and Modern: The Invention of a Genre,” Word & Image, vol.15, no.1(1999), pp.7-18.在第二階段,隨著書面語言的發展,“藝格敷詞”逐漸從口頭表達演變為一類能夠生動描繪對象的文學體裁的代稱。具有典范意義的文本隨之樹立,荷馬(Homer)在《伊利亞特》中對阿基琉斯之盾的敘述便是其中之一。[2]這是一個充滿想象性敘事與描述的文本:“(神匠在盾上)還鑄出一片國王的屬地;景面上,農人們/正忙于收獲,揮舞鋒快的鐮刀,割下莊稼,/有的和收割者成行,一堆接著一堆,/另一些則由捆稈者用草繩扎綁,/一共三位,站在稈堆前,后面跟著/一幫孩子,收撿割下的穗稈,滿滿地抱在胸前,/交給捆綁的農人,忙得不亦樂乎。過往亦置身現場,/手握權杖,靜觀不語,站在割倒的稈堆前,心情舒暢。/谷地的一邊,在一棵樹下,使者們已將盛宴排開——/他們殺倒一頭碩大的肥牛,此刻正忙著切剝。與此同時,婦女們/撒出一把把雪白的大麥,作為收割者的午餐。”[古希臘]荷馬:《伊利亞特》,陳中梅譯,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449-454頁。但這個術語如此小眾,并未引起太多關注,直到14世紀,它才又受到部分人文主義者的青睞,被用來指代描述藝術作品(特別是造型藝術)的文學形式。可以看到,在“藝格敷詞”的古典起源中,它指向的是一種“敘述”(narration),而在14世紀的定義中,它已經演變為了一種“描述”(description)。二者的區別在于:敘述處理的是原發行為或動作(action),而描述則預設了被描述的對象(object),進而指向作為主體存在的藝術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藝格敷詞”在當時備受看重的詞源核心是“完滿地講出”(To tell in full)[3]參見Ruth Webb,“Ekphrasis Ancient and Modern: The Invention of a Genre,” Word & Image, vol.15, no.1(1999), p.13.,這使本來作為修辭的“描述”潛在地獲得了與藝術作品親密無間的通達性,或者說,某種替代性。但在文藝復興之后,這一內涵空洞的概念再次經歷了漫長的沉寂,直到穆雷·克雷格(Murry Krieger)于1965年在愛荷華大學現代文學研究中心發表的會議論文將它重新引渡回學術視野[1]參見Murray Krieger,“The Ekphrastic Principle and the Still Movement of Poetry”, in The Play and Place of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67, p.124.,標志這個術語的生命周期進入第三階段。真正使這個術語煥然一新的是米歇爾(W.J.T.Mitchell),他在《圖像理論》一書中對其進行了兩方面的讀解:若狹義理解,“藝格敷詞”是一類相對小眾的文學樣式,特指描述視覺藝術作品的文學;若廣義理解,“藝格敷詞”指的是對視覺再現的語言再現。[2]參見[美]W.J.T.米歇爾:《圖像理論》,陳永國、胡文征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后一種理解方式經過米歇爾的強調與闡發,又將同一表現對象在不同媒介中疊合、轉化的色彩注入到“藝格敷詞”的意義世界,這使“藝格敷詞”成為符號學視角下適用于指涉媒介間性的綜合話語,與當代藝術的媒介屬性產生了互文的效果。
我們發現,這三種意義層面上的“藝格敷詞”在中國傳統藝術主題中均得以發生。篇幅所限,此處僅舉一例說明。北宋文人蘇軾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以他的《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文本為直接來源的“東坡赤壁”主題自宋代起延綿至今。該主題的跨媒介特性與“藝格敷詞”的關聯首先在于,作為源頭的詞賦具有激發聽眾想象的能力。如南宋詩人王十鵬在《梅溪集》所說,“讀公赤壁詞并賦,如見周郎破賊時”[3]水賚佑編:《蘇軾書法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第1081頁。,從文本的具象內容來看,《念奴嬌·赤壁懷古》至少塑造了“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英雄形象和戰爭場面,《赤壁賦》與《后赤壁賦》至少塑造了“我”與客人重訪傳說中的三國故地的場景。由于通曉凝練的語句誘發并匹配了讀者腦海中既有的對三國風煙的認識,詞賦因此帶來了視覺的通感,這也為圖像的再現提供了原始的動力、預留了巨大的空間,由是契合了“藝格敷詞”的原始內涵。在第二層面,除大量的書法作品外,還有百余幅創作于北宋至清初的“東坡赤壁”繪畫留存至今,而圍繞“東坡赤壁”書畫的題跋行為與留存于畫史當中的、對這些作品的著錄構成了對該主題圖像的新的文學描述。所以,對題詩、作跋、品評、記錄這一中國古代常見的藝術再書寫現象而言,“藝格敷詞”的狹義定義同樣具有解釋效力。在第三層面,由于“東坡赤壁”主題歷史中有著豐富的多媒介轉譯現象,不僅其圖像的形制涉及長卷、立軸、小品、冊頁、扇面、石刻、鏡面、器皿等,作為原始文本的《赤壁賦》在南宋初年便被配樂歌唱,還被譜成琴曲流傳至明清,同主題的戲劇則至晚在元代便已出現,這一現象適配于“藝格敷詞”的當代語境。顯然,以“東坡赤壁”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藝術主題能夠成為、并且理應成為當今跨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對象。
但借助西方話語工具分析中國傳統的藝術實踐并止步于逐一匹配的層面,極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作為舶來語的“ekphrasis”長期以來并不具有統一的內涵,而在既有的中文語境中,它不僅被翻譯作“藝格敷詞”,還被譯作“仿型”“符象化”“藝格符換”“圖說”“繪畫詩”等,這些譯名的導向性并不一致,多數僅勾勒出詞源歷史的部分意涵,或預設了對不同媒介的關切。對試圖探究中國藝術主題的讀者來說,舍近求遠地借助這一概念勢必會帶來困惑。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米歇爾對“藝格敷詞”的闡釋存在一定罅漏。他從媒介的共同性出發,認為“一切藝術都是‘合成的’藝術(既有文本又有形象),一切媒介都是混合媒介”[1][美]W.J.T.米歇爾:《圖像理論》,陳永國、胡文征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2頁。,文學和圖像無法保持純粹性,特別是圖像同樣具有議論、抒情、敘事等過去被認為只屬于文學的功能,媒介的差別體現在藝術的符號、形式、材料和運作機制方面,但在對共同對象的表達中,它們不意味著本質的區別。不過米歇爾也強調,每一種媒介載體都具有排他性,意圖僅通過自身完整地展現對象。若將主題研究置于這一理論框架當中,尚有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例如,在存在符號、形式、材料、運作機制等差別的情況下,不同媒介如何能夠“完整地”展現同一主題?這種完整性是否能在媒介差異的基礎上導向審美空間的一致性?至少,現有的“藝格敷詞”媒介理論以表征的相似性掩蓋復雜的審美問題,無法彌合主題研究中勢必要面對的“異”與“同”的張力,而藝術的表達形式與其引起的審美體驗之間缺少銜接,這一模糊地帶的存在又使得不同的藝術媒介之間仍然壁壘高筑。盡管此路不通,但“藝格敷詞”仍如迷宮中的指示牌,提示我們應回到中西方藝術歷程中有關媒介與審美通感的認識理路,借助歷史的縱深視野重估今日的藝術媒介與跨媒介問題。
三、媒介神話的生成路徑與“詩畫一律”的意義轉換
跨媒介理論的歷史發生場域始于文學與圖像的關系認識。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曾提出“畫是無聲詩,詩是有聲畫”的看法,賀拉斯(Horace)在《詩藝》中也曾寫下“詩如畫”的字樣——這些殘章斷句,均表達了“詩畫相似”的意涵。但是,德國美學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著名的《拉奧孔》一書中終結了這種對詩與畫之間簡單對應關系的描述。他認為造型藝術在媒介、題材、感觀上都與文學藝術不同:首先,造型藝術只限于描繪可見事物與美的事物,而文學卻有多種審美范疇;其次,造型藝術是空間性的,而“詩的意象是精神性的”,“這些意象可以并存在一起而不至互相遮掩互相損害,而實物本身或實物的自然符號卻因受到空間與時間的局限而不能做到這點”[2][德]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1頁。;再次,造型藝術只能通過視覺被整體、霎時地把握,而詩卻富于記憶和想象。萊辛為不同的藝術媒介確立了各自的合法性,也決絕地為其劃分出了互不侵犯的領地。
從萊辛開始,基于形式功能來認識媒介差異在西方藝術歷程中有著持久的影響力。對媒介形式的純粹性與獨立性的追求與18世紀現代藝術體系的發明密不可分,而另一方面,現代藝術學科與藝術門類制度的建構也必然要求媒介的分立。因此,形式主義美學家羅杰·弗萊(Roger Fry)旗幟鮮明地將媒介差異視作其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的起點,他說,“詞語只能喚起模糊而又籠統的意象,而畫家卻被迫做到更加精確。”[1][英]羅杰·弗萊:《弗萊藝術批評文選》,沈語冰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273頁。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更激進地指出藝術的本體就在于“有意味的形式”。盡管許多當代藝術家努力打破門類的傳統邊界,用難以被直觀把握和知性理解的復合裝置為自己的作品爭取某種多義性,但針對媒介的顛覆性宣言與藝術實踐中對媒介的刻意疊加,反而將其推上了更高的神壇。理論界同樣存在這種傾向。近年來興起的媒介美學便將鮑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觀點“靠媒介來思索,靠媒介來感受”重新引回公眾的視線。媒介逐漸被認為是人的延伸,是知覺得以成立的前提和一切技術與工具的基礎,從而也是結聯主客體的橋梁和理解主客體的中心,媒介甚至成為世界呈現其固有結構的基礎。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相關著作更使媒介具有了一種本體論的意味,他無限放大了媒介帶來的感官差異及對人的認知影響,提出了“媒介即訊息”的著名論斷。有關媒介的神話隨著實踐的熱情在幾次理論熱潮中接近成型,但這一潮流也向我們提示西方學界或許缺乏討論媒介審美通感的話語基礎。
以上判斷在跨文化視野中或許能得到更好的觀照,因為對媒介差異的強調始終未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主流的藝術觀念。介于符號和圖像之間的漢字體系在其自甲骨文演變而來的歷程中保留了象形特征,“文圖同源”的看法奠定了關于媒介的認識基礎,并施加著一種源頭式的思維影響。由于圖畫具有形象直觀的作用,圖譜與經史常以“左圖右書”[2][宋]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頁。的方式并置,共同被視作成教化、助人倫的最佳手段。當然,圖像也曾被認為是比文字低一等的媒介,東漢時期的思想家王充便認為圖畫僅保留了形象,但文字可以記載言行、事跡、思想,所以更勝一籌。[3]“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漢]王充:《別通篇》,黃暉編:《論衡校釋》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96-597頁。這種重言輕形的看法預示著繪畫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實行教化的輔助工具。但繪畫的地位還是經歷了緩慢的抬升。南朝謝赫所謂“圖繪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1][南朝]謝赫:《古畫品錄》,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355頁。,唐代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中說的“其于忠臣、孝子,賢愚美惡,莫不圖之屋壁,以訓將來。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跡,墨匠儀形”[2][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錄序》,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6頁。等記錄,都對繪畫記錄形象和傳遞道德觀念的作用予以肯定。而皇家帝王“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3][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第56頁。的行為,進一步使圖傳經史的傳統通過畫院機構及相關藝術家的意識形態化創作得以加強。當張彥遠宣稱“書、畫異名而同體”[4][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第1頁。時,他不單是論及施行教化對語言和視覺的雙重依賴,同時也對軒輊難分的文學與圖像功能進行了確認。
盡管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從文獻記載還是圖像資料來看,早期中國的文圖并傳現象主要基于文、圖二者在形象表達方面的互補性,沒有自覺涉及審美經驗的層次,但這為宋代出現的“詩畫一律”說預留了充分的理論空間。“詩畫一律”說是中國美學史上最有影響力的藝術觀念之一,它在媒介認識論領域開辟出一條非對象化的道路,為彌合不同媒介的差異提供了一種中國化的解決方案,也為探討藝術主題的多樣性與穩定性提供了更切合的認識框架。
“詩畫一律”理論最直接的來源是蘇軾的《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一詩。[5]“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宋]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525-1526頁。這首詩宣言式地提出了全新的藝術評價體系,從創作和鑒賞層面指出詩與畫具有共同的主體要求和審美標準,而將長期被視作繪畫突出特征的“形似”排除在新的評價體系之外。蘇軾還有許多有關“詩畫一律”的論述散見于畢生詩文當中,如他認為繪畫與詩歌的意趣能夠在渾然天成般的作品中實現通融,《跋蒲傳正燕公山水》中說:“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為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氣度,而得詩人之清麗也。”[6][宋]蘇軾:《跋蒲傳正燕公山水》,[明]茅維編:《蘇軾文集》卷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12頁。更重要的是,這種媒介聯動和藝術家角色的混同,沒有被當作曇花一現或絕世難尋的創作現象,而是被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作者意識和身份認同,因為蘇軾認為杰出的詩人同時應是高妙的畫家,反過來亦成立(“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7][宋]蘇軾:《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43頁。),文士之所以區別于俗士,便是依靠對不同藝術媒介的貫通(“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8][宋]蘇軾:《次韻吳傳正枯木歌》,[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962頁。)。因此他才會自我標榜道:“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1][宋]蘇軾:《韓干馬十四匹》,[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768頁。。
“詩畫一律”說對當時的文藝領域起到了春風化雨的效果,它的現實影響在藝術批評與藝術創作中都得以體現。
一方面,它為文藝評價體系吹來新風,繪畫與詩歌評論開始大量使用蘇軾倡導的新觀念與新語匯。如北宋張舜民的《跋百之詩畫》道:“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孔武仲《東坡居士畫怪石賦》云:“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跡而同趨。”[2]水賚佑編:《蘇軾書法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第1047頁。黃庭堅《次韻子瞻子由題憩寂圖》云:“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3][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55頁。“詩畫一律”觀念的浸染,甚至在官方編纂、但因黨爭之故將蘇軾排除在外的《宣和畫譜》中都能發現蹤跡。其中又以《墨竹敘論》篇最為典型[4]“繪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黃鉛粉則失之,是豈知畫之貴乎,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黃鉛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于形似。而獨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畫史,而多出于詞人墨卿之所作,蓋胸中所得,固已吞云夢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則拂云而高寒,傲雪而玉立,與夫招月吟風之狀,雖執熱使人亟挾纊也。”《宣和畫譜》卷二十,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年,第247頁。,它指出盡管繪畫能彌補文學形容所不及之處,但繪畫與文學的追求都應在形似之外,而以詩意為先端并以筆墨入畫者才是真正的知畫者。
另一方面,“詩畫一律”在創作領域被廣為踐行,并帶來了藝術家主體意識的凸顯。文人紛紛以此法作詩、繪畫,追求胸中逸氣的暢發,不再恪守專門從業者的技巧與模板。職業畫家也受到該理論的影響,如郭思整理其父郭熙生前所述《畫意》道:“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5][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 41頁。其后還羅列古人清篇秀句,為讀者提供“有發于佳思而可畫者”,以期達到引發創作靈感的效果。宋徽宗領導下的畫院亦以詩題選拔宮廷畫家,懂得藏意而非直白描繪詩句的更容易獲得青睞。[6]“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于橋頭竹外掛一酒簾,書‘酒’字而已,但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后而已,便表得馬蹄香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于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宋]俞成:《螢雪叢說》,程毅中編:《宋人詩話外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219頁。這樣一種取士的傾向帶來了畫意與詩意的競爭,甚至隱含著圖畫能更好地傳達詩意的期許。學者的研究也指出,宋徽宗時期的畫院對當時和后世的創作風尚產生了重大影響,帶來了整個宋代畫學的文人性轉變,使繪畫與作為士大夫正統的文學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7]參見李慧漱:《宋代畫風轉變之契機——徽宗美術教育成功之實例》(上),《故宮學術季刊》1984年第一卷第4期,第71-91頁;李慧漱:《宋代畫風轉變之契機——徽宗美術教育成功之實例》(下),《故宮學術季刊》1984年第二卷第1期,第9-36頁。因此,“詩畫一律”的提出與推行是宋代文藝高峰的重要理論表征和觀念載體。
四、“言—象—意”:中國藝術媒介觀的理論支點
“詩畫一律” 對中國藝術的影響遠不止于宋代,它深刻塑造了此后中國傳統美學對媒介的本質與媒介間性的認知。
由于蘇軾把詩歌的審美理想引入到繪畫當中,把傳統文論對“意在言外”的追求轉化成“超以象外”的圖像目標,象形藝術在高度理論自覺的支撐下追求跨越摹仿和再現的圍城。換言之,蘇軾強調“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1][宋]蘇軾:《書朱象先畫后》,[明]茅維編:《蘇軾文集》卷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11頁。,這種自我意識的凸顯要求藝術的目的從再現外界轉向對個體經驗和內心感受的傳達,從而將審美的可能注入到媒介象形的表達空間中。由于相同目標的存在,不同的藝術媒介被整合入同一個評價體系當中,這也使繪畫同文學建立起了更加本質的聯系,不再自滿于作為另一種媒介的補充。“書畫同源”說所暗示的媒介在表達形式上的相近,逐漸轉換為媒介在審美經驗上的一致,而從“書畫同源”到“詩畫一律”的轉變,便是將詩的審美經驗與畫的審美經驗等同起來,在審美層級上把二者視作可以融合的媒介。這樣一種看法強調了人類感知經驗的不可分割性。
經由蘇軾及其后學團體的推動,“超乎形似,得之象外”進一步成為藝術媒介共同的追求,而在“詩畫一律”這一歷久彌新的潮流背后,對媒介終極價值的理解是不言而喻的,即認為它們能夠跳脫出外在形式之圭臬,共同抵達主題所包蘊的最高真實——顯然,這樣一種認識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根深蒂固的哲學基礎的。對真實的開啟決定了藝術主題的意義世界,而藝術媒介向最高真實的通達路徑無疑涉及本質性的美學觀念。當我們談論“最高真實”時,似乎無法繞過由柏拉圖開啟的西方哲學傳統。但中國哲學思維中罕見這種自上而下、最高存在逐級被分為存在鎖鏈(Chain of being)般的層級嬗遞,情況甚至正相反:一條自下而上的理論框架經過先秦哲學的醞釀,在魏晉時期便被闡發出來。特別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王弼(226-249)的論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的藝術媒介論、功能論及本體論。
我們會發現,中國哲學在其開端便已確認媒介存在的必要性。《莊子·天道》云:“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2][戰國]莊子:《天道》,陳鼓應編:《莊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56頁。《易傳·系辭上》云:“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3][魏]王弼:《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55頁。——即便“言”有著“不盡意”的局限性,世俗之中仍要“貴言”“盡其言”。以上文本談論的是符號、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關聯,但“言”同樣可被理解為種種媒介手段的具體表現形式。莊子的本意是要破除包括語言在內的對形、色、名、聲的迷信,但《易傳》為彌合“言”與“意”之間的不對等關系提出了解決辦法:設立“象”。
“象”是什么?《系辭》中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圣人設卦觀象”;“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1][魏]王弼:《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45頁。可見“象”是智者為探究天下玄妙、明其形容物宜而創造的,是智者識道、體道的一種形而下的工具。在漢代人眼里,《易》之“象”是對天地萬物的模擬,“象”昭顯在物象、形象或現象中,它對接自然中的物理存在,但它自身卻是存在的抽象。王弼在批評漢儒象數學的機械性的同時也繼承了前代的觀念,進一步指出“象”能夠向上接引“意”,向下接引“言”。[2]“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茍在健,何必馬乎?類茍在順,何必牛乎?爻茍合頃,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何必乾乃為馬?……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而忘意之由也。” [魏]王弼:《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09頁。值得注意的是,王弼雖然認可“龍”與“乾”、“馬”與“坤”的象征意義,但他否認“象”與“意”之間對應關系的唯一性,他認為只要觸類合義都可以為“象”,這是針對漢儒抱守經典、尋章摘句、牽強附會的解經思路而言的。王弼強調“象”的包蘊性,這樣才不會拘泥于“象”而失去更重要的“意”。
王弼的《明象》篇分為兩條線索,一條論述“意—象—言”,一條論述“言—象—意”,這種雙向的路徑將當時盛行的“言意之辨”推向了新的層面。關于后者,最核心的表述是: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3][魏]王弼:《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09頁。
“意—象—言”本是《易》的作者建構《易》的思路,即從義理到卦象,再由卦象到爻辭。而“言—象—意”是王弼提出的解讀《易》的方法:因為言辭(爻辭)是由《易》的卦象產生的,所以可以通過言辭的內容追溯到卦象的意義;卦象是表達圣人義理的,所以可以通過卦象所表現的內容理解圣人的本意。卦象通過爻與爻、卦與卦之間在結構上的組合和變化而具有一種意向性,這是《易》作為經典的玄妙所在,但“象”作為一種符號與其意義之間的聯系是松散的,因此需要“言”在先,對“象”之所指進行固定,然后才能由“象”達“意”。在王弼看來,真正表意的是“象”,而不是“言”。他在肯定媒介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時破除了對媒介的迷戀,這是王弼易學體系中極具特色的第一步。接下來,王弼把他的邏輯關系繼續深入。他認為,“言”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表“象”,而“象”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表“意”。換言之,“言”與“象”都僅僅是在追求“意”的不同階段的工具而已。
當主語被置換為具有跨媒介屬性的中國藝術主題時,情況也是相似的:最高的真實并不停留在物象中,而要在意境當中找尋。此種觀念在“詩畫一律”的提出之前已經過長期的醞釀,如晉代王羲之論書曰:“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1][唐]張彥遠:《晉王右軍自論書》,《法書要錄》卷一,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7頁。南朝的謝赫在《古畫品錄》中將“氣韻生動”置為繪畫六法之首而以“傳移模寫”為末,荊浩在《筆法記》中駁斥作畫只求形似之后,也進一步區分道:“夫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于山,橋不登于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2][唐]荊浩:《筆法記》,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605頁。“有形之病”,病在無法表現物象的形態;“無形之病”,病在無法傳達氣韻精神。象外之意,從此成為中國文藝作品不竭的追求。蘇軾的伯樂歐陽修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引用此詩的沈括則說:“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他贊美王維不合時節的《雪中芭蕉圖》,也是因其“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3][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9-160頁。。
有必要指出,“言”“象”“意”之間的轉換機制是通過“忘”來實現的。忘“言”以得“象”,忘“象”以得“意”,即通過知性的懸置,放棄當下階段中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和言說的執著,實現不同層級間的意義傳達,以進入更高的體悟中。顯然,“得B忘A”的結構有著重前輕后的含義,他們秉承的都是同樣的原則:相對于“言”來說,“象”是“言”之體;相對于“象”來說,“意”是“象”之體。但“得象忘言”,不是對“言”的徹底鏟除;“得意忘象”,也不是對“象”的全面掃清。[4]王弼在《周易注》中部分采用了漢儒常用的方法,比如損卦九二爻辭和睽卦六三爻辭用了卦變說和互體說等,可見不是盡黜象數,而是有所保留。“忘”可以說是王弼最重要的新解,把老莊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言無言”一類吊詭表述中所隱含的智慧揭示了出來——“忘”不是要從“言”或“象”中提煉精微,“意”與“言”和“象”的區別也不是精粗之別。《說文解字》解釋“忘”為“不識也”,段玉裁注釋道:“識者,意也。今所謂知識。所謂記憶也。”[5][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段玉裁注,2023年4月27日,電子檢索資源: https://www.zdic.net/hans/忘。可見,“忘”由“識”中來,又能由“識”中出。在前引文字中,王弼援用《莊子·外物》中的“筌蹄之言”來進行比喻,其中“筌”是捕魚的竹器,“蹄”是捕兔的網,這個比喻強調了“言”與“象”在實現“意”這一目標過程中的工具性。那么,“言—象—意”的結構一方面要求“尋言觀象”“尋象觀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得象忘言”與“得意忘象”,目的就是要去除對工具性、知識性的“言”和“象”的留戀與遮蔽,得到一種超然的領悟。
“忘”也是微妙的藝術創造過程的核心要義。充滿靈感與激情的藝術創作難以被復制、再現,更難于用語言來描述,如果創作體驗中有什么一定之規,便是此難以捉摸的“忘”境。郭熙云:“欲奪其造化,則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飽游飫看,歷歷羅列于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1][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冊,第636-637頁。鄭板橋也為中國繪畫的創作過程提供了一個精妙的例證[2]“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清]鄭燮:《板橋題畫蘭竹》,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179頁。,落在紙端的竹枝葉影并不是最初的、外在的“眼中之竹”,它經過了與畫家心源孕育、氣質磨合的“胸中之竹”的階段,但當它成為“手中之竹”時,不單單浸潤了非一日積淀的技法筆力,更重要的是突破種種先在的預設,由是才能參隨造化,從“胸中之竹”轉化為有著法外之趣的“手中之竹”——畫面若能使觀者感受到這股不滯于有形之物、不全然托生自畫家胸臆的淋漓元氣與生機,才是畫中神品。
董逌對李成山水畫的品評,可以視作對上文所論的延伸與綜合: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于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于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為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于山林泉石,巖棲而谷隱,層巒疊嶂,嵌欹崒嵂,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群山橫于前者,累累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托于畫以寄其放,故云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后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邪?[3][宋]董逌:《書李成畫后》,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658-659頁。
李成的畫代表了中國藝術所引發的審美活動中的最高境界:不失形似,卻又難以用形似求之;畫作當中淡化了知識的紛擾,去除了利害的糾纏,得到了物象的真實卻又“殆與物忘”,最終得意而忘象;畫作因此寄托著精神之玄覽,展露畫家的人生境界,并與大道冥合。這里面無一字談媒介,卻無疑是對媒介屬性的超越。
結語
“言—象—意”結構對中國藝術主題研究及中國藝術媒介觀的影響集中在兩方面。其一,王弼的用意是“崇本舉末”——既關注本體,又關注形相。追求“意”的過程并非要將“言”舍棄掉,因此在“言—象—意”結構中,作為載體和媒介的“言”有著明晰的通路,即由“象”達“意”。對擁有跨媒介屬性的中國藝術主題而言,這一理論框架為不同藝術媒介完整地揭示主題意涵提供了理想的范式。其二,“意”在“言—象—意”結構當中居于最高位置,正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樣,它也成為中國藝術的最高追求,為不同的藝術媒介框定了共同的目標,促使中國的藝術實踐與批評不是“唯寫形論”“唯物象論”的,而是兼及“象”與“意”。在這一最高境界上,同一主題分衍出的各異的媒介形式引發的審美體驗是可以相通、交融的。由于這一通路的存在,藝術媒介的壁壘被認為是可以打破的,不同媒介帶來的審美經驗可以無間融合。中國藝術哲學中看似缺少對“媒介”的專門論述,但在“言—象—意”的理論背景下,“言”的差異中被認為能誕生出“象”的接近,由此昭示“意”之相通的可能,這是歷史中長期存在的觀念,談論跨媒介的中國傳統藝術主題不得不對這重基礎特質予以審視和觀照。在此基礎上,獨立的藝術門類才可能發展成多位一體的綜合媒介,藝術主題“多樣”與“穩定”的特征才得以和解。如此語境下,媒介的分立局面有著更多溝通與交融的可能。
還可以發現,古典文藝作品從“言”到“象”、由“象”及“意”的過程,是媒介通過對物象的呈現,顯現意境的過程。“意境”本是一個詩學范疇,最初由唐代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在近代經過王國維等人的闡發后才成為一個具有普遍價值的美學范疇,但是,它與中國藝術理論中長期存在的虛實觀、形神觀和真實觀一脈相通。它們共同指向的、也為“言—象—意”結構所觸及的最高真實,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個超越知識與工具、懸置情感與理性之后復歸本源的純粹美感世界。這樣一個美感世界同時是密合無際的,無法被經驗分割,更不會為媒介割裂。這一看法并非意在消弭媒介之間的客觀差異,而是試圖在審美經驗層面談論媒介的互動、共生與間性。由此,它回應了本文開頭所提出的關于“異”與“同”的張力問題,甚至還從另一個角度呼應著跨媒介藝術的先驅迪克·黑根斯在20世紀的大膽宣言:“我想說的是,媒介的使用在整個藝術中或多或少是普遍的,因為與‘分類’思維相比,‘連續性’才是新思維的標志。”[1]Dick Higgins,“Intermedia,”Leonardo, vol.34, no.1(2001),p.50.
盡管借助西方當代媒介理論特別是“藝格敷詞”理論,可以對中國藝術主題建立起某種方便之理解,但對中國藝術主題跨媒介屬性的初步探索顯然彰顯了與西方既有的藝術話語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希望它能為當代的媒介神話提供一個反思的立場,并向我們揭示喧囂中的匱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