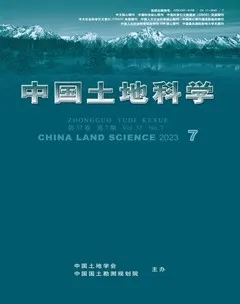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影響研究
——基于浙江省德清縣改革試點的經驗證據
趙 偉,諸培新,余 杰
(1.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2.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資源環境與發展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5;3.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城鄉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基本的經濟關系。從中共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到中共二十大報告“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全面推行鄉村振興”,表明城鄉融合是破解我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重大戰略,也是新時代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1]。土地作為城鄉發展的關鍵要素和基本載體,土地市場是實現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重要渠道和紐帶[2],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不僅會影響經濟發展效率,更會影響城鄉收入分配格局[3]。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城鄉建設用地市場處于二元分割的狀態,城市內建設用地入市及轉讓交易有著清晰的制度安排,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長期處于“隱形市場”下。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2021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強調“積極探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探索靈活多變的供地方式”[4]。自此,我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現了從基礎探索階段到具備明確政策指引的合法入市階段的演進[5]。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豐富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制度的重大創新[4],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這一土地資源配置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對于促進城鄉土地要素流動,使地租地價真正成為供求關系的“晴雨表”[6],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及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7]。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作為農村土地改革的核心內容,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早期學者們主要探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正當性。學者普遍認為法律規范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嚴格限制,導致農村形成大量的隱形集體建設用地市場,造成了集體土地收益的流失,也嚴重妨礙了國有土地市場的正常運行[8-9],因此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必然趨勢[8-13]。隨著我國不斷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改革,相關研究逐步轉向入市主體及其利益分配[14-15]、入市主體之間的行為選擇[4,16]、入市存在的困境及改進等方面[17-19]。研究認為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中存在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分配的方式、比例和基數不合理等問題,導致地方政府和村集體之間存在較大的利益沖突,需要構建統一完整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體系來進行化解[15]。此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發展的影響也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有研究認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切入點,能夠較好地滿足城鄉融合領域蘊藏的潛在需求,并且入市產生的租金分配及租賃土地增值的紅利收入增加了農民財產性收入,能夠有效縮小城鄉之間收入差距[12];還有學者認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能夠顯著提升農村土地利用效率,優化城鄉建設用地空間,促進農村地區發展[5]。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多從對農民或者農村的視域下展開,但少有從城鄉融合發展角度進行研究,且鮮有從縣域視角研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事實上,隨著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部分地區開始以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構筑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暢通了城鄉之間土地、資本等要素流通渠道,那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在優化城鄉資源配置的過程中,能否發揮促進城鄉互動協調、共同繁榮的目標?二者之間存在何種作用機制?現有文獻不能給出明確的回應。同時,德清縣作為我國首批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試點地區和先行區,區域內改革經驗為浙江乃至全國提供了改革樣本和經驗參考。鑒于此,本文以德清縣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準自然實驗,運用合成控制方法(SCM),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影響城鄉融合發展進行深入分析,然后采用中介模型探明了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相較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有:第一,從城鄉融合的視角,基于要素流動及公共服務優化兩個層面,搭建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第二,在實證方法上,以縣域為研究對象,采用合成控制法這一前沿的政策評估工具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并探究了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要素投入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決定了只有實現要素的合理流動,才能提高其資源配置的效率。根據要素配置理論,要素市場化配置可以通過市場規則、價格及競爭配置要素,以期實現要素使用效率的最大化。長期以來,受制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土地資源難以跨越城鄉流動的制度障礙,而構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從根本上打破了農村土地只能通過國家征收方式進入市場的限制,是助力鄉村振興及城鄉發展的關鍵舉措[20],對于充分發揮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關鍵角色及維護社會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21]。因此,本部分將深入剖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用于城鄉融合的影響路徑,闡明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圖1)。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突破當下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農村居民通過土地發展權公平參與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一方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使城鄉建設用地依照統一市場的邏輯進行優化配置,暢通要素城鄉雙向流動的通道,從而優化城鄉要素空間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有效盤活并釋放農村低效用地,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集體土地利用效率,充分釋放集體土地區位價值,為鄉村發展提供資本積累及發展平臺,激發鄉村地域發展潛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有效緩解當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土地要素約束及城鄉發展失衡的局面,促進城鄉在經濟、社會、生態及空間等方面的高質量融合,為重塑新時代城鄉關系帶來新的發展契機[22]。

圖1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Fig.1 The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iz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據此,提出假說1: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高。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集體建設用地價值的顯化,促進要素實現城鄉地域“空間”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首先,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配置土地資源,促進農村資源要素的有效流動,實現“資源”變“資本”,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并且相較于土地征收模式的“一次性”補償,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核心指向是一種持續的收益,有助于土地流轉收益從靜態向動態的轉變。同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規模的擴大有利于農村工業化的發展,促進農村居民就業的多元化,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23],縮小城鄉發展差距[24],促進城鄉經濟融合發展。其次,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能夠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進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在城鄉之間實現“空間”流動,從而促進城鄉空間融合發展。此外,經濟結構的變化引起生產布局區位因素的變化[25],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為城市內產業的轉移提供了用地空間,形成產業協同的新動能,進而催化城鄉要素的流通,形成城鄉區域間協同發展的空間機制,強化城鄉地域之間連接紐帶,推動城鄉空間融合發展。
據此,提出假說2: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基于資源空間配置產生要素流動效應,促進城鄉經濟融合及空間融合發展,從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優化城鄉土地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基于公共服務優化效應為區域創造更加宜居宜業的生產生活條件,促進區域城鄉社會及生態融合發展。一方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能夠改善區域城鄉基礎設施服務水平,促進區域周邊配套措施的完善,優化城鄉居民的居住環境及空間布局,從而促進城鄉生態融合發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產生的公共服務優化效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轉變區域公共服務供給的導向,增加和擴大對農村地區環境公共服務領域的資金投入,進而優化區域城鄉生態環境發展質量,促進城鄉生態融合發展;此外,區域城鄉空間及布局的優化更有利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盤活及利用,并提高農村集體議價權,真正發揮地租和地價的“擠出效應”,實現資源節約及人居環境優化,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促進城鄉生態融合發展。另一方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能夠為鄉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來源,促進區域城鄉公共服務的普惠共享,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地域延伸及社會事業向農村地區覆蓋,逐步轉變“重城鎮、輕鄉村”的局面,推動實現城鄉一體的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及基礎設施配套,提升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此外,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能夠優化城鄉建設用地配置,緩解產業發展的高用地成本,為城鄉產業人才提供安居之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有效緩解社會資本從實體經濟中過多流出的發展態勢,促進城鄉社會融合發展。
據此,提出假說3: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可以優化基礎設施及人居環境水平(公共服務優化效應),促進城鄉社會融合及生態融合的發展,從而推動城鄉之間深度融合發展。
2 實證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定
近年來,以隨機實驗、對照實驗及準自然實驗為代表的政策定量評估推動了實證經濟學的可信性革命[26],尤其是雙重差分法模型(DID)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但這兩種方法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陷。其中,DID方法必須要求控制組與處理組遵循嚴格的共同趨勢假定,對于對照組的選擇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而PSM方法則要滿足條件獨立性檢驗,并要求在大樣本的情況下只能計算政策干預的平均效應。
相對于DID和PSM方法,基于非參數估計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通過將多個不受政策影響的個體加權組合成“合成控制組”,并通過預測變量合成與實驗組高度相似的“反事實控制組”,可以有效避免選擇“控制組”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并且不存在大樣本、樣本可觀測和整體性分析的局限性,進而保證了結果的科學性與穩健性,逐漸成為了國內外政策評估的前沿方法之一。
本文以德清縣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準自然實驗,構造出實驗組德清縣的“反事實”對照組,即擬合本文研究范圍內未被選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的地區,稱之為“合成改革地區”,用來反映未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情形。真實改革試點地區與合成改革地區在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即可視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
假設共可以觀察到j+ 1個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其中第一個地區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試點實施的地區,其他的j個地區并未受到改革政策的影響。假定為第i個縣在第t年未實施改革政策時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為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后i第個地區在第t年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當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后,縣域范圍內每個個體的改革政策效果是可以觀察到的,即。可以觀察到,反事實變量效果可以通過估計得到。其中,αt為第t期的固定效應,θt為系數向量,Z1為可以觀察并不受改革政策影響的控制變量,λ t為因子向量,U1為不可觀測地區的固定效應,ω1t為擾動項,p1t為政策試點實施地區的政策效應。
為了得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必須估計改革試點地區沒有進行政策試點改革時的。因此,如果存在一組向量,滿足:
為了進一步厘清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本部分利用前文所選定的25個縣(市、區)2005—2019年面板數據,并參考溫忠麟等[27]分步回歸方法對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分析,中介效應檢驗模型構建如下:
式(4)—式(6)中:被解釋變量mergeit表示縣域i在第t年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Treatit表示政策實施虛擬變量,2015年及2015年之后賦值為1,2015年之前賦值為0。Meit表示各中介變量(勞動力流動、資本流動及公共服務水平);α0、α1、α2、β0、β1、β2、γ0、γ1、γ2、γ3為待估系數,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μi與μt表示縣域與年份的固定效應,Z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
2.2 變量選取及解釋
本文將各縣域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作為被預測變量。城鄉融合是一個動態復雜系統,已有的研究從多個層面來分析測度城鄉融合發展的水平,張海朋等[28]、施建剛等[29]從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多個維度測度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參考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經濟—社會—空間—生態4個層面構建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指標體系并采用熵權法測度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表1)。同時,為了保證實驗組和對照組能夠更好的擬合,選取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對外開放水平、金融發展水平作為預測變量來控制基本面的影響;對外開放水平用當年外商投資額占GDP 比重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用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表1 縣域城鄉融合指標體系Tab.1 County-level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county level
2.3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
2.3.1 研究區域介紹
德清縣為浙江省湖州市管轄,位于浙江省北部,地處長三角腹部,是滬、寧、杭金三角的中心。德清縣總土地面積為937.95 km2,下轄5個街道、8個鎮。2022 年德清縣生產總值658.2 億元,常住人口65 萬,三產結構比為4.2%∶57.8%∶38.0%。2015年德清縣入選了全國首批15 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此后又被選為全國33 個集體經營性改革試點之一,2015年8月全國首宗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德清縣上市,隨后又有多宗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截止到2019 年底,德清縣已實現集體土地入市208 宗,面積1 593.64畝,成交金額4.22億元,集體收益3.39億。德清縣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探索,為浙江省及全國其他區域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提供了改革樣本和經驗支持。
2.3.2 數據來源
本文以德清縣為研究對象,為了更科學地觀測政策效應,綜合考慮數據可獲取的基礎上選取湖州市、寧波市、溫州市、紹興市、金華市5 個地級市范圍內未實施入市改革的部分縣(市或區)共24個地區作為對照組①浙江省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區域內根據經濟發展程度可劃分為三個級別,以杭州—寧波為第一梯隊,溫州、紹興、金華、嘉興為第二梯隊,臺州、湖州、麗水、舟山、衢州為第三梯隊,綜合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從三個梯隊中選擇代表城市,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在此基礎上,本文共選取了包括德清縣在內的25個縣(市、區),其中湖州市選取了德清縣、長興縣、安吉縣;寧波市選取了象山縣、寧海縣、余姚市、慈溪市;溫州市選取了永嘉縣、平陽縣、蒼南縣、文成縣、泰順縣、瑞安市、樂清市;紹興市選取了柯橋區、上虞區、新昌縣、諸暨市、嵊州市;金華市選取了武義縣、浦江縣、磐安縣、蘭溪市、東陽市、永康市。。此外,本文選擇的樣本時間跨度為2005—2019 年,這樣選擇的好處是既可以觀察改革政策前的發展特征,又可以準確地考察改革政策后政策效應的影響。本文所需數據主要來自《浙江省統計年鑒》、《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縣(市、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告等,其中少數缺失的數據采取線性插值法或者均值插值法進行補充。
3 實證結果分析及檢驗
3.1 合成控制法結果分析
按照上文研究設計,將德清縣作為處理組,其余24個縣(市、區)作為對照組,以對照組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及其主要的影響因素作為預測變量,通過對控制組中各樣本的預測變量進行加權,進而擬合出一個與處理組特征性質接近的“反事實”合成組(以下簡稱合成德清),權重組合被約束為正且總和為1,構成合成德清縣的最優權重有三個縣或者區權重為正,其余地區權重都為0,其中長興縣的權重占比最大達到75.7%,柯橋區和上虞區分別占8.5%和15.8%。合成控制法的有效性受到政策改革前后各變量擬合程度的影響,由表2可知各預測變量的真實值與擬合值之間的差距非常小,這也表明了通過上述最優權重組合的篩選之后,合成德清縣可以較好地代替真實德清縣的發展特征,所以采用合成控制方法可以較為準確地評估入市對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

表2 預測變量的真實值與擬合值對比Tab.2 Comparison of the truth and fitted values of the predictor variables
圖2橫軸代表時間、縱軸代表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值,實線代表德清縣,虛線代表合成德清縣、豎虛線代表政策改革的時間節點。由圖2可知,在2015年德清縣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政策前,合成德清與真實德清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演變路徑可以較好地重合,變動趨勢大體一致,因此,可以較好地代表對照組評估政策效應;從2015年政策實施后,合成德清與德清縣展現出不同的變動軌跡,并且隨著時間的增長,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距逐漸拉大,這表明相較于未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合成德清,真實德清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有明顯的提高,反映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政策效應。為了更直觀地觀察改革政策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本文進一步計算了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值,從圖3 中可以觀察到,政策實施前2005—2014年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值基本圍繞在0值波動;但在2015年改革政策實施之后,二者之間的差距隨改革時間的增長呈現波動上升趨勢,顯著地促進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高。

圖2 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的城鄉融合水平值Fig.2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values of Deqing County and synthetic Deqing County

圖3 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差值Fig.3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Deqing County and synthetic Deqing County
3.2 穩健性檢驗
盡管本文發現真實德清縣與合成德清縣在改革前后存在顯著差異,但這種差異不排除是由一些未觀測的因素所導致,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安慰劑檢驗和排序檢驗方法來進行穩健性檢驗。
3.2.1 安慰劑檢驗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電力電子器件對多電平逆變器的電平數目的要求也越來越多[3-4],這使得逆變器內部的主電路的功率半導體管數量不斷增加、電路的內部結構復雜、控制方式繁瑣,極大地提高了其發生故障的概率,降低了電源系統的可靠性[5-7]。因此會引起一系列的電源故障問題,如會造成變電站中電源的損壞,導致區域性停電、部分電網癱瘓等,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企業正常生產,這將直接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構成重大的威脅[8]。因此,為了避免此類事故的發生,不僅要提高逆變器的生產質量,還要對其進行相應的故障建模以及對出現的故障進行診斷和研究。
“安慰劑檢驗”的基本思路是:選取對照組中未實行改革的地區,假定其實行了改革,如果結果表明改革后該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差距的變動趨勢和試點地區相同,那就說明即使沒有實施改革政策,該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也會發生相關的變化,此時表明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變化可能是時間趨勢或者受到其他政策改革的影響,與研究的政策改革無關,說明得到的結果是不穩健的。反之,則說明前文的實證結果是可靠的、穩健的。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39]的基礎上,選取2015年之前未實行改革的地區進行與前文同樣的分析。對于安慰劑地區的選擇,本文選擇最優權重組合中貢獻值最大的長興縣作為樣本,從安慰劑的檢驗結果(圖4)來看,長興縣的實際值和合成值在2015前后與實行改革地區的趨勢恰好相反,這表明入市改革促進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提高的結果是穩健的。
3.2.2 排序檢驗法
為了進一步增強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本文繼續采取ABADIE提出的一種排序檢驗[40],用于判斷區域內是否還有地區出現與改革區相似的情況及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和安慰劑檢驗的選取的控制單元不同,排序檢驗采取的是隨機控制分析單元[41]。本文借鑒鄧慧慧等[26]的做法對事前均方差MSPE大于10倍、5 倍和2 倍的樣本進行剔除,以排除2015 年之前各地區迭代路徑上與原始路徑較大差異造成的干擾。由圖5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德清縣實施改革后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有著較為明顯的提升,這表明假設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變化并無影響,則在這18 個縣(市、區)地區范圍內,碰巧看到德清縣的處理效應最大的概率是1/18 = 0.056,因此,可以認為德清縣的改革效應在10%水平下是顯著的。

圖5 德清縣與其他縣(市、區)的預測誤差分布圖Fig.5 Distribution of prediction errors between Deqing County and other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3.3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分析
表3報告了各變量中介作用實證結果。模型(1)的結果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顯著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高,這也與前文合成控制法的實證檢驗結果保持一致,驗證了假說1。模型(2)的結果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顯著促進區域勞動力的流動,模型(3)的結果表明勞動力流動的sobel檢驗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通過暢通勞動力要素的流通,促進城鄉之間的深度融合,并且中介效應的占比為2.36%,驗證了假說2;模型(4)和模型(5)的結果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未能通過資本流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可能的解釋是當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依賴下,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收益在政府、集體與農民之間的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的不完善,未能發揮“取之于地,主要用之于農“的政策導向功能;模型(6)結果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能夠促進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并且由模型(7)可知,公共服務水平的sobel檢驗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可以通過公共服務優化效應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這一中介效應路徑占比為30.7%,驗證了假說3。

表3 各變量中介效應檢驗實證結果Tab.3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of each variable
參考相關研究[42],本文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采用TOPSIS 方法對城鄉融合數值重新測算,并再次帶入基準模型中,表4 結果顯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顯著提升了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勞動力流動及公共服務水平都能發揮中介影響效應,各基準結果影響系數方向及大小都未發生較為明顯的改變,進一步驗證了前文部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表4 替換被解釋變量后的穩健性估計Tab.4 Robustness estimates after replacing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4 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2005—2019年浙江省25個縣(市、區)的面板數據,利用合成控制法評估了德清縣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并采用中介模型明晰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主要結論如下:
(1)與合成德清縣相比,真實的德清縣在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后,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
(2)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影響效應隨時間推移逐步增加,利用安慰劑檢驗和排序檢驗方法依據不同的控制單元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都表明了改革政策促進德清縣城鄉融合發展結果的穩健性。
(3)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優化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重要路徑,基于要素流動效應(勞動力流動)及公共服務優化效應對城鄉融合發展發揮促進作用,并且勞動力流動效應和公共服務優化效應的中介占比分別為2.36%和30.7%。
根據上文得出的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法律制度,注重改革之間的協調聯動。中央層面盡快出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化流轉規定》,以法律規范性的文件明晰有關入市方式、范圍、用途,對相關入市主體的權利及義務做出明確的規定,完善入市的交易機制、監督機制及糾紛解決機制,以規范集體土地入市行為;考慮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數量的有限性,應聯動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積極探索進城落戶農戶自愿有償退出或者轉讓宅基地機制,打通農村閑置宅基地或者廢棄集體公益用地轉化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通道。
第二,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機制。加快構建適合國情并兼顧國家與農村集體之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既要保證農村集體的收益不受損害,又能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首先,應盡快通過頂層設計以法律形式明確地方政府采取累進稅率對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進行征稅,在此政策出臺之前可以在現有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收中適度上調商服用地的增值收益征收比例;其次,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要優先用于可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鄉村共同富裕及農民可持續增收的項目,同時設置相應的鄉村產業用地目錄, 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產業發展的用地需求,以確保鄉村地區的優先發展。
第三,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要素優化配置,助力實現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動能。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統籌作用,致力于城鄉公共服務的均衡化發展,通過公共服務建設持續優化鄉村治理環境,推進城鄉一體化醫療衛生共同體建設,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實現城到鄉的流轉及再分配,促進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實現交互共享,使全體居民受益于城鄉公共服務的溢出效應,推動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空間、生態等多個層面的高質量融合發展。同時,新時期應繼續深化城鄉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通道,促進各類要素實現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使市場在城鄉要素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注入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