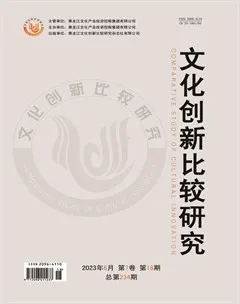漢哈體態語對比研究
馬合帕力·俄孜合提,賽力克布力·達吾來提肯
(1.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新疆伊寧 835000;2. 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00)
體態語, 是指在交流中運用身體的變化, 如表情、動作、體姿、身體空間距離等作為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輔助工具, 同時也是一種非語言符號[1]。體態語雖然是一種無聲語言, 但它同有聲語言一樣也具有明確的含義和表達功能, 有時還具有有聲語言達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所謂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本文通過對漢哈體態語進行分析、整理、歸納,總結出漢哈體態語的共同點及不同點, 并對其差異原因進行闡述, 最終梳理出了體態語在漢哈民族交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1 體態語概說
體態語是日常生活中借以傳達真實想法和情感變化的輔助交流方式, 而不同民族往往有著意義不同的體態語。置身于不同民族和地域時,了解當地的體態語,有助于更快地融入當地群體。
1.1 體態語的定義
提到交流,自然會想到語言,即每天說的不計其數的話。 但是,除了有聲語言,還有一種對日常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身體語言——體態語[2]。體態語是一種表達和交換信息的可視化(有的伴聲) 符號系統,它由人的面部表情、身體姿勢、肢體動作和體位變化等構成。 在現實生活中,體態語使用極其廣泛,而且有時更能無聲勝有聲地巧妙表達信息, 同時留給對方更大的想象空間[3]。心理學家得出一個有趣的公式: 一條信息的表達=7%的語言+38%的聲音+55%的人體動作,這表明,人們獲得的信息大部分來自視覺印象。因而美國心理學家艾德華·霍爾曾十分肯定地說:“無聲語言所顯示的意義要比有聲語言多得多。 ”[4]
1.2 體態語的分類
體態語的分類方法主要有兩種。
一是根據體態語的性質, 將之分為生理性體態語和符號性體態語。 生理性體態語指的是因內在情緒影響,自然地表現出的一些討厭、高興和憤怒的表情、姿態及動作,譬如,生氣時會臉紅,高興時會微笑等。這種體態語往往由生理特征所決定,與特定群體的身體狀況有著較大關聯。 而符號性體態語主要指的是約定俗成的、具有形式和意義的體態語,在不同地區,符號體態語通常對應著不同的含義。 譬如,豎起食指在哈薩克族群體中通常有著“請注意傾聽”的意思, 而漢語中該意義則并不明顯; 豎起拇指和食指,在漢語中既可表示“八”也可表示“手槍”,而哈語中則只有“手槍”的涵義,當用該手勢指向自己或他人時,則代表“自殺”或“槍殺他人”的意思。 故而,符號性體態語往往代表了民族在歷史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定習慣。
二是根據交際者的狀態, 將體態語分為動態體態語和靜態體態語。動態體態語,通常而言表現在頭部與肢體的運動當中,或者是面部表情的動態變化,動作的幅度、 位移距離等也同樣可以傳達不同的體態語意義。 譬如,點頭的力度決定了肯定的程度,拍手掌表示對他人的支持、鼓勵和贊賞。靜態體態語則是由靜態的表情和姿態來表達態度。譬如,撇嘴表示不滿或生氣等消極態度; 豎起大拇指表示贊賞或支持等肯定態度。在具體交際過程中,動態體態語與靜態體態語往往交替出現。
本文結合以上兩種分類方式, 對漢哈體態語進行粗淺的對比分析。
2 漢哈體態語對比
漢哈兩個民族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兩個民族體態語的異同主要可表現為形同義同、形同義異、形異義同三種,此外兩個民族還因地理環境、文化習俗等原因,存在一些本民族特定的體態語。
2.1 形同義同的體態語
由于漢哈兩個民族長期交流融合, 故而兩個民族存在著諸多相同的體態語, 這些體態語也包括從第三方國家借用后共同使用的體態語。譬如,漢哈兩個民族均有見面握手的習慣;“點頭”表示贊成、肯定的意思,點頭還有一種作用,是在熟人見面時,互相點一點頭,表示打招呼問候等意思;“搖頭”的動作多表示拒絕和否定等意義, 而微微搖頭表示讓旁邊的人不要說,保密;“翹起大拇指”的手勢表示很好,棒極了等意義,是對對方的贊美或鼓勵,也可以用它來表示第一;“朝手心吐唾沫”表示動手干活;“翻白眼”表示生氣、挑釁;(正在談話時)“別過臉”表示厭惡、輕視、 蔑視;“手指朝內多次彎曲” 表示喚小朋友過來;“摩拳擦掌” 表示對即將要做的事情迫不及待。“手指向外甩”表示走、離開、滾開的意思;“招手與揮手”表示叫別人過來與再見;“抬起肩膀再放下”表示不知道或無奈;“撓下巴”表示思考,想不出辦法;“食指多次觸碰臉頰”表示嘲笑別人不害臊;把食指豎著放在嘴中間表示安靜或別講話的含義。
2.2 形同義異的體態語
用右手在頸部劃過,在漢文化里,這一動作通常表示“抹脖子”“砍頭”,這是由于我國封建社會往往以斬首作為死刑方式;但在哈薩克族的語境中,這一動作則表示“吃飽”或者對某人“受夠了”的意思,唯獨沒有死刑的含義。 這是因為哈薩克族往往更熟悉絞刑,因而未將這一體態語同死刑聯系起來。 再如,叉腰這個體態語, 漢族無論跟別人說話的時候還是隨便站著的時候都可以兩手放在腰部, 但哈薩克族則不能, 因為叉腰是女子失去丈夫時表達悲痛心情的一種方式。漢族洗完手后可以甩手,但哈薩克族認為洗完手后不能甩手,這樣會甩出病菌或臟污,因此洗完手后要用毛巾擦干。
2.3 形異義同的體態語
對可愛而又調皮的小孩子表達親昵感情時,漢族有時在小孩子的鼻子上刮一下; 而哈薩克族則是輕輕撫摸小孩子的頭。 在親人去世向其他親屬報喪時,漢族會一進門就下跪,以這種體態語來通知;而哈薩克族報喪時,報喪的人會騎著快馬直沖家門,進入房內傳送不吉利的消息。 說錯話或說了不該說的話漢族會捂嘴,而哈薩克族習慣于伸舌頭。漢族在表示“請”這個含義的時候,一般出現在重要的場合或正式場合,右手從腹部向外微曲伸開;而哈薩克民族則是右臂稍微彎曲前伸,右手五指微攏,掌心向上,同時左手手心基本向上,指尖約略靠近右手腕,這也是表示感謝并接受的姿勢,它可以用在飲食活動上,例如,右手端著倒了奶茶、馬奶子或其他流食的碗及其他物品時, 做出以上姿勢就表示“請飲用”“請接受” 的意思, 而對方則應該用同樣的姿勢接碗或物品,表示接受和感謝[5]。 除此之外,在飲茶方面,哈薩克族人在接過倒茶人遞的碗時, 如果想表示感謝就微笑著點一下頭, 而漢族在感謝倒茶人的服務時則用手指輕敲桌面來表示。
2.4 漢哈獨有的體態語
抱拳禮蘊含著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 在見面打招呼的方式上,漢族現在有時仍會采用“抱拳拱手”的傳統方式。 抱拳禮,源于周代以前,有3 000 多年的歷史,是漢族特有的傳統禮儀。 抱拳禮,無高低貴賤之分,是一種類似現代人握手一樣的常規禮儀,也是一種內涵豐富的禮儀。它的姿勢是抱拳,以左手抱右手,自然抱合,松緊適度,拱手,自然于胸前微微晃動,不宜過烈、過高。 在使用拱手禮的時候男女拱手禮也存在差異,據段玉裁所著的《說文解字注·手部》記載:“謂沓其手,右手在內,左手在外。 男之吉拜尚左,女之吉拜尚右。 兇拜反是。 ”可知,男子行拱手禮時,一般右手在內,左手在外;若遇喪事行拱手禮,則正好相反;女子行拱手禮時,左手在內,右手在外,若遇喪事行禮,反之。
哈薩克族比較傳統的打招呼方式則往往先右后左,挨面頰兩次。晚輩拜見長輩時,晚輩俯身向前,長輩親吻晚輩的左面頰, 再親吻右面頰, 最后親吻前額。 年輕媳婦拜見公婆時,要左腿向前,屈膝,成弓步,手心向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放在左膝蓋上行跪拜禮[6]。
當避免霉運時,漢族往往朝前“呸呸”吐幾口,表達驅邪避災之義;而哈薩克族則向左肩后吐三口,這是由于在哈薩克傳說中,左肩上有魔鬼的燈,故而遭遇不幸時會吹滅左肩的燈,使右肩的神燈來保佑自己。
在起誓方面,漢族通常“指天發誓”,但哈薩克族則忌諱這種方式, 他們認為天是上天和天使居住的純凈之地,故而他們往往會把手放在心臟位置,表明自己違背誓言,則任由上天懲罰自己的內心;而漢族把手放在心臟位置, 則主要表達祈禱或擔心憂慮等含義。
3 漢哈體態語存在差異的原因分析
體態語通常是人們在交際過程中, 用以輔助語言表達和傳遞內在情感、 態度的形意結合的交流方式。而漢哈體態語存在的差異,則是由于不同民族在發展過程中, 生活環境和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存在差別,進而使交際的語境存在差異,并導致體態語出現了較大不同。
3.1 不同的生活環境
體態語作為社會交際的工具和社會角色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 它具有民族性,其中又包含著文化和歷史的因素。
哈薩克族是馬背上的民族, 他們的交通工具以馬為主,所以他們的很多體態語都跟馬有關。 譬如,在草原上, 哈薩克族人彼此騎馬相遇, 即便毫不相識,雙方也要勒住馬,在坐騎上相向欠身,彼此致意,同時彼此讓路,目送對方先行;若對方年長,更應致敬問候,表示謙恭,并主動讓路,請年長者先行[7]。 馬鞭盡管對牧民來說十分重要,但走進別人的氈房,特別是老年人的氈房時,是絕對不允許帶進去的,所以他們在進屋時,都要將馬鞭放在門外,然后再進屋,這樣做是表示禮貌和對主人的尊重[8]。 過去,人們在給問路的行人指明方向時不會用手指而是用馬鞭。哈薩克族家中如有客人因事來訪, 可從他手中的鞭型得知事因。 例如, 如果對方把馬鞭塞在馬靴筒腰里,或者插在上衣腰帶中,又或者只是握在手中則可以看出他是來這家尋仇或者報仇來的; 如果客人來訪時將手中的馬鞭掛在氈房外的綁繩上則說明貴客到,主人則會盛情款待。客人若將他手中的馬鞭留在了主人所坐的上席中,則表示貴人是來定親的,如果女方不愿接受這門親事則會把馬鞭送回男方家中,表示拒絕。 德高望重的人或者長者們在解決糾紛時會把馬鞭收起握在手中向上舉起, 懂此法者則會肅靜傾聽。 在比賽及決斗中對判定的結果有抗議者也會把馬鞭扔在眾人眼前, 在爭執不休的談判場中因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敗訴仍不甘心的人也會做同樣的舉動。
漢族歷來以勤勞、 富于創造精神著稱。 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 漢族歷史上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家庭副業,是一種典型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9]。漢族的農業生產在歷史上素來發達,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細作聞名于世,而農業的繁盛也使漢民族盛行敬天法祖的思想。例如,在古代人們會舉行祭祀田神、農神的活動,跪拜天地以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小孩會拿著破掃帚扎成的火把去田地、河邊等地焚燒茅草,為了避免害蟲出現。
3.2 不同的生活習俗
體態語具有明顯的民族性, 不同民族的體態語會因為本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及生活習俗等原因出現較大差異。
在餐具方面,除手抓羊肉和馕等食物外,哈薩克族的羊肉湯等食物均需用勺子來吃, 故而哈薩克族人習慣用手作出勺子的形狀來意指吃飯, 這也體現了生活習慣對體態語的影響[10]。
此外,哈薩克族的游牧生活中,需要不斷地搬遷住所, 因此很少有桌椅等固定家具, 一般都席地而坐,但坐姿男女有別:男子是盤腿而坐,女子右腿屈膝,左腿跪坐[11]。 這些都是在長年累月的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禮儀規范。
漢族主要生活在中原地區,以農耕經濟為主,在飲食方面通常以黍米和菜、肉混合制成,而為了方便撈取食物中的菜葉,漢族往往習慣于使用筷子,正如《禮記·曲禮》中記載:“羹之有菜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由于漢族使用筷子吃飯,所以漢族常用兩手指戳唇表示吃飯[12]。 農耕文化將漢族束縛在土地上,因此相對于哈薩克族來說,漢族很少搬遷,因此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桌椅家具,隨之而來也產生了一系列對人儀態的要求,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如松,坐如鐘”等,也體現了生活習俗同體態語之間的密切聯系。
4 結束語
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工具, 它是人與人之間傳遞感情、態度、信息和想法的主要手段,而非語言的體態語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它與其說是語言的附屬品,倒不如說是語言的延伸,是人際交往中一種傳情達意的方式。了解這一點,不僅有助于理解別人的意圖,而且能夠使自己的表達方式更加豐富,表達效果更加直接,進而使人與人交際更和諧。當然不同民族及不同地區會存在體態語的各種差別, 這勢必會造成溝通交流上的不便,甚至造成阻礙,這就需要語言學習者重視不同民族體態語的學習和積累, 通過了解體態語的差異看到影響這些差異的民族心理、地理歷史、風俗文化等因素,對于語言學習和民族交往交流有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