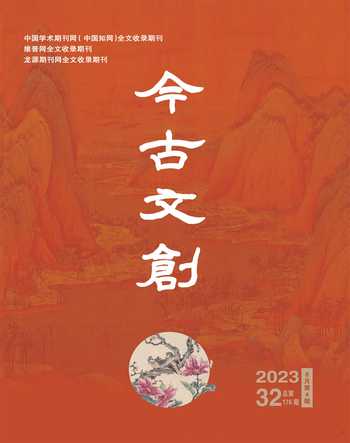唐 · 謝利的身份認同構(gòu)建
【摘要】電影《綠皮書》講述了美國非裔鋼琴家唐·謝利與意裔司機托尼·維勒歐嘉于20世紀60年代由紐約前往美國南部的巡演旅程,以及在旅程中兩人建立的跨種族的友誼的故事。影片中唐·謝利的混雜性身份致使其難以在種族主義環(huán)境中形成身份認同。謝利最終實現(xiàn)身份認同的路徑與霍米·巴巴提出的模擬、第三空間策略暗合。霍米·巴巴的策略有助于消解殖民文化本真性,解構(gòu)二元對立,實現(xiàn)身份協(xié)商。
【關鍵詞】身份認同;混雜性;模擬;第三空間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2-008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24
《綠皮書》由彼得·法雷利執(zhí)導,在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上一舉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和最佳男配角3項大獎。影片根據(jù)美國非裔鋼琴家唐·謝利博士(Don Shirley)及其雇傭的意裔司機兼保鏢托尼·維勒歐嘉(Tony Vallelonga)的一段旅途經(jīng)歷改編。1962年,鋼琴家謝利博士計劃自紐約一路南下巡演。在種族隔離制度尚未結(jié)束的時代,尤其是在種族歧視尤為嚴重的南方,黑人單獨出行會惹來不少麻煩。為確保自身安全和演出的順利舉行,謝利博士雇了托尼為他駕車并保護他的安全。兩人在巡演過程中遭遇不少麻煩,但他們在朝夕相處中互相影響、互相感染,最終跨越種族藩籬,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發(fā)展出一段非同尋常的友誼。[1]
作為一部極具觀賞性的公路喜劇片,《綠皮書》以清晰明快的敘事講述黑人鋼琴家謝利在旅途中不斷完成身份認同建構(gòu),抵抗種族主義的曲折,聚焦黑人在以白人文化為主導的美國社會中對自身身份認同的迷惘。本文從后殖民主義視角,借助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第三空間等理論,通過分析謝利身份認同嬗變的歷程,探討殖民話語內(nèi)在的罅隙,尋求美國非裔群體構(gòu)建自我身份認同的有效途徑。
一、混雜性:顛覆民族本質(zhì)主義
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擴展了傳統(tǒng)的身份認同概念,形成了更廣泛的概念——混合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側(cè)重個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中進行集體身份選擇時所產(chǎn)生的思想震蕩與精神折磨,其中包含著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欣悅。[2]
當前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身份的混雜性成為一種趨勢。霍米·巴巴便介入并批判了嘗試界定民族性的本質(zhì)主義文字。在他看來,民族本身就是一種敘述,它的不確定性如同敘述的不可靠性一樣。[3]《綠皮書》呈現(xiàn)的謝利和托尼兩人的形象都與對其民族的本質(zhì)主義認識相悖,實現(xiàn)了對各自文化身份的解構(gòu)。
謝利自幼便接受了母親的音樂啟蒙,隨母親在各個教區(qū)與音樂廳演出,后又成為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的第一名黑人學生。謝利逐漸成長為影片中呈現(xiàn)的鋼琴大師,出入音樂會,廣泛結(jié)交社會名流。除琴技精湛、獲音樂博士學位外,他還有心理學與禮拜儀式藝術博士學位,精通多國語言。他的住所則位于卡內(nèi)基音樂廳寬敞的閣樓之上,屋內(nèi)陳設雕像、陶瓷與象牙等等令托尼新奇的玩意。初次與托尼見面時,謝利著一身華貴的民族禮服。在日后謝利與托尼的旅行中,也可見謝利并不喜歡炸雞、黑人流行音樂等典型的黑人文化符號。可以說,謝利除膚色外,完全是一個白人精英知識分子形象,這也正是歐洲殖民者進行殖民統(tǒng)治時自居的文明、高雅的偉岸形象。
相比之下,托尼的形象則更“黑”,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警察甚至稱他為“半個黑鬼”。影片開頭花了足足14分鐘介紹其出身背景。托尼居住在紐約最窮的布魯克斯社區(qū),公寓破舊,生活拮據(jù)。在夜總會歇業(yè)后,托尼不得不另尋工作維持生計。他誤以為謝利博士的頭銜意為醫(yī)生,也無法寫出流暢的英文書信,可見他并未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只能從事出賣體力的工作。影片開頭他將為黑人使用過的茶杯直接丟棄的行徑與證明了其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作為意大利裔,托尼并非新英格蘭白人,不具備刻板印象中白人的許多典型特征,他的日常交際也大多局限于同族裔親友。綜上可見,托尼并不符合對白人本質(zhì)主義式的認識。
謝利與托尼在膚色和社會身份上形成了對民族本質(zhì)主義認識的顛覆。兩人也都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中進行集體身份選擇中經(jīng)歷思想與精神上的激蕩。謝利渴望得到白人精英社會的接納,但這一愿望在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難以實現(xiàn),隨著巡演俞走向南方,其黑皮膚引發(fā)的沖突也俞為凸顯;而托尼具有更強烈的種族觀念,他很重視自己作為意大利裔這一文化身份,這也是其經(jīng)濟社會地位卑下、游離于主流白人社會之外的客觀結(jié)果。
二、模擬:消解殖民文化本真性
影片中呈現(xiàn)的不少細節(jié)均表明,謝利在較長時間里以白人精英身份自居。謝利與托尼初次見面時,坐在“酋長寶座”上的謝利衣著華麗,這與坐在沙發(fā)上穿著皺巴巴西服的托尼已經(jīng)形成了不對等關系。在與托尼的相處過程中,謝利也展現(xiàn)了善解人意、翩翩君子的形象。他不厭其煩地教謝利寫作書信,給托尼零用錢購買需要的東西。即便托尼將他專輯名Orpheus(地獄中的俄爾普斯)誤解為Orphan(孤兒),或是討論有關“匹茲堡”的低俗問題,謝利也都沒有動怒,而是耐心理性地予以解釋。謝利認為普遍意義上的黑人是粗魯、無知的,因而抗拒黑人文化。當托尼在車上播放時興的黑人流行音樂時,謝利多次強調(diào)自己學習的是古典樂,從未接觸過黑人通俗音樂,更不知道小理查德、阿瑞莎·富蘭克林、恰比·卻克等當紅黑人歌手。途徑肯塔基時,托尼購買炸雞,并認為謝利一定喜歡吃炸雞,因為炸雞被認為是黑人唯一吃得起的肉類,而謝利認為吃炸雞與其身份不符而不愿意吃。在僅為有色人種提供服務的小酒館內(nèi),謝利不愿意參與黑人們玩的游戲,只一個人安靜地喝酒。謝利行事頗有原則性。當他發(fā)現(xiàn)托尼偷拿走加油站旁禮品店的紀念品石頭時,他要求托尼必須將石頭放回,否則就不能開車。他不愿把吃完的雞骨頭搖下車窗扔掉,還執(zhí)意要托尼停車撿起污染環(huán)境的紙杯。即便遭到拘禁,謝利也不同意托尼通過行賄警察的方式使自己獲救,同樣他也認為仰賴與司法部長關系而脫身的做法并不高尚。此外,托尼也偶爾表現(xiàn)出作為雇主的傲慢。例如,謝利在下車時一定要等待托尼為其打開車門;他嘗試將托尼規(guī)訓至上流社會端莊持重的體系中,要求托尼注意措辭,少說臟話;謝利甚至還要將托尼難念的姓氏“維勒歐嘉”更改為“瓦利”。
謝利作為黑人表現(xiàn)出對白人文化價值觀的追求,這在后殖民批評中往往被稱為“模仿”(mimicry)。當殖民話語鼓勵殖民主體采納殖民者的文化習俗、假設、建制和價值等去“模仿”殖民者時,結(jié)果從來就不是對那些特性的簡單再生產(chǎn),卻往往是一份對殖民者的“模糊的拷貝”。[4]55模擬所帶有的“幾乎相同又不完全一樣”的特性與巴巴理論中對矛盾、混雜等概念一脈相承。模擬人只是一種怪異移位的殖民者形象。
因此,謝利在白人精英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仍是尷尬的。他學習古典樂出身,卻在大多數(shù)時候不被允許彈奏“屬于白人的”古典樂,而只能彈奏流行樂。在旅途不斷深入種族歧視更為嚴重的南方后,他不能為自己定制西服、不能與白人一同用餐、不能與白人同住一間旅館、不能使用白人的衛(wèi)生間,甚至被警察刁難關進監(jiān)獄。謝利歷經(jīng)多次種族歧視后,也無法再保持一直以來的理性克制。
弗朗茨·法農(nóng)在《黑皮膚,白面具》中分析黑人與精神病理學的關系時指出,黑人都是精神分裂者,黑人渴望成為白人,卻又無法成為白人。霍米·巴巴揚棄法農(nóng)的觀點后,進一步指出殖民定型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熟悉是因為它已經(jīng)被部分地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所同化,陌生是因為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并不想讓你那么像,而總要與你保持一定必要的距離和生疏感。如果“他者”可以被教化、正常化、文明化,那么其所謂的“低下性”就不是一種本質(zhì)特性,而只是文化的建構(gòu)。[4]70殖民者往往一方面促進被殖民主體不斷文明化,另一方面又以本體論式的劣等性對這種趨勢加以抵制。不論謝利對白人文化價值觀的模仿達到何種程度,白人社群仍然會從本體論意義上將其排斥在群體之外。由此可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呈現(xiàn)悖論,即殖民者渴望同化被殖民者,又畏懼被殖民者被完全同化——一旦被殖民者被完全同化,殖民者的優(yōu)越性也將蕩然無存。白人社會渴望維護自身的優(yōu)越性,就必須維持主體與他者的二元對立關系,繼續(xù)將被殖民者封閉在原有的本質(zhì)主義認識里,于是謝利便不可能得到白人社會的完全接納。
雖然謝利在身份認同上遭遇挫敗,但他卻在客觀上發(fā)揮了兩個作用:
第一,揭示殖民話語的悖論性。謝利在經(jīng)教化、正常化、文明化后仍然不能進入白人社群,這表明殖民話語是自相矛盾的。在殖民者發(fā)布殖民主義的話語與命令時,如果其立場是游移的,情感是矛盾的,那么他們的話就是充滿縫隙的,對聽話人來說就有了抵抗與協(xié)商的機會,他可以對這個命令進行有利于自己的闡釋。[5]
第二,消解殖民文化的本真性。殖民話語不是單向流動的,被殖民文化在接受殖民話語同化過程中會進行無意識的反抗,“模仿”本身就構(gòu)成對被模仿之物的一種嘲諷。謝利在追求白人文化身份的同時,不自覺地讓原本純粹的白人文化打上黑人印記。
總而言之,謝利對白人文化身份的追求形成了“模擬”。模擬即主體對客體的模仿過程,但由于主體永遠無法達到客體,只能形成一種似像非像的境地,由此消解了殖民文化的本真性。盡管謝利在主觀上尋求融入白人群體而遭遇身份認同的挫敗,卻在客觀上揭示了殖民話語的一道裂縫。
三、第三空間:解構(gòu)二元對立,實現(xiàn)身份協(xié)商
謝利不僅沒有得到白人社群的認同,也得不到黑人社群的認同。阿肯色州途中,謝利與托尼停車休憩,此時路旁農(nóng)莊勞作的黑奴均以驚異的眼神看向儀容整肅的謝利,難以想象他居然雇用了一位白人司機。在黑人旅館,西裝革履的謝利與周圍衣著樸素的黑人同胞格格不入,只能一人在陽臺上喝威士忌;面對黑人同胞的邀約,他也無所適從。此外,謝利的種種生活習慣也都與傳統(tǒng)黑人文化價值觀相距甚遠。這一狀況的出現(xiàn)是白人與黑人文化二元對立的必然結(jié)果。在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下,帶有混雜性身份的個體只能在兩種對立的文化中選擇一種,必然遭受身份上的撕裂。
霍米·巴巴指出,突破二元對立的策略在于“第三空間”。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會打開一片“罅隙性空間”、一種罅隙的時間性,它既反對返回到一種原初性“本質(zhì)主義”的自我意識,也反對放任于一種“過程”中的無盡的分裂的主體。這里所說的罅隙性空間就是“第三空間”。[4]39第三空間是一個沒有二元對立的混雜空間,在這一空間內(nèi),文化差異得以以平等方式呈現(xiàn),文化認同通過相互協(xié)商實現(xiàn)。
影片中,謝利與托尼便實現(xiàn)了一種第三空間式的協(xié)商。影片最初,謝利以雇主身份自居,與托尼的關系并不平等,謝利只認為托尼是個極擅長撒謊的大嘴、喜好賭博、知識匱乏的下等白人,而隨著旅途深入,兩人因共同經(jīng)歷波折艱辛而逐漸加深對彼此的認識,脫離剛剛相識時的粗淺的印象,并最終形成跨種族的友誼。托尼信奉拳頭、槍與金錢,而謝利則更強調(diào)尊嚴并拒絕暴力。謝利的行事風格在南方顯然行不通,因而不時遭到麻煩而陷入需要被幫助的境地,于是在旅途進程中,謝利與托尼的尊卑關系也在發(fā)生悄悄改變,這為兩人友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托尼給妻子寫最后一封信時,謝利稱贊他寫得已經(jīng)很好;而擅長使用金錢解決問題的托尼,在巡演最后一站拒絕餐館服務人員的收買,維護了自己和謝利博士的尊嚴。在謝利博士的幫助和影響下,托尼在性格上日趨完善。另一方面,托尼多次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保護了謝利的生命安全,努力為謝利爭取最優(yōu)質(zhì)的演出條件。托尼一直鼓勵謝利嘗試如炸雞、黑人流行音樂等黑人文化符號。在巡演的最后一站,面對種族主義的挑釁,謝利沒有再委曲求全,而是在托尼的陪伴下走進只面向黑人的橘鳥餐廳,用手拿著炸雞大快朵頤,彈奏肖邦《冬風練習曲》實現(xiàn)自己演奏古典樂的理想后又與黑人樂手合奏一曲布魯斯。在托尼的幫助下,謝利博士逐漸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
謝利博士與托尼從最初不平等的雇傭關系,在一次次事件中逐步接受彼此的行事方式,逐步理解彼此的文化身份。影片最后,謝利駕車載著疲憊的托尼回到托尼家中,并與托尼的家人共度圣誕。謝利攜酒與托尼一家人共飲的場面意味深長,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謝利一人在陽臺孤獨地飲酒的場景。謝利已然打破心中的藩籬,實現(xiàn)身份協(xié)商。此時,謝利已經(jīng)放下自己自居的高高在上的白人觀念,表現(xiàn)出對托尼的尊重,這正是兩人第三空間文化協(xié)商的結(jié)果。
黑格爾用“主-奴”的關系范疇來論述二元對立中的承認問題。在二元對立的體系內(nèi),雙方力量不對等,形成主奴關系。奴隸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屈從于主人,喪失自我意識的實現(xiàn),因而奴隸已喪失作為人的資格,奴隸指向主人的承認只是一個“非人”對人的承認,而主人欲求的承認則是一個與其地位對等的具有自我意識的“自我”,在兩者之間只有奴隸的“一種片面和不平衡的承認”。[6]在主奴關系中,主奴雙方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承認。第三空間正是試圖解構(gòu)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對抗斗爭關系,它并非是差異的或抗爭性的立場位置的大結(jié)合,相反它“既非這個,也非那個,而是之外的某物”。謝利放下雇主身份,與托尼實現(xiàn)身份協(xié)商。相應的,在白人與黑人的關系中,或者更宏觀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中,雙方都必須放下傲慢的民族本質(zhì)主義,在平等基礎上展開協(xié)商,才能形成主體層面的互認。
四、結(jié)語
縱觀整部電影,謝利的南巡演出似乎對美國南方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觀念影響甚微。但謝利的經(jīng)歷揭示了一條后殖民主義的反抗策略,即通過模擬消解殖民文化的本真性,在第三空間內(nèi)解構(gòu)二元對立,實現(xiàn)身份協(xié)商。影片也啟示我們,在當代文化多元的世界中要消除對民族、身份的本質(zhì)主義認識,以世界主義的開放、包容心態(tài)與各民族開展平等的文化協(xié)商,消解民族文化間的沖突。
參考文獻:
[1]鞠薇.“神奇黑人”和“白人救世主”——電影《綠皮書》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種族關系呈現(xiàn)[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04):69-73.
[2]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02):37-44.
[3]王寧.敘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J].外國文學,2002,(06):48-55.
[4]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研究[D].北京語言大學,2004.
[5]賀玉高.霍米·巴巴的雜交身份理論及其不滿[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8(05):222-226.
[6]陳良斌.“主奴辯證法”的揚棄與承認的重建——從黑格爾的“主-奴關系”論到馬克思的承認理論[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2(05):118-124.
作者簡介:
仲靖,男,江蘇淮安人,河南大學外語學院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