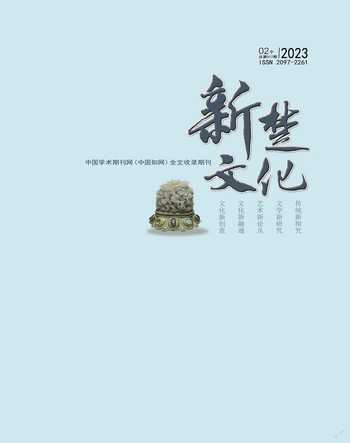“道”的不可言說性探析
蔡梓忻
【摘要】“道”在老子哲學中是核心概念,老子由“道”展開其整個哲學理論系統,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本體論學說,將“道”提升為統攝一切存在的根本。自老子提出“道”,它就是不可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道”難以用語言、概念來表述的特征,體現出老子哲學思想的形學本色,從道不可言說的性質出發,分析不可言說的原因、特征及其表達方式,說明道本就不可言說的樣貌。
【關鍵詞】老子;道;《道德經》;不可言說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5-0004-04
“道”的本意是道路,《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從辵,從首。一達謂之道。”[1]由道路之義可引申作動詞“取道、經過”,引申為抽象義“方法、規律、學說”等。而老子則將“道”第一次抽象到哲學的最高范疇。《道德經》首章即言:“道可道非常道。”[2]表示道的不可言說,認為一旦將“道”言說出來,也就非“常道”了。莊子也有類似的闡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莊子《知北游》)“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3](莊子《齊物論》)等論說,也都表示著語言表達“道”的局限性,用語言表達的“道”是不完整的,會造成對“道”的含義的虧損。越用語言描述越是遠離道的本質,不可言說也就成為“道”的一個顯著特征。
一、形而上的“道”難以用形而下的語言講清
首先,在討論“本體”式的具有“超驗的”意味上的“道”是形而上的,區別于具體的形下世界,《周易·系詞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4]老子所說的“常道”即是形上之道,“非常道”便是形下之器。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5]普通的“非常道”是有各種具體的規定的特性的,“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3](莊子《達生》),因而是可以言說的,而“常道”是形上的本體,《道德經》中講“道”為“萬物之奧也”[2](《道德經》第六十二章),“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 [2](《道德經》第十四章),“常道”是無形無象,沒有規定性的,也即超越了具體可名狀的有限存在物的無限的形而上本體,自然也就難以用形而下的語言描述。因此老子取名為“道”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2](《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王弼在此注道“名以定形,字以稱可”[4]。“名”是切中事物本質的嚴格的命名,“字”“稱可”只是反映事物與稱謂相應的一定特征,因此老子是在無法言說“道”的情況下“字之曰道”。王弼注解說:“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5]即是用“道”來表達其“大”這一特征的稱謂,所以“道”是“字”而不是“名”,“道”這個總括天地陰陽、宇宙萬物的至大的稱謂本身是有限的,不能與真正的終極本源相提并論,由于“道”本身是什么,老子認為是不知道的,于是只能字曰道,這也表現了老子認為形下的語言難以為形上本體的“道”來命“名”。莊子也說“道之為名,所假而行”[3](《莊子·則陽》)。
其次,僅是道家所談的“道”也有著復雜的含義,“道”的內涵不是唯一的,在不同語境之下有不同的涵義。例如,在老子看來,“道”首先是天地萬物的本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2](《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創生萬物,為萬物之母,但不為任何事物所生。其次“道”是實存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道德經》第二十一章)。“道”雖然“惟恍惟惚”,似有似無,但是是實存的。再次,道是世間萬物運行的規律,老子認為世間萬物運行的規律是由道支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2](第二十五章),“道”廣大無邊,周流不息,伸展遙遠又回歸本原。僅老子的“道”就已經有豐富的內涵,“道”作為一個超出經驗世界的抽象的最高本體,是幾乎無法言說明白的,語言能夠描繪的東西是有限的,而道體是無限的。老子之道作為最高的形而上的本體,逐漸成為整個中國哲學領域乃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概念,并經由后世,不斷增添新的內容。
二、道變化于靜與動之間
“道”不是寂靜不動,亙古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周流運動,發用流行的。老子說道是“周行而不殆”[2](《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是循環運行、永不停息、永不衰竭的,正是由于道在無止境的運動中,才能創生萬物。“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2](《道德經》第五章)也是說明“道”生生不息,動而不止的本性。并且老子以“反”“復”等來說明了“道”生生不息運動的無限性。《周易》中也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4](《周易·系詞下》)《周易》構建了一個運動變化的形而上體系,干道變化,則萬物漸始,而坤道變化,則萬物受生,“變化”是《周易》對世界狀態的概括,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也表達出道是動極而靜,靜極而動的動態過程。韓非子也表述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6](《解老》),荀子也有類似表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7](荀子《解蔽》)。因此道本身并不是靜止不動的道運動不永不停歇的,處于永恒的運行變化之中,不斷地生化流行出萬物,這為用語言表述“道”增加了難度。
三、中國傳統詩化語言的表達方式
“道可道,非常道”構成了語言表達的難題,“道”在本性上不可說,但是又不得不用語言言說,“道”的難以表述和理解,同語言表達的狹隘性和中國傳統的語言表達方式也有關。
(一)受限于語言表達的局限性
亞里士多德說過語言表達是心靈印象的符號,文字是語言的符號。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也表示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體系。“作為事物的符號,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語言與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本質的聯系,一個事物之所以用某個詞語來代表,完全與該事物的本質無關。一個事物之所以用某個詞語來代表,完全是一個民族的習慣的產物,是約定俗成的。”[8]因此,語言是人類約定俗成的一種符號,與其所代表的事物沒有天然的、必然的聯系,那么語言也就無法反映所指代的事物的真實原貌,于是在傳達信息時,就會削弱其傳情達意的功能,因此語言本就很難對事物做出全面表述,那么面對“道”這種極其抽象、且復雜模糊的對象的時候,想要清楚地言說就更加困難,反而會造成其意義上的殘缺和扭曲,以至于詞不達意。同時,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隨之發生改變,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改變,語言符號與意義的聯系也會發生變化,同一語言符號,過去、現在與將來所表達的意義可能大有不同,產生的語境也可能不同,從而造成理解的偏差。
(二)漢字表意具有本土文化的特點
漢字是由古老的象形文字演變而來的表意文字,以“六書”即象形、形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等方法構字。相比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漢字重在表意,借助可感的形象符號標記語言指稱的客觀對象,一字可以多義,一義可以多字,因此漢字在表達上就具有模糊性、廣泛性,也造成了《易經》所說的“言不盡意”。
(三)詩化的語言表達方式
基于語言本身的局限性和中國文字的特性,中國傳統的語言表述方式就是一種詩化的含蓄的表達方式,強調意境,欣賞言簡意賅、言少意足。“意”有著重要的地位,用很少的字營造出豐富的意境來傳達信息是中國傳統語言表達的常見方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9](《論語·衛靈公》),老子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2](《道德經》第四十五章),莊子說“所以論道,而非道也”[3](《莊子·知北游》),于是對“道”的闡述,不是做邏輯的言說,而要用詩化的語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4](《周易·系詞上》)。對于“道”的論說,不是以西方慣用的“某某某是某某某”的下定義的方式,而是以隱喻、寓言等“象”的句法,為縹緲的“道”立象,用“象”來隱喻指涉“道”,“道”體現在萬物中,那么認識“道”就可以借助“物”“象”來表現,用描述性的方式,闡述對“道”的想象和體悟,從而立象以盡意。
1.以描寫的表達方式塑造“道”的形象
對“道”的闡釋,老子在《道德經》中不以定義、判斷的方式言說,而是以描寫的表達方式,塑造一個形象,通過描繪“道”的“象”,引發個體在頭腦中對“道”的想象和感受。如:“(道)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2](《道德經》第四章)“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2](《道德經》第十五章)老子用“似……”“……兮”“若……”來描述“道”,使人在頭腦中得以形成“道”的“象”。
老子論“道”時,還以一些具體的、形下可感的事物來類比“道”以求理解,對“道”的隱喻方式有很多,“水”“母”“牝”等都是他常用的事物。例如在闡發“道”時,貫穿著以“水”為隱喻的表達,老子選擇生活中最常見的水作為隱喻來詮釋“道”,以“水”的特性來詮釋“道”的特征。老子認為水的特性是處下、柔弱、不爭,這些特點與“道”相合,“天下莫柔弱于水”[2](第七十八章),但同時,水又具有強大的力量,長養萬物,依據對水的經驗性的認識,借水喻道,便于理解“道”的特性。此外還有關于“牝”的隱喻,“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2](《道德經》第六章),著眼于“牝”(母)的產生生命的方面,“牝”是雌性的獸類動物,用“玄牝”借喻有無限造物能力的“道”,植物、動物、人類生命的產生延續是由雌性完成的,谷神即生養之神,“轂,生也”。老子用“牝”隱喻道生化萬物的“生”的特性。此外還有以“弓”來喻“道”,如:“天之道,其猶張弓歟?”[2](《道德經》第七十七章)儒家在論述“道”“仁”“德”等的時候,在話語表達模式上也具有同樣的取向,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9](《論語·陽貨》)天以“四時行,百物生”的“象”與人進行對話,與道家的表達方式異曲同工,還有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9](《論語·顏淵》)
2.以故事、寓言的方式體現“道”
莊子擅長以寓言的形式表達對“道”的認識,通過講述故事,借他人之口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樣的表達既生動形象,又增強了可信度。在《莊子》中,幾乎都是以各種看似縹緲、奇詭的故事構成,故事中的鳥獸蟲魚、神鬼精怪、歷史人物甚至是各類杜撰的人物都是莊子的傳聲筒,通過他們之口傳達的是莊子的想法。如《莊子·逍遙游》中惠子與莊子爭辯大瓠——“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3]惠施認為,葫蘆太大,不能做容器盛水,也不能剖開舀酒舀湯,是無用之物,意在諷刺莊子學說大而空洞,玄而無用,莊子則反駁凡物皆有用,大有大用,小有小用。莊子擅長從各種寓言、故事入手,依托形下的現實經驗展開,最終導向形上的“道”。在《莊子》中,這種寓言式的表達比比皆是,如庖丁解牛、莊周夢蝶、莊子與惠施論魚等。寓言既是莊子言說自己思想的方式,同時也是莊子想要言說的內容本身。同樣的方式在《論語》中也出現了,《論語》常以孔子與弟子對話的故事的方式論說“道”“仁”“德”“禮”等,例如《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讓三人談談自己的志向。通過對話,三人表達了自己的志向,孔子贊賞了曾皙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吾雩,詠而歸”[9]。類似的話語模式在《論語》中也不少見。
3.小言與大言
這種“立象以盡意”的表達方式是中國傳統的詩化表達,“象形”漢字是形成這種詩化表達的基礎。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寫言生于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肯定“象”的中介作用,通過“象”來領會“言”,這種詩的語言可以通過莊子提出的“小言”“大言”進行理解。“大言炎炎,小言詹詹”[3](《莊子·齊物論》),“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3](《莊子·天地》)。“小言”是“常言”“俗言”,局限于描述形下的器物世界,“小言”不能得“道”,反而會遮蔽“道”,“大言”則是“道體之言”,可以通“至道”,與“道”溝通,是生命“詩意的道說”[10]。“大言”就是“去言”,“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3](《莊子·徐無鬼》);“至言”就是“去言”,“道言”的本質就是去言、不言的,即“道”就是“不可言說”。
4.悟道的方式
因“道”的“不可言說”,以及詩化的語言表達方式,道家提倡的理解“道”的重要方式就是“心齋坐忘”“妙悟”“得意忘言”的方式,“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3](《莊子·外物》)。“道”并不是通過語言表達講清的,道家希望,聞“道”者,不執著于語言本身,而是通過體悟的方式“悟”道,通過體悟言外之意,而達到“道”的境界[11]。
參考文獻:
[1]許慎.臧克和,王平,校訂.說文解字新訂[M].北京:中華書局,2002.
[2]王弼,注.老子道德經[M]∥蔡元培.諸子集成:第3卷.香港:中華書局,1978.
[3]王先謙,注.莊子集釋[M]∥蔡元培.諸子集成:第4卷.香港:中華書局,1978.
[4]孔穎達.周易正義[M].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9.
[5]王弼.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王先慎,注.韓非子集解[M]∥蔡元培.諸子集成:第7卷.香港:中華書局,1978.
[7]王先謙,注.荀子集解[M]∥蔡元培.諸子集成:第4卷.香港:中華書局,1978.
[8]馬佩.語言邏輯[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9]蔡元培.諸子集成:第1卷[M].香港:中華書局,1978.
[10]尚歡.從符號化建制到詩意的道說——基于索緒爾語言學的“結構”之思[J].理論界,2021(05):72-78.
[11]孫瑋志.從“道可道,非常道”看《道德經》的表達困境[J].銅仁學院學報,2020,22(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