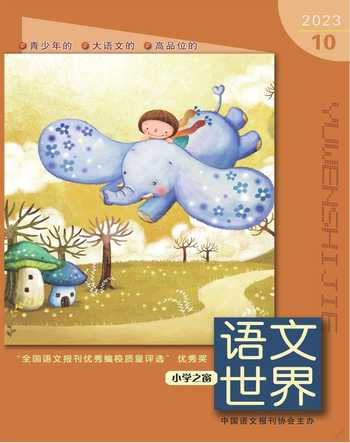實現文本深度解讀的多元視角探索
逯青
文本解讀被視為有效備課和高效教學的前提,但在教學實踐中,許多教師習慣把課文看上一兩遍,再看看教師用書,就算完成了文本解讀。這樣的文本解讀難以支撐課堂教學,教學效果可想而知。有鑒于此,教師要在課前認真地研讀文本,以多元化的視角對文本進行深入探究,找到屬于自己且適合課堂運用的解讀方式,這樣才能在課堂教學中游刃有余,輕松地把學生引入深度學習之中。
一、從文體視角進行解讀
統編教材安排了豐富的文體,以單元閱讀形式推出的文體就有童話、寓言、神話、現代詩、民間故事、小說(含古典名著、外國名著)等。但是,有些教師在教學中不論什么文體教起來都一個樣,走的都是課題教學、初讀課文、精讀課文、總結課文的套路,毫無疑問,這樣的閱讀教學,學生的閱讀能力是很難有長進的。破解這樣的困局,教師首先要在文本解讀時重視從文體視角出發,把握文體的特點后,找到深入閱讀文本的有效抓手。
如教學五年級下冊的《跳水》,課文所在單元語文要素學習目標是“了解人物的思維過程,加深對課文內容的理解”,但不能因為重視引導學生體會思維過程就忽視文體特點,相反教師要做的是體會小說中人物的思維過程,理解人物形象,注意從情節的發展中尋覓隱含的因果關系,找出人物內在的思維發展軌跡。可見,教師在文本解讀中需要重視對小說文體特征的把握;編者也通過課后練習提示教師引導學生從小說情節開始進入文本解讀。課后練習1是“默讀故事的起因、經過和結果,把下面的內容填寫完整,再講講這個故事。水手拿猴子取樂——( )——( )”。這里說的事情發展的順序,啟發教師在文本解讀中先要按照小說情節進行把握,即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然后進入到對小說情節的梳理,以猴子、孩子、水手三者交替活動影響與推動情節的發展:猴子在被水手取樂后,轉而拿走孩子(船長兒子)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并爬上了桅桿取樂孩子,引發水手的笑聲,氣得孩子爬上桅桿去追猴子……這是從思維發展的學習要求,此時教師應注意解讀出當孩子爬上第一根橫木時,如果在平常情況下,水手們會意識到有危險并對孩子提出警告與要求,但那一刻水手們都沉浸在猴子與孩子的玩樂中,一心只想著看熱鬧,在發出的陣陣歡笑聲中發泄船行大海中的枯燥寂寞,忘記了接下來會發生的危險。這樣就能夠從情節的發展中,推測人物的思維發展與變化。此外,在船長拿槍逼兒子跳海這一情節發展的高潮中,教師也需要停下來思考:此時此刻,船長是怎么作出這樣的決定的,以達到了解人物思維過程的學習目標。這樣的解讀,充分體現了文體視角,從小說情節發展中看人物思維過程,解讀頗有深度。
二、從原著視角進行解讀
統編教材選入的課文,有不少是從名著中節選的片段,即使不是節選的很多在選作課文時也有改動,足見課文與原著之間肯定存在不同。教師在解讀文本時,如果結合、對照原著進行研讀,往往會有新的收獲與發現,這也是文本深度解讀的重要視角。
如教學三年級下冊的《燕子》,課文是從鄭振鐸先生的散文《海燕》的第1自然段中節選的。盡管課文所在單元的語文要素學習目標是“試著一邊讀一邊想象畫面”和“體會優美生動的詞句”,但有些教師在解讀文本時受原人教版教材編者改編的影響,即把課文結尾“有趣的一幅圖畫”變成了五線譜譜出的“春天贊歌”,因而喜歡用燕子與春天來統攝全文,解讀的結果是:燕子在春光中飛來,在天空中斜飛,在湖面上掠過,在電線上停歇,給早春的山光水色增添了生機,把春光點綴得更美麗。這樣的解讀顯得有些平面化,如果教師讀讀鄭振鐸的原文,了解文章的創作背景(被迫離開家鄉遠去歐洲的途中在大海上看到海燕),就會發現文本中的小燕子是作者在對家鄉的回想中出現的;尤其是讀原文結尾的“啊,鄉愁呀,如輕煙似的鄉愁呀”,就能夠感受到作者在小燕子身上同樣寄托著揮之不去的鄉愁。重視從原著的視角出發解讀文本,就不應過度強調小燕子與春天的關系,反而需要關注一些“飛倦了”的燕子帶來的有趣圖畫與作者背井離鄉形成的對比,當然這只是教師的把握。至于學生,則需要從每個自然段中讀出獨特的畫面,關注作者用怎樣生動的語言來描繪畫面,能夠注意到燕子飛行的畫面與停歇的畫面背后的情感更好。
三、從作者視角進行解讀
作者每寫一篇文章都是有感而發的,這種“感”源自內心的觸動,必然會受到時代背景和個人境遇的影響。這些影響往往以隱含的方式出現在文本中,教師在解讀文本時,就需要學會站在作者視角聯系作者的人生經歷進行研讀,從而把握隱含在文本中的深層內涵與情感密碼。
如教學六年級下冊的《匆匆》,作者朱自清以飽含深情、清新優美的文筆表達了對時光易逝的感嘆以及對生命價值的思考,以此啟發讀者珍惜時間。在文章開頭部分,朱自清以燕子、楊柳、桃花三個充滿春天氣息的美好事物組成的排比句來表達春去春又回的感覺,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流露出的是一種充滿哀傷、彷徨的情感,感嘆自己過去的八千多日里“除了徘徊,又剩下些什么呢”,表達出沉重悲憤的語氣;前后之間情感變化十分明顯。這難道僅僅是因為朱自清感覺時光流逝得太快嗎?如何理解這種變化就需要聯系他的經歷來看。朱自清在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1921年參加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時期的重要作家之一。而到了《匆匆》創作的1922年,中國處于五四運動高潮過后的失落期,內有軍閥混戰不休,外有帝國主義侵略。這種內憂外患讓朱自清深感痛苦不安,所以盡管他個人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越來越好的成績,但他仍然感覺到個人的這點成就在國家與民族的重重危機面前,就“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個人的命運只有與國家、民族、時代結合起來才能不“白白走這一遭”。這樣的解讀才能體現出朱自清在《匆匆》中借時光流逝所表達感慨的深刻性。
四、從學生視角進行解讀
上述教師對文本進行的深度解讀最終還需要落實到學生的學習需要上,也就是說在文本解讀中教師還需要重視從學生視角進行解讀,即解讀出適合學生理解的內容深度,否則解讀得再深刻也是徒勞無功的。從學生視角進行解讀,教師需要考慮學生的年齡、知識、經驗、思維等多方面因素,確定學生在感受、理解、欣賞與評價上的最近發展區。教師以此作為立足點進行文本解讀,才能找到學生對文本的興趣點、疑惑點和難點。
如教學五年級上冊的《落花生》,課文所在單元語文要素學習目標是“初步理解課文借助具體事物抒發感情的方法”,教師一讀就明白課文是采用借物抒情的方法,學生讀課文時盡管在前一課《白鷺》學習中接觸了借物抒情的方法,但是對課文怎么借助具體事物抒發什么樣的感情感到茫然;換言之,這就是學生解讀《落花生》的盲點。教師在此應該弄清楚抒情方法對于小學生來說是很虛的東西,因而需要教師適時補充,從抒情的基本方式說起,舉例解說間接抒情中有借景抒情、借物抒情還有托物言志,《落花生》就屬于托物言志的間接抒情方式。從學生視角進行解讀,教師才能找到文本解讀的關鍵所在。
總之,教師只有從多元化的視角對文本進行深度解讀,才能找準教學目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