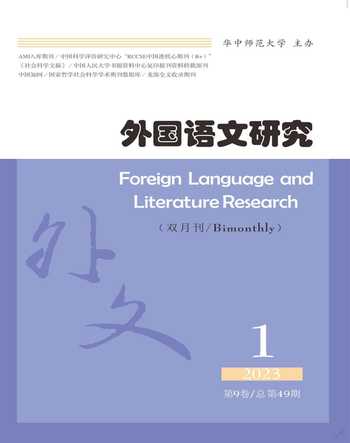非自然敘事與認知
張玉紅 許慶紅
關鍵詞:非自然敘事學;反模仿;認知
作者簡介:張玉紅,安徽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安徽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和美國、新西蘭族裔女性文學。許慶紅,安徽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主要從事英語文學、西方文論和比較文學等領域的研究。
近些年,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呈上升趨勢,隨著認知研究①的蓬勃發展,以及國內學者對“ 物敘事” ②的提出與研究進展,關于非自然敘事的研究空間也得以極大拓展。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越來越注重與認知科學的交叉,文學研究中出現了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文學研究者借鑒認知科學提供的理論啟示、研究方法乃至技術手段,拓展相關文學研究理論視域、更新研究方法、延伸研究路徑(熊沐清296)。20 世紀60 年代以來,隨著文學進入更加具有先鋒性的后現代主義時期,文學敘事藝術繼現代主義敘事研究之后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關注點。后現代敘事實踐的創新速度驚人,而敘事理論卻發展緩慢,未能將這些創新充分概念化,并整合到現有的敘事理論模型之中。在這一背景下,非自然敘事學(Unnatural Narratology)的概念應勢而生。
非自然敘事學始于1987 年其首創者布萊恩· 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對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反常或極端敘事的探討, 旨在分析現當代歐美小說多種反模仿的敘事行為。在《非自然的聲音:現當代小說的極端化敘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中論及“ 非自然” 的概念時,理查森把非自然界定為反模仿、陌生化的場景、實體和事件,如不可能的空間、顛倒的因果進程以及公然蔑視自然口頭敘事范式的敘述行為(48- 52)。他認為,面對偏離現實主義認知框架的時間形式,經典敘事學的時序概念束手無策。在對模仿(mimetic)、非模仿(nonmimetic)和反模仿(anti-mimetic)的虛構作品進行區分之后,理查森繼而指出,只有反模仿才是非自然的。受莫妮卡· 弗盧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與理查森的啟發,一批敘事學研究者,如揚· 阿爾貝(Jan Alber)、亨里克· 斯科夫· 尼爾森(HenrikSkov Nielsen)及斯特凡· 伊韋爾森(Stefan Iversen)也加入到自然敘事學與非自然敘事學的辯論中,與理查森一起撰文闡述非自然敘事理論。“ 非自然敘事” 與“ 非自然敘事學” 概念在阿爾貝、伊韋爾森、尼爾森以及理查森的合著論文《非自然敘事、非自然敘事學—— 超越模仿的范式》(“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Mimetic Models”)中得以正式形成:“ 非自然敘事學” 所研究的“ 非自然敘事” 指的是“ 違背傳統現實主義參數的反模仿文本,或者是超越自然敘事規約的反模仿文本”(114)。
作為一種新的詩學,非自然敘事學研究一直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之中。其研究者從未希望或試圖將非自然敘事學視為嚴格統一的敘事研究范式,他們在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目標等方面觀點并不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大陣營,即本質派與非本質派。前者以理查森和尼爾森為代表,關注文本的“ 內部本質”;后者以阿爾貝為代表,重視對文本進行“ 外部闡釋”(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19)。對于非自然敘事學研究的“ 內部本質” 與“ 外部闡釋” 陣營的形成,認知進化與文化進化理論提供了嶄新的闡釋視角。認知與文化有著相互纏繞、相互促進的關系,因為人是進化的產物,基因、環境和文化促進了人的進化,也影響了人對文學的闡釋。認知進化與敘事有著密切的關系,敘事是文化學習,也是社會學習,而文學研究者們“ 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話語、方法和技術去討論文學藝術問題或文藝作品,其中有些人有著自覺的理論建構意識,引發了許多傳統的、經典的和流行的文學研究范式嬗變,甚或衍生出全新的研究范式”(熊沐清299)。隨著認知與進化的發展,敘事研究的概念與實踐也呈現出豐富多樣性。
非自然敘事的基本概念方面,理查森意識到文學進化過程中“ 模仿論” 所受到的挑戰,“在文學進化過程中,模仿的規約持續受到原創作品中不斷涌現的新文學形式的挑戰”(“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88)。不同于傳統敘事中的“模仿”,理查森提出了“反模仿”的敘事概念和實踐,認為違反非虛構敘事前提、現實主義實踐的非自然事件、人物、背景或框架表征,或其他建立在非虛構敘事基礎之上的詩學,都是“反模仿”的(Unnatural Narrative 3-5)。以理查森為代表的本質派從敘事本質出發,關注文本對敘事規約的反叛,將文本中的非自然敘事等同于“反模仿”敘事,認為非自然敘事指的是那些“反模仿事件、人物、場景或敘述行為的敘事”(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5),而現有敘事理論“幾乎是完全建立在模仿敘事作品和模仿概念的基礎之上的,并未給當代文學作品中廣泛存在的創造性的、不可能的、戲仿的,或矛盾的事件和人物留有任何理論空間”(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87-388)。理查森以莎士比亞戲劇《仲夏夜之夢》和《麥克白》為例,撰文探討劇中的“反模仿”敘事時間,解釋其中的時間和因果關系的非自然構造,引起人們對廣泛存在的各種非自然敘事文本的注意(Richardson, “Time is Out of Joint” 299, “Hours Dreadful and Things Strange” 284)。事實上,“反模仿”的敘事概念和實踐與后現代小說的敘事實踐相互纏繞,如弗盧德尼克在《走向“自然的”敘事學》(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一文中所言,結構主義敘事理論中的自然敘事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無法對違背現實主義傳統的后現代小說中的反常敘事模式做出合理解釋。基于這一問題,理查森撰文對弗盧德尼克的自然敘事理論做了補充,在自然敘事學的基礎上提出“非自然敘事學”,專門研究虛構敘事文本中具有“反模仿”元素或呈現“反模仿”特征的事件、人物、環境和結構。通過借鑒后現代主義理論,理查森研究分析了果戈里、康拉德及貝克特等作家作品中呈現出的違反常規敘述的敘事時間、聲音和情節進程,確定了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的六種類型時間結構,構建了一個非自然的模型③。
通過區分“反模仿”(即適當的非自然)、“非模仿”(或傳統的非現實主義)和“模仿”(或現實主義),理查森認為違反模仿常規是非自然敘事的首要特征。一個與現實世界具有相似的概率標準的虛構世界是模仿的,一個基于熟悉的命運或天意概念的超自然世界是非模仿的,而一個過去的事件可以被改變或抹去的世界是反模仿的或非自然的(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92-393)。因此,本質派通過解讀虛構敘事文本中與故事、時間、敘述、人物和結構相關的“反模仿”元素,發掘在主流敘事建構過程中被忽略的敘事實踐,為當代文學作品中廣泛存在的反模仿敘事提供了一種闡釋方法,豐富了敘事的概念與實踐,實現了文學闡釋與認知進化的同步發展。
從認知科學的角度而言,進化是認知的,文化也是認知的,認知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維度,而文化本身的進化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影響了文學研究,人的認知生態位說明,文化比基因更能促進人的進化。因此,多數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本都旨在打破現實主義,嘗試模仿幻覺、嘲弄“自然”文本規約,但是,自然敘事理論似乎無法給讀者提供闡釋和認知這些具有“非自然敘事”元素文本的理論支撐。理查森等人基于認知理論,提出可以依照流動的、變化的規約,通過“豐富認知框架”(frame enrichment)來拓展敘事研究(“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118)。
綜合來看,無論是本質派還是非本質派,二者對非自然這一概念的界定都是以反模仿為理論基礎,強調偏離現實世界認知框架的各種敘事策略。然而,與“ 內部本質”陣營有所不同,在非自然敘事實踐方面,非本質派傾向于從認知文化層面闡釋和解讀文本里的非自然元素。阿爾貝倡導使用認知敘事學的相關成果去解讀一些敘事文本依賴并挑戰人類基本的意義建構能力的行為,“ 非自然敘事文本中大量存在的棘手難題可以借用認知敘事學的一些觀點進行闡明”,通過闡釋和理解非自然敘事,發掘其認知功能及其意蘊,“ 讓奇特的敘事更加具有可讀性”(“Impossible Storyworlds” 81)。將現實的經驗世界視為基本參照,同時關注讀者的認知維度,非本質派更偏重于尋找非自然事件認知上的作用,并判斷其意義。
從認知角度而言,非自然敘事學為敘事文本中非自然元素的系統研究提供了新的認知敘事類別和小說中敘事表現的擴展模型,包括類型多樣的非自然敘述者、非自然人物、不可能的事件序列和非自然場景。從理論屬性來看,非自然敘事學者認為他們并非意欲否定、推翻或替代現有的其他敘事理論,而是通過關注虛構文本中那些被忽略的“ 反模仿” 敘事元素,建立“ 一個模仿和反模仿雙重互動的模式”(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 5),對現有敘事理論進行認知方面的補充和拓展。戴維· 赫爾曼(David Herman)認為, 敘事就是一個認知資源庫,通過閱讀敘事,人類可以認識自己的經驗,但“ 任何一個單一的研究視角:模仿、綜合或意識形態的視角,都必然是不充分的。留下來更多的是對反模仿人物的分析和拓展”(234)。赫爾曼從認知科學的基本框架開始理論建構,在敘事學研究中引入心理學前沿理論,豐富了敘事學領域基本概念的內涵,在認知敘事學的道路上不斷開拓。弗盧德尼克將“ 非自然敘事” 界定為“ 邏輯上或認知上的不可能,以及寓言、魔幻、超自然”,認為以自然敘事學為表征的普適認知敘事研究方法不僅可以“ 為敘事性的建構提供理論原型”,而且“ 可以成為認知起源的核心生產模式”(Towards a “Natural”Narratology 234)。弗盧德尼克曾多次撰文對自然敘事學和非自然敘事學之間的異同進行剖析,并與理查森和阿爾貝等人展開對話。就此意義而言,非自然敘事學的研究效果,更多產生于人們對非自然敘事文本的闡釋過程之中,產生于文化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之中所發揮的作用。讀者通過對非自然敘事文本的關注,解讀出作品中被經典敘事理論忽視的那部分內容,使用認知敘事學的相關理論對非自然敘事元素做出合理的解釋,并重新建構意義。
除了前面述及的“ 反模仿” 概念,非自然敘事學中最貼近認知敘事學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 不可能的故事世界”(impossible storyworlds)。阿爾貝在論文《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以及怎么理解它們》(“Impossible Storyworlds-And What to Do with Them”)中首次對“ 非自然” 這一概念做了界定,并闡發其所包含的兩種“ 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其一,“ 非自然” 這個術語指的是物理上、邏輯上或人類世界不可能出現的行為,這些行為已經被“ 規約化”(conventionalization),成為熟悉的敘述表現的慣例。其二,“ 非自然” 還指尚未被“ 規約化” 或者仍然被陌生化或者仍處于被“ 規約化” 過程中的現象,就像后現代主義文本中的大多數非自然元素及其呈現的“ 不可能性”,比如死去的敘述者、化身成其他人物、倒退的時間線和能夠改變形狀的設置一樣。阿爾貝認為,“ 非自然” 這一概念就變成了一個基本的認知類別,給人們留下奇怪、令人不安的印象,“ 認知敘事學的觀點可以幫助闡明非自然元素所造成的大量的、有時難以解決的闡釋困難”,并提倡使用“認知敘事學的研究來闡明有些敘事文本如何不僅僅會依賴而且也會猛烈地挑戰基本的思維理解能力”(“Impossible Storyworlds” 80)。阿爾貝相信,由于我們受到自身認知結構的限制,所以只能通過使用框架和認知草案來研究非自然。阿爾貝認為“敘事中的這類非自然(或不可能)是基于‘自然(真實世界)中的認知框架和草案的,而這種認知框架和草案又是和自然規則、邏輯原則和標準化的人類知識和能力限度相關”(Unnatural Narrative 3)。以阿爾貝為代表的非本質派從認知出發,提出非自然敘事的闡釋策略,幫助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借助真實世界的認知將非自然敘事“規約化”(3)。換言之,要理解非虛構敘事文本中的非自然元素,讀者需要調整、整合或拓展其認知框架,通過認知閱讀,把非自然敘事元素“規約化”。
針對“不可能的世界”,非本質派的研究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相對性的問題。如果將“非自然”定義為物理上或邏輯上的不可能性,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跨文化以及文化的進化或變化,人們將很難決定這些術語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很多概念在某種文化中具備不可能性,但在其他文化中,其可能性卻被廣泛肯定。因此,需要從認知的角度假設科學標準是唯一可能的仲裁者。正如阿爾貝和理查森在他們最新合編的《非自然敘事學:延申、修訂與挑戰》(Unnatural Narratology: Extensions, Revisions and Challenges, 2020)一書中所指出,當把一個行為或事件定性為非自然時,其不可能性通常是根據科學公認的物理定律或邏輯公理來判定的,比如,強風不能像盧西恩(Lucian)的《真實故事》(A True Story)那樣把船吹向月亮。無論人們是否利用愛因斯坦或亞里士多德的科學理論,這些事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能的。邏輯的公理同樣是普遍的:被排除在外的中間法則同樣不會,也不能隨著時間或跨文化而改變。他們認為,非自然敘事學所提出的非自然概念與支配物質世界的已知定律、公認的邏輯原則(如非矛盾原則)或人類對知識和能力的標準限制相矛盾,比如,說話的乳房、尸體,或飛行的島嶼在世界各地和整個時間段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識別非自然敘事的唯一前提是敘事接受者相信這些準則、原則和限制(Alber &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9-10)。雖然本質派與非本質派對非自然的表述不同,但他們都認為,非自然指的是由經驗證據和基礎科學探究建立的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的事物或現象。
事實上,非自然敘事無處不在,甚至會自發地獨立產生。堅持模仿立場的認知敘事學理論強調人類體驗與文學交互作用的同源性,忽視甚至拋棄了許多未被理論化的經典和現代敘事的非自然特征,包括數以千計的反模仿人物(從阿里斯托芬的戲劇到貝克特筆下“無法稱呼的人”,再到兔八哥),以第一人稱復數“我們”敘述的原住民小說,梵語戲劇和中國古典小說,反現實主義的日本能劇,具有很多反現實主義技巧的中世紀敘事。正如阿爾貝和理查森在《非自然敘事學》后記中所言,非自然研究涉及大量西方經典文學作品,從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到詹姆斯·喬伊斯,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從莎士比亞到斯威夫特和菲爾丁,可謂成果頗豐,針對與西方傳統關聯較弱的古典梵語故事、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漫畫、漫畫小說、電影、電視和數字媒體的非自然分析也日漸豐富(Unnatural Narratology 209-218)。因此,每一個時期,每一種類型的非自然敘事都在蓬勃發展,值得研究者從這個廣闊的理論角度進行研究。
縱觀近十年的非自然敘事研究,非自然敘事理論拓寬了研究的邊界,突破了現有敘事理論的模仿偏見,為廣泛存在但長期被忽略的邊緣敘事實踐提供了新的解釋模式,成為敘事理論中一個重要而富有成效的新范式。受到維克多· 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y)、米哈伊爾·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克里斯汀· 布魯克- 羅斯(ChristineBrooke-Rose)、莫妮卡· 弗盧德尼克、布萊恩· 麥克黑爾(Brian McHale)、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和沃納· 沃爾夫(Werner Wolf)等人在敘事理論研究方面的啟發,非自然敘事學家將認知敘事學、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后殖民以及接受理論等其他研究理論融入非自然敘事研究,實現理論和方法的交叉與互補,致力于尋求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④。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非自然敘事的文本案例屬于激進政治運動所尋求的實驗藝術形式,但非自然敘事理論在意識形態上仍是中立的。還有理論家指出,非自然敘事學研究者應該將非自然敘事學與情感研究、文化相對主義、流行文化等研究融合,拓展非自然敘事學的研究范疇,以求在發展過程中不斷修正、完善、拓展其自身的理論建構。然而,在非自然敘事學不斷拓寬研究邊界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作為一個新興的敘事研究范式,非自然敘事理論受到學者們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批評與挑戰。自2010 年起,西方敘事學界對非自然敘事學的研究表現出極大的學術興趣,對其探討的熱度不斷增強。文學研究領域的著名期刊《文體》(Style) 在2016 年第4期以專題論壇的形式,隆重推出“ 非自然敘事學” 專題,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其發起批評和挑戰。有些學者對非自然敘事學的創新性或對模仿的潛在理解持懷疑態度;有些學者則認為,由于非自然敘事學內部未能形成統一的定義,那么從其研究的出發點、內容和屬性三個方面來看,其學理性都不強;還有學者認為非自然敘事學內部在非自然、規約與不可能等概念的界定方面仍存爭議,缺乏作為一個敘事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針對以上的質疑與挑戰,理查森與阿爾貝也圍繞非自然敘事的基本特征、中心策略及其影響在最新出版的《非自然敘事學:延伸、修訂與挑戰》一書的前言部分進行了回應。
非自然敘事理論的內部差異對非自然敘事學作為一個敘事研究新范式的整體性建構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不利于非自然敘事學作為一個一元敘事研究流派的進一步確立。非自然敘事在對現有的模仿敘事研究進行補充和拓展的同時,也因研究者所持立場不同,其內部存在諸多觀點差異,面臨一個如何統籌和整合內部的多維研究視角的問題,但其研究視角的多維性又將吸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輕的研究者,運用非自然敘事理論解讀文本中的非自然元素,推動非自然敘事學迅速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