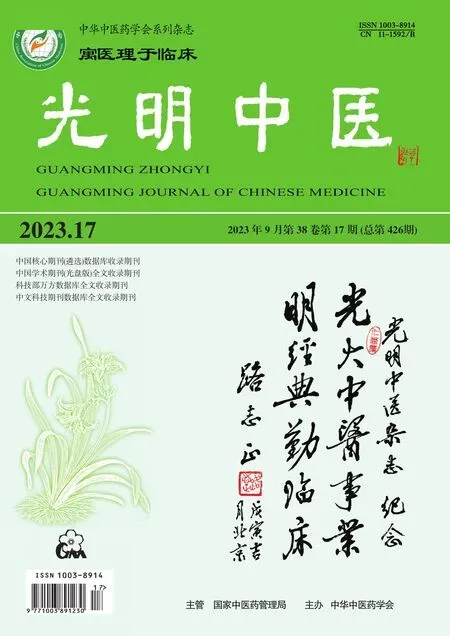火針結合桃紅四物湯外涂治療老年性瘙癢癥臨床觀察*
林楚華 溫鴻源 葛敏恩 龍潔珍 張永杰 黎健東 張貴鋒△
老年性皮膚瘙癢(Senile pruritus, SP)是一種60歲以上老人的常見疾病,發病率為14.2%~41%[1-3],其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認為SP是由于皮脂腺和汗腺分泌減少造成皮膚干燥所引起[4]。另外與甲狀腺功能亢進癥、白血病、惡性腫瘤等疾病也存在聯系[5]。嚴重的SP不僅可以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甚至引起抑郁癥[6]。臨床一般使用鈣調神經磷酸酶抑制劑,盡管其不良反應很少,但仍有患者使用后發展為刺激性皮炎[2];糖皮質激素止癢療效良好,但長期使用會引起皮膚萎縮、毛細血管擴張或過敏,且停藥后戒斷反應明顯[7]。故而,探索治療老年性瘙癢的新型外用藥物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研究發現中醫藥療法,如針刺、中藥熏洗等在治療SP上較西藥具有一定優勢[8],筆者前期試驗中也發現,火針結合桃紅四物湯加味外涂治療SP短期療效可觀[9],但SP病癥遷延難愈,極易反復,因此長期治療對于SP患者十分重要。故本研究旨在探討采用火針+桃紅四物湯加味外涂聯合治療SP的長期療效,具體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20年1月—2022年7月在肇慶醫學高等專科學校附屬醫院接受過診治的120例SP患者,隨機抽簽分為觀察組60例及對照組60例,隨訪2年后,觀察組1例死亡,2例失訪,對照組2例死亡,2例失訪。觀察組:男性36例,女性21例;年齡64~86歲,平均(70.35±5.10)歲;病程7~19個月,平均(13.02±2.03)個月。對照組:男性38例,女性18例;年齡63~85歲,平均(70.52±4.98)歲;病程7~14個月,平均(12.76±1.99)個月。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試驗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知情并簽署同意書。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②符合《中西醫結合臨床皮膚性病學》[9]中的老年性皮膚瘙癢癥的診斷標準;③皮膚瘙癢,無原發性損害,反復搔抓后出現繼發性損害;④瘙癢部位分布均較為分散,且不同部位程度相當。排除標準:①伴肝腎疾病、糖尿病、精神疾病、血液疾病、腫瘤等原發疾病;②合并嚴重心腦血管疾病;③研究中途失訪;④對研究所用治療方法有禁忌或對治療藥物過敏;⑤近期經西醫激素類、抗組胺類藥物治療;⑥患有老年癡呆、精神障礙等無法配合研究。
1.3 治療方法2組患者均接受包括健康宣教及遵醫囑用藥等基礎護理,對照組患者采用氯雷他定(北京雙鷺;國藥準字H20060157;5 mg×10片) 10 mg/次,1次/d,口服治療。觀察組患者采用火針結合桃紅四物湯加味外涂治療[10],桃紅四物湯加味(桃仁10 g、紅花10 g、熟地黃20 g、當歸20 g、白芍20 g、川芎 20 g、制首烏20 g、蒺藜20 g、白鮮皮30 g、百部30 g、皂角刺30 g),用1500 ml水煮成500 ml待藥汁涼后,用開塞露8支加入藥汁中,攪勻后裝入備好的無菌容器(免洗洗手液瓶洗凈消毒)中,使用時,從瓶中擠到醫用棉簽后涂于患處,3次/d。火針(楊氏美容針,平頭)采用散刺法,以阿是穴為主:消毒后,在患處選6~8個點散刺,用火針松散點刺病灶局部,每針間隔約 1.5 cm,隔天1次,每天1組阿是穴;觀察組患者先接受火針治療,局部消毒,待治療處干燥再外涂藥汁。2組治療時間均為4周,隨訪2年。
1.4 觀察指標
1.4.1 瘙癢評分瘙癢評分:從程度、部位、頻率、持續時間以及睡眠5個方面進行評分,對瘙癢癥狀進行評估:①瘙癢程度:由輕到重為0~4分;②瘙癢部位以面積計算標準:頭頸部面積為9%,雙上肢為18%,軀干為27%(含會陰1%、胸腹前側13%、背部13%),雙下肢(含臂部) 46%,瘙癢面積為0則計為0分,0<瘙癢面積≤25%計1分,25%<瘙癢面積≤50%計2分,瘙癢面積≥50%計3分;③瘙癢頻率:無感覺計0分,每日1~3次計1分,4~6次計2分,每日6次以上計3分。④瘙癢持續時間:無感覺計0分,持續1~30 min 計1分,持續30~60 min計2分,持續60 min以上計3分。
1.4.2 抑郁評分老年抑郁量表(GDS-30)[11],采用“是”或“否”的定式回答,“是”計1分,“否”計0分。得分在0~10分為正常,11~20分為輕度抑郁,20~30分為中重度抑郁。以得分≥11分為有抑郁癥狀。
1.4.3 焦慮評分老年焦慮量表(GAI-20)[12],采用“是”或“否”的定式回答,“是”計1分,“否”計0分,得分<9分為正常范圍,得分≥9分為有焦慮癥狀。
1.4.4 睡眠質量評分匹茲堡睡眠量表(PSQI)[13],該量表每個成份采用0~3等級計分,各成份累計得分則為PSQI總分。總分>8分判為有睡眠紊亂狀況。
1.4.5 血清學指標SP的發生與血清炎癥因子之間存在一定聯系[14],因此將測定血清學指標:白介素4 (IL-4)、白介素6 (IL-6)。

2 結果
2.1 2組患者治療前后瘙癢癥狀評分比較治療4周結束后,觀察組在6個月時,瘙癢程度、面積、頻率及持續時間均有顯著降低(均P<0.05),且療效優于對照組(均P<0.05),而對照組僅在6個月時在瘙癢程度上較前明顯好轉(P<0.05),在12、18及24個月時,2組間比較,差異均無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治療前后瘙癢癥狀評分比較 (分,
2.2 2組患者治療前后焦慮癥狀評分比較觀察組在6個月時,患者的焦慮癥狀評分有明顯降低(P<0.05),且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隨訪的第12、18及24個月時,2組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對照組在治療前后,焦慮癥狀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治療前后焦慮癥狀評分比較 (分,
2.3 2組患者治療前后抑郁癥狀評分比較觀察組在6個月時,患者的抑郁癥狀評分明顯降低(P<0.05),且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第12、18及24個月時,2組組間比較,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對照組在治療前后,抑郁癥狀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治療前后抑郁癥狀評分比較 (分,
2.4 2組患者隨訪前后睡眠質量評分比較觀察組在6個月、12個月時,患者的睡眠質量評分均有明顯降低(P<0.05),且6個月時,觀察組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觀察組在隨訪的第18及24個月時,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在治療前后,睡眠質量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患者治療前后睡眠質量評分比較 (分,
2.5 2組患者血清指標比較治療前,2組患者的血清IL-4、IL-6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治療后的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2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指標比較
3 討論
SP被定義為見于60歲以上人群的無原發性皮膚病變的廣泛性瘙癢癥狀[15]。目前SP的病理機制研究尚未完全闡明,多認為其與皮脂腺功能減弱有關,當周圍環境發生變化時SP將被誘發,促使患者對皮膚進行抓撓,而反復抓撓會造成皮膚損傷、疼痛和感染。同時,它還會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不利后果,包括焦慮、抑郁、睡眠模式紊亂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現階段臨床常采用西藥對癥治療[2],但易產生耐藥性及不良作用且長期療效欠佳。
SP屬中醫學“癢風、癢證”范疇,中醫認為此病證屬血虛風燥,治宜祛風止癢、養血潤燥、益腎養肝等為主。中醫藥療法在治療SP的短期療效上已經展現出一定的優勢[16,17],但是SP作為一種遷延難愈的反復性疾病,容易受到季節交替、氣溫、濕度、情緒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故長期有效的治療方法顯得尤為關鍵。
火針療法是指將特制的針具用火燒灼透紅之后,以一定的手法迅速刺入人體局部皮膚肌肉或腧穴內的治療方法,《靈樞·終始第九》言:“癢者,陽也,宜淺刺也”,后世醫家將“火”與“針”結合,發現在治療皮膚病中療效顯著。桃紅四物湯為活血化瘀方中的經典方,由四物湯(當歸、白芍、熟地黃、川芎)加桃仁、紅花組成,具有養血活血、祛瘀生新之功[18],且桃紅四物湯在皮膚病的治療中已經取得初步成效[19,20],因此,本試驗選用針刺聯合中藥外用可調理全身之氣血,起到內外兼顧之功,且針刺的遠期療效在臨床已經得到認可[21-23]。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重,老年人口比例增多,這一群體的生活質量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研究發現,火針聯合桃紅四物湯外涂治療SP的短期療效顯著,在后期的隨訪中,火針聯合中藥外治法在6個月時仍可以緩解患者的瘙癢、抑郁、焦慮及睡眠癥狀,且相較于藥物,中醫聯合療法除了可以緩解瘙癢癥狀外,還可以改善患者整體狀態,起到全身調節的作用。在隨訪結束時,發現聯合療法在各方面比較上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季節變換及年齡增長有關,另外在本試驗中,治療后觀察組與對照組相比較時,炎癥因子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后期試驗中需要進一步探究潛在原因。在今后的試驗中,應聚焦于SP長期療效的治療手段,采取定期干預方式,為進一步改善SP患者生活質量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