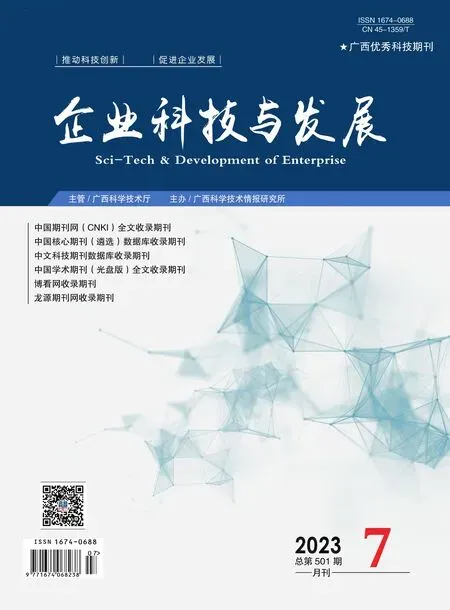基于水泥基復合材料的混凝土梁修復加固研究
覃忠源
(廣西路建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廣西南寧 530001)
0 引言
鋼筋混凝土材料的廣泛應用,推動了現代建筑的發展。鋼筋混凝土受設計不當、氣候條件或使用年限等因素的影響,結構質量日益下降,因此近年來對加固鋼筋混凝土(RC)結構的需求不斷增加。為提高鋼筋混凝土梁的抗彎強度,許多研究者提出采用鋼筋混凝土夾套、鋼纖維增強混凝土(SFRC)夾套、外部黏結鋼板和纖維增強聚合物(FRP)等措施提高混凝土力學性能[1]。然而,鋼筋混凝土夾套與混凝土的界面結合強度低,其脆性不適合提高混凝土延性;SFRC護套與混凝土具有良好的界面黏結強度,但其延展性也較低[2];FRP 和鋼板會導致混凝土表面分層,容易過早失效。因此,為有效地加強RC 結構,必須采用具有延展性的材料,以提高加固效果,提升梁的力學性能。其中,聚乙烯醇混合纖維增強水泥基復合材料(ECC)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工程水泥基復合材料,其在壓縮和拉伸狀態下都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并且具有較好耐火性,可以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曹君輝等[3]發現SPH-ECC 和聚乙烯醇纖維工程水泥基復合材料(PVA-ECC)與普通混凝土具有相似的界面黏結強度,然而PVA-ECC 的極限強度和耐火性較低,與單纖維增強ECC 相比,SPH-ECC 等混合纖維可以提供更高的極限強度和更好的耐火性,以及提供更好的鋼筋防腐蝕保護[4]。然而,目前鮮有研究評估使用混合纖維加強RC 結構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采用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和嵌入式鋼筋的全尺寸加固RC 梁在破壞模式、荷載-中跨撓度曲線、開裂模式、界面黏結滑移、應變分布等方面表現出的性能。研究的開展可為提高混凝土梁修復加固效果及水泥基復合材料的裂縫寬度控制能力提供參考。
1 試驗材料與方法
1.1 試樣制備
本研究選取1根未加固的RC對比梁(CB)和3根加固的RC梁(SB-1、SB-2和SB-3),分別采用不同配置的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和內嵌鋼筋進行四點彎曲荷載試驗。這些梁的截面構型及其配筋細節如圖1 所示。對比梁[圖1(a)]的尺寸為200 mm(寬)×325 mm(高)×3 500 mm(長)。未加固的RC 對比梁被設計為下加固方式,在底部放置3 根直徑為16 mm(D16)的鋼筋,在頂部放置2 根直徑為12 mm(D12)的鋼筋作為吊架[5]。為使混凝土具有足夠的抗剪能力,將馬鐙的中心間距分別設置為100 mm 和125 mm。對于加固梁,采用3 種不同的SPH-ECC 層結構。

圖1 梁橫截面細節(單位:mm)
對于SB-1[圖1(b)],在2 根D16 鋼筋的RC 梁部件底部僅應用了1 層SPH-ECC 層。對于SB-2[圖1(c)],在RC 梁兩側采用2 層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每側采用1 根D16 鋼筋。對于SB-3[圖1(d)],在RC 梁的兩側和底部分別施加SPH-ECC 層,形成“U”形包圍圈,底部放置2 根D16 鋼筋;并且,在RC 梁和SPH-ECC層的所有主鋼筋的兩端均進行90°的彎曲,延長長度為70 mm,實現混凝土和SPH-ECC 與鋼筋之間的界面結合。此外,所有測試的梁均基于實際應用中的全尺寸進行澆筑[6]。
對于CB 梁,鋼筋籠在澆筑混凝土之前制作,然后放置在模板中。混凝土梁在24 h 后脫模,并在自動控制濕度和溫度的霧室中養護55 d,然后進行測試。對于加固型鋼,其RC 型鋼部分按照與CB 型鋼相同的方式進行澆注,當養護齡期為28 d,將RC 梁部件分別移入模板中。然后,按照圖1(a)所示的配置,在RC梁的現澆表面涂抹50 mm厚的SPH-ECC 層。對于SB-1 和SB-3,在澆注鋼筋和SPH-ECC 層之前,將RC 梁進行上下旋轉[7]。對于SB-2,由于鋼筋和SPHECC 層能容易地放置在梁的兩側,因此不需要旋轉。加固后的梁在24 h 后脫模,并在測試前再進行27 d的養護。
1.2 試驗方法
4根梁均在四點彎曲下進行試驗,純彎曲跨和剪切跨的長度均為1 000 mm,在位移控制速率為1 mm/min的情況下施加垂直荷載,直到梁頂表面出現明顯的混凝土破碎和剝落。在純彎曲跨內安裝3臺線性變差變壓器(LVDT),測量梁跨中及各荷載點的撓度。對于加固梁,在支撐端附加了額外的LVDT,以捕獲SPH-ECC層與RC梁部分之間界面的黏結滑移。各梁的LVDT 布置根據加固方案的配置進行設計[8]。為測量梁的上、下表面的應變情況,需要安裝應變片(如圖2 所示),采用數字圖像(DIC)技術,利用3 臺覆蓋整個梁的高分辨率單反相機捕捉混凝土的損傷和裂紋擴展歷史。

圖2 設置LVDT用于測量界面結合滑移
2 實驗結果
2.1 破壞模式及荷載-跨中變形曲線
圖3 為試驗梁的荷載-跨中撓度曲線,圖4 為試驗梁的破壞模式。從試驗結果和圖3 可以看出,CB、SB-2 和SB-3 的荷載-跨中撓度曲線總體上呈現出3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未開裂階段、開裂階段、最終破壞階段。在未開裂階段,荷載隨跨中撓度線性增大。開裂階段是在微裂縫形成后開始,荷載-跨中撓度曲線斜率略有減小,然后曲線以幾乎恒定的斜率繼續發展,直到縱向鋼筋屈服[9]。在開裂階段結束時,曲線的斜率幾乎減至0,此時開始到達最終破壞階段。在最終破壞階段,跨中撓度逐漸增大,但持續荷載沒有進一步增加,直至CB、SB-2 和SB-3 純彎跨頂面混凝土破碎,導致梁破壞[如圖4(a)、圖3(c)、圖3(d)所示]。對于SB-1,雖然撓度曲線也大致呈現如上3 個不同的階段,但是在開裂階段開始后不久,RC 梁部件與ECC 層之間的界面就發生過早的剝離,導致持續載荷突然下降和撓度曲線斜率降低。對于SB-2,當載荷為110 kN 時,觀察到SPH-ECC 層出現第一條裂紋,但當載荷在55~65 kN 時,RC 梁實際已經形成裂紋,因此會進一步導致載荷-撓度曲線斜率變化,并且當負載達到約55 kN時,SB-2的開裂階段結束。

圖3 試驗梁的荷載-跨中撓度曲線

圖4 試驗梁的破壞模式
2.1.1 SB-1梁
對于SB-1,在開裂階段開始后不久,SPH-ECC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和RC 梁之間的界面脫黏發生在5.26 mm 的跨中撓度處(如圖3 所示)。界面脫黏主要發生在梁的左手側(LHS)剪切跨度,在LHS支撐端觀察到明顯的黏結滑移(如圖5 所示),其中在RC 梁拱腹處應用水泥基復合材料,碳纖維增強聚合物的嵌入條作為增強層。當測試的RC 梁通過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以類似于SB-1 的配置進行加固,但沒有任何嵌入鋼筋時,沒有出現脫黏現象。此外,SB-1在脫黏前的剛度(15.22×103kN/m)遠高于CB(8.88×103N/m)[10]。因此,可以得出結論,SB-1 中的界面脫黏的原因可能是因嵌入鋼筋引起的SPH-ECC 層剛度增加,以及可用于抵抗產生的界面應力的相對較小的接觸面積。脫黏后,混凝土剛度降至9.89×103kN/m,僅略高于CB,這是因為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是獨立彎曲的。脫黏后,在SB-1 的RC 梁底部立即觀察到拉伸裂紋。試驗結束時,發現RC 梁部件的破壞模式與CB 的破壞模式非常相似,并且在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中觀察到的損傷很小,最大載荷為213.4 kN,僅比CB的載荷高26.6%。

圖5 滑移梁失效
2.1.2 SB-2梁
對于SB-2,當載荷達到約55 kN 時,未開裂階段結束,在此之后,裂紋階段開始,在純彎曲跨度內的SPH-ECC 層中出現多個微裂紋。當施加的荷載達到270 kN 時,這些裂紋在接近開裂階段結束時變寬且越來越明顯。當施加的荷載達到270 ~310 kN 時,SPH-ECC 中的鋼筋屈服導致剛度逐漸降低,最終加速了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的拉伸應變軟化現象,導致裂縫局部化。當跨中撓度從17.5 mm 增加到22.4 mm 時,梁的承載力基本保持不變。此后,跨中頂面混凝土壓應變達到混凝土破碎應變的0.33%(如圖6所示),進一步導致混凝土負載能力的逐漸下降,峰值負荷為310 kN,為CB荷載的184%。

圖6 SB-2和SB-3梁壓縮應變
對于SB-3,其在RC 梁周圍形成“U”形包層,其顯示出354 kN 的峰值載荷,為CB 荷載的210%,是所有加固梁中最高的。當載荷約為75 kN 時,SB-3 的未開裂階段結束,而開裂階段持續到約320 kN 的載荷。然后在純彎曲跨度中,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底層內出現多個可觀察到的裂紋,當跨中撓度約20 mm時,達到峰值荷載,荷載幾乎保持不變,出現裂紋局部化,直到梁在跨中撓度為46 mm 時失效。當失效發生時,跨中頂面的應變達到0.33%的混凝土壓碎極限(如圖6 所示)。與SB-1 和SB-2 不同,SB-3 即使在混凝土發生壓碎后,也沒有觀察到明顯的界面脫黏。
2.2 界面黏結行為
加固層與RC 梁構件之間的界面黏結是影響加固體系性能的關鍵因素之一。當界面結合強度不足時,可能因脫黏而發生過早破壞。因此,對于加固梁,在試驗期間連續監測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與RC 梁構件之間的界面黏結滑移。使用LVDT 記錄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相對于RC 梁部分的位移。在加固梁的2 個支撐端記錄的界面黏結滑移值,然后與跨中撓度及荷載-跨中撓度曲線繪制在圖7中。對于SB-1 及SB-2,從圖7 中可以看出,當外加荷載約119 kN 時,LHS剪切跨界面黏結滑移從幾乎為0跳變至0.9 mm,同時外加荷載突然下降。之后,LHS黏結滑移逐漸增大,直至被破壞,而右側(RHS)黏結滑移基本為0。

圖7 界面黏結滑移
2.3 應變分布
使用DIC 和應變片獲得的最佳擬合數據繪制了不同加載水平下測試梁的應變分布沿梁深的發展情況(如圖8 所示),未繪制SB-1 的應變分布,是因為SPH-ECC層的底表面過早脫黏而出現拉伸應變的進一步增大。鋼筋屈服應變(0.31%)和混凝土峰值壓應變(0.33%)也分別用實線和虛線表示。圖8 中的破壞荷載為混凝土發生破碎時的荷載水平。總體而言,從SB-2 和SB-3 獲得的DIC 和應變片數據來看,應變沿截面深度呈線性分布。圖8(a)顯示,CB 為未加固鋼筋,在荷載達到130 kN(峰值荷載168.5 kN 的77%)之前屈服。對于SB-2[如圖8(b)所示],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內嵌鋼筋在峰值荷載(310 kN)之前屈服,而RC 梁部分嵌鋼筋在峰值荷載之后屈服。從圖8(b)可以看出,SPH-ECC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和RC梁部件鋼筋屈服后不久,混凝土在頂面發生了壓碎。這種破壞非常接近試驗預期的平衡破壞,主要是在梁上添加了2根額外的鋼筋,而沒有增加梁的整體剛度。對于SB-3,如圖8(c)所示,SPH-ECC 層鋼筋屈服于320 kN 左右(峰值荷載354 kN 的90%)。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即使在達到峰值荷載之后,也直到實現了更大的撓度才會發生混凝土破碎,表明梁的加固仍然不足,這主要是由于使用了“U”形外殼和底部SPH-ECC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內的鋼筋位置較低導致的,從而增加了梁截面中性軸的深度。
3 結論
本文為進一步提高混凝土梁修復加固效果,提出使用鋼筋和聚乙烯醇混合纖維增強水泥基復合材料(SPH-ECC)和嵌入式鋼筋對鋼筋混凝土(RC)梁的彎曲加固效果,研究結論如下:①SB-1由于具有明顯的界面脫黏而導致過早失效。對于SB-2 和SB-3,其最終的抗彎破壞是由純彎曲跨度內的頂面混凝土破碎引起的。對于SB-2,在混凝土破碎后不久,出現了少量的界面黏結滑移。對于SB-3,即使發生混凝土破碎,也幾乎沒有觀察到界面黏結滑移。②SB-2 和SB-3 的應變沿截面深度呈線性分布,并且SPH-ECC水泥基復合材料層內嵌鋼筋在峰值荷載(310 kN)之前屈服,而RC 梁部分嵌鋼筋在峰值荷載之后屈服。結果表明,SPH-ECC 水泥基復合材料具有良好的裂縫寬度控制能力,其對RC 梁部分的裂縫具有有效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