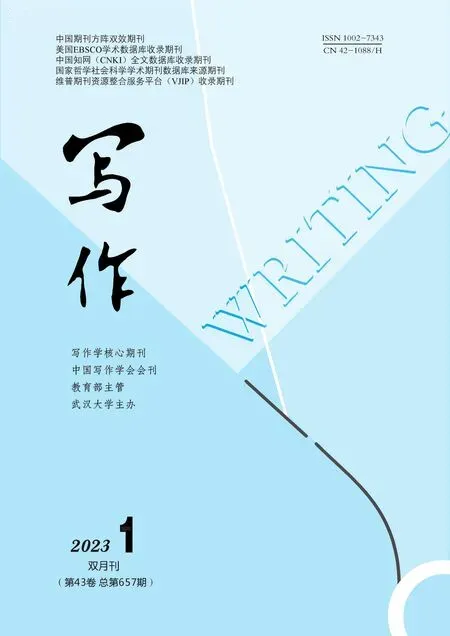王兆勝“寫作”的特征與貢獻
李沛霖
王兆勝既是一位散文作家,也是一位學術研究者。迄今為止,已出版散文集《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年版)、《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情之一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散文理論著作《真誠與自由——20世紀中國散文精神》(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等,以及批評著作《林語堂的文化情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閑話林語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年版)等;發表學術論文三百余篇①該數據參考王兆勝《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封面內頁“作者簡介”。。從“寫作”②“寫作”泛指“寫文章”,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16 年版,第1450-1451頁。的廣義看,它們都屬于“寫作”范疇,構成王兆勝獨特的寫作譜系。
目前,學界有關王兆勝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關注王兆勝的散文創作情況。如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解讀王兆勝散文創作中的真實性與時代感特征③張偉:《真實性與時代感——王兆勝散文的魅力及其啟示》,《文藝爭鳴》2021年第3期。;從美學角度論其“和諧澄明”的創作特征④陳劍暉:《喧囂世界中的和諧澄明——談王兆勝的散文隨筆》,《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4期。;圍繞“和諧之美”“赤子之心”等關鍵詞,對王兆勝的散文作品思想主題進行解讀⑤羅振亞、劉波:《以人心豐富世界——王兆勝散文集〈天地人心〉》,《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等等。二是關注王兆勝的散文研究情況。如從研究內容切入,考察王兆勝散文研究的尺度與風度⑥陳劍暉:《風度與尺度——論王兆勝的散文研究》,《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又或是揭示王兆勝散文研究的辯證思維①趙佃強:《王兆勝散文研究的“辯證法”》,《東吳學術》2020年第1期。,等等。以上研究分別著眼于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兩大視角,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兆勝作為一位集創作、研究、編輯于一體的當代學者,其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一直處于相互影響的疊加態,僅從單一維度進行分割研究,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試圖將王兆勝的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統攝于“大寫作”②方長安:《中國寫作學優秀論文選(1980—2020)·序》,《寫作》2022年第5期。視野進行考察,揭示其創作與研究相互對話、滲透與啟發的內在圖景,在雙重維度的聚合中透視、把握王兆勝的“寫作”特征與貢獻。
一、融通散文觀念的散文創作
王兆勝開展散文創作的最初契機,是想“以散文隨筆的形式對文化和人生發言”③王兆勝:《后記》,《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頁。。可見,散文創作在其心中,是承載作者思想與情感的一種“寫作”。而支撐王兆勝持續開展散文創作的源動力在于:學術研究與創作實踐可以融通互補、相得益彰。王兆勝曾在第一部散文集《天地人心》中談道,“從事學術研究之余多寫散文”,一是為了感受“散文寫作之甘苦”,二是“補充學術研究之枯燥干澀”,三是希望增強散文創作的思想含量。由此,學術研究是考察王兆勝散文創作特征時不容小覷的重要因素。王兆勝曾明確指出,散文創作想要“更全面、健康和持久的發展”,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借鑒④王兆勝:《后記》,《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頁。。當代作家在從事散文創作時,對于散文之“散”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觀念誤區與理論障礙,致使散文作品存在“無度與失衡”“‘神’散或無神”和“缺乏心靈與人生智慧”⑤王兆勝:《“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的病癥。面對這一困境,王兆勝試圖突破“散文形散、神不散”⑥20世紀60年代,肖云儒提出的“散文形散、神不散”的散文觀,見肖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報》1961年5月12日第8版。和“形散神也飄忽無蹤”⑦20 世紀90 年代,以劉燁園為代表的“形散神也飄忽無蹤”的散文觀,見劉燁園:《新藝術散文札記》,《領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頁。的理論局囿,將散文之“散”的重心由“形”“體”轉移到“心”,于2006年提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觀。而這一散文觀念正是多年來指導與貫穿王兆勝的創作實踐的核心理論,更是讓其散文呈現出“形神合一、心靈散淡”的創作特質。
散文的“形”即“形體”,指結構布局、用詞遣句;散文的“神”,指“精神”“神采”“神氣”或“神韻”⑧王兆勝:《“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王兆勝將散文的“形”和“神”放置于藝術形式層面進行理解,提倡“形聚神凝”。值得注意的是,“形不散”和“神不散”,不僅僅是“不散”這么簡單,更重要的是,這兩者需要同步規范,缺一不可。王兆勝曾將“形”比作“蠟燭”,“神”比作“燭光”,指出若有其中一者“散”,則易跳躍、昏暗以至于熄滅。考察王兆勝的散文作品,可以發現,其散文的結構布局、用詞遣句與散文的行文思路高度統一,具有“中心明確、緊湊集中,字字珠璣、環扣主題”的特征,可謂“形神合一”。以《柔韌之道》為例,該文以“柔韌”為觀察點與敘事核心,開篇指出“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者則是那些柔韌的事物”,進而溯源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柔韌之道”,后論述“柔韌”的價值與意義,最后升華至“柔韌文化”。通篇圍繞“柔韌”這一關鍵詞,聯系古今中外的種種現象,在邏輯的層層推理下,詮釋柔韌之道于現代文明的重要性。此外,王兆勝的作品《赤子之心》《夢想之樂》《愛之普照》等均具有“開篇點題”“一條線索貫穿全文”“首尾呼應”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正文部分,散文標題的創作也獨具匠心①王兆勝曾表明:“我一向不喜歡花里胡哨和低級趣味的書名,而偏愛優雅閑逸、靈氣充沛和有文化感的書名。”王兆勝:《自序》,《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呼應主題。以《雙峰飛渡有鴻聲》為例,一方面,散文標題取自正文內容中有關丁曉原學術成果的評價語,“這是飛渡‘晚清’與‘五四’這兩座高峰的現代性關節點”;另一方面,散文標題巧妙地與丁曉原的姓氏相聯系,“在丁曉原的名字里,‘丁’字像拐杖,又是倒過來的問號,這是不是他‘飛渡’雙峰的一個憑借?”②王兆勝:《雙峰飛渡有鴻聲》,《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180頁。如此對于散文標題的思量,進一步深化了王兆勝散文“形神合一”的藝術特質。
與散文的“形”“神”不同,王兆勝將散文的“心”理解為“情調”“情緒”“筆調”“步調”“品格”“格調”等。在散文寫作中強調“心散”,即用“一顆寧靜、平淡、從容、溫潤和光明的心靈”進行書寫③王兆勝:《“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這個闡釋,主要涉及創作視野、情調與心境。由此,“心散”的散文觀念,影響著作者的意象捕捉力與觀察敏銳度,同時煉化著創作情調與心境。散文意象的選擇是“心靈”的直接反映,“意象是經作者的心理、情感和意識多重綜合而構成的一個或多個詞象組合,是心和概念表象與現實意蘊的統一”④陳劍暉:《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頁。。當王兆勝用一顆“溫潤、自由、散淡的心”去觀察世間萬物時,那些能夠走進其創作視野的意象,多具有輕靈、澄凈、寧靜與原生態的特征,如水、雪、花絮、肥皂、陽光、魚、泥土、地心泉、寸石、草莓、龜等。在書寫過程中,王兆勝會用一顆“散淡、寧靜、從容的心”去敏銳地觀察與捕捉意象所具有的聲音、色彩、形體等特征,以此抒發童真、質樸、純美、自由的心靈情調。以《楊柳花絮輕似雪》為例,作者所選取的意象為“樹絨花”,其花絮在都市中十分不受市民歡迎,但在王兆勝心中,“樹絨花”卻是“悠閑、寧靜、自得、愜意”之物。作者將樹絨花的花絮“在空中敏感地隨風飄舞”視作“機警動物耳毛一樣的靈性”,并認為花絮是“心靈剔透的”,具有一顆“靈性之心”。他將“樹絨花”花絮那似雪非雪的靈動感,“那種有心而又似乎無心的飄浮感,那種不為萬物負累身心輕松快樂的逍遙境界”⑤王兆勝:《楊柳花絮輕似雪》,《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上升為一種真正的大自由。可以說,這是一篇典型的“以散淡的心靈體驗物性之美”的佳作。顯而易見,不同于“緊張、焦躁、世俗之心”的“心靈散淡”⑥王兆勝曾談道:“散文是最重心靈散淡自由的一種文體”;此外,王兆勝認為古今中外的散文經典都具有“結構嚴緊、精神飽滿、心靈散淡”的特點,而這些散文經典正是其散文觀的立論基礎。王兆勝:《“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是王兆勝散文創作的重要特質。
如果說“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觀是王兆勝核心理論的第一層次,那么“天地之道”可視為其理論思考的第二層次,即在“靜心”創作的過程中觀察“物性”。在此基礎上,“人之道”與“天地之道”的辯證統一則是理想級別的第三層次,“理想的散文理論應將中國古代‘物的文學’與中國現代‘人的文學’辯證地統合起來”⑦王兆勝:《中國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問題》,《天道與人道:中國新文學創作與研究反思》,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頁。。與散文理論同步發展的散文創作也逐漸達至“人文關懷”與“天地情懷”相交融的創作境界。
的確,學者出身的王兆勝,十分關注文化與人類命運的發展,書寫了較多與人緊密相關的時代論題與社會問題。如《都市燈光》《和諧之美》《敬畏之心》《給予之福》等,其中涉及生存問題、環保問題、道德問題、人性問題、城鄉關系問題等。與此同時,王兆勝注重“心靈對于天地宇宙情懷的觀照”①王兆勝:《中國當代散文研究觀念的調整與創新》,《文化自信與文學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2 年版,第107頁。。王兆勝認為,在中國新文學“人的文學”觀念底下,“物”不被重視,這是一種認知誤區②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為打破這種不平衡,王兆勝在創作中將“物”與“人”等量齊觀,注重“物性”描寫。首先是在作品數量上,帶著對于宇宙、自然的敬畏與仁慈,在日常創作中關注天地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創作了大量以“物”為主體的散文作品,如《水的感悟》《高山積雪》《陽光》等。其次是在書寫方式上,通過“以物為師”的方式,建立“人”與“物”的聯系。在自然萬物的身上尋求人生智慧、精神氣質、審美情趣,啟示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理想、生活方式,如《向“物”學習》《樹木的德性》《親近泥土》《木龜》等。總的來說,王兆勝的散文創作,既關注人性,又體味物性。在“人”與“物”的互文中,物性被人的現代性照亮,現代性被物性提升,逐漸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王兆勝的散文創作既得益于理論的規約,在文體層面有規整的形制,又融通理論的精髓,從心靈維度獲得無垠的空間,在“自由”與“限制”中獲得發展的潛力與張力。
二、吸納散文創作經驗的散文研究
在王兆勝眼中,散文研究不僅僅是散文觀念、散文理論的建構,同時是一種“創造性寫作”。想要其富有生命力,就不能過于固定化與程序化,要既有理性與邏輯,也有情感、想象與審美。而這樣具有透視力的研究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兆勝的散文創作經驗。自從事林語堂散文研究開始,王兆勝便在導師的建議下同步開展散文創作,以求開拓研究視域,在實踐中有所體悟③王兆勝曾回憶從事散文創作的機緣:“在研究林語堂之時,林非先生還希望我多研究散文,有時也動筆寫寫散文,這樣才能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視域,并有所實踐和體悟。”王兆勝:《代前言》,《文化自信與文學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0頁。。由此,創作實踐作為王兆勝學術道路上的一條支流,為其散文研究注入了感性的成分,使之充滿性靈的豐沛與心靈的力量,探索出富有主體性與創造性的研究方法、路徑與寫作方式。
其一,“心靈對語式”研究。王兆勝曾在《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一文中談道:“用‘心靈’之光燭照文學,就是要求研究者突破理性邏輯的限制,有情、有韻、有味、有感、有覺、有悟、有慧地同作品對話,以獲得獨特的個人性理解及其創造。”④王兆勝:《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東方論壇》2019年第5期。這種研究強調的是跳出邏輯思維,獲得“心靈”對話與“心靈”感悟的能力。對王兆勝而言,這個“心”主要聯系著情感、悟性、人生和生命。面對研究對象,王兆勝并非單一地采用學理、邏輯和概念去解讀⑤王兆勝曾提及:“我研究林語堂很少用概念和理論去套,那是形式主義研究,我稱為廣場太極拳,是一種沒有生命參與的僵化研究。”王兆勝:《代前言》,《文化自信與文學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2頁。,而是結合人生經歷之起伏、創作實踐之甘苦,以情感為紐帶,走進作者的心靈世界。以林語堂“生命悲劇意識”的研究為例,這是王兆勝所揭示出的未被文學史發現的林語堂的另一面。王兆勝曾自述人生情感經歷,“我出身農村,童年飽受生活磨礪,少年喪母為我的人生蒙上了陰沉的暗影……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相繼去世……隨后,家父亦與世長辭”⑥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所有這些長期以來都成為其“悲觀”的依據。面對林語堂的作品,具有“悲觀”意識的王兆勝敏銳地關注到林語堂所歷經的“悲情”人生,如林語堂從小生活在農村的大山深處,深感“山之高大,人之渺小”;又如林語堂的二姐早逝,令其悲痛。這些相似的成長經歷所帶來的情感體驗,為王兆勝讀懂林語堂文本中的“生命悲劇意識”提供了通道。在此基礎上,王兆勝體悟出了林語堂所說的“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樂,這樣才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覺,有醒覺而后有哲學的歡笑,另外再加上和善與寬容”①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頁。這樣一段核心語句背后的深意。此外,除了走進林語堂的世界,王兆勝還試圖讓林語堂的思想照亮自己的世界。如從林語堂的作品中獲取“如沐春風、其樂融融,有一種被溫暖撫摸和陽光照亮的感覺”,學習林語堂“超越悲劇的努力與創造”等等,由此實現與研究對象“靈魂感應地進行著雙向交流”。概言之,在“心靈對語式”觀念影響下,王兆勝創新性地解讀出林語堂散文抒情中的復調性,即“歡笑底下的‘悲情’,也知道了‘悲劇’中的喜劇意味,那是林語堂用歡快、幽默消解‘悲劇’的努力與智慧”②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這些使得王兆勝的林語堂研究獲得了“這或許標志著林語堂研究一個新階段的到來”③王兆勝回憶,其博士論文答辯主席、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給他的評語是:“這或許標志著林語堂研究一個新階段的到來。”王兆勝:《代前言》,《文化自信與文化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9頁。的高度評價。
其二,“心、腦并重”的創造性寫作方式。其中,“心”指心靈、精神;“腦”主要包含理論、邏輯、概念等。之所以采用這樣的論文寫作方式,是因為王兆勝認為當下文學研究多采用“填充式寫法”④王兆勝認為“填充式寫法”是指“確定好論文框架,將準備的資料和理論術語填加進去,于是論文成為一種簡單的操練行為”。王兆勝:《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東方論壇》2019年第5期。,存在“腦大于心”的病癥。由此,在撰寫研究論文時,王兆勝反對概念的堆砌與理論的套用,尤為注重“心靈的參與”,將其視為一種心靈、精神與理論、邏輯并重的“創造性寫作”⑤王兆勝:《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東方論壇》2019年第5期。。
一方面,“用化解和富有智慧的理論話語進行研討”⑥王兆勝:《中國當代散文研究觀念的調整與創新》,《文化自信與文學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05頁。。在王兆勝的散文研究文論中,幾乎看不到散文理論、概念與研究對象相糾纏的痕跡。吸納了散文創作經驗的王兆勝,在行文時,能跳出理論、概念、邏輯的纏繞,注重為文的通徹、明暢、生動、情懷。以《雙峰飛渡有鴻聲——評丁曉原〈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為例,王兆勝在評論丁曉原的著作時,說道:“本書緊緊抓住‘現代性’這一維度,從而在‘晚清’與‘五四’之斷崖間拴上了一條索鏈,從中可見傳統散文向現代散文過渡的刀光劍影,以及觀念、文體之變。”⑦王兆勝:《雙峰飛渡有鴻聲——評丁曉原〈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文匯讀書周報》2016 年6 月27日第5版。這樣一種由“心靈”生發文本的寫作,擺脫了學理性論文的窠臼,生動形象地傳達了作者的核心觀點。化解理論,用文化思想、智慧與“心靈的表達”⑧王兆勝曾評價散文創作,“散文創作最益于養‘心’,最益于心靈的表達。”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發聲,正是王兆勝所期待的“真正好的文學研究方法”⑨王兆勝指出:“真正好的文學研究方法是消化理論后的無理論,是穿越知識、文化、思想、理論后的智慧生成。”王兆勝:《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東方論壇》2019年第5期。。
另一方面,“重視寫作過程中的創造性發揮”。王兆勝曾這樣理解散文研究的寫作:“這頗似文學創作,作家如按原設得以順利進行,但無靈感產生,也不會是佳作。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不重視寫作過程尤其是其間的創造性發揮,而以填充方式進行,哪怕再好地完成原來構思,也不會有創新性論文生成。”⑩王兆勝:《關于文學研究的創新性問題》,《東方論壇》2019年第5期。基于散文創作的經驗,王兆勝期待散文研究的寫作,既能基本符合前期材料與理論的預設,又能超越預設束縛,又或者“修正原來的預想”;在全身心投入的寫作過程中,能夠發揮想象力、迸發靈感,從而使研究論文具有創新性。
考察王兆勝的散文批評思路,可以發現,其在沉浸式的寫作過程中,善于發揮想象力,讓不同時空的散文作品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從而挖掘出有價值的研究視角。如面對郁達夫《故都的秋》時,王兆勝將作品與歐陽修的《秋聲賦》相聯系,從“物性”的角度對《故都的秋》進行解讀,得出新的結論①王兆勝認為《故都的秋》“主要不是寫人,更不是闡釋現代性,而是通過‘物’之變幻來感悟生命之易逝的”。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又如,王兆勝將劉燁園的《自己的夜晚》與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相聯系,想象那種通達與豁然,參悟作者的“情緒、意象、氣息、生命的流動與升騰”②王兆勝:《中國當代散文研究觀念的調整與創新》,《文化自信與文學發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08頁。。具體到王兆勝的批評文字,除了文章標題與預設性結構,在每段的細節論述之中,也充滿了想象力與靈感。以《詩化人生》為例,該文主要討論“詩心”對于人的影響③王兆勝:《詩化人生》,《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4頁。。在論及“詩心可以讓人體悟大自然的規律與心情”這個分論點時,王兆勝在論段中展開了極富想象力的論述:這種季節的更迭與人生的春夏秋冬何異?生命在自然和人生這一點具有一樣的節奏;由此,體悟出人到晚年應遵循冬季的規律與特征,“以寧靜的智慧和從容的風度安享時光與歲月”的真諦。王兆勝的散文研究在吸納散文創作經驗的基礎上,融入“生命、感覺、智慧與審美”,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理論與方法,構成其散文“寫作”的重要部分。
三、散文“寫作”的貢獻
一直以來,王兆勝的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不斷對話、滲透與啟發,既具有獨特性又具有互文性,對于中國當代散文的發展與建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其一,探索出一條散文理論、創作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寫作”道路。20世紀90年代,學界盛行“作家學者化”和“學者作家化”的口號,學者與作家兩者之間的融合成為文學發展的一個方向。王兆勝作為新一代的“學者散文家”④王兆勝:《新世紀二十年中國散文創作走向》,《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身體力行地實踐與深化著這條道路,并獲得了一個散文研究者“相對完整的生命形式”。
一方面,理論指導創作,創作糾偏理論。王兆勝的散文創作一直以其散文理論為指導,融通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觀、“人之道”與“天地之道”辯證統一的境界,生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提升了創作格局。除了每篇散文作品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含量外,還涌現了大量哲思類散文文本,如“物性散文”《向“物”學習》《物的解放》等。還值得一提的是,王兆勝在散文創作中對于意象特征的敏銳性捕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散文研究中習得的形象思維與直覺能力。反觀之,在創作中踐行散文觀念,有利于檢驗理論的科學性,并對其進行糾偏。如王兆勝回憶自己在創作一篇題為《豬友》的散文時,想到人對待豬的殘忍,以及牛、騾子等動物的可憐。他聯系當代散文作品,發現較少有作家從仁慈、關懷的角度去寫這些動物,由此反思在“以人為主題”的散文理念下,散文創作道路的偏向,進而得出“人之道”與“天地之道”應辯證統一的理論觀點。
另一方面,創作啟發研究,研究中有創作。在散文創作過程中迸發的靈感,同時會啟發王兆勝在文學研究中獲得一個新的“支點”。以《朱馬拜小說的“知”與“不知”》為例,該文所選取的研究切入點“知”與“不知”正是王兆勝的一篇散文作品所關注的主題——“不知”之益①王兆勝曾回憶到,《說“不知”之益》這篇散文激發了他在研究時行文運思的靈感,找到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即“不只是看作家作品對于‘知’的部分,還要注意其‘不知’之處”。王兆勝:《“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而當散文研究被正兒八經視為一種“寫作”,散文創作中所帶有的文學性、藝術性的表達方式便會過渡到散文研究之中,成為散文研究的一種新突破。如其《閑話林語堂》,相較于之前的著作《林語堂的文化情懷》,其文學性與審美性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此外,王兆勝的系列評論性文章《心弦上彈出的雙美——林非散文的價值和魅力》②該文發表于《寫作》2002 年第1 期,被收錄進散文集《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年版)第5 輯“書中日月”;還被收錄進散文集《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輯,改名為《心弦上彈出的雙美》。《天唱的絕響》③該文被收錄進馬一夫等主編的《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散文集《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輯。《用心弦彈出的生命樂章——讀賽飛的海島散文》④該文發表于《當代文壇》2014年3期,被收錄進散文集《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輯,改名為《賽飛的海島散文》,原文略有改動。《肖鳳:超越苦難與體味美麗》⑤該文被收錄進《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四章第七節,被收錄進散文集《天地人心》(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5輯“書中日月”,改名為《超越苦難與體味美麗》,原文略有改動。《雙峰飛渡有鴻聲——評丁曉原〈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⑥該文發表于《文匯讀書周報》2016年6月27日第5版,被收錄進散文集《負道抱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輯,改名為《雙峰飛渡有鴻聲》,原文略有改動。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文論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在發表后大都被收錄進散文創作集中。可見,這些批評文論既具有學理性,又具有文學創作的審美性與觀賞性,是批評、研究與創作相統一的典型案例。
其二,以“心靈”為基點統攝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為當代散文立“心”。王兆勝認為當代散文存在的“創作無序”“批評僵化”等問題,其根源在于“心靈缺位”。由此,“心靈”作為一個基本透視點,始終貫穿于王兆勝的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之中。目前,已有一些學者以“心靈”為關鍵詞評價王兆勝的研究特征與貢獻。如朱壽桐認為王兆勝是“在心靈場域建構學術矩陣”⑦朱壽桐:《在心靈場域建構學術矩陣——論王兆勝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白浩認為王兆勝在進行“心學”的建構⑧白浩:《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論王兆勝的“心學”建構》,《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的確,王兆勝對于“心靈”的提倡從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在繼承中國古代、現代的相關理論思想的基礎上,使其適合當代散文的發展,讓當代散文回歸散文的本性,在時間與空間維度建立起一顆具有深度與溫度的“散文的心”。
王兆勝認為中國人自古注重“心”的力量,如老莊所重視的“天地之心”、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心”,都極富心性。單就散文而言,20 世紀30 年代,郁達夫更是明確提出“散文的心”這一概念,并將其視為現代散文最重要的部分。在郁達夫的理論中,“散文的心”接近于中國舊式說法的“作意”,外國修辭學里的“主題”或“要旨”⑨郁達夫:《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5-9頁。。雖然,郁達夫從散文的結構論出發,將散文的“心”與“體”對立,“心”被界定為散文的思想要素。但“散文的心”的內涵遠不止于此,還應當看到,在其統攝下現代散文所具有的特征:一是散文富有個性;二是散文內容范圍擴大,大至宇宙,小至蒼蠅;三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⑩郁達夫:《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5-9頁。。在王兆勝的散文觀中,其關注宇宙萬物的“天地之心”“人與自然的融合”等觀念與郁達夫“散文的心”都是互通的?王兆勝在《“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中,直言郁達夫的“散文的心”是其引入“心散”觀念的理論依據之一。。
在傳承古代、現代的“散文的心”思想基礎上,王兆勝試圖創制出適應時代的“散文的心”,使當代散文擁有“天地情懷、中國智慧、世界眼光”。在時間的維度上,讓當代散文的“心”面向中國散文文化①陳劍暉:《散文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中的求“道”傳統與抒情傳統,反撥“新散文”與“大歷史文化散文”對于傳統散文的擠壓與誤讀,引導實用性散文與抒情性散文等傳統散文在當代回春,讓當代散文富含文學性、思想性與審美意趣。在空間的維度上,讓當代散文的“心”面向鄉村與城市,面向中西文化,更面向天地宇宙,打破城鄉“二元對立論”、中西文化“一元論”,克服人本主義局限。王兆勝用其散文創作與散文研究的“寫作”實踐,生動地詮釋了其“寫作一面是一種社會責任承擔,另一面是心靈和精神的需要”②王兆勝:《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頁。的散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