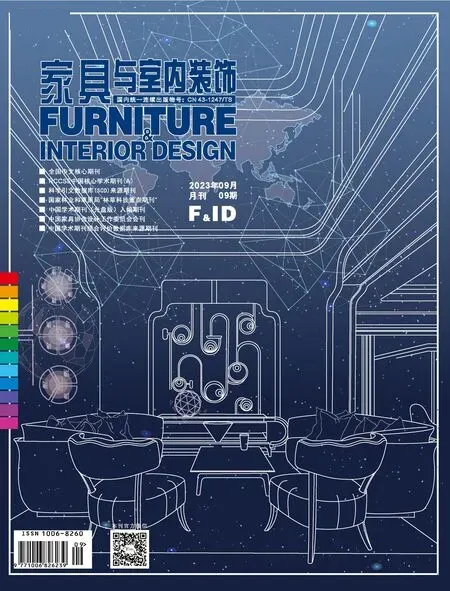基于數量化理論的蒙古族唐卡感性意向研究
■宋海軍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陰山戈壁、大漠南北的廣袤草原,自古便是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唐卡也逐步被草原人民所熟知,經由元、明、清三代藝人的不斷積累,逐漸形成頗具特色的北方游牧民族繪畫藝術。時至今日,蒙古族唐卡已逐漸成為草原游牧文明藝術成就的重要體現,是一種展現宗教信仰、地域文化、民族審美的獨特藝術載體[1]。如何在民族文化內核繼承性的基礎上融入符合時代語境的審美需求,形成科學的、客觀的、規范性的文化可持續創作,日益成為值得深入討論與研究的話題。
1 蒙古族唐卡概述
“唐卡”,蒙古語譯為“布斯吉如格”,原字面意思為“一種可鋪開收卷的物品”[2],是用彩緞裝裱的卷軸畫,通常被供奉于寺廟等場所,原是藏傳佛教中一種獨特的繪畫藝術。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建立后,推行將占領地的工匠作為戰利品貢獻給可汗或賞賜予功臣的政策[3],此舉措使得蒙古族對其他民族的文化、藝術、宗教等方面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為藏地唐卡的傳入奠定了基礎。
蒙古族唐卡,也稱蒙地唐卡、蒙古式唐卡,是百余年間蒙藏兩地文化交融下的產物,在表現手法方面沿襲了藏式畫派的藝術風格,同時也融入了中國傳統美術、清朝宮廷畫、印度及尼泊爾佛教畫派的藝術特色,其最大的特點在于融入了蒙古族地區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歷史、民族信仰等元素,無論是莊嚴寶相的宗教類還是精致嚴謹的記事類,蒙地唐卡在人物刻畫、服飾、思想觀念及設色等方面均表現出其獨有的藝術魅力與藝術價值。
2 研究方法與理論基礎
2.1 數量化理論
數量化理論是由日本林知己夫教授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一種研究多個變量間關系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4],依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該理論可分為Ⅰ、Ⅱ、Ⅲ、Ⅳ四種,其中數量化理論Ⅰ主要用來研究一組定性數據與定量數據間的對應關系[5],將難以定量化的問題進行賦值轉換,使其變得可進行定量檢測,從而實現對因變量的預測。在設計學中可運用該理論來研究公眾的感性需求與設計要素間的映射關系[6]。宋瑩[7]等人在歸納出男士襯衫主要設計要素的基礎上,配合數量化理論模型,進一步證實了公眾感性需求與男士襯衫設計要素間的轉換,陳金亮[8]等人通過數量化理論建立了SUV前臉造型設計要素與公眾感性意向間的映射關系,提高了公眾的認同感,在方案轉換中使得設計更具人性化。許小俠[9]等人通過建立數量化模型,多種控面板的感性意向進行了精準預測,從而為設計方案提供了客觀依據。在蒙地唐卡意向再設計中,公眾的感知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公眾的審美傾向及偏愛的藝術特點,以此方法為基礎可以揭示蒙地唐卡中各類設計要素及其類目與公眾感性意向間的規律,最終使得藝術設計作品可快速匹配不同需求與場景。
2.2 語義差異法
語義差異法是由美國心理學家Charles E.Osgood及其同事共同創立,該方法以感性意向為基石[10],是一種結合人的聯想,再運用語義區分量表來對研究對象的意義或概念進行判定的研究方法。李倩文[11]通過語義差異法建立了男西裝感性意象二維空間,并提取了感性意向有關的設計要素。劉靜怡[12]通過語義差異法為萱草紋樣再設計提供可靠依據,胡佳馨[13]基于感性意向理論,利用語義差異法制作評價問卷,總結感性詞匯,最終得出公共家具的設計要素,為此后的設計實踐提供了參考與新路徑。本次研究可通過語義差異法來獲取公眾對于蒙地唐卡的感性評價,將公眾的感性認知與數量化理論I中構建起的蒙地唐卡形象模型相結合,使得一些較為主觀且不便描述的特征通過量化的方式較為清晰地展現出來,進而探尋感性評價與設計要素間的關聯。
3 蒙地唐卡感性意向模型構建
3.1 樣本選取
感性意向的研究多以感性工學為基礎,通過實驗分析公眾對某類事物的感性認知,并將其感性需求與設計目標形成映射關系[14]。本次研究對蒙地唐卡相關文獻、書籍加以研讀,并對相關博物館蒙地唐卡藏品進行考證與拍攝,共收集34幅不同特征的唐卡圖像,再由具有設計或藝術背景的成員組成專家小組進行聚類分析,最終篩選出14幅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作為本次的研究對象,如表1所示。

表1 蒙地唐卡樣本
3.2 作品構成要素提取
蒙地唐卡圖式中包含諸多要素,不同要素間的組合可建構出不同的意蘊及意境,作為一種藏地傳入的繪畫藝術[15],蒙地唐卡在繪制方面同樣恪守了藏式唐卡的繪畫原則,但在個體形象、題材、設色、三個方面仍能窺探出蒙古族對唐卡藝術的意會與解讀。
個體形象方面,蒙古族特有的人物形象是構成蒙地唐卡地域特征的要素之一,依據薩班的佛像度量經典,可以較為清晰地觀察到蒙古族人物的具體特征,例如人物頭部偏大、脖子部分較短、整體身材比例較為豐腴[16],此外,蒙古族歷來尊崇“長生天”,將蒼天視為永世的最高神靈,(蒙古語中將其稱為“孟克騰格里”意思為不朽的蒼天)因此可以看到在一些唐卡中,在形象方面除佛教體裁的本尊以外,四周還會站立著一些沒有真身的空盔甲或空服飾,這種表現手法正是薩滿教中“空靈”的觀念與佛教結合的產物[17]。
題材方面,除傳統的佛教體裁之外,蒙古族唐卡的歷代傳承人在結合了本民族的文化內涵、地域特色、宗教信仰等因素后,在原有的基礎上衍生出了重大事件、歷代可汗、民俗生活、戰神等多種類型的主題。在設色方面,據《蒙古風俗鑒》第三卷記載,甲乙(青色)為興旺、戊己(黃色)為衰、庚辛(白色)為始、壬葵(黑色)為終[18],由此可見蒙古族對顏色的使用也存在其特殊含義,例如敬獻哈達時多為青白兩色,在人名或地名時也常將“呼和”(青色)作為選擇,呼和浩特(蒙古語為青色的城),在唐卡繪制中,常用群青色來描繪背景或天空,這種顏色醒目但不刺眼,使得整體畫面莊重典雅。結合綜上所述,歸納出三種主類型象因子后,針對每種因子的具象呈現特征,又細分為15項類目(因子水平),依次為:“個體形象”因子,包括頂盔摜甲、民俗服飾、蓮花座、神獸、白馬;“設色”因子包括對比強烈、和諧統一、簡練、沉穩端莊、節奏活躍;“題材”因子包括歷代可汗、英雄人物、重大事件、宗教遺風、戰神。對三種主體形象因子由A1-A3進行編碼,對其細分類目由C11-C35進行編碼,如表2所示。

表2 設計要素分類
3.3 感性意向評價提取
本次研究從各類相關文獻、報刊以及各網站中的唐卡評論等多種途徑,共收集語義詞匯3252字,其次利用詞頻分析程序將收集到的句子、短語、語段等拆解成獨立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再次邀請具有美術及設計研究背景的教師組成專家小組,對拆解后的詞匯進行梳理,去除語義不明及相關性較低的字詞,最終得到五組形容詞,再對其進行反向概念配對,最終得到五組形容詞對,分別為“威嚴的”—“祥和的”“簡約的”—“繁復的”“雍容的”—“平易的”“莊嚴的”—“輕松的”“華麗的”—“質樸的”。
通過語義差異法測量公眾的感性意向評價,將挑選出的14個樣本與5組感性詞匯結合,構建蒙地唐卡七級語義評價量表(-3,-2,-1,0,1,2,3),將感性詞匯置于量表左右兩側,被試者可根據自己主觀傾向對樣本進行打分,得分趨近于負值則說明該樣本符合左側形容詞(-3為最符合),反之則說明該樣本符合右側形容詞(3為最符合),選擇0則表示持中立態度,如圖1所示。

■圖1 評價量表及語義詞匯
3.4 感性意向調查及結果分析
本次調研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線下采用抽樣調查法,面對面進行問卷填寫,線上調研通過“問卷星”等專業調研平臺,共收集問卷302份,其中男性129人占比42.72%,女性173人占比57.28%,且被試者各項信息分布均符合統計學標準。將問卷數據清洗后進行均值處理,得到所有樣本在五組詞匯中的感性傾向,如表3所示。

表3 語義感性詞匯均值表
表中數值越靠近極值表明該樣本在該組語義詞匯下的情感認同度最高,通過對所有樣本的均值計算可看出,在“威嚴的”這一感性傾向下,最接近極值的是樣本3,均值為-0.42;在“簡約的”這一感性傾向下,最接近極值的是樣本14,均值為0.12;在“雍容的”這一感性傾向下,最接近極值的是樣本3,均值為-0.34;在“莊嚴的”這一感性傾向下,最接近極值的是樣本7,均值為0.19;在“華麗的”這一感性傾向下,最接近極值的是樣本4和樣本1,均值為-0.19。利用表3中的數據還可觀察不同語義感性傾向下得分最高的各個樣本,可將其解釋為在該種語義情感下,公眾對其認可度最高,相反也可找到公眾最不認同的樣本,在進行蒙地唐卡再設計中,可依不同需求、不同情景找到對應樣本,解構其包含的設計元素進行針對性設計,也可依據需求探析得分最低的樣本解構其設計元素后規避其設計特點,以此提升最終設計作品的公眾滿意度,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究樣本中的何種類目會直接影響公眾的情感傾向,則需要通過數量化理論I建立公眾的感性意向與蒙地唐卡設計要素間的線性模型,其次通過多元回歸分析得到類目得分、復相關系數、常數項、偏相關系數等數值,其中類目得分代表了各類目對感性詞匯的影響和傾向,其影響程度可作為再設計時創新要素的參考[19]。
4 蒙古族唐卡意向模型構建
4.1 關聯模型構建
利用數量化理論I可以將原先難以量化統計或研究的問題變得可量化計算,從而對一些基準變量進行預測,更為客觀全面地探索事物間的聯系與內在規律[20]。依據數量化理論原理,將形象因子作為項目,因子水平作為類目,假設現有K個樣本,共有m個項目,第i個形象因子Xi有ri個因子水平類目,則對于第n個樣本來說,δk(i,j)(k=1,2,3,...,n;i=1,2,3,...,ri)記為第i個形象因子的第j類因子水平在第k個樣本中的反應,其取值范圍如下。
假設因變量與各項目、類目間的反應存在線性關系,則可建立如下數學模型。
其中bij僅依賴于i形象因子的j類因子水平類目系數,εk為第k次抽樣中的隨機誤差。依據表1及上述公式可建立蒙地唐卡樣本的反應矩陣(表4),以反應矩陣為自變量,以蒙地唐卡感性語義詞匯均值為因變量,將所有數據整理后代入SPSS25.0中,為后續模型的求解及驗證提供數據基礎。

表4 唐卡反應矩陣
4.2 模型求解與分析
由于數量化理論I與多元回歸分析模型相同[21],故此本次研究利用SPSS25.0對模型進行求解,獲取模型的類目得分、常數項、決斷系數、復相關系數、偏相關系數等數值。
首先建立模型,觀察決斷系數(R2),該數值可代表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程度,其次觀察模型的顯著性(P值),若該值小于0.05則表明在這個模型中,至少有一個自變量(因素水平)會對因變量(感性評價均值)產生顯著性影響,若P值大于0.05則表明該模型中所有自變量均與因變量無顯著性影響[22],在此過程中剔除無效數據。模型精度可通過復相關系數解釋,一般為大于0.85表明模型較為理想[23]。觀察所有數值,以“簡約的——繁復的”為例,再次采用后退引入法進入模型,共得到五個模型,觀察所有數據最終確立第四個模型為最優模型,該模型顯著性良好,根據圖2中的直方圖及P-P圖可知,該模型的回歸標準化殘差整體呈正態分布,各項數值均與本次研究較為符合且擬合度較為理想,最終結果見表5。

■圖2 標準化殘差分布

表5 感性評價“簡約的——繁復的”與因素水平間的線性關系(最優模型5)
因變量“簡約的——繁復的”第四個模型保留C14、C22、C31、C32、C33、C35共計六個變量,其最終的模型回歸方程可寫為。
(因變量Y1簡約的——繁復的,模型4),利用同理可寫出其余幾組有效感性評價詞匯的回歸方程。
4.3 結果分析
依據模型中的決斷系數,可判斷模型對各形象因素及感性評價得分的解釋程度,顯著性P值可確定各自變量是否對因變量產生顯著性影響,通過類目得分可觀察各自變量對感性評價的強弱及傾向,基于此可得出以下結論。
感性評價“簡約的——繁復的”這一語義詞匯與蒙地唐卡造型意向的關聯性預測模型如Y1所示。其決斷系數為0.985,表明該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可用于解釋98.5%的情況,且模型精確度較高。在Y1模型中,C14、C31、C32、C33、C35的方程顯著值小于0.05,表明該因素對當前語義詞匯均值的影響程度較高,C22的方程顯著性大于0.05,表明該因素對前語義詞匯的均值有影響但不顯著。這表明,在設色方面,沉穩端莊的色彩風格也可對當前語義情感產生顯著性影響,在體裁內容方面,描繪宗教戰神的唐卡更符合這一情感,而民俗服飾這一個體形象雖對這一情感產生影響但較不明顯,依據以上原理可用來觀測因子水平對其他感性評價的影響顯著程度。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各影響因素的關聯程度及傾向,還需觀察該模型類目得分。
類目得分可用來觀測模型對感性詞匯的相關程度,其值的大小可用來說明關聯的強弱,類目得分存在正負兩種,本次研究中,得分為正值表明該類目情感傾向偏向右側語義詞匯,得分為負值表明該類目情感傾向偏向左側語義詞匯。在感性評價“簡約的——繁復的”預測模型Y1中,C31歷代可汗、C32英雄人物的類目得分均為負值,表明在蒙地唐卡再設計中,具備以上因素可使得公眾感受到簡約,C14、C33、C35、C22類目得分為正值,表明在蒙地唐卡中,相應的編碼對應因素可以使公眾感受的較為復雜的意向。依據同理可得到其他各影響因素與其他感性詞匯之間的關聯性及情感傾向,以此來對蒙地唐卡再設計進行理論參考與設計指導。
在具體創作方面,利用該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唐卡創作的場景適配性,例如想要快速提升某幅唐卡的可識別性,使其傳遞一種瞬時性信息,讓公眾在短時間內可以理解其內涵并形成印象定勢。以往的創作只能通過創作者的個人經驗加之對“命題”的個人理解,而通過構建數量化理論的映射模型,可對具體創作提供更為準確客觀的指導,例如在具體操作中可以考慮以歷代可汗或民族的英雄人物為主要題材,輔以簡練沉穩色彩,使其情感傾向更偏向于簡約,以此達成最終目標,使得創作方向更為明晰。除此之外,該方法還可運用到壁畫、版畫、產品設計、家具設計等領域中,用來進一步探討公眾對于目標對象情感傾向性的具體影響因素,使其對具體設計行為提供更為清晰、客觀的指導與參考。
4.4 基于蒙古族唐卡與數量化理論的討論
社會的發展影響公眾的審美趣味及其美學價值傾向,社會存在也決定了社會意識,這些影響也為后來藝術設計的發展提供了經驗。當今時代,對于心理、信息、行為此類“非物質”的設計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得設計研究領域的疆土得到進一步拓展。數量化理論屬感性工學中的研究方法,該類研究方法探討了人對感性認知的需求[24],日本筑波大學教授,設計學博士原田昭先生,對于感性工學的定義包含了諸多概念,在其研究所中常將一些研究數據或測試信息結合量表進行計算,得出結論,試圖通過量化來探尋普遍的認知規律。感性工學將研究基礎建立于理性之上,與笛卡爾式的、量子力學類的自然科學不同,其底層的邏輯在試圖用理性的方式對感性進行探索,在生理上找到心理的基石,嘗試將人的“感受”進行量化,使其可以進行統計或計算,以此來得出客觀的、科學的、具有代表性的規律[25]。
現今唐卡藝術,已不再將宗教作為唯一的代名詞,其題材與形式美法則,也日益貼合公眾的生活,表現出新時代下公眾審美偏好。同時我們也能意識到“物”的更新,其意義不單在于所處的位置,更在于其內部復合屬性與不同時代背景下審美需求激發的結果。蒙地唐卡,作為草原地區多民族融合的視覺化闡釋,經過語境化的重置,其器物本身已不再是限定時空下的滯留之物[26],需不斷的進行創新與繼承,沒有繼承的創新易走向虛無主義,缺少創新的繼承則易于陷入復古主義。
以感性工學為底層邏輯,對公眾的審美心理進行預測,以蒙地唐卡為載體,深挖其背后體現的文化儀式、內涵、符號等含義,將其所要傳達的愿景更為直觀、貼合地再次重現在大眾眼前。運用此種研究方法,可對唐卡這一特殊文化符號進行量化剖析,以具體的數據分析作品構建的內在邏輯,為類似內容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同時,對受眾審美心理的量化表達,也為類似內容的藝術創作與設計提供參考,使創作或設計者充分考慮與作品接收者間的審美距離,為不同個體預留出一定的接受空間,可盡量延長作品的“生命周期”,“活”于歷時與共時之中,為創作出符合時代語境的蒙地唐卡、當代壁畫等藝術作品提供新的思路。
5 結語
蒙地唐卡不僅是一種傳統繪畫藝術,也是草原文化的重要體現形式,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重要范式,其展現了受宗教觀念、民族精神、地域文化等多種影響下人民理念世界的表達。雖然蒙地唐卡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且包含諸多可值得深入探究的信息,但隨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該藝術形式已逐漸變得式微,對其的研究也不夠重視。本次研究基于感性工學理論,結合當今語境下公眾對蒙地唐卡的語義感知傾向,構建二者間的關聯模型,客觀、科學地將公眾的情感映射到蒙地唐卡的設計要素當中,研究結果表明,運用該方法可有效地提煉出具備明顯感性傾向的設計元素,也為日后的蒙地唐卡再設計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與創新方向。
本次研究屬于感性工學運用在民族藝術中的一次探索性嘗試,還存在諸多不足,在未來的研究中,可融入形態分析法進一步清晰、細致的解構蒙地唐卡中的各類設計要素,在感性觀測方面,可結合眼動、腦電、肌電等技術,更為精準、完善的探究公眾的情感傾向,為蒙地唐卡再設計及民族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探索更為科學、精準的研究與設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