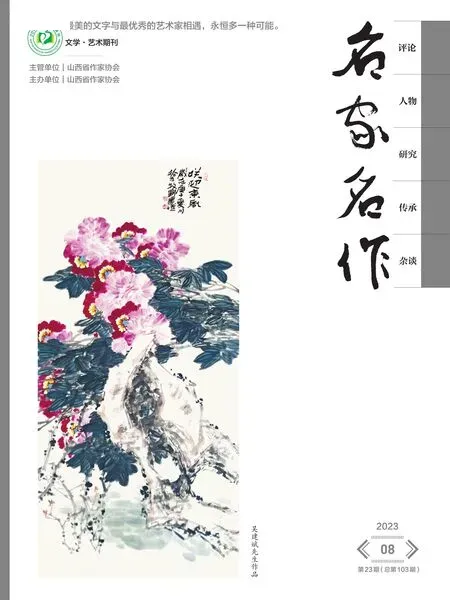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打擊樂化”和聲音響研究
謝 東
20 世紀的作曲家在鋼琴創作中為追求新的音色而挖掘出了鋼琴的“打擊樂風格”音響。對于廣大聽眾來說,這些新潮的、強烈尖銳的不協和音響是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而中國的作曲家在鋼琴音樂創作中,從適合中國聽眾欣賞習慣的音響出發,對人們熟悉的民族打擊樂器進行模仿,將濃郁的中國特色融入音色、節奏、和聲、調式等創作中,創作出了許多中國聽眾感到親切又熟悉的中國風格“打擊樂化”音響的鋼琴作品。
中國傳統民族打擊樂器的發聲是豐富多樣的,它們的泛音共鳴都很復雜。因此,要對打擊樂音響進行傳統意義上的和聲分析非常困難。本文試圖從不同發音體制作材料出發,將中國的民族打擊樂器進行分類;然后分析不同發音體質地的不同音色特點及其與和聲音響的聯系,最后總結出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不同“打擊樂化”音響與之相對應的不同的和聲特點。
一、中國民族打擊樂器分類
中國民族打擊樂器根據其發音體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為四類:(1)響銅,如大鑼、小鑼、 鑼、云鑼、大鈸、小鈸、碰鈴;古老的鐘、編鐘等;(2)響木,如板、梆子、木魚等;(3)皮革,如大鼓、小鼓、板鼓、排鼓、象腳鼓等;(4)響石,指用石頭或玉雕刻磨制的打擊樂器,如編磬、石琴等。
二、打擊樂器發音特點與和聲音響的聯系
(一)響銅類
響銅類打擊樂器因其是金屬發音體質地,發音理所當然“金屬感”十足,所產生的泛音也非常密集、復雜,聽覺上會覺得音響喧囂、強烈、聒噪、尖銳,在鋼琴上表現這類打擊樂器時,常使用高音區和中低音區密集的柱式和弦織體來表現。這類樂器的音色在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屬于模仿較多的,具體的和聲結構將在下文進行闡述。
(二)皮革(鼓)類
皮革質地的打擊樂器主要為鼓類樂器,它們的發音相較于響銅類打擊樂器來說沒有什么泛音,但是有共鳴,音響較結實低沉,余音較短,所以在鋼琴上表現皮革類打擊樂器時的織體一般使用較低音區雙音或和弦。如《長短的組合》第一小節左手低音區的大七度就是模仿鼓的聲音(見譜例1)。《濤聲》的引子和尾聲低音區的柱式和弦模仿寺廟的鼓聲(見譜例2、譜例3)。

譜例2

譜例3
(三)響木類
響木類打擊樂器音色較清脆單一,常作為節拍型打擊樂器,因此其和聲織體較為簡單,通常是通過重復的單音來表現。如第一節打擊樂音色模仿中提到的《皮黃》中二六中左手對板鼓的模仿(見譜例4)。
綜上所述,從鋼琴上對各類打擊樂器發音模仿所形成的織體看,響木類打擊樂器相對較單一,泛音復雜的響銅類和共鳴豐富的皮革類打擊樂器具有相對復雜的和聲織體。下面將對六首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對響銅類和皮革類打擊樂器音色模仿的和聲進行細致分析。
三、現代和聲與民族色彩和聲的結合
大部分響銅類打擊樂器的演奏方式是由槌或棒敲擊發音體來發聲的,如鑼、編鐘、鐘等;另一種演奏方式則為發音體互相撞擊發聲,如鈸、碰鈴等。前者的發聲方式與鋼琴相差無幾,鋼琴同樣也是琴鍵帶起琴槌敲擊金屬琴弦來發聲,所以才有“鋼琴其實就是一件打擊樂器”的說法。不過鋼琴相比真正的打擊樂器發音體面積要小得多,鋼琴琴槌敲擊細小的琴弦所產生的泛音遠遠沒有響銅類打擊樂器被敲擊后所產生的泛音復雜,作曲家在鋼琴作品中運用非常不和諧的現代和聲來模仿這些打擊樂音響,具體的幾個和聲從整體來看就是以非三度疊置的現代和聲為主,四度、五度是我國民族和聲中常用的色彩和聲,又屬于20 世紀現代和聲的范疇;二度、七度既能表現民族打擊樂器獨特的泛音,又是現代音樂追求不協和因素的表現。
(一)含有二度音程和聲的頻繁使用
緊張的二度音程成為和聲結構里的重要因素。大二度是相對較溫和的不協和音程,而小二度是極不協和音程,這兩者在表現響銅類打擊樂器音響的和聲結構中經常出現。因此,二度疊置(包括轉位音程),二度與三度、四度、五度疊置的和聲成為常用的鋼琴打擊樂化和聲手法。
如在《山歌與銅鼓樂》中就運用了非常多的二度音程與其他音程疊置的和弦來表現銅鼓的音響。第6 小節右手大二度與四度疊置和弦,第7 小節右手和弦的根音與左手和弦高音構成極不協和的小二度關系(見譜例5)。

譜例5
第14 小節右手大七和弦第一轉位使根音與高音形成小二度,同時右手和弦低音升D 與左手低音降D 因交錯節奏形成一個二度,這樣形成的幾個極不協和二度音程很形象地表現了熱烈的敲擊銅鼓的場面(見譜例6)。

譜例6
《長短的組合》中也是運用小二度音程的疊置來表現鑼的熱鬧。由兩個小二度和一個三全音構成的“葡萄和弦”是整部作品中和聲材料的核心,在同等數目的和弦中這幾乎已經是最不協和的和弦(見譜例7)。
《皮黃》中搖板的末尾部分,第160 小節將左右手分聲部排列的兩個減五度音程中間形成一個小二度的和聲,此處是模仿鑼的音色,用小二度和聲來表現其不協和的音響(見譜例8)。

譜例8
(二)四度、五度民族色彩和聲的運用
鐘、編鐘等屬于中國古老的響銅類打擊樂器,其音響具有典型的中國民族色彩。這類打擊樂器在鋼琴音響上表現的和聲就用到許多四度、五度疊置的和弦。
《濤聲》末尾登殿主題在高音區模仿編鐘音色,左右手分別由四度、五度構成民族色彩和弦,而將兩個和弦對比來看,兩個和弦中每個聲部與聲部之間形成的也大多都是協和的純五度。高音區不管從單個和弦來看,還是從整體來看,這里的和聲關系都是純四、純五度,音響聽起來五光十色,極具古老的打擊樂器編鐘的韻味(見譜例9)。

譜例9
《五魁》的作者周龍也提道:“我受到中國的一些銅器打擊樂的聲音啟發,如鐘、磐、饒、鑼,它們不像西洋的鐘,聲音是共鳴和諧的,里面的泛音特別復雜,這些結合的音響,使我產生一些構思。”這些想法在《五魁》的和聲上有一定體現。中段第66 小節第一二拍雙手縱向上由兩個純四度疊置構成,橫向上整體呈平行八度移動,第三拍右手變為小七度,右手低音與高音形成大二度,這里既表現了傳統的鐘聲,二度音程又表現其泛音音響(見譜例10)。

譜例10
四、結語
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打擊樂化”音響的創作技法整體上來看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一方面由借鑒西方現代創作手法和吸收民族音樂文化特色而形成,另一方面在表象上體現著濃郁的民族氣質的同時又富有鮮明的現代氣息。例如在音色上,作曲家把眼光聚集在中國傳統的民族打擊樂器上,通過對各種打擊樂器音色的模仿來表現相應的題材,鋼琴作品中體現出濃郁的中國傳統樂器音色。而在和聲特點上不僅運用了20 世紀西方現代音樂創作手法特點,還結合了我國具有民族特色的和聲技巧。可以說,在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打擊樂化”音響是我國作曲家從傳統的民族音樂中提煉出與現代音樂的相通之處,然后運用現代創作手段將我國傳統的音色、和聲等民族音樂要素包裹其中形成的,它是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鋼琴音響。“打擊樂化”音響在中國當代鋼琴獨奏作品中的具體表現就好像穿著西方現代作曲技法的外衣,內在實則還是一顆蘊含著民族民間文化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