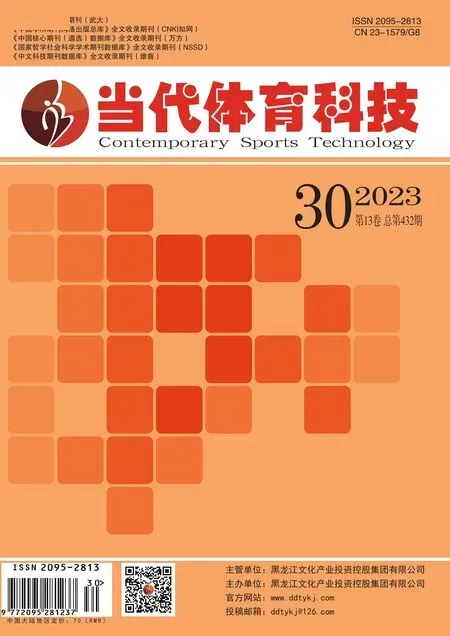我國學校體育生命教育的哲學審視與文化反思
李海鳴
(中國礦業大學體育學院 江蘇徐州 221116)
體育生活不僅是現代社會每個成員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組成之一,也將伴隨個體度過生命的全程。當今弘揚主體性的時代內涵強調,回歸主體生命,因此,生命教育是學校體育場域的重要維度。現代性起源于生命的解放沖動,當現代性成為一個問題時,解決的方案也將需要生命哲學的整體關照[1]。從生命哲學的視域審視我國學校體育教育與生命教育疏離的問題,思考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深度融合的解決方案,讓生命“詩意地棲居”在學校體育的場域中。因為“教育的本質是生命教育”,生命本就是學校體育教育的原點。在學校體育“塑造生命”的教育實踐中,恢復學校體育中“主體生命”詩意存在的理想,既是題中應有之意,也是學校體育教育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1 我國學校體育生命教育的哲學審視
1.1 自然生命是學校體育教育的邏輯起點
自然的原初存在、依賴物的獨立發展以及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這3 種發展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生命哲學對人的生成發展的高度概括,與上述3 種發展形態相對應,人的生命活動鏈條展現了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的3 種生命存在方式。人的3 種生命存在方式使人的生命處于不斷變化的歷史和具體的存在中,并蘊含著無限豐富的生命內容。在人的3 種生命存在方式中,人首先是一種生理性自然生命的存在,失去了自然生命,人也就成為虛無。人的生命意義的生成和人性的建構都是建立在自然生命這一物質載體的基礎之上,人的自然生命不僅包括被簡單看作肉體存在物的低級內涵,還包括被視為富有能動創新性存在物的高級內涵[2]。顯然,與人的生命相關的活動都以人的自然生命為起點,宏大的人類歷史的啟幕也是以“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為起點,同樣,學校體育教育的邏輯起點同樣建立在人的自然生命存在的基礎之上。在學校體育的身體規訓和生命塑造中,從自然生命的低級內涵到富有能動創新的精神生命高級內涵的生成過程,建構了尊重和敬畏生命的價值體系,奠定了發展和完善生命意義的根基。
在“存在論”的立場中,世界統一于存在。任何現實的存在物都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在學校體育教育的場域中,現實的、自然生命的人即是學校體育教育的對象性存在物,學校體育教育正是通過身體手段的自覺實踐對現實的、自然生命的人這一對象性存在物完成了規定性改造,完成了從自然生命到社會生命的價值升華,以及對精神生命的超越。海德格爾將“存在”解釋為當下的在場,而這個“在場”被表示為有現實人的出現,這樣“存在者本身的存在”被認為是最先考察的對象,和認識中的首要概念[3]。因此,在學校體育的場域中最先考察和認知的對象自然是作為學生主體生命的存在者,沒有學生自然生命的“在場”,學校體育教育也就失去了對象性的存在物。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學校體育場域中現實的存在者,學生的自然生命的“在場”,也就形成了學校體育教育的邏輯上的起點。
1.2 社會生命的塑造是學校體育教育建構人性的自覺實踐
在生命哲學的視域中,“人是什么”探討的是人的本性的建構問題。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不同的生命存在形態和生命活動方式。渠敬東認為,人有其生命,往往是被社會賦予的,“就存在論來說,中國人原不是個體本位的,無論君親師友,還是天地族群,都是人依社會連帶關聯而實現的自我構成。人因倫常關系……形成了自然、人際與天道之整全世界的關聯”[4]。實踐和超越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殊本性,由于人的實踐性,人的社會生命在超越自然生命的基礎上以及與社會關聯的實踐中形成了人作為社會存在物的特殊表征。實踐包含目的性,人的社會生命的底色正是通過現實社會中的“實踐”得以不斷發展延續,人性的建構也是人有目的實踐的結果,學校場域中體育教育的自覺實踐是對人的社會生命的塑造,同樣是人性形成和建構的過程。“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是教育面對的3個根本問題,同樣也是學校體育教育面對的問題。社會的進步終歸表現在人的社會生命的發展上,學校體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社會需要的人,學校體育“使人成為社會人”的人性養成教育過程,其實正是對人的社會生命的塑造過程。
學校體育是基于人性的身體活動,首先強調的就是學校體育在培養人的自然性、社會性和主體性中的重要作用[5]。學校體育是基于主體體驗自省以及主體間互相交往的教育過程,學校體育在對人的自然生命的規訓中提供了主體自省和主體間交往的機會。在主體生命的體驗和自省中,體會失敗和成功、堅強和軟弱、勇氣和懦弱等不同的生命感受,在返于自身、歸于自身的自覺反省的認識下切入人性的深處,去把握社會生命的氣息和脈動。同樣,學校體育教育中主體生命間的交往和交流是主體生命的“原始沖動”,拉近現代社會彼此疏遠的人際和彼此芥蒂的信任,建構遵循社會倫理規約的義理人性,在外在觀念內化為自我以及自我意識的外化中形塑了人的社會生命的形象,建構了充滿張力的社會生命的意義。現代化社會科技發展帶給人類豐富的物質財富,也不可避免地帶給人們與外在世界的矛盾沖突,諸如人們對于自然環境破壞以及對自然界生命的掠奪,不僅破壞了自然自身的秩序,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災難性后果。在學校體育教育對主體社會生命的塑造實踐中,將體育規則和體育倫理道德滲透在主體生命的人性建構中,促成自我分裂和解體的異化人性調整生命活動的航道,引導現代社會中膨脹欲望帶來的人性異化回歸人性的本真,豐富和拓展人性的內涵。
1.3 精神生命的超越是學校體育教育對“意義世界”的追求
在生命哲學的視域中,精神層面的生命意味著對“人生至道”的生命體認和意義追問,是為人的存在尋找“精神家園”。因此,無論是對生命追求自由的倡導,還是對生命自我實現的宣揚,都指向生命哲學中的生命“意義世界”。人生是單向旅程,出發了就意味著沒有回程,在這一航程中,是精神的燈塔在指引著生命的航向[6]。學校體育中對人的精神生命的超越彰顯學校體育對“人成為人”的“意義世界”終極追求。學校體育教育在人的自然生命的生存基礎上,通過對主體社會生命的塑造形成了體育自覺實踐中對社會現象是非功過的功利性價值判斷,通過對主體精神生命層面的意義追求,實現著超越性精神追求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理念。學校體育教育在對人的主體生命的體育實踐中引領人對至真生命本然的認知,對至美生命情感的體驗以及對至善生命信仰的追隨。體育倡導的更高、更快、更強,既是對人的自然生命生理極限的挑戰,也是人的精神生命對“意義世界”超越精神的追求。
因此,學校體育教育不是放羊式的快樂教育,享受樂趣的學校體育教育應當是建立在對人的自然生命獸性規訓的基礎上。細品這種看似矛盾的說法,實質上正是苦盡甘來、人生至道的生命應然意義。如果說人的社會生命是基于實踐功利和社會道德需求呈現的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那么人的精神生命則是建立在超越的人生意義精神追求的基礎上展現的天地境界,是人類安身立命和最高支撐點的意義世界。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文明下,在人性欲望膨脹所致的對自然世界生命的無限索取中,人類自身也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是要尋求一種在保障個體自然生命的前提下,在不同生命主體之間互生共融的和諧局面。在生命底色和生命意義的疏離中,學校體育的身體規訓和生命展演成為找回精神生命意義的重要場域,成為拯救人性的重要途徑。
2 對我國學校體育生命教育的文化反思
2.1 對我國學校體育生命教育本質問題的反思
對學校體育教育本質的思考一直是學界致思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是指學校體育教育這一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的質性規定。我國學校體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價值立場還是課程體系,都存在“鐘擺”現象,這是源于學界對學校體育教育本質的認知不同造成的。目前,學界對于我國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論調多集中于教育活動論、社會活動論及人化論等。沿著我國學校體育教育的歷史足跡,人們顯然忽略了學校體育教育中對人的主體生命塑造的發展線索。在學校體育的場域中,盡管人的主體生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但是人的主體生命一直都隱身在學校體育場域中,是最能展現生命創造和自由意識的體育本質的重要元素。
“教育的本質是生命教育”,因此,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同樣是在學校這一特定場域通過身體的手段進行的生命教育,就其本質來說,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是對學生生命的塑造。從生命哲學視域上講,人的整全生命是身體、文化、社會等元素凝結形成的復雜的整體存在。就學生主體生命塑造而言,學校體育教育的歷史做法并沒有體現對學生生命塑造的學校體育本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學校體育確立的增強體質的教育思想,是在國民體質羸弱的現實國情下對學生實施的單向度身體層面的改造;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引進國外的自然主義、快樂主義等體育思想,還是實施的素質教育、健康教育的教育理念,都沒有實現對學生主體生命塑造的體育理想。
對于學校體育教育生命本質的曲解體現為:只把學校體育看作為一門課程,導致學校體育地位的弱化;把學校體育塑造生命的任務弱化為增強體質或者促進健康,萎縮了學校體育的功能。學校體育的目標主體是青少年的全面健康發展,不能局限于青少年體質健康[7]。長期以來,我國學校體育教育一直在學界質疑和探索中前行,學校體育教育誤將體質當目的[8],一度受到學者詬病,而學校體育立足于學生健康,同樣遭到學者的質疑[9]。學校體育教育既要立足于體育本質,也要立足于教育本質,這是確立學校體育地位的前提,也是理解學校體育教育本質的基礎。人們應當客觀承認,學校體育“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在一定范圍的確是真實客觀存在的現象。只有明確學校體育教育的育人地位,確立學校體育教育的生命本質,才能真正實現學校體育教育塑造生命的本質功能。
2.2 對我國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疏離問題的反思
立足于體育和教育的生命本質,學校體育教育就應該與學生主體的生命教育緊密聯系。事實上,在我國學校體育教育的實踐中,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就是當下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的疏離問題。“在人性異化和學校體育異化的當下,筑造了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隔離的圍欄。”[10]應當承認,人們現在既沒有在頂層設計上將生命教育納入學校體育教育的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中,也沒有在課程設計和課堂實踐中將體育教學與生命教育有機結合。每到體育課時體育老師就生病的現象,折射出的不僅是體育教育的邊緣化問題,深層意義上應該歸結于對于生命教育的漠視。與體育課程相比,在現有的學校教育課程體系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門課程的地位弱于體育課程。在無法改變應試教育分數評價的導向下,如何提升學校體育教育的地位,將學校體育與人最寶貴的生命結合起來,的確是當前學校體育再也不應該忽視的重要問題。
在學校教育的“五育”體系中,體育教育屬于身心和諧發展的層次,“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身體不僅是“德、智”所寄,也是勞動教育的物質基礎。體育也與美育相關,體育美不僅能塑造外在的體態美,而且能培育內在的心靈美。因此,在學校教育的“五育”體系中,體育的地位毫無疑問應該占據最為重要的一席。盡管只有學校體育并不能完成生命教育的重任,但是學校體育對于學生主體生命的塑造和教育的作用無疑是最重要的。在學校體育“以體化人”的體育實踐中,通過對學生自然生命的身體規訓,增強學生身體體質;通過身體運動和體育比賽,將體育倫理和體育規則滲透在學生主體社會生命的自覺實踐中,建構主體生命的“義理人性”,追索精神生命的人生意義。
無論對于學生個體還是國家和社會而言,學生主體生命都是最為寶貴的。主體生命的生存、安全以及主體間交往等問題都是生命教育的重要主題。現代工業文明導致的既有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的混亂,已經讓主體生命無法“詩意地棲居”。在生命信仰失落、社會規范解體、理性破滅以及傳統否棄的現代社會,福柯宣告著“在現代生活中,人已經死了”“主體性的黃昏”以及“告別主體性”成為社會時尚調門,改變“天人二分”和“自我中心”的觀念,重構主體性生命的意義就成為生命哲學關懷下的生命教育問題。在學校體育的時空展演中,主體生命通過體育實踐的中介去體驗與他人交往的快樂幸福,體驗生命的意義,實現人生的價值升華。
2.3 我國學校體育實踐中生命教育的轉向與融合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教育不應該僅僅放在口頭上,而應該落地生根。在當下社會,人們感嘆人的生命生生不息,亦逝者如斯,演繹著人世間的興盛與衰敗,在“天道有常”與“人生至道”的生命圖景中,學校體育教育回歸人的生命本源,是學校體育教育躬身自省的反思與自問。中國人所要的社會科學,一定是基于體驗的、反躬自省的、將心比心的科學,而不是所謂功能論、協調論或是均衡論這樣的概念空殼[11]。歸屬于社會科學的學校體育,同樣不需要這樣的概念空殼,而是需要落地生根的體育教育與生命教育的融合。新時期我國學校體育的改革,應以生命教育為發展取向”[12],以學生自身發展需求為出發點,以實現學生全面發展為落腳點,回應新時代人才培養的要求[13]。
在學校體育教育與生命教育的融合問題方面,首先應回歸生命本原,確立生命關懷的學校體育教育的本真價值。學校體育面對的是人的生命,回歸生命本原,既是學校體育本然的生命品格,也是現代社會生命意義的追求使然。其次,應重視生命體驗,建構生命張力的體育課堂。生命的意義就是生命的體驗,通過人的感悟、體驗來思考生命的意義。建構學校體育充滿張力的生命化課堂,體育教師引導學生個體生命體驗的同時,也將內心對生命的體悟與思考傳遞給學生,學生作為具有生命和感受能力的人,會體驗到運動對自己身心產生的影響[14]。生命張力的體育課堂,不僅是體育知識的傳遞,還是生命意志的滲透以及對生命內涵的領悟。此外,優化學校體育系統中的生命元素,從課程設計到評價體系都應立足于人的生命素養養成和身心和諧發展的目標取向。
在學校體育的時空,“讓生命詩意地棲居”,這是學校體育教育的理想圖景。學校體育的生命本質回歸,是學校體育內在的生命品格與價值追求,實現生命教育與體育的融合,在體育體驗中感受生命的靈動、體悟生命的真正內涵[15]。學校體育場域中的生命教育,要在自然生命維度上提升人的健康素質,在社會生命維度上關注社會生命的人性建構,在精神生命維度上高揚意義世界的生命終極追求。倡導學校體育回歸生命本質,將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的融合付諸實踐,這是新時代學校體育的新的必然路向。
3 結語
學校體育場域中,生命教育的缺失現象已經引起學界的關注。將生命哲學思想引入對學校體育生命教育缺失的思考,既是對當下社會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回應,也是對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疏離問題的反思。自然生命的存在是學校體育的邏輯起點;社會生命的塑造是學校體育“建構人性”的自覺實踐;精神生命的學校體育教育超越是學校體育對生命“意義世界”的終極追求。反思學校體育中生命教育本質的曲解問題,解決學校體育與生命教育的疏離和融合等問題,是對當前學校體育生命教育缺失的深刻反思,只有將生命教育融合在享受樂趣、增強體質、健全人格、錘煉意志的體育實踐中,才能真正實現學生主體生命詩意存在的生命理想,展現新時代學校體育應有的責任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