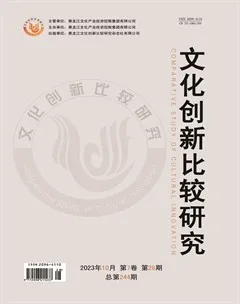喬姆斯基語言學的科學研究
蔡軍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湖南長沙 410205)
轉換生成語言學的誕生是從1957 年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出版專著《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開始的,其誕生不僅對語言學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還對心理學、生物學、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發展有一定的啟示。然而,許多不了解喬姆斯基理論的人,一方面對其著作中晦澀難懂的討論及陌生的符號不知所云,另一方面認為它“違背科學理論建設的基本邏輯原則并且嚴重脫離語言實際”[1]。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與他們所熟悉的傳統的語法大相徑庭。其實他們的問題在于混淆了“語言學”和“學語言”兩個基本的概念[2],不了解喬姆斯基眼中的語言學研究及其語言觀哲學基礎。本文以此為出發點,探討語言學研究的科學性質及其哲學基礎,以期消除人們對該理論的誤解,并真正地理解語言學研究的本質。
1 內在主義語言觀
眾所周知語言學將語言視作研究對象,生成語言學的學者們將語言學視為研究語言本質的科學。那么,語言究竟是什么?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是人區別于其他物種的屬性,是表達思維的系統,因此人們大腦之中的“內在性語言”(即I-語言)是第一性的,而在交際過程中所使用的“外表化語言”(即E-語言)是第二性的[3]。這種內在主義語言觀不同于把語言視為身外之物的外在主義語言觀點,是生成語言學最具革命性的一個標志。
每個正常語言使用者的大腦中都掌握著自己母語的語法知識。本族語使用者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語言組詞造句,具有理解自己語言的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產出與理解語句的語言能力完全是下意識的。雖然很多時候人們意識不到,也說不出其中的規律與道理,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正確地使用和理解自己的語言。喬姆斯基把說話者對自己母語的這種下意識語言知識稱為“語言能力”,而把具體環境中語言實際使用稱為“語言運用”[4]。語言能力體現為規則的有限集合,可以反復地運用以生成無限數量的合格句子,其中包括許多從未見聞過的。這就是所謂的“有限的手段,無限的運用”。語言能力是語言運用的基礎;失去了語言能力這一根基,語言運用便無從談起。語言能力具有穩定性,但語言運用則受心理與社會因素影響;語言能力是完美的,但語言運用并不總是能夠真實地作出反映。
喬姆斯基明確表示語言學研究的是I-語言,而不是E-語言。I-語言指個人頭腦中掌握的語言知識,或者說語言能力,大體上相當于通常所說的“語法”。內在性的I-語言與交際使用的外化E-語言相比更加可靠,因為盡管I-語言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但至少恒定存在于由物質構成的人腦之中。語言最終在于心理/大腦,因此內在性語言是基本的,外表化語言是派生的。
因為語言結構具有遞歸屬性,可以無限地構成新的結構,所以語言是一個無限系統。受規則制約的無限系統是無法依靠學習掌握的。而正常的語言使用者都具有說出和理解無限多語句的能力。那么這種能力是如何獲得的呢? 兒童在習得母語時顯得異常輕松,似乎毫不費力,這種特別之處在于:其一,缺乏成人的刻意教導;其二,兒童語言發展呈現明顯的階段式,無論兒童個體所處的外部環境如何不同,但他們所經歷的階段和花費的時間大致相同,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在其他技能發展方面并未出現;其三,兒童在短短的兩三年之內完成了語言習得所表現出來的快速性,能夠自由地與成人進行語言交流,掌握了高度規則化的系統,是無數已經成年了的語言學家窮盡畢生精力都難以揭示的規律。基于母語習得的一致性和快速性等事實,喬姆斯基認為最佳的解釋是假設習得的過程由大腦中一個語言器官所決定的。他還設想,語言器官是通過生物基因遺傳而與生俱來的,其初始狀態是人類普遍共同的;在不同語言經驗的引發和作用下,人類成員的語言器官經過生長到成熟的過程,最終形成其不同的穩恒狀態。語言器官的初始狀態和語言學家所構建的關于這一狀態的理論,均被稱為“普遍語法”。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先天的普遍語法或語言器官是基礎,起著內因的作用,而來自具體語言的語料是誘因;內因在外因的作用下,按照生物基因的遺傳程序完成個體的語言發展。智力、外部環境等外在因素對生物遺傳程序所規定的內在發展影響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面臨著“刺激貧乏”問題,人的語言或內在語法知識不是依靠學習獲得,而是依靠生物基因“生長”出來,每個人都能在適當的環境下正常地發展出語言,就像每個人都會長出兩條胳膊,而不會長出兩個翅膀一樣,這是人的生物遺傳基因使然。
語言習得的過程由天賦的語言器官所決定的這一主張稱為語言的“天賦假說”。喬姆斯基認為,使用和獲得語言的能力是人類所獨有的,反映了語言的生物屬性。說到先天論,不能望文生義造成誤解:大腦內部物質及構造,使得人類具有語言天賦;由于動物的大腦不同于人腦,因此動物無法掌握人類語言。依靠生物遺傳的語言器官或普遍語法知識不存在人種、個體、民族、家族等差異,因此兒童不選擇母語,只要在適當語言環境下,接觸到一定的語言材料,兒童就可以發展出以所接觸語言為母語的個體語法知識來。
2 語言研究的本質
由于喬姆斯基堅持內在主義語言觀,導致許多人對其語言研究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首先,什么是科學? 1888 年達爾文認為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得出結論”。《辭海》的定義是,“科學: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的規律的知識體系”[5]。可見,科學有4 個典型特征。第一,客觀理性,即科學研究以客觀事實為基礎;第二,可證偽,任何理論的正確都是相對的,總有一天現在的理論要被推翻、修正;第三,局限性,任何理論的正確性僅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第四,普遍必然性,真理源于實踐,也必須回到實踐中去解釋其適用范圍內的事實,并驗證真偽。那么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生成語言學是不是一門科學呢?
一門學科要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必須具備3 個條件:有客觀的研究對象;有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有系統的科學理論[6]。“神學”不是科學,因為神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客觀存在的。雖說“電子”“原子”肉眼看不見,但是可以通過科學實驗來證明它們的存在。而神不同,它看不見摸不著,既不能證明它的存在,也不能證明它不存在。
語言學研究描寫一些平凡甚至被人忽略的事實,提出科學假設來解釋事實,因此語言學是科學。譬如人們習以為常的蘋果掉落在地上這件小事,牛頓的貢獻在于提出萬有引力的道理。同樣如此,語言學的客觀研究對象是語言,它從小問題中發現總結規律,提出科學假設和理論。理論從不同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抽象概括,挖掘其本質特征,揭示表象背后的規律。由于語言學家對研究對象考察的角度不同,理論也各不相同。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假設,因此各種理論無對錯之分,理論只有優劣之分。評判理論優劣的標準是該理論是否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與解釋力。譬如,在翻譯研究中,這個《紅樓夢》的譯本比另外一個譯本好,但如果被問及好的標準是什么?他們很難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答案。這樣的研究和基于此提出的假設理論是在敘述研究者個人的內心體驗和感受上,因研究者個人的修養、對事物的認知和欣賞水準的差異而不同,不能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別人也無法重復和驗證,因此缺乏概括力和解釋力。喬姆斯基指出理論建構的目標是解釋[7],如圖1 所示的生成語法學中的X’理論。

圖1 生成語法學中的X’理論圖
這一結構程式使語法得到更高度的概括,揭示各種句法單位的內部結構及共性。該理論揭示了短語和分句都是向心結構,并且X’中間層具有可遞歸性。這樣的定義具有普遍性,適用于其他結構及語言。同時也可以通過語言事實進行驗證,不僅英語如此,其他層次結構化語言也都如此。X-階標理論挖掘了語言本質特征,揭示表象背后的規律。當然該理論隨后也得到不斷修正,如Abney 提出的“DP 假設”使理論更加完善[8]。以上說明喬姆斯基理論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解釋力,它是剛性的、嚴謹的,不會因人而異。喬姆斯基后來提出的最簡方案更加貼切地說明了這一點。語言學理論應尋求更大的解釋力,即為各語言現象背后的共性構建統一解釋模型,這一點與喬姆斯基建立普遍語法的初衷是一致的。
學語言所學的是個別語法。研究語言就是給全人類增加新知識。語言學要探索的是人類迄今為止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及其背后隱藏的規律,即普遍語法。因此語言學與學語言是兩碼事,研究語言是學術活動,學習語言不同于學術研究。在研究語言過程中,喬姆斯基理論采用了許多數學概念和數學符號,人們把它跟數學等同起來。其實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是經驗科學,只是像某些學科,如物理學一樣使用數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但是它并非數學本身。認為語言學屬于經驗科學的人們也存在分歧,與喬姆斯基的理念不同,他們認為語言是一種交流的工具,它的使用離不開交際,更離不開語境;它的產生是人類生產活動的產物,具有時空、社會、民族、人文等特性,因此也離不開社會。因而語言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但是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是自然科學。因為每門學科既可以把研究對象和其他事物聯系起來研究,也可以分開來研究。譬如,進行數學計算時,不會考慮其反映的社會問題,因為數學題所涉的社會問題與計算無關,依此類推語句表達的社會問題也與語法無關。因此普遍語法理論研究關注語法結構形式,即語言本體研究,不涉及交際功能,也不涉及說話時的環境。當然,這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已,并不反對其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
3 喬姆斯基語言研究的哲學觀
哲學是思想的源泉,喬姆斯基關于語言研究的思想主張的出現絕非偶然,他從哲學的高度探討了語言的本質及對語言學研究的科學定位。喬姆斯基的唯理主義思想起源于柏拉圖,在批判、繼承笛卡爾和洪堡特的基礎上形成。他的唯理主義是建立在生物遺傳學基礎之上的一元論,克服了前輩思想家建立在“上帝”基礎之上的心物分離的二元論,其中既有繼承和發展,也有批判和揚棄。
喬姆斯基的語言觀受到了笛卡爾唯理主義的影響。鄒化政指出,唯理主義認為真知是超越經驗本身的,經驗僅是激活我們的先天認識原則的手段,只有理性演繹才能獲得一切知識[9]。由于人們往往憑借“經驗”去看待問題,并斷言經驗論是對的,而不去深究感性與理性之間的復雜關系,由此造成被“表象”所迷惑。所以對事物的認知,不僅要關注其“表象”,也要在認識來源上把握其“普遍必然性”,即不是直接從現有經驗去歸納、概括、抽象,而是肯定思維的能動作用。因此,對于語言,笛卡爾提出了“天賦論”,主張語言知識源于人的語言官能及普遍語法,語言是內在的。
洪堡特認為語言是一個內部相互聯系的有機體,是人類本質的組成部分[10]。語言能力是人類特有的種系生物遺傳屬性,而人類內在需求觸發了語言的萌發,而不僅是因為交際需求。他把語言稱為“創造性的活動”,講話者是語言的創造者,同時也接收并理解所創造出的言語成品,產品可以隨著外部條件的變更而改變,這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創造活動。正是由于語言是大腦的一種能力,講話人可以在任何時候都對有限的語言材料進行無限的創造和利用。因而語言學習是個再生成的過程。反觀普遍語法,它潛藏于人腦中,由此及彼被演繹推導出來。這反映了洪堡特對語言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理解。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及“天賦假設”語言觀是對笛卡爾和洪堡特觀點的繼承和揚棄。經驗是表象的東西,它不直接體現本質,我們所接觸的言語是語言的實際運用,但它不是語言本身。
隨著語言研究的發展,人們對身與心的關系不斷探索深入。心智哲學源于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即世界上不僅有物質而且還有心智,物體和心智是相互獨立的。在笛卡爾看來,“我思故我在”,心智的思考以“思”為前提,與身體無關,身體不能思想。換而言之,世界上存在著不依賴于精神的肉體物質,也存在著不依賴于肉體物質的精神,它們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獨立的本原,均由上帝創造。喬姆斯基認為,對語言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希望通過深度挖掘自然語言的本質來獲取人類所特有的心智知識。他認為“把如此復雜的人類成就歸于幾個月至兩三年的經驗,而不歸因于幾百萬年的進化或深深植根于自然法則中的神經組織,這是毫無道理的。其實,后者更符合物質規律,更能使人們認識人在獲得知識方面與動物的不同”。同時他還指出,語言是“心智的一面鏡子”[11]。語言不是簡單的社會行為產物,而是儲存在大腦中通過生物遺傳、進化獲得的一種能力。喬姆斯基把學語言比作學走路,學走路本身不是學習,而是大腦的發育成長,語言同樣如此。喬姆斯基把語言看作人腦的一個特殊器官,即語言機能,是人類所特有的。在喬姆斯基看來,說英語和說漢語的兩個人頭腦里的語言機能是相同的,即語言運算系統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兩人認識的詞匯不同而存在差異。
人們對喬姆斯基提出的心智概念存在不少誤解,認為這會將人們導向二元論。事實上喬姆斯基看待心智是自然主義的,即人的語言知識或者語言機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這一點與柏拉圖、笛卡爾的哲學思想不同,他們對心智的看法是非自然主義的,認為人的心智和心智的活動是非物質性的,不受自然規律控制。同時,也與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的看法完全不同。喬姆斯基把語言看作人腦中的心理客體,是人類經過漫長進化期后構建的心智結構,是大腦中的程序裝置,類似于計算機中預置的程序;結構主義只承認語言有物理表現,不承認語言有心理表現,因此有嚴重的局限性。喬姆斯基的“心智主義”與神學無關,與個人的意志、精神等也無關。此外,不同于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喬姆斯基主張心智并不獨立,而是以物質為基礎,心理依賴物質。
心智與大腦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目前仍是知識空白。喬姆斯基把一切自然之物看成是完美的,并以此作為科學信念和科學公理。他后來提出的最簡方案理論就是秉承這一科學公理。眾所周知,語言的基本功能是有效表達和交流思維,但是我們的言語行為產出有時并不完美,因而需要一種能同時完成表達功能和交際功能的語法機制。既然語言呈現交際不完美性和思維完美性,而又將人類語言視為自然進化之物,那么最簡方案理論平臺就要研究出這個自然之物的語言系統完美地滿足同其他系統的接口條件[12]。雖然“心智”說和“天賦”說在目前看來只是一種假設,但是隨著其他學科的進步,解開人腦活動的奧秘指日可待。
4 結束語
打破思維桎梏,生成語言學顛覆了以往對于語言學研究的傳統認知,將語言學視作同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學等學科一樣的自然科學。人類所產出的語言不再僅被當作人類溝通交流的手段,更被看作了思維表達的工具,被看作了人類共有的真正物種屬性。喬姆斯基繼承并發揚了唯理主義的傳統,認為人類語言的語法知識是先天的、普遍性的。人腦中設有語言習得裝置,一經外部語言環境觸發,短時間即可習得語言,能很好地解釋刺激貧乏現象。多年來,圍繞喬姆斯基語言理論的爭議一直不斷,有高度贊賞的,有難以認同的,或對假設提出質疑的。本文從喬姆斯基理論出發,論證分析了語言學的科學性質及哲學基礎,全面刻畫喬姆斯基語言觀,有助于消除對生成語法的誤解。語言科學研究是透過事物看本質,進行科學分析,才能去偽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