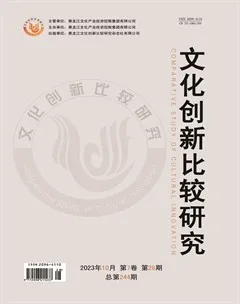西方場所特定性(Site-Specific)舞蹈中的先鋒精神探究
常方,趙宇
(1.漢陽大學,韓國首爾 04763;2.山東藝術學院,山東濟南 250300)
場所特定的舞蹈始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即后現代舞蹈時代。它可追溯到坎寧漢和凱奇等當代藝術家的初期實驗作品,試圖避開劇場空間,打破藝術和日常的界限。克洛伊切爾和帕夫里克解釋說:“在這個時代,很多體裁的藝術家都在抵抗傳統的創作過程,測試藝術和日常的界限。”所有空間都被認為是可以進行舞蹈表演的空間,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間、廢棄工廠、建筑空間,以及湖泊、山地等自然環境空間。藝術家們通過后現代主義思想,打破藝術和日常界限的演出逐漸形成演出場的設定和新意義,這種舞蹈表演類型被稱為場所特定舞蹈(Site-Specific Dance)。
場所特定舞蹈表演是從后現代舞蹈時代的“一切都是舞蹈(Everything is dance)”口號下嘗試的各種實驗工作之一的“去劇場化”開始的。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先鋒派在文化領域突破了多項傳統規范,創作了大量藝術、文化或社會實驗性、激進性或非正統性的作品,被許多人視為現代主義的重要象征。很多藝術家參與先鋒派并持續進行富有先鋒精神的藝術活動,從達達主義到后現代主義,開啟了創新視角。
1 場所特定(Site-Specific)的概念及特性
Site-Specific 是指在特定場所進行的表演藝術、在特定場所或特定空間獲得創意后制作的作品類型[1]。特定場所的演出在舞蹈領域可能比較陌生,但在美術、話劇等其他表演藝術領域已經普遍化。在劇場以外的街道上演奏音樂或唱歌,即興跳舞,在啞劇場、美術館以外的街道、地鐵站等日常生活空間展示美術作品。但是在野外進行作品演出并不都屬于場所特定。“場所特定”最基本的定義是離開原來基礎的場所,使用其他場所,根據場所的特性,創意性地展現作品。
首先,“場所特定”一詞的由來雖然不明確,但至少可以確認在美術史的脈絡下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在場所特定的美術中,“場所特定” 可以說是包括前面用語概念的更廣義的用語[2]。具體提及該用語的尼克講述了包括表演、視覺藝術等在內的擴張場所特定藝術。另外,還參考了塞爾托的“空間實踐”概念和吳杰的“秘密場所”概念,試圖整理現代表演藝術的“場所特定性”概念。場所特定美術的場所性以極簡藝術、表演和突發事件的形式,在展現經驗性和現象學討論的同時進行實踐。Words 是讓觀眾直接參與設置和意圖的作品,作家在兩個房間的紙上寫了一個詞,掛在不同的位置上,房間里準備了梯子和筆,觀眾邊走邊在墻上寫字,由作家調節的電機中隨著觀眾的涂寫,流淌出詩意的句子。觀眾實時直接參與作品制作的行為,就是場所特定演出的一大特性,即觀眾參與性。
如果說過去現代主義美術徹底區分了作品的空間和現實的空間,即日常的空間,將觀眾排除在場所和作品之外,那么突發事件和極簡主義的場所特定作品則讓作品、場所和觀眾實際遭遇、實時遲到和體驗,使觀眾不再被解釋為超越時間的不特定的多數,而是形成作品,進而成為自己生產和接受作品的主體。他們克服了主體對場所的疏遠,正在生成傳統演出空間的新替代場所。
目前,在“場所特定戲劇(Site-Specific Theatre)”一詞的起源尚未明確的情況下,戲劇史中針對新空間的多種嘗試可以找到與場所特定戲劇所向往的各種脈絡的共同點。理查德·謝克納的環境戲劇(En vironmental Theatre)和當時的街頭劇就是場所特定戲劇的代表。他確立了環境戲劇的基本原則,即一旦打破空間規則,觀眾就可以成為參與者,而且每次演出都會形成和創造觀眾和演員融合的新空間。話劇《你的沙發》[3]不會像現有的電視劇結構一樣,以一種趨勢吸引觀眾或結束。觀眾在觀看期間會創造各自的途徑,有些觀眾看到的東西,其他觀眾可能看不到,有些先來的觀眾看到的,后來的觀眾可能不會看到。因此,可以更個別、更自主地體驗演出,是場所特定的另一個特性,即自主性。
因此,場所特定指向舞臺外現場發生的實際活動的現場。在一個空間內相互作用并存在的行為者和觀看者創造的場所特定演出形式,將現有的舞臺和觀眾席、演員和觀眾之間的界限和距離全部解體。演出分為劇場內規定的距離(distance)和界限,舞臺上的華麗看點填滿的典型習慣或拒絕是商品。這也使拒絕藝術成為一個批評對象或可以分析的藝術,拒絕成為瞄準制度框架的藝術。
2 先鋒派(Avant-Garde)的特性
先鋒派是革命性前衛部隊的軍隊用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以社會激進變化為導向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中被廣泛使用[4],成為藝術史上的重要論題。20 世紀是先鋒派的時代,先鋒派作為同時代美術的話題,它通過拓寬美術領域,革新實踐,對新事物的評價和分類起到重要作用。
先鋒派理論1852 年在《藝術家、科學家、產業家》一文中表示,藝術的力量是社會、政治、經濟改革最直接、最迅速的道路,并要求藝術家們“作為(民眾的)先鋒服務”。20 世紀初,破壞對純藝術的傳統想法、對藝術的制度框架提出質疑的一系列藝術家們自稱是先鋒藝術者。法國詩人博德萊爾就“先鋒派”稱其為理念上激進的左派藝術,被稱為先鋒派的集團包括未來派、表現主義者、達戴斯特、超現實主義者[5]。他們圍繞近代藝術的習慣和制度的保守主義問題,夢想著新的藝術,否定傳統藝術,提出了藝術的新前景。
當然,如果摒棄藝術制度,肯定會出現某種“新事物”,但新事物概念太普遍,新的藝術不能馬上命名為先鋒藝術[6]。先鋒派意義不是制度化新追求的結果或單純與以前不同的新事物,而是更具體的蘊含著追求社會革新變化的精神。因此,有必要基于對先鋒精神的根本理解來理解先鋒派,新事物的類別不僅太普遍和模棱兩可,而且不能明確提出區分流行性革新和歷史必然革新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可以表明,先鋒精神以下面兩個特點為滿足條件。
第一,先鋒派藝術家們蘊含著超越藝術實踐的時代精神。先鋒精神追求面向社會的開拓精神和先驅者的姿態,追求與至今為止的藝術表現相反的方法和表現。另外,在表達這一觀點時,超越單純的審美技術表現,將社會批評與藝術實踐同時進行,作為社會、文化變革的主體進行活動。
第二,摒棄脫離生活的藝術。他們在先鋒派之前的藝術一直起到區分藝術領域和生活領域的框架作用,因此批判了藝術與生活背離的文化。先鋒藝術家們脫離了創作作品的行為本身僅限于藝術實驗的理由,即藝術實驗和現實參與,排斥對現實的漠不關心。這種思維直接介入現實問題,通過藝術進行生活變革,發展為實踐“生活與藝術融合”的前衛的理念。
3 場所特定舞蹈的特性
一戰以后,人們對現存的一切事情都充滿了懷疑和抵抗,同時也為現代藝術的轉型提供了決定性的契機。以反藝術和反文明為名,藝術家們以近代絕對價值和固有觀念的解體為目標,試驗了多種前衛、激進的藝術思潮。場所特定舞蹈就是該時期的產物,它以一種新的視角進行舞蹈創作,具有獨特、先鋒的藝術審美特性。
第一,將熟悉的地方轉變為獨創性和藝術性,具有重新發現不熟悉場所的獨特性。作為場所特定舞蹈創作的先鋒編舞家斯蒂芬·科普洛維茨就針對各種大眾所熟悉的日常場所創作了很多具有先鋒精神的作品,無論是在英國國立圖書館公演的作品Babel Index,公交站公演的Fenestrations,還是在博物館公演的Genesis Canyon,都是對熟悉的場所進行針對性創作,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具有獨特性和先鋒性。
第二,即興性和現場性。根據演出當天的天氣或周邊環境、地形特征等因素,同一個作品演出的呈現和結果會完全不同。例如,約安·布爾喬亞在法國露天廣場演出的作品Passants 和在巴黎萬神殿演出的作品《歷史的機制》雖然使用了相同的道具和主題動作,但是場所的變換使作品完全呈現出不同的氛圍和思想。這是因為場所特定舞蹈是演出者和觀眾的距離、場所的歷史、場所的過去或現在的用途、場所的設施材料和質感、周圍的噪聲、自然采光等多種要素具體化后形成的。
第三,比現有的傳統劇場演出更具擴張性和包容性。隨著觀眾層的多樣化及觀眾數量的增加,場所特定舞蹈給演出者和觀眾都帶來了積極的效果。舞蹈消除了舞臺和觀眾席、演員和觀眾之間的界限,觀眾可以選擇參與作品共同演出,打造了 “民主結構(democratic structure)”[7]的舞蹈,這是為了體現身體的物質實體(substance)及其特別的物理效果[8]。舞蹈表演中的開放空間不僅是演出場所,還具有根據獨有的特點和與觀眾的距離,刺激觀眾的好奇心和視覺的效果,同時給表演的舞蹈演員帶來新的靈感和能量。
4 西方場所特定舞蹈中的先鋒精神的表現和追求
4.1 內在的意識形態表現
場所特定舞蹈最重要的是編舞家創作的靈感是從演出場所獲得的,即作品的創作可以說是從對場所的研究開始的,編舞家從場所獲得靈感,計劃作品的主題和意圖。而意識形態是指人們在與物質世界相互作用時,根據所經歷的感覺,在他們的腦海中形成的想法。場所特定舞蹈中呈現的先鋒精神將編舞家的構想解體、抽象化、現代化,最大限度地把意識形態通過藝術化身體本身,表現精神和藝術能量。
約安·布爾喬亞在法國露天廣場演出的作品Passants 和在巴黎萬神殿演出的作品《歷史的機制》雖然使用了相同的道具和主題動作,但是場所的變換使作品完全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氛圍和先鋒思想。Passants 通過廣場上觀眾和演員在圓形裝置上不斷地行走、跌落、彈起,表現了生命的不斷輪回,利用人與蹦床力的對抗表現編導對生命不屈的理解與藝術表達。而《歷史的機制》只通過4 名演員以同樣的形式呈現了歷史的更迭。雖然作品構成相同,但編舞家對兩個作品的意圖不同。這意味著編舞家有意利用現有的舞蹈作品,并安排在特定場所的 “重構(reframing)”概念中。在重構過程中,場地與創作工作有一定的相互關系,編舞家可以改變或修改有關場地物理成分的編舞意圖和主題等。例如,在DV8 的作品The Cost of Living 可以看到,該作品原本是針對傳統舞臺的作品,之后被制作成舞蹈錄像帶,再之后作品更名為Living Costs,2003 年在倫敦的現代美術館再次公演,觀眾邊散步邊觀看演出,雖然作品的主題及內容都一樣,但通過場所和作品的相互作用,使演出更加豐富多彩,給觀眾帶來新鮮和刺激的體驗。編導通過特定場所的特性結合藝術表現形式和手法,試圖擺脫不合理的現實,找回對人類生活和人類本性的關心,縮小生活與藝術的差距。
舞蹈家們為了完成真正的自我恢復,集中于人類內心的原始欲望和感情,通過藝術創造行為,通過多樣的藝術嘗試,通過自我告白尋找真正的自我,進而通過藝術拯救社會。藝術是人的藝術,是人性表達的藝術,藝術的價值在于展現人的生存狀態,其著重點在于精神[9]。
4.2 對舞蹈空間絕對自由的追求
薩莉·貝恩斯提出,20 世紀60 年代的后現代舞蹈編舞家們拒絕了現代舞蹈的所有傳統舞蹈要素,他們自己制定了新的形式和美學標準,并在框架中行動起來[10]。即擺脫了在這個時代被認為是舞蹈范疇的固定觀念和固定形式,將舞蹈要素和多樣的藝術及生活要素結合起來進行了實驗。
編舞家們之所以能夠進行這種新的嘗試,是因為被稱為先鋒派代表舞蹈家的默斯·坎寧漢在自己的攝影棚邀請羅伯特·鄧恩主辦研討會而從中受到很大的影響。參加該研討會的舞蹈藝術家們努力將舞臺擴張的概念運用到實際演出中。西蒙·波蒂在畫廊演出See Saw(1961 年)和Roller&Huddle(1961年),史蒂夫·帕克斯頓乘坐巴士與觀眾前往新澤西森林演出Afternoon(1963 年)。不僅如此,在劇場外演出傾注很多努力的編舞家崔莎·布朗通過從大廈屋頂上安裝安全裝置慢慢走下大廈的作品Man Walking down the side of a building(1970 年),得到大眾的關注。將舞臺這個空間轉換成大廈這個場所的想法延續到在紐約惠特尼博物館內畫廊的墻壁上慢慢走動的。
在后現代舞蹈主張的“Everything is dance”,即“一切都是舞蹈”的口號中,對舞臺這一空間的觀點不是藝術的特殊存在,而是應該與平凡的日常生活在同一條線上存在。一般認為,后現代主義出現之前的現代舞蹈時代,在觀眾席和舞臺位置、演出者和觀眾關系明確區分的劇場進行演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后現代舞蹈時代,分離舞臺和觀眾之間關系的演出形式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在這種認識下,特定場所舞蹈被解釋為打破演出空間的特權意識框架,我們生活的任何空間都可以成為舞臺的概念,喚起多種藝術體現方式和空間體現形式。
場所特定舞蹈演出大部分是脫離定型化的舞臺形態的劇場演出。例如,街道、工作的建筑物、公共空間的公園、森林等多種場所。這是在藝術工作中反映主要概念的結果,即在日常空間和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空間中進行舞蹈表演的日常性和任何人都可以獲得觀看演出機會的平等性。“Site-Specific”的背景空間是無限的。不管是哪個空間、哪個地方都是作品產生的原動力。
5 結束語
舞蹈無論是在傳統的演出空間,還是在河流、圖書館、教堂、森林,都有超越直接背景的能力。就像20 世紀70 年代藝術家們試圖擺脫他們的“框架”一樣,舞蹈脫離了傳統演出空間,如果進入更加日常、更容易接近的社會,舞蹈就會快速發展,與更多的人有關。
在創作特定場所演出的特定場所舞蹈的過程中,編舞者在表演者及其動作中展現了編舞家對演出場所文化的解釋,同樣重要的是觀眾也會參與其中,每個空間都有其自身的空間背景和意義。通過編舞者的關心和解釋,展示該場所的文化知識,創造相互的空間,不僅將實體空間的多義性極大化,還創造了虛構的空間,體現了概念藝術的先鋒精神。舞蹈演員們的動作不是人們經常在劇場看到的華麗技巧的動作,而是根據各部分的環境和氛圍自然的動作。舞蹈演員的身體更關注他們所在空間的細節和他們身體相互作用的方式,他們正在尋找縫隙和隔間以適應“日常空間”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創作,且在空間中突破身體所屬位置的界限,與空間進行對話。
通過對場所特定舞蹈中出現的先鋒派精神的研究,可以摸索出融入空間的“靈魂”或舞蹈“靈魂”的新藝術選擇。通過創造新的材料、新的關系、新的意義,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