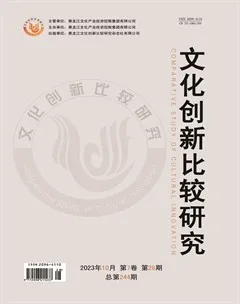價值生態視域下中國故事的傳播路徑
修雨薇
(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北京 100031)
2013 年9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1]。隨后的十年,總書記反復提到這一目標,并對實現目標的方式方法進行持續探索。在加強我國國際傳播工作發表的重要講話(2021 年)[2]及黨的二十大報告(2022 年)中,總書記更是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中國故事,即通過文學藝術形式凝聚中國人共同的經驗與情感,飽含對中華文化、現實情境,以及未來的想象與思考[3]。不可否認,文化可以跨越國界,直通心靈。而文藝創作可以更自然地向全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要在創作上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選用跨文化的主題,更要把控精準傳播的規律,才能將文藝作品轉化為公共文化產品,將中國形象傳達到位[4]。
1 理論辨析:從價值鏈到價值生態
如何使文藝創作的故事動人,傳播有效呢?根本原因在于文藝作品的價值屬性。我國對文藝作品價值的探討源于20 世紀90 年代。1992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文化、媒體行業被列入第三產業。自此,文化生產成為國民經濟建設的重要一環,在體制機制、信息技術的推動與促進下,不斷蓬勃發展。
價值是一切實踐的本體,是任意物質形態的一種積極屬性。通過生產活動,價值在新創與舊有之間“重獲生命”,其理論形態呈現點、線、面、體的層次變化(見表1)。1985 年,邁克爾·波特提出價值鏈理論。他認為,價值鏈是圍繞內部的生產經營活動展開的,打通了產品、組織等主體核心節點的各環節,包括一系列支持性的設施與活動,是價值創造活動的細分與延伸。1993 年,彼得·海因斯拓寬了價值鏈的研究范圍,供應商和受眾被納入價值鏈[5],服務成為價值鏈的核心,受眾需求既是價值生產的終點,更是鏈條內部與外部展開深層次連接與互動的橋梁。不可否認,外部價值鏈的拓展也帶來了一定問題。許多有條件的企業和組織開始尋找機會,“廣開門路,多種經營”,副業收入甚至超過了主業,價值鏈重心逐漸偏移。

表1 價值鏈、價值網、價值生態理論辨析
在此情境下,美世咨詢公司的亞德里安·斯萊沃斯基于1998 年在《利潤區》(Profit Zone)一書中提出價值網絡的概念。價值網適用于影響企業生存的競爭環境,它以既有的用戶和受眾為中心進行價值創造,使橫縱價值鏈中的各個環節、不同的主體按照整體價值最優的原則融合連通,形成一張巨大的價值網絡[6]。由于價值網是立足核心能力所建構的,一旦價值網形成,產品的特性、成本結構、價值觀念與生產流程等便被固化,將無法靈活應對新技術與新市場的沖擊。
隨后的2007 年,格雷格·赫恩等學者又提出了價值生態(Value Ecology)的概念,即價值創造生態(Value Creating Ecology),是價值鏈理論的變形[7]。價值生態的營造是一個由上至下的過程,在這一新的價值體系中,消費者成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價值從產品本身發散到產品所處的平臺場景之中,各主體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每一個產品、活動的決策不僅與核心環節密切相關,更需要各類參與主體的支持與服務(應用)場景的推動。盡管每個參與者都各具特色,但小到個體創作者、工作室,大到企業、集團等,都將不斷優化自身價值創造模式,以融入動態的價值體系中,通過交換資源來開展每一項活動,最終成為對內容或產品生產、傳遞價值的重要一環。
文藝創作在價值取向與社會責任方面的特殊性,使其更適用于價值生態理論。一方面,受泛在化的網絡與沉浸式的智能技術手段影響,文藝創作越來越重視網絡平臺的力量,不斷地將作品傳遞給“志同道合”的用戶。另一方面,在傳統文藝與網絡文藝融合的趨勢下,文藝作品的形式更為多變、類型更加多樣,致使生產模式復雜變幻,視聽產品占據主流。在文藝創作市場中沒有絕對的合作與競爭,相比于壟斷與多元化經營,創作者更偏愛“術業有專攻”的精益生產模式,通過與其他主體的交流與協作,共創作品價值。文藝作品在網絡平臺中快速流動、在價值生態中動態變化,它們共同構建起立體的中國故事,搭建內容價值交互的閉環,詳見圖1 所示。

圖1 文藝創作由鏈至生態的演化過程
2 傳播場景:以平臺為媒介傳遞內容價值
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對規范平臺經濟發展提出了新要求:“著眼長遠、兼顧當前,補齊短板、強化弱項,營造創新環境,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8]。當女性經濟、銀發經濟、單身經濟作為三股洪流涌入互聯網市場,越來越多的平臺無障礙地進入,分食平臺經濟的蛋糕。用戶是“多屬”“動態變化”的,許多文藝平臺都面臨用戶增長停滯、倒退的問題。出于擴大業務版圖,提高盈利能力的目的,文化藝術行業各平臺開始全方位、多角度地思考自身價值生態的建構路徑,將平臺的傳播能力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連接起來。
實際上,文化作品若想更好地走出去,需要國內的各類平臺企業共建陣營,共同拓展中國地域文化的傳播空間。奈飛作品在全球的話語權與傳播力源于其對多元文化的雜糅與調適[9]。同作為東方國家的韓國,通過東西方融合的敘事方式、民族與地緣文化的充分植入、頻繁的國際合作,構建了自己的傳播話語權。文藝平臺的媒介功能更應在價值生態的不斷演化中被充分挖掘,立足數智化技術的相關特性,逐漸成為全球公共傳播的重要手段。我國應該形成一個由文藝平臺導流、數智化技術支撐、政府主導的傳播環境。各類平臺是一個個公共服務化的“場”,借由互聯網更快地實現渠道化、去中間化。
2.1 網絡文學平臺
文學是一切藝術的母體,在文學傳播的場域里,網絡文學平臺的建構不可或缺。目前,國內主要的網絡文學平臺有起點中文網、縱橫中文網、晉江文學城、中文在線、紅袖添香、騰訊文學、愛奇藝文學等。實際上,不同網絡文學平臺的特質不同,輸出作品的題材、類型也有差異。例如,紅袖添香主要服務于女性受眾,主要發布情感類、女性題材的內容;中文在線的輸出作品以IP 改編動漫為主;晉江文學城的作品多數被改編為影視劇;愛奇藝文學、騰訊文學中的小說更是直接為影視化改編服務。盡管與傳統文學相比,網絡文學的創作門檻低、作者來源廣泛,但不乏優秀的作品借助平臺資源,經過實體傳播、在線翻譯傳播、海外本土化傳播、IP 傳播等手段,被海外用戶所關注、認可。根據2022 年6 月發布的《2021 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數據顯示,截至2021 年,中國網絡文學共向海外輸出網文作品超過1 萬部[10]。2022年9 月,《贅婿》《地球紀元》《第一序列》等16 本中國網絡文學作品,涉及科幻、歷史、現實和奇幻等多類題材,首次被收錄至大英圖書館的中文館藏書目中。
2.2 長視頻平臺
一直以來,以原創影視作品為核心的視頻平臺都是傳播領域的“常勝將軍”。國內主要的(長)視頻平臺有愛奇藝、優酷、騰訊、Bilibili 等。2017 年以來,愛奇藝(國際版)、騰訊視頻(WeTV)等影視平臺積極推動自制內容(網劇、網絡電影等)出海,例如:《無證之罪》《風起洛陽》《鬼吹燈之精絕古城》等。雖然觀影數據可觀,但傳播影響力與觸及度還不足。收集2018—2022 年愛奇藝的海外新聞(包括官網新聞稿、海外媒體報道新聞、企業博客)進行分析,共提取出線上、內容、視頻、娛樂、伙伴、服務、技術、用戶等多個關鍵詞。愛奇藝作為一家視頻平臺企業,立足科技創新建立智能化的制作管理系統與生產標準,嚴密把握原創作品的制作質量與生產進度; 擅長制作原創影視劇與綜藝選秀類節目,通過自制、買斷、分成等方式,將專業性、商業性、娛樂性、蘊含個性化表達的內容積累匯聚成金字塔,與眾多內容創作主體建立合作關系;還能依托智能技術(奇觀、HomeAI等)為用戶帶來沉浸式的平臺觀影體驗,并在馬來西亞Astro 平臺開設全球首個愛奇藝高清電視頻道。愛奇藝十分重視自身平臺及娛樂版圖的對外宣傳,形成一種擁抱價值生態的布局。
2.3 短視頻平臺
主打“快節奏”“碎片化”的短視頻內容也正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相比于傳統的圖文,短視頻更容易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以更直接的方式讓世界“看懂”中國。自Tik Tok(抖音國際版)于2017 年上線,許多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視聽產品獲得外國網友的關注。一方面,短視頻作為新路徑,使中國文化正在以一種更具真實性、多樣性的方式在異邦煥發耀眼的光彩。另一方面,盡管短視頻能夠在傳播形式上進行創新,但它很難在有效的時間里實現更深層次的文化輸出。隨后,長短視頻嘗試融合,視聽形態再次變換,情節密度、情緒起伏更強的微短劇攜多類型題材出現,帶來了《胡同兒》《二十九》等現象級作品。
平臺直接面向用戶,使用戶能夠根據需求自由地選擇想看的內容。愛奇藝的蘋果園、優酷的文娛生態便是最好的借鑒。上述兩者的成功,離不開智能技術與技術架構的支持。對各類平臺來講,其技術架構的搭建不僅需要依靠企業自身的技術團隊與技術投入,還與國家數智化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息息相關。同時,政府下屬、主管的各類媒體平臺,既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者,更是文藝作品標準的制定者,為推動影視作品走向海外樹立標桿的作用。有了互聯網平臺去打開、延展用戶渠道,相關部門更應在政策法規、內容標準、通用行業規范等方面做出努力,更好地用“有形”的手去塑造好傳播生態的架構和版圖。因此,若想提升中國故事的傳播影響力、使其內容價值受到國際認可,需要政府相關部門(中宣部、出版局、電影局、廣電總局等)及主流媒體平臺(學習強國等)主導發力,讓世界感受到的不僅是愛奇藝、優酷等個體影視平臺帶來的商業價值,更是中國文化、意識形態的獨特魅力與璀璨光輝。
3 升維路徑:以多重視聽語言建構立體故事
3.1 用世界語言展現人文關懷
在第九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上,萬瑪才旦曾談到,“電影創作要以人為本,越是人性的就越是世界的”。人性本身是一種復雜的狀態,人性的異化與復歸值得創作者不斷探索。而影視作品中對人性的表達可以打破文化的壁壘、時代的隔膜,引起全世界觀眾的共鳴。不少文藝作品,掙脫了既有“事件”的束縛,以深刻的方式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表達了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香魂女》從農村婦女地位的問題入手剖析人性的復雜變化,講述了一首兩代女性命運的悲歌。《撞死了一只羊》以“輪回”為議題,深入解讀人性的懺悔與救贖。《洛桑的家事》透過西藏的人文背景,講述三個家庭之間愛與寬容,矛盾與和解。《回西藏》以“孔繁森”為人物原型,通過更接地氣的方式講述漢藏團結的故事,將這段人與人之間從隔閡到溝通,從工作搭檔到生死之交,跨越文化、信仰的友情緩緩道來。撥開藝術形式的外殼,不難發現,富有感染力的個體故事,典型的社會現象與問題,各民族的文化歷史,更容易被海外觀眾理解與接受。
3.2 用樸實語言展現地方特色
將地方文化特色與現代文明的氣息相結合,更利于提升國民的文化自信,促進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從而展現更為立體、動態的中國。在政策機制的激勵與多方資源的相互作用下,許多充滿“市井煙火氣”“文學性”的現實題材網絡文學作品脫穎而出,具備被轉化為視聽作品的條件。例如,描繪上海30 年城市發展變遷的《上海凡人傳》,更有聚焦中軸線保護為主題的京味作品《京脊人家》等。“北京作家日”更是推出“優秀文學作品翻譯工程”,讓更多北京故事被世界看到。不僅是文學作品,如今的中國紀錄片與20 年前大不相同,內容一改歷史文化與自然風光,觸角全方位延伸,從美食、民俗到科技與經濟,甚至開始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納入其中。隨著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出品的中英雙語系列微紀錄片《京味》、上海廣播電視臺攜手Discovery 打造的 《行進中的中國》等作品成功“出海”,全世界對中國的了解不只站在“游客”視角,而是透過地域文化(京味文化、海派文化等)看到時代發展的車輪為這一古老的國家帶來天翻地覆的影響,領略動態變化中的中華大地上,首都北京、經濟中心上海等城市正在發生的故事。
3.3 用科幻題材展示技術進步與發展
近年來,有不少科幻題材的、蘊含對人工智能思考的網絡文學作品、視聽作品進入大眾視野,例如:網絡小說《第一序列》《地球紀元》《夜的命名術》,電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上海堡壘》,電視劇《三體》《光·淵》等。不可否認,在智能技術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是混沌的,甚至在有意無意地成為被“實驗的對象”。但人們也在積極地接納新技術、適應新的應用環境,并把這些新的學習、實踐感悟加入文藝創作中,“數字生命”“人工智能的倫理”等問題在作品中被持續挖掘。與其他科幻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相比,《三體》“捍衛”原著,盡可能地保留了原著小說的語言與情節,將其轉化為視頻語言。相比于第一部,《流浪地球2》對于科學技術倫理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不可否認,科幻題材與中國情境的結合,開辟了新的“想象空間”,成為中國文藝作品與世界對話的重要媒介。
3.4 用主題創作記錄時代與“新人物”
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文化歷史的滲透更利于觀眾對“新人物”產生情感認同。對于創作者來說,“新人物” 開創性的業績與充滿煙火氣的生活故事,成為塑造人物形象、建構人物成長路徑的重要元素,使觀眾可以透過作品中的人物境遇全方面了解事件的影響。2019 年3 月,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的文學藝術創作提出了要求,要創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藝術作品。隨后,以新時代為題材的電視劇如雨后春筍般涌出,如有聚焦于英雄與時代的作品《功勛》《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毛澤東》,有小人物與時代的作品《外灘鐘聲》《裝臺》《我在他鄉挺好的》,有聚焦于小家庭與時代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都是一家人》《人世間》,有聚焦于鄉村與時代的作品《山海情》《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焦裕祿》,有聚焦于歷史與時代的作品《覺醒年代》《尋路》《理想照耀中國》,有聚焦于正義與時代的作品《破冰行動》《獵狐》等[11]。文藝創作的正確方向就是要堅守人民至上的立場,通過描繪“新人物”,凝聚“榜樣”的力量。“榜樣”是建構時代和大眾認知的重要話語符碼[12]。而多種形態的視聽作品不僅成為人民群眾了解、學習人物精神與品格的有效工具,更是展示中國時代風貌與人民形象的絕佳手段。
4 結束語
在互聯網與智能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移動設備普遍化、功能化,不僅“入侵”人們工作與生活中的碎片化時間,還兼容了各類制作型應用產品,使人們可以借助工具快速完成網絡視聽作品的創作。文藝作品的價值創造不再是單一的、獨立的、封閉的,而是形成一個價值生態環境,各種文藝形態、各個文藝創作主體在平臺中不斷地角逐,因“志同道合”而共贏。文藝創作不僅與動態變化的用戶需求密切關聯,還需要借助平臺的力量落實標準、開拓渠道,生產出更多大眾喜聞樂見的內容。創作主體們也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合力,在完美的形式以外,將個性化的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悟、對科技發展的思考、對時代與榜樣人物的敬畏之情融于文藝作品的價值創造之中,借助多重視聽語言共同打造立體的中國故事,留住真實的中國記憶,全面展現中國的形象,將文化與價值的多元性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