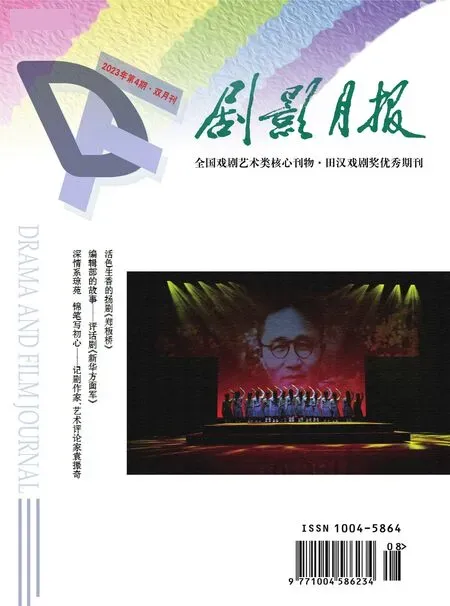閩劇《紅裙記》青衣動作的表演分析
■黃怡萱
閩劇在地方俗稱為福州戲,是福建省主要戲曲劇種之一,流行于福州市及閩中、閩東等福州方言地區。閩劇中的女性角色根據不同年齡、性格、身份進行行當細分,青衣通常飾演那些命運多舛、凄風苦雨卻又堅忍的女性。悲情主義是絕大多數青衣的情感基調,注重以“生活化”、細致豐富的動作表演詮釋人物的內心活動。青衣在戲曲舞臺上,往往是最能揭露生活的深刻角色,留給觀眾的感悟也最為突出。閩劇《紅裙記》中的柳氏便是這樣一個封建背景下命運悲慘的人物,要充分詮釋這一角色,除了要深入生活、理解人物,還要熟練掌握一系列的程式規范動作。
一、青衣動作的程式化
戲曲舞蹈表演體系的程式化發展源于我國的國劇運動,將戲曲舞蹈表演的程式化引申為對戲曲藝術特征的概括。強調戲曲舞蹈整體、寫意、形象的特點展示,是戲曲舞蹈表演特征的重要表現。“程式化”是指藝術形式的整體規范,簡單來說是指藝術都有一套固定的標準,是具有規范化的表演模式。戲曲舞蹈表演的程式化區別于現實主義的常態化表演形式,強調的是藝術積累與生活化表演結合的形式,并且通過舞蹈表演體現出戲曲的神韻。旦行的特色表演,在于手上。臺上一伸手,就知道其有沒有功夫,主要以蘭花指來進行表達,這也是閩劇旦行的基本手勢之一。蘭花指的指法是用單指,即中指與大拇指捏在一起,食指向上指出,無名指與小指微曲放松;掌形也要有指花,即大拇指向內貼近中指骨節,中指稍微低于其他三指,指尖均向上翹,為蘭花掌。這與中國古典舞中的基本手型“蘭花手”頗有相似,但蘭花指更注重手指延伸與氣息的交織,其指法常常用于向人行禮作揖、捏手絹、梳理妝發、女紅等,體現出女子的賢惠、莊重。在進行戲曲表演時,為保證人物的戲劇形態,需要通過具有豐富表現力的細節動作來進行有效的表達。因為家庭、社會處境的影響,青衣的舉止較端莊,且出手要穩。在《紅裙記》中,青衣柳氏家境貧寒,丈夫嗜賭,是一個依靠做針線貼補家用的普通家庭婦女,因此干起活來手腳麻利、動作敏捷。所以在搓線這類動作時手指輕快熟練,不拖泥帶水,將舊時代勞動婦女應有的姿態完美地詮釋出來。
閩劇中青衣的基本步伐有臺步、碎步、圓場步、促步、云步等。臺步是青衣行當最基礎且常用的步伐,其形態是右手蘭花掌貼于肚前,左手蘭花掌扶在左胯前,腰部收緊直立,其步法是一只腳勾起向前邁出,先用腳跟落地,然后腳心、腳尖依次落地,不等前一腳掌落地,另一只腳就跟著起步,與前腳相同的步法,走動時雙腿并攏,利用膝蓋向前推的力量交替,步子慢而又穩,能夠清晰地反映出女性的內斂和小心翼翼。圓場步是建立在臺步的基礎上的細化,上身保持平穩放松,邁步的距離縮小,起步腳落在主力腿的腳心處(也就是半腳),小腿發力,步步緊跟,給人一種身輕如燕的感覺,對觀眾展現一種歡快、自然的情緒。當然不同年齡、不同性格,步法也有所不同。
戲曲舞蹈表演的程式絕非生活動作的簡單映射,除了對自然狀態的觀察與模仿,還要對抽象化的生活形態進行提煉,并在生活動作基礎上加工轉化成有意義的單一動作,再通過手、眼、步、身的組合構成一套規范的程式動作,它升華了生活的自然形態,使生活動作得到了更集中、更鮮明、更強烈的反應。比如“女紅”。俯首,后背微微放松,微垂著頭,一手拿針線,一手捏著布料。手腕帶著轉動手掌將針向下穿,并快速將手從布料下面取出針線并拉長,再以手腕帶動手指從底部向上穿,如此循環。在《紅裙記》中,柳氏在家做針線活,運用的就是此程式動作。比如“望門”。右腳向左前方邁,左腳于后墊步,重心在前腳,身體稍稍向前傾。雙手蘭花指手心向前置于腹前,左手比右手更置于前,脖子伸長目光向右前望去。《紅裙記》中柳氏在王成龍葬身江流后因滿懷思念,期盼丈夫死而復生歸來,常常在家門口望著、等待著,這時運用的就是該程式動作。比如“拂去灰塵”。四指微屈,大拇指向里靠攏,身體微側,頭畏著,手腕發力用手背輕拍掃去灰塵。在《紅裙記》中,柳氏在裁縫完衣服后要掃去衣物上的臟塵,運用的就是這組動作。比如“提襟關門”。一手先捏裙提起,另一只手做蘭花掌向上位于山膀處,同時右腳向前一步,雙手掌心向前,并向里漸漸靠攏并往前推,右手蘭花掌手心朝旁向里推將門鎖拴上。《紅裙記》中王成龍出門,柳氏將家門關緊運用的就是這一程式動作。由以上舉例可以看出,青衣的程式動作較為簡單,動作幅度變化較小。戲曲表演不僅是程式化的,在表演過程中更需要非常細膩的表現,青衣表演也不例外,在具體人物刻畫中,需要以準確的程式動作來詮釋人物情感。
二、程式動作的性格化
戲曲舞蹈的程式動作是經生活所提煉的產物,在日常動作的基礎上進行細化與升華,產生了程式動作的舞蹈化與性格化。而戲曲具有很強烈的抒情性,戲曲情節一般一波三折,必然要經過大喜大悲的情感變化,如何體現人物內心情感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戲曲舞蹈通過動作夸張化的方式,將人物內心情感更生動地表現。很多戲曲舞蹈動作,既是情節的展開,又是情感的表達。我國文化講究的是含蓄美,無法用語言表達情感時,肢體動作和表情就被夸張。舞蹈動作可以帶動戲曲情節的發展,也能表達人物內心情感,豐富人物形象,就閩劇《紅裙記》中的某些片段舉例:比如“女紅”在劇中出現多次,它作為人物的形象塑造環節,每一次呈現都在提醒觀眾,柳氏是一位賢惠的平凡婦女。開篇以此動作出場,直觀地展現出柳氏是一位家境清寒的婦女,其針線手勢以及手臂移動的幅度都較小,動作緩慢,滿眼盡是滄桑,表現出對丈夫一事無成、家庭溫飽問題無法解決的無奈與無助。而第二次出現,是王成龍去世后,柳氏為還賭債通宵達旦地趕補衣物,眼眶發紅卻又強撐睜大,目光緊追著針線移動,整體動作敏捷麻利,絲毫不敢松懈。比如“望門”,在王成龍溺江后,柳氏悲痛欲絕,尋尸未果后她站在家門口,滿眼淚水向遠望去,對自己斥罵丈夫的行為后悔不已。這一“望門”,顫抖的指尖一點一點地向前伸去,身體隨著手的推移也跟著向前,她思念丈夫,盼望著丈夫能夠死而復生歸家團圓。比如“拂去灰塵”,柳氏為還亡夫賭債靠針線活掙錢,完成后柳氏將線頭處理好并插入發髻中,起身,把衣服展開抖平,再用手輕輕地拍打以拂去衣物上的臟塵,確認沒有任何問題后將其折疊好放回籃中,這一自然的“拂去灰塵”動作體現出柳氏心思細膩、做事講究的特質。比如“提襟關門”這一動作在王成龍上街當米、柳氏目送后出現,低頭提起衣裙,右手順勢向上于山膀,向后退兩步后雙手拉開將門關上,并拴好門鎖,動作輕快靈敏,表現出對丈夫改邪歸正的欣慰之情。此動作除了單純表示關門以外,在柳氏與許相公(王成龍)未能相認成功時,柳氏心里安慰自己丈夫早已離去,眼前人并非己夫,神情逐漸黯然,身體無力地往后退,轉身提起裙擺回到屋內,雙手關門,動作緩慢,滿眼早已被淚水浸滿,門縫外的許相公(王成龍)身影逐漸縮小直到雙門關閉,柳氏垂頭嘆氣,沉重地將門鎖扣上。她對王成龍的眷戀,在門鎖后的那一刻便就此消散。
以上四個青衣動作規范程序,不僅是一般性的動作表演,還因具體情境中情感的不同而有動作力度的不同,同樣是“關門”,欣喜、憤恨、焦急、沉痛情緒下的動作形態在力度的表現上都不同。觀眾對演員表演的審美,不僅在于對其虛擬動作的認可,還審視著演員情緒表演是否到位,與他們心中的人物情感表達是否一致,只有一致才能產生共鳴,藝術效果才能實現。在閩劇中,腳底下的形態與動勢能夠明顯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與心理狀態。然而不同的步法它所表達的情緒也不同,步法的處理方式不僅關系到演員表演身段的體態美與動作美的呈現,更重要的是人物內在感情的表現。在《紅裙記》第一場“借裙”中,柳氏在家縫補衣服,丈夫和搖籃中的孩子正在熟睡,突然嬌兒驚醒哭啼。柳氏迅速放下手中的針布將其抱起,過程中腳底下臺步速度快而輕穩,清晰地映射出柳氏想要安撫孩子的焦急情緒。將孩子抱起之后安撫,待熟睡后將其放回搖籃中,又走向床邊欲叫醒丈夫卻又放棄,重回大廳縫補衣服,整個過程中柳氏運用的還是青衣臺步,與前一次相比,腳步明顯變得更謹慎緩慢,中間帶有停頓與嘆氣。這一小段的動作將柳氏對丈夫的氣憤與無奈鮮明地表露出來。柳氏在與王成龍爭吵衣食問題時,柳氏弟弟前來看望,柳氏一聽到其弟的呼喊,連忙開門上前迎接,腳下臺步大而歡快,在弟弟告知柳氏三日后參加母親的壽宴并送來一條綾羅紅裙作為宴裙,她雙手捧著紅裙興奮地繞著屋子并尋找光亮處欣賞裙子,這里所采取的步法是圓場,腳底細、碎、快。破舊的裙擺被柳氏腳下輕快而幅小的節奏帶起了一層又一層細小的波浪,她內心得到紅裙的欣喜由此流溢出來,還有家人對她的掛念使她獲得滿足的安全感。所以說臺步的表現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是隨著人物的情緒和心理的變化而變化的。
對人物情緒進行表達的手段不單單步法,手的手勢與動態也可以鮮明地反射出人物當時所處的情境、所表露的情緒與心理變化。在《紅裙記》第一場“借裙”中,王成龍欲向柳氏借紅裙當賭注,謊稱上街買米,柳氏雙手搭袖捧著紅裙遞給王成龍時中途又收回來,這樣一個動作她重復了兩遍,心里總是千萬個不舍得,既擔心紅裙一去不復返,又擔心全家的溫飽問題,“紅裙”是柳氏心里的最后重要支撐,這樣一個一遞一收的簡單動作,將她對紅裙猶豫不決的矛盾心理表現出來。另外,在《紅裙記》第五場“餞別”中,許相公(王成龍)應王達官邀請去做客,在等待王達官出門買酒時,因害怕與柳氏相認便掩面假裝睡著。柳氏出門撞見正在休息的許相公(王成龍)并發覺天氣寒冷想要叫醒他,柳氏與其相隔1米之遠,一只手起水袖掩面,另一只手以“蘭花掌”將袖簾輕輕拉開一角,小聲呼喚試圖叫醒他,看得出柳氏小心翼翼不敢與男子相近的心理,同時也側面反映出舊社會女子只能守著死去的丈夫一輩子、以示自己的節操的普遍現象。
三、林夢萍的柳氏表演
在戲曲舞臺上,演員通過動作語言來體現人物,人物通過動作語言來體現靈魂,除了需要演員對人物性格熟練掌握以外,還要在程式動作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劇本的人物性格進行二度創造,使戲劇表演更具感染力。閩劇《紅裙記》雖然是傳統故事改編,但編劇王仁杰對其民間化、精致化的創造是非常明顯的,在他的筆下,人物遵循的是“溫柔敦厚”的詩禮傳統,而角色飾演者閩劇青衣科主教林夢萍,將柳氏堅強、隱忍、善良的性格特性鮮明地表露出來,她在表演中運用了簡單細膩的青衣程式化動作塑造出富有真實感的柳氏,并將人物內心世界進行分層展示。作為閩劇青衣科主教,林夢萍所飾演的柳氏以細微幅小的肢體動作展示弱女子的姿態,在表演上注重動靜、急緩、悲喜等反差巨大的情緒,產生獨特而具有感染力的表現效果,把閩劇青衣的凄美溫婉、完整純粹地表現出來,雖然每一處動作的處理都不相同,但又各具韻味。
總之,戲曲的程式化表演,不只是對于行當程式動作的掌握,需要在程式動作訓練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劇本的角色性格進行人物性格化的動作改變,需要演員進行自我表演的二度創造,賦予程式化以靈魂,由此真正地詮釋出有個性、有生命的角色形象。程式化動作是生活動作經過美化而形成的,結合人物個性進一步發展成舞蹈化動作,閩劇青衣作為一門塑造女性人物的藝術語言,其蘊含的女子個性化表現手法在當代民族舞蹈與古典舞的建設中有著重要的借鑒與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