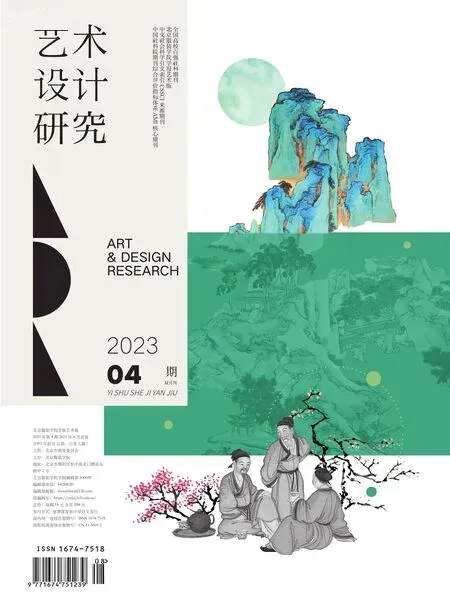20世紀初敦煌藝術在英國的接受與闡釋
——以《伯靈頓雜志》為中心
白薇臻
20世紀初,西方掀起了對包括中國新疆、西藏、甘肅在內的中亞地域的探險熱潮,而西方考古探險隊對敦煌藝術的發(fā)掘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數量浩繁、意蘊豐富的敦煌藝術瑰寶一經面世就震驚了世界。具體到英國,1909年,當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將從中國敦煌發(fā)掘的大量文書和藝術珍品運回英國后,英國對中國敦煌藝術的整理、鑒賞和研究也隨即展開。其中,著名漢學家R.彼得魯奇、勞倫斯·賓雍、阿瑟·韋利,以及現代主義美學家羅杰·弗萊等學者紛紛撰文介紹斯坦因、伯希和的中國西域探險發(fā)現,這些文章從1910年起集中刊發(fā)在《伯靈頓雜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上,共同構成了英國敦煌藝術研究的早期積淀,為英國知識階層和普通民眾深入了解以佛教藝術為特征的中國敦煌藝術提供了便捷通道。因此,本文將以知識精英刊發(fā)于《伯靈頓雜志》上評介敦煌藝術的文章為研究對象,勾勒出20世紀初英國學者接受與闡釋敦煌藝術的歷史圖景。
一、彼得魯奇對中國佛教藝術的介紹
目前可以查到《伯靈頓雜志》上介紹有關斯坦因敦煌發(fā)現的最早文章,可追溯至1910年法國著名漢學家R·彼得魯奇撰寫的《遠東佛教藝術與新疆文書》(Buddhist Art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彼得魯奇是法國漢學泰斗沙畹(émman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弟子,長期致力于中國繪畫藝術的研究。1914年底,他受聘為斯坦因工作,幫忙整理和研究后者從敦煌帶回來的佛教繪畫品,①這也為他深入探討敦煌藝術創(chuàng)造了條件。
在《遠東佛教藝術與新疆文書》一文中,彼得魯奇簡要介紹并評說了斯坦因敦煌之行的價值和其所獲藏品的特征。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敦煌藝術之于西方理解佛教藝術的重要價值,在文章伊始便說道:“最近在中國新疆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將在很多方面改變我們之前關于遠東的佛教和佛教藝術的既有觀念。”②隨后,彼得魯奇認為過去對中國藝術的忽視,原因在于我們對文獻來源知之甚少。而最新發(fā)現的“中國文本以一種精確的方式引導我們,去關注一種復雜的美學,它為我們提供了以悠久文化為前提的規(guī)范”。③這即是說,敦煌藝術品的傳入為西方探究中國古典藝術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樣本,從而培養(yǎng)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敦煌藝術的基本感知,同時也匡正了長久以來對佛教藝術及其演進的誤解。
彼得魯奇隨后以中國重要的佛教塑像和石窟藝術為例,分析了犍陀羅的希臘式佛教藝術在遭逢中國藝術之后,展現出哪些與眾不同的特征。其演進分為不同階段,首先是從中國新疆的吐魯番一直到敦煌,沿途發(fā)掘的佛教彩色塑像仍保留著犍陀羅的風格;其次便是以敦煌、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為代表的佛教雕塑,既能看出印度藝術對其的影響,而中國等東亞藝術的影響也深刻體現其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塑像類型。然而,他也指出,云岡石窟仍不乏犍陀羅風格的古跡,例如云岡大佛、雙腿盤坐的菩薩。但這種純粹的犍陀羅式的打坐姿勢在唐朝時期的作品中就已難覓蹤影。此外,云岡石窟的一些精舍(Vihāras),其壁龕的裝飾物通常也用于犍陀羅藝術,但這種風格顯然正趨于消亡。④
最后,彼得魯奇將中日佛教藝術相對比,認為當佛教與中國藝術相逢,就如敦煌藝術表現的那樣,根深蒂固的中國藝術傳統顯得如此強大,足以將其藝術風格施加于其他藝術之上。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認識到佛教藝術在穿越亞洲的漫長旅途中都發(fā)生了哪些變化。當它到達高麗(Corea),然后到達日本時,不僅僅追隨了印度或希臘化的傾向,也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這表明中國除了對印度佛教產生了卓著的智識性價值以外,如今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對佛教藝術的貢獻。⑤
1911年,彼得魯奇又在《伯靈頓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伯希和在中國新疆的探險》(The Pelliot Mission to Chinese Turkestan)的文章。依據敦煌繪畫對中國世俗藝術和犍陀羅藝術元素的不同運用,他將這些繪畫品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繪畫與犍陀羅的希臘式佛教藝術存在明顯親緣關系。彼得魯奇首先以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在挖掘敦煌的一座寺廟廢墟時發(fā)現的一系列泥塑像和淺浮雕為例指出,“這些塑像據推測出自7世紀或8世紀。最受矚目的一點是,它們與犍陀羅的希臘式佛教藝術存在親緣關系。希臘化的程式仍然完全控制它們,人物自身的類型仍保留著印度—希臘王國(Indo-Greek)的風格;另一方面,它們堅守一種完全自由的風格,以此保持著生命的所有脈動”。⑥
第二類繪畫則受到中國世俗藝術的影響。彼得魯奇指出,從敦煌帶回的繪畫品中充滿鮮明的中國特征,其例證就在斯坦因和伯希和帶回的幡幢上,那些佛本生故事的場景以一種僅僅會在純粹的中國作品中使用的方式來表現。同時,“在中國世俗藝術的影響下,繪畫中產生了和神靈一樣多的侍從、大臣和皇室成員的形象。從中沒有發(fā)現持續(xù)出現的印度或印度—希臘王國的藝術程式,而這足以證明,當佛教藝術傳入中國時,它遭逢了一種足以將其自身施加于他者之上的世俗藝術”。⑦彼得魯奇隨后又以伯希和帶回的一個殘片為例,繼續(xù)論析敦煌佛教藝術中的中國世俗藝術元素。他寫道,這一殘片是個迷人的例證,它描畫了一種天使或“童子(putti)”的形象(某些菩薩的慣常侍從)。⑧但從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中國人的長相,風格也是中國式的。
第三類繪畫是兼具印度影響和中國風格的混雜物。彼得魯奇以細膩的筆觸介紹了一幅敦煌繪畫品,它描畫了一個憑借飄逸的絲帶而凌空翱翔的飛天。盡管這種優(yōu)雅的處理具有印度佛教藝術的鮮明特征,但這個人物是按照中國的方式處理的:其上身赤裸,皮膚白皙,畫得既柔美又準確。同時,飛天的頭也沒有按照印度風格戴著冠或梳著發(fā)髻,肩膀垂落的頭發(fā)也遵循著中國風格。由此,靈巧的中國風格與神秘的印度風格緊密融合在一起。
最后,彼得魯奇指出,在中國新疆的探險發(fā)掘之前,除了書面文獻之外,西方幾乎沒有任何相關實證。而伯希和與斯坦因帶回的這些文書、繪畫、版畫、布料、雕塑等,從“佛教藝術的構成和歷史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文獻”。⑨從而一方面使西方學者肯定了中國藝術的力量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則使印度藝術和中國藝術的影響交會浮出水面。透過敦煌藝術,“我們將看到古老的中國哲學與其強健的藝術,是如何與精致優(yōu)雅而又飽含情感和感官享受的印度藝術交織在一起的”。⑩
盡管彼得魯奇1917年便因病去世,對佛教藝術的探究也就此永久擱置,其對中國佛教藝術的早期關注及研究也只能由這兩篇論文中得以窺見。但他在這兩篇論文中的研究思路和觀點為其后西方學者的中國佛教藝術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指導。在彼得魯奇去世三年后,其有關中國繪畫的重要論著《中國畫家:一項批判性研究》(Chinese Painters:A Critical Study,1920)的英譯本面世。在這本書中,彼得魯奇分兩部分介紹了中國繪畫的創(chuàng)作技法、基本特征和歷史演變。其中,第一部分專論繪畫技巧,包括:畫家的工具、形式表現、主題分類、靈感;第二部分則以時間順序介紹了中國繪畫從源起到清代繪畫的發(fā)展。第二部分的二、三章《佛教介入之前》(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Buddhism)和《佛教的介入》(The Intervention of Buddhism),以斯坦因、伯希和的西域考古探險所獲品為例,細致闡述了中國繪畫在佛教介入前后的突出特征,是彼得魯奇中國佛教藝術研究的集中呈現。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附有勞倫斯·賓雍于1919年10月為其撰寫的傳記介紹。賓雍在其中充滿深情地回顧了彼得魯奇年僅45歲的一生,認為他的去世使得“世界失去了一位最能干、最忠誠的遠東藝術的研究者和闡釋者”。?而“在他去世前的幾年里,他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對東方藝術、中國語言和佛教畫像的研究上”。?由此可見彼得魯奇在西方研究中國佛教藝術的歷程中所起到的先驅作用。
二、賓雍與敦煌繪畫的初遇
在彼得魯奇之后,英國著名漢學家勞倫斯·賓雍的相關研究也值得關注。1910年6月,賓雍在大英博物館白翼館舉辦了中日繪畫展,其中的展品就有《女史箴圖》以及斯坦因帶回的25件幢幡。同年8月,賓雍便在《伯靈頓雜志》上發(fā)表了文章《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繪畫(一)》(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詳細介紹了展覽中的一些重要展品。
賓雍在這篇文章中高度贊揚了中國藝術,認為唐朝繪畫就如唐詩一樣偉大,其繪畫色彩清新、明亮,線條穩(wěn)定、流暢。他寫道:“唐朝(7至10世紀)或許是中國藝術史上最偉大的時期,就如同其詩歌一般。但關于那個輝煌的時代,僅殘存寥寥無幾、令人疑慮的碎片!斯坦因博士在西域的敦煌所發(fā)掘的繪畫,其中的幾幅正在大英博物館展出,雖然并不是絕佳的藝術品,但是無論如何它們描摹出了這個時期佛教繪畫的基本特征,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它們的藝術價值各不相同,其中的一些繪畫鮮明地反映出了原稿在設計上的巨大活力和絢爛色彩。少數一些繪畫也標明了日期。但目前討論這些繪畫還為時尚早,因為毫無疑問,斯坦因博士將在其即將面世的書中予以充分論述。我只想在此指出這些絹畫的存在,幾乎所有的畫都未曾裝裱,并且可被追溯至一千年以前抑或更久,但其色彩就像昨天才畫的一樣,那么清新、明亮。這些畫作的存在必定會讓那些傾向于懷疑幸存于世的中國藝術品是真正偉大的古物的人停止疑慮。”?
其后,賓雍依次介紹了吳道子、韓幹、趙孟頫、李龍眠等中國畫家的繪畫作品和風格,指出除了出色的創(chuàng)作技法之外,這些繪畫亦體現了藝術家的個人特征,畫家“巧妙地安排空間中的形式和線條的質感,可以使最簡單的材料成為最令人著迷的設計;但是單憑這些技巧并不能表達我們感受到的一切,在這樣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藝術家自身是什么樣的人”。?
1910年11月,賓雍又在《伯靈頓雜志》上發(fā)表了《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繪畫(二)》(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I),按照時間順序承續(xù)上一篇文章,繼續(xù)介紹了元朝、明朝及其之后的大英博物館中國繪畫藏品。值得關注的是,賓雍再次呼吁西方應認真對待遠東藝術。他認為通過這些西傳的中國古典藝術品,“表面上的陌生感已經消失了,我們至少了解了一些東方的觀點,也知道了激勵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理想,我們也并不需要他們的目標和我們的保持一致……只有那些對西方藝術的評判是純理論的或善變的人,在面對這個關于美的新世界中真正令人欽佩的事物時,才會感到茫然無措。”?賓雍無疑在此強調西方應拋卻歧視,對中國古典藝術的觀念和理想有所了解。
1921年,斯坦因出版了《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畫》(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賓雍撰文《敦煌繪畫及它們在佛教藝術中的地位》(The Tun-Huang Paintings and their Place in Buddhist Art)作為此書的導論:一方面簡要回顧了斯坦因殊為不易的西域之行,肯定其帶回的敦煌文物的寶貴價值;另一方面也集中闡釋了他對敦煌繪畫及其與佛教藝術之關聯的認知。在論及斯坦因的敦煌探險之旅時,賓雍指出其掠回的成果使得“佛教藝術的發(fā)展史和東進史變得越來越明確”。?隨后,賓雍梳理了佛教藝術從印度經由犍陀羅、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歷程,認為“南疆藝術雜糅了眾多元素,這反映了其文明的融合性”,?其中就包括了印度藝術、希臘藝術、波斯藝術等元素。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指出中國繪畫是一種獨立而成熟的藝術傳統,不管從別的藝術中借鑒了多少元素,它都能將這些元素融入自身風格之中”,例如中國藝術中常見的流暢穩(wěn)定的線條和精妙的留白。?
1925年6月,斯坦因和賓雍在《伯靈頓雜志》上共同撰文《斯坦因爵士發(fā)掘的唐代繪畫遺跡》(Remains of a Tang Painting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文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斯坦因回顧發(fā)現這一絹畫的歷程;第二部分由賓雍詳細介紹斯坦因帶回的唐代絹畫殘片。
賓雍一開始便給予斯坦因帶回的絹畫殘片以極高評價,認為早期的中國繪畫,特別是非佛教且可以明確年代的繪畫是極為罕見的,這使得斯坦因對這些唐代殘片的發(fā)掘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總體而言,這幅絹畫的布局很清楚。盡管僅留有部分殘片,使人不能窺見整幅絹畫的本來面貌,但賓雍隨后利用不同部分的圖案和色彩,拼湊出了繪畫的基本布局和原有的裝裱。從布局上來看,這是一幅描摹唐代貴婦及其隨從,以及一些舞者和樂師的畫。隨后,賓雍將這一絹畫與日本繪畫相對比,認為殘片中的女性和隨從讓人想到了日本圣德太子及其兩個兒子的肖像。但它與另外一幅日本早期的繪畫更為相似。這就是保存在奈良正倉院的一組六塊嵌板組成的屏風畫,每個嵌板上都畫著一個美麗的女人,或站或坐在一棵樹下。?然而,二者的相似不僅體現在畫面布局上,女性的相似類型也體現出它們對美有著相同的理解。具體而言,唐朝的美以飽滿、圓潤的臉頰,飽滿、紅潤的櫻桃小嘴,豐腴的體型為主要特征,且遵循相同的描繪慣例,例如用兩三條曲線表現喉嚨等,也同樣在日本繪畫中有所體現。此外,她們濃密的卷發(fā)也驚人地相似,而且前額上都有一個碩大的結,甚至于繪制前額和臉頰上的斑點的方式也是相同的。因此,賓雍得出結論:“毫無疑問,這幅日本畫是以唐朝繪畫為原型的,甚至可能比以往想象得更為接近。在遙遠的中國的另一邊發(fā)現這一確鑿的證據是多么有趣啊!”?
作為東亞藝術的研究者,賓雍顯然注意到了中日藝術的因緣關系,并從斯坦因帶回的這一殘片中找到日本藝術從中國藝術中汲取養(yǎng)分的確切證據,從而彌補上了佛教藝術東進鏈條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三、弗萊和韋利對敦煌藝術的闡釋
與彼得魯奇和賓雍的敦煌藝術研究注重文獻價值和史料考據不同,英國著名的形式主義美學家羅杰·弗萊于1912年6月在《伯靈頓雜志》上撰文,以感性的語言評價了斯坦因同年出版的《契丹沙漠的廢墟—在中亞和中國西陲進行考察的個人記述》(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1912)。
弗萊在這篇文章中,首先贊揚斯坦因道:“作為一名發(fā)現者,斯坦因配得上他的所有好運,即便這仍是多么驚人的好運啊!”?隨后,弗萊接著肯定了斯坦因所獲藏品的價值,他寫道:“我們可以確定這座長久以來隱匿的洞窟中的所有物品……它們?yōu)樘骄刻瞥瘋ゴ蟮淖诮趟囆g,以及中國和薩珊藝術之間的關聯帶來了新的曙光。這種早期藝術的許多問題還有待解決,但是每一項新的發(fā)現都意在表明,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初幾個世紀,東西方間的相互聯系是多么的深遠。同時還使我們更加認識到,這些影響的潛流可能會對歐洲藝術產生多大的影響。”?由此看出,弗萊認為斯坦因的西域之行及其所獲文物的價值有兩點:一是確證了中國唐代存在偉大的佛教藝術;二是揭示了中西方藝術在早期相互影響的事實。
盡管這是一篇短小的書評,但弗萊對中國佛教藝術的興趣延續(xù)至其之后的中國藝術研究,因此英國學者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曾說,雖然弗萊晚年迷戀青銅器,但“佛教影響下的中國藝術是弗萊的舊情人”。?同時,弗萊也自覺運用佛教藝術來闡釋和豐富自己的形式主義美學。例如他曾將唐代的佛像和意大利藝術家喬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336)的雕塑并置對比,從而認為相較于西方雕塑中突然轉折、生硬的線條,唐代佛像圓潤、流暢的線條使輪廓構成和諧、統一的卵形結構,而這正是西方現代藝術所力圖追求和獲得的程式。?
除弗萊之外,與其同屬布魯姆斯伯里團體(Bloomsbury Group)的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也展現出對敦煌藝術的濃厚興趣。1918~1919年,數位英國學者在《伯靈頓雜志》發(fā)表了系列論文,向公眾介紹包括大英博物館在內的英國博物館近期所獲的重要收藏品概況,其中一篇由韋利執(zhí)筆。韋利撰寫的短文即1919年2月發(fā)表在《伯靈頓雜志》上的《公共收藏最新收購品之七—敦煌白描畫—大英博物館印本部斯坦因藏品》(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 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 Print Room, Stein Collection),簡短介紹了一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館印本部的斯坦因藏品。這是一張來自敦煌的白描畫,其創(chuàng)作年代可追溯至公元966年。畫作由黑色碳精在發(fā)黃的紙上勾勒而成,全畫僅有幾處紅色和綠色的點綴,例如出現在駱駝的鞍韉之上和馬的鞍韉之后。畫作背面還有文獻,記載了敦煌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元忠及其夫人潯陽翟氏修繕寺院的事情。盡管文字和繪畫哪一個創(chuàng)作得更早還未有定論,但是韋利推斷:由于畫作上有潦草的練筆,其內容來自于背面的文獻,因此繪畫不應早于文獻,或許二者為同期創(chuàng)作。?
這篇文章雖短,但是韋利追溯了這幅敦煌白描畫所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并以寥寥數筆勾勒出畫作的基本特征和創(chuàng)作手法:一方面展現出重視文獻、注重考據的學術傾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韋利對中國歷史文化、繪畫藝術的了解。這篇文章或是韋利有關敦煌藝術的最早研究,其后他便一直關注著包括敦煌藝術在內的中國佛教藝術,并在數部論著中以專章探討敦煌藝術。
1923年,韋利出版《中國繪畫研究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該著是英國早期研究中國繪畫的重要論著。書中第十章標題為《敦煌繪畫》(The Tun-huang Paintings),詳細探討了中國本土藝術風格對敦煌藝術的影響,并認為敦煌藝術之所以展現出獨特的藝術特征,原因之一是佛教在敦煌與在中國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存在差異。1931年,韋利出版《斯坦因所獲敦煌繪畫品目錄》(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一書,他不僅簡短介紹了畫家身份、繪畫技法、斷代線索、創(chuàng)作背景等內容,還輯錄并英譯了絹畫題記,?概述了佛教東傳的歷史,使之成為敦煌藝術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誠然,韋利的目錄存在很多誤譯或錯解,伯希和與英國漢學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都曾撰文訂正,但此書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此后,敦煌藝術成為韋利關注的焦點,其敦煌研究還深入到敦煌文學和宗教,例如出版譯介敦煌變文的《敦煌歌謠故事集》(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1960)、翻譯敦煌詞曲、研究敦煌寫卷和遺畫等。即便從未到訪過中國,韋利也憑借著其對中國詩歌和文化的譯介,著力構建出一個詩情畫意的古典中國形象。他曾表示理解和同情中國人對斯坦因、伯希和劫掠中國文物的痛恨,展現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
四、20世紀初英國接受敦煌藝術的意義
經由上述梳理,20世紀初英國接受和闡釋敦煌藝術的基本圖景已浮出水面。盡管西方漢學家發(fā)表在《伯靈頓雜志》上的中國敦煌藝術的早期研究篇幅不算長,多是對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考古探險歷程的介紹,以及對其所獲敦煌絹畫、白畫、塑像等的描述,但卻對西方理解佛教藝術的演進和中國古典藝術的價值意義重大。他們的評介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推動了敦煌藝術在西方社會的接受與傳播;另一方面亦表明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品評再一次發(fā)生了改變,尤其體現在以下兩點。
首先,促成了西方評介中國藝術的歷史性轉折。縱覽中國藝術趣味在西方的接受歷程,20世紀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美術的興趣基本上只限于工藝品和裝飾性繪畫”?,因此對中國的高雅藝術視而不見或普遍貶低。到了20世紀初,西方掀起了重新審視和研究中國藝術的熱潮,甚至從雋永典雅的中國傳統藝術中找到與現代主義審美理念的契合之處,使得中國古典藝術成為其從傳統藝術中蟬蛻而出的重要借力。與歐洲17、18世紀盛行的“中國風”相比,“20世紀初英國再度出現的這股中國浪潮不應被單純理解為歷史性的風格復興,而應該將其放置于文學詩歌、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時尚消費彼此交織流動的圖景中,作為洞察現代主義思潮與實踐的有效框架”。?其中,作為英國最重要的藝術評論和鑒賞雜志,《伯靈頓雜志》于1903年在倫敦創(chuàng)刊,并于20世紀上半葉密集刊發(fā)了大量有關中國古典藝術的評論,成為英國乃至西方研究和傳播中國傳統藝術的重要陣地。這些有關中國藝術的評論有助于西方學者和普通民眾意識到中國不僅有華美且充滿異域色彩的裝飾藝術,還擁有深刻的美學精神、高雅的藝術形式和高超的創(chuàng)作技藝,從而促進了西方品評中國古典藝術的歷史性轉折。
其次,使得西方將研究目光從日本藝術轉到中國藝術。自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熱”盛行歐洲,歐洲對亞洲藝術的感知多來自于日本藝術,因此西方學者多透過“日本之眼”鑒賞(或誤讀)中國藝術,甚至有學者認為無需區(qū)分日本藝術與中國藝術?,從而使得中國藝術長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本文梳理的學者在探討中國敦煌藝術時就多次提及日本藝術,將中日藝術并置呈現,這證明他們對日本藝術頗為熟悉。例如彼得魯奇在介紹中國世俗藝術之于佛教藝術影響時,自覺地將敦煌繪畫品與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的玉蟲廚子上的裝飾相比,指出二者刻畫人物的異同。?隨后,他又通過對比日本繪畫與敦煌繪畫,認為中國藝術對日本佛教藝術的影響要遠早于宋朝,可追溯至唐朝時期。由此便能解釋為何12世紀的日本佛教繪畫具有印度-希臘和中國風格的混雜特征。直至20世紀初期,隨著以敦煌絹畫、塑像,早期青銅器、壁畫,傳統繪畫、書法等為載體的中國藝術形式進入西方視野,西方逐漸將目光從日本藝術轉向中國藝術,從而發(fā)掘出中國古典藝術在形式風格、創(chuàng)作技法和審美理念上區(qū)別于日本藝術的獨特魅力。
綜上,這些由西方漢學家刊發(fā)于《伯靈頓雜志》上的文章是西方敦煌藝術研究的拓荒之作,開啟了國際敦煌學研究的序幕。從中西藝術交流史的視角來看,它們既是20世紀初西方重審中國藝術的一個鮮明例證,又是促使西方的中國藝術研究發(fā)生歷史性轉折的助推力量,值得學界細致梳理與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敦煌藝術珍品在海外的流播其背景是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文物的瘋狂劫掠,西方漢學家的相關研究也直接得益于此。所以我們可以說,敦煌藝術的外傳是一種被動的文化交流與互動,而敦煌藝術品更見證與承載了中華文明的厚重歷史,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蘊。然而,即便是以平等、包容、尊重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藝術的西方知識精英,也受限于其主體身份和文化背景,著眼于敦煌藝術的形式之美而未能深究其深層的文化內涵和歷史語境,由此陷入了闡釋中國藝術的矛盾悖論和誤解誤讀之中,這亦說明不同文明間要實現真正的交流互通并非易事。因此,當我們梳理中國藝術被西方接受的歷程時,更需堅守身為中國學者的本土學術立場,既要挖掘西方對中國藝術的理解、闡釋和發(fā)揮的階段性特征,也要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進行思考與辨析,由此呈現中外文化交往的宏偉歷史圖景。
注釋:
① Raphael Petrucci,Chinese Painters:A Critical Study.Norwood,Mass:The Plimpton Press,1920,p.7.
② Raphael Petrucci,“Buddhist Art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18,no.93,1910,p.138.
③ ibid.2.
④ ibid.2,p.143.
⑤ ibid.2,p.144.
⑥ Raphael Petrucci,“The Pelliot Mission to Chinese Turkesta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19,no.100,1911,p.212.
⑦ ibid.6.
⑧ 原文為putti,解釋為菩薩的慣常侍從。然而,根據彼得魯奇所附的圖片,殘片所畫的應是“蓮花童子”,而非“脅侍”的形象。因此,這或是彼得魯奇的誤讀。
⑨ ibid.6,p.218.
⑩ ibid.9.
? ibid.1,p.7.
? ibid.1,p.8.
? Laurence Binyon,“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17,no.89,1910,p.255.
? ibid.13,p.256.
? Laurence Binyon,“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I”,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18,no.92,1910,p.91.
? (英)勞倫斯·賓雍著,鄭濤譯:《敦煌繪畫及它們在佛教藝術中的地位》,(英)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畫》,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 同上,第15頁。
? 同上,第20頁。
? Laurence Binyon,“Remains of a Tang Painting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46,no.267,1925,p.269.
? ibid.19,p.270.
? ibid.19,p.275.
? Roger Fry,“Reviewed Work(s): Ruins of Desert Cathay by M. Aurel Stei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21,n o.111,1912,p.174.
? ibid.22.
? Kenneth Clark,“Introduction of Last Lectures”.In Roger Fry.Last Lec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p.xxvi.
? Roger Fry,Transformations: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New York: Chatto& Windus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Inc..1968.p.76.
? Arthur Waley,“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Print Room,Stein Collectio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34,no.191,1919,p.55.
? 袁婷:《魏禮與敦煌絹畫研究》,《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2期,第110頁。
? (英)邁克爾·蘇立文著,趙瀟譯:《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頁。
? 汪燕翎、梁海育:《尋找“宋瓷”—20世紀初英國的現代主義中國風》,《藝術設計研究》,2022年第6期,第78頁。
? 趙成清:《拉斐爾·皮特魯奇20世紀初中國古代畫學研究》,《中國美術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9-110頁。
? ibid.6,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