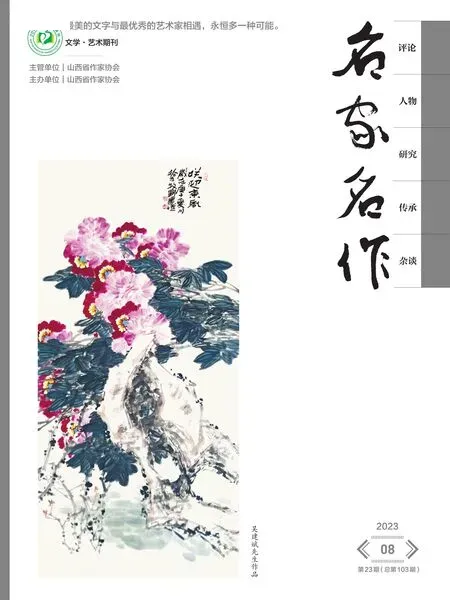汪立三器樂音樂創作生活綜述
杜 欣
汪立三先生(1933—2013 年)是我國著名的作曲家、音樂教育家。縱觀汪先生的人生旅途,器樂音樂創作貫穿他的一生,且鋼琴音樂創作是他主要的創作領域。他是我國最早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進行創作的作曲家,也是擅于使用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創作具有中華民族精神氣質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音樂作品的作曲家。
汪立三先生祖籍為四川省犍為縣,1933 年3 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漢市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汪正琈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喜愛京劇;母親蘇必蕙學的是會計專業。童年時期,常跟隨父親進出于戲院的汪先生對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他便曾嘗試著寫作以京劇曲牌為主題的旋律。之后由于抗戰全面爆發,汪先生一家遷往四川成都。1944 年,他考取教會學校——高琦中學,在這里開始了和西方文化的接觸。
一、求學時(1933—1959)
(一)積極的學習態度奠定了扎實的專業基礎
幼少年時,汪立三先生家庭里充盈著中華傳統文化氛圍,而在學校則受到歐洲音樂文化的熏陶,這為他日后進行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1948年,汪先生考入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現四川音樂學院),師從何惠仙學習鋼琴,并跟隨小提琴家張季時學習小提琴。1950 年,他在天津備考中央音樂學院時,跟隨彭維明老師(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教師)學習鋼琴,同時他以中國傳統說唱性曲藝四川揚琴為素材,寫下了目前可考的第一首鋼琴作品《揚琴印象》。
1951 年,汪先生考入了上海音樂學院,進入作曲系與鋼琴系進行學習。在此期間,汪先生因生肺病休學了兩年,本該回家養病的他在當時校長賀綠汀的特批下住在琴房,并且可以使用唱片室和圖書館,這使汪先生在這兩年里在各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長進。康復后,他正式師從丁善德、桑桐學習作曲與和聲,跟隨陳銘志、朱啟東學習復調與配器。此外,沈知白傳授的音樂史學課程,蘇聯復調專家阿爾扎馬諾夫以及精通欣德米特教授的作曲理論體系的楊與石所傳授的音樂技能,都在汪立三先生的知識體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音樂課程學習的豐富性與系統性,使汪立三先生掌握了扎實的知識與技能,為他日后的音樂創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二)“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1953 年,在賀綠汀先生的要求下,讀一年級的汪先生在還未上過作曲主課的情況下創作了根據陜北“信天游”同名民歌改編的鋼琴敘事曲——《蘭花花》,講述了一個淳樸姑娘的悲劇故事。這是汪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國鋼琴作品國民普及度與知名度最高的經典作品之一。同期他還以朝鮮民歌《道拉吉》為主題創作了一首小提琴曲《抒情曲》,并在校報上發表了文章《我們的好朋友靳卯君》。另外,他還發表過一些關于音樂創作的具有啟發性的見解。由此可見,汪立三先生早在最初的音樂學習中就已經開始了“創作”相關理論的思考和研究[1]。
1957 年,汪先生創作了一部優秀的鋼琴組曲作品《小奏鳴曲》,樂曲分為三個樂章,是一部運用現代技法并結合中國傳統五聲調式創作而成的作品。該作品以講述民間故事為目的,具有濃郁醇厚的中國氣質。作品獲得了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舉辦的鋼琴作品創作競賽一等獎,同時也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音樂創作中的經典之作。二十多年后,在人民音樂出版社再出版時,汪先生為三個樂章分別加上標題《在陽光下》《新雨后》《山里人之舞》,以方便學生理解。1951 年4 月,受到“雙百方針”的鼓舞,汪先生與蔣祖馨、劉施任等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論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的評價問題》一文,引發了青年學人與樂界前輩的論戰。迫于時代語境,這場討論未能順利地進行下去,但其對我國的音樂創作特別是交響音樂的創作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57 年8月,汪先生完成了民歌作品《詩》,用一部以《梅花三弄》《小河淌水》為素材創作的鋼琴曲來抒發自己內心的境遇。
二、沉淀時(1959—1978)
(一)在困境中向陽而生
1959 年,汪先生被送到北大荒的佳木斯合江農墾局文工團進行勞動改造。不久后,汪先生創作了一部東北味兒十足的女聲小合唱《北大荒的姑娘》。作品由廖云擔任作詞,描繪了活潑且不服輸的農墾區姑娘們突出的風采,音樂具有濃郁的東北二人轉風格,深受農墾區群眾的歡迎。身處逆境的汪先生在文工團里半年工作、半年勞動,同時也不忘音樂創作。舞蹈配樂《跳鹿》是汪先生根據赫哲族音調創作而成的,也是其在改造階段具有影響力的作品。遺憾的是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這兩部作品現都無完整的音樂保存[2]。
(二)用于教育目的的創作
1963 年,文工團解散,汪先生調入哈爾濱藝術學院教授作曲、復調。這一年他為“哈爾濱之夏”創作了以印尼音樂元素為素材的民樂合奏曲《巴厘舞曲》[3]。1964 年5 月,汪先生將李劫夫在1963 年寫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改編為鋼琴獨奏作品。1965 年,哈爾濱藝術學院與現在的哈爾濱師范大學合并,成立了哈爾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汪先生繼續在此任教與創作。他以非洲音樂素材創作了一部朗誦、民樂與鋼琴協奏曲《非洲戰鼓》。其創作的其他體裁作品還包括表演唱《三個婆婆》、小歌劇《游鄉》等。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除《我們走在大路上》外,其他作品皆未能留存。1973—1974 年,鑒于外國作品在當時多不便公開彈奏,汪先生為妻侄吳進文創作了用于練琴的套曲作品《童心集》。該作品以中國民族調式為基礎,采用多調性寫作手段創作而成,共有17 首鋼琴小品,作品規模龐大,直至2007 年才定稿完成。1977 年,汪先生運用多調性的手法將賀綠汀的《游擊隊之歌》改編為鋼琴敘事曲,并根據陜北秧歌劇《兄妹開荒》改編了同名鋼琴作品。后一部作品以西洋作曲技法融合地方性歌舞劇創作而成,深受百姓喜愛,擁有著極高的傳唱度。
這一時期的汪先生將音樂創作真正融入自己的生活,開始了以教學為目的的創作,同時其音樂風格開始成型。他用行動向世人展現了自己豁達的心境。人生這條道路上總會出現一些彎彎繞繞,面對它,接受它,走過它,迎來的就會是通衢大道。
三、復出后(1978—1989)
1978 年12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
(一)如雨后春筍般呈現的音樂創作
1979 年,汪先生當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黑龍江分會常務理事。同年,鋼琴組曲《東山魁夷畫意》誕生,這部作品是汪先生根據日本現代畫家東山魁夷的四幅繪畫作品《冬花》《森林秋裝》《湖》《濤聲》創作而成。他以日本都節調式為整部作品的核心音調,每一首的標題下方都題上了短詩,通過音樂的形象表現出繪畫中的意境,形成詩、樂、畫三位一體的完美結合。這部作品也成為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1980 年,汪先生創作的《他山集》堪稱他創作技法最盛和藝術表現水平最高的作品。全集分為《書法與琴韻》《圖案》《泥土的歌》《民間玩具》《山寨》五首序曲與賦格。他在作品中融入湖南花鼓、信天游、彝族舞蹈以及中國傳統古琴音樂與書法的元素,又采用了欣德米特、巴托克、巴赫等西方創作手法。該作品將中國音樂旋律流暢的特點與西方音樂和聲、復調融在一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音樂風格,體現了西為中用、中西結合的理念。此外,其于1980 年所創作的《夢天》,是中國第一部用十二音序列體系創作的鋼琴曲;另一部采用同樣作曲技法的《秦王飲酒》是在1982 年完成的。1982 年,汪先生在《音樂藝術》第三期發表了《夢天》的鋼琴曲譜,講到“《夢天》是我根據李賀的詩譜寫的兩首鋼琴曲之一,作于1980 年(另一首是《秦王飲酒》)”。兩首曲目都是以我國唐代詩人李賀的同名詩篇寫作而成,后合并為組曲《幻想曲兩首——李賀詩意》。這部作品采用中國傳統五聲調式,融合西方現代作曲技法,生動地描繪了不落凡塵的詩篇意境[4]。1983 年,汪先生創作的鋼琴奏鳴曲《幻想奏鳴曲“黑土”——二人轉的回憶》第一稿完成。這部作品是在美國鋼琴家杰弗里·杰柯布的邀請下所作,采用中國風味濃郁的黑龍江“二人轉”曲牌為素材,利用多調性的創作手法完成。從其該時期的作品可見,汪先生在樂曲的創作中始終致力于將中國本民族音樂元素放在首要地位,嘗試打破傳統作曲的限制,進行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創新性實踐。
1989 年,他繼續選擇以民族音樂為寫作素材,創作了組曲《窗花集》,包括《兒歌》《秧歌》《山歌》《悲歌》《大花臉》五首。其中第五首《大花臉》是以中國京劇人物為素材創作而成,全曲充滿了京劇開場鑼鼓喧天的韻味。1999 年創作了由《頑強的小花》《大頭娃娃舞》《紅綠燈下》三樂章構成的鋼琴組曲《小弟的畫》;包含《鑲金邊的浮云》《大山的傳說》《戲法》三個如童話般樂章的《音詩三章》,均體現了汪先生對童心的向往。2002 年汪先生退休后到上海定居。
(二)深刻思想在學術與教育上的體現
除器樂音樂本體創作外,汪先生還致力于創作理論的研究。1982 年在《音樂藝術》發表了《“夢天”作者的話》;1983 年在《人民音樂》發表了《在全國交響音樂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1986 年在《中國音樂學》發表了《新潮與老根》(香港第一屆中國作曲家現代音樂節的專題發言),體現了他深刻的音樂思想;另有文章《“海邊賣水”及其他》在1986 年發表。1987 年出席德國“異國的世界——西方的幻想”東西方文化討論會;1988 年赴紐約參加中國海峽兩岸作曲家座談會;1990 年赴香港參加中國樂史國際研討會;1992 年于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劉靖之所編的《中國新音樂史論文集》中發表了《中國新音樂與漢語特點有關的若干理論與實踐之回顧》等。
20 世紀60 年代,汪先生在哈爾濱藝術學院承擔普通及專業音樂教育的任務。在課程規劃方面,他不僅重視學生音樂學科的專業化修養,還關注教育學科的專業化,培養各級各類學校的師資;在授課形式方面,以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代替過去學生被動接受的授課形式,以提升學生對音樂美的感知力和創造力,培養出了許鏡清、烏蘭托嘎等優秀的作曲家,為我國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汪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美育”的主張為根本,堅持把審美教育與專業培養高度結合,采用寓教于樂與潛移默化的方式提升學生健康的審美經驗以及整體把握能力,真正做到了“和風細雨之于禾苗,潤物細無聲”。
四、暮年時(2003—2013)
2003 年,汪先生突發腦梗。病情好轉后,他創作了四部作品,并于2003—2007年出版。其中《讀魯迅〈野草〉》是以鋼琴小品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讀后感,另外三部作品都是鋼琴組曲。根據黎巴嫩作家紀伯倫詩作完成的《先知集》包括以青海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為核心素材的《先知》、將中國五聲調式和弦與西方功能和聲結合的《蒼茫的I、IV、V》、用弗里吉亞調式體現西方古典色彩的《舒曼的異國》、根據中國古典詩詞文化創作的《如夢令》以及風格迥異的快板作品《閃光的小河流呀流》五首,體現了汪先生對人生百態的哲理性感悟。《小麥青,大麥黃》《舞》《泉》《儺》是《紅土集》中的四首樂曲,以中國戲曲元素創作而成的《儺》體現了源于祭祀儀式的中國獨有的神秘感。汪先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動物隨想》采用音樂形式表現了動物的百態,體現了這一時期汪先生依然渴望擁有童年的純真,包括《大象的舞步》《沙漠里的駝鈴》《青蛙的樂隊》《拉手風琴的熊》《蜘蛛的八卦陣》《歸心似箭的燕子》《玻璃缸里的珊瑚蟲》《夢中的蝴蝶》《困在籠中的大蟒》 九首樂曲。這部作品再次采用西方作曲技巧結合濃郁民族元素的創作手法,體現了汪先生為鋼琴音樂中國化不懈奮斗的主張,同時影響和啟迪著后世的中國鋼琴音樂創作。2013年7月6日,汪立三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0 歲。
五、結語
汪先生的作品數量并不算多,卻敢于將中華傳統文化元素與西方古典文化進行融合。他的大膽創新為中國鋼琴音樂作品的創作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在學術上大膽發表自己的藝術見解,為中國音樂發展盡力;在教育上用積極的態度和先進的思想培養了很多學者與作曲家,為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