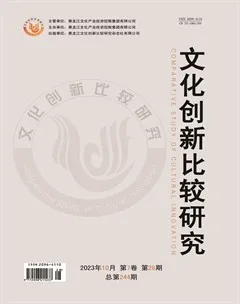從被凝視到反凝視:《茶蓬河的戀人》中的女性主體性建構
胡敏娜
(廣州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 510006)
美國小說家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以撰寫其與隊友在越南戰爭中的經歷而聞名。他的半自傳性小說集《士兵的重負》(The Things They Carried)是“關于越戰期間及戰后美國士兵經歷的沉思,是一部越戰回憶錄”[1]。整個作品由22 個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中短篇小說組成,《茶蓬河的戀人》 (“Sweetheart of the Song Tra Bong”)是其中的第9 篇。故事講述了到越南美軍駐地探親的高中畢業生瑪麗如何從一個對戰爭一無所知的平民,轉變成一個熱衷于戰爭的戰士的過程。奧布萊恩通過刻畫戰爭語境下女性從邊緣性客體到主體的身份轉變,顛覆了主流戰爭敘事中的“襯托男性英雄主義的輔助性角色”的傳統女性形象,同時也揭露了戰爭對人性的巨大沖擊。
經過文獻檢索發現,國內尚未有專門針對《茶蓬河的戀人》的文學闡釋,只有幾篇有關《士兵的重負》的研究性論文涉及對該作品的解讀。黃珊珊分析了故事中的男性氣質和男性同性社會關系之間是如何實現對彼此的完善和鞏固的[2]。湯鳳娟指出敘述者拉特的講述中存在不可靠敘事,并探討了不可靠敘事產生的原因[3]。歐華恩認為,“瑪麗的變化表明‘戰爭使人瘋癲’,這種瘋癲是對官方真理片面嚴肅性歡快的諷刺性模擬,是狂歡式的瘋癲”[4]。康雅麗和梁超群指出,“瑪麗的故事暗示了戰爭對于整個人類的存在級意義,它啟示我們擺脫基于狹隘自我的直覺,從整個人類的角度思考戰爭的存在論價值”[5]。國外學者關于該作品的研究為數不多。Vanderwees 指出,故事打破了性別二元對立,批判了普遍的男性話語[6]。Faubion 認為,瑪麗的“野蠻”轉變使得她能夠將自己的身體投入到語言過程中,從而產生她自己真實、道德的言論[7]。這兩個結論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本研究基于凝視理論,探討瑪麗是如何從一個戰爭語境下的“被凝視”的客體,通過身體意識的覺醒、話語權的建構,激發女性主體意識,對“男性凝視”發起“反凝視”,打破戰爭話語中性別化的二元對立,成為一個在戰爭中占據主體地位的女戰士。
1 被凝視:瑪麗的性客體化和自我物化
“‘凝視’是攜帶著權力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福柯在《規訓與懲罰》對觀看中的權力因素進行了分析,指出權力體制下凝視會對人產生壓迫效果。法國哲學家、思想家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是由男人決定的……男人是主體,是絕對;女人是他者”[8]。在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女性是逐漸以他者身份構建出來的“第二性”,而男性凝視是構建女性“第二性”的手段。在男性凝視下,女性被物化為性的客體和欲望的對象。“女性在淪為‘看’的對象的同時,體會到男性凝視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男性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9]
1.1 被物化的女性身體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身體—話語—知識—權力”的權力系譜,意在說明權力自外而內對身體進行規訓,使得身體本身變得溫順,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10]。在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戰爭場景中,男性牢牢掌握話語統治權,成為女性美的構建主體。進入男性視野的女性身體在被異化為“物” 的基礎上,被男性凝視、評判,成為滿足男性視覺快感的欲望客體。
在越南茶蓬河附近的美軍駐地,一群戰地救生員談論要湊點錢“從西貢帶幾個成熟的女人來,來調劑一下生活”,福斯提出“領來一個女孩”。他的異想天開,遭到了眾人的奚落。為了回應隊友們對他的嘲諷,也為了解相思之苦,他寫信邀請遠在美國的剛高中畢業的女友來越南相聚。由此可見,瑪麗是作為“消磨時間”的欲望對象進入男性視野的,她的到來“對士氣大有益處”。故事講述者拉特著力描述了瑪麗的容貌、身材、衣著和神態:“那個漂亮的金發女孩子……穿著裙褲,白色的裙褲和性感的粉紅色針織套衫……一個高大的金色女郎……兩腿白嫩、修長,藍色的眼睛,皮膚像草莓冰淇淋……或許她的雙肩太寬,但是,她的大腿非常漂亮……她穿著藍色毛邊短褲和黑色泳裝上衣……她穿著內衣,展示她的大腿。”在男性的凝視下,瑪麗展示了一個“美國甜心”的典型特征: 迷人的外貌、時尚的穿著、溫柔的笑容、優雅的舉止、陽光友善的性情。男人們“非常欣賞”她,“真的很喜愛她”,認為她“十分吸引人”。
美國當代著名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莫爾維在其《視覺快感與敘述電影》一文中闡述道:“在一個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男性和被動/女性。”[11]瑪麗的身體被男兵們長時間地觀察、注視,給他們帶來了具有沖擊性的視覺快感。“男性權力和男性話語在女性身體上得以施展,規訓著女性的生存。”[12]瑪麗自覺接受了男性對女性身體的審美規訓,且將這種規訓根植于心,對被物化的身體進行自我審視,以迎合男性的視覺凝視并期望獲得他們的青睞。
1.2 被規訓的女性話語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認為,話語和權力密不可分,話語是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載體和實現方式[13]。通過操縱和塑造話語,權力可以影響和控制個體的思想、行為和身份認同。凝視作為一種權力運作手段,通過特定的視覺觀察和注視方式來實施權力控制。話語權力試圖通過不平等的凝視策略,以及對言辭、表達和語言規范的掌控,來塑造、影響和控制個體的主體性。故事中,被規訓的女性話語一度限制了瑪麗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式,剝奪了她的個人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的權利。她被禁錮在特定的社會期望和角色定位里,其女性主體意識被壓抑。
在福斯勸說瑪麗不要再參加特種隊員埋伏任務的過程中,瑪麗“順從到了沉默的地步”。對其他戰地救生員提出的問題,瑪麗感到很不安,擔心回答這些問題會給她帶來麻煩。她“一直看著桌子對面的福斯”,希望得到他的同意。見福斯沒有說話,她只好“嘀咕了一兩句含糊不清的話,卻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回答”。在男性凝視下,瑪麗自我約束自己的行為和言辭,顯示出被動和順從的態度,以避免挑戰男性的權威,滿足男性對于權力和控制的期待。在福斯的勸說下,瑪麗妥協了,和福斯正式訂婚了,并答應他“不會再有埋伏了,也絕不會再有深夜回來的時候了”。如果瑪麗遵守約定,她“會成為一個甜美的新娘”,繼續和家鄉的女孩一樣,保有“純潔天真”,保持對戰爭的一無所知。當男性作為戰爭親歷者言說他們的經歷時,女性只能作為被動的傾聽者,只會“用那些甜蜜的、圓圓的、大大的眼睛盯著你。她們不懂得子彈的尖嘯聲,就像沒法告訴別人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一樣”,甚至會被評價為“愚蠢”。沉默或失語,將會固化女性的客體地位,使其屈服于男性的權力及話語。
2 反凝視:瑪麗主體地位的確立
“凝視”這一行為滲透著濃厚的性別意識。在兩性關系中,因為“男性被賦予了‘看’的權力,女性則是男性‘觀看’的對象或客體”,從而導致了“女性景觀、男性觀看”的局面。隨著被凝視者的主體意識覺醒,凝視者和被凝視者的主客體身份會發生轉換,觀看行為可以是“對抗性的,是抵抗的姿態,對權威的挑戰”。故事中,瑪麗拒絕被固定在被凝視的位置,以反抗姿態對來自權威意志的男性凝視投以 “反凝視”,確立了戰爭場景下的女性主體地位。
2.1 身體意識的覺醒
女性身體意識屬于女性的主體性特征之一,是女性對客觀身體與主觀思想的意識集合。女性從小就被灌輸“要培養良好風度”的思想,被教導和訓誡“應該時常觀察自己的身體”。瑪麗初抵營地時,精心打扮,主動迎合男性審美標準,充分展示自己的活力、魅力和性感,順應男性的欲望凝視。在參與戰地急救工作后,她摒棄了依附于男性審美需求的穿衣風格,不再將外貌和性感作為吸引男性凝視的手段。她“很快習慣了那種不修邊幅的生活方式,不再化妝,不再修指甲,不再佩戴首飾。她把頭發剪短,用一個深綠色的頭巾扎上,衛生已成為無足輕重的事情了”。在執行埋伏任務時,她“戴了一頂闊邊的呢帽,穿了一件極臟的綠色作戰服……她的臉用炭涂成了黑色”。瑪麗主動突破傳統的性別規范,恢復自然體態,跳脫“男性景觀”的框架。
瑪麗沉著冷靜,從不躲避恐怖的場合,處理急救工作快速準確。她由一個“始終微笑著”“既靦腆又調情”的甜美女孩,變成一個“面部表情一下換了個模樣,幾乎是寧靜的,大大藍眼睛壓縮成嚴謹、聰慧的焦點”的醫務人員。在學會了拆卸步槍,摸索出開罐頭的技巧后,她變得更為自信,“行為舉止有了一種新的權力”。福斯發現“她的身軀似乎也不那么自如了——許多部位過于僵硬,原來圓潤的部位現在直挺挺的”。瑪麗拒絕順應男性欲望幻想的規訓,脫離被凝視和順從的狀態。她也不再刻意用熱情和笑聲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而是通過將聲音調成“更低的音調”和“保持沉默”來表達內心真實的感受。她低頭看著男友的時候,“面部是毫無表情的、眼神極其平淡”。身體呈現的背后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瑪麗通過自我身體言說,表達了自我認知的轉變、自己的內在與外界凝視的斷裂。伴隨著身體意識覺醒,女性身體客體回歸至女性身體主體,瑪麗擺脫了被物化的定位,她“不再是無能為力的觀看對象,而是觀看主體”[14]。
2.2 話語權的建構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認為,“女性話語權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張、資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綜合體現,它既包含著對女性言說及其主張所具地位和權力的隱蔽性認同,又取決于一種話語有效的社會環境表達機制與主體資質,還直接表現了女性對自我現實狀態的把握及相應主觀心態的流露”[15]。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女性被建構為他者。“他者往往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被邊緣化、屬下化,失去話語權,產生自卑感。”[16]要建構女性話語權,女性要用自己的聲音挑戰“被強加的沉默和隱性”,從而建構女性主體地位和獲得凝視男性的權利。故事中,瑪麗通過構建“話語權”,實現了從被凝視者到擁有絕對權力的凝視者的角色轉換。
在男友福斯的安排下,瑪麗不遠萬里,中轉了5次,從美國的俄亥俄州來到了越南廣義省的美軍駐地。初抵戰爭的前線,瑪麗“還有點兒不知所措”,但是戰爭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打定主意要“學會些什么”。在福斯的反對下,瑪麗堅持要去附近的村莊感受當地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氣息和風俗習慣。在她的眼里,敵方平民和自己并無二致,甚至愛上了美好、淳樸的鄉村生活及當地的孩子。日漸提升的戰地急救能力和生活技能在深層次上改變了瑪麗的精神面貌,她變得愈發自信,“行為舉止上有了一種新的權力”。福斯驚訝于她的轉變,提醒她得考慮回家了。瑪麗卻笑著告訴他別提回家的事,反而直言:“我想要的一切,就在這里”。瑪麗放棄了早日成為賢妻良母的夙愿,她希望“不用急著結婚,可能先去旅行,可能住在一起。不一定要3 個孩子。也不一定要在伊利湖畔有所房子”。新的環境激發了瑪麗的自我意識,她在戰爭環境中找到了幸福感和價值感,她告訴福斯“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幸福。從來沒有”。她不再局限于被動地滿足男性社會的期待和需求,她通過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聲音、觀點和情感,抵抗社會規訓的凝視,拒絕承擔“被社會規訓的角色”和“被性別定型的角色”。
福斯在特種隊員居住的茅屋處見了瑪麗最后一面。福斯不甘心失去她,試圖懇求她回歸。瑪麗鎮靜地對“單腿跪在那里,動彈不了”的福斯說了下面一段話,表明她已在戰爭中找到了自我價值,并堅定了繼續投入戰爭的決心。
“談什么都沒有意義了,” 她說“我知道你想說什么,但是,這樣……這樣不錯! ”
……
“你不屬于……你現在待的這個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你躲在這個小堡壘里,在鐵紗網和沙袋后面,你不知道里面的一切。有時,我想吃了這個地方,我想吞下整個越南——那土、那死亡……我只想吃了它,讓它在我體內——那是我的感受,就像……我變得害怕……但是,這不錯。你知道嗎?我感覺到了我自己。夜里,我埋伏的時候,我感覺到了我自己的身體,我能感到我的血液在流動,我的皮膚和指甲在動,就像我渾身全是電,我在黑暗中發亮——我幾乎在燃燒——我將燒得化為烏有——但是,沒有關系,因為我確切地知道了我是誰。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這種感覺。”[17]
瑪麗不再是一個被動的、順從的、柔弱的客體,而且通過建立自己的話語,掌握話語權,成了戰爭中的主體。
3 結束語
在故事的結尾處,瑪麗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離開特種部隊,獨自走入山區再無蹤影。她可能和越南當地人生活在一起,也可能在某個地方暗中觀察著特種隊員。以“獨行戰士”的身份,瑪麗作為觀看主體對男性進行了徹底的“對抗性凝視”,突破了男性凝視背后的權力控制,確立了女性在戰爭中的主體地位。通過書寫瑪麗的戰爭故事,奧布萊恩塑造了一個前后反差極大的女性人物形象,打破了傳統戰爭敘事中男性英雄主義的范式,消解了戰爭話語中性別化的二元對立,擴充了對戰爭場景中女性身份的理解維度,推動了女性身份和權力書寫空間的拓展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