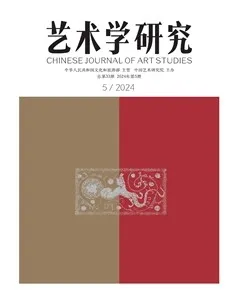吳越國的佛教文化與藝術
【摘 要】 存續于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國,自創立者錢镠始,三世五王均采取“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政策,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緊密聯系,致力于開發經濟、發展文化,形成了既深受中原文化影響又體現獨特地域環境與人文歷史的吳越文化。作為吳越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與藝術,上承晚唐之風,下開宋韻文化之源,顯示出中國文明與文化傳統連綿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吳越國各代君王均采取護持佛教的策略,通過實施禮遇名僧、包容諸宗、興寺建塔、開窟造像、雕刻經像、求取天臺教籍等措施和行動,促進和加深了佛教的中國化,并為儒釋道三教融通及佛教文化進一步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性形塑奠定了基礎,亦使吳越國及其文化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發揮了賡續中華文脈的獨特作用。
【關鍵詞】 吳越國;錢镠;“善事中國”;佛教文化與藝術;佛教中國化;傳統文化主體性形塑
由錢镠(852—932)創建、定都杭州的吳越國,因其三世五王積極采取“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政策,致力于開發經濟、發展文化,故而得以在10世紀南北紛爭之中,保國安固,拓出一方凈土,護佑一方黎庶。作為五代十國中存續最久的政權,吳越國素有“佛國”之稱,自武肅王錢镠始,及至忠懿王錢弘俶(929—988),均采取護持佛教的策略,成為佛教發展的有力“外護”。針對唐武宗會昌滅佛的影響,他們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恢復吳越地區佛教的發展,促進、加深了佛教的中國化,并為儒釋道三教融通及佛教文化進一步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性形塑奠定基礎,亦使吳越國及其文化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發揮了賡續中華文脈的獨特作用。
吳越國自創建者錢镠開始,便采取了立足兩浙、崇奉中原的政策。后梁開平元年(907),錢镠接受后梁的進封,正式建國,奠定了五代吳越割據政權之基。錢镠在唐、梁易代之際,向梁稱臣,此舉被認為是確立了吳越國“尊奉中原,連橫諸藩,對抗淮南”的基本立國戰略,為吳越國處理與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及宋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范例[1]。錢镠臨終時曾留下遺訓:“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2]《錢氏家乘》所載《武肅王遺訓》中亦有述及錢镠“善事中國”的訓誡:“凡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識時務,如遇真主,宜速歸附。”[3]錢镠所尊奉的“中國”,乃指在中原地區建立的政權。錢镠奉此為正朔,稱臣納貢,避免卷入爭戰之中。吳越國的后續繼承者,錢元瓘(887—941)、錢弘佐(928—947)、錢弘俶均奉行此政策。錢弘俶最終納土歸宋,不僅是時勢使然,事實上也是吳越國一向奉行“善事中國”政策之必然。
錢氏吳越國“善事中國”的政策,也被后人譽為“保境安民”之舉。吳越國對外“尊奉中原”“連橫諸藩”,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對內則采取“安民”政策,這些安民政策中比較引人矚目的部分,便是對佛教的護持。錢氏家族自錢镠開始,便對佛教采取崇奉、護持的態度,并且沿襲唐代成規,制定了一系列佛教政策。根據賴建成總結,錢氏采取的佛教措施包括:創立僧官制度,州立僧正,寺立僧主,設有國師、僧統、都僧正等僧官職位;設壇度僧時,必以明律召大德監壇[4]。錢镠的做法,也為此后錢氏諸王制定佛教政策提供了參照,吳越國的后續繼承者—錢镠之子文穆王錢元瓘,錢元瓘之子忠獻王錢弘佐、忠懿王錢弘俶均積極護持佛教。其中,錢弘俶尤為潛心佛事,在位期間廣建佛寺、禮遇諸宗,且遣使往高麗、日本求取天臺佚籍,天臺宗由此得以振興。
吳越國錢氏諸王一以貫之的護持佛教政策,無疑為佛教在吳越國境內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以杭州為中心的吳越佛教文化發展漸至興盛。吳越佛教的發展,為隋唐佛教向以杭州、揚州、福州、廣州為中心的宋元近世佛教的轉型奠定了基礎。吳越國境內佛教的興盛,不僅對佛教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影響了佛教物質文化,如吳越國曾大舉興寺建塔、開窟造像。吳越地區現今仍保留有大量佛塔、造像等吳越國時期的佛教藝術遺存,這也成為佛教物質文化史、藝術史研究的寶貴資料。概言之,吳越國佛教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及其影響,主要可見于禮遇名僧,包容諸宗;興寺建塔,開窟造像;雕刻佛教經像;求取天臺教籍諸方面。
一、禮遇名僧,包容諸宗
吳越國之禮遇、護持佛教,始自錢镠,此后三世諸王,對名僧大抵采取延請、禮遇之態度[1]。武肅王錢镠曾禮遇洪諲、道怤、楚南、文喜、可周、虛受、昭國師、彥偁等名僧。文穆王錢元瓘亦禮遇名僧,如曾于杭州創建龍冊寺,使道怤居之,《宋高僧傳》謂“吳越禪學自此而興”[2];又如曾造千佛伽藍,召希覺為寺主,并私署其號“文光大師”[3]。忠獻王錢弘佐在位時間較短,但亦禮遇名僧如皓端、全付諸人。忠懿王錢弘俶,對境內名僧更是優待非常,法眼宗二祖德韶(891—972)、三祖延壽(904—975),均深受錢弘俶禮遇。錢弘俶以德韶為國師,以弟子禮事之,并于宋建隆元年(960)邀德韶弟子延壽至杭州,主持重修靈隱寺等事宜。據《咸淳臨安志》載,杭州六和塔,即為延壽主持興建,目的乃“以鎮江潮”,且塔中“內藏佛舍利”[4]。此外,錢弘俶還曾命道潛“入王府受菩薩戒”,并加以優待—造大伽藍使居之,賜號“慧日永明”,“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5]。
錢氏諸王禮遇僧人,且對佛教各宗采取包容態度,這促使吳越國境內佛教諸宗均有活動與發展,其中禪宗最興。吳越國初期,溈仰宗、曹洞宗、臨濟宗均有僧人活躍;中期,雪峰義存禪師弟子在杭州日漸活躍[6];中期以后,法眼宗因德韶、延壽一系深受錢弘俶崇奉護持,發展尤盛。另外,律宗、天臺宗、密宗、華嚴宗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律宗方面,道宣南山宗一脈法系中的杰出代表,如慧則、元表等,為避北地之亂南下,傳南山律于吳越境內;有“律虎”之譽的贊寧(919—1001),被錢弘俶署為監壇,任兩浙僧統,錢氏納土歸宋后,曾令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宋,宋太宗賜號“通慧大師”[7]。天臺宗在會昌滅法后,教籍損毀、散佚,義寂(919—987)尋求德韶幫助,后者說服錢弘俶遣使訪尋天臺教籍,天臺宗漸得復興。密宗經咒在吳越國境內尤為流行,僧侶受持密咒風氣熾盛,如禪宗、天臺宗等亦有受密宗儀軌、持咒活動之影響。吳越國境內研習《華嚴經》風氣亦盛,這也助益了宋初子璿(?—1038)、凈源重振華嚴宗。
二、興寺建塔,開窟造像
吳越國錢氏諸王崇佛,曾于境內大規模地興建寺塔、開鑿石窟,吳越國境內現今仍保留著不少佛教藝術遺存。吳越國境內的佛教藝術遺存,作為承載佛教義理與觀念的表法工具,宗教屬性無疑仍是它們的根本屬性。另外,正如柯嘉豪所指出的,這些物質世界的遺存,相較于語言、思想與儀式,有其特殊的效力—“物品令神圣變得具體可及。物品讓一個人得以與神靈溝通并感知他們的存在。物品通常是傳播宗教理念與情感最富表現力的工具”[1]。林立的寺塔與遍布的造像,構成了這一東南佛國引人矚目的文化景觀,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助力錢氏諸王以佛教弘化。
關于吳越國時期興建的佛寺情況,朱彝尊《曝書亭集》云:“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2]極言錢氏所建寺塔之眾。據杜文玉的統計與考證,吳越統治時期[從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止]興建的寺院有355所,其中杭州城內外(錢塘、仁和兩縣)共計213所,前代始建的寺院106所在吳越統治時期仍然存在,因此吳越統治時期,境內寺院數量達到461所[3]。實可謂晨鐘暮鼓,梵音不絕。
與廣興佛寺相應的,是吳越國起塔之風的盛行。在佛教中,塔被視為佛陀精神與教義之表征,《長阿含經》載:佛陀涅槃前交代弟子收取舍利起塔供養,“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4]。佛涅槃后,舍利成為佛陀、佛陀精神與佛法的象征;舍利與塔結合形成舍利塔后,舍利對佛的表征成為舍利塔的意義所在。對象征佛陀的佛舍利之崇拜,在中古時期的王權政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見佛之舍利,如見佛之法身,因此南北朝至隋唐的帝王便通過對佛舍利的崇拜,將王權與佛教中至高的神圣力量相連,以增強王權的合法性。吳越國自錢镠開始,便通過迎接、供奉舍利塔的方式,建立起對象征佛陀的佛舍利之崇拜。后梁貞明二年(916),錢镠命其弟錢鏵并僧清外等前往明州鄮縣(今寧波)迎阿育王釋迦舍利塔,并于次年正月,于杭州城南羅漢寺建木浮屠,以供奉釋迦舍利塔。另外,后唐天成四年(929),余姚縣修舜井,獲古佛舍利數十粒,錢镠命徐仁綬諸人迎之,同樣起塔供養,“定浮圖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5]。錢镠建塔供奉阿育王釋迦舍利塔的做法,或也啟發了錢弘俶模仿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的舉動。南宋志磐《佛祖統紀》載:“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1]錢弘俶于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至宋太祖乾德三年(965)集中造阿育王塔,所造之塔均為單層方形小塔,亦被稱作寶篋印塔。
此外,吳越國境內樹立經幢的風氣亦盛。經幢是唐代才發展起來的一種多面體佛教石刻建筑,其上多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劉淑芬指出,經幢的性質乃是一種“法舍利塔”,有些經幢同樣也承擔埋藏舍利的功能[2]。相關資料記載中的吳越經幢有27處40余座,實際存世5處7座[3]。經幢的設立主要由錢氏王室與高官贊助,目的主要在于鎮護國家與滅罪度亡。吳越國經幢構造復雜,其上的書法與雕刻均極精美,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是對唐代經幢工藝的繼承與超越。
除了興建寺塔,吳越國境內同樣流行開窟造像。唐以后,隨著佛教中心的南移,北方不再流行開鑿大型石窟,石窟造像藝術逐漸向南方轉移。吳越國時期,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地區成為南方開鑿石窟造像的中心之一。吳越國時期的石窟造像,主體部分集中分布在杭州西湖周邊地區,主要有西湖石刻群和飛來峰石窟群,其中南山石窟群多由錢氏家族出資開鑿,主要分布地點有慈云嶺、圣果寺、石屋嶺、煙霞洞、天龍寺等。吳越國的石窟造像情況,亦與此際佛教文化發展相呼應,如石窟造像題材中常見“西方三圣”,乃受吳越國境內凈土信仰盛行的影響—吳越國境內結社念佛相當流行,禪宗、天臺宗、華嚴宗等學者亦兼弘凈土,如對吳越佛教產生深遠影響的高僧永明延壽即主張禪凈雙修,延壽所著《萬善同歸集》列舉的修行方式中,凈土念佛法門即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吳越國石窟造像還出現了一些極具吳越地域特色的造像題材,如白衣觀音與十六羅漢。吳越國時期的石窟造像藝術不僅是研究唐宋之際石窟造像藝術演變的重要因素,且其石窟造像中的特別表現題材,如觀音、羅漢等,也為探究宋代以來觀音、羅漢相關題材的繪畫風格演化提供了參照。
三、雕刻佛教經像
唐、五代時期,復制與傳播佛教經咒與圖像是僧人弘法及社會各階層信眾祈求福祉、積攢功德的重要手段。對于雕版印刷術在唐代的興起,不少學者認為其與佛教淵源甚密,如向達認為中國印刷術之起源與佛教關系密切,其演變情況則“由印像以進于禁咒,由禁咒進步始成為經文之刊印,而其來源則與印度不無關系”[4];辛德勇認為,佛教密宗信仰,乃是雕版印刷術產生最重要且最直接的驅動力[1]。浙江地區在中唐時期便出現了雕版印刷書籍的現象;吳越國時期,錢弘俶在位期間曾大規模地雕印佛經與佛教圖像,分別于后周顯德三年丙辰(956)、北宋乾德三年乙丑和北宋開寶八年乙亥(975)三次大規模雕印《寶篋印陀羅尼經》,置于銅、鐵阿育王塔及雷峰塔中供養,丙辰、乙丑、乙亥本發愿文中均提及造此經“八萬四千卷”。盡管這一數目或為虛指,但吳越國時期雕刻佛經數量之巨,可見一斑。
另外,錢弘俶倚重的高僧延壽,在吳越國的佛教經像雕刻中起到了尤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張秀民根據《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統計,經延壽之手刊印的經咒與圖像有:《彌陀塔圖》(親手印十四萬本)、《彌陀經》、《楞嚴經》、《法華經》、《觀音經》、《佛頂咒》、《大悲咒》、《二十四應觀音像》(用絹素印二萬本)、《法界心圖》(印七萬余本)、《孔雀王菩薩名消災集福真言》(十萬本)、《西方九品變相毗盧遮那滅惡趣咒》(十萬本)、《阿閦佛咒》、《心賦注》。錢弘俶與延壽主持刊印的佛教經像、咒語中,有數字可考的部分共計六十八萬二千卷(或本)[2]。佛教對印刷物的巨量需求,顯然成了吳越國雕版印刷急速發展的動力之一,這反過來也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傳播,并且為北宋時期以杭州為代表的浙江地區成為全國的出版中心奠定了技術基礎。
四、求取天臺教籍
吳越國時期,在義寂、德韶等高僧的努力與錢弘俶的支持下,經會昌毀佛及唐末戰亂雙重打擊而嚴重散佚的天臺教籍,得以從高麗、日本回流中土。天臺教籍的復歸,一方面是中國佛教史尤其是天臺宗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為宋代天臺宗再度振興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東亞佛教交流史中重要的一環。
天臺宗的發展,至唐末日趨困頓,到了吳越國初期,由于錢氏對佛教的護持態度,天臺宗的處境相對有所改善。據《佛祖統紀》載,十四祖清竦主持國清寺以后,嘗云:“王臣外護得免兵革之憂,終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3]可見清竦對“王臣外護”的認識與爭取。此際,天臺宗雖在吳越國“終日居安”的和平環境中逐漸恢復了弘法活動,但直至十五祖義寂時期,仍然處于教籍散佚的狀態,據《宋高僧傳》載,義寂面臨的乃是天臺宗自始祖智者大師智顗(538—597)以來幾代積累的教籍多數焚毀、散佚,天臺宗陷入傳法無憑的困頓局面—“先是智者教跡,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4]對于體系龐大、論證精密的天臺宗而言,離開了教典的支撐,一則其教理講習體系無法承續,二則其修習止觀的實踐活動也難以展開[1]。這也是為什么教籍之零落會對天臺宗的發展產生重大沖擊,搜求天臺教籍自然也成了義寂和同時代的天臺宗僧人的當務之急,然而義寂早期的搜求,僅僅是“適金華古藏中得《凈名疏》而已”[2]。
天臺教籍最終得以順利復歸,既有賴于義寂等天臺宗僧人重振天臺的志愿、禪宗僧人如國師德韶的助力,也離不開吳越國“王臣外護”的作用。據《景德傳燈錄》載,義寂搜求天臺宗教籍,得到了吳越國國師、法眼宗二祖德韶的協助,“有傳天臺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寢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于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赍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3]。另如《宋高僧傳·義寂傳》也強調了德韶的作用,“后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于日本國購獲僅足”[4],可見德韶協助之功。義寂與錢弘俶的相識,也得益于德韶的引薦。關于錢弘俶的遣使,《佛祖統紀》載:“初天臺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云,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5]吳越時期天臺教籍的復歸,為宋代天臺宗的復興奠定了文獻基礎,天臺宗之法脈由是得以賡續。此外,吳越國向日本、高麗求取天臺教籍的舉動也促進了東亞佛教的互動,如宋建隆二年(961),高麗國派諦觀法師(?—約970)奉天臺教籍至螺溪,諦觀得以親聽義寂說法,并以師禮之,這些舉動顯然促進了兩國佛教在學術層面的深入交流。
吳越國面對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的局面,采取“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政策,在風雨飄搖的動亂時勢之中,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緊密聯系,為吳越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同時,吳越國也在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與文脈的賡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吳越文化既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又在其獨特的地域環境與人文歷史中形成了吳越特色,折射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與包容性。吳越國時期的佛教文化與藝術,上承晚唐之風,下開宋韻文化之源,既是吳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文明與文化傳統連綿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之呈現。
[1] 參見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291頁。
[2]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鑒小組”校點:《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七《后唐紀六》,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9冊,第9066頁。
[3] 錢文選輯:《錢氏家乘》卷六《家訓·武肅王遺訓》,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頁。
[4] 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8頁。
[1] 參見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第47—70頁。
[2]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十三《后唐杭州龍冊寺道怤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10頁。
[3]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十六《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第402頁。
[4] 潛說友纂:《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佛塔·六和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冊,第2997頁。
[5]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十三《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道潛)》,第316頁。
[6] 參見孫旭:《吳越國杭州佛教發展的特點及原因》,《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7]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版,第397頁。
[1] [美]柯嘉豪:《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導言”,趙悠等譯,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24頁。
[2] 朱彝尊:《書〈錢武肅王造金涂塔事〉》,朱彝尊著,王利民等點校《曝書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
[3] 杜文玉:《吳越國杭州佛寺考—以〈咸淳臨安志〉為中心》,《唐史論叢》第26輯,三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251頁。
[4] 《長阿含經》卷三,佛陀耶舍、竺佛念譯,[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第20頁。
[5] 錢儼撰,李最欣校點:《吳越備史》卷一,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匯編》(10),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6頁。
[1]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394頁。
[2] 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13頁。
[3] 關于吳越國經幢的文獻記載與存世基本情況,參見魏祝挺:《吳越國經幢初步研究》,《東方博物》第61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1—76頁。
[4] 向達:《唐代刊書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36頁。
[1] 辛德勇考辨了中國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年代問題諸說,并且在藤田豐八、禿氏祐祥、向達等學者關于中國的印刷術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術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討論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唐代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指出密教信仰對雕版印刷術的推動作用并考辨相關史實,認為雕版印刷起初的應用范圍,經歷著從密教領域擴充到所有佛教信徒之間,進而再從佛教輻射到基層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一個基本路徑。參見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285頁。
[2] 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242頁。
[3] 志磐:《佛祖統紀》卷八《興道下八祖紀第四》,[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190頁。
[4]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七《大宋天臺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第162頁。
[1] 張風雷認為,天臺宗強調“依妙解以立正行”,圓頓止觀的修習必須以對天臺圓教義理的正確悟解為基礎,只有通達體系龐大的天臺圓教義理,才有可能樹立正確的觀法;此外,就天臺的止觀修習功夫而言,同樣是一個龐大嚴密的觀門系統。概言之,天臺宗的教理與止觀修習實踐,都是不可以離開教典而“別傳”的。參見張風雷:《高麗義通與宋初天臺宗之中興》,《佛學研究》2007年刊。
[2]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七《大宋天臺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第162頁。
[3] 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天臺山德韶國師》,[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1冊,第407頁。
[4] 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卷七《大宋天臺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第162頁。
[5]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394—395頁。
責任編輯:韓澤華
——雷峰塔與吳越國佛教藝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