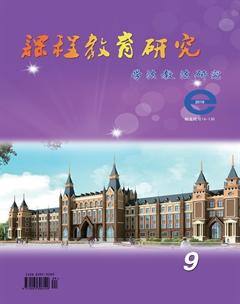高中物理課堂“有效教學”的策略
譚文才
【摘 要】提高課堂教學效益的教學策略有很多種,要根據具體教學內容、教學目標、學生情況、資源條件等具體確定;“追求有效”的反思意識,準確把握課時教學目標,掌握學生情況,優化教學過程,運用評價手段等,是“有效教學”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有效教學;教學反思;過程優化
【中圖分類號】G63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9)09-0171-02
一、學生分析策略
“學生有無進步與發展是教學有沒有效益的惟一指標”,因此,了解學生、熟知學生,是使學生獲得進步與發展、實現“有效教學”的基礎。
學生分析策略是深刻了解學生的途徑和方法,通過對學生的分析,了解學生的學習基礎,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感,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了解學生的個性特點。
通過對學生的分析,不但要掌握全班學生的普遍情況,而且要掌握個別學生的個性差異。只有做到對學生的全面了解,才能恰當地確定教學目標,恰當地選擇教學方式、方法,有針對性、分層次、有成效地實施教學,才能實現“有效教學”。
二、目標分析策略
考察一節課堂教學是“無效”還是“有效”,主要看教學目標的達成情況,否則就沒有意義。因此,通過課前目標分析確定恰當的課時教學目標,是實現“有效教學”的又一關鍵環節。課前目標分析,是指教師在教學準備階段分析課標、分析教材、分析學生,研究制定課時教學目標的過程。具體策略是:
1.將教學目標分解、細化為一個個具體的,能夠操作、易于檢測的學習任務。
舉例:必修2第七章第8節《機械能守恒定律》,對于“能用實例說明機械能和其他形式的能的轉化”這一教學目標,其中“說明”可以具體分為“用語言描述”、“用圖表說明”、“用實驗演示說明”等;而“其他形式的能”可以分解為“電能”、“熱能”、“勢能等,即可形成“機械能”教學單元中多條具體的學習目標。
2.教學目標要明確行為主體、行為動詞、行為條件與表現程度。
行為主體即學習者,行為目標描述的應是學生的行為,而不是教師的行為。規范的行為目標開頭應是“學生應該……”,書面上可以省略,但思想上應牢記,合適的目標是針對特定的學習者的。
行為動詞用以描述學生所形成的可觀察、可測量的具體行為。如寫出、列出、認出、辨別、比較、對比、指明、繪制、解決、背誦等。
行為條件是指影響學生產生學習結果的特定的限制或范圍等,對條件的表述有4種類型:(1)允許或不允許使用輔助手段,如:“可以或不可以帶計算器”。(2)提供信息或提示,如“給定一個物體所處的運動狀態,能確定該物體受力”。(3)時間的限制,如“在10分鐘內,能做完……”。(4)完成行為的情境,如“在課堂討論時,能敘述……要點”。
表現程度指學生對目標所達到的最低表現水準,用以評量學習表現或學習結果所達到的程度。如“至少寫出3種解題方案”、“百分之九十都對”、“完全無誤”等。
上述方法描述的是學生的外顯行為,確定的學習目標比較具體、明確、清晰,也便于觀察和測量。
3.對教學目標進行必要調整,使其更適合學生的學習基礎和學習能力。
在了解學生元認知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尤其在對學生已有知識的了解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目標的修改。如摩擦力一節的教學,初中對摩擦力的概念已經介紹了,摩擦力的主要教學目標應當確立為學生通過觀察演示、實際體驗等方式掌握摩擦力大小和方向,不應糾纏于摩擦力概念的教學。
目標分析策略,可以避免由于教學目標指向不明確,而導致教學偏離方向;也可以避免由于課時教學目標制定得過于空泛,或不切合學生實際,而不能有效達成教學目標,從而避免教學“無效”現象的出現。
三、過程優化策略
優化教學過程是實現課堂教學“有效”的有效手段,“有效教學”是優化教學過程的必然結果,優化教學過程要以教學目標為中心。教學活動的設計、教學方式和方法的選擇、教學資源的整合、教學手段的使用和教學活動的開展等教學過程都必須緊密圍繞教學目標并服從于教學目標的達成,這樣的教學才可能是優化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不斷控制與目標達成無關和不利于目標達成的各種因素的產生,并創造性地引導各種因素向著有利于教學目標達成的方向發展。
優化教學過程要堅持促進學生的發展,既要利于學生的當前發展,又要注重學生的長遠發展。問題設計要有深度,不僅要激發學生積極參與的興趣,更要引發學生深度思考,使之成為學生探究的持續動力。要給學生足夠的學習探究時間,使學生成為信息加工的主體,成為意義的主動構建者。
優化教學過程要注重實效。教師要樹立“有效”意識,在課堂教學中注重“質量”和“效率”,追求高“效益”。處理好形式與內容、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杜絕形式化、避免膚淺化;處理好“預設”與“生成”間的關系,使教學始終圍繞著目標達成逐步深入,實現“有效教學”。
四、課后反思策略
反思是進步的階梯,沒有反思就不可能有進步。實現“有效教學”必須有追求有效的自覺意識,這種意識首先來自對教學的反思。教師要形成課后反思的習慣,每節課后都要反問自己幾個問題:本節課的教學是不是“有效”的?教學目標確定得是否準確,預設目標是否都已達成?教學活動設計得是否合理,學生參與的程度如何?使用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是否合適?對課堂上出現的臨時問題處理得是否恰當?
課后反思既是上一節課的總結,又是下一節課的開始。反思是否及時,是否透徹,反思后是否能夠及時進行調整和修正,是能否逐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實現“有效教學”的關鍵環節。
五、學習評價策略
學習評價策略不是課堂教學評價,課堂教學評價包括對課堂教學的輸入、過程和結果三個方面的綜合評價。
1.在教學準備階段,教師要根據學生應達成的各項學習目標,事先制定評價標準、設計評價工具,并使每位學生都對評價內容和評價標準有所了解,使學生對本節課的學習任務以及通過本節課的學習,應該知道什么、學會做什么,一清二楚。
2.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的學習行為應及時給予評價,以幫助學生改進學習,或激勵學生更好地學習。
參考文獻
[1] [美]加里·D·鮑里奇.有效教學方法(第四版)[M].易東平譯.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2]宋秋前.有效教學的理念與實施策略[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3]高慎英.劉良華.有效教學論[M].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