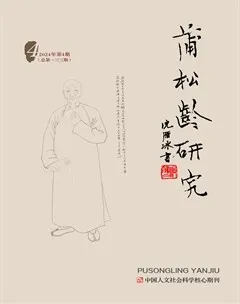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聊齋志異》之“緣情”興寄與“情緣”敘事
摘要:優秀的小說家之創作常基于詩詞、史筆以及議論,使其小說文本兼具詩性之情、史筆之事、哲思之理。《聊齋志異》即是身兼詩人、詞人、小說家多重身份的蒲松齡所創作的優秀小說集,既興發于“緣情而綺靡”的詩性,又以敘述哀怨纏綿的“情緣”故事見長。在《青鳳》《狐夢》《宦娘》《荷花三娘子》《葛巾》《小翠》《辛十四娘》等名篇中,蒲松齡寫出了以書生為代表的男子們與各種花妖狐鬼化身的女性們的相親相愛。這種相親相愛往往始于“緣”,終于“分”。緣起時,男女邂逅,憑著一見如故或一見鐘情,拉開一場場如同《牡丹亭》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序幕;緣斷時,男女往往因某種原因抱憾而散,曲終人不見,令人凄婉傷感。作者筆下種種“情緣”敘事是自我身世身影與心象幻影的詩意投射,既投射出作者關于人間情緣及自身情緣的感受,亦投射出“緣斷情猶在”的人生信念。《聊齋志異》這種兼具傳情性、傳奇性的“情緣”敘事多遵循“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傳統詩道,以凄美為審美格調。
關鍵詞:情緣;緣情;夙分;傳奇;凄美;興寄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在中國文學史上,相對晚熟的小說雖以史家、文家的敘事寫人為主,但其經典佳作卻往往興于“詩”,成于“意”,且又多在敘事寫人中寄寓某種哲思。正如朱光潛所言:“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一部好小說或是一部好戲劇都要當作一首詩看。” [1]349《聊齋志異》既是一部帶有“緣情”詩性的敘事佳作,又是一部長于傳達“情緣”的小說名著。可以說,蒲松齡醉心于“情緣”敘事并借以自我撫慰的內在動因便是揮之不去的“緣來緣去”觀念。由此釀成的“情緣”敘事既撲朔迷離、跌宕起伏,又蕩氣回腸、綺靡凄楚。結合蒲松齡《同畢怡庵綽然堂談狐》那番“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豈必皆游戲?緣來緣去信亦疑,道是西池青鳥使” [2]85的夫子自道,我們可深深地感受到這些悲歡離合故事所蓄積的別樣滋味與況味。
一、《聊齋志異》敘事樂章中回蕩著“緣來緣去”音符
在《聊齋志異》中,各種各樣的狐鬼女子紛紛來到俗界,或為滿足男子們艷遇與狎昵的綺念,或為扮演“賢內助”甚至“賢妻良母”的角色,并被賦予美麗、多情、善良、機智等資質。她們之所以甘愿為滿足男性這些世俗的欲望而不辭勞苦、不計得失,是因為前世早已埋下了一顆顆展開“情緣”敘述的神秘種子。
“雅愛搜神”的蒲松齡從干寶《搜神記》那里吸取了怎樣的敘事寫人法寶?對此,可借楊義論志怪小說之言作回答:“經以人情,緯以神秘,乃是志怪幻想的精髓之所在。” [3]125-126《聊齋志異》中的狐鬼女性常如同巫山神女那樣縹緲,來時讓人莫問來路,并要求男方保守秘密;去時也不告知去處,從而賦予“情緣”敘事以神秘性。
在中國文化中,“緣”,也常被稱為“舊緣”“宿緣”,是維系以男女為主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聊齋志異》敘事樂章中回蕩著“緣來緣去”音符。據統計,該書中曾7次直接以“情緣”一詞來詮釋男女之聚散。具體篇目和使用情形是,《蓮香》寫女鬼李氏有言:“妾為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 ① 表明自己為了情緣,不惜夜奔獻身。《辛十四娘》寫辛十四娘有言:“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感慨自己為了踐行一場情緣,惹來了如此諸多煩惱。《俠女》寫俠女有言:“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言下之意是,男女情緣的斷與不斷皆取決于天數。《阿英》寫鸚鵡化身的阿英有言:“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余,時作一面之會,如何?”阿英明知二人再聚會有災難,提出適時進行“一面之會”,可惜甘玨未能接受阿英這番生離死別前的好言,強行挽留,導致鸚鵡阿英為貍貓所傷,含怨離去。《白于玉》《賈奉雉》《羅剎海市》3篇也分別用到“情緣”一詞。此外,以“緣”字組合的其他詞也出現了70多次。可見,“情緣”或“緣”在小說敘事中的分量。
追蹤中國“情緣”敘寫史,在早期文學創作中,盡管“情緣”觀念尚未形成,但卻已含有關于男女莫名其妙相遇相愛的書寫。如《詩經·國風·鄭風·野有蔓草》有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意思是,有位美麗姑娘,眉目流盼傳情,今日有緣相遇,令人一見傾心。一見面就有好感,看似有幾分輕浮、風流浪漫,但在后人看來,這就是多年修成的“緣”使然。
佛教傳入后,其“五百世冤家”之說又催生了不少以“緣”為基調的文學故事。“締結良緣”觀念最遲在宋代已經頗為流行,無名氏所著的《張協狀元》第十四出有兩句膾炙人口的俗語:“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兩句俗語告訴世人:相逢(包括邂逅)、相識、相戀,突如其來,飄忽而去,不可捉摸,既是一場冥冥之中的注定,又充滿了匪夷所思的變數,仿佛這才是所謂的“真正愛情”。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一曾為張生與鶯鶯見面定調:“與那五百年前疾憎的冤家,正打個照面兒。”在理性主義者看來,男女一見面就彼此歡心,一拍即合,速度過快,有輕薄輕浮之嫌,唯有了解極深、相處極久,才能有情、深情若此。仿佛只有日久生情,才合乎愛情哲學。然而,事實卻是,男女之愛常常會“發乎情,止乎禮”,甚至被“恩愛夫妻不到頭”的魔咒摧毀。更不用說許多看似理性選擇的婚姻亦會遭遇挫折或失敗。每逢此時,人們也會感慨萬端地用“緣分”的到與不到、盡與不盡來解釋或寬慰。
從中國文化與文學傳統看,“緣”“分”以及“緣分”觀念最初生發于儒學,后來在佛學的影響下,得以根深蒂固。徐欣萍曾將“緣分”分為“緣”“分”進行解釋,認為“緣”主要源自佛家因果報償與道家順應自然觀念,間或受到儒家思想影響;而“分”則主要發自儒家凡事盡己及倫理義務觀念。[4]57-97明清文人熱衷于圍繞耐人尋味的“情緣”觀念做文章,以至于出現了《五美緣》《夢中緣》《畫圖緣》《醒世姻緣傳》《意中緣》《鏡花緣》《啼笑因緣》《再生緣》等小說與彈詞,再加《玉嬌梨》又名《雙美奇緣》,《兒女英雄傳》也叫《金玉緣》,《花月痕》亦稱《花月奇緣》等等,可謂“緣來緣去”,形成中國古代小說選材的偏好與敘事的基調。蒲松齡雖未用“緣”字來命名他的小說,卻率先在其小說正文的字里行間高頻率地運用了“緣”“分”以及“情緣”等字詞,并圍繞“緣來緣去”“緣起緣斷”等觀念,敘寫了近百場事出偶然、勢在必然而又聚散隨緣的離合悲歡。他的非凡和高明之處在于,并非僅僅停留于抓取一個個帶有神秘色彩的“緣來緣去”故事做文章,而是注重吸取他的前輩文人湯顯祖《牡丹亭》那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觀念,為各種情緣故事敘述注入了“文情”與“文意”。后來,這種情調或許又直接或間接沾溉了他的晚輩文人洪昇的《長生殿》,使得這部戲劇奏出“只怕無情種,何愁有斷緣”的強音,這仿佛是蒲松齡一度有過的人生之感。
面對一部厚厚的《聊齋志異》,到底應如何尋求觀賞的突破?清代著名評點者但明倫曾針對《雙燈》這篇小說給出過一種答案。這篇小說借助“雙燈”意象,敘述了魏運旺與狐女的一段姻緣故事。故事伊始,狐女款款走上魏運旺所在的閣樓,與他夜夜云雨。何以有如此莫名其妙的艷遇?蓋因有“前因”未了,狐女便須前來“奉事”;綢繆半載之后,狐女決然離去,并留下這樣的理由:“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此中無奈,意味深長。該篇題名“雙燈”,顯示出蒲松齡小說敘事寫人之巧妙精工。故事拉開序幕時,作為意象的雙燈其“來也突焉”,“楚楚若仙”的狐女帶著雙燈突然來到魏生的床前,求得成雙;故事落下帷幕時,雙燈“去也忽焉”,魏運旺“佇立徬徨”。而“雙燈”伴隨了狐女與魏生恩愛半載的夫妻情緣,結尾除了“姻緣定數”的交代,飄然而去的狐女再無其他聲息。對此,但明倫評曰:“有緣麾不去,無緣留不住,一部聊齋,作如是觀;上下古今,俱作如是觀。”這是在告訴讀者,“情緣”是整部《聊齋志異》精彩敘事的密碼,也是其妙筆寫人的機杼。蒲松齡筆下的鬼、狐、仙與人的遇合常不遵循社會的規矩、世俗的禮法而行事,仿佛一切風云變幻都取決于夙緣。
與《雙燈》故事敘述相仿佛,《馮木匠》所敘也是一場艷女夜奔,與馮明寰纏綿數月乃去的凄美故事。女子離去的理由也在一個“緣”字:“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兩情之合離,姻緣之來去,皆聚散不由人。
綜上可見,《聊齋志異》誕生于《牡丹亭》《長生殿》兩部頗重“情緣”的戲曲之間,是基于雄厚的“情緣”“奇緣”文化的積淀。這種敘事格調,是蒲松齡當年“緣來緣去信亦疑,道是西池青鳥使”心境的寫照,是蒲松齡面對慘淡人生而生出的諸多的無奈、太多的無常之心境的詩意映射,也是蒲松齡面向現實世界而其精神與靈魂無處安放的詩性抒寫與哲思寄托。他靠著天才的解悟與妙筆生花的傳達,演奏出一曲曲“情”字當頭、非同凡響的“情緣”故事華章。
二、《聊齋志異》常敘男女初見之“驚艷”
粗略看來,《聊齋志異》像許多描寫戀情發生的文學作品一樣,熱衷于敘寫一見鐘情、一見如故的情緣。然而,與蕓蕓眾作不同的是,《聊齋志異》善于使男女一見鐘情那令人刻骨銘心的“銷魂瞬間”,開啟于某種較為獨到的“驚艷”觀感,我們可將其視作“眼緣”。
“眼緣”一詞,本指眼睛的邊緣,現常指男女初次見面就對眼、順眼,一見面就有好感,英文原為eyes-affinity。對此,吳慧平《“眼緣”及其他》與康健、李景艷《試析“眼緣”詞義變化及其流行用法》二文均予以認同并引用,且后者進一步指出:“(眼緣)是一種通過眼睛所看從而獲得的一種感知,‘緣’字的詞素義由‘物之邊緣’轉移到‘機緣,緣分’,側重于一種較為抽象的心理感受。‘眼緣’也隨著‘緣’字義項的轉移延伸出新的義項。” [5]雖然“眼緣”是一個現代詞,但“眼緣”命題早已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佛法所說的“眼緣色境”,意為人與人見面第一好感印象,無非觸發于愛美悅色。人們常將其定義或概括為“一見鐘情”。這種情愛反應盡管備受質疑,備受爭議,卻又能代代相傳,相當于古代戲劇中經常呈現的“驚艷”一幕,富有審美生命力。《聊齋志異》寫戀情之所以令人心往神馳,一個原因便是富有包孕性的“眼緣”敘述頗能激發閱讀興味。
中國文學作品寫“眼緣”特別傳神者,當數《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戲所敘“驚艷”。寫張生與鶯鶯,一個是癡情的風魔漢,一個是美若天仙的佳人,這對五百年前的風流冤家陡然乍見,便引發出一場風流浪漫。尤其是鶯鶯“臨去秋波那一轉”,令張生神魂顛倒,相思成疾。明代“三言”“二拍”等小說敘述男女情緣,雙方一見面常發生“四目相視,俱各有情”的雙向互動,同樣是眼緣的作用。清代《聊齋志異》寫男女情緣,則更像明代湯顯祖《牡丹亭》寫柳夢梅、杜麗娘的情緣那般,格調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先看《嬰寧》寫書生王子服在“游女如云”中,偶爾看到嬰寧,“拈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遂“注目不移”,目不轉睛地注視對方,一見面便忘情。“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王子服那明亮而滾燙的目光,讓嬰寧感到“目灼灼似賊”。待嬰寧遠去后,王子服“神魂喪失,怏怏遂返”。王陽明曾有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蒲松齡筆下的王子服不僅有一雙愛美悅色的“賊眼”,而且有一顆敢于追求的“賊心”“賊膽”,竟然在經過一場相思之后,只身到南山尋訪自己的意中人。第二次見面時:“生無語,目注嬰寧,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兩次邂逅,全靠眉目傳情表達愛慕。如此經典的敘述,實是作者蒲松齡情懷的寄寓,因而在小說最后,作者竟直呼“我嬰寧”,足見作者對自己喜歡的可愛女子之傾情。眼觀對方,不僅限于一次書寫,這是《嬰寧》敘事技巧推陳出新的表現。讀罷《嬰寧》,我們再看《織成》,該小說寫柳生再見織成時,仿佛精魂出竅,“徘徊凝注”,故引來女方如此戲謔:“耽耽注目,生平所未見耶?”如此目不轉睛地深情相看,好像平生沒見過一般。這種責問很逗情,不僅搔到了當事人心癢之處,也撥動了讀者的心弦。
《聊齋志異》所敘“眼緣”,似乎兩性有別。如果說,男性大多是“注目不移”“狂顧”式的,正視之中含有神魂顛倒之情,那么,女性則往往是“斜瞬”“顧盼”,非正眼看,顯出“驚鴻一瞥”“秋波送嬌”之態。如,《邵女》寫男主角柴廷賓,見到邵九娘:“偶會友人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為邵氏。”男性的狂顧,女性的秋波斜轉,有效地碰撞在一起,成就了一場奇緣。《花姑子》寫安幼輿與香獐精花姑子初次見面的情景就較為旖旎:“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這位帶著餐具出場的花姑子,也是“秋波斜盼”,給安生類乎天仙的好感。接下來,寫行酒場景,也是一番眉目傳情:“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花姑子的“嫣然含笑”,引發出安生“注目情動”。故趁花姑子父親離席,安生開始尋隙調戲。面對安幼輿突如其來的無禮舉動,花姑子警覺地抗拒了安生的粗暴接觸;當父親來問究竟時,她又巧妙掩飾。正是那份從容而機靈的掩飾,更令安生增添了好感,乃至于“魂魄顛倒,喪所懷來”。隨后,小說繼續寫花姑子深夜探訪,用自己所攜“蒸餅”,救好了安生的相思病,并發生了一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的甜蜜戀情。花姑子被父親帶走后,安生四處尋訪花姑子,不料誤入蛇精假冒花姑子的圈套。蛇精以“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等甜言蜜語誘騙,致使安生中毒,生命岌岌可危。又是幸得花姑子及時趕來,想方設法使安生起死回生。在這場悲歡離合的奇緣敘事中,除了巧于掩飾、蒸餅救治等環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男女雙方一“注目情動”、一“秋波斜盼”的脈脈含情眼神更令人過目不忘。
在蒲松齡這位多情多才的小說家筆下,男女不期而遇的眼神盡管并非千篇一律,但脈脈含情、愛美悅色卻是一致的。人們常拿宋代以來流行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① 這句諺語來詮釋審美之道或美學原理,強調美不美,脈脈含情的“眼緣”具有決定意義。當今學者常把“情人眼里出西施”與“美”“愛”聯系起來闡釋,劉旭光認為:“西施或許是個幻相,但這個幻相產生的原因,卻是‘愛’,而愛這個行為,并不僅僅是主觀情感的投射,它包含著對客體存在的肯定,對客體某種性狀的贊同。” [6]《聊齋志異》所敘男性眼里的花妖狐魅之所以被視為夢中情人或紅顏知己,首先是因為她們既“美”且“有情”,遂令男子哪怕是僅僅一瞥,便過目不忘。
在《聊齋志異》世界里,男性角色對突如其來的美人“狂顧”“注目”,即時擦出愛的火花,常常是“情緣”敘述之始。憑著各種“眼緣”,男女主人公往往來不及履行或索性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清規戒律,就急不可耐地進入“狎昵”狂歡。
三、《聊齋志異》“情緣”敘事多以“緣情綺靡”詩性為底色
“情緣”敘事在蒲松齡生活年代前后的小說世界里已經較為廣泛地出現,且有所總結。明末馮夢龍編《情史類略》,繼“貞”類之后,便列出“緣”類,又將其細分為意外夫婦(妻)、老而娶者、妻自擇夫、夫婦重逢四類,旨在“令人知命”。[7]99-185蒲松齡兼具詩人和小說家身份,其《聊齋志異》中的很多故事其實都是他為了抒發某種情感而作。或者說,“傳情”成就了《聊齋志異》的“文心”和“詩心”。
在繼承屈原楚辭凄婉哀怨創作風格的基礎上,《聊齋志異》“情緣”敘事中的幸福快活音符多伴以琴棋書畫、詩酒風流,體現了耐人尋味的文人情調。關于《聊齋志異》的創作之道及其性質,蒲松齡在其《聊齋自志》中說:“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對這段耳熟能詳的作者告白,人們多從取材方面解讀,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齡先說從屈原、李賀兩位詩人那里吸取靈氣和妙音,自然使小說帶有“緣情而綺靡”的詩性;然后才說接受干寶、蘇軾的敘事意趣與興味。后面,作者更是明確強調其筆法上的“寄托如此”,強調所成就的是一部“孤憤之書”,都是在傳遞這部小說內在的“詩性”蘊涵。
在《聊齋志異》的情緣世界里,“情”字當頭,“夢”字托底,其間不乏傷感。《聊齋志異》之“聊”不是聊天之“聊”,是“聊慰寂寞”之“聊”,是“姑妄言之姑聽之”之姑且;所謂“異”不僅指“異域”鬼怪之“異”,而且指“心存遐想”的異想天開之“異”。《聊齋志異》看似帶有游戲色彩的傳奇故事背后,實際上是用奇幻的筆法表達人生感悟。蒲松齡《堤上作》詩云:“獨上長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計全非。聽敲窗雨憐新夢,逢故鄉人疑乍歸。”思鄉惆悵兼自傷身世。其《感憤》更是寫道:“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斗酒難消磊塊愁。”漂泊的身世,哀怨的心境,只好寄托于《聊齋志異》鬼狐敘寫。總之,《聊齋志異》“情緣”敘事中的“新夢”與“舊夢”變奏,仿佛《紅樓夢》中的“新愁”與“舊愁”更迭,讓人一唱三嘆。
《聊齋志異》情緣世界中充滿詩情畫意,艷妻或膩友,愛情或友情,令人流連忘返。蒲松齡在《嬌娜》篇末贊嘆:“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饑,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所謂“色授魂與”,是一種心靈上的默契,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比“顛倒衣裳”的肉體欲望更難能可貴。蒲松齡伴隨著他由衷羨慕的主人公慕蟾宮、溫如春,一度陶醉在《白秋練》那清越優雅的吟詩聲中,沉迷在《宦娘》那“和風自來”“百鳥群集”的琴聲里,心靈受到陶洗,生活得以詩情畫意,這些消解了他現實世界的不適,令其在精神的世界里得以圓融。《青鳳》所寫男女“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是出于一場“眼緣”:“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這種見色生情的狂妄之言也許正是作者的心聲,寧要美人,不要高位,情場得意足可補償仕途失意。耿去病狂則狂矣,貴在多情、癡情。這次見面后,青鳳的叔母“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搴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于青鳳也”,“不能忘情”說的是耿去病對青鳳一見鐘情后的堅持。一年后,二人再次邂逅,“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阘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自此,二人開啟了一段夫妻生活。更為傳奇的是,兩年后,青鳳的叔父也被一個姓莫的人獵捕,他事先預感此禍,就托兒子向耿生求救,最終一家人喜獲團圓。《云翠仙》的“異史氏曰”再次以夫子自道的方式吐露了這種心聲:“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若能得一嬌妻,便是拿皇帝高位都不換,再次發出愛美人勝過愛江山之嘆。
蒲松齡除了將濁氣濃郁的官場、烏煙瘴氣的科場寫得淋漓盡致,還將各種柔情繾綣的情場寫得纏綿悱惻。這種“情緣”的走勢又常常根據女性是“狐”是“鬼”而有所分辨。一種是男子與女鬼藝術化的風雅情緣,人鬼情緣中,女鬼可以死而復生,與男子歷經磨難而善始善終;另一種是狐女承擔了進入俗世的代價,人狐婚戀中,狐女往往為了一種使命含辛茹苦,雖始于姻緣夙分,最終卻因狐女心灰意冷,選擇逃離,導致“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當然,《聊齋志異》中的一些篇章就是以某個詩句為“詩心”的。比如《錦瑟》是據李商隱的詩句生發而成;《宦娘》則是對《詩經》“琴瑟友之”的完美詮釋,同時表達了作者對知己之情的向往。
基于以上各種因素,我們要洞察“緣情而綺靡”的《聊齋志異》“情緣”敘事,應該進一步分而論之。
第一種情況,《聊齋志異》敘寫人鬼情緣往往寄寓藝術化的人生體驗,男女來往往往能自由自在,結局悲喜不一。以《連瑣》《宦娘》為代表。
在《聊齋志異》的鬼女“情緣”敘事中,器樂藝術成為其中一大要素。《連瑣》寫女鬼連瑣與書生楊于畏的戀情,極富詩意性。蒲松齡沒有讓男女情緣流于淺浮,而是筆鋒一轉,寫他們步入風雅而浪漫的交往。在挑燈會晤之夜,連瑣與楊生談詩論文,琵琶傳情,共同的興趣消除了二者的距離,他們的感情得以驟然升溫。連瑣“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弦索”。從其所作《蕉窗零雨》之曲中可以看出,連瑣才藝雙全,多情善解。在詩情畫意中,兩顆心靈在碰撞,其樂融融,以至于“挑燈作劇,樂輒忘曉”,度過了一段“剪燭西窗,如得良友”“兩人歡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于畫眉者”的生活。連瑣一再叮囑楊于畏:“君秘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樂器暴露了兩人的秘密。在薛生的一再追問下,誠實的楊生“不得以告”,終于說出了他和連瑣交往的事。最后,經過危難的考驗,連瑣與楊生的情感也得到升華。這是湯顯祖《牡丹亭》“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戲劇的重演。連瑣得以起死回生,終于從如夢的二十年鬼蜮世界返回到她眷戀的現實人間。結尾,作者不再交代式地寫出人物死生相隔的命運或花好月圓的結局,而是以連瑣的“二十余年如一夢耳”一聲嘆息作結,讀來余韻繚繞。吹拉彈唱藝術在小說“情緣”敘事中洋溢,倍添溫馨浪漫。
我們再看《宦娘》,該小說寫知音之戀,充滿著浪漫、哀怨的詩意性。故事發生于一個雨夜,“少癖嗜琴”的溫如春借宿于一老太太家,對她的侄女宦娘一見鐘情,系情殊深。溫如春提出要結親,可老太太表示非常為難,“溫問其故,但云難言”。為什么“難言”,老太太沒解釋,作者也沒交代。后溫如春求娶同樣喜琴的良工為妻,良工有意,奈何其父葛公不允,溫如春從此便“絕跡于葛氏之門”。后來,葛家便發生了三件奇事:一是良工在花園里拾到了一張抒寫少女懷春之情的《惜馀春》詞;二是前來“問名”的劉公子遺“女舄一鉤”(女鞋一只),葛公厭惡他的輕薄,拒絕了劉公子的提親;三是溫家的菊花“忽有一二株化為綠”,而這種綠瓣的菊花本來只有良工的深閨中才有,同時,溫如春在自己的花圃邊也撿到了葛公已經燒掉的《惜馀春》詞。有關情詞、女舄、綠菊等三件事發生得撲朔迷離,極其巧合。以致讓葛公誤認為女兒與溫生偷情,便只好決定將良工嫁給溫如春。兩人喜結良緣后,情詞為何人所寫、女舄自何而來、溫家的綠菊是怎樣變綠的,在讀者心里仍是個謎,就連溫如春與良工也“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直至宦娘被迫在古鏡下現身,這些疑團才被徹底解開。原來,溫如春遇雨借宿之夜,生前以未諳琴技為憾的宦娘喜歡上溫如春;良工由于酷愛音樂而對溫如春非常傾心;宦娘助人為樂,暗中成全這一對嗜琴的“知音”。小說結尾,宦娘在辭別小夫妻倆時說,他們倆日后如能在快意時對著她的小像“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她就非常滿足了。從結構上看,這段奇緣“以琴起,以琴結,脈絡貫通,始終一線”,開篇溫如春嗜琴而得以學藝于道人,絕技成而得以識宦娘,中間彈琴又使良工芳心暗許,宦娘則牽線搭橋成就溫如春、良工琴瑟之好,最后宦娘授溫如春小像,使其常常焚香對彈。從始至終,以“琴”為線貫穿全文。“琴”乃是古代文化的一個標志性意象,自從有了“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故事,它就成了知音的代名詞,《宦娘》中以“琴”為線索敘述溫如春與宦娘、良工的愛情,其中也蘊含著尋覓知音的情感。這種感情,仿佛是蒲松齡的隱情“自述”。尤其這篇小說中的《惜馀春》詞最能反映作者對知己的渴求,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刬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里,度將昏曉!" 今日個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該詞雖是宦娘所作,其后卻又出現在良工住所,詞中所表達的情感是二人共有的。細心的讀者已經發現這首詞同時見于《聊齋詞集》,顯然是蒲松齡直接將自己的詞心移諸故事人物宦娘名下。且在結尾,小說又敘述宦娘在幫助溫如春和良工喜結良緣后,謝絕了他們的挽留,“出門遂沒”。對于這樣的戛然而止,馮鎮巒評曰:“結得飄渺不盡,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確,除了凄冷的別離之感,如此帶有幾分傳奇性的“情緣”敘事也精彩演繹了陶淵明的詩意:“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聊齋志異》的“情緣”敘事將詩性的傳情與戲曲小說的傳奇合而為一,形成幽怨哀傷、纏綿悱惻的優美篇章。
第二種情況,相對于人鬼故事的詩意風流,《聊齋志異》中的人狐故事多以狐女來到世俗人間,經歷煩惱,艱難曲折,最終離散為結局,可謂“煩惱人生”。其以《小翠》《辛十四娘》《云翠仙》等小說為代表。
《小翠》寫王元豐與小翠的情緣緣于一場報恩。越人王太常有一子“名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太常為此憂慮不已,他曾救助過的狐仙為報恩,將女兒小翠嫁給了他的兒子元豐。婚后,生性活潑的小翠十分擅長戲謔,終日和元豐以及丫頭們一起嬉戲玩耍:“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為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幾弄帶,不懼,亦不言……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蒲松齡以“刺”“蹋”“著”“蹴”寫出了小翠的活潑可愛,而“弄”字則寫出了她對婆婆的責罵毫不在乎。然而,當丈夫被責罵時,小翠心疼了,“女始色變,屈膝乞宥”祈求夫人寬恕,寥寥數語便寫出了小翠的善良與多情。后來,小翠將王太常癡呆兒子治好,卻因打碎玉瓶遭到責罵,才道出自己的身份和報恩的究竟。蒲松齡寫小翠與王元豐的情緣可謂一波三折,曲折離奇的故事之下,緣分具有決定意義。
《辛十四娘》則敘述另一場情緣之殤。這篇小說哀傷沉重的敘事基調,可以從辛十四娘的“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感嘆看出。主體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敘述馮生遇艷并狂熱地求娶狐女辛十四娘的故事;后半部分主要敘述辛十四娘嫁給馮生后,憑著聰慧和識見勸丈夫慎于交友,并在馮生身陷囹圄后用心搭救的故事。小說敘述馮生遇艷、獲艷的經過,曲曲折折,饒有林泉丘壑之美。其中,后半部分敘寫辛十四娘一波三折的辛勤持家之功。面對狡詐陰險的楚公子,辛十四娘勸告馮生盡量不要與此類“猿睛鷹準”的人來往。馮生盡管表示言聽計從,但又受不了楚公子再次登門時的激將奚落,難以割舍交結之意。沒過多久,辛十四娘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原來楚公子一直對馮生的“嘲慢”耿耿于懷,蓄意報復馮生,尋機將馮生灌醉,誣陷他強奸殺人。免不了又是勞苦辛十四娘想法營救。經此一劫,馮生由此悟出交友宜慎之道。正當他痛改前非之時,辛十四娘卻忽然作別,說出了一番深情而沉重的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并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訴。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由此看來,辛十四娘后悔為情緣而遭遇煩惱,再加世情冷漠,人性險惡,不免悲觀厭世,況且已為夫君選好了配偶,是該離開了。小說寫辛十四娘與馮生的患難之情,突出了辛十四娘的賢惠與識見,其格調類似于話本小說反復宣揚的“有智婦人,賽過男子”這一主題。《辛十四娘》在貌似平常的婚戀敘事中,寄寓了作者對人生的感悟:既能直面世態人情,寫出了世情冷暖,并包含著“酒能誤事”“禍從口出”等人生經驗;又不免過于倚重辛十四娘式的女性智慧,顯示出男性對女性“賢內助”角色的期待。莊子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這也許正是辛十四娘式的傳統女子飽經滄桑而得以超脫的最好闡釋。
《云翠仙》未言明云翠仙具體是什么神仙,她的出現是為了誡勉梁有才那般“嗜賭”的丈夫。梁有才通過巧言令色騙得云翠仙母親的信任,一旦得到云翠仙,便“由此坐溫飽,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最終在一群賭友的鼓動下,竟然打起了賣掉云翠仙以付賭資的主意。梁有才這種對“情緣”如此不珍惜的男性角色,作者給他安排了終得惡果的結局。
從深層次上看,《聊齋志異》的“情緣”敘事也傳達了這樣的感喟:古代賢惠女子似乎永遠沒有享受幸福的福分,因為她們要肩負起男性不堪重負的社會責任。而每到苦盡甘來之時,也許就是她們失望離去之期。
第三種情況,小說敘狐鬼輪流與男子柔情繾綣,以歷經曲折而享受人生美滿為結局。
在古代,文人熱衷于“紅袖添香夜讀書”,將女性的“伴讀”視為津津樂道的風流雅事。讀《聊齋志異》,我們隨處可見這樣的鏡頭。如蒲松齡依據《桑生傳》敷演新篇,敘寫一狐一鬼共嫁桑生的故事,題名《蓮香》。作者既寫出了一狐一鬼輪番結交桑生的喜怒哀樂,又寫出了他們之間為追求真愛所達到的“生生死死隨人愿”的人生境界。《蓮香》寫狐女蓮香“夜來扣齋”,與桑生“息燭登床,綢繆甚至”;后來,女鬼李氏又翩然而入,而桑生面對接連到來的美女,不僅不拒絕,而且還不顧蓮香的危言勸阻,“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欲兼有“雙美”而后快。桑生這種心態雖然還不能說就是蒲松齡內在情感的外化,但至少已打上了其意趣的烙印。女鬼李氏所言:“妾為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愿常侍枕席。”強調了男男女女得以相處,之所以歷盡艱難心不變,全賴“情緣”的力量。
《聊齋志異》所敘“情緣”既浪漫,又傷感。多數情緣為世俗所不容,乃至于中斷。即使緣斷,仍情意綿綿。蒲公以其生花妙筆講述了一幕幕人鬼(狐)“不了情”“未了緣”,在感動你我的同時,更告訴了世人什么是情緣的真諦。借用洪昇《長生殿》中的一句話說:“只怕無情種,何愁有斷緣。”有些人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其實就是“窮書生的意淫”,這樣的論調大概是出于對其生活境遇和人生經歷的通觀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聊齋志異》就是一部“緣情”“寫心”之作,作者善于通過“情緣”敘事,投射自己百無聊賴的心影,傳達借紅巾翠袖療救心靈傷痕的心聲。
四、《聊齋志異》善以“情緣”敘事寄寓詞家傷心懷抱
蒲松齡也是一個詞人,廣義上,詞屬于詩而更具“緣情綺靡”特質,因情緣而“傷心”是宋代詞人敘事抒情的基本格調。而宋代詞人的“傷心”又得到清代文人的會心評判。馮煦在《蒿庵詞論》指出:“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 [8]60把秦觀、晏幾道視為古代傷心人的代表。傷心人自有療傷的方法,那就是借寫艷情抒寫身世之感和憂傷懷抱。因而,周濟在《宋四家詞選》中評價秦觀的《滿庭芳》一詞說:“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又是一法。” [9]1652將落魄潦倒的身世之悲寄托于香艷的情感,是古往今來文人聊以自慰、借以意淫的慣用策略。就連英雄詞人辛棄疾也未免如此,因而梁啟超曾評價他的《青玉案·元夕》說:“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 [10]813除了詞人擅長借“情緣”敘事傳達“傷心”之感,小說家更是擅此道。身為詩人、詞人的蒲松齡可謂是古往今來以小說敘寫“傷心”懷抱的杰出代表,他將源源不斷的無限“傷情”寄托于他敘寫“情緣”的小說之中。
蒲松齡畢生熱衷科舉,屢敗屢戰,屢屢落第。原因是復雜的,其中答案之一應是,盤桓于他心頭的“緣來緣去”幾乎擠占了他興趣的全部。科舉仕進的“正途”抵擋不住不務正業的“情緣”誘惑,這“情緣”又恰恰為慰藉現實世界的失落而生。在他構想的故事中,各色人物常為某種感動人心的情緣而來。花妖狐魅富有人情味,人類之中卻不乏禽獸野性。二者的錯位顛倒,激發起小說家投身到奇中含情、幻中寓理的傳奇性敘事中。在《聊齋志異》的世界里,所謂“傳奇性”,并非靠大起大落、匪夷所思取勝,而是靠情意綿綿增加吸引力。從根本上而言,陌生化的傳奇性,就是蒲松齡所熱衷記錄的“異”。既是遷想妙得、荒誕不經,又符合人間事理常情。關于《聊齋志異》這部書的“孤憤”性質,蒲松齡曾坦言,它是有寄托的,正所謂:“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用以寄托的載體,主要是“情緣”敘事,即借紅顏佳麗的溫情,實現失意文人的自我設計,是一種“窮而后幻”的精神療救。由其小說的字里行間,我們能感受到,蒲松齡不是一個甘于寂寞的人,他平生都在尋找知己。然而,其《偶感》一詩卻發出“此生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的感嘆。據考察,蒲松齡一生,幸遇多才多藝的紅顏知己顧青霞。然而,他們不僅不能朝暮相處,而且又遭遇紅顏薄命。關于蒲松齡與顧青霞的交往及彼此情感,袁世碩在《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齊魯書社1988年版)、馬瑞芳在《狐鬼與人間——解讀奇書聊齋志異》(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中都進行過翔實的考證。孫啟新《也談顧青霞》又對顧青霞的一生及其與蒲松齡之間的交情作過評述。[11]這種知己之感與人生遺憾對蒲松齡的影響是深遠的,乃至于他對能否得到“知音”一度失去了信心。《聊齋自志》最末留下的是“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的困惑。現實世界里知己難求,“情緣”難寄,只能到異想天開的文學世界里尋求補救。
在《聊齋志異》“情緣”世界里,“情”字當頭,“夢”字托底,其間不乏傷感。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由性愛心理形成的人生夢幻感讓人如癡如醉、似夢似幻,作者至少兩次用到“夢幻”一詞。蒲松齡還有一首詩題名《夢幻八十韻》,“夢幻”字眼赫然入目;有一篇文《代信侯侄祭蘇若佩文》寫道:“理數渺其難窺兮,似浮云之與水月,華屋紛而零落兮,亦夢幻之與花空。”可見,“夢幻”時常浮上蒲松齡心頭。過眼煙云般的夢幻終會破滅,破滅帶來的常是心灰意冷。此前,明代董說的《西游補》第一回曾感嘆:“總見世界情緣,多是浮云夢幻。”可見,夢幻又是超凡脫俗、無可奈何的。相對而言,《聊齋志異》的夢幻執著于現實人生,帶有世俗性。其后,《紅樓夢》不僅以“夢”為名“大旨談情”,“情”“夢”意識非常鮮明,而且于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說:“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提出了“夢幻情緣”這一命題。
無論如何,《聊齋志異》“情緣”敘事是畢竟聊慰寂寞的一劑良藥。這類故事中的男子相貌均較模糊,身份卻頗明了,大多是蒲松齡式的落拓不得志、窮困潦倒的清貧書生。他們或孤燈冷案,獨居荒園;或落魄途窮,寄人籬下,卻未能免除向往功名富貴、愛美悅色的俗情。作為落寞書生,蒲松齡的心境正如他在《大江東去寄王如水》中所說的:“糊眼冬烘鬼夢時,憎命文章難恃。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復爾爾。”一方面坦然承認“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另一方面又為超凡脫俗奮力自拔,竭力規避“俗不可耐”。從《沂水秀才》這篇小說以“俗不可耐”“秀才裝名士”等譏諷沂水秀才來看,兩位狐女風雅可人,正是聊齋先生的白日夢;《嘉平公子》寫嘉平公子長得風儀秀美,與溫姬緣來緣去,未能善始善終,原因在于嘉平公子胸無點墨,不夠“風雅”;《云蘿公主》寫云蘿公主與安大業結合,六年為期,源自安大業主動選擇的俗人之路。總之,在《聊齋志異》所敘的狐妖精魅的世界里,落寞才子常常于夜深人靜時,艷遇花容月貌女,形成一道道以“情緣”為主調的癡心妄想。通過“情緣”書寫和人生之感的“寄托”,蒲松齡的才情得到釋放,其躁動的靈魂也同時得以安放。
從跨文類視角看,蒲松齡以詩家筆意寫《聊齋志異》,尤其是在傳奇化“情緣”敘事上實現了筆法、筆勢、筆意的新跨越,即“由簡單機械到繁復多姿的藝術技巧推進;更為重要的是在形式之外的精神價值遞增,從單純的以詩詞輔助敘事、填補結構到將身世之感、孤憤之意融入虛幻的故事加以充分彰顯,再到跨越文體、文本與人物類型的詩性交融” [12],不再停留于句法、文法的簡單套用,而是注重從精神命脈上實現脫胎換骨。
從歷史的時空和文化語境看,在蒲松齡生活的天地里,明代戲曲小說關于姻緣天定、前定等宿命觀念,想必還在流播回蕩著。湯顯祖《牡丹亭》第十出借后花園花神之言:“因杜知府小姐麗娘與柳夢梅秀才,后日有姻緣之分。杜小姐游春感傷,致使柳秀才入夢。”賦予柳夢梅與杜麗娘之情以“姻緣之分”。另外,吳炳《綠牡丹》寫謝英和車靜芳、顧粲與沈婉娥兩對才子佳人的姻緣,其第三出也有所謂的:“姻緣姻緣,事非偶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無名氏(后署“無心子”)《金雀記》寫晉潘岳才高貌美,王孫之女井文鸞以金雀擲贈之,因成良緣,其第七出也有所謂的:“始信姻緣非偶,天意有在矣。”徐復祚《紅梨記》寫北宋時期才子趙汝舟與妓女謝素秋的離合情緣,其第三出更是唱道:“今日相逢,實為天作之合。”在這樣的語境下,對于一個富有天才想象力的小說家來說,蒲松齡也曾直面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的“影響的焦慮”。他和其后的紀昀、袁枚都樂于通過寫狐鬼來寄托情感,排遣人生煩惱;他們也都樂于選取花妖狐魅的故事來講,且都關注到“緣”這一故事核心。然而,無論是風流倜儻的紀曉嵐,還是情根深種的袁枚,卻未能把故事講得那么精彩。原因為何?答曰:取決于有無抓住“文意”“文情”等小說根本。《聊齋志異》之“情緣”敘事,上通明代《牡丹亭》以及各類才子佳人戲曲小說之姻緣敘事,下啟《紅樓夢》等一系列戲曲小說之情感敘事。其中,清代津門李慶辰仿《聊齋志異》創作了一部《醉茶志怪》(又名《奇奇怪怪》),庸叟楊光儀為其作序說:“竊謂著述家之有說部,誠以蘊蓄于中者,既富且久,而長此寂寐,無以自達,不得已寄情兒女,托興鬼狐,子虛烏有,感觸萬端,其志亦可悲矣!” [13]1意為追隨《聊齋志異》“情緣”敘事之“寄情兒女,托興鬼狐”,且以“悲”為審美格調。再者,《紅樓夢》的評點者脂硯齋更是曾借“頑石草木為偶”評說道:“歷盡風月波瀾,嘗遍情緣滋味,至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 [14]9在脂硯齋看來,《紅樓夢》所傳達的是作者歷遍“情緣滋味”的人生之感,更是作者“胸中悒郁”之宣泄。
將身世之感寄托于艷情,《聊齋志異》可謂承前啟后。可以說,在“天緣”宿命敘述中,《聊齋志異》與《紅樓夢》,二者一前一后、一文一白,遙相呼應,共同成就了清代小說關于“情”“夢”敘事之瑰麗。
五、《聊齋志異》“情緣”敘事中的定數觀及其凄美感
在《聊齋志異》世界里,我們常常讀到時過境遷后狐女的聲聲長嘆:“緣分盡矣!”仿佛人仙情緣注定不能天長地久,只能限于“曾經擁有”。因為,期限已到,女仙們就要離去。《鳳仙》《狐夢》如此,《小翠》《辛十四娘》無不如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聊齋志異》“情緣”敘事中,“緣分”是“緣斷”無可奈何的理由或精美漂亮的借口。
中國古代小說所敘男女角色的緣結定分、悲歡離合,往往遵從命運安排,身不由己、合于命數,甚至有一定的期限。李海超《情緣論:情感本源的機緣化闡釋》認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機緣”一詞為佛家使用得最多,其含義是受教者自身的根基(即“機”)與施教者的因緣(即“緣”)的結合。后用來泛指各種機會、緣分、際遇等。不過,“機”與“緣”這兩字相應的含義,其實是漢語從來就有的。“機”與“緣”的結合,固然是佛家的一種創造性的運用,但其文字含義,并非全部來自佛家的發明。我們今天用“機緣”這一術語反過來講儒家的傳統,不能說完全是借鑒了佛家的觀念。況且,我們所講的“機緣”在根本上是一種“情緣”,對情感本源地位的肯定,自與佛家學說有根本差異。“任何一種情緣都是人的某種際遇的情感反映,而任何一種際遇,對主體來說既是‘機遇’,也是‘遭遇’。”如果說,機遇是好的開始,那么,遭遇便意味著不能善始善終。“是情感造就了機緣,無情不成緣,也可以說,情感正是一切機緣中的第一機緣。發揮機緣作用的情感即是‘情緣’。” [15]169-182《聊齋志異》的“情緣”敘事有“機遇”的成分,又有“遭遇”動勢,二者合成因緣際遇。雖懷才不遇,卻蕩氣回腸,士不遇之缺憾靠艷遇補償。
據統計,《聊齋志異》中與“緣”相關聯的“夙分”一詞出現過8次。《胡四姐》寫胡三姐被拒之門外,抱怨胡四姐取代自己,說:“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蓮花公主》寫膠州竇旭“晝寢”時,被一褐衣人邀至一富麗堂皇的“桂府”,殿上大王與之相見,感嘆“忝近芳鄰,緣即至深”,在吟詩答對中,竇旭因“君子愛蓮花”答對,又引起大王“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的感嘆。《阿繡》寫狐女幻化成阿繡被發現破綻,無奈地對劉子固說:“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夙分耳。”除了蒲松齡,信緣信命的定數思維和宿命觀在清代文人群體中較為普遍。紀昀也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常常傳達出“夙緣”觀念,在自題小詩中,他表明其寫作意圖就在于證實因果、緣分之不妄:“前因后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16]9紀昀鐘愛運用佛教因果觀念寫出諸多傳達人情世故的鬼怪故事。如《灤陽消夏錄》有一段文字記周虎與一狐仙燕婉相處二十載的故事,后狐仙忽然絕去,突如其來,不為別的,只是因為緣分已了:“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 [16]22可見,處江湖之遠的蒲松齡與居廟堂之高的紀昀都有一顆以因緣果報來勸世的婆心,只是筆法不一,效果有差。
同時,《聊齋志異》的各種“情緣”敘事常常帶有“命數”與“定分”等觀念。其中,《荷花三娘子》寫荷花三娘子最后的留言是:“聚必有散,固是常也。”《狐夢》敘述了畢怡庵與狐女的“夙緣”,寫“狐癡”的意外艷遇,終因泄密終止了這場嬉鬧。不獨人狐戀如此凄美,《葛巾》寫人與花妖,因為男主人公心生懷疑而導致緣斷。該小說結尾一段寫道:“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并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后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可見,在《聊齋志異》的“情緣”敘事中,因緣而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詩化的緣分又常常走向煙消云散。既有“好事者”的提醒與作梗等因素,也有世俗偏見毀壞與拆散的力量,還由泄密、疑猜等人性缺陷導致。再看《嫦娥》,寫嫦娥嫁給宗子美,既給他帶來富足的生活,也給他帶來精彩有趣的人生體驗。一天,家中忽然來了強盜,將嫦娥搶走了。歷經曲折,宗子美又與嫦娥相逢,嫦娥解釋說:“妾實姮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寇劫,所以絕君望耳。”《蕙芳》寫一個叫蕙芳的十六七歲、“光華照人”的美女,自愿找上門來,不聽馬母好心規勸,與賣面為生、家境貧寒的小商販馬二混結為夫妻。馬二混自從娶了新婦,不用再去賣面,而且“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過上了神仙般富足的生活。過了四五年,蕙芳忽然說:“我謫降人間十余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最后還對丈夫交代說:“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在這類小說的敘述中,天界的神仙被貶謫至人間,總有個期限,期限一到就得重回天界,留給人的只有深深的相思與懷念。
與此同時,在《聊齋志異》文本世界里,“情緣”“緣分”等觀念,揮之不去,增強了小說的傳奇性、凄美感。《聊齋志異》以悲為美,狐鬼情緣故事體現了這種創作追求。《聊齋自志》曰:“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清雍正年間南邨(高鳳翰)《〈聊齋志異〉遺稿·跋》之二指出:“聊齋少負艷才,牢落名場無所遇,胸填氣結,不得已為是書。余觀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 [17]31世間男女相親相愛的緣分是由很多巧合、很多陰差陽錯帶來的,是由很多突如其來、很多始料未及造成的。緣分盡了,即意味著二人由于某種原因要分開了,甚至再也無轉圜的余地;緣分未盡,即表明二人經歷了一系列考驗,最終得以團圓收場。
盡管在《聊齋志異》所敘“情緣”故事的情場上,癡男怨女始于神秘莫測之“緣”,終于被識破或遭泄密之“分”,結局讓人嘆惋,甚至給人以宿命感和神秘感,但這類小說卻能在志怪之中賦予以傳奇性,在悲歡離合的“緣分”敘事中傳達出凄美之感。在現實人生路上,“情緣”受挫或深陷困境的男男女女們常常像《紅樓夢》第二十八回所寫的寶玉那樣,發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一聲長嘆,追悔中充滿傷感。而在文學與美學的世界里,若無如此蕩氣回腸的“情緣”發生,怎會有審美化的傳奇敘事出現?
“情緣”首在“有情”,否則不能叫“情緣”。先有文心和詩心,然后才有故事,故事只是其文料。當然,《聊齋志異》“情緣”敘事還憑著敘述男子與狐或鬼共事的悲喜哀樂,力求踐行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等傳統中和審美詩道。《荷花三娘子》《蕙芳》《辛十四娘》《阿繡》《香玉》《葛巾》《羅剎海市》《書癡》《狐夢》《公孫九娘》《小翠》等一系列小說篇章,結局都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幸而當事人或早有預感,或選擇認命,面對生離死別,多能哀而不傷。
的確,就《聊齋志異》凄美的審美格調來說,小說秉持的是適度的中和之美。其傳奇性的“情緣”敘事已表明,這部小說中的“孤憤”并非是極端的憤怒。以往人們多看重這部小說的“憤”,看重其對社會現實嬉笑怒罵的批判性。事實上,《聊齋志異》在面向現實的敘事中雖然有諸如《夢狼》這種以“官虎吏狼”痛斥官場的成分,但總體而言,蒲松齡的精神風貌更似《罵鴨》中那位寬厚的失鴨老翁,即使是“罵”,大概也是處在盜鴨者“求罵”的情形下,不得已而為之。作者借助“情緣”敘事進一步消解了心頭憤憤不平的怒氣,也不斷地將心頭的怒火化作緣情的綺靡。
總而言之,《聊齋志異》是蒲松齡遵循“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緣情而綺靡”等詩作傳統創作的一部經典小說集,其中的“情緣”敘事不惑于以往志怪小說的神秘,不浮于時興艷情小說的表象,而常常寄寓某種人生質感、人生哲思,雖不乏宿命感、低沉感等復雜感受,但終以傳奇感、凄美感取勝。既映現出作者借此聊慰寂寞、沉醉夢幻等強烈心愿,又映現出作者借此寄托懷抱、夢幻難恃等微妙心境。
參考文獻:
[1]朱光潛.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M]//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路大荒.蒲松齡年譜[M].濟南:齊魯書社,1986.
[3]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徐欣萍.華人關系互動中的緣分運作及其心理適應歷程[J].本土心理學研究,2012,總(37).
[5]康健,李景艷.試析“眼緣”詞義變化及其流行用法[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1).
[6]劉旭光.作為惠愛的“審美”[J].社會科學輯刊,2020,(3).
[7][明]馮夢龍.情史[M]//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8][清]馮煦.蒿庵詞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梁令嫻.藝蘅館詞選[M]//[宋]辛棄疾,著;吳企明,校箋.辛棄疾詞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8.
[11]孫啟新.也談顧青霞[J].蒲松齡研究,2012,(1).
[12]方弘毅.從“穿插”到“互文”——《聊齋志異》對“以詩詞入小說”敘事傳統的開拓[J].江蘇
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20,(5).
[13][清]李慶辰.醉茶志怪[M].濟南:齊魯書社,2004.
[14][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批.脂硯齋評批紅樓夢[M].黃霖,校點.濟南:齊魯書社,1994.
[15]李海超.情緣論:情感本源的機緣化闡釋[J].當代儒學,第22輯.
[16][清]紀昀,著.閱微草堂筆記[M].韓希明,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17][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The Expression of “Orginating from Affection” and the Narration
of “Love Fate” in the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Li Guik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excellent novelists is often based on poetry,making their novel texts both poetic,historical,and philosophical.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an excellent novel written by Pu Songling,who is also a poet and lyricist. It not only originated in the poetic nature of “love and ornate” ,but is also known for narrating melancholic and lingering“love stories”. In such famous works asQing Feng,Fox Dream,Huan Niang,Lotus Three Women,Ge Jin,Xiao Cui and Xin Fourteen Women,Pu Songling wrote about the love between men and various fox ghosts represented by scholars. This kind of love often begins with“fate” and finally “foreordination”. At the time of origin,men and women meet,with the first sight or love at first sight,open a scene like the“love does not know the beginning,a deep” like the Peony Pavilion;at the end of fate,men and women often regret and disperse for some reason. This matter is like the end of a song and the separation of people,which is sad. All kinds of “love fate” narration in the author's works are the poetic projection of the figure and illusion of his own life,which not only projects the author's feelings about the human love and his own love,but also projects the life belief that“fate has ended but the love is still there”. The narrative of “love” in the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which is both emotional and legendary,mostly follows the creative poetry of“complaining but not angry” and “mourning but not hurting”,and takes the sad beauty as the aesthetic style.
Key words: emotional connection;fate;fatalism;legend;melancholic beauty;placing Trust
(責任編輯:朱" 峰)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05?21
①本文所引《聊齋志異》原文皆出自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①自宋代時就開始流行的諺語,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山谷上》曾記載:“諺云:情人眼里有西施。”在有情人眼里,對見到的女子怎么看都會像西施一樣美麗。
收稿日期:2024-05-30
作者簡介:李桂奎(1967- ),男,山東臨沂人。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文學與文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