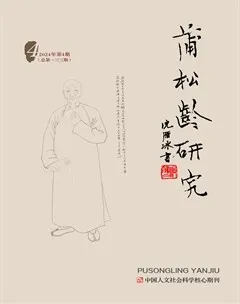心魔遁形與妖魅再現(xiàn)
摘要:網(wǎng)絡電影《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以聊齋小說《瞳人語》為取材緣由,又吸收了《畫皮》《聶小倩》等其他聊齋小說的敘事元素,把原著小說中緣起緣滅的個人心魔加以遁形化處理,改編成一個融浪漫與魔幻于一體、尋找男女真愛和人間正義的主題故事,敘事格局的擴張和異類形象的賦魅增加了它影像傳播的神秘感和陌生化,從而在游戲性、趣味性、奇觀性等美學特征上呼應了網(wǎng)絡青年們的審美接受趣味。因此,既置身于大眾傳媒和網(wǎng)絡傳播不斷興起的時代語境,又與傳統(tǒng)文化記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該影片需要進一步加強二者之間的深度融合,在傳統(tǒng)文化借鑒與故事情節(jié)模仿、類型話語整合與審美元素凸顯、古裝場景仿真與現(xiàn)實世界隱喻等方面均留下了可供深入探討的空間。
關鍵詞:聊齋小說;《瞳人語》:電影改編;心魔;妖魅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聊齋小說的電影改編在新世紀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更多的影像作品不再走院線發(fā)行與傳播的傳統(tǒng)渠道,而轉(zhuǎn)向了更為快捷多元的網(wǎng)絡空間傳播。多達幾十部的以《聊齋》為題材名目的網(wǎng)絡電影紛紛在各大視頻網(wǎng)站獲得首播,這種電影視頻的網(wǎng)絡發(fā)布與傳播現(xiàn)象,在2015年之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更為成熟便捷的時代大環(huán)境下,變得愈加凸顯和流行。聊齋題材電影的網(wǎng)絡輸送與審美接受改變了院線電影接受的時空條件限制,由于接受時間和空間的多元化,欣賞者在節(jié)約消費成本的同時,還容易在更短的時間內(nèi)獲得新近改編作品的審美風貌和文化信息,有助于促進與擴充聊齋小說的影像生成傳播;但這種新的傳播現(xiàn)象在帶來更為迅捷便利的大眾獲取優(yōu)勢的同時,也可能會因為視頻網(wǎng)站的把控不嚴、制作團體精品意識的淡薄和青年消費群體的淺思維慣性等問題,進一步拉低聊齋題材電影審美生成與傳播接受的文化品位。跟風從眾的故事套路與噱頭賣點的商業(yè)獵奇在消解聊齋原著的審美內(nèi)核的同時,也常常會在無個性的影像技術的粗鄙化生成中淡化對藝術創(chuàng)新的深度探索,導致著面向《聊齋志異》經(jīng)典的空洞化寄生。
出于對上述改編現(xiàn)象的審美考量,筆者試選取聊齋小說《瞳人語》的網(wǎng)絡電影改編為探討對象,進一步分析由北京漢人唐朝傳媒影視有限公司和陳氏影業(yè)(海口)有限公司聯(lián)合出品、邢帥執(zhí)導的網(wǎng)絡電影《聊齋志異之瞳人語》與原著小說之間的改編癥候。這部于2024年3月5日在視頻網(wǎng)站首次推出的影片因為更加靠近當下的網(wǎng)絡傳播與消費語境,不僅與原著小說的精神內(nèi)核相去甚遠,還與眾多的聊齋院線電影產(chǎn)生了鮮明的藝術區(qū)隔,因為自身具備了更多古裝通俗化的審美流行元素,所以在故事賦魅與傳統(tǒng)放逐、類型整合與元素凸顯、古裝仿真與現(xiàn)實隱喻等方面均留下了可供探討的話語裂隙。這種中間模糊地帶的審美建構(gòu)成為網(wǎng)絡時代聊齋小說影像生成的重要樣本,它在放大新時代大眾消費的精神面貌的同時,又指涉甚至固化了審美多樣化的虛假表象。因此,筆者以此為探討個案,從改編中的心魔遁形與妖魅再現(xiàn)角度切入,力求以點帶面,并適當擴充到聊齋小說網(wǎng)絡電影改編的整體面貌和發(fā)展趨勢,進一步深化對此類改編現(xiàn)象的審美觀照和規(guī)律認知。
一、心魔的緣起緣滅
在《聊齋志異》中,《瞳人語》并不是一篇特別出色的小說,它篇幅不長,故事結(jié)構(gòu)也相對簡單,把倫理教化放在傳奇故事中加以灌輸,在寓教于樂中實現(xiàn)道德規(guī)訓與人性整合的表達方式,與眾多聊齋小說的思想審美訴求比較一致。它的主人公方棟出場伊始就交代是一位人品有缺陷的男子——雖頗有才氣,但“面佻脫,不持儀節(jié),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 [1]15。方棟這種為人輕佻、貪戀美色的表現(xiàn)顯然是一種惡習,違背了儒家士人持重修身、德才兼?zhèn)涞奈幕瘋鹘y(tǒng)和建構(gòu)模式,當然在人格操守上要受到傳統(tǒng)士人的批判,因此但明倫就有了“無德,則才適以濟惡耳,何足貴” [1]15的評語。但由于在蒲松齡生活的年代,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已經(jīng)變得非常流行,用佛家戒語闡釋儒家失德之人的生命遭遇也變得更為可能,以心魔的緣起緣滅借喻方棟自我迷失、回歸的心智發(fā)展歷程就顯得順理成章,這種以參緣內(nèi)悟的自我反省方式而最終達成道德境界提升的人生歷練,融匯了自律與他律之間的雙向互滲,形成了以佛證儒的思路模式。
在《西游記》第十三回中,唐三藏在法門寺面對眾僧的詰問而回答:“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 [2]154聊齋小說《瞳人語》里的方棟雖為文化人,卻任由欲念滋生,在清明節(jié)郊外尾隨嬌艷女郎,心中種下了邪念,則招致了后面目疾的懲罰。面對眼睛上百藥醫(yī)治無效的惡疾,方棟試圖以堅持誦讀《光明經(jīng)》的方式來摒除邪念,加以懺悔,一年后萬念俱凈,產(chǎn)生了巨大的效果。因此他所有的困厄皆是心魔所擾,看到的美色其實是一種色障,而恰恰遮蔽了他的正念,貪戀美色的邪念成為他遭受報應的緣由,回歸斂念熄欲的初心,才是作家心心念之的正途,所以方棟在這次事件中自覺悔悟,即使一目重見光明,也悟到了人生的道理,“由是益自檢束,鄉(xiāng)中稱盛德焉” [1]16。蒲松齡在這里敘述的其實是一個浪子失德又回歸正途的故事,還告訴世人緣起緣滅、止色熄欲的人生道理,在修身與悟性的層面融合了儒釋兩家的生存理念。
當然,從現(xiàn)代的視角來看,方棟在小說中依靠誦經(jīng)最終治療目疾的行為是缺乏科學依據(jù)的,這種僅靠欲念流轉(zhuǎn)消解的故事處理方式不免打上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鮮明烙印,但是作為一種人生訓誡和隱喻,它還是與那個年代的人心和道德達成了雙向和解。如同《畫皮》里的王生見色起意、沉迷欲望而不聽勸阻、最終落得個被厲鬼剖腹挖心的凄慘結(jié)局,方棟因為追慕美色而目盲疾生,煩躁不已,同樣有著作家關于因果報的考量在內(nèi),即只有深植善果,遠離色欲,才能免遭囹圄之災;兩人的區(qū)別就在于貪慕之色在主動性與被動性上存在差異而已,王生所遇美女乃厲鬼化身,憑借其美麗的畫皮外表設局引誘王生上鉤,而方棟見到的美女主仆則出身高貴,正色拒絕品行不端的陌生男人的騷擾,為良家大方之人。她們是作者設定的身潔德正的理想女性,因此方舒巖對她們“車幔洞開,召人窺視,亦未免冶容誨淫” [1]17的批評顯然是非常狹隘的。兩篇小說中,蒲松齡強調(diào)的還是為人要心無雜念、遠離邪念,方能修身立德,否則任由心魔肆虐,就會遭受因果報應,沒有好下場。因此,人心正方能萬邪不侵,心善則容易福澤庇佑,這種關于做人道理的闡釋才是小說的真正主旨。
而在邢帥執(zhí)導的《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中,方棟釋放的心魔發(fā)生了由欲到愛的位移,并得到了及物性的回應。作為一名畫師,他精通才藝,很快與醉月樓彈琴的靈兒成為藝術上的知音;身邊還有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柳青青,方棟與柳青青之間因為深厚的感情基礎而獲得了愛的升華,最終結(jié)為夫妻,終得美滿結(jié)局;他面對靈兒始于貪戀其美色,而后轉(zhuǎn)為心靈相通,再到合力反抗黑山老妖結(jié)為戰(zhàn)斗伙伴,關系進一步親密化,但因為人、妖殊途而無法生死相依,只能黯然收場。這種一分一合的結(jié)局處理看似逃不脫聊齋小說妖界與人世難以深度共融的生存法則,但卻以對真情真愛的珍視與呵護放大了美好人性的存在視域。原著小說里方棟見色欲起的心魔在這部影片中被審美置換,這種負面形象的建構(gòu)被轉(zhuǎn)移到故事開頭遭受貓妖誘惑而喪生命亡的老男人張金貴身上,方棟心魔的遁形恰恰對應著制作者偏愛于惡自外來、正邪二元對立的捉妖打怪升級敘事,他從小說里的主動貪戀美色,清明節(jié)尾追主仆女子受到滋生目疾的懲罰,到影片里通過貓妖幻化的美女誘惑的外在考驗反而遇到了真愛,顯示出改編影片主題的游移。
在這部影片中,方棟與靈兒經(jīng)過音樂、繪畫等方面的才藝切磋,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惺惺相惜的知音般的美好感覺,他眼疾的發(fā)生更多源于心中的好奇所遭遇到妖力的外在侵襲。雖然靈兒警告他不要給自己的畫像點睛收筆,但是他還是抱著“美女怎么能有眼無珠”的念想加以補筆,結(jié)果在兩股黑煙入眼后目盲昏睡。小說中的兩個瞳人遷徙私語、進出眼眶的傳奇懲戒,也變?yōu)榱藶檎鎼鄹试缸晕覡奚牧嗲嗷硗始脑⒎綏澋难壑袀鬏敼饷鞯母腥斯适隆7綏澋男蜗笤谟捌懈啾徽苫幚恚谱髡咴跀⑹鰰r間上多次閃回到過去,帶有主觀懷舊的敘述視角展現(xiàn)他和柳青青之間兩小無猜的童年場景,這種溫馨情愛“前史”的改編豐富了原著小說的表現(xiàn)意蘊,再加上他與善良貓妖緣起情生的主線敘事,進一步向影像接受者強化了情愛話語強勢在場的鮮活印記。從心魔邪念的遁形到男女真愛的發(fā)生,這種審美改編的背后其實包含著一個移情的過程,通過批判單純的欲望來彰顯情愛話語也更加符合當前大眾文化消費的辯證法。在物質(zhì)豐盈的年代里,文藝作品對真愛的彰顯往往對應著社會人群中情感填充的迫切性,郝建認為隨著時代的推移,“愛情片不再是傳達某種社會批判的工具,它自身的趣味,某種純粹的形式和性愛的本能顯現(xiàn)就是它的意義” [3]53,因此《聊齋志異之瞳人語》選擇了在魔幻打斗敘事中謳歌真愛真情的主題模式,這種借古裝形式進行故事新編的審美包裝恰恰迎合了大眾文化消費渣滓泛涌的話語癥候。
大眾文化更多是一種輕飄飄的樂感文化,它從本能上拒絕板著面孔的高蹈說教和精英式的深度反思,也不愿意再繼續(xù)承擔傳統(tǒng)文化知識傳輸者的角色和功能。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正是不滿足于它的這種文化習性而對之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但這種“平易近人”的審美風貌反而在后工業(yè)消費中進一步膨脹開來,尤其在新世紀的網(wǎng)絡審美文化中如魚得水。小說《瞳人語》的電影改編,充分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文化被扁平化處理甚至消失的話語癥候。小說中方棟妄念緣起緣滅的自悟自省過程帶有蒲松齡借用佛家話語來證因證果的說教痕跡,但這一切都在改編影片里消失殆盡;影片里增加的伴隨方棟對抗黑山老妖的巫馬軒雖然是道士身份,但主要是起到了一個行動元的作用,其精神氣質(zhì)和文化內(nèi)涵更加接近于俠客,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道家或道教都相去甚遠。所以,當改編者更加傾向于展現(xiàn)一個去欲生情的通俗故事時,就容易放棄原著小說內(nèi)在的文化邏輯和審美氣韻,主人公方棟的心魔被位移到那些貪色身死的次要角色身上之后,其妄念遁形的省悟過程就容易被忽略不計。也就是說,原作中的正題被處理為影片中的次主題,而與次主題相對應的男女真愛則上升為影片改編的表現(xiàn)重點,所以關于傳統(tǒng)文化背景和底蘊的傳承并不是大眾審美改編的著眼點。
通過電影改編,方棟在小說中一個人起伏生發(fā)的“欲念”緣變?yōu)橛捌泻蛢蓚€女子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愛”緣,這種古裝人物掩蓋下的“濫情”主題也揭示了大眾文化消費無“情”不成局的通行法則。在一個全民都可以對情愛私人話語津津樂道的去私人化的網(wǎng)絡時代,《聊齋志異之瞳人語》通過一男二女的三角戀情所設置的故事,很容易成為博人眼球的文化消費泡沫,改編題材的扎堆和主題的同質(zhì)化,使得它既無法保留原作的傳統(tǒng)文化底色,也難以傳達出自己的審美個性。制作匆匆傳播也會匆匆,不久就會在暗潮涌動的網(wǎng)絡“海洋”中被沖刷遺忘,再也難尋蹤影。
二、敘事格局的擴張
我們再來看蒲松齡的《瞳人語》,會發(fā)現(xiàn)作家在敘事格局的設置上并沒有太大的“野心”。在小說中,貫穿全篇的主要人物是方棟,前半部分是他外視角里郊外遇艷受挫被罰醒悟的敘述,后半部分是他內(nèi)視角里對兩個小瞳人遷徙私語的主觀感知。雖然小說中也有方棟的妻子出現(xiàn),但她除了幫助方棟驗證小瞳人所講的珍珠蘭枯死的事實外,并沒有其他的情節(jié)功能,那種類似于《畫皮》里的家庭故事并沒有在該小說中展開敘述,貪色輕佻的方棟郊野覓歡的婚外冒險故事及其后續(xù)懲戒才是蒲松齡尋求道德教化的深層緣由。作家正襟危坐證因證果,在緣起緣滅的故事敘述中驅(qū)逐小說中人物的邪念貪欲,“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瞇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 [1]16,這種因果報應的設置也暗示了改過自新、回歸夫妻人倫的重要性。
與小說《畫皮》中的厲鬼顯形、挖心傷人的驚悚情節(jié)不同,影片中方棟野外偶遇的芙蓉城七郎之婦及其婢女乃正直之人,她們正色拒絕并呵斥方棟的行為比化身美女誘使王生入局的美色圈套要更為簡單明了,方棟遭受目疾的懲罰同樣比王生一步步誤入陷阱,最終遭遇剖腹挖心的過程變得更為迅捷。這種現(xiàn)世因果報的短小敘事反映了作家注重個人修為和道德勸誡的主題灌輸,即做人一定要心正,所有的婚外美色都不應在意念貪戀的范圍之中,必須非禮勿視,否則將遭受嚴厲的果報懲罰。因此作為方棟貪戀對象的芙蓉城七郎之妻婢二人更多的是欲望客體化的存在,是她們的匆匆一現(xiàn),驗證了方棟心性不正的個人品行,并隨著方棟的受罰而消失在后面的情節(jié)進程中。小說《瞳人語》的敘事之奇主要表現(xiàn)后半部分兩個瞳人寄生方棟眼中的過程,從敘事功能上來看,瞳人寄生其實也是方棟遭受懲罰的一部分,但作家在全知敘述視角中加入了方棟本人的主觀限制視角,通過他的感知來體驗一對異物活動的軌跡,由雙目迷障到一目能視來檢視自我,從而修身立德,回歸正途。這種關于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敘事過程緊扣著個人的自悟,雖然包含著獵奇的敘事環(huán)節(jié),其實并不復雜,它的敘事格局相對于其他聊齋名篇而言顯得相對局促,如果加以電影改編,則需要做更多的藝術考量。
顯然,該小說內(nèi)視角的限制敘事不容易被轉(zhuǎn)換到影像情節(jié)中。在電視劇《西游記》中,被吞入妖怪腹中的孫悟空可以繼續(xù)叫陣,甚至在妖怪的腹腔中穿行,作為一個與外界呼應的敘事環(huán)節(jié),這一切都可以在仿真的環(huán)境空間里加以主觀化表現(xiàn);而小說《瞳人語》中的瞳人在方棟眼中進出活動的情節(jié)則比較曲折悠長,他們與方棟之間的呼應較少,且通過影像模擬、建構(gòu)一個眼睛內(nèi)的主觀環(huán)境要更為艱難,就會像B超透視一樣讓接受者難以直視,也不容易傳達敘事意圖,因此在改編中需要加以簡化和外化,《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中外視角展現(xiàn)柳青青在方棟眼中的幻入幻出就屬于這種影像轉(zhuǎn)換中的藝術加工。從這個角度來看,內(nèi)視角的講述方式更加適用于文字敘述,而一旦到了影像敘事中,外視角的細節(jié)呈現(xiàn)和整體切入更加契合其媒介特征。所以小說《瞳人語》的電影改編需要擯棄長段落、小格局的內(nèi)視角敘事,而代之以大格局、正邪二元對立的全知視角敘事,方能滿足聊齋電影審美再生的改編需求。雖然屬于古裝電影的類型系列,但《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仍然是大眾文化背景下的藝術消費品,它寄生在網(wǎng)絡傳播的接受鏈條中,其鮮明的娛樂性和商業(yè)化色彩必然尋求著“被看”的制作預設,這既是它的生產(chǎn)初衷也是它的屬性“宿命”。“現(xiàn)代電影是有關‘看’的電影觀看者被敘述者以‘看中之看’電影手法引入所敘之事中,觀看者與所敘之事彼此交融,衍生意義” [4],從此種意義上來看,放大格局是《聊齋志異之瞳人語》意義增值的重要改編處理方式。
仔細考察《聊齋志異之瞳人語》的故事布局,不難發(fā)現(xiàn)它的取材靈感雖然來自聊齋小說《瞳人語》,但在異類形象的介入敘事上無疑又糅合了蒲松齡的另一篇小說《聶小倩》,甚至它的男女三角故事還存在著小說《畫皮》中家庭生活的變體。這種情節(jié)元素的多方引入和拉長無疑豐富了影片的敘事內(nèi)容,融傳奇、驚悚、情愛、喜劇等類型元素于一體,等于在原著小說的基礎上脫胎換骨,以新的故事面貌登臨不斷推陳出新的網(wǎng)絡平臺,力圖滿足觀賞者多方面的消費需求。因此,原著小說中方棟的邪念生成于自己的意念之中,需要在接受懲罰和自我懺悔中消除心魔,這是一個個人自省自新的過程,主要靠自我修正來完成心靈的蛻變,驅(qū)除作祟的欲念并不需要太大的故事世界;而在電影改編中,作祟的欲念由方棟的精神內(nèi)部移到了他的外部世界,作惡的黑山老妖暗藏著危害世人的欲念,操控靈兒和閔兒兩個貓妖化身美女吸食男人的精魄來增加自己的法力,與方棟、巫馬軒等正派人物形成了激烈的沖突。從個人自省中的改邪歸正到懲惡揚善中的兩派形象之間的二元爭斗,改編電影在敘述格局上必然有一個尋求擴張的變化趨勢,它的故事愈顯驚奇,情節(jié)也就變得更加曲折,在外部場景和形象細節(jié)的設計上契合了影像媒介的物質(zhì)仿真品格,形成一個首尾呼應、懸念迭出、環(huán)環(huán)相扣、多地輾轉(zhuǎn)的敘事場域,體現(xiàn)出改編者借多種聊齋文化元素包裝影像世界的敘事“野心”。
與小說《畫皮》中虛妄的人鬼戀情不同,《聊齋志異之瞳人語》顯然是借鑒了小說《聶小倩》中的人鬼真愛敘述,靈兒和閔兒不再是供姥姥驅(qū)使的冤鬼,而是轉(zhuǎn)為比原型更為可愛的貓妖,這種人與妖之間自然生發(fā)的跨界真愛以及相互救助的俠肝義膽顯然把關系復雜化了,它不僅替接受者驅(qū)除了因為鬼魂原型產(chǎn)生的恐懼意味,而且更容易在富有“在地”色彩的人、妖之戀中彰顯跨界情感緣起緣滅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這種敘事策略與陳嘉上的電影《畫皮》對人狐戀情的刻畫比較類似。方棟分別與青梅竹馬的柳青青、遭受控制而楚楚可憐的貓妖靈兒產(chǎn)生了真摯的愛情,但是這種復雜的三角關系并沒有像電影《畫皮》里的王生、佩蓉、小唯之間的關系那樣尖銳犀利,而是在自我奉獻和相互救助中變得溫情脈脈,雖然都沒有擺脫人與妖最終是不能在一起的生存法則,但小唯的退出是那樣的心有不甘并且驚心動魄,靈兒的回歸自然卻顯得一唱三絕,余音裊裊,既主動成全了方棟與青青,也留下了“此事古難全”的無盡惆悵。因此,在這部影片中,關于揚善與懲惡的情節(jié)敘事幾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二者之間形成了相互補充和對應的格局,其中的善,包括嚴父教子的溫馨親情、共同克敵的厚重友情,還有兩性相通的男女愛情。對于靈兒和閔兒來說,被脅迫的她們還有一個從惡到善的轉(zhuǎn)換過程,這樣一個強大的正義團隊雖然法力不強,但憑著向善認知的精誠合作,最終鏟除了以黑山老妖為首的邪惡勢力,讓世界重歸安寧祥和,這種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回歸平衡的情節(jié)生發(fā)過程顯示了改編者對原著小格局敘事的大膽突破。
在敘事場景的描繪上,該影片也突破了原著小說郊外和家中兩個僅有的故事地點,擴散到妖物害人的密林院落、紙馬紙人晃動的喪事鋪子、整潔寬敞的方家屋宅、人聲鼎沸的青樓妓館、陰森恐怖的黑山洞府等多個地方;讓多條故事線串聯(lián)起多處故事場景,并根據(jù)故事線交叉進展的需求,在故事場景的時間與光影、封閉與開放、仿真與幻化的展現(xiàn)上別具一格,把人物的活動軌跡和空間安排得條理清楚,符合了一個完整古裝故事的邏輯呈現(xiàn)和復雜講述方式,以較為恰切的故事體量為網(wǎng)絡大眾提供了審美消費的機會。這部影片里的不同的人物關系、相異的故事環(huán)節(jié)中的場景風格也會發(fā)生變化,或偏于陰森恐怖(兇宅慘案);或偏于日常搞笑(情侶吵鬧),還有的偏于激烈兇險(妖洞除兇)等等。這種設置的差異既產(chǎn)生了敘事節(jié)奏的變化,也帶來了故事風貌的多樣化。陳旭光認為:“網(wǎng)絡電影因其具有不同于銀幕電影的媒介性而產(chǎn)生了不同于銀幕電影的訊息,如游戲性、趣味性、奇觀性等美學特征與青年文化性等文化特性。” [5]《聊齋志異之瞳人語》的敘事布局在此種意義上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網(wǎng)絡電影的諸多審美特征,暗含著創(chuàng)編者多方取巧的制作預設和傳播考量。
三、形象與格調(diào)賦魅
毫無疑問,《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敘事布局的擴散改編中設置了一系列被審美賦魅的形象。出于改編接受的考量,它雖然取材于大家并不太熟悉的《瞳人語》,但還是充分發(fā)掘并巧妙利用“畫皮”系列、“倩女幽魂”系列等多個十分經(jīng)典且歷史較為悠久的IP(知識產(chǎn)權),在調(diào)動人們集體記憶的基礎上加以審美創(chuàng)新,力爭達到傳播與接受最大化的藝術效應。
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場景的氛圍建構(gòu)上,該影片堅持把日常化與陌生化相結(jié)合;既能夠讓觀眾感受到父子、主仆、義兄妹關系的倫理秩序的家庭溫暖,也可以在富有奇觀懸念的正邪二元對立中,調(diào)動接受者的審美注意力,滿足他們獵奇、窺私的觀賞欲望。一方面,方棟的家庭關系相對于原作變得復雜了。他由已婚變?yōu)槲椿椋≌f中他的妻子被青梅竹馬的義妹柳青青替換,進一步增加了情愛書寫的張力和版圖,又增添了他的父親和仆人等形象,從而讓方家的敘事進一步接續(xù)上傳統(tǒng)倫理的敘述根脈,以精心布置的家庭關系網(wǎng)絡和日常生活圖景增加了人物形象的“在地性”癥候;另一方面,氤氳不散的荒郊野外的兇宅傳說、不斷升級的懸念迭出的捉妖除怪故事,再加上神秘的小鎮(zhèn)死亡事件、棺材里的死尸、上下左右靈活跳起的貓妖、功力深厚的黑山老妖、能夠偽裝和變換身份的道士、方棟百毒不侵的體質(zhì)等等,共同構(gòu)成了另一個奇特詭譎的世界。這種在兩線交叉敘述中不斷凸顯現(xiàn)實仿真與超現(xiàn)實隱喻的兩個維度的做法,顯然于外在表現(xiàn)層面上比原著小說要寬廣得多。
由于借用了《畫皮》《聶小倩》等聊齋小說的傳統(tǒng)文化元素,《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異類形象的賦魅建構(gòu)上有所突破,不僅黑山老妖呈現(xiàn)出女性化的猙獰狠毒,靈兒和閔兒也不再是《聶小倩》中的鬼女原型,變?yōu)閶尚】蓯鄣呢堁齻儽拘陨屏迹诶涎破瓤刂浦鲁鰜砦澈蒙腥说木辏龅胶萌司腿菀赘钠煲讕茫蔀榭梢员徽群透脑斓漠愵愋蜗蟆堬φJ為:“在我國歷史上,關于鬼狐的傳說由來已久,影響非常廣泛深遠;蒲松齡的家鄉(xiāng)附近,丘壑縱橫,狐兔出沒,更有利于鬼狐故事的傳播,引起無限的遐想。” [6]15依托著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和更為熟悉的地緣優(yōu)勢,作家塑造了一系列鬼狐化身的女子形象,來舒緩自己心中的郁悶,在精心設置的理想世界中放飛和寄寓美好的人性,這種跨界書寫的形象賦魅方式也成為聊齋小說影像改編的重要生成路徑。《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中身份多變的異類形象為影片增色不少,在故事的開端,郊外宅院里假扮新娘誘惑好色男人的貓妖迅速進行人、獸面孔的真假切換,讓被誘惑者在先喜后驚中恐懼而死;后面的醉月樓情節(jié)中,貓妖又以色藝俱佳的美少女形象出現(xiàn)在鬧市,在與方棟的情感親近中瞳孔閃現(xiàn)并放射白光的神奇妖力;還有幻化為山野村夫的閔兒假裝送食偷襲方棟,一襲黑袍的老妖頻頻出現(xiàn)在凡世宅院和妖界洞府危害他人等等,這些面對科學理性昌明的新時代而憑借聲像音畫技術塑造出來的神秘形象有效地豐富了人們的審美想象力,為聊齋小說的影像傳播拓展了藝術的空間。
另外,《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賦魅建構(gòu)上還呈現(xiàn)為審美格調(diào)的神秘化。在敘事場域的拓展中,它較為準確地吸納了聊齋小說擬實空間與虛幻空間相結(jié)合的表達優(yōu)勢,又對原著小說的敘事空間進行改造與創(chuàng)新。“《聊齋志異》作品的開篇往往從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人物寫起,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和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都在人世間,大多數(shù)事件發(fā)生并完結(jié)于人物生活的現(xiàn)實世界” [7]112,在小說《瞳人語》中,方棟清明節(jié)外出的郊野和他的家中均為擬實空間,他因色犯戒的開端和悔過自新的結(jié)局都發(fā)生在擬實空間中,而目疾之后二瞳人寄居出入的敘事發(fā)生在一個虛幻的主觀世界里,成為方棟內(nèi)在感知并悔過醒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虛實之間的敘事結(jié)合使得該小說在日常生活與奇觀細節(jié)之間的描繪上達到了平衡,并增加了故事情節(jié)的曲折性。而在《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中,既有方家、醉月樓、郊外宅院這樣的擬實空間,也有黑山老妖的陰森洞府這樣的虛幻空間,但不管是在擬實空間還是在虛幻空間里,由于異類形象幻化人形神秘在場的緣故,都會借助光影、色彩、聲音等視聽元素的渲染而呈現(xiàn)出或朦朧幽深或玄虛縹緲的場景氛圍,如貓妖害人時的荒涼夜色、紅色婚服、恐懼變臉和凄慘聲響,醉月樓外的老妖,人未到但是聲音伴隨黑煙率先抵達的巨大威懾,黑山洞府內(nèi)伴隨著白骨森森、骷髏遍地的正邪雙方之間的激烈打斗,都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原著小說的表現(xiàn)視域。這種借用影像表達技巧為聊齋小說改編賦魅增色的方式已成為當代改編者的重要共識,該影片的這種藝術建構(gòu)借助于網(wǎng)絡平臺的影像傳播,不斷激發(fā)接受者的審美口味與欣賞興趣,未嘗不是一種較為恰切的制作策略。
相較于陳嘉上的《畫皮》和《畫壁》、葉偉信的《倩女幽魂》這樣的院線聊齋大片,《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異類形象和場景格調(diào)的賦魅建構(gòu)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過分看重于故事性的擴充改編,致使制作者受到資金、周期和技術等元素的制約,在影像細節(jié)上不可能像上述大片那樣做到美輪美奐。與之前出現(xiàn)的網(wǎng)絡微電影不同,《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之類網(wǎng)絡電影在放映時間等方面已經(jīng)具備了此類“大電影”的某些癥候,按照愛奇藝總裁李巖松對此類影片“投資在50萬元到3、4百萬元之間,時長超過60分鐘,沒有特別大的造景,制作、拍攝、周期相對也短,核心是故事” [8]的界定,它是比較符合這種認知范疇的。這些網(wǎng)絡電影的生產(chǎn)方往往通過在線接受和分賬的方式獲得收益,追求投資回收的快捷化和擴散性,觀賞者網(wǎng)絡平臺會員計費或刷單的單次投入通常要比院線電影購票要更加低廉實惠。這種文化商品的傳輸和流通路徑?jīng)Q定了網(wǎng)絡電影不會像院線大片那樣具有鮮明的精品意識,而只能是相對廉價的文化消費品,因此它們的文化藝術性會大打折扣。不難看出,《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敘事層面上鋪開了故事,把原著小說關于心魔打開與回收的因果自悟、內(nèi)在性較強的奇幻故事,改編為多線交織卻清晰流暢、易于觀賞接受的外在性故事,但在奇幻元素的審美呈現(xiàn)上又顯得缺乏雕琢和打磨,這種帶有偷工減料式的成品制作背后,有著網(wǎng)絡大電影體裁自身的多重因素的牽制。
《聊齋志異之瞳人語》不僅在形象歸屬的設計上,由小說《畫皮》《聶小倩》里的鬼文化范疇轉(zhuǎn)向了狐和貓文化范疇,其文化記憶所蘊含的恐懼情結(jié)有所下降;而且在魔幻元素的電腦特效運用上也不如陳嘉上、葉偉信的大片那樣精雕細琢,閔兒貓臉原型的暴露和老妖狐貍身段的展現(xiàn)都不是那么的驚悚恐怖,她們主要充當了故事情節(jié)中的形象元素,而自身在妖類原型的自足性裝扮上都不如周迅和劉亦菲扮演的角色那么張力十足和充實飽滿。制作經(jīng)費投入的限制和明星的缺席,使得網(wǎng)絡電影更愿意借助故事情節(jié)而不是演員的人氣來吸引傳播流量。之前大多聊齋電影慣常使用的“魔幻+電腦特技”的精細化、虛擬性的影像生成方式,因為投入成本過大而被后來的網(wǎng)絡電影所壓縮,這種高科技技術更新的緩慢和滯后也成為網(wǎng)絡電影軟硬件疲軟的重要癥候。在觀眾素質(zhì)逐漸提高的今天,網(wǎng)絡電影制作者仍需要自覺擁有精品意識,向高端品牌靠攏,不斷打造網(wǎng)絡影像敘事的高地。在審美引領而不是消費迎合上下功夫,從而促進網(wǎng)絡電影在生產(chǎn)質(zhì)量和傳播價值上都得以大幅度地提升。聊齋小說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增長點,且經(jīng)歷了較長的影像改編時期,積累了豐富的制作經(jīng)驗,成為多種媒介形態(tài)交互疊加和借鑒的重要IP。網(wǎng)絡電影同樣可以借助自身的文本特點和傳播優(yōu)勢,把聊齋文化元素加以影像轉(zhuǎn)換和審美創(chuàng)新,進一步促進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再現(xiàn)。《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形象與格調(diào)層面上所做出的種種賦魅化處理,則需要加以深刻的藝術反思。
司若和黃鶯認為:“網(wǎng)絡電影一方面延續(xù)了電影這一藝術形式對人類時間與空間觀念展示的特點,另一方面由于其置身于非線性邏輯的視頻平臺中,導致原本傳統(tǒng)的觀眾觀看行為轉(zhuǎn)變成用戶的觀看——使用行為,出現(xiàn)多場景、多線程和多故事線選擇的特點。” [9]對于《聊齋志異之瞳人語》這樣的聊齋題材類改編電影而言,雖然它們采用的是靈活快捷的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傳播,但是其傳播的語境和地域主要還是國內(nèi)或者華語文化圈,從愛奇藝、優(yōu)酷、騰訊等各大平臺的主要服務地區(qū)和影片自身的字幕語種的單一化設置可以鮮明地感受到這一點。顯然,這些聊齋題材的網(wǎng)絡電影在故事風格上更具草根化,在故事情節(jié)的游戲性和魔幻元素的奇觀化方面更加靠向青年文化人群的審美消費趣味,更具有網(wǎng)絡傳播的在地性;因此它們不像聊齋院線大片那樣承擔著傳統(tǒng)文化輸出的重任,需要在文化蘊含和字幕翻譯上做足功夫,不會因為負擔過重而顯得過分高冷,而只需要裝扮出一副“親民”的姿態(tài),獲得廣大青年網(wǎng)民的青睞即可。網(wǎng)絡電影的這種“如釋重負”既帶來了新時代的發(fā)展機遇,同時又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一方面,相對于國內(nèi)院線電影嚴格的多層級審查機制,網(wǎng)絡電影相對較低的準入機制確實為其爭取自由發(fā)展的空間帶來了機遇。另一方面,網(wǎng)絡電影的自我“減負”也容易失去院線大片的雍容純正的審美氣度和守正出新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在輕飄飄、滑膩膩的“失重”狀態(tài)下淪落為網(wǎng)絡空間瘋狂搞怪的影像垃圾和故事邊角料。
聊齋題材的網(wǎng)絡電影改編既需要承擔一定的傳統(tǒng)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責任,又要遵循其審美消費品的商業(yè)化生成法則,它不是類似于蒲松齡式的個人化創(chuàng)作,而是多工種團體合作的產(chǎn)物,所以應該把這類改編現(xiàn)象當作一個多方力量博弈協(xié)作的復雜系統(tǒng),過分地拘泥于原作和遠遠地偏離聊齋文化都是不可取的。改編者仍需要在激活人們傳統(tǒng)的集體無意識與深沉當代文化觀照之間做出平衡和考量,而放棄文化呈現(xiàn)的民族化特色而陷于追求獵奇的影像制作陷阱,正是當下許多此類電影呈現(xiàn)的癥候。“奇觀電影和其他后現(xiàn)代藝術一樣,往往缺乏時間性的歷史深度” [10]54,聊齋題材的網(wǎng)絡電影雖然和諸多的原著小說一樣在故事時間、發(fā)生年代的交代上往往語焉不詳,但不妨礙承載傳統(tǒng)文化和審美藝術的密碼,以富有歷史在地性的“擬古”影像敘事對接《聊齋志異》因緣際會、吐納古今的表現(xiàn)場域,這既能延續(xù)文化傳統(tǒng)的精髓,又能與當下世界的話語癥候發(fā)生對話。菲斯克認為:“文化商品的頻繁再生產(chǎn),不僅僅是文化工業(yè)的需求,也是大眾文化的力量使然。具體文本的貧乏性和對意義不斷流通的強調(diào),意味著大眾文化的標志在于其重復與聯(lián)系。” [11]152而置身于當代文化工業(yè)并作為特殊商品的聊齋題材的網(wǎng)絡電影,不應當隨波逐流,需要不斷注明其跨類與越界的身份標識,走出文本貧乏性的生成困境,為新世紀文藝的多元繁榮添磚加瓦,而《聊齋志異之瞳人語》在改編方面所取得的經(jīng)驗和教訓,可以給此類電影的生產(chǎn)者帶來更多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清]蒲松齡,著.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M].任篤行,輯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2][明]吳承恩,著.西游記[M].黃肅秋,注釋.李洪甫,校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3]郝建.類型電影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4]林黎勝.“視點鏡頭”電影敘事的立足點[J].電影藝術,1995,(2).
[5]陳旭光,張明浩.后疫情時代的網(wǎng)絡電影:影游融合與“想象力消費”新趨勢——以《倩女幽
魂:人間情》為個案[J].上海大學學報,2021,(3).
[6]張稔穰.《聊齋志異》藝術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
[7]尚繼武.《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
[8]于帆.網(wǎng)絡大電影:有商機?靠投機?[N].中國文化報,2016-2-22.
[9]司若,黃鶯.中國網(wǎng)絡電影發(fā)展脈絡與未來趨勢研究[J].電影藝術,2020,(4).
[10]劉偉斌.圖像的狂歡與幻境的超越:現(xiàn)代性理論視域中的視覺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8.
[11][美]菲斯克,著.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The Demon in the Heart and the Demonic Reappearance
——On the network Film Adaptation of the Liaozhai Novel “Tong Ren Yu”
Zhao Qingchao
(School of Humanism,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Jiangxi 343009,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 film“Liaozhai Zhiyi's Tong Ren Yu” is based on the Liaozhai novel“Tong Ren Yu”,and absorbed the narrative elements of other Liaozhai novels such as “Painted Skin” and “Nie Xiaoqian”. The original novel's origin and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s heart demon to be recluse treatment,and adapted into a melting of romance and magic to seeking true love of man and woman and justice on earth theme of the story. The expansion of the narrative pattern and the enchantment of otherworldly images have increased the sense of mystery and strangeness of its communication. Thus echoing the aesthetic acceptance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terms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layfulness,fun and spectacle. Therefore,be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mass media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as well a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memory,the film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leaving room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borrowing and storyline imitation,genre discourse integration and aesthetic element highlighting,ancient costume scene simulation and real world metaphor,and so on.
Key words: Liaozhai novels;“Tong Ren Yu”;film adaptation;heart demon;demonic
(責任編輯:陳麗華)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82?14
收稿日期:2024-04-01
基金項目:江西省文化藝術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電影改編研究”(編號:2019049WX02C)
作者簡介:趙慶超(1976- ),男,山東曹縣人。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學與影視藝術理論研究。